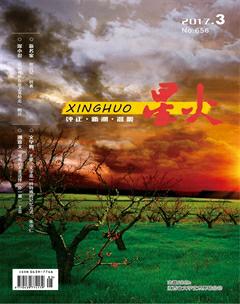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鲍贝,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学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青年作家深造班学员。有作品在《十月》《人民文学》《钟山》《作家》《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发表、转载。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著有长篇小说《观我生》《空花》《书房》《空阁楼》《独自缠绵》《你是我的人质》;中短篇小说集《松开》;随笔集《去西藏,声声慢》《去耐斯那》《悦读江南女》《穿着拖鞋去旅行》等。
1.
我把一大束勿忘我插进一只陶罐里,最近发现用这种质朴的陶罐插花很好看,比透明的玻璃花瓶更有质感,别有一番田园风味,尤其用来插这些粉紫色的小碎花。拧亮台灯,顺手把天棚上的顶灯熄灭,夜晚已睡意朦胧,不需要过于强烈的光亮。一壶老白茶刚刚煮好。花香、书香和茶的暖香交织浮动,若有若无。书桌上电脑开着,小说写了一半,故事里几个人物一直在脑海里晃荡,晃荡来晃荡去,晃出来千头万绪,却又毫无头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写。正绞尽脑汁思考,手机响了一下,是有人想加微信。
在请求通过的验证栏里写着:“你好,我是《观我生》的主人公。”
半夜居然还会有这种事发生?纳闷又好奇,摁下“接受”键,夜晚忽然变得有些诡异,甚至有些惊悚。
《观我生》是我在5年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被我写死了,死于自杀。可是,此时此刻,他却突然出现在微信中,仿佛阴魂不散、百转千回之后又找上门来——
“你好,是天葬把你的微信号给了我。”
“啊,你好,是吗?”这深更半夜的,真吓人,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泽郎。”
“泽郎,你好,我叫鲍贝。”
“我知道你,鲍贝,女作家,喜欢走世界。”
“你看过小说了?”
“还没有,是听天葬说的,他说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了,然后,你把它写成小说出书了。是吗?”
“是的。不过,小说里的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因此,小说中的你其实已不是你,你只是故事最初的一个原型。”
“原型?那还不就是写我吗。”
“应该这么说,是你的故事启发了我。”
“能否满足我一个请求?”
“请说。”
“可否寄本小说给我,签上你的名字,也签上我的,可以吗?”
“当然,当然可以!”
“太好了!我很好奇,想看看你是怎么写我的。”
“是这样,泽郎,由于小说情节的推动,最后把你给写死了,不,不,我是说,把小说里的那个你给写死了,不是现实中的你,请你千万别对号入座。小说都是虚构的。”
“没事没事,人最后总要死的嘛,谁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垂不朽?”他在这句话的后面特意加上了一个笑脸符号,表示他根本不介意我在最后是把他给写死了,还是写活了。他只是对内容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也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就如5年前的那个冬天,也是因为好奇,我才会写下这个故事。想起来,五年前的那场旅行,也是阴差阳错,我经过拉萨,到尼泊尔,最后到达不丹。途中遇到天葬涅磐,“天葬涅磐”是微信网名,泽郎可能打不出涅磐两个字,或者嫌麻烦,直接就省略成“天葬”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天葬涅磐的真名应该叫利嘉则仁,是个读过很多书的藏族小伙,在北京工作。知道我经常行走西藏,便自然而然地跟我讲起他朋友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之前,他的朋友是个喇嘛——
“喇嘛是在25岁的时候,遇到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北京女孩。两人相遇并相爱了。这两个人,一个是从小在寺庙里修行的喇嘛,一个是来自北京城的开放女子,他们把人世间最无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不管世俗的眼光,也不管佛门的戒律,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刻骨铭心、爱得诚惶诚恐、爱得天崩地裂,爱到背叛宗教最后连信仰都变了。最后,喇嘛为了爱情还了俗,彻底离开佛门净地,跟着女孩到了北京。他从一个佛世界,迅速坠入俗世间的过程惊心动魄。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适应都市生活,除了念经,什么都不会。面对喧嚣的高科技发展中的现代生活,他几乎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步入红尘的他,就是个一无所知的废物。爱情毕竟不能当饭吃。女孩很快就把他给甩了。在北京,喇嘛一个人举目无亲,被抛弃在茫茫人海里……”
这就是天葬涅磐对我讲述的全部内容,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细节和更多的场景,当时连他朋友的名字都是隐去的。
雖然,我对这个喇嘛的爱情充满好奇,但真正让我震撼并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的原因,并非那场爱情。爱情没什么好说的。爱情只是一场致幻。就如梦境。作为一个喇嘛,一个虔诚的佛教圣徒,为一场爱情放弃修行,成了宗教的背叛者,成为一个现世罪人,最终又被爱情抛弃……当然,我并不想对此作出任何是非对错的评价,更无意于谈论宗教。真正击中我的是这个毫无生活能力的喇嘛,连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失去之后,他将如何获得重生?又靠什么来支撑他顽强地活下去?
想到那个喇嘛是否能够劫后重生,又该如何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个世界时,我的内心充满荒凉和苍茫。可以这么说,他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毫无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与这个现实世界毫无关系,恰恰就是与这个现实世界最有魅力的一种关系——至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通过他,我看见孤独、纯真、挣扎、欲望、荒凉、悲绝、坚强、冷酷、成长、轮回、迷失、救赎和自我救赎等,这些原本沉寂在生命中的许多词汇,开始在我心里交织浮动,并被某种遥远而神秘的声音唤醒。一个生下来就被送进佛门去修行的生命,他本不应该存在于这个兵荒马乱的现实世界中。然而,命运却偏偏将他抛置于此。就像进行一场穿越幽暗森林的孤独的冒险。而对于我来说,要鼓起勇气去写这部小说,也像是进行一场穿越幽暗森林的冒险。虽然我并不了解他的生活状态,更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仍然抗拒不了去尝试书写此种冒险所赋予我的隐秘的快乐与冲动。
从不丹回来之后,我便以这个故事为原型,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观我生》,201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以精装本形式再版。2016年,我又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带我去天堂》,发表在《星火》第四期。
为了书写方便,我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北京换成了杭州,杭州是我居住的城市,写起来比较顺手。至于安排主人公从拉萨出发,途经尼泊尔,最后到达不丹虎穴寺去跳崖自杀所选的这条路线,正是我在旅行中走过的那条路。因此,书中所提到的路线和地名几乎都是真实的。每一条路,每一家酒店、餐馆和咖啡馆的名字也都真实可寻。有个姐妹带着我的书去尼泊尔,按照书中所提供的路线,很顺利地找到了我曾经去过的某家咖啡馆,并在咖啡馆里连同我的书拍了张照片发在微信上。当然,也会有路线属实而店名虚构的部分。比如在杭州的某位朋友看完小说之后,居然根据小说里描摹的地址,去西湖边找那家虚构的“梅茶馆”,绕来绕去,却怎么也找不到。
这就是写小说的好玩之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回到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这个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微信里的泽郎,神秘又诡异,仿佛从天而降。他无缘无故的出现让我想起里尔克在《严重时刻》里所状描的几句诗: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这个“无缘无故在世上走”的人,是他,也是我,或者,也是所有人。要不是我在5年前“无缘无故”走到不丹去听来这个故事,并把它写出来,这个叫泽郎的人,此刻就不会“无缘无故”地走向我。如果仅仅是来索要一本书,那倒没什么,可是,我总有点担心,会不会发生些别的什么事儿?
怎么说呢,小说的主人公是他,但也不是他。小说里所有状描的细节和经历,都和现在的泽郎毫无关系,都是经过虚构想象出来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小说的源头却是因他和他的故事而起。
生活总会有惊奇和意外突然而至。直到现在,我仍然会孩子气地觉得生活总在前面,就在前面的某处准备给我一个惊奇或者某件意外的事。而生活确实也常常如此。就如这个夜晚,泽郎的出现就是一份惊奇。
然而惊奇并非惊喜,倒有点让我心生不安和惶然。为什么不安,却又说不清楚。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好事。也许是我过于敏感?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我向泽郎再次解释:
“小说都是虚构的,务必请你不要对号入座。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两者之間千万不可混淆在一起。”
“明白明白,我明白的……”感觉得出来,泽郎已经很不耐烦。我也觉得自己强调得有点过了,不就是一个虚构的小说嘛,又不是纪实,谁会介意你最后是把主人公给写死了还是写活了。我不再解释,岔开话题——
“明天寄你书,地址?”
“四川红原金珠小区。”
“没房号,能收到?”
“能。地方小。”
对话至此,差不多就该结束了。我随手记下这个地址,心中仍有好奇。我到过藏区很多地方,却并不知道有个地方叫红原。应该是座县城,也不知道他在红原县干什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于是又忍不住问他:
“你家住红原?还是在那儿工作?”
“我开了个小酒吧,在红原。”
“不错,有机会去你酒吧坐坐。”
“非常欢迎!你到红原县,找泽郎酒吧,随便找个人问下就知道,就在红原路上。小地方,好找,到时候,让我陪你喝一杯!”
“好,庆祝你重生。”我安静地打着字,心里却有点懵,盯着手机屏幕好一会。从喇嘛到酒吧老板的身份切换,似乎有点戏剧化,很魔幻,我需要稍稍调整和消化一会。
“你在哪儿?”他问我。
“杭州。”
“哦,没去过。”
“有空过来玩。”
“非常感谢,有机会去。”他又在句子后面加了个笑脸符号。紧跟着又发过来一句:
“我还有很多故事,你都可以写,有机会我讲给你听。”
“你们都是传奇。”我也发过去一个笑脸。
“不传奇,但调皮。”
他说的“调皮”,应该是指“有趣”,或者“有点意思”的意思。想起来他在寺院里当喇嘛的时候说的都是藏语,汉语应该是他去北京之后才开始学的。
“你的汉语不错。”
“不行。还要学习。”
“已经很好了!”
“要是有你一样的才华,我也会把自己的故事都写出来,分享给大家看。”
“你的文字表达已没有任何问题。”
“谢谢,是很大的鼓励。”
这样的对话,因其简略而妙趣横生。就像一个外国人在说汉语,有点生硬,但酷酷的。
由于我们身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和他原先奇特的身份和经历,使得他在我心里始终有点神秘而遥远的感觉。而此刻,我们相隔着遥远的时空,居然通过微信在你一句我一句地发生着对话,这种感觉真的很虚幻。
已过零点。铁壶里的水又烧开了,不断发出扑哧扑哧沸腾的声音。我关掉烧水键,电源指示灯灭掉之后,水开的声音才慢慢变弱。
泽郎又发过来一句:“来了几位朋友,我要去陪他们喝酒了。”
“好。”
“真希望你也能过来,就坐在我的小酒吧里,一起喝酒说话,多好!”
“下次一定去。回头再聊。”
“好,再聊。”
放下手机,不再看微信。茶已淡至无味,夜静了下来。我又回到自己。想着是应该换茶呢,还是干脆泡杯咖啡。我的夜晚从零点开始,得为自己提提神,开始写新小说。
我为自己泡了一大杯卡莎咖啡,此种咖啡绵密浓郁,强度指数12,有着非凡的烈性和强劲,犹如酒中白烧,味道醇厚辛辣。每次只要喝上一杯,便可清醒至天亮,大脑几乎能够整夜保持在活跃状态。最近写小说的这些夜晚,对自己有点狠。可以这么说,在深夜里喝大杯浓咖啡,是一个女人用来自毁自残的最佳配方,也是能够让我保持最好写作状态的良药。
2.
书寄出后,我便把泽郎这个人抛至脑后。本来就素昧平生,那夜从天而降在微信中现身之后,我仍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完全形同虚构。就如我每次呕心沥血地写完一部小说,就彻底摆脱了那个故事。我创作的激情和兴奋点永远都只停留在书写期间或还未完成的下一部。对于已经付印流入市场的小说,几乎都不愿意去重读,那会让我疲惫。
然而写作经年,虚构的人物无数,连自己都数不清,也记不清了,还从未碰到过小说中的主人公哪天突然找上门来的。
唯独泽郎。泽郎是个意外。这个意外,原本以为在那个深夜找上门来相互牵扯一通便也罢了。给他寄书,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貌。如若不寄,也不会有多大关系。他若出于好奇,非要看这本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通过天葬涅磐,或者,直接去书店购买一本即可。
但是,恰恰是我寄给了他书。通过寄书,又加了微信,一个写作者和书中主人公的友谊便微妙而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平时通过微信的联系便成了彼此之间的家常便饭。
有个深夜,他又突然发信来——
“你好!”
“你好。”
“在写小说?”
“没有。”
“那你在干什么?”
“看书。”
“什么书?
…………
我无语。心里有些抵触,很反感这种对话,尤其在两个并不熟知的人之间。难道我还需要去告诉对方我正在看什么书、做什么事?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他一定是在百无聊赖中随便想找个人来闲扯解闷。我可不愿意去配合他的无聊。
我没回复,接着看书。还没看几行,又有一条新的微信:
“我在看你的书,《观我生》,看到第二章了。此刻我正在尼泊尔。”
我不得不作出回应:“你去尼泊尔了?”
话一问出,便知中计。小说总共就四章,按地名进行分块:第一章:拉萨;第二章:尼泊尔;第三章:不丹;第四章:杭州。他说他看到第二章,也就是说主人公已经到了尼泊尔。看来,他是铁定把自己当成那个主人公了。
“是”,他果断回复,“我在尼泊尔,你也在,我们在一起,此刻我俩就在那个旅馆房间里。我在房间躺着休息,而你在浴室里洗澡,洗完澡你是穿着白色睡裙走出来的,我知道你还有蓝色的和红色的睡裙,你写睡裙那段文字太美、太性感,我想你穿上它们也一定很美、很性感……但是,你怎么就把我写睡着了?我怎么会睡着呢!我想,这种时刻男人一般都不会睡着的,反正,我是绝对不会睡着的。”
天哪!我的手指划过这些文字,身上一阵鸡皮疙瘩。我必须纠正他这么臆想下去。
“那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你并不是现实中的你,我也并非现实中的我,那都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不过用了第一人称来写。”
“知道是你虚构的。我在你书里有两个名字,一个叫贡布,另一个叫Frank,两个名字我都喜欢。你在书里的名字是古若梅,很有意思。这些,你都不用多解释,我都知道的。”
我无语,说不清楚了,不想再回复。把手机扔开,合上看了一半的书本,离开书桌。
身后的书架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小说书籍,古代的、现代的,国外的、国内的,还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小说,我的目光停留在《观我生》这本书上,然后,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翻开。翻到第二章:尼泊尔。
很快,便找到了泽郎说的那段关于睡裙的文字:
梦里的那条蓝色长裙,随着梦的消逝而消失了。我的箱子里,根本没有一条深蓝色连衣裙。昨晚冲完澡睡觉,套在身上的是一条白色睡裙。是柔软的棉布料子,长袖,圆领,极保守的一种款式。要不是它的过于宽松和镶在领口的那圈蕾丝白色小花边,让它看上去像条睡裙,完全可以当成普通的连衣裙穿出去。除了这条白色睡裙,我还带着一条红色丝绸睡裙,是法国一位内衣设计师最得意的作品。优雅、慵懒,性感和激情,是它的象征。那位设计师的理念是:满足所有对美好事物有着疯狂迷恋的女性。
我好像并未疯狂迷恋过任何事物。这个世界在我眼里总是淡的、冷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本能地拒绝过于浓烈的事物和情感。而这条红色的丝绸睡裙,我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内衣店里突然邂逅到它。我承认,在那个瞬间,它像一团火一样将我迅速点燃。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出于一种女人的天性。我模糊地相信着,在未来遥远的某个时刻,穿它在身上,是必须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几乎每一次的旅行,我都要带着它。把它压在所有衣物的最下面,塞在箱子里最隐秘的地方。可是,我从没有在旅途中穿过它。一次都没有。从买下它至今,我只试穿过一次,就是在巴黎那家内衣店的更衣室里。我站在落地镜子前,褪去所有现实中的服饰,换上这条睡裙。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轻薄华丽的丝绸紧贴着我的身体。我看见镜子里的那个自己,竟然如此轻盈性感,有着迷人的欲遮还休的风情。记得那天,我一个人,揣着那件红睡裙走回去的路上,一直深陷于一种自陶醉般的满足和莫名的忧伤中。我经过凯旋门,经过巴黎铁塔。风吹乱我的长发,拂过我的脸庞,轻柔而温暖,犹如一双饱经沧桑却又充满爱情的手……
重读5年前写下的这些文字,并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当时写下这部小说,也属正常。但谁又能想到,会引来泽郎这么个不折不扣一根筋搭牢硬把自己当成主人公、并把小说中所有细节都往自己身上去套的神经病?真是件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儿。
他现在才看到第二章,要是看到第三章的不丹,和第四章杭州那段,里面有大量关于男女主人公的性描写片段,那还了得?!
还有,他最后是被我写死掉的人,他果真不会介意吗?要是他介意,然后不屈不挠地来找我算账……想到这儿,我都心惊胆颤了!
忽然问自己,小说家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每天吃饱了撑着似地捕风捉影,抓住一个偶尔进入内心的故事片断或一个被感动的瞬间,便开始进行虚构、杜撰,编造故事,写出一种叫小说的东西供人消遣。在编排故事的时候为所欲为、痛快淋漓,敲打键盘的手就像上帝的手,极权在握、呼风唤雨,可以任意又任性地安排小说中的人物谁可以继续活下去,谁好去死了……好吧,此刻遭报应了!被我写疯写到失魂落魄直至写死去的人,现在附了魂魄返回人间来找我了。
泽郎就是个阴魂不散的人。我已经被他搞得有点阴郁了。重新坐回书桌旁,手机在桌上响了好几遍,微信提示:“您有5條未读信息。”
不用看,我也知道是泽郎。深更半夜的,除了他,还会有谁?我决定不回复。但还是好奇,打开微信,去看他发的内容:
“有一个地方特别佩服你,我们没见过面,你居然知道我脖子上戴一条绿松石项链,还知道这是我的护身符。嘿,它真是我的护身符。以前修行时戴着,还俗后也戴,此刻我还戴着它呢。”
“你想不想看看这条绿松石,是否就是你想像中的那条?我可以拍一张发你。”
“对了,你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吗?如果你想看,我手机里就有照片,过去的和现在的都有存着。”
“小说里好像一直没有描写我外貌特征的文字,都不知道你想像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你想像中的我帅吗?是否很高大威猛?嘿嘿,女人一般都喜欢又帅又高大的男人。”
“你在吗?那我先看书了,你忙完回复我。”
“嘿,你在吗?”
…………
你在吗?
你是谁?
我又是谁?
他问的那个“你”,到底是现实中的我,还是小说中的我?我有点崩溃。此刻的我,明明坐在自己最熟悉的书房,却无端端地感觉自己像是坐在虚构的小说世界里。
不,比小说更像小说。
“在。”
手指一动,我又回复他了。
大多数读者包括我看别人写的小说,都会去想像小说中的人物大概长什么模样。我闭上眼睛,想象我看过的作品中以及我自己写下的每一个人物,他们蜂拥而至,面目清晰,却又模糊不清,我仿佛看见他们,却又不能够说出他们。
比如,以泽郎为原型写的《观我生》里的主人公贡布,他在我为期一年的写作时间里,几乎与我朝夕相伴,很多时候我的文字描写完全是被他推着走,而不是受我所控。另外小说中的“我”,也有着与我本人相暗合的性情,他们的一举一动、音容笑貌与神情在我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但我仍然无法具体到画像一样地去画出他们。虽然在长期的写作中,小说家所做的事情就是为想象中的人物画像,这里的人物包括想象中的他人和想象中的自己。但需要用想象去描摹出来的却是逼近人物内心与灵魂的文字,而不是外部相貌。
有个朋友在看完第三遍《观我生》之后,找我喝咖啡。我们俩坐在西湖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窗外是传说中的断桥,细雨纷飞,梧桐叶到处飘,天空阴沉灰暗,其实多半是霾让天空变灰变暗,而非雨雾。我们喝着咖啡,聊着小说里的人物,有点雾里看花,就像看着窗外的烟雨西湖。
我不说还好,说来说去把她想象中的人物说到变了形,她有点受不了。她说她想象中的那个人,可不是这样的!但到底是怎样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被好奇心缠绕,知道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非要看原型本人的照片。
还有个在拉萨的朋友叫小雅,她看完这个小说,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推荐给她身边的另一个朋友立言看。立言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也睡不着。某个晚上,她抱着书找到小雅。说是还书,其实是想聚在一起说说小说里的那个主人公。那个叫贡布的喇嘛,使得她们坐立不安,彻夜恐惧,她们是被吓着了。
那晚她俩挤在一张床上睡,越聊越恐怖,就给我发微信,问我真的有这样的喇嘛吗?他所有的经历都是真的吗?
小雅和立言,她们身居拉萨,天天会在大街上碰到喇嘛。现在的她们都不敢多看他们,说是对这种身穿僧袍的喇嘛都有心理阴影了。我是可以理解她们的。她们年轻单纯,又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尤其在圣城,喇嘛差不多就是神和信仰的化身。可是,我在小说里却把她们以往对喇嘛的这种身份认知完全给颠覆了。
我只有努力劝慰她们:“小说是虚构的,别当真。”
她们回复我:“虚构又不是撒谎,它只是你们小说家用来表达经验和重构世界的工具。”
我无言以对。她们比我深刻。
在这个深夜,我也像一个被好奇心驱使的读者,突然就想知道被我虚构的那个人,他到底长啥样?
微信一直没有动静。我想泽郎可能睡着了,或者看书看入了迷,忘了还有微信这件事。
夜晚又开始进入零点,每次在这个临界时刻,我又要开始纠结,喝茶呢还是喝咖啡?
还是为自己选了咖啡。咖啡散发出来的浓香让整个书房都弥漫着温暖的气息,而我置身其中。全世界安静下来,思绪开始纷飞,某些细节在我眼前舞动、活跃、纷至沓来。
我在写一个关于鱼的故事。我发现在写这条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写人,写我自己。描摹鱼的委屈、愤怒、无奈和爱恨情仇,也都是我们人的情感。鱼生活在海洋里,在我肉眼看不到和我经验够不着的地方,我允许自己用想象的翅膀飞起来,用文字进入虚构。
咖啡续了又续。这是一个“人鱼合一”的夜晚,我一直写,一直写,直至凌晨天光渐亮,世界正从沉睡中清醒过来,而我却脑门发热头部注满了铅似的从激情澎湃的虚构世界中抽身而退,就如结束一场爱情长跑之后的虚脱,满身疲惫而凌乱。收拾自己的最好办法,是立刻上床睡觉。
手机一直处于静音,后半夜开始就没碰过它一下。准备睡觉之前,又习惯性地看了下屏幕。不看没事,一看吓我一跳。
阴魂不散的泽郎,居然也没睡。他看书看到天亮,微信发到天亮。这些微信有的间隔几分钟,有的间隔半小时,最后一条发送时间是在两分钟之前:
“我失眠了。整夜睡不着。我已看完第三章。此刻我在不丹。你也在。你和我共处一室的情节看得我心惊肉跳,紧张得汗都流出来了!我现在浑身发热,喘不过气来。我们一路上居然发生那么多事情,仿佛都是我在亲历亲为。我知道所有情节都是你虚构的,但对我来说,这些经历比我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真实,它们让我着魔,也让我着迷。”
他看个虚构的小说就这般心惊肉跳、又紧张又窒息。此刻的我却是在现实生活中要去面对这么个大活宝,我才心惊肉跳、又紧张又窒息呢!睡意全被他赶跑了。身体疲软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脑海里却在万马奔腾、思潮翻涌。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再看他之前发的几条信息,更是被他搅得心神不寧、尴尬至死。
“原来两个人的性爱可以这么美妙,美到极致,就如佛光普照,灵魂升入天堂。”
“在你的小说中,我居然还有个还俗之前的名字叫哈姆,现在我有三个名字了,贡布、Frank,哈姆,好幸福。可是,你后来写的这一段话,让我好难过:
……我就在他身边。我们那么近,我们又那么远。身体紧密地粘合在一起,而灵魂却早已飞越千山万水。我们只不过借彼此的身体,将自己点燃,然后各自表述,各自过错成。身体完成了我们的爱恋与欲望。他爱的人不是我,我爱着的那个人,至今下落不明,但绝对不会是Frank,不会是贡布,更不会是哈姆。
我们都无力推开命运的流离失所和生离死别。既然如此,那么,一晌贪欢又有什么不对?它至少还证明我们与这个世界与我们的此刻,还是粘连的,仍有着丝丝缕缕的牵引。我们从未孤绝。
当然,这也不过是狡辩,为这件不应该发生却已然发生的事情找个理由。但,我要拿這个理由何用?是为将来回忆的时候,有个托词吗?……
你的意思是,我们虽然做爱了,但其实并不相爱,对吗?”
“如果世上真有这么美的爱情,这么美的性,这么美的女人,我真的愿意为她去死。”
“我翻看了你发在朋友圈的所有微信,里面有好多你的照片,每一张我都喜欢。照片上的你和小说里的你,在我心里是吻合的。”
“你写我们在床上的那几段,好疯狂,我反复读、反复品。这些文字让我晕眩,心跳加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很神奇。”
“嗨!你终于穿上了那条红睡裙,是穿给我看的!不信你自己看,在137页最后。”
…………
崩溃,这也太像小说了!比我虚构的小说还要离奇一万倍。我开始有点后悔寄书给他。如果他是在书店或别处买到书,至少不会直接找我抒情,他独自去想象、去意淫、去天马行空……都跟我没关系。可现在这个局面,让我很是尴尬,不知该如何收场。他抱着小说意淫了一个通宵,我想他一定被纷纷而至的情欲给点燃,并被烧得通体发热。让他自行冷却去,再懒得去做扑火工作。
我决定不回复。
关机睡觉前,还是没忍住好奇心,翻开书本第137页。事隔5年,我都忘了在不丹那个章节里,我还虚构过一条红睡裙。
我终于在这个夜晚,穿上了这条红睡裙,轻薄华丽的丝绸紧贴着我的身体。它与这个浓烈的充满爱情的夜晚如此吻合,我的身心变得无比轻盈。我想让今晚的这个男人,看见我穿上红睡裙的模样。今晚,我是他的新娘。
……忽然酥油灯落了地,光亮瞬间消失。他控制不住地抱起我,凶猛的吻,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红睡裙上。我的身体被贡布使劲压着。他有一股蛮横的劲道,似乎欲将我碾成粉碎。我有些眩晕,想放弃一切追问,就这样死于宿醉……
赶紧打住。看不下去了。如果这些激情描写的文字都要拿来往自己身上套,整本书里应该还有更多热血沸腾的段落……那,这个叫泽郎的男人他还想活不想活?
不管他了。睡觉。但愿梦里风轻云淡,安然无事。
3.
事实上在梦里也不得安宁。醒来时,梦已飘忽得不知所终。依稀还能够记得有人送来一束鲜花,我却始终看不清他的真面目。我并不知道,他来时是坐车还是步行,去时却见他骑上马绝尘而去,只记住了他的背影,当然,对于那个背影的记忆也是极其模糊的,还得靠想象去作些填充。
这是一件很让我困惑的事情。我好像从没做过这样的梦。我是在天蒙蒙亮时睡下去的,下午三点醒来,也就是说,这个梦整整做了一个白天。白天做的梦,被称之为“白日梦”。据说白日梦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做了也白做。
起床,刷牙洗脸梳头下楼到厨房里去找吃的。下楼梯的时候感觉自己像在飘。睡裙太长,裙摆拖在楼梯地板上酥软无力,我的两条腿和整个人的骨架也是酥软无力的,像是另一种疲累。
咖啡在咖啡机上煮着,面包在烤面包机上烤着,牛奶最快,倒进杯子里微波炉转上一分钟就好,但我的胃拒绝空腹喝牛奶,只好耐心等着烤面包。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吃得更简单的人了。一个人在家,不管中饭还是晚餐,几乎顿顿都跟早餐一样解决,简单、方便、快速完成。
吃完面包喝完牛奶,咖啡也煮好了。我端着咖啡杯去阳台呼吸新鲜空气,花园里鸟语花香,可惜不见蓝天白云。下午三四点的阳光过早地显出它的软弱无力,霾占领了整个天空,阳光仿佛虚晃一下便遁形而去。眼前尽是灰黯。白天又快接近尾声。不过也没关系,再过两小时,灯光便可以亮起来。对于把自己关起门来写作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灯光和电脑。阳光和外面的世界暂时跟我不发生任何关系。
喝完咖啡,回到书房,回到我的电脑前,准备接着写昨天未写完的故事。书桌边上有个炉子,铁壶里的水烧起来,很快就可以泡上自己喜欢的茶。
当我喝上第一口茶的时候,心会安静下来,写作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
这一天,原本是个极平常又正常的日子,直至我手机里的微信出现新的信息。真是万恶的微信啊,让我现在想起,依然心有余悸。是谁在这个世上发明了手机又创造了微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得安生。
发过来的先是一张图片,点开,吓得我,差点惊叫失声!
一个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喇嘛笔挺挺地躺在板床上,赤脚,光头,身体是横着的,照片上只看得清半边脸部,眼睛和嘴唇全都紧闭着……那是一个死去的人,不,是一具尸体!
难道这人就是泽郎?泽郎死了?死了的泽郎又通过自己的微信发给我他自己死去的照片?
手机躺在左手心,右手指僵在手机上方,仿佛我的双手就抱着那个人,或者那具尸体。我的心怦怦直跳,既恐惧又惊疑,怔懵了好一会。
新的微信又进来:
“别害怕!那个不是我。”
“请你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你这是恶作剧!”我狠狠回复。
“对不起,但从宗教意义上说,生死轮回也没什么好怕的。”
“别跟我谈什么宗教和轮回,我没兴趣。”
“你生气了?”
我没理他。
过了一会,信息又进来:
“结局真糟糕,原来我是这么死的。”
“这只是小说的结局,那不是你。”
“我明白。我还是很不安,有很多担忧和害怕。”
“你还是个佛教徒呢。”我有点烦,忍不住想嘲讽他一下。
“我早已还了俗,与你一样生活在这个俗世上,这你知道的。”
“好好活着,别无事生非。”
“我今年正好39。”
“什么意思?”
“在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在他的生命中,每逢9必会出现一个坎,需要得到高人指点或神的化解方能平安度过。在你小说里我死于40岁。再过3个月就是我40岁生日。总之,我感觉已离死期不远……”
“那不过是个巧合!”有這么个逻辑来推理人的生死的吗?我哭笑不得,但又不能置之不理。
“怎会有这么巧的巧合?这一定是冥冥中注定了的,为什么这个事不早也不晚,恰巧在这个时候让我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提醒?既然冥冥中给了我这个提醒,那么结局应该还来得及更改。可我一点头绪也没有,不知道如何去改变我的命运。”
“谁能具备任意改变和编排自己命运的能力?你别迷信了,再次请求你别当真,那不过是虚构的。再说那个小说写于5年前,你想想,就算你在40岁死去,那也是5年前的40岁,跟你现在的40岁有何关系?完全搞不到一块去的。况且现实生活中的你,不活得好好的嘛?硬要去扯出这些无中生有的理论来吓唬自己干什么?”
真是绕啊,打出这些文字,我觉得自己也跟着对方在神神叨叨地说些莫明其妙的话,真是活见鬼了。
他锲而不舍:
“你相信预言吗?5年前的我才35岁,还没到40当然不会死,再过三个月我就走到那个节点上了,这个节点就是一个坎,过不过得去这个坎,我一无所知,但命运已给了我这个提醒,你说我能不紧张?”
我被他传染了,也紧张起来。虽然没有跟他面对面,但通过这些文字,还是能感受得到他极度的恐慌和不安。使劲想,怎样才能去说服他,帮他克服这种莫须有的不安,彻底驱走他的心理阴影。但又觉得在他这份近乎偏执的恐慌面前,好像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不理他又不行。生死是大事。你总不能置一个人的生死于不顾。
问题是,我又如何顾得了?
站在泽郎的角度去想,是我的小说给了他一个命运的启示和提醒,或者说,是冥冥中的一个诅咒。无论是诅咒也好,提醒也罢,都如驱之不去的阴影一般笼罩着让他不得安生。除非等到他平安度过40岁生日,他才有可能松一口气。问题是,他该如何度过眼前这3个月?90个白天和夜晚,每一个日子都将在他的忐忑不安中变得无比恐惧而漫长。
下午开始到深夜,我没写一个字。手指打着字,心里有略微的不耐烦和无可奈何。好几次,都想狠狠心拒绝再聊下去,但终究还是克制住了。这件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压根就不信那些。但对一个把所谓的预言和命运的巧合相信到骨髓里去的人来说,却是一件生死大事。就如同还俗之前的他,对于宗教信仰的坚信不疑。
后来我干脆把电脑也关上了,一直盯着手机,用微信聊天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我们通过微信谈人生、谈命运、谈信仰、谈因果、谈生死轮回。
我知道谈人生改变不了人生,谈命运改变不了命运,谈信仰也改变不了信仰……但,还是要谈。
这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交谈,直抵伟大却虚无的真理。
看过一部电影叫《无间道》,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在那个你死我活的丛林世界中,这是一条中立、冷酷、无情的规则,另外,从因果上来说,“还”也是命中注定的事,不管你以何种方式“还”,或者,被注入何种内容去“还”。
写小说这么些年,在虚构故事的时候,我在电脑键盘上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像上帝一样任意编排着人物的命运和生死。这种挥笔豪迈、快意酣畅的感觉我想每一个写作者都曾经拥有过,都很享受。好吧,享受的时刻你尽情享受。现在事儿来了。
经过你想象或者虚构的人物终于找上门来了。找上你的那个人,无论他跟你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之间必然有因果。有什么样的果,必然就有什么样的因。事出必有因。命运中的因缘巧合,你看不见,但它存在着。或许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个叫泽郎的人,他跟我毫无关系。但他就是出现了。以一个小说原型的身份,外揣一份你写的结局让其陷入恐慌的理由,你就得担负起开导和劝慰的责任,如同欠债还钱般天经地义。不然,万一他出什么事,虽然从法律上你不用去承担任何责任,但在良心上,你总是会过意不去,会受到自我谴责。
就在我们谈人生、谈命运、谈信仰和生死轮回的同时,我仍不忘作出努力,试图去开导他。或许,奇迹会出现,或许他突然就从我的哪句话或哪一件事中得到某个启迪,瞬间顿悟了呢。
我问他:
“你去过尼泊尔吗?”
“没去过。我只到过印度,那时候没护照,也是偷跑过去的,后来被发现,进去了两年。”
“怎么就想到跑去印度?”
“绝望。没地方可去。从印度边境过去很方便。但到那边才发现,根本没办法生活。我汉语、英语都不好,工作不好找,也没个认识的人。想回来学语言,结果被抓了起来。”
“当时就没想过要在北京待下去?”
“在北京的日子生不如死,只想分分钟逃走。”
“理解。”
“那时候的我每分钟都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你不会理解的。”
“也是。那你有没想过回寺庙去?”
“回不去的。”
“是回不去,还是不想回去?”
“两个都有。还了俗就不能回去,寺院里有规定。”
“你到过不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