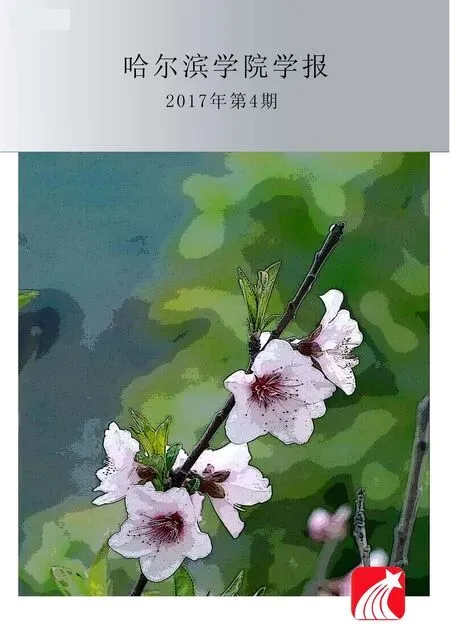“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之构建
——以《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路径
刘宗武,刘 毅
(1.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广东 佛山 528500;2.吉安市人民检察院,江西 吉安 343000)
“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之构建
——以《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路径
刘宗武1,刘 毅2
(1.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广东 佛山 528500;2.吉安市人民检察院,江西 吉安 343000)
主体权限的混乱、内容比例的失衡和规范协调的缺失是当前检察组织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由组织规范的庞杂性与立法资源的有限性、检察体制的变动性与规范制定的灵活性所决定,“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实则具有必然性。这一体系的构建应沿着两大路径展开:一是对《检察院组织法》内容、结构体系的反思与整合,二是对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丰富和完善。
检察院组织法;检察组织规范;规范体系;纲目型
在立法滞后与规范缺失的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问题顺时应势地成为检察学与立法学双重目光的聚焦点,其修改已经箭在弦上。站在国家法律体系的全局性视野下,这一研究态势的形成无疑充满了必要性与紧迫性。然而,立足于检察规范体系本身,以《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为契机,似乎也更需要唤醒对其所归属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深入思考。下文将从《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入手,对其内容、结构体系进行反思与整合,并以对单行检察组织规范进行完善为路径,对构建“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进行探讨。
一、《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检察院组织法》是1979年颁布的,1983年、1986年分别对部分条款作了修订。从颁布到现在已有三十八年,亟需修改完善,以适应我国法治发展形势和检察工作需要。
(一)修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必然要求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开始,历经2004年、2008年两个《司法体制改革意见》出台,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经过几轮的司法体制改革,实践中检察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正顺应了这种现状,即将检察改革成果制度化、法律化的需要。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办公室王洪祥主任指出:“已经建立的中国特色法制体系是初步的,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修改、完善已有法律的任务还很繁重……从某种程度上讲,组织法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司法改革的成果丰硕,需要上升到立法;人民检察制度,历经沧桑,薪火相传,日臻成熟完善,如果仅停留在实践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创新发展和司法改革的成果就得不到巩固。”[1]
(二)修法是由其根本性、组织性和先进性性质决定的
修改《检察院组织法》一是由其根本性性质所决定的。根本性又称宪法性,意指所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法律效力层次上具有最高性。《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立法法等一起构成了我国的宪法性法律。[2](P374)从宪法的内涵和组织法对于检察机关的意义来说,把《检察院组织法》定位为“根本法”并无不妥。[3]二是由其组织性性质所决定的。《检察院组织法》是规定国家重要权力——检察权的组织法,其主要规制的是检察权的规范行使,是检察权行使的前提。三是由其先进性的性质所决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立法的科学性。作为宪法性法律,其规定的内容具有根本性,因而必须科学、合理,否则难以发挥检察职能,与立法的目的相悖。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检察院组织法》曾为检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4]其立法科学性是值得肯定的,因而具有先进性;二是与时俱进性。诚然,法律应保持稳定性,不宜朝令夕改,作为根本法性质的组织法更应保持稳定性。但当社会经济和法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时《检察院组织法》也必须进行修改,这也是由其先进性性质所决定的。
(三)修法是完善立法内容本身的需要
《检察院组织法》立法严重滞后,其“内容、结构体系都需要丰富和发展”。[5]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检察院组织法》是1979年颁布的,其内容、体系结构已经严重滞后,需要进行“大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该法第5条设置的检察职能和保护任务是片面的。例如,在法律监督方式方面,没有规定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权;再如,在检察保护任务方面,只规定了保护公有制经济形式,而对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保护没有作出规定。二是结构体系安排比例失衡,“头重脚轻”,法条之间存在交叉、重合的现象,条文设置不够科学、合理。例如:整部法律共28条,总则就有10条,涵盖面广,包含内容多,因而形成总则部分一头过“重”,分则一头相对过“轻”的格局。又如,对检察领导体制方面的规定分散在第3、10条,而第4-9条又夹杂职权、原则等内容,法条之间存在交叉、重合。三是有些条文规定得过于原则、单薄,有失严谨,有些内容未有专章单列。例如,该法不加区分地将机构设置与人员任免规定在同一章节中;对军事检察的规定未单列;对派出机构职能、规格等内容没有明确界定。四是法条用语存在过时表述,如“敌我矛盾”“反革命”等词语。
(四)修法是维护法制统一性的需要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的相继修订,我国现行《检察院组织法》与多部法律规定存在冲突。例如,刑诉法与民诉法在多次修改时对检察职权所作的诸多调整,在《检察院组织法》中均未体现,致使检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面临尴尬的境地。[6]又如,根据《检察院组织法》第16条规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将案件退回检察机关补查。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五)修法是构建“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客观需要
目前以《检察院组织法》为主要法律规范的检察组织规范存在主体权限混乱、内容比例失衡和规范协调缺失等诸多问题,难以称之为“规范、完整和完善的检察组织规范体系”。而笔者提出的“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需要对其内容、结构体系进行反思与整合,即以对单行检察组织规范进行完善为路径。因此,《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既为构建“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带来了契机,也顺应了构建“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客观趋势。
二、我国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现状与反思
(一)检察组织规范现状
检察组织规范,是指以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组织目的、组织职权、组织人员、组织管理和特殊检察组织等内容为调整对象的规范。以调整范围为标准,可将其分为综合性检察组织规范和单行检察组织规范;以是否为有权立法主体所制定为标准,可分为检察组织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前者是立法的产物,而后者的制定在我国主要由最高检来进行,因而并不能被纳入立法体系。从检察制度的初建到检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组织规范也不断得以完善,这一脉络可以从一系列检察组织规范的出台中得以集中展现(见表1)。
1979年至2002年,我国共制定检察组织规范六部,其中,由一部综合性检察组织规范,即《检察院组织法》,以及《检察官法》《检委会组织条例》等多部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组成。

表1 我国现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情况
(二)体系性缺位:基于立法现状之反思
尽管规范体系的建立需要以一定数量的规范作为载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即为正比关系。规范体系的形成实则在规范制定的有序性和规范之间的逻辑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观我国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则体系性的缺位实为其最鲜明的特征。
1.主体权限混乱。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家公职人员编制管理和职级确定确系中组部职司所在,但由其以发文形式对检察官等级问题进行规定实有不妥。1995年《检察官法》设专章规定了检察官等级,同时规定“检察官的等级编制、评定和晋升办法,由国家另行规定”;1997年中组部依此制定《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的同时,继续指示:“本规定的实施办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这就使得对检察官等级这一问题,先后需要三个主体参与规范,这不仅影响规范制定的效率,更易催生出规范内容上的抵牾。况且,由中组部这一党委机关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定,不仅有违党政分离的原则,也不符合《检察官法》所提出的“由国家另行规定”的要求。因此,明确各类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主体,是实现检察组织规范体系化的基本路径。
2.内容比例失衡。检察内部领导机构和检察人员管理体制是当前单行检察组织规范所主要致力于调整的两大领域。除《检委会组织条例》系对检察机关业务决策机构进行规制之外,其余四部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均系针对检察人员管理中的各类问题而制定,这就诱发了在规范制定上的“畸形”:一是在某些检察组织事项上的调整力度尚属不够,如在检察派出机构方面,缺乏有关派出机构运作程序、人员配给以及经费职级保障等方面的规范;[7]二是针对某些组织事项的规定尚属空白,如检察直属机构的相关问题,尚无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有效规定。内容比例上的设置不均,将使一个有序而稳定的检察组织规范体系丧失建立的根基。
3.规范协调缺失。“因事而立”是检察组织规范制定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特色。这一模式虽能及时应对检察实践中不时出现的新问题,但同时也极易导致规范制定上的各自为政。规范协调性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一是作为综合性检察组织规范的《检察院组织法》与各单行检察组织规范之间缺乏照应。换言之,《检察院组织法》中还有很多内容未能有效借助单行检察组织规范予以进一步细化,如受法律文本结构的限制,对派出机构的有效规制只能借助单行检察组织规范进行,否则检察派出机构只怕是寸步难行,甚至陷于“有名无实”的窘境。二是单行检察组织规范之间缺乏衔接与配合,如针对检察官等级这一问题,制定权限赋予的分散性极易引发规范内容上的冲突和衔接不畅,使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大打折扣。
三、“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提出及必然性
(一)“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内涵
“纲”与“目”是在种属关系确定与划分中所使用的两个概念。在《现代汉语辞典》给出的解释中,纲为“提网的总绳,比喻事务最主要的部分”;[8](P412)目为“网眼,为大项中再分的小项”。[8](P903)这组概念在检察组织规范结构的探讨层面显得尤具价值。要言之,在对《检察院组织法》这一综合性检察组织规范与《检察官法》等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关系的把握上应树立纲目关系的认识,其中《检察院组织法》为“纲”,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则作为“目”,是在具体内容上对前者予以延伸和细化。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检察院组织法》在检察规范体系中素享“根本法”[3]或“小宪法”[5]之美誉。这也决定了《检察院组织法》应尽可能对检察组织的原则性和纲领性问题予以规定,属于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顶层设计”;而单行检察规范则在具体区域发挥其承载作用,从而属于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砖石构造”。
(二)构建“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必然性
1.组织规范的庞杂性与立法资源的有限性
检察组织规范在内容上主要包括:(1)源于机构设置、人员组成、纵横关系的检察体系构造;(2)源于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的检察权配置和运作;(3)源于诉讼和非诉讼活动的具体制度设计。因此,检察组织规范的庞杂内容远非一部《检察院组织法》或单行检察组织规范所能包举,这就决定了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必将朝着多文本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检察组织关系时,考虑到其难以为有限的立法资源所全面覆盖,立法者就只能选择放弃在某些细微层面上的目光投入,而借助检察组织系统的内部约束力来实现规范的普及与适用。因此,最终所形成的必然是“检察组织规范体系”而非“检察组织法律规范体系”。
2.检察体制的变动性与规范制定的灵活性
在深化检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组织体制和人员管理等体制性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经历持续性的调试,这就决定了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不能一蹴而就。检察组织规范也会因此在时间效力上被打上阶段性的烙印,体现为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制定的“快频化”,在规范名称的确定上或更倾向于使用“暂行”“试行”等语词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细则性内容交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制定更能适应检察体制改革的需要。但必须指出,有关检察组织的原则性和纲领性规范必须由组织法加以规定,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只能在其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细化和完善的作用。换言之,后者在制定过程中应牢固遵从体系化这一标准指引,以期在顶层设计之下形成纲目对应的规范体系。
四、“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设想
“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形成,既需要对作为“纲”的《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结构进行修改与完善,同时也离不开对作为“目”的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与丰富。
(一)《检察院组织法》内容结构的整合
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系统,《检察院组织法》的“各个组织要素要能够构成纵向的层次结构和联系、构成横向的分工结构和联系,这种横向和纵向的组织体系构成要科学、合理方能有效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功能、达到其组织的目的”。[9]现行的《检察院组织法》在内容结构上存在较大程度的滞后性,对此,需要通过规范条文的块状化和集中化、章节架构的层次化和递进化予以优化,形成“块状化、递进式”的结构体系。修改后的《检察院组织法》内容结构体系应由如下五大版块所构成:(1)总则部分,即关于立法依据、立法宗旨、组织性质、组织任务、组织活动原则、基本法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2)检察组织体系,具体包括检察层级设置、检察内设机构、检察直属事业机构、检察派出机构等问题。其中,检察内设机构可以区分为内部领导机构、职能机构和管理机构;(3)检察管理体制,分为检察领导体制以及检察人员和经费管理体制;(4)检察职权体系,由诉讼职权、监督职权和其他检察职权所组成;(5)特殊检察机关。只有在对《检察院组织法》内容体例予以明确的基础上,才能为单行检察组织规范制定方向和调整领域的确定提供重要依据。
(二)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方向
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不是盲目的,检察体制改革方向应是重要参考。由于检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为检察职能的有效履行提供体制上的保障,因此,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和丰富将适应检察体制改革的需要,主要集中在检察组织体系与检察管理体制两大层面。
1.检察组织体系层面的规范制定
一是顺应检察内设机构改革的方向与需要,及时制定《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组织条例》。具体而言,该条例内容的确定可遵循如下思路:其一,设三章分别就检察领导机构、检察职能机构、检察管理机构进行规定。结合检察体制改革的趋势,“检察职能机构”一章主要规定刑事检察部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诉讼监督部门的设置和职权;“检察管理机构”一章则主要规定办公室、政工部门、机关党委、计财装备处等部门的设置和职权。其二,由于最高检于1980年已制定《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而检察委员会只是业务领导机构,故应对《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进行修改与整合,将其纳入“检察机关内部领导机构”一章进行系统规定。
二是尽快制定出台《检察直属事业单位组织条例》,填补检察直属事业机构规范上的空白。从当前设置情况来看,检察直属事业单位设置主要集中于省级人民检察院和最高检,主要包括机关服务中心、信息中心以及检察官学院,其中最高检还设有检察日报社、理论研究所和中国检察出版社。然而当前却缺乏一部统一的单行检察组织规范集中对其组织与管理进行系统的规定,相应的规范制定仍停留在一些内部的规章制度层面。这就需要尽快制定一部《检察直属事业单位组织条例》,根据是否属于全额拨款为标准,分别就其机构设置、人员招聘、辞退以及工资待遇等管理问题进行详细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人、财、物的统一调配。
三是制定专门的《检察机关派出机构组织条例》,为检察派出机构的切实有效运作提供制度上的保障。设置混乱、审批权限不清、缺乏人员经费保障是派出机构在组织层面所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因此这一条例应着重解决如下问题:(1)明确派出机构的审批权限,采用归口审批制,并对当前的派出机构进行精简和规范,如派出地级院由最高检审批,派出基层院和检察室由省级院审批;(2)人员编制和职级的统一;(3)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将其纳入检察经费改革进程中加以解决;(4)明确派出机构的职权,引导其有效执法、规范执法。
2.检察管理体制层面的规范制定
首先,在人员管理层面,尽快制定《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办法》,同时修改《检察官法》,推动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实施。第一,明确将检察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检察行政人员,并对其职责、编制和员额进行系统的规定。[10]第二,对《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进行整合,在《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办法》中设专节予以规定。第三,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和《检察官培训条例》的相应内容分别纳入《检察官法》的第七章和第九章之中,改变“政出多门”的规范制定模式,通过规范清理实现规范内容上的协调。
其次,在经费保障上,探索制定《检察机关经费管理条例》,为省以下检察经费统一管理提供有效依据。第一,由于检察经费保障问题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检察机关内部事项,因此,对于经费保障的外部性和原则性问题必须在《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以减少检察经费改革的阻力;第二,由于《检察机关经费管理条例》属于最高检制定的内部规范,故应着重就检察系统内部区域性的经费保障标准、经费拨付、经费使用和审计进行规定,以规范检察经费在检察机关内部的审批、流转和使用。
此外,在是否应针对特殊检察机关另行制定单行检察组织规范这一问题上,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认为,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无需另行制定规范,可以设置专章对特殊检察机关进行规定,在有效避免重复立法的同时,足以凸显专门检察机关在组织规范上的特殊性。
综上,检察组织规范的完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立法者断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易言之,“纲目型”检察组织规范体系的构建在具体进路上呈现出双向的互促性:一方面,《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并非旨在“拾遗补缺”,而更应通过确立“纲”的标尺,以把握“目”的完善,避免在制定单行检察组织规范时只顾“各扫门前雪”;另一方面,对作为“目”的单行检察组织规范的制定与展望,也可以为“纲”的修正提供必要的参考。
[1]陈国庆.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紧迫性与必要性[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6).
[2]曹建明,等.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1999年4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吴美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若干基本问题匡正[J].中国检察官,2011,(23).
[4]孙谦.关于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若干思考[J].人民检察,2011,(12).
[5]庄永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35年需大修[N].检察日报,2014-06-06.
[6]杨柳,王新友.尽快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N].检察日报,2013-03-15.
[7]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课题组.检察机关派出机构体制研究[J].人民检察,2010,(9).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卞建林,田心则.论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结构体系的立法完善[J].人民检察,2007,(2).
[10]姜微,杨金志.上海启动司法改革试点[N].人民法院报,2014-07-13.
责任编辑:孙 畅
Construction of “Type-based”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Norm System——By Means of Revising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Law”
LIU Zong-wu1,LIU Yi2
(1.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Gaoming District in Foshan City,Foshan 528500,China;2.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Ji’an City,Ji’an 343000,China)
The main problems in present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norm system include chaotic permission for subjects,unbalanced content proportion and inadequate standard adjustment,which is the result of complexity of organization norms the limitation of legislation resource,the variability of procuratorate system and the flexibility of norm making. Therefore,the type-based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norm system is inevitable. There should be two approaches:1. integrating and reflecting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Law”;2. Enriching and completing uniline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norm system.
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law;procuratorate organization norm;norm system;type-based
2016-09-02
刘宗武(1984-),男,江西吉安人,硕士,主要从事检察理论与实践研究;刘 毅(1989-),男,江西吉安人,硕士,主要从事检察理论与实践研究。
1004—5856(2017)04—0077—06
D626.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4.018
——有关群文阅读教学法的实践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