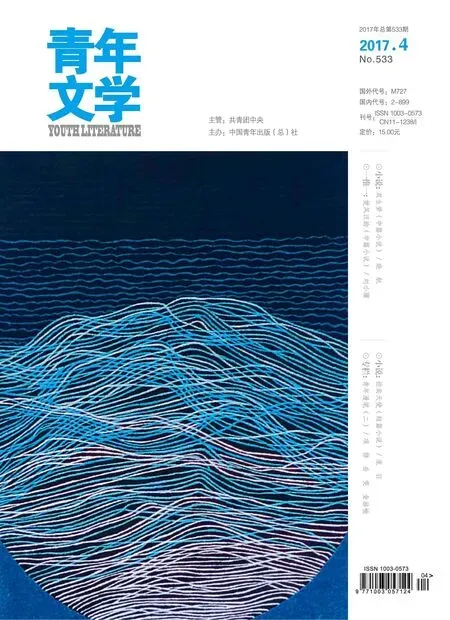单程青春
⊙ 文 / 陈蔚文
单程青春
⊙ 文 / 陈蔚文
陈蔚文:一九七四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月报》《大家》《钟山》等刊。出版有小说集《雨水正白》、散文随笔集《见字如晤》《未有期》等十本。曾获《人民文学》散文奖等奖项。现居江西。
深秋,北去旅途中带了两本书,纳博科夫的《玛丽》和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玛丽》多年前看过,有些淡忘,重购后翻开,忽然记起了其中熟悉段落,记起主人公加宁,一个内心充满热与凉的漂泊青年,住在柏林铁轨旁的膳宿公寓,和一群落魄流亡的房客。
多年前的摘抄本上还有一些书中段落:“那逐渐渗入室内的阴沉暮色正在慢慢穿透他体内,把他的血液变成了雾……他没有力量是因为他没有具体的欲望,这使得他十分痛苦……没有任何东西能缓解他的消沉情绪。”
我怎么把加宁给忘了呢,当年读《玛丽》时离他多么近!他就像住在隔壁的落魄青年,夜晚踩出疲杳的上楼脚步。或者,他近到可以拼凑出部分的我。
《玛丽》是纳博科夫第一部俄语小说,俄文名叫《玛申卡》。老年的纳博科夫在谈到《玛丽》时说:“由于俄国非同一般的遥远,由于思乡的痴狂陪伴我一生,我已习惯于在公众场合下忍受其令人断肠的怪癖,因此我毫不困窘地承认自己对这部处女作在情感上的强烈依恋。”纳博科夫的依恋是有理由的,因其中映照着他本人的青春,晦暗幽深的隧道,远方是让人期待的模糊的一团光。而此后光亮普照,那种让人心悸的期待却永远消逝了。
向北的列车上,书中主人公加宁身下的隆隆震颤仿佛穿过书页直透到我身下,此时的震颤与一九二六年柏林的震颤重叠在一起:膳宿公寓,六间房的各色房客走动,包括忧郁的青年加宁,房客们身世不同,性情各异,唯一相同的是窘迫。房客中有两个跳芭蕾舞的同性恋科林和戈尔洛茨维托夫,这对整日走街串巷揭下剧院招聘启事的天鹅湖上的同命鸳鸯,为庆祝老诗人拿到去巴黎的签证(后遗失,老诗人为此断绝了唯一希望),他们想开个派对,鬼鬼祟祟地去采买物品。——鬼鬼祟祟在这此处用得多么好!一对善良卑微,看去不无滑稽的人,他们对生活不肯绝望,想方设法抓住日子里一点值得庆祝的理由,他们尽力延长放大这点欢乐,从拮据生活费里挤出点钱操办这个派对。
连加宁以及其他房客恐怕都瞧不起他俩,而这对鸳鸯仍勉力要保住生活的这点薄焰。那个派对,与其说集合了欢乐,不如说放大了失意,像尾随一切短暂欢乐而至的阴影。
加宁最终没去见初恋的女人玛丽。他从邻居的一张照片中发现邻居正等待的妻子原来就是他中学时代的初恋情人,而后几天里,加宁不断地追忆与玛丽的往昔。
他做了个决定,他把邻居的闹钟拨慢,想代替他去接玛丽,并期望着与她重叙旧情,然后私奔,重演他们白桦林般金黄的爱情,然而,在等车的时间里,加宁顿悟到,玛丽已成别人的妻子,无论过去多么让人怀恋,毕竟一去不返。
加宁用四分之一财产购了张去德国的火车票。火车开动时,他的脸埋在雨衣褶子里,睡着了。
多么逼真的青春!铅灰的青春,夹杂着点玫瑰色回忆,那点玫瑰色后来也消遁于岁月的灰中。
纳博科夫是在一九二五年春结婚后不久开始写《玛丽》的,次年年初完成,时年二十六岁,如此年轻,就已显示出如此非凡的写作才华。纳博科夫说:“众所周知,初次进行创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品的强烈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个替代者放进他的第一部小说,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现成题材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为了摆脱自我后可以去轻装从事更美好的事情。”“加宁”就是年轻的纳博科夫,他的青春,他不能忘怀的初恋,书中加宁住的膳宿公寓近旁每五分钟就有一列火车开走,沉闷的轰隆声逐渐穿透整座房子,但某种意义上,每一列火车都带不走流亡的主人公加宁,也带不走年轻时代的纳博科夫,因为,没有一列火车能驶返他的青春,驶返青春时的故乡俄罗斯。
麦卡勒斯的《婚礼的成员》也在旅途读完,一个南方小镇女孩弗兰淇在某个夏天突然地成长,因为哥哥的婚礼而引发一场她成长的骚动。这个美国南方小镇女孩渴望离经叛道,却总弄巧成拙。她有点笨拙(好像突如其来的身体拔节使她衣裤短了一截似的),有些神神道道,无缘无故,不是因为过热的天气使她昏了头,而是突然到访的青春令她无所适从。
弗兰淇,当然也是麦卡勒斯本人青春的某段缩影。和忧郁的俄国青年加宁相比,这女孩更有种糊涂的明亮感:“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尘土白得耀眼,在头上,天空亮得像玻璃。”在这条路上,走着炽热的女孩弗兰淇。
或者,美国南方小镇与阴沉柏林的不同气候是造成这两种青春不同的原因之一吧。她的青春像夏天背上黏附的那层汗,加宁,他则裹着自己的体温,走在湿冷泥泞的街道,窘迫而保持优雅,不是诗人卡明斯说的“我们以白熊踩着旱冰鞋式的优雅一天天成熟”的那种笨重的优雅,是一个动荡时代和国家赋予这位清俊的俄国青年仿佛与生俱来的躁动而消极的优雅。——他在此中更清醒地领受人生,从消极中逐渐走向成熟。
弗兰淇和加宁,他们相同的是,都有一颗易敏感与战栗的灵魂。
青春,一生里最接近诗的年华,即使他此前从未读过一句诗。
写《婚礼的成员》时的麦卡勒斯二十九岁,仍算年轻,但多病的她在这年左半身完全瘫痪,并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试图自杀。
小说中的女孩弗兰淇,那种成长中的不知所措,若非亲历,不会写得那般真切。“这个夏天,弗兰淇已经离群很久。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那是美国南方小镇上弗兰淇的十二岁,也是所有女孩的十二岁。成长的寂寞、惶惑,对未来的满心期待与茫然。——彼时二十九岁的麦卡勒斯大概不会想到,四年后,由《婚礼的成员》改编的舞台剧在纽约百老汇剧院上演,引起轰动,连演五百零一场!她大概更不会想到,距离这场轰动上演后三年,丈夫李维劝说麦卡勒斯与他一起自杀,她成功逃走,丈夫却在巴黎的酒店里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身亡。
“人们飘零着的同时却被限定,被限定而又飘零着。”这是《婚礼的成员》中的一句话,也是麦卡勒斯所有作品中表达的主旨。
不知是否是阅读上的巧合,在看完这两部小说之后,又看了南非作家库切写的《青春》,他六十二岁时写的自传体小说,也与青春有关。
主人公约翰是一位南非大学生,数学专业,却是文学爱好者,视现代主义诗歌巨匠艾略特和庞德为自己的“引路者”,他渴望在诗歌领域有一番成就。然而先要解决温饱。他在伦敦(他相信命运之神只居住在欧洲的大城市中)IBM公司做一份计算机编程员工作(这份工作是一个没有三十岁的世界,它只接纳年轻人)。这位外省青年孤独至极,连性也不能填满孤独的罅隙,他常要注意自己元音的发音,以免露出外省人身份。
约翰像个局外人般游荡。“他时不时地有短暂的机会从外部看自己:一个喃喃低语的,忧心忡忡的,不成熟的男人,单调平凡得你都不会对他看上第二眼的人。”这也是许多青春的写照,外貌的单调平凡毫不影响他们(我们)内心的翻腾,神经质的自卑与自大并存,向往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而什么是“理想生活”,却连自己大概也描述不清。
在伦敦等待了几乎两年,命运之神依然没有顾临。“他心里明白。除非他促使她来,否则命运之神是不会来找他的。他必须坐下来创作,这是唯一的办法。”小说结束了。现实生活中,库切从IBM公司辞职,离开了英国,到美国攻读文学博士,从此走上了作家的道路。二〇〇三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六十二岁的库切再度审视青春的彷徨之途时,会有什么感想?一定会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吧,那的确是个多数人都不敢冒险做的决定,放弃一份光彩务实的职业,去向一条“务虚”的未知之途。
在连贯的时间里读了这三篇小说,似乎一下把“青春”这列呼啸的火车带至面前。它们都算不得三位作家创作生涯里名气最大、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纳博科夫最知名的小说是《洛丽塔》,麦卡勒斯的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库切的代表作通常认为是《耻》),然而这三个青春样本中都有一种真切的恍惚与疼痛感,它们分别发生在柏林、美国南方小镇与伦敦,却又如同发生在身边,发生在中国的城镇,与我们并没什么阻隔。——青春的内质何其相似,玻璃碎片般的敏感、自我怀疑、无聊的消磨,感情用事,拼了命地想特立独行却又无一长技。总之,各种难解的困境。
青春,使我们像整个世界的局外人,还是唯一的那一个。
回想我的青春,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我密集地读了不少港台小说,曹丽娟的《童女之舞》,黄碧云的《盛世恋》……都与青春有关,或说都是青春期的爱情。有一阵子,你会以为爱情就是青春以及人生的全部内容。实际上,青春要泥沙俱下得多,没有哪个阶段比青春更懵懂而锐利,犹如单薄的鞋底与石子路面的摩擦。
甚至想不起青春的一些具体情节了,如游园惊梦,但我记得整天思虑的都是那些其实对生活没有任何实质影响的事物,如同云的倒影,井的幽深回声,我们与自我如此紧密,又如此疏离。像触到自己肌肤有时那一刹的陌生感,好像那是他人的皮肤。
俄国青年加宁常回想那段当临时演员的荒谬经历:“里面没有头脑的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参与拍摄的电影的内容一无所知。”青春也正如此,我们更多在“演”自己,演完整个剧情却根本没弄懂其中要义。
这段里程,一切都在加速度地消耗,肉体、精神,那种感觉,大概像在高速公路上寻找一个正确的出口,怎么都找不着,突然找到一个出口,慌不择路冲了出去,这一冲便再回不来了。那个出口,是否通往正确很难说,但一些没及时说出的话,没冒过的险,没审视过的内心,没定居下来的城市,没来得及看但此后再没勇气看的恐怖片,统统错过了……
中年很快到来,那些曾热病般的没头没脑,渐渐冷静了下来,回到生活柴米油盐的现场,越来越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不再有批判冲动,顺应现实,彻底丧失革命性。
当有一天,在街上或地铁用余光打量那些青春,他们介于加宁和弗兰淇之间的年龄,或是南非青年约翰的同龄人,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笑或闷头发短信,一览无余的荷尔蒙在他们脸上身上涌动,你意识到这点时,发现自己的青春永远过掉了。它是不设返程的站台。但并没有什么遗憾,也许你更愿意是此刻的自己,不复青春的自己,泯然众人的自己。就这么普通也没什么不好,你终于认同与接受了这份普通,以及没有奇迹的人生。
也只有这时,你意识到青春里荒唐与虚掷的那部分的价值,它们使你成了现在的这个人,一个面有沧桑之色,看上去无法想象你也曾那样神经质般青春过的中年人。

⊙ 李瑶瑶·轻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