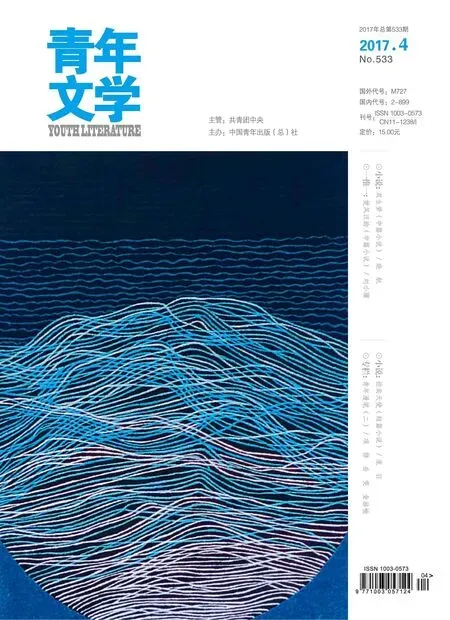大地的子宫
⊙ 文 / 周齐林
散 文
大地的子宫
⊙ 文 / 周齐林
周齐林:八〇后,江西永新人。作品散见于《作品》《北京文学》《芙蓉》等刊,著有小说集《像鸟儿一样飞翔》、散文集《心怀故乡》。曾获首届全国青年工业文学大奖新人奖,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现居东莞。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后的油格屏山上树木茂盛,时而有老虎出没,擅长狩猎的乡里人背着猎枪上山,总会满载而归。山上弥漫着野味,山下的田地里绿油油,满是稻谷的清香,乡里人日复一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田地里,纤细的禾苗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变成一串串沉甸甸的闪烁着金黄光亮的稻穗。大地肥沃,一切显得生机勃勃,土壤里正孕育着一个个新的生命。
那时母亲刚从几里外的东里村嫁过来,作为村里排得上号的美丽姑娘,母亲面色红润,腰肢细软,乌黑的长发里散发着诱人的发香。母亲不仅漂亮,还是做农活儿的好手,她吃苦耐劳,挑着一担一百多斤的稻谷行走在田埂上,健步如飞。乡里人见了,都暗暗佩服。父亲个子矮小壮实,但做木匠在方圆几里颇有名气。所以在父亲的几封情书的攻势下,母亲被父亲娶回了家。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那个阴雨绵绵的夜晚,怀胎十月的母亲生下了我,而此刻父亲正在外地的一个富裕人家做木匠。
母亲生下我没过几个月,连绵的细雨裹着丝丝寒气下了整整一周,田地里金黄的油菜伏倒在地,在雨水的浸泡下渐渐糜烂。母亲见了一脸心疼,她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子,用了一个下午把浸泡在水中的油菜收割上岸。一整个下午下来,母亲全身几乎被汗水浸透。当晚,母亲就发病了,全身酸软,一股酸痛隐隐在骨子里弥散开来。接下来她一连打了半个月吊针,病情才稍有缓解。风湿性关节炎就这样开始隐匿在她骨子里许多年,并在时光的推移下张牙舞爪。
那些年,父亲每次做完木工活儿回家,总会带回来几斤肉给母亲补身子。父亲十分细心地给母亲煲汤,在浓烈的香味里,我看见父亲对母亲的爱意。浓浓的香味弥漫在整个房间,这幅画面,成为我记忆中最温情的一面。在父亲的照顾下,母亲的风湿病慢慢得到了控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打工的浪潮迅速席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父亲的木匠生意慢慢变得冷清起来,我家的生活慢慢变得穷困,我们变得面黄肌瘦。一九九六年的夏天,做木匠的父亲跟着乡里人去了南方打工。刚到南方那段时间,父亲像一尾搁浅的鱼,迟迟找不到事情做,他挣扎着,祈求早日回到大海里。一连两个月,父亲没有寄钱回来,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经常倚靠在门前,默默朝远方张望。为了弥补家用,母亲想着各种办法。
绿色意味着希望。初夏时节的田埂上,毛豆粗硬的茎秆上挂满饱满的豆荚,豆荚浑身布满细细的绒毛,嫩绿的豆荚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显得青翠可爱。为了弥补家用,母亲想到了田埂上的毛豆。
次日黄昏时分,母亲挎着一个大竹篮出去了。快天黑时,我远远地看见母亲回来了。竹篮里盛满毛豆。晚饭后,母亲忙完家务,把我们召集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带着我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剥起来。昏黄的灯光把母亲弓着的身子折射在满是灰尘的墙壁上,一颤一颤,左右晃动着。
剥到十二点,我支持不住了。母亲看着我一脸疲惫的样子,命令我们赶快上床睡觉。我迟疑着。哥比我懂事,坚持着说不困,要留下来。昏沉里爬上床,很快我便入睡了。夜半醒来,门檐下的那盏灯依然亮着,昏黄的灯光把夜色涂抹成一个遥远的童话。伴着光晕,能听见母亲和哥剥毛豆发出的声音。
次日醒来时,我看见哥的大拇指都剥肿了,而母亲天蒙蒙亮时就已起来,挎着剥好的毛豆赶集去了。晌午时分,我欣喜地看见母亲篮子里的毛豆没了,换来的却是满篮子的生活用品、蔬菜和一些肉。吃饭时,母亲说毛豆卖两块钱一斤,一共卖了三十五块钱。母亲边说边冲着我们笑,脸上鼻子上满是细密的汗珠。
黄昏里,我站在门槛上,看见豆荚的青绿在烈日的曝晒下变成枯黄的色泽。青翠欲滴的毛豆,在裹着缕缕绒毛的豆荚的结实保护下,紧密地包裹着两粒嫩绿的毛豆。豆荚的保护,避免了田间害虫对于毛豆的侵袭和吞噬,避免了暴风雨的袭击和吹打。
多年后,剥落在地的豆荚常让我想起四处奔波的母亲,而豆荚紧密包裹着的青豆则常常让我想起年幼时的我们。
母亲就用这三十五块钱支撑着接下来那几日的生活开支。下一次赶集的前一天黄昏,母亲挎着篮子,又带上了我们,去田埂边摘足满篮子的毛豆。一晚上,一竹篮的毛豆剥完,天边已露出一丝鱼肚白。这回母亲兴冲冲地把一塑料盆的毛豆端到圩上,到散圩时,毛豆还剩下一半没卖完。到最后,母亲无奈,贱价卖掉剩下的一大半,剩余的便带回家。母亲买了一点猪肉,就着剩下的毛豆,炒了一盘毛豆子炒肉,算是犒劳我们兄弟俩。正是嘴馋的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而一旁的母亲紧锁着眉头,脸上满是忧与愁。
次日上午,母亲带着我们哥俩来到村里刘阿婆家两亩地宽的稻田前,拔稗草。上午十点,烈日当头,阳光十分恶毒。一阵热浪袭来,让我浑身禁不住一阵颤抖。这片两亩宽的稻田因无人伺候,已长满了稗草。卑微的稗草密密麻麻地隐藏在稻苗之间,真假难辨,它们偷偷争抢着稻苗的营养,疯狂生长。稻田里还残留着一些水,双脚踩在田地里,会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我一脚踩进田里,齐腰深的稻子就差不多把我淹没了。稗草为了安全地抢走稻田里的养分,故意把自己装扮成稻子的模样。这种以假乱真的骗术,让我陷入为难的境地。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我迅速认清了稗草的真面目,稻苗分叶处有毛,而稗草则没有。
两亩稻田在幼小的我眼里显得十分宽阔,站在稻田的一角落,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天气愈来愈热,到了晌午时分,空气仿佛凝固了,原本微微摇摆的稻子开始变得纹丝不动。我们挥汗如雨。黄昏时分,晚风吹拂时,我们终于上岸了。一旁宽阔的土路上铺满了我们拔出来的稗草,一辆装满货物的板车从上面轧过,我仿佛听到稗草发出疼痛的呻吟声。
傍晚,母亲去喂猪了,她吩咐我去刘阿婆家拿拔稗草的四十块钱。我在夜色里飞奔着,来到村后山脚下的刘阿婆家。刘阿婆两手颤抖着从叠了好几层的钱包里,拿出四张十块的钞票递给我。临走时,刘阿婆两只生满老茧的手拽着我的胳膊说,小林子,你妈妈这么辛苦供养你们哥俩读书,以后长大了千万要孝顺,不要像我这两个孩子一样,简直就是败家子,就像田里的稗草一样。刘阿婆的两个儿子不孝顺,一年到头很少寄钱回家,对他们二老不管不顾,在她眼里,他们都成了只知索取的稗草。年幼的我对这样的比喻感到稀奇,多年后才知晓败家子的败字是从稗草的稗字演变而来的。
与刘阿婆相反,我对稗草的情愫里含着一丝怜爱与亲切。凡夫俗子命运的卑微与稗草极其相似。我从母亲身上,看到一棵稗草的坚韧与顽强。稗草作为稻子的祖先,就因争夺了稻子生长的养分,而遭到了人类的围追堵截。
母亲把一大捆稗草背回了家,扔在了牛圈里。在昏黄的灯光的映照下,家里那头黄牛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食槽里的稗草。人们眼里视为敌人一般的稗草,在一头牛眼里,却成了一顿美味。大地哺育出的稗草,以另外一种方式喂养着我们。
二
午后,母亲一觉醒来,屋外一阵卖凉粉的声音传入她耳中,她疾步走出屋外,见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妇人正挑着担子戴着草帽,喊着卖凉粉了卖凉粉,两块钱一碗,声音拉得很长,带着一股余音在半空中回荡着。一碗凉粉就算卖一块五也很值,我们熬夜剥好的毛豆才卖三块一斤。对,卖凉粉!母亲拍了桌子,发出啪的一声响,像是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当天晚上,母亲就去了一趟姑姑家。姑姑早年擅长做凉粉,母亲是向姑姑取经去了。
多年后,每逢夏季,我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母亲年轻时在微凉的晨曦里做凉粉的情景,她半弓着身子,双手伏在石板上,不停揉搓着那一小袋用纱布装好的木瓜籽,整个身子上下起伏着,木瓜籽在长久的揉搓下变得黏滑无比,直至手中的木瓜籽慢慢失去黏滑时,母亲才缓缓站起来,长长地舒一口气。一个小时后,那一桶黏糊糊的水像是被施展了魔法一般,凝固成了母亲想象中的凉粉,她半蹲在水桶边,久久地凝视着,嘴角不经易间露出灿烂的笑容。我恍惚中看见母亲的模样,像晨风里,被风吹拂的花朵,摇曳着身姿,笑靥如花。
烈日缓缓升起,释放出的万丈光芒烘烤着大地万物,晨曦的雨露化为风里的一丝热气。此刻,母亲头戴旧毡帽,肩挂湿毛巾,挑起担子出发了。担子左边是用毛巾覆盖着的碗筷,右边是新鲜滑嫩的凉粉。我站在门槛边巨大的阴凉里,看着母亲一步步走进烈日深处,晃动的担子在她肩膀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拐了一个弯,母亲就不见了,我匆忙跑到屋后,一直看到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才回到屋内。
在午后苍白炽热的阳光里来回走动着,很快我额头上就爬满汗珠。我站在村头的那条马路上朝远处张望,却始终不见一个人影。蜿蜒的马路像一条烫死的蛇,此刻正冒着滚烫的热气。哥哥做好饭菜后又加入了我的行列,我们一起朝马路的尽头张望着,一直到饿了才起身往回走。
一直到黄昏时分,余晖落尽,阳光变得柔和,母亲才挑着担子出现在家门口。一天的曝晒,母亲满脸通红,像是一块在火炉里锻造许久的铁,刚刚从火堆里取出来一般。见母亲一脸欣喜地归来,我迅速去井边舀了一瓢清凉的井水递到她手里。母亲咕噜几声一饮而尽,我站在她跟前,清晰地看见她的喉结上下滑动着,粗重的鼻息声在我耳边响起。喝完水,母亲一脸骄傲地解下系在胯间的钱包,一个倒扣,包里的钱纷纷落地,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纸币,它们皱巴巴地堆积在一起,呈现在我和母亲面前;还有五毛、一块的硬币坠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在演奏一曲悦耳的凯旋之歌。母亲和我相视一笑,顿时变得兴奋无比。我们盘腿而坐,一张张地清算着,数了一遍又一遍,直至母亲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数完,母亲小心翼翼地从中抽出一张一块的递给我,作为对我的奖励。于是暑假时,每晚的黄昏时分,都成为我幼小心里的一个节日。

⊙ 李瑶瑶·你好,鸵鸟
当然也有例外。一次,回来时,母亲显得异常疲惫,她一边吩咐我们去里屋拿药膏,一边挽起裤腿,母亲摔破的膝盖渗出鲜血来,血沾湿了裤子。我们一脸担心地问母亲怎么了,母亲却笑着说,没事,不小心摔了一跤。
几天后从婶婶那里我们才知道实情,原来母亲挑着凉粉去山里卖,卖完凉粉从山路上回来时天已擦黑。走到山林里的小路时,碰到两个穿着花哨的地痞流氓。他们一个放哨,一个佯装吃凉粉,借着母亲打凉粉时的疏忽,一下子抢走了母亲的钱包。母亲心一慌,拽住钱包,却被一个流氓一脚踹倒在地,走了几步,他又转身回来,一脚踹在装凉粉的水桶上,只听咔嚓一声响。这一次母亲几乎空手而归,盛放凉粉的塑料桶中间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几乎分成两半。
烈日下,母亲肩上那桶凉粉,在冰块的浸泡下,变得清凉无比。在日复一日的奔走里,冰块的冷透彻到骨子里。母亲挑着担子四处奔走,桶里的冰凉反衬着她的汗流浃背。多年后我才知道,从母亲挑着凉粉在烈日下四处奔波的那一刻开始,那股寒冷与冰凉就开始在她生命中驻足。她用自己生命的热量温暖着我们的成长,自己却一点一滴地凉下去,那股寒冷是从腿部的骨头开始侵袭的。
三
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母亲总是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天气预报说晴时,母亲眉头舒展,若是连日阴雨绵绵,她就眉头紧蹙,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母亲,这个很少把情绪挂在脸上的女人,这个一直把内心疼痛隐藏起来独自咀嚼的女人,此刻却小孩子一般被天气左右着情绪。当村里人都抱怨着烈日的毒辣时,母亲却一脸兴奋地在烈日下奔走着,满脸汗水。
母亲年复一年在烈日曝晒下奔走,方圆几里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酷暑时节,人多的地方是卖凉粉的好去处。我和哥哥是走读生,每天都是回家吃饭。母亲每天早上出去卖凉粉前,都是先做好饭菜放在锅里热着。
那天中午我吃完饭回到学校,远远的,我看见学校的后门聚集着许多人。踮着脚,我隐约看见母亲那张熟悉的脸,细密的汗珠爬满她的额头,她正忙着给人打凉粉。看着母亲浑身汗湿的样子,我心底顿时一疼。我迅速走过去,走到中途,看见自己暗恋许久的那个女孩子正在买凉粉吃。我犹豫着,忽然掉转方向,朝教室走去。趴在课桌上假寐着,眼睛却时刻盯着教室门外的方向,母亲那张被烈日晒得通红的脸不时闪现在我眼前,让我感到内疚不安。几分钟后,我暗恋的那个叫兰的女孩端着一碗凉粉走进教室,我看着她一勺接着一勺地舀进嘴里,静静地吃着,一阵凉风透过窗户袭来,吹乱了她的发梢。一碗清凉的凉粉,混杂了母爱的味道,还有一份爱恋的青涩。
时间变得异常难熬,终于,上课的铃声激烈地响起来。聚集在学校后门的人渐渐散去,我隐约看见母亲挑着担子匆匆离去,两个保安催促着,厉声呵斥她以后不允许来了,扰乱学校教学秩序,再来就要没收东西。几分钟后,比我高一年级的堂姐出现在教室门口。我迅速跑到教室门外,堂姐一边递给我两个苹果和一根香蕉一边说,林林,这是你妈妈刚才叫我拿给你吃的。我把苹果和香蕉放进课桌里,课上不时看它们一眼,心情很是复杂。
那天从学校出来,母亲挑着卖剩的半桶凉粉去赌场卖。那时村子里有个小赌场,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村里懒散的人吸过去。他们一整天待在里面,用以打发无聊的时间。母亲刚卖掉三碗凉粉,还没来得及收钱,派出所抓赌的警察突然从天而降,一时间满屋子的人乱了阵脚,捂着钱仓皇而逃,母亲使劲护着手中的那桶凉粉,慌乱之中,桶子被人踢了个底朝天,半桶的凉粉流了一地。母亲几乎哭出声来,这凉粉是她的命根子,她靠这个供养着两个孩子上学。母亲跟着一屋子的人被带到了派出所,容不得任何辩解。
下午放学归来,我在婶婶家吃完晚饭,和哥哥跑到派出所的屋后,我踩在哥哥的肩上,爬到窗户口,透过那扇锈迹斑斑的窗户,我看见母亲独自蹲在墙角,一脸愁容。我轻声叫了句妈。母亲眼前顿时一亮,她疾步走到窗户下,问我们哥俩吃饭没,末了吩咐我们不要担心,很快就可以放出去了。屋外响起开门声,我迅速跳下窗去。在灯火阑珊的夜色中,我和哥哥匆匆往学校的方向跑去。晚自习后,我和哥哥回到家,屋子依旧空荡荡的。那一晚,母亲在派出所冻了一夜。次日清晨放出来时,母亲一脸的疲惫。休整几日,母亲又浑身是劲地上路了。
四
母亲的风湿病又犯了。几年前那股聚集的冷意,渗透到母亲的每一块骨头里。
一次,早上还是晴天,中午时分一场暴风雨突如其来,母亲挑着凉粉恰好行走在无避雨之处的旷野里,回来时全身湿淋淋的,桶里的凉粉却完好如初。母亲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她使劲弓着身躯,仿佛只有如此,才能把渗透进骨头里的疼痛挤压出去。
母亲生下我没几个月,下地抢收浸泡在田地里的油菜,留下的风湿病病根,此刻变得肆无忌惮,它开始露出狰狞的獠牙,撕咬着母亲的身体。年长后,我慢慢认识到,就像农民种下的秧苗,生活里你不小心种下的疾病的种子,随着岁月的增长,它会逐渐疯长成啃食你生命营养的一株稗草。这株稗草,会在你生命开始苍老时,疯狂地繁殖。
床头上,母亲紧咬着牙,不让自己吭声,但潮水般汹涌而来的疼,瞬间就把她淹没了。她喘着粗气,额头上冒出一阵阵虚汗。
母亲递给我五块钱,微凉的月夜中,我飞奔着往四里地之外一个小镇的药店跑去。那里有专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我在夜色中疾跑着,夜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我把那一二十粒用白纸包裹着的细小药丸紧握在手掌心,在夜风里飞速往家里跑着。许多年后,当我在异乡漂泊的夜里回望故乡,总会看见那个少年,在夜色里奔跑,喘着粗气,细密的汗珠爬满额头。
我一路跑到家里,母亲依旧躺在床上,平日里泛着红晕的脸,此刻变得惨白。母亲颤抖着手服下药,很快睡去。细小的药丸功效如此显著,这一晚母亲睡得很沉。深夜我和哥哥听着母亲响起均匀的鼾声,心底倍感踏实。许多年过去了,我参加工作之后才知晓,这种药丸见效如此之快,是因为里面含有比较多的激素。它在能达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同时,却埋下了致命的危险。
五
多年前,母亲卖凉粉时遭遇的那场暴风雨,在她的生命里留下了后患。
那是我读高三下学期临近高考时,母亲一连好几日吃不下饭,浑身无力。一次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带着我上山挖草药,我们一人一把锄头在山间的土地上寻觅着草药的踪迹。母亲几锄头下去额头便满是虚汗。我转身回头看身后的大山,多年前还是郁郁葱葱的山林,此刻已是密密麻麻的坟墓。鸟语花香的山林,已经变成了阴气重重的乱坟岗。回望不远处母亲那张苍白的脸,我内心隐隐感到一阵惶恐与不安。
草药挖回来,服用几日,效果甚微。酷热的夏季,乡里的汉子袒胸露乳躺在凉椅上纳凉,母亲却浑身发冷,蜷缩在床上,需要盖两床被子来抵抗来自骨子深处的那股凉意。
二〇〇三年六月,非典爆发的高峰时期,高考前几天,高三毕业班提前放假,我提着一大包行李回到家,家中没人。父亲给我留了一张纸条,叫我安心高考,他带母亲去省城南昌治病了。一晚难眠,夜里总是梦见母亲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梦中,一具棺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顿时惊醒过来。窗外,夜凉如水,环顾四周,我一脸冷汗。我决定去省城南昌看望母亲。
高考前夕,定居在县城的老姑父和老姑妈一路打听,找到我住的宾馆。年近七旬的他们紧握着我的手,叫我安心高考,不要想太多。我紧抿着嘴,说好。他们陪我聊了很久。看着他们返回时蹒跚的脚步,想起千里之外的母亲,我眼底忽然一热。我躲到暗处,使劲仰起头,不让自己流下泪来。
几夜无眠,那一年高考,本想给父母亲一个好消息的我,却还是发挥失常了。高考后,提着满袋子的书本回到家,刚走到院落里,就看见形销骨立的母亲坐在后门的板凳上。我叫了声“妈——”,不争气地流下泪来。母亲转身回头,见是我,眼眶顿时湿润起来。母亲看着我,我久久地看着母亲,相视无语。母亲紧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哭啥,妈不是还在吗?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母亲最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手术后,母亲的性格变得暴躁了很多,枯坐在家里时会无端地发脾气摔镜子。家里已经欠了许多外债,父亲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去。一个月后,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清晨,父亲再次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路。父亲嘱咐我照顾好母亲,母亲病后性格会有点暴躁,要多体谅她。我默默点头,站在马路边,目送着父亲的背影渐渐消失在马路尽头。
三个月后,陪母亲去省城复查,我静坐在弥漫着福尔马林气味的医院走廊上,耳边响起啼哭声、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不远处,冰凉的机器在暗处发出淡绿的光,仿佛夏季墓地里闪烁的磷光。我一脸焦虑。几分钟后,当看见母亲一脸灿烂地走出诊疗室时,那颗久久压在我心头的巨石终于落了下来。
回去的车上,窗外微风轻拂,青草在风里摇曳着身姿。看着母亲脸上洋溢着的笑容,一股重生般的感觉瞬间来到我心间,那么强烈那么充满希望。我倚靠在车窗前,冲窗外的一花一草微笑着,感觉全世界都在向我微笑。在日渐荒芜的内心里,一朵希望之花突然绽放开来,花香顿时弥漫整个心房。
回到家,已是黄昏,炉火已熄灭多日,母亲和我在院落劈柴生火煮饭,淡淡的炊烟缓缓升起,朝天际飘去。这幅简单却温馨的场景,充满象征意味,多年以后一直在我脑海深处回荡着,每次想起,我的心总会感到温暖。
一个月后,我去了隔壁县的一个中学复读,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在学校时,我担心着大病初愈的母亲能否照顾好自己,每天晚自习后总会第一个跑到学校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那边的电话久久没人接听时,我就会特别担心。反复地重拨,直到电话那边响起母亲熟悉的声音时,我才放下心来。有时,是因为母亲睡着了,只是一场虚惊。
六
许多年后的今天,母亲已年近六十,满身的疾病让她过早地衰老了。她在村头的小路上走着,步履蹒跚,晚风吹乱了她鬓边的白发,难以根治的顽疾,加速着她的衰老。深秋的黄昏,微凉的空气,田野里遍地的金黄,映照着她眼底的那丝苍凉。
寂静的午后,她倚靠在凳子上打了一个盹,醒来,看见一个卖凉粉的女人吆喝着从她眼前一晃而过。往事顿时翻涌心头,她像是看到了许多年前的自己。眨眼间,几十年已悄然而逝。她要了三碗凉粉,然后叫醒午睡的我们,我和哥哥端着凉粉围在她身旁,恍惚间一切仿佛回到从前,咯咯的笑声碎了一地,随后便陷入沉重的静默和虚无之中。院落里二十年前栽种的木瓜树已经枝繁叶茂,母亲说,等她走了,就把她埋葬在这棵木瓜树下,这样还可以守家。
收拾屋子时,翻出一张老照片。母亲拿着照片久久端详着,照片随着手指的抖动而微微颤抖着。黑白照片上,年轻的她长发披肩,笑容灿烂,脸上弥漫着代表青春和健康的红晕。一张照片,让另一个自己穿越时光的迷宫,与此刻的自己重逢、会聚、叠加。她们彼此细细端详着,像失散多年的亲人,陌生与熟悉交织在一起。
像是得到某种强烈的提示,母亲放下照片,拿出裤兜里随时携带着的一块小镜子。她低下头,打量着镜中的自己,而后又看一眼照片,一种强烈的反差迅速蔓延。老了。她在心底叹息了一声。在那块小镜子里,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自己脸上密集的老年斑,纵横交错的皱纹,像是在密谋着下一次时光的偷袭。她捂着自己的肋部,忽然感到一丝疼。她能隐约感到在她苍老的躯体内,秘密萎缩的器官正逐步退化。她深呼一口气,在缓缓吞吐而出的气息里,仿佛闻到了腐朽的气息。
照片中,她的手指光滑修长,弥散着青春的活力和气息。风湿性关节炎,几十年病痛的纠缠,把她灵巧的双手改变了模样。
六十岁,是否意味着已走过人生抛物线的顶端,往泥土深处滑落下去。以前,关注天气的细微变化成了卖凉粉的母亲的一门功课,她准时地出现在电视机前,按着电视机里科学预测出的结果来安排自己的出行。几十年后的今天,水肿的膝盖,让她拥有了预知天气的能力,这带着强烈的反讽意味。她躺在床上,蜷缩着身躯,紧咬着牙,从膝盖提前到来的阵阵隐痛中预知着天气的阴晴变化。
时光充当了最好的魔法师,当初面色红润、腰肢细软、浑身散发着青春健康气息的母亲在几十年的时光里迅速变老,她生满老茧的双手像皲裂的树皮。黄昏里,母亲枯坐在门前的板凳上,默默注视着远方的那一片田野。蜿蜒交汇的河床是大地的血管,被污染拥堵的河流,仿佛被病菌侵袭的血液。人在变质的河流里,莫名其妙地患病死去。大地是人类的母亲,漆黑的土孕育着人的成长。大米、蔬菜、床板,一切来源于大地的土壤。人在泥土的喂养之下慢慢成长,最终又深埋在一小块泥土深处,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里,像一个熟睡的婴儿。一切回归到原点,初洗如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