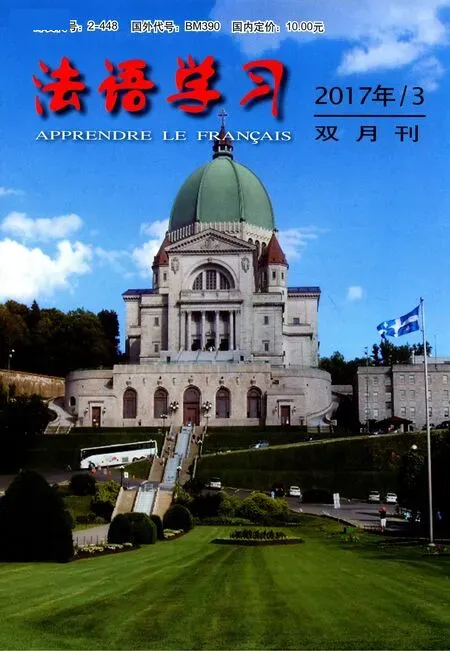被遗忘的译者
——朱育琳与波德莱尔①
杨玉平
被遗忘的译者
——朱育琳与波德莱尔①
杨玉平
朱育琳是1960—1970年代一个活跃于上海的文学小组的领袖,也是一位波德莱尔的秘密译者。他翻译的《恶之花》仅有八首留存于世。但从保存下来的译稿来看,朱育琳对源语言和目的语的语言特点、诗歌传统与文化背景了如指掌,译诗的目标十分明确,加上个人经历的苦难,使他的译诗在忠实与创造之间张弛有度,具有一个时代的特色,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朱育琳译《恶之花》不但能启发我们对翻译艺术的思考,也有助于更新我们对当代翻译史的认识。
朱育琳;翻译;波德莱尔;《恶之花》
一、被遗忘的译者
2017年是波德莱尔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众所周知,这位法国诗人与中国现代诗歌有着深刻的渊源。自1919年以来,《恶之花》被不断译介,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译者自然功不可没。在众多译者中,不乏像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陈敬容之类的知名作家与诗人,也有建国后像郭宏安、钱春绮这样的学者或翻译家。然而,有一位译者至今不为广大读者熟知,他的贡献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1993年,陈建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诗人,著有诗集《陈建华诗选》(2006)。在《今天》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亡友朱育琳的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边》,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与朱育琳先生私谈:波德莱尔翻译·翻译风格及其他》(1997)、《梦想与挣扎》(2009)、《一九六○年代的文学追忆》(2009)、《我与波特莱尔》(2010)等文章。2006年,《陈建华诗选》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201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学回忆录《灵氛回响》。1998年,钱玉林的《记忆之树——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抒情诗选》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钱玉林后来又发表了《寒夜篝火边的弦琴与歌唱》、《我们的文学聚会》等回忆性文章。至此,一个以朱育琳为首的文学小组1960年代在上海的地下阅读与写作活动渐渐清晰。我们也由此认识了一位波德莱尔的秘密译者。
朱育琳生于1931年,在北京度过青少年时代,精通英语和法语,建国前就读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对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都非常熟悉。1950年代初,朱育琳在北京大学学习西方语言与文学,后来转到上海同济大学学建筑,1957年被打成右派,毕业分配至新疆工作,又因健康原因回到上海养病。在这个结缘于福州路上海旧书店的文学小组中,朱育琳年纪最长,是公认的领袖。1968年,文学小组被人告发,朱育琳在遭受酷刑后跳楼自杀,结束了短暂而不幸的一生。
二、命运的契约
朱育琳不但写诗,而且译诗。从他的阅读范围来看,他熟悉的外国诗人应该不少,但为什么要选择翻译波德莱尔?首先,这是个人喜好问题。朱育琳特别钟爱19世纪西方文学,而且“他的趣味倾向于一种表现复杂人性的、更为真实而震撼人心的文学,然而,这常常是阴暗的、变态的”。他还喜欢“那种能引起极度美感想象的作品”(陈建华1993:261)。从这一点来说,波德莱尔完全击中了朱育琳内心深处的审美需求。波德莱尔上下求索,以自身为试验品,遍尝人间罪恶,他的《恶之花》颠覆传统美学,极尽阴暗、变态的恶之美,开创了现代派诗歌的道路。朱育琳与波德莱尔的文学品位更是不谋而合。作为19世纪重要的文艺批评家,波德莱尔最欣赏的本国作家是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看到了巴尔扎克写作中蕴含的现代性,称其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复杂的怪物,巴尔扎克自己则是怪物中的怪物。而在外国作家中,波德莱尔对美国人爱伦·坡无比崇拜,他不但写文章向法国读者介绍爱伦·坡,还亲自翻译爱伦·坡的作品,称其为精神上的兄弟。朱育琳的趣味与波德莱尔惊人地一致,他“喜欢品评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怪物’”(陈建华1993:261),同时也堪称爱伦·坡的知音。他喜欢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啧啧称赞其构思的奇妙、语言的精湛”(陈建华 2009:66)。他还翻译爱伦·坡的诗。不过,朱育琳对波特莱尔和爱伦·坡的喜爱有什么关联吗?他是在阅读波德莱尔后才知道爱伦·坡的吗?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朱育琳翻译波德莱尔似乎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事。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文艺界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波德莱尔在现代中国确曾风光无限,然而建国后一切都悄然改变。波德莱尔与新中国是格格不入的。恶魔诗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与新中国“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必然产生冲突;他的颓废、对人类命运不可救药的绝望则与共产主义弘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人生态度背道而驰;象征主义的写作方式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更是毫不沾边。尽管1957年7月,为纪念《恶之花》初版百年,《译文》推出了波德莱尔专刊,对波德莱尔及其作品做了较全面的介绍,试图重新诠释波德莱尔的诗歌艺术。但很快波德莱尔又戴着颓废诗人的帽子被再度打入冷宫。因此,在1960年代,翻译波德莱尔远非明智之举,不仅没有任何出版的机会,甚至可能给译者自己招来麻烦或者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朱育琳为何要翻译《恶之花》呢?显然,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人爱好范畴,隐含着更深刻的动机。应该说,朱育琳不幸的命运使他对波德莱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从而在更深的程度上体验波德莱尔笔下的苦难。1957年《恶之花》初版百年之际,波德莱尔在中国重逢良机,朱育琳却开始了人生的“恶运”*《恶运》(Le Guignon)是波德莱尔的一首诗,朱育琳曾翻译这首诗。。这个才华出众、满怀理想的青年,本应拥有美好的人生和灿烂的未来,却沦落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右派。在失望与孤独中,文学是他唯一的安慰,是他宣泄苦闷、表达怨愤与反抗的唯一工具,也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希望之光。文学使难以承受的命运变得可以承受。在波德莱尔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因此他称波德莱尔为“波兄”。波德莱尔在写作《我心赤裸》(Moncurmisnu)时,说自己“投入了全部的心灵、全部的柔情、全部(扭曲)的信仰和全部的仇恨”*Baudelaire C.Correspondance, tome II.Paris, Gallimard, 1973, p.610., 朱育琳在翻译波德莱尔时,又何尝不是如此?陈建华相信:“老朱和波兄之间是订立了某种契约的。”(陈建华 2006:153)
研究朱育琳翻译的《恶之花》绝非易事。出于各种原因,朱育琳不愿将译作轻易示人。他的骤然离世更使他的翻译活动成了无解之谜。我们直到今日依然无法知晓他究竟译了多少首《恶之花》。幸运的是,陈建华保存了其中8首,并以附录的形式展示在《陈建华诗选》中。除去这八首和他翻译的爱伦·坡的《给一个天堂里的人》(ToOneinParadise),朱育琳的写作和翻译手稿全部遗失。
陈建华保存的8首译诗分别是:《恶运》、《烦闷》(Spleen:Pluvise,irrité...)*波德莱尔共写过四首《Spleen》,此为第一首。、《裂钟》(LaClochefêlée)、《天鹅》(LeCygne)、《L’Héautontimorouménos》*朱育琳未将这首诗的标题翻译过来。标题是希腊文,意为“自己的刽子手”,也是古罗马戏剧家泰伦斯的一部剧作的名称。、《秋天小曲》(Sonnetd’automne)、《月亮的悲哀》(TristessesdelaLune)和 《异域的芳香》(Parfumexotique)。陈建华后来又记起朱育琳最后一次给朋友传阅却不让抄录的3首诗中的几句:“让我沉醉一个美丽的谎, /进入你的眼睛,像一个梦,/在你的睫毛的阴影里长眠。”*陈建华:《与朱育林先生私谈:波特莱尔翻译·翻译风格及其他》,载《今天》,1997年第1期,第177页。这首诗的题目是拉丁文:Semper Eadem,意为“永远如此”。
我们并不清楚朱育琳是怎样读到波德莱尔的。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读过《恶之花》了吗?还是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发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抑或是在上海旧书店的旧书堆里通过不懈的寻找发掘到他的书?除了《恶之花》,他还读过波德莱尔的其他作品吗?他读到的《恶之花》是哪家出版公司的哪种版本?这些我们都无法知晓。不过,朱育琳读到的应该是原版的波德莱尔,也就是说,他阅读的是法文版的《恶之花》。此外,我们也不知道朱育琳是何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只知道1966年他在上海旧书店邂逅陈建华时,就给陈建华介绍了4首译诗:《秋天小曲》、《异域的芳香》、《恶运》和《月亮的悲哀》。
三、翻译方式与风格
1.形式与节奏
一位高明的译者一定时时意识到忠实与创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激发的关系,巧妙地驾驭并利用二者之间的张力服务于自己的译文。从朱育琳的译稿来看,他对源语言(法语)和目的语(汉语)的语言特点、诗歌传统与文化背景有很深的认识,译诗的目标十分明确,因此能够娴熟地戴着脚铐跳舞,在两种文本间自由穿梭,形、音、意等方面的转换得心应手,使他的译诗既忠实于原作,又融入了自我的创造,展示出高超的翻译技巧,有好几首堪称佳作。
如何处理形式与节奏的关系,是译诗的难点。而波德莱尔又是一位非常注重节奏的诗人,他认为,诗的目的就是追求美,而“美的形成需要节奏”*Baudelaire C.《Etudes sur Poe》, O.C, tome II.Paris, Gallimard, 1976,p.329.。《恶之花》虽未严格遵守法国古典诗歌的法则,但从整体上说属于格律诗,形式与节奏都遵循法国诗歌的传统。面对中西诗律的巨大差异,《恶之花》的译者们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各不相同,译本基本可分为两大类:格律诗译本与自由诗译本。戴望舒翻译的《恶之花》可说是格律诗译本的代表。戴望舒的雄心是向读者最大程度地呈现原诗的面貌,即再现波德莱尔的“质地”与“形式”,其做法是“把alexandrin,décasyllabe,octosyllabe译作十二言、十言、八言的诗句,把rimes suivies,rimes croisées,rimes embrassées都照原样押韵”*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3页。戴望舒所说的alexandrin,décasyllabe,octosyllabe分别指法文含有十二音节、十音节和八音节的诗句;rimes suivies,rimes croisées,rimes embrassées分别指法文诗歌里使用的“随韵”、“交韵”和“抱韵”。。为此,戴望舒刻意将译诗诗行字数对应原诗诗行音节数,甚至不惜大量使用双音词和虚词。例如《信天翁》(L’Albatros)第一句(Souvent, pour s’amuser, les hommes d’équipage)*Baudelaire C.O.C, tome I.Paris, Gallimard, 1975, p.9.被译成:“时常地,为了戏耍,船上的人员”。(戴望舒1983:119)十二个汉字确实对应了原句的十二音节,却失去了自然的语感,也无法体现原诗的二分节奏。朱育琳显然不欣赏戴望舒拘泥于外在形式的完全对等,直言戴望舒“译得不好”(陈建华2006:152)。他自己的译稿则兼具格律诗译本和自由诗译本的特点,既不刻意将诗行压成豆腐块,又注重内在的节奏。例如《恶运》原本是一首八音节的十四行诗,但在朱育琳笔下,变成了音节数量不等的诗句,最长的有十一音节(远离了荣名的庄严的陵堂)(陈建华2006:185),最短的有六音节(永远无人知晓)(陈建华2006:185)。音节数量发生变化后,原诗的节奏划分自然无法不受影响,但朱育琳利用汉语的特质,把不同长度的音组组合在一起,单是第一节中就有单字音组、双字音组、三字、四字,甚至五字音组,音组的搭配错落有致,保留了比较自然的语感。在押韵方面,朱育琳尊重原诗的模式,即abba cddc eef ggf;原诗设六个韵脚,译诗也设六个韵脚。
朱育琳翻译的另一首诗《烦闷》也体现出他对诗歌音乐感出色的理解和把握。在波德莱尔写下的四首《烦闷》中,第一首(Spleen:Pluvise,irrité...)是唯一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采用亚历山大体,押韵格式为abab abba ccd eed,设5个韵脚,阴阳韵交替出现。下面是这首诗的第一节:
La mortalité sur les faubourgs brumeux.(Baudelaire 1975:72)
朱育琳的翻译如下:
多余的五月对全城恼怒:
把冰凉黑暗的大雨浇灌;
湿透了墓地里苍白的住户,
湿透了迷蒙的郊区的穷汉。(陈建华2006:187)
我们可以看到,朱育琳翻译的这4句中前两句都是十音节,后两句都是十一音节。尽管与原作音节数量并不完全对应,但由于诗句中的每个词都配合意义表达的需要,所以给人的感觉是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与中国传统诗歌无与伦比的节奏感相比,中国现代诗歌饱受诟病。传统诗歌对节奏的要求十分严谨,但从大的方面讲,主要依赖于诗句的音节数(即字数)、音顿的数量和位置的对称。朱育琳的这四句译诗基本符合这些要求,尤其是后两句,音节数(都是十一个字)、语法功能(动词词组+限定性词组+名词性词组)、音顿的数和位(三字音组+三字音组+五字音组)几乎完全对称,复沓的使用(湿透了……/湿透了……)甚至有股戴望舒早期诗歌的韵味。为了表现首句“五月”“恼怒”的情绪,朱育琳在韵脚安排上煞费苦心,“怒”、“灌”、“户”、“汉”皆为降调的去声。
朱育琳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的语言非常讲究,熏染了古汉语特有的雅致。在《烦闷》中,他把“Mon chat sur le carreau cherchant une litière”(Baudelaire 1975:72)译成 “我的猫在方砖地上寻梦”(陈建华2006:187)。“寻梦”一词本是《牡丹亭》第十二出的题目,讲述少女杜丽娘希冀回到梦中,与前几日在梦中遇到的少年柳梦梅重逢的隐秘的渴望。但这个词的意义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寻梦”可以理解为追寻梦想,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睡觉。显然,一只寻梦的猫就是一只睡觉的猫。猫是波德莱尔最喜爱的动物,在《恶之花》中,波德莱尔写了好几首以猫为主题的诗,将猫的形象诗意化了。而朱育琳使用的“寻梦”一词不但还原了波德莱尔笔下猫具有的宁静慵懒之美,还使猫的形象符合中国读者的传统审美需求。
2.主体意识与过度阐释
朱育琳的译稿确实体现出译者高超的文学和语言修养,但细读之下,会发现某些诗句存在明显的过度阐释问题。朱育琳的悲惨身世使他与波德莱尔产生共鸣,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恶运》第一句“Sisyphe, il faudrait ton courage ! ”(Baudelaire 1975:17)(意为“息息弗斯,需要你的勇气!”)被译成“息息弗斯,我仰慕你的气概。”(陈建华2006:185)朱育琳舍弃了原文的无人称句式,添加的主语“我”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直接宣泄了译者的感情。这句译诗可谓将忠实与创造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但过于强烈的主体意识会产生过度阐释。在《天鹅》第二部分第四节中,朱育琳把“l’il hagard(惊恐的眼睛)” 译成“憔悴的眼睛”,接着把“la superbe Afrique ”(美丽的非洲)译成 “高傲的非洲”(陈建华2006:191)。在陈建华看来,“憔悴”和“高傲”两个词具有政治含义,表达了译者“对恢复人的尊严的渴望,对剥夺人的尊严的抗议”。(陈建华1997:173)但与原诗对照,确实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这首诗最后一节的翻译出现同样的问题,原文是:
Ainsi dans la forêt où mon esprit s’exile
Je pense aux matelots oubliés dans unele,
Aux captifs, aux vaincus !...bien d’autres encor !(Baudelaire 1975:87)
朱育琳的译文是:
一个古老的“记忆”号角般吹响,
在流放我灵魂的森林里!
我想起水手被遗忘在荒岛上,
想起俘虏,被征服者……一切悲凄!(陈建华2006:191)
从总体来看,《恶运》这首诗的翻译非常高明,译者对原诗的理解不可谓不深刻,但译者对第三节的处理却与原文产生了出入。原诗第三节是:“— Maint joyau dort enseveli/Dans les ténèbres et l’oubli,/Bien loin des pioches et des sondes;”(Baudelaire 1975:17),朱育琳译成:“多少昏睡的珍宝,沉埋/在不可探测的深海,/永远无人知晓。” 波德莱尔是一位象征派诗人,擅长使用意象化的语言,在这里他借助“沉睡的珍宝”、“黑暗”、“镐头和钻机”的意象哀叹真正的艺术珍品被世人遗忘的命运。在朱育琳笔下,我们看到“昏睡的珍宝”和“不可探测的深海”两个意象,但“不可探测的深海”这个意象在原诗中并未出现,朱育琳用它代替了原诗中的“黑暗”,并以“永远无人知晓”这个直接点破寓意的句子强化、扩充了原诗中“遗忘”一词(l’oubli)表达的内涵,随后将其移到第三行,占据了末句“远离镐头和钻机”的位置,而“远离镐头和钻机”这句诗完全消失了。难道对朱育琳来说,象征的手法固然美妙,但已经不能如直抒胸臆那般痛快淋漓地表达内心的苦闷?
与《恶运》一样,《天鹅》这首诗也堪称佳译。我们来看《天鹅》第二部分第一节的翻译:
巴黎变了,但我的忧郁如故!
古老的郊区和新建的皇宫,
于我都成了寓意深长的画图,
而我珍惜的记忆比岩石还重!(陈建华2006:190)
波德莱尔的原诗是:
Paris change ! mais rien dans ma mélancolie
N’a bougé ! palais neufs, échafaudages, blocs,
Vieux faubourgs, tout pour moi devient allégorie,
Et mes chers souvenirs sont plus lourds que des rocs.(Baudelaire 1975:86)
与波德莱尔的原诗对照,我们发现译诗第二句中没有出现与“échafaudages(脚手架)”和“blocs(大块)”两个词对应的译语,而在原诗中,这两个词与“palais neufs”(新建的皇宫)和“Vieux faubourgs”(古老的郊区)共同构成第三句的主语。朱育琳为什么要删去这两个词呢?在这一节中,这两个词确实是翻译的难点。首先,“blocs(大块)”一词所指并不十分明确。其次,从中文的审美角度讲,4个名词或名词化短语共同构成一个主语的确太长,会使诗句产生头重脚轻的感觉。而从现有译本来看,译者们的处理也并不理想。也许朱育琳考虑这两个词并不重要,删去它们不会损害诗句的意义,保留下来反而会显得拥挤不堪?不但如此,朱育琳还把第三句开头的 “Vieux faubourgs”(古老的郊区)放到第二句开头,这样做解决了押韵问题(宫/重),还使译诗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变得语言简洁、意象明晰。从全诗来看,这也是朱育琳刻意追求的风格,旨在传达作者讽喻现实时沉郁悲愤的情绪。朱育琳友人们的反应应该能证实我们的猜测。陈建华写于1967年的《登吴郡华山》和钱玉林写于1969年的《皇家园林——拟波德莱尔》无论从主题、语言风格,还是写作手法都明显受到这首诗的影响。尤其是《登吴郡华山》,残破简洁的意象、短促有力的诗句、抑扬顿挫的音韵,都让人想起朱育琳翻译的《天鹅》。
结 语
近年来,陈思和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提出“潜在写作”的概念,指作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当然,其写作成果最终还是得以发表,否则就无法进入文学史的研究视野了。陈思和认为,“潜在写作”的价值在于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史的内容,还原了某些特殊时代精神现象的多元性。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能否认为,朱育琳的例子说明中国当代翻译史存在“潜在翻译”的现象,并与“潜在写作”呈现出极为相似的特点,值得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与同时期的正常写作相比,“潜在写作”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环境。与同时期的正常翻译相比,“潜在翻译”亦是如此。拿与朱育琳同时从事翻译的诗人穆旦来说,穆旦于1957年受到批评后,即放弃写诗,转入诗歌翻译,并出版了大量译诗集。与朱育琳相比,穆旦是幸运的。首先,穆旦是一位知名诗人,其次,他选择的翻译对象如普希金、雪莱、济慈、拜伦等诗人的作品都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范围内。这两点保证了他的译诗在生前得以发表。更重要的是,穆旦在翻译过程中知道自己的译诗是有机会发表的,他可以通过译诗来延续自己的诗歌生命。诗人穆旦消失了,译者穆旦诞生了,这一转换过程充满痛苦,但至少还存有希望。这是非常时期从事正常翻译的译者拥有的一丝权利。而默默无闻、从事“潜在翻译”的朱育琳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如前所言,朱育琳在翻译《恶之花》时看不到任何出版的希望,甚至有可能招来灾祸,事实后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如此惨烈的翻译环境下,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心甘情愿地自投死路,把译诗看成一项神圣无比的事业?唯有把朱育琳的译诗回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特点。在政治高压下,借译诗来书写苦难,在译诗中寻求生命的寄托。译诗与写作、译者与作者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消失了,这是导致译者在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后,体现出极为强烈的主体意识、产生某种程度上有意为之的过度阐释的原因。“息息弗斯,我仰慕你的气概”,那不但是波德莱尔的呼声,更是朱育琳面对不幸命运发出的感慨和自我激励。有谁能比正在经历恶运的他更深刻地理解《恶运》?那只惨遭放逐,“向上帝吐出它的咒诅!”(波特莱尔1957:138)的《天鹅》不就是他的写照吗?正是这些因素使朱育琳的译诗承载了一个时代特有的苦难感,在浓厚的悲剧色彩下,散发着某种英雄气息,感动并影响了他那些稀少而珍贵的读者。
波特莱尔.《恶之花(选译)》.陈敬容译.译文.1957, 7:134-143.
陈建华.《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今天.1993, 3:255-265.
陈建华.《与朱育林先生私谈:波特莱尔翻译·翻译风格及其他》.今天.1997, 1:163-179.
陈建华.《陈建华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陈建华.《一九六○年代的文学追忆》.书城.2009, 9:61-69.
陈建华.《我与波特莱尔》.字花.2010, 3-4:7-10.
戴望舒(译).《戴望舒译诗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Baudelaire, C.Correspondance, tome II.Paris:Gallimard, 1973.
Baudelaire C.Oeuvrescomplètes, tome I.Paris:Gallimard, 1975.
Baudelaire C.Oeuvrescomplètes, tome II.Paris:Gallimard, 1976 .
ZhuYulin,untraducteurclandestindeBaudelaire
Résumé:Chef d’un groupe littéraireShanghai dans les années 1960, Zhu Yulin était un traducteur clandestin de Baudelaire.Pourtant, seulement huit poèmes de sa traduction nous sont parvenus aujourd’hui.Grceune bonne connaissance des langues française et chinoise ainsi que des traditions poétiques des deux pays, Zhu, inspiré par sa douleur personnelle, a produit une excellente traduction qui se promène entre la fidélité et la liberté.Sa traduction nous permet de réfléchir non seulement sur l’art de la traduction, mais aussi sur l’histoire de la traduction contemporaine en Chine.
Motsclés: Zhu Yulin ; traduction ; Baudelaire ; Les Fleurs du Mal
(作者信息:杨玉平,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
① 本文为天津市社科项目“法国象征主义与文革地下写作”(立项号:TJWW12-003)阶段性研究成果。
H315.9
A
1002-1434(2017)03-003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