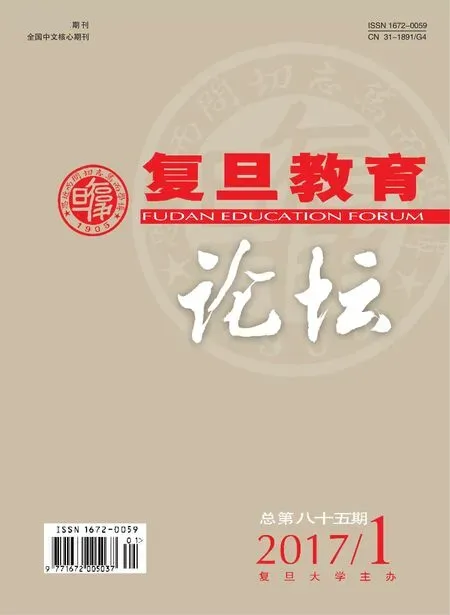高校学生申诉权研究
申素平,史三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专题·
高校学生申诉权研究
申素平,史三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872)
学生申诉权是宪法所确立的申诉权的具体体现,其存在不仅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而且契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通过扩大申诉范围、细化申诉规则、健全申诉组织、引入申诉追责以完善申诉运行机制,健全学生权力组织及弘扬权利文化观念是保障高校学生申诉权的必由之路。
学生申诉权;权利保障;高校学生申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简称《教育法》,下文中提到的法律,均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二条规定,学生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①进一步确立了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使其成为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重要形式。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高校学生申诉制度的完善,少有对制度背后的申诉权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从申诉权的角度入手,对学生申诉权的性质、必要性以及保障问题进行法理探讨,希冀丰富有关研究。
一、学生申诉权的性质
(一)申诉权是宪法所确立的源于人权的基本权利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该条规定确立了申诉权的基本权利地位。自然法理论将人权分为先于国家的人权与基于国家的人权两类[1]。申诉权的产生源于公权力的不当行使,其应属基于国家的人权。中国法哲学研究中,有学者从人权的实现和存在形态这个角度进行区分,将其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2]。从中国的法律实践看,作为实有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其范围要小于作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意义上的申诉权。
(二)申诉权是一种救济性权利
有学者认为,《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规定的申诉权兼具监督权与救济权两种内涵[3];亦有学者认为申诉权仅为一种救济性权利[4]。我们认为,申诉权应属救济权性质的权利。原因在于:从法律规定看,《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申诉权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法失职为前提,以“申诉”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行业规范,也是在救济权的意义上讨论申诉问题。如上文所述的《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又如《规定》在确认学生申诉权时也指出:“对学校给予的处理或者处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上述规定均是在当事人权益受到侵害的前提下赋予其申诉权。当然,从申诉的处理过程看,受理申诉的往往是被申诉者的上级单位,这种处理程序本身即可对被申诉者起到一定的震慑和监督作用;但从该项制度本身的定位看,其还是立足于对申诉者的权利救济。
(三)学生申诉权是一种行政申诉权
所谓公民行政申诉权,是指作为当事人的公民或其利害关系人认为有关组织的职务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依法向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提出撤销或变更原处理决定、责令限期改正或重新处理、停止侵权、直至赔偿损失的请求的权利。[4]学生申诉权是公民行政申诉权的一种,是行政申诉权在高校这一场域的具体体现。行政申诉权主要是相对于诉讼申诉权而言的。二者在定位与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在申诉对象上,前者是对行政性权力行使的异议,而后者是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异议;其次,在处理依据上,前者既包括法律法规,亦包括情理、习惯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而后者依据的主要是正式的制度性规范;再次,在救济方式上,前者不限于撤销或纠正不当行政行为,更重要的是对申诉人的合理诉求进行救济,具有协商性、综合性、非正式性及平衡性等特点,而后者的救济方式法律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受理机关在救济的方式上并不具有太大的自由度。[5]作为行政权力体系内的自我矫正机制,申诉在很多纠纷的解决上更为灵活、更有效率、更为圆满。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行政申诉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尚未能像行政复议那样获得正式的国家立法。
二、学生申诉权的必要性
(一)学生申诉权是落实宪法申诉权的需要
保障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目标。作为一项宪法所确立的源于人权的基本权利,学生申诉权应为高校学生所平等享有。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宪法》本身还不可以作为维护公民权利的直接法律依据,《宪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尚需借助其下位法律得以具体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果我们把《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类型理解为部分应有权利的法律宣示,也就是部分应有权利转变为法定权利,那么这种带有宣示意味的法定权利需要通过下位法加以具体规定后方可进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样才能使得宪法所规定的法定权利有更多的转变为具体权利及实有权利的可能。我们当前对法治国家、现代大学制度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扩大相关主体的实有权利范围、使其逐渐接近应有权利、法定权利的过程。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加强对学生申诉权的保障,正是落实学生法定权利、扩大学生实有权利、践行宪法核心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
(二)学生申诉权是学生权利救济的需要
人类公共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具有侵略扩张的本能,为此,人们设计出了不同的制度框架,如权力分立、行政诉讼、复议、申诉等,以期将权力约束在服务人们福祉的范围内。同时,对于那些可能或已经脱缰的权力行使,需要相应的纠偏与救济机制,以预防和弥补人们遭受的损害。高教领域也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单位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动,社会联结方式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转变[6]。具体到高教领域,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关于学校法人地位的规定为标志,以大学章程的普遍制订为形式,高等学校在法律上和形式上获得了独立的法人地位。但实际上,公立高校在人、财、物等方面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行政权力,法人地位有待真正落实。在此情形下,国家对高校的控制没有实质性地减弱,高校亦承担了部分超越其职责的义务,因而在具体管理中容易逾越法律的授权,干预学生的权利。同时,高校学生普遍缺乏社会阅历,有着较高的流动性,加之学生自治组织的孱弱,更易遭受公权力的侵害。因此,通过赋予学生申诉权实现对学生权利的救济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迫切。
(三)学生申诉权契合我国文化传统和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
学生申诉权不同于诉讼权,其存在更为契合我国的文化传统和高校学生管理的实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学生在老师面前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实践中,每有学生在校受到处分或者人身伤害,即便学校并无过错,学生父母仍能理直气壮地缠讼闹访。其理由主要在于,学生表现不佳有学校管束不力、教导无方的原因,正所谓“教不严,师之过”。此等观念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从构词上看,“师父”一词置老师与父亲于同等的地位,至今民间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而在古时中国,父权是与君权、夫权并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父者一度甚至有对子女生杀予夺之权。为人师者既然有堪比人父的权力与权威,自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学生的是非荣辱老师均脱不了干系。数千年的文化浸淫已将传统的师生之道浸入中国人的骨髓,舶自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恐难彻底荡涤之。
在家长面前,学生也难称得上具有独立的地位。在家长看来,高校有义务将学生的平时表现及时告知,以便其能及时采取措施教育学生,实现家校共育。尽管高校学生绝大多数都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家长的知情权和相关要求权并没有法律依据,但一旦学生的权利受到校方的限制,家长仍能底气十足地与学校交涉。这是因为在很多家长看来,学生尚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作为家长仍享有事实上的知情权及相关权利。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往往要对家长的诉求给予一定的呼应。在处理一些涉及学生重要权利如受教育权、人身权的事务时,多将家长知情、参与乃至同意作为必需的一环。在诸多日常学生事务的处理中,如办理助学贷款、学生校外住宿等,也要求必须有家长的同意或参与。
不仅如此,在社会上甚或在一些国家机关面前,也存在忽视学生独立主体地位的情形。实践中,每有涉及高校学生的违法案件,只要事不严重,一些公安机关倾向于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让高校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亦规定,行为人致人损害时年满十八周岁的,应当由本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经济收入的,由抚养人垫付,垫付有困难的,也可以判决或者调解延期给付。
既然在传统的文化语境和现实的生活实践中学生没有被作为一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自然也难以充分享有相应的权利。因此在日常高校管理中,校方自行打开宿舍房间检查卫生、没收危险物品,或者将学生的成绩单邮寄给家长的情况并不罕见。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行为一概定性为高校权力的扩张或者滥用,高校自身亦未必愿意为之,但是若用现代法治话语体系去度量校方扮演的家长角色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已经逾越了法律的界限。在此背景下,一味套用现代法治话语,单纯强调诉讼意识,未必能换来我们期待的善治,而通过申诉机制,将法理与情理糅合,灵活解决争议,更能契合高校管理的现实。
三、学生申诉权的保障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种重要基本权利,学生申诉权的保障既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也有迫切的现实需求。但实践中,学生遇到权利侵害之情形,往往并不寻求申诉救济,而是诉诸信访这一非正式的救济渠道。纪检监察、信访②等渠道在事实上受理了大部分的本应属于学生申诉的案件,导致学生申诉权的落空。以某驻京高校为例,该校自2011年至2015年期间,信访与监察部门受理的具有申诉性质的信访案件年均20余件,但在此期间未举行过一次申诉会议。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复杂,既有学生申诉制度自身的原因,又有制度之外以及权利文化观念的影响。从学生申诉权保障的视角看,当前应主要从完善学生申诉机制、健全学生权力组织、弘扬权利文化观念等方面促进高校学生申诉权的实现。
(一)完善学生申诉机制
首先要明确申诉范围。《规定》的最新修订内容从形式上扩大了学生申诉的范围,但相关概念有待进一步明确。原《规定》第五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此处表明学生对学校的“处分与处理”有异议,可以提起申诉,但第六十条在规定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受理范围时,却限定为“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将学生申诉范围限定在涉及学生身份变化的处理和处分。《规定》修订后在关于学生申诉范围与申诉委员会的受理范围上实现了统一,均为“学校的处理或者处分”,并将“处理”置于“处分”之前。这意味着学生申诉的范围扩大,但“处理”的具体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我们认为,学生申诉作为高校内部的自我纠偏机制,没有必要对其受理范围作出限制。换言之,只要学生认为学校的惩处决定、管理措施或者其他决议有违法或不当之处,且可能致其权益受损的,学生均有权提起申诉。这既符合《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的立法本意,能够充分保障学生的申诉权,也有利于学生申诉制度的有效利用。不过在扩大申诉范围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学术争议和非学术争议,并建立相应的争议处理规则。
其次要细化申诉规则。申诉的受理者行使的是一种裁判权,裁判权的有效行使需要必要的仪式、规则,以建立并维护裁判者的责任感、荣誉感,增强申诉人的信任感。从对申诉处理过程的观察看,我们认为有必要借鉴仲裁、诉讼的某些庭审规则,以增强申诉裁判的公信力。具体应从以下两方面改进校内申诉评议会议规则:首先,在座位的安排上,要将评议人与申诉人、被申诉人相区分,尤其是与被申诉人相区分。实践中,申诉会议举行时,参与人往往依据其职位高低依次落座,而其中的被申诉人往往是校内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其座位往往尊于大部分的申诉评议者,这种潜在的地位压力不仅会对评议者构成干扰,亦会让申诉人质疑申诉的公正性,最终有损申诉机制的公信力。其次,在评议的流程上,亦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则,如控辩流程要清晰,会议记录应详细等。这些内容对被申诉人的权利保障十分必要,可以避免使申诉裁判沦为对申诉人的会审。
第三要健全申诉组织。根据《规定》的最新修订内容,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相关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负责法律事务的相关机构负责人等组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聘请校外法律、教育等方面专家参加。在申诉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上,《规定》在修订稿中强调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如何完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的构成,以提高其独立性与决策科学性,依然是没有完全解决的突出问题。除学界已有的建议外③,申诉委员会的完善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校内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尤其是有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比例。目前,作出对学生不利决定的校内主体主要为行政管理部门,在校内多元利益群体中,其他校内行政部门与作出处理决定的部门处于同一个文化场域之中,彼此间有着纷繁复杂的利益关联,为提高相关人员的中立性、客观性,有必要限制校内管理人员在学生申诉委员会中的比例。
另一方面,应考虑吸收德高望重的退休人员参加。如前文所述,申诉的处理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其不仅仅依据法律法规及校内制度等正式规定,还揉进情理、道德等诸多柔性规则,在对后者的把握上,退休人员往往有着更大的优势:首先,处理申诉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退休人员有丰富的校内工作经历,容易把握其中的分寸;其次,退休人员已经不在工作场域之中,较少受到人际关系的拘束,有着更高的独立性;再次,很多退休人员时间精力都很充足,有意愿参与其中,并且申诉过程中与学生的思想沟通以及与行政部门的协调往往更为有效。因此,在申诉委员会的构成上,在增加法律人士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发挥退休人员的作用。这样更契合中国的文化背景,亦更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第四要引入申诉追责。学生权利的被漠视,不能仅归咎于制度的缺位,更有制度的阻塞——已有的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校内职能部门授权的模糊性及职责的交叉性等为其推诿敷衍创造了条件,而校内干部人事评价体系缺乏学生群体的参与亦加重了这一情形。高校学生申诉制度中,被申诉人与申诉的裁决者是“铁打的营盘”,彼此要长时间地相处,若无有效的追责机制,面对与自己并无利益关联的学生,裁决者是否有动力去为“流水的兵”——学生伸张正义,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引入申诉追责,一方面,对于那些确有瑕疵的被申诉者,应有必要的惩戒,在职称评定、人事任免、绩效考核等方面要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负有受理申诉职责的部门和个人,若有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的,亦要进行追责。
(二)健全学生权力组织
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是推动和完善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配套工程,其实质是建构能够应对“冲突和多元利益”需要的决策权结构。[7]目前的大学治理中,校内的利益相关主体至少包括教师、管理人员及学生。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目前大多有着自己的利益表达渠道——如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等,尽管其运行现状距离预期可能还有距离;但就学生群体而言,其利益表达机制还严重欠缺,学生尚未对学校的有关管理决策形成有效的压力机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结构,需要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目前,关于高校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的定位与设计还缺乏应有的重视。就保障包括申诉权在内的学生权利而言,学生代表大会不仅必要而且必需。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助于从源头上保障学生申诉权。在校内有关学生权益的制度建设方面,要将学代会的参与和同意作为必须环节。这样有助于在制度设计之初便在其中明示学生的申诉权,对学生形成一个明确的权利提示,对管理部门则是一个权力警示。
另一方面,对校内管理形成压力,使其谨慎用权。在校内有关学生权益的制度施行中,应赋予学生质询权。其质询权既包括对普遍性问题的质疑,亦包括学生个体的申诉,有关部门必须限时回复,且学代会若有异议可要求学校最高决策机构予以复议。在一定程度上,学代会的质询权可以视为学生申诉权的集中行使。比之于申诉,质询的方式更易得到重视。
为达至上述目的,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加强学代会的立法。可借鉴《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第32号令)的形式,以教育部命令的方式发布“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大会规定”,在其中明确学代会的职权、组织规则与工作机制等,赋予学生申诉权更强有力的外部保障。
(三)弘扬权利文化观念
毋庸讳言,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权保障观念的薄弱是学生申诉权得不到保障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充分弘扬权利文化观念,努力促进权利文化观念的养成——这比制度的设计更为艰难、更为重要。
弘扬权利文化观念在高校与学生身上分别有不同的体现与要求。就学生而言,要加强自身的公民意识培养。公民意识是法治的内生性信仰,具体包括护法精神、权利主张精神、义务的自觉履行精神[8]。为此,学生需要摒弃传统的厌讼观念,将申诉视为维护自身权益、促进学校法治的正义之举,而非制造事端。就高校而言,在日常管理中,应秉承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尊重权利,敬畏权利,在面对学生申诉时,应依法认真对待,不以其他非正式的手段和方式去干扰学生申诉权的行使。高校应将校内的申诉渠道、方式予以充分的明示,不仅方便学生行使权利,也在宣传一种权利本位的价值理念,涵养法治秩序的文化氛围。这种价值理念与文化氛围的养成对于我们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校园是至为关键的。
注释
①2005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正在修订。教育部于2015年底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修订对照表,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部属高校征求意见。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将于2017年初正式颁布。
②实践中,信访通常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书信的方式向受理机关反映问题;一种是到信访办公室或其他有信访接待任务的领导处反映问题(《教育信访条例》规定,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信访接待日制度。目前国内高校也大多参照此规定建立了学校领导接待日制度)。
③具体可参见:尹力,黄传慧.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J].高教探索,2006(3);湛中乐.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研究(下)[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6);尹晓敏.论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功能的失落与复归[J].高等教育研究,2009(3)。
[1]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2]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形态[J].法学研究,1991(4).
[3]陈久奎,阮李全.学生申诉权研究[J].教育研究,2007(6).
[4]茅铭晨.论宪法申诉权的落实和发展[J].现代法学,2002(12).
[5]范愉.申诉机制的救济功能与信访制度改革[J].中国法学,2014(4).
[6]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6).
[7]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J].教育研究,2009(6).
[8]马长山.公民意识: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J].法学研究,1996,18(6).
Research on Student's Right to Appeal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EN Su-ping,SHISan-jun
(School of Educ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Student's right to appeal is a specific form of right to appeal provided by the Constitution.Its existence is not only based on a solid legal rationale,but also more adapted 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tudentmanagement pract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To guarantee student's right to appeal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student's appeal system by scope expansion,regulation refinement,organizational enhancem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ccountability,to develop student organizations, and tonurture a culture of rights.
Student's Right to Appeal;Guarantee of Right;Student's Appeal System
2017-01-09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高等教育法制的国际比较与最新发展”(10XNJ068)
申素平,河南濮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书记兼副院长,教育学博士,从事教育法律与政策研究;史三军,江苏宿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教育法律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