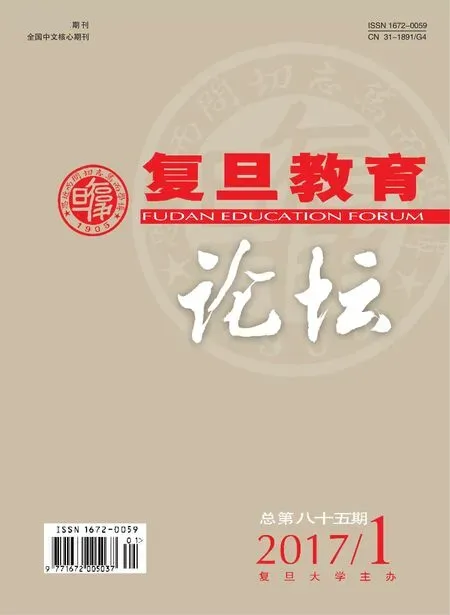良法善治须加力
庆年
·评论·
良法善治须加力
庆年
又到除旧迎新时。媒体上,形形色色的年度“回顾”“盘点”“十大……”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回首过去,瞻望未来,为的是探寻新一年的进路。然而,观者身份不同,视角各异,尺度不一,所见未必相同。从高等教育治理的角度看,笔者以为,2016年最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开始施行;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三是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章程全部完成核准。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法治应包括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如今,其精神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中央的文件写得明明白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在确立良法之治。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同理,于是有《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之议。虽然历经三年,且分两次获得通过,但是“靴子落地”终成现实,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事实上,中国教育法治正在不断推进,若干关键问题成为教育法制的重要议题,有了新的突破。比如,人们十分关心的学术权力在高等学校的地位问题,已经越来越明了。也许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教育部201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高校学术权力的规范性文件。它的颁布和实施,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要件,为高等学校治理结构优化作了方向性的指引,对于正本清源,使高校运行真正回归学术共同体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学术委员会在高校的地位和职责,把学术权力的规定性上升为法律,成为国家的意志。可以这么说,学术委员会制度的法制规范形成,是中国高等教育法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良法与善治都不会自动到来,也不会一下子形成,肯定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这一过程可能很漫长,因为我们缺乏法治的基础和文化。大学章程建设的情况很能说明这一点。1995年教育部提出了制订大学章程的要求,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但是应者寥寥。到2010年,制订了大学章程的公办高校不过二三十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制订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提出,教育部明确了要求和进程,发布了数个规范文件,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大学章程建设才得以加速。2016年,大学章程核准工作终于完成。从无章可循到建章立志,无疑是教育法治的一大进步,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不过,又不能夸大其意义。抽样调查表明,高校师生参与大学章程制订的程度普遍不高,大学章程文本宣示性强而可诉性弱,外部治理关系不明确,内部权力规范程度不高,反映各高校个性特点不够,章程实施、监督、修订体制不健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很显然,大学章程核准任务的完成,并不是大学章程建设的终点,而是大学章程建设的入轨。构建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才刚刚迈出第一步。提高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能力和水平,还有许多坎要跨过去。
良法善治是中国高等教育腾飞的基础,值得我们锲而不舍地付出努力。本刊今年辟教育法治专栏,冀各方贤能不吝惠赐,为加快中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贡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