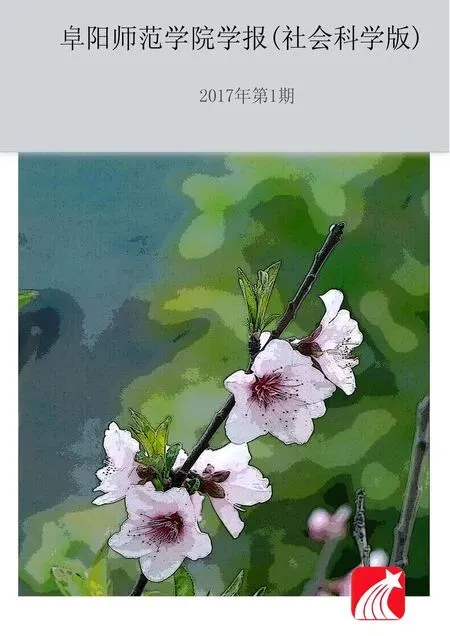《第六病室》: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标识
张 蕾,徐曼琳
《第六病室》: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标识
张 蕾,徐曼琳*
(四川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重庆 400031)
契诃夫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大师,他最终树立了以短篇小说表现复杂社会生活现象和重大主题的卓越典范。契诃夫小说作品创作内容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886年以前,以笔名契洪特发表了一些滑稽作品活跃在幽默刊物上;1886年之后,契诃夫开始发表一系列严肃作品,更加关注社会政治,在后期的作品中他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深深地触动了读者的心灵。创作内容是创作思想的外衣,内容的变化植根于思想的变化,契诃夫创作思想的革新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中逐渐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而《第六病室》正是其思想革新心路历程中的标识。
《第六病室》;契诃夫;思想革新;标识
安东·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作家之一,他树立了以短篇小说表现复杂社会生活现象和重大主题的卓越典范。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作幽默小品;80年代末,他的作品反映生活更广,主题挖掘更深,批判力量显著加强;从90年代起,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日趋激进,反映到其作品中,就是抗议现存社会秩序、渴望新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笔锋更加深沉道劲。通过系列作品展示了其创作思想的演进过程,其中,小说《第六病室》是体现其创作思想革新的重要标识。
一、契诃夫的生活境遇与创作阶段演变
1860年契诃夫出生于俄国南方的塔甘罗格市,父亲经营着一个杂货铺。契诃夫的父亲对东正教十分虔诚甚至于狂热,这对契诃夫后来萌生悲天悯人的情怀产生了很深影响。1868年契诃夫进入塔甘罗格中学学习,中学时期是契诃夫个性和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他自此对书籍、知识等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时,使用笔名“契洪特”向幽默刊物投稿滑稽作品,自此拉开文学创作生涯的帷幕。1879年契诃夫中学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1]。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1880年。19世纪80年代,正是沙皇专制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反动势力猖獗,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缺乏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由于通过发表滑稽作品可以获得一定的稿酬,保障自己的生活所需,这使得作家在早期惊人地多产,契诃夫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1880年3月,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发表于《红蜻蜓》,这是作家的处女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大量滑稽小品奔涌而至,到1884年,他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梅尔柏密尼的故事》。
如果契诃夫只是写滑稽小品这类作品的话,那就只能成为类似于戏台上插科打诨、引人发笑的小丑角色,而不可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有所作为。但事实上,他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契诃夫能从最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看到社会弊端,启迪人们思考重大社会问题,在那些看似平淡、不动声色、似乎信手拈来的素材中,却融入了他炽烈的热情与深沉的思考。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生活中的片段,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的描绘与刻画,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会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体现深沉的创作主题,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2]。他的短篇小说行文淳朴、确切而极富表现力。善于描写对象的突出特征,几笔便勾勒出生动逼真的形象,很少使用精雕细琢的手法,但作品的每个细节都经过周密构思,高度提炼,形成了感人的艺术力量[3]。
托尔斯泰曾将契诃夫与普希金并列,认为他像普希金一样,以简洁、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方式在俄罗斯文学中“把形式向前推进了一步”[4]。契诃夫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俄国经典文学的传统,这一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果戈理的《外套》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沿袭下来的,都描写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给予无限同情。在契诃夫的很多小说中,都可以发现这样的小人物,如在《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公务员,《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苦恼》中的马车夫等。作家以幽默讽刺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的遭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对于这些“小人物”的态度具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他使我们看到人的尊严是如何被践踏于金钱和权力之下。总的来说,契诃夫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是位忧国忧民的作家。伍尔夫认为,人的心灵和灵魂是契诃夫很多小说作品所着重描写的方面,“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5]。可见,契诃夫对人的描写深入到了内心世界。
随着俄国革命运动发展趋向高潮,在他的作品中,增强了乐观主义的格调,那些标识契诃夫艺术成就的著名短篇小说,如《变色龙》《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姚内奇》《在流放中》《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等,都成为俄国文学中的杰作。的确,从很多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人物心理刻画的精湛技巧,要知道,想要让一个篇幅不长的文本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就必须要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契诃夫的很多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手法炉火纯青。毋庸置疑,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诸多成就使得他与莫泊桑、欧·亨利一起获得“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的美誉。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创作道路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1886年以前,活跃在当年的幽默刊物上的契洪特,一直到1886年,契洪特才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为契诃夫所代替(1880-1886);其二,从1886年起一直到1892年写出《第六病室》为止,这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第二阶段(1886-1892);其三,从作品《第六病室》之后,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民主性色彩更加强烈。
在契诃夫文学创作的晚期(1892-1903),很多作品对黑暗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入,思想更加深刻,让人不禁感叹他的确是19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级别的人物。创作内容是创作思想的外衣,与作家的生活经历、选择作品内容更改过程相对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契诃夫的创作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本文主要探究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从第一阶段发展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创作思想革新在其代表作品中的典型体现及显著标识。
二、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动力探因
契诃夫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文学天才分不开,也与他勤奋多写积累的技巧经验分不开。当我们探究他的文学创作从第一阶段发展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原因时,发现除了文学创作的技巧有所提升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演进,这可以找到清晰线索,小说《第六病室》是其创作思想革新的重要标识。一般研究契诃夫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从小说《第六病室》起,契诃夫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揭露程度明显加强,作品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统治,表现出当时人民备受压迫、历尽煎熬的情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角色——拉京医生和病人格罗莫夫的思想交锋是契诃夫自己当时思想中矛盾交织的外化。从中发现在契诃夫其他作品中难以觅见的思想冲撞,这是其创作思想乃至选择题材转变轨迹的化身[6]74。推动契诃夫创作思想发生革新的原因和动力多种多样,笔者打算从精神和现实两方面着手分析。
(一)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精神动力
1884-1886年,契诃夫以“微型小说家”的身份活跃在俄罗斯文坛上,很多小说充满幽默感,但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多是饭后消遣娱乐的谈资。他自己承认,有时一天就能写一篇小说,可见并未严肃地对待创作,没有意识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道理。虽然如此,但随着搜集创作素材的扩展,他将视线转向了劳动者的困苦生活一面,他的创作主题渗透到了忧民的领域,《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思想、艺术的一次飞跃;《万卡》是《苦恼》的姐妹篇;还有与它们相近的短篇小说《瞌睡》等。正是这一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随年龄的增长、眼界的开阔、声誉的鹊起,慢慢地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逐渐成长为后来严肃而深沉的契诃夫。
就在1886年,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格利果罗维契写信给契诃夫,称赞他“从艺术的视角来看,你具有真正的文学创作天才”[7]43,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指责他将才华浪费在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上,而没有肩负作家的使命,浪费了创作精力;希望他能充分发挥天赋,运用自己的才华创作出更多有意义的作品来。老作家的鼓励与训斥,对当时正处于苦闷彷徨中的契诃夫来说,犹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具有发聋振聩、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文学家如柯罗连科等也规劝他珍惜自己的才华。契诃夫深受启发,认真思考一个作家所应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感,对待文学创作也更加严肃了,而不仅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的消遣、也适合于苦闷中的别人消遣的需要。这一年,契诃夫写出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1887年发表了《伤寒》《吻》《婚礼》等一系列思想深刻的优秀小说。
1888年,契诃夫获得了普希金奖金。此时他在俄国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日益增高,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在这一年他更为经常地在自己的书信中流露对周围现实的不满情绪。他指出:“俄国人民贫穷和饥饿,令人遗憾。”[8]261目睹这“不堪忍受的生活”场景,契诃夫感到“苦闷和忧郁”[9]247。可见,他对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感到十分不满,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为痛惜,在思想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契诃夫的思想探索再次陷入困境。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的心情,第一次拜见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托翁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谦虚可爱的人”,两人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契诃夫甚至在1900年的书信中写道,他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契诃夫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洞……契诃夫还说,他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托尔斯泰的信仰最让他感到亲切……总之,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托尔斯泰主义使契诃夫深受影响。契诃夫在写给苏沃林的一封信中承认,托尔斯泰主义曾给他以巨大的影响。
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中有深刻的体现,它主要指的是托尔斯泰对现实的无情批判,积极地宣扬悔罪、拯救灵魂、禁欲主义、“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观点。诚然,托尔斯泰主义是契诃夫精神探索的重要结果,有其合理成分:托翁对沙皇俄国时代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对人的道德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人能够完善自己的道德,展示出人性中温顺的一面,不以暴力来对抗恶势力,它的核心是爱的原则;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局限性,托尔斯泰主义太过理想化,其基本面是空想的,与时代脱节,不切实际。
关于托尔斯泰主义,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人民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9]。契诃夫为了给自己的世界观寻找一个支柱,曾一度称赞过托尔斯泰主义,他说:“托尔斯泰哲学强烈地感动过我,有六、七年的功夫它占据了我的心。”[11]126当时,他意识到自己缺乏明确的世界观来指导创作,因此陷入了彷徨。契诃夫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总的观念”来指引自己,为此苦苦探索着,这反映在《乞丐》《鞋匠的魔鬼》等小说中[11]463。
但此后,当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契诃夫深入思考人民的痛苦及其来源时,逐渐地对托尔斯泰主义产生了怀疑。他开始思考如何使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唤醒人民的觉悟,这突出体现于小说《第六病室》《在流放中》等作品中。以此,他开始谴责托尔斯泰主义,这说明契诃夫已经摆脱了它的影响。当我们深入探寻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原因时会发现,为期三个多月的库页岛之行对契诃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其创作思想革新的现实动力。
(二)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现实动力
19世纪80年代的库页岛成为沙皇俄国囚禁成千上万苦役犯、流放犯之地,无论是从地理环境还是从气候等各方面条件来看,这里都极为艰苦,常人很难在此生存下去。1890年契诃夫从莫斯科来到库页岛,进行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他目睹了沙皇专制下的社会生活:犯人没有自由,戴着镣铐,过着非人的生活。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在岛上的所见所闻所感:“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库页岛)简直是一座地狱。”[8]26库页岛之行意义重大,如果说在去库页岛之前,作家还处于迷茫苦闷的状态,在创作思想方面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突破口的话,那么经历这次考察的触动,对专制统治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解,思想面貌焕然一新。此前,契诃夫从来没有想到在俄国的大地上,竟然还会有这般黑暗的地方。此后,从契诃夫所写的信中我们看出他内心所有的震撼:“在过了库页岛的艰辛生活之后,我现在觉得,我在莫斯科的生活是如此地庸俗和枯燥,我简直要咬人了。”[8]26以这次考察素材为基础,契诃夫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库页岛旅行记》,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详细地记录下来,深刻揭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深深地触动了读者的心灵。由此可以看出其创作思想经受了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般的洗礼。
可以说,库页岛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是沙皇专制统治的黑暗最为集中之地,具有“滴水观海,一叶知秋”的作用。库页岛之行加深了契诃夫对当时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认识,提升了思想境界。他在1891年明确表示:“……如果说我是个文学家,我就要生活在人民中间,哪怕是一点点社会政治生活也是好的。”[12]由此可知,契诃夫已经从那个不关心政事、靠幽默作品讽刺社会现实的作家转向深刻揭露专制制度的作家。同年,契诃夫创作并发表了中篇小说《决斗》,这部作品的意义重大,它是文学史上第一部向托尔斯泰的“勿抗恶”进行挑战的作品,表明契诃夫从库页岛回来之后思想上的诸多转变,他开始否定之前所认同的托尔斯泰主义。
此后,契诃夫明确表示说:“托尔斯泰的教义不再感动我了,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对它抱着反感……”[16]231可以看出,契诃夫逐渐摆脱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影响,这在文学创作方面主要表现在他于1892年所创作的小说《第六病室》《在流放中》中。契诃夫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以及看破红尘的悲观主义。尤其是在《第六病室》中,作家表现的是重大社会课题,对人物的语言及心理刻画栩栩如生,思想异常深刻,难怪列宁在看了之后“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也好像被关在六号病房里了”[11]462。通过分析《第六病室》,我们会了解到契诃夫创作思想是如何渗透其中的,并发现其思想革新的关节点及其化身,因此,《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显著标识。
三、小说《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显著标识
《第六病室》的主人公是拉京医生。他是清白、正直的知识分子,信仰“内心平静”和“勿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每天喝喝啤酒,看看闲书,与世无争。当他结识了被贴上“疯子”标签的病室中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后,对自己的信仰开始发生动摇。这是因为,格罗莫夫在与拉京的激烈辩论中指出,禁欲主义、寻求“内心的平静”这一套,不过是“托钵僧精神,浑浑噩噩的麻木”!拉京在自得其乐无所作为的时候,却享有高俸,过着悠悠然、近乎随心所欲的生活;但是,当他有所觉醒时,却失去了自由,被当作“疯子”被关进了第六病室,遭到看门人的毒打,第二天就悄然死去。在临终之前,拉京终于用嘎哑的声音喊出:“不许人思考,不准有思想,不经审判就剥夺人的自由,正义、法律与人权在哪儿?”[11]463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正是契诃夫与托尔斯泰主义决裂的最佳见证,是他创作思想革新的显著标识。
(一)拉京和格罗莫夫的角色设置折射契诃夫创造思想的革新
《第六病室》的问世标志着契诃夫在创作思想和表现创作思想的艺术手法方面臻于成熟。契诃夫通过描写一所精神病院病室里的种种弊病,猛烈地抨击了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人,特别是爱独立思考、有见解的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诬陷,或者可能被当作“疯子”关进“监狱”似的第六病室。而其他人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像一具具“行走着的尸体”,然而,这种人却生活得好,他们对那些稍有反抗精神的人不断排挤,想让后者与自己一样地臣服于专制制度。在《第六病室》中,拉京医生和病人格罗莫夫是两个典型人物,契诃夫把作为“疯子”和作为“有头脑的”格罗莫夫金针度线、巧妙穿插,恰到好处地安排他们争论,妙手织就、衔接自然。读罢全文,掩卷思索,两人看似荒诞的对话却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契诃夫创作思想的革新。
二人有话可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虽然存在分歧,却有很多共鸣处。拉京说:“问题在于您跟我都在思考,我们看出彼此都善于思考和推理,那么不管我们的见解多么不同,这却把我们联系起来了。”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热爱书籍,拉京“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而格罗莫夫也看过很多书,“他老是坐在俱乐部里,兴奋地扯着稀疏的胡子,翻着杂志和书籍”,他们有学问、有思想,不幸的是,处于专制社会现实生活的“万马齐喑”之中。他们都想找人通过表达,排解心中的愤懑、不满,以此获得共鸣,这是人之常情。
格罗莫夫是沙皇制度的牺牲品,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儿,被社会的黑暗刺痛了神经,害有强烈的被害幻想症。他说:“既然社会认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适当的必要手段,各种仁慈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会引起沸沸扬扬的不满和报复情绪,那么,联想到正义不可笑吗?”可见,他完全看透了社会的本质,“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然而,就算是被沙皇制度迫害至此的人,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讲到人的卑鄙,讲到蹂躏真理的暴力,讲到将来终有一天会在地球上出现的灿烂生活。”从格罗莫夫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智慧,他那进步的思想,但这样的人却要经历牢狱之灾,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个黑白颠倒的社会!
而作为“健康人”的拉京医生则代表了另一类人的形象。从一开始对他的介绍中我们就隐约地感到,如“他的脚步轻,走起路来小心谨慎,蹑手蹑脚。要是他在一个窄过道里碰见了谁,他总是先站住让路,说一声‘对不起!’”。在对他管理医院的一系列细节的描写中,我们更能看出拉京软弱无能的特点,他认为“人们既然开办了一个医院,容许它存在下去,可见他们是需要它的。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所以起初工作认真勤快,后来,发现在这个医院里偷窃、徇私、诽谤等恶习泛滥,而治病不过是庸医们借以骗人的假象。于是心灰意懒,不再天天去医院,即使去的话,也不过是治五、六个病人(以前一般治五十个病人)。在家中,他就把时间消磨在书上,“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啤酒,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腌渍苹果”。
在契诃夫创作《第六病室》的意蕴中,拉京的种种行为都体现了契诃夫早期所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即鼓吹放弃斗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从而要求人们对一切采取漠视的态度。当然,这种无聊的生活,拉京有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欺骗老百姓”,为此他时时感到良心不安,但又总用“我无能为力”的想法来麻醉自己,开脱自己。契诃夫将自己早期的这种与世妥协的思想赋予给了拉京这个角色,这也体现在他早期的创作之中,他总是写一些与社会政治关系不大的幽默小品文,内容平庸,对社会生活不闻不问。相比之下,格罗莫夫的思想积极,虽然他被周围的人视为“疯子”,但却敢于说出现实的真相,他把社会的本质看得一清二楚,正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主人公之口揭示了当时社会“吃人”的性质,实际上就是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病。在契诃夫后期的作品中,创作的思想逐渐深刻,他对社会制度的黑暗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二)主人公对话中的思想交锋是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显著标识
医生拉京和病人格罗莫夫谈话的思想交锋是契诃夫创作思想演变的一面镜子;通过谈话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创作思想的演进。起初,拉京设法劝服格罗莫夫,让他冷静下来,“社会在防范罪人、精神病人和一般不稳当的人的时候,总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剩下来您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心平气和地认定您待在这个地方是不可避免的”。这正体现了契诃夫早期所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即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摆脱罪恶,鼓吹“勿以暴力抗恶”,对现实中的一切好的坏的都予以接受。在作家的创作思想方面就表现在他一直心平气和地进行幽默性的创作,作品中并没有过多掺杂社会上的政治事件等重大主题。
对于拉京的这种劝说,格罗莫夫表示毫不赞同。拉京认为“人的恬静和满足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他认为应该蔑视痛苦,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对于拉京这一明显具有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格罗莫夫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说:“人的机体组织如果是有生命的,对一切刺激就一定有反应。我就有反应!受到痛苦,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见肮脏,我就憎恶。依我看来,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做生活。”在这里,格罗莫夫通过自己的这一番话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对拉京所说的话针锋相对地反驳,最后甚至连拉京也说道“您讲起道理来很出色”。格罗莫夫的这种反抗精神,正体现了契诃夫在创作思想上的革新,即应该对外界的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要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弊病进行揭露,进行大胆的反抗。
后来,格罗莫夫甚至批评拉京的懒汉哲学,因为拉京“二十多年一直住着不花钱的房子,有炉子,有灯火,有仆人,同时您有权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哪怕一点事不做。如果用房门把拉京您的手指头夹一下,恐怕就要撤着嗓门大叫起来了!”在拉京被关到第六病室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以前我满不在乎,活泼清醒地思考着,可是生活刚刚粗暴地碰了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泄气了……我们软弱啊,我们不中用……”这正如格罗莫夫一贯所说的,拉京在这之前没有经历过生活中的痛苦,没有体会到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而是自娱自乐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对周围的黑暗现象熟视无睹、漠不关心。但后来关在第六病室中的拉京亲身体验到了这种痛苦,意识到用软弱的、漠视一切的托尔斯泰主义来对待生活是完全不可行的。
契诃夫早年学医,一直以“业余文学家”的身份进行创作,这段经历却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与医学有着不解之缘。而契诃夫以职业医生的敏锐透视生活,其作品被称为“生活的切片”。如果我们对照《第六病室》中的主人公拉京的职业和他的处世态度,就会发现拉京竟与1886年以前的契诃夫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孤独、骄傲、不屑与平庸为伍,信奉托尔斯泰主义[6]75。换言之,拉京其实就是早期的契诃夫的化身,只不过作为鲜明的文学形象,拉京这个角色在各个方面表现得更极端罢了。
在《第六病室》中,契诃夫常以旁白穿插自己的思想观点,在谈到关于“为什么人类不会长生不死”话题时,契诃夫认为“这是新陈代谢啊!可是用这种代替不朽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这是多么懦弱啊!”可见契诃夫当时已经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局限性。而“疯子”格罗莫夫的思想正体现了转变后的契诃夫自己的思想,只有他才是这个社会真正清醒的人。“第六病室”就是当时黑暗的沙皇社会的缩影,置身其中,作家仿佛也在备受煎熬,特别是库页岛之行以后,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契诃夫也难以保持早期内心的平静,不再对社会政治不闻不问,而是写出大量与社会政治有关的作品,担负起严肃的社会责任。他写道:“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10]35
主人公间的思想交锋实际上外化了契诃夫思想交织、冲撞、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将思想转变前后的自己分别赋予医生拉京和病人格罗莫夫这两个角色,他以第六病室作背景,描写两人之间的争论,涉及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交锋,标识着契诃夫新旧世界观的冲撞。而最终的结果是拉京不由自主地被格罗莫夫的深刻思想所折服,认同格罗莫夫的一些观点。正因如此,拉京也“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空气,杂役、助理护士、病人,一碰见他就追根究底地瞧他,然后交头接耳地说话”,大家都以为他疯了。殊不知,正是谈话使得拉京的思想变得“正常”和积极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围的人却生活在受压迫和谎言之中,丝毫未察觉。当拉京被关在第六病室后,终于亲身体会到了格罗莫夫的痛苦,虽然内心仍然用那套托尔斯泰主义来安慰自己,但内心已经难以保持平静,他跳了起来,想要用尽全力打死将他关起来的那些人。
虽然拉京的这种抗争念头转瞬即逝,但仍有着深刻的意义:拉京原来信奉的“勿抗恶哲学”失灵了,他不再安于现状,而是希望进行反抗,与黑暗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遗憾的是,他反抗之愿未偿就离开人世。从契诃夫给主人公所设计的结局——拉京医生的死亡——来看,这是艺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完全符合现实生活逻辑。主人公拉京的死亡意味着契诃夫本人思想的彻底转变,与他早期所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真正决裂。由此,《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思想革新的重要标识。很多文学家、政治家读后都感慨万千。著名画家列宾读了《第六病室》后说的话生动地表明了它的社会影响,他说:“我惊愕,我神往,但我高兴,因为我尚未落到安得列·叶菲梅奇(即拉京)那种地步。”[7]119“第六病室”境域正是沙俄专制统治的缩影,契诃夫虽然难以完全漠视,但作为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肩负起了应有的责任,后期创作出一系列抨击沙皇专制制度的作品,因此获得了伟大的荣誉。
结语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很多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契诃夫自身思想的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也可以从不同时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看出来,作家的创作思想也相应地在不断地发生革新。《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是他的创作思想革新的重要标识。从此以后,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契诃夫的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具有了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我们知道,很多作家的思想都体现在他笔下主人公的形象之中,有时,甚至通过他给角色所设定的背景、过程与结局,可以找到作家自己的思想缩影。所以通过《第六病室》中两位主人公的思想交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契诃夫创作思想的变化与革新。
说明:本文的研究以严纲、张韧、吴宗惠、白烨选编的《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01-461页的《第六病室》为底本,出自这里的内容,没有标注文献与页码。
[1]Кузичева А. П. Чеховы. Биография семьи. М.: «АРТ», 2004. — 472 стр.
[2]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5.
[3]张羽,陈燊.俄国短篇小说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382.
[4]刘文飞,陈方.俄国文化大花园[M].长沙: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75.
[5]李辰民.走进契诃夫的文学世界[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16.
[6]岳进.痛苦的自省——透过《第六病室》探寻契诃夫的思想冲撞[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23(12).
[7]朱逸森.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8]契诃夫.契诃夫全集:二十卷本:第14卷[M].莫斯科: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1944-1951.
[9]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70.
[10]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1]严纲,张韧,吴宗惠,白烨.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12]契诃夫·契诃夫文学书简[M].朱逸森,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194-195.
2016-11-15
张蕾(1993- )女,安徽合肥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生,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徐曼琳(1969- ),女,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系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1.17
I106
A
1004-4310(2017)01-0090-07
——巴金《第四病室》与契诃夫《第六病室》比较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