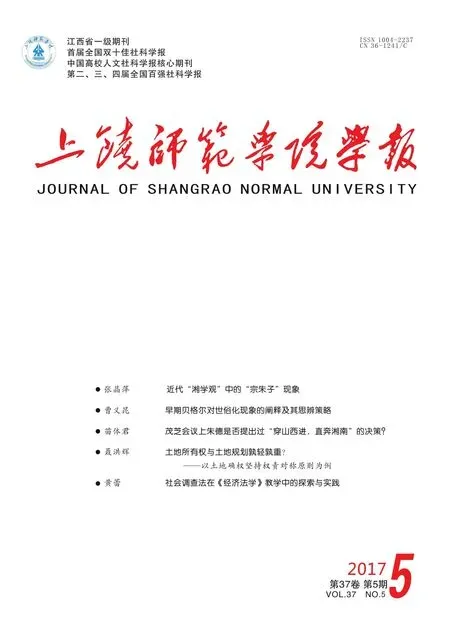近代“湘学观”中的“宗朱子”现象
张晶萍
近代“湘学观”中的“宗朱子”现象
张晶萍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从某种程度上看,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过程,就是恢复“朱张会讲”的历史记忆、将朱子学内化为兼具国家意义与地域意义的学术资源的过程。“朱张会讲”这一历史事件使岳麓书院成为“紫阳讲学之道场”,并于清代获得理学大本营的地位。晚清湘军的崛起塑造了湖南“理学之邦”的形象,强化了湘人对湖湘文化的历史记忆。维新运动前后,叶德辉提出“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借以维护儒学义理与儒学经传的信仰。民国时期,李肖聃重拾洛闽之绪,以“宗朱子”为标准,构建了一幅从宋至清的完整的湘学知识谱系。探讨近代地域学术文化观中的“宗朱子”现象,可以反观朱子在近代的命运和影响。
朱张会讲;历史记忆;朱子;湘学;近代
自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以后,士人论学无不以“宗朱子”为准则,以至于出现了“宁道周孔误,不言程朱非”的现象。然而,具体到各地,“宗朱子”的内涵与表现是不同的,特别是如何将朱子纳入到本土的知识谱系中来、内化为兼具国家意义与地域意义的学术资源,各地的具体路径不一。朱熹与湖南渊源甚深,“朱张会讲”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对于湖南而言,朱熹不仅是高高在上的官学人物,而且也是“过化存神”的地域先贤,其教化渗透到湖湘文化精神内部,是湖湘文化精神的有机构成部分。晚清以降,随着湖南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升、湖湘地域文化意识的强化,有关湖湘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叙述逐渐成熟,对朱子学与湖湘文化关系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在南宋“朱张讲学”的客观历史之外,还存在着近代以来对朱张讲学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既是客观历史的反映,更是记忆者主观愿望的投射,是历史与现实双向互动的反映。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诠释朱子学与湘学的关系、朱子学的内涵与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寄托文化理想。因此,以近代湘学观中的“宗朱子”现象作为视角,可以反观朱子学在近代的命运与影响。
南宋时期,由于朱张会讲、特别是朱熹对张栻的表彰,湖湘学派盛极一时。张栻去世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湖湘学派分崩离析,走向沉寂,朱张会讲的历史记忆也逐渐被淡忘。但湖湘学派的一些精神、理念,沉淀为湖湘文化的基本要素。晚清以降,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以“理学之邦”“忠义之邦”闻名于世,强化了湘人对地域学术文化的认同,也激活了湖湘文化的历史记忆,形成了对“朱张二子之垂教”的崇拜。从曾国藩、郭嵩焘等湘军将领,到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学人,都不断回溯湘学历史、总结湘学特色。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为了抵制康梁学说在湖南的流衍,叶德辉等人正本清源,维护湘学传统的纯洁性,提出了“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学术主张。此后,在追溯湖南地域文化精神的源流、趋向时,人们不断深化对朱子学与湖湘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的认识。发展到民国时期,李肖聃在叙述《湘学略》时,正式为朱子确立一个学案,将朱子学纳入了湘学知识谱系之中,并以“宗朱子”为标准,建立了一幅从宋至清末的完整湘学知识谱系。
一、从朱张记忆到理学传承
南宋以后,有关朱张会讲的历史记忆,主要依托历代岳麓书院建筑、祀典、院志而流传,在地方志中记载无多。康熙年间,长沙郡守赵宁重修岳麓书院,偏沅巡抚丁思孔“循故事,疏请院额经籍于朝”,被部臣以“通志载朱张讲学之事未详”为理由,搁置其议。礼部在回复之时称:“臣部移咨翰林院,查取湖广长沙府新志,书内止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作记,并未载有张栻朱熹讲学之处。志书系一处之志书,旧志内有张栻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该省所送翰林院新志又未载有张栻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1]请书额疏第二疏要求湖南地方官查明再议。为此,丁思孔等人“备考新旧志书、宋史及诸家文集所纪述,再疏申请”[1]新修岳麓书院志序,最终获康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及经史讲义。此事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在地方历史记忆中,朱张讲学并非不可或缺的历史事件;旧志有新志无,表明朱张讲学的历史正在被淡化。其二,在争取皇帝赐额的过程中,有关朱张讲学的历史记忆复活,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强化了岳麓书院作为理学重镇的地位;而新修书院志又凸显了朱张讲学这一标志性现象。无论是诸家序言,还是院志发凡体例,都将朱张讲学的历史叙述放在突出的位置。
如湖广总督徐国相在为康熙年间《新修岳麓书院志》作序时,称:“书院之创,则始于宋郡守朱洞。至南轩晦庵诸先生设皋比,横经于此,生徒日数千人,遂与嵩阳、白鹿并传。我皇上颁赐御书匾额经解讲义于其内,大道昭揭,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诸生匡坐嘉鼓箧,朝弦而夕诵之,于以阐洙泗之微言,发濂洛之奥义,其盛典也。……士之披览是书者,应不徒考其山川灵异,与夫名物器数,而欣欣然讲肄诵习,率循朱张二夫子之教训,以仰承圣朝菁莪棫朴之化。”[1]新修岳麓书院志序这里提到岳麓书院的关键事件有三,分别是长沙郡守朱洞创设书院、张栻朱熹讲学于此、康熙帝赐御书匾额。
又如,湖广布政使司黄性震在序中云:“自南轩晦庵两先贤讲道于斯,四方学者接踵而至,遂名闻天下,历元明来,代有迁流,而书院迄今不废,岂山川之灵欤?抑志书所传,使后之诵读者鉴古可以知、瞻前足以励后也。”[1]新修岳麓书院志序也将张栻朱熹讲学视为岳麓书院标志性事件。
又如,湖广提刑按察使司郑端在序中称:“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相与讲习于岳麓,而书院之名遂历久而弥著。至于为学之要,则周子主静、张子求仁、朱子居敬,入门虽别,而归宿则一。”[1]新修岳麓书院志序以为朱张讲学是岳麓书院之名“历久而弥著”的源泉所在。
又如长沙郡守赵宁在序中称:“考宋开宝九年,郡守朱洞始创书院;咸平间诏以国子监书赐正,至乾道元年,南轩张氏来主教事,而紫阳朱子访友星沙,聚徒讲学,一时弦诵彬彬,拟于洙泗。厥后盛衰递嬗,不能更仆。”[1]新修岳麓书院志序也是将朱张会讲视为岳麓书院形成“弦诵彬彬、拟于洙泗”气象的有力证据。
康熙年间《新修岳麓书院志》在凡例中强调:“书院自朱张绍述濂溪阐明性学,后之名臣硕儒遂多接踵。是书院实乘岳麓之灵,而岳麓又以书院显也。故兹编大旨崇重书院,以示高山仰止之意,非但具图经而资觞咏耳。”[1]凡例表明院志重在表彰书院的人文精神、借以传承朱张二子开创的学统。
在书院强化对朱张讲学的历史记忆之时,地方文献也加强了对朱张讲学的记载。以省志变化为例。清朝康熙、雍正年间两修《湖广通志》,均“北详而南略”[2]湖南通志序,对湖南的山川人物多有遗漏,屈原之忠谠、朱张之芳踪、元公道脉之流传、西山政教之遗泽,乃至地方官吏之善政良法,都未能在《湖广通志》中得到充分的记载。至乾隆年间,湖南修纂《湖南通志》,强调:“考人物而《骚》、《雅》竭忠爱之忱,《太极》启图书之秘。观典礼之明备,表节孝于幽微。朱张之讲学,可以尊闻而行知。真魏之政教,可以设诚而致行。韩柳欧李之文章,可以守先而待后。”[2]湖南通志序朱张讲学的历史记忆逐渐恢复,并成为湖南历史叙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当然,朱张讲学的历史叙事、朱子学之精神的传承,主要还是依赖于岳麓书院。乾隆八年(1743),皇帝为表彰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功绩,御赐“道南正脉”金匾。但细究“道南正脉”之含义,与其说是对张栻作为理学正宗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岳麓书院朱子学统的肯定。而书院也自觉地将朱子学统视为本院的文化资源,从李文炤到罗典等历任岳麓书院山长,皆“以洛闽正学陶铸弟子”。作为湖湘学术重镇,书院学风又影响到整个湖南的学术倾向,以至于当乾嘉汉学风靡全国之时,“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4]。颂扬朱子、崇奉理学成为湖湘学术的一大特色。
晚清湘军的崛起,一方面进一步塑造了湖南作为“理学之邦”“忠义之邦”的形象,另一方面则激活了对湖南理学传统的记忆与认同。曾国藩和其他湘军集团将领如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有研习理学的经历。曾国藩之问道,“始于从唐镜海先生游,因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诸公讲求义理之学也”;左宗棠之进德,“始于受贺蔗农先生之教,因读陆稼书、陈榕门之书,而尤心敬张杨园之说也”;胡林翼之建业,“始于家居读《礼》,因其父芸阁宫詹所著《弟子箴言》,而究穷于性理之学,故其后事业足传。而及其巡鄂,犹师事姚桂轩而日与讲论也”;罗泽南“秉义讲学,苦战殉军”;刘蓉、郭嵩焘等,“皆承洛闽之绪,而立名业”[5]300。湘军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理学迂腐无用的印象,提高了程朱之学的声誉。正如后人所言:“清代程朱之学,得湘人而益显,曾文正所谓大本内植、伟绩外充者也。”[5]300由晚清湘军向上倒溯,人们进而发现,早在南宋末年,湖南岳麓大社就涌现了一批以身殉国的志士。“考之往载,有闽洛大儒之垂教,而宋末大社诸贤以兴;有李(恒斋)罗(慎斋)诸贤之施范,而咸同戡定之英以出。虽群公遭时匪同,所树异轨,而其渐渍圣贤之训,以植事业之本,则若共出一涂,未始有标奇诡以制偏胜者。”[5]133诸人与湘军所遇不同、所成就事业不同,但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这种精神是理学熏陶培育的结果。这样,从宋末岳麓大社诸儒以身殉国到晚清湘军出任时艰,构成了一条以理学修身应世的意义链。湖南作为“理学之邦”“忠义之邦”,不但有现实支撑,更有历史记忆的复活。
理学熏陶源自何人?如果单纯地从岳麓书院的历史说,其源于朱张讲学,朱张二夫子垂教后世。然而,湘军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湖南人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负感,也使湘人产生了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化使命感,其学术观念也由地域学术观念上升到国家学术观念。当湘人以中国理学正宗甚至是儒家文化命脉所系的身份自居时,对朱张讲学的历史记忆简化为洛闽之教,地域性的张栻淡化,国家主流性的朱子凸显。此后,宗朱子既是部分湘人的学术宗旨,也是湘人追溯湘学历史、呼唤地域文化精神、编排知识谱系的标准。
二、从汉宋兼采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
晚清湖湘学风在崇奉理学的主流之外,也有汉宋兼采的支流。1833年,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和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协助下,仿效阮元学海堂模式,在岳麓书院内创办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以“奥衍总期探郑许,精微应并守朱张”为宗旨[6]。郑许代表了汉儒经学考据之学,朱张代表了宋儒天道性理之学,湘水校经堂将汉宋兼采作为自己的宗旨。湘水校经堂时断时续,分别在咸丰年间、光绪年间经历了几次重修。光绪年间,经学政张亨嘉奏请,校经书院获光绪皇帝御赐“通经致用”匾额一块,从此与岳麓书院分庭抗礼。湘水校经堂塑造了湖南在岳麓书院之外的又一种学术传统,培养了不少经学人才。两种学术传统,在晚清时期融合出了“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学术理念,其代表人物是叶德辉。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借助于公羊学说,宣传维新变法理论。随着梁启超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康梁学说在三湘大地传播,受到青年学子的热捧。为抵制康梁学说对湖南学术风气的破坏,以叶德辉、王先谦为代表的湘中守旧派摇唇鼓舌,攻驳辩难,正本清源,维护湘学的纯洁性。叶德辉以湘学代言人自居,打出了“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旗帜,以对抗康梁学说。
首先,叶德辉强调湘学以理学为传统。
他指出:
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而湘人乃笃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流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7]176
在叶德辉看来,湘学自有其优良传统,所重在于经世、在于对理学的崇奉;而湘中无知之徒,竟然依附康门表彰异学,对湘学来说,是丢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对于儒学来说,则是一种援儒入墨,自毁长城。他认为,正是因为湘中弟子不知向学、湘人不懂考据,故容易被康有为借考据形式所表达的“异端邪说”所迷惑,造成儒学信仰的动摇。叶德辉表示:“鄙人一日在湘,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有所不顾。”[7]177他认为,自觉地抵制异端邪说、维护湖湘忠义之邦的形象,是他作为一个湖南学者应有的自觉,“否则月旦乡评,交相讥刺,不目为耶氏之奴隶,或目为康党之门人,则鄙人将见外于乡人而终身不能言学矣”[7]179。叶德辉先后作《〈輏轩今语〉评》《正界篇》《〈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等文,从考据与义理两个层面批驳康有为的公羊学说。
其次,叶德辉提出了“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主张。道咸以后,学术思潮由汉宋之争走向汉宋调和,陈澧与曾国藩均为汉宋调和论的代表。陈澧的《汉儒通义》主要是从汉儒的议论中发明汉儒义理,证明宋儒所讲义理,汉儒均已及之。叶德辉对此“心有未洽”。在叶德辉看来,汉宋之学各有其宗旨,亦各有其所长,“许郑之长在通贯经义,程朱之长在敦行践履”[8]34。他认为,性与天道,圣人不可得而闻,本非汉儒所究心所擅长,何必非要在汉儒言说中寻找此类义理?宋人的性理之说,原亦有虚有实,实者入理,虚者入禅。朱子之学实,陆子之学虚。性理之说,高明者与释氏离合在毫发之间;卑陋者乃以语录空谈导天下之人以不学。叶德辉宣称:自己“于宋学,独重朱子”“于朱子之学,尤重实践”[8]36。在他看来,朱子可贵之处,就在于针对性命之说的弊端,“救之以主敬,辅之以读书”[8]36。因而,朱子之学不仅与陆子有异,亦与周程张子有异。叶德辉不仅否定了汉儒言义理的说法,而且对宋儒义理本身作了分辨,认为值得倡导的宋儒义理并非性命之说,而是朱子一派务实的义理。因此,叶德辉将理学落实为朱子学,尊奉理学就是尊奉朱子学。故叶德辉表示自己“最服膺朱子之学,最畏居理学之名”[8]37,以将朱子学与理学区分开来。后来,叶德辉进一步提出:“吾生平颇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然非曾文正、陈澧调人之说,所谓汉宋兼采者,则以朱子自有真实之处,在学者之探求,不在口说之争辨耳。”[9]7
再次,叶德辉提出了“朱子乃清代汉学之初祖”的看法。在维新运动新旧之争时,叶德辉论及朱子,重点在于朱子的“敦行践履”,在于朱子对儒学道统的传承。而维新运动之后,叶德辉在教授弟子、传承经学之时,则对朱子的经学多有阐发。他教诲弟子:“自郑君而后,学问之博、识见之卓,无如朱子。朱子疑东晋古文《尚书》,则阎惠之开山也;于《阴符》《参同契》《韩文》皆有考异,则清儒校勘学之先异也。朱学后辈,有王伯厚、黄东发,伯厚著《困学纪闻》、东发著《黄氏日钞》,则清儒考订学之鼻祖也。伯厚又有《郑氏易注》《三家诗考》,则清儒辑佚学之所自出也。清儒以朱子之学为学,而攻朱子,实为数典忘祖。而朱子学之所以可贵,不在其空言义理,而在其实事求是,谈言微中,直达窍要,百年迷雾,旷若发蒙。”[10]叶德辉在经学教科书《经学通诰》中将朱子列为经学史上的四大流派之一,不但是南宋经学的大宗,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视朱子为经学通人:“朱子五经,《易》复古本,《尚书》辟伪孔,《诗》采三家;《礼》通古今;《春秋》虽无成书,所撰《通鉴纲目》,意在上续获麟。《尚书》又有蔡沈《集传》,乐有蔡元定《律吕新书》。是六经通学,郑氏以后,惟朱子一人。”[9]5他认为朱子之学“三传而为王应麟,四传而为黄震,遂开有清顾、惠二氏之学,流衍至于乾嘉,号为汉学”[9]5。朱子学是清代汉学的初祖。“炎武之学出于朱子,而实事求是,遂于东南汉学之先。论有清一代儒宗,当以炎武与元和惠周惕为不祧之祖。”[9]5他批判清儒号为宗汉、实攻朱学者,是数典忘祖。
叶德辉的言论,既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也代表晚清以降湖南保守人士对湘学传统的重建。无论是从尊奉理学的传统出发,还是从维护经学传承的传统出发,最终都归结到尊奉朱子。戊戌维新新旧之争时的“宗朱子”,代表了对儒学义理的信仰不容动摇。叶德辉以“宗朱子”抵制康梁学说中的“民权”“平等”等“邪说”。维新后的“宗朱子”,代表了对儒家经传的维护。
三、以宗朱子为标准,构建湘学知识谱系
进入民国以后,学术思潮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湖南地域学术文化中的理学传统逐渐沦亡,朱张记忆淡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对湘学的探讨中,朱子与湘学的关系得到了更深刻的阐发,“宗朱子”成为构建湘学知识谱系的标准。这在李肖聃的《湘学略》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李肖聃(1881-1953),号西堂,笔名星庐、桐园等,湖南望城人,早年从乡中耆宿问学,受到湘学传统的薰陶。清末李肖聃留学日本学习政法,归国后一度在报社工作。民国初年,主要在大、中学任教。李肖聃一生历经晚清、民国,见证了清季民初学术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目睹了清季民初价值失范、人心不古的社会乱象。在此背景下,他试图从传统学术资源中寻求对策,特别是寄希望于恢复湘学的理学传统。
李肖聃推崇中国传统的宋学,认为修身立行是最重要的学问,是保家卫国的根本。在李肖聃看来,宋贤之中,濂溪周子通天道、明圣功,二程涵养用敬、进学致知;张载明理分之旨、证天人之谊,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成为尼山以后的第一大哲,其学说成为千余年来规范人心的体系,影响及于国外。对湖湘而言,朱子已经成为湘人立身行事的准则,不敢有所逾越。这种风气到光绪年间有所变化。“光绪以来,老辈颇怡情声乐,山长不到书院,后生不礼前辈,群居终日,醉饱嬉游,英少相习,渐成风气。”[5]308但湘学尚理学的传统依然存在,光绪之后的湘中老辈尽管在行为上较为放诞,不如前辈谨严,而“不敢昌言排诋朱子,官师相戒,以身与妓席为羞,先民遗教,犹有存者”[5]308。至民国年间,则湘人不仅不再以理学修身制行,且在思想信仰上也不再尊信程朱理学。这使李肖聃十分痛心。在李肖聃看来,理学圣贤之教不惟在过去有效,即便在乱象纷呈的民国时期,也是应对时局的利器。因此,他主张重拾洛闽之绪,培植立身修行的根本。故在教育、研究中,他反复述说先贤事迹、凸显扬朱子之于湘学的重要性。
在叙述岳麓书院历史时,他强调:
窃惟岳麓天下名山也,自宋时长沙守朱洞,大修书院,礼湘阴周式为山长,始启儒风,化此南邦。厥后朱紫阳、张南轩二先生,讲道兹山,群彦云从,《宋史》称潇湘之间,有洙泗之风。今考黄梨洲《宋元学案》,于岳麓诸儒,详述师承,可见当时徒友之盛。自元逮今,绵二千年,流风未衰。因知大儒讲学,正人心而维道统,其功效久著如此。[5]124
湖南忠义之气藏菹郁积,待时而宣,正得益于大儒之教,尤其是朱子之垂教。
士欲修行立身,持家卫国,未有不践履笃实而能有成者也。《大学》平治,本于修身,圣门四科,首言德行,士之贵于三民,以此焉耳。去圣久远,群言日漓,天未丧斯,宋贤辈奋。濂溪周子,作《太极图说》以通天道,作《通书》以明圣功。二程上承师说,益以自得,涵养用敬,进学致知。横渠著《西铭》以明理分之旨,作《正征蒙》以证天人之谊。而朱子集四子之业,集诸儒之成,其立言多合于洙泗,其为学一本于艰苦。积物而穷理,铢积而寸累,其进以渐焉,其立以诚焉。故其学范围千年之人心,而其义且施于异族。信哉!自尼山以来,命世大哲,未有若紫阳之盛者也。[5]299
李肖聃多次阐发湘学历史,追述湘学理学传统,如在《最近湘学小史》中称:“濂溪传道,朱张继兴,岳麓诸儒,多明性道。王船山之所讨论,李恒斋之所编辑,莫不宗师横渠,祖述紫阳。皆理学也。”[11]“祖述紫阳”是湘学的传统。
在李肖聃论述湘学的代表作《湘学略》一书中,正式将朱子纳入到湘学知识谱系中。《湘学略》共26略,从纵向层面勾勒宋代以来湘学演变的轨迹,精心挑选湘学史的代表人物与代表成就,构建了一幅完整的湘学知识谱系,其中第4篇为《紫阳学略》。
《紫阳学略》有三个特点:
其一,重点阐发朱熹与湘学的渊源关系、朱子在湖南“大儒过化存神”的影响,将朱子学视为湘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略述及朱子的大事有:几次监南岳庙,37岁时始与张栻通书,论“未发之中”;38岁时,访张栻于潭州(长沙);64岁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朱熹辞职而不被允许,于第二年到任。“长沙士子,夙知向学,及邻郡数百里间,学子云集。朱子诲诱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5]20朱熹任荆湖南路按抚使时,“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事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5]20虽然朱熹在岳麓讲学前后不过三月余,朱子文集中的《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亦非为岳麓而发”,湖南跟从朱熹问学者不及跟从张栻问学者多且著,但是,“‘忠孝廉节’四字刻于讲堂,‘赫曦’、‘自卑’两亭立于山麓,湘浦有朱张之渡,潇湘有洙泗之风”[5]21,朱熹对湘学的影响超过了张栻。可见,“大儒过化存神之妙,又岂论其时之久暂哉!”[5]21
其二,揭示湖南的朱子学,展示湘人对朱子的崇奉。在《紫阳学略》中,李肖聃除了介绍朱熹本人在湘活动、讲学情况,还列出了39位湘人叙述朱学的40余部著作,以示朱子对湘学影响深且远大,崇尚朱子成为湘学的一大传统。
其三,明确表达恢复湘学崇奉朱子之学术传统的思想主张。李肖聃指出:“咸同诸公,始多尊崇紫阳,而干略又同新建。曾、罗逝后,老辈多宗汉师。自皮先生《南学讲义》,言乾嘉汉学皆出宋儒、且多出于朱子,群士始稍解迷惑。迄梁启超衍其师说,著书诋程朱,谓但读王懋竑《朱子年谱》即可卒业。”[5]23这使李肖聃十分不满。“吾恐学者学迷于其说,尽屏朱子之书而不读也”[5]23,故作《朱学篇》揭橥朱学宗旨。在《紫阳学略》,李肖聃附上了自己早年所作《朱学篇》。在《朱学篇》中,李肖聃把朱子看成“孔子后一人”,以为:“濂溪著《太极图说》《通书》,横渠著《西铭》《正蒙》,二程亦有《遗书》,皆足千古。即象山、阳明,或崇德性,或致良知,皆有孤诣。然王言满街都是圣人,陆言六经皆我注脚,持论过高。求其博大精深,可法可师,实推朱子为最。”[5]23朱子一身兼孔门四科之长。
李肖聃还援引湘中耆宿的学术思想来维护朱学,指出皮锡瑞“学兼汉宋,《南学讲义》指示最详”[5]24,叶德辉为《经学通诰》“亦言南宋经学以朱子为大宗”,继而提出对汉学家的质疑,以为:“吾观汉学诸家,但借单词碎义,轻笮宋贤,西河、东原,攻朱尤甚。姚姬传曰: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遗忘可也,欲将以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曾文正亦言:五子立言,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至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故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摈弃群言以自隘乎?”[5]24李肖聃认为,朱子学不但流传于本国,而且流传到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崇尚朱学,而中国宋元明清四代亦崇朱学。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谓“朱学宗旨,在完成人格,斥功利而重道德”,李肖聃认为“其言亦可味也”[5]25。总之,“自孔子卒后,千六百年而有朱子,实命世之大贤也。”[5]25因此,这篇学案不仅仅客观“叙述”朱子与湘学的渊源、对湘学的影响,而且还明确表达恢复宗朱子的思想主张。
《湘学略》凸显了湘学重“洛闽之绪”的特色,贯穿了“崇朱子”的旨趣。该书不但浓墨重彩地介绍朱熹讲学及其对湘学的影响,而且把“崇朱子”当成一个评价标准,以此考量其他学者的得失。但凡崇奉朱子的学者,都受到李肖聃的肯定,如李文炤“一以朱子为宗”[5]40;如湘军将领诸人“以理学植其根本”[5]300。同时,该书对其他湘学人物的解释也与众不同。如,湘潭诸胡是晚清湘中著名的汉学群体。但李肖聃在《湘学略》中重在揭示湘潭诸胡与广东学者陈澧的学脉关系,意在“欲胡氏承东塾之传,崇朱子之学,以教湘中子弟”[5]16。陈澧是晚清时期与朱次琦齐名的岭南学者,也是汉宋调和论的代表。在李肖聃看来,陈澧“其心尤欲泯郑、朱之争,通汉、宋之邮,与湘乡曾文正国藩,持论若合符契。其平生通今博古,精思力践,又诚无愧古人”[5]16,实际上也是崇奉朱子的。又如,王文清在清初以精通三礼著称一时,但李肖聃从宋学的角度解读王文清,认为从王文清劝示诸生的那些学约、学箴来看,“皆本朱子说以立言,知其得力于宋学者深也”[5]44。换言之,王文清之可称道不在于其考据成就,而在于践履宋儒的修身治性。李肖聃认同湘学的“崇朱学”传统,而对光绪以后湖南士风变化颇为不满,对放松了身心修养的晚清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不无微辞。因此,李肖聃所构建的湘学知识谱系实为朱子学视野下的湘学知识谱系。李肖聃的这些观点都影响了后人对湘学传统的认识。
综上所述,近代“湘学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它恢复朱张讲学历史记忆、确立崇奉朱子之传统的过程。清初,随着岳麓书院获得皇帝赐额,不但院志对朱张讲学大讲特讲,而且地方文献中也加强了对朱张讲学的记载。“紫阳讲学之道场”是岳麓书院得以被认证为“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的关键要素。晚清湘军的崛起,塑造湖南“理学之邦”“忠义之邦”的形象,增进了湘人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激活了湖湘文化的历史记忆。由湘军上溯到宋末,从宋末岳麓大社以身殉国到晚清湘军出任时艰,构成了一条以理学修身应世的意义链,“朱张二子之垂教”的意义得以凸显。湖南维新运动新旧之争时,为了正本清源、维护湘学传统的纯洁性,叶德辉提出“尚汉学而独崇朱子”的思想主张,一方面化解汉宋调和论和晚清公羊学说对朱子理学义理所造成的危机,另一方面确立朱子作为“汉学之初祖”的地位。进入民国时期,李肖聃基于复兴地域文化传统、拯救世道人心的目的,在绍述乡贤的同时,重拾洛闽之绪,将朱子纳入了湘学知识谱系中来,并以“宗朱子”为标准,构建了一幅从宋至清的完整的湘学知识谱系。由此可见,在近代“湘学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诠释朱子与湘学的关系、朱子学的内涵,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近代地域文化观中的宗朱子现象,折射了朱子在近代的命运与影响。
[1]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M].影印.扬州:广陵书社,2010.
[2]陈宏谋.湖南通志[M].影印.济南:齐鲁书社,1996.
[3]张晶萍.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省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4-39.
[4]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M].1883(光绪九年刊):5.
[5]李肖聃.李肖聃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吴荣光.湖南述别四首[M]//岳麓书院续志.长沙:岳麓书社,2012:607.
[7]苏舆.翼教丛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叶德辉.郋园论学书札[M].长沙:叶氏刊,1898.
[9]叶德辉.经学通诰[M].长沙:湖南教育会,1915.
[10]杨树达.叶郋园先生经学通诰跋[J].东华,1932(42):39.
[11]李肖聃.最近湘学小史[J].长沙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4:88.
“Zhuzi Worship”in Modern“View of Xiang Learning”
ZHANG Jingp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81,China)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view of Xiang Learning”is,to some certain degree,the restor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of“the talk between Zhu and Zhang”,and the interiorization of Zhusim into the academic resources with national meaning and regional meaning.The“talk between Zhu and Zhang”gained a name for Yuelu Academy,i.e., “Ziyang Lecture Ashram",and the academy was regarded as the bas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In the late Qing era,the rise of Xiang Army portrayed the Hunan image of“the state of Neo-Confucianism”,and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Huxiang culture of Hunan people.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Movement,YE Dehui put forward the idea of“Zhuzi Worship in advocating Sinology”,in order to keep to the beliefs of Confucian morality,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LI Xiaopeng picked up the Cheng and Zhu Neo-Confucianism again,and built a complete genealogy of Xiang Learning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with“Zhuzi Worship”as the standard.Thus,the exploration of“Zhuzi Worship”in the view of modern regional academic culture can reflect Zhuzi’s destiny and influence in modern times.
“the talk between Zhu and Zhang”;historical memory;Zhuzi;Xiang Learning;modern times
B25
A
1004-2237(2017)05-0001-07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5.001
2017-09-29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项目(17A138)
张晶萍(1967-),女,江西鄱阳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E-mail:zhangjp83@126.com
[责任编辑 邱忠善]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