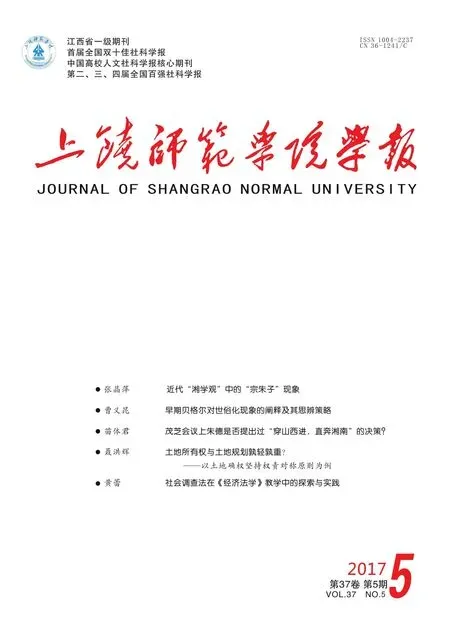早期贝格尔对世俗化现象的阐释及其思辨策略
曹义昆
早期贝格尔对世俗化现象的阐释及其思辨策略
曹义昆
(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334001)
彼得·贝格尔是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理论家和宗教社会学家,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发表《神圣的帷幕》一书,对当时知识界公认的西方工业社会普遍世俗化现象进行了阐释,从而使他赢得世俗化理论家的声誉。贝格尔的阐释工作主要围绕“世俗化”概念的定义、世俗化现象的西方宗教渊源、世俗化在社会结构层面的表现以及世俗化与多元主义的关系等方面而展开。从大处着眼、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和比照,是贝格尔对世俗化现象阐释所采取的基本思辨策略。这样的思辨策略固然使他的相关论述极具思想穿透力和说服力,但也导致研究方法上对经验的事实和证据有所忽略或甄别不足的缺陷,为他后期职业生涯中放弃世俗化命题的重大学术转向埋下伏笔。
贝格尔;世俗化;西方宗教;社会结构;多元主义;思辨策略
彼得·贝格尔(Peter L.Berger)①又译“彼得·伯格”。,美国当代知名社会学家,以研究知识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理论著称于世,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堪与马克斯·韦伯比肩。1969年,时年40岁的贝格尔正式发表《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 y)②此书于1973年略有修订后在英国再版,更名为《宗教的社会现实》(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本文写作主要依据这一英文版本和中译本。,在该书的后半部分,他对当时知识界所公认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遍世俗化现象进行了阐释,这项工作使他声名鹊起,为他赢得了世俗化理论家的声誉,他也被视为是世俗化命题“最老练的”论证者[1]74。
一、“世俗化”释义
所谓“世俗化命题”(the secularization proposition),是指对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衰落或边缘化的判断。需要指出的是,该命题的基本主张在西方学界由来已久,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但以它为核心而建立的、作为宗教社会学研究指导范式且逻辑严明的世俗化理论,正式出现和论证完善工作则要迟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此之前,“世俗化”一词使用较为混乱,并未获得客观描述和传达某种经验事实的价值中立属性,而是和表示意识形态的词语“世俗主义”(secularism)往往纠缠不清,因此在学界饱受非议,英国社会学家大卫·马丁当时甚至建议将这个词语从宗教社会学辞典中剔除掉[2]。贝格尔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做法,认为如果穿透意识形态的迷雾,不涉及价值判断而单从纯粹现象描述的角度看,“世俗化”还是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积极术语使用,前提是要严格加以定义。
贝格尔对“世俗化”的正式定义是:
世俗化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这种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3]128
单凭这一定义,我们还不能看出贝格尔所言的世俗化和现代性的社会条件有何必然关联。为避免误解,他马上指出:世俗化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趋势,原因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工业经济模式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世界各地传播。说到底,“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作为基本的社会力量,势不可挡地推进世俗化”[4]116。可见在早年贝格尔那里,世俗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内在、必然特征,现代性必然伴随世俗化的说法对他而言不成为问题。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贝格尔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世俗化理论家。
根据这一定义,贝格尔分析了西方现代社会世俗化的三种表现形式: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基督教会撤出过去控制和影响的领域,造成教会和国家的分离、教会领地的缩小、教育摆脱教会的控制等;其次,在文化和各种象征的层面,哲学、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宗教内容消淡,以彻底世俗的眼光审视世界的科学主义兴起;最后,从个体意识的层面来看,世俗化在现代西方世界造就了数量巨大的一批人,“他们看待世界和自我根本不需要宗教解释的帮助”[5]128。
值得注意的是,贝格尔在此谈及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等客观层面的世俗化的同时,也特别提到主观层面的世俗化,即宗教世界观在个体头脑中被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所替代。笔者认为,贝格尔对“世俗化”主观维度的强调,既缘于对韦伯所主张的“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思想的直接继承,也与他从认知角度研究宗教的方法论进路有关。对他而言,无论宗教为主、客观“实在”(reality)提供终极意义的合法化维护从而使实在更具理所当然性(taken-for-granted),还是实在的理所当然性与宗教无涉情况下的个体主观意识的世俗化,都是着眼于宗教世界观认知功能的存废立论。从认知的角度阐释宗教和世俗化,在他从西方宗教传统内部的观念因素探寻世俗化的成因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思路中,得到极好的展现。
二、世俗化之西方宗教探源
世俗化的成因是什么?贝格尔认为,作为现代世界大范围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世俗化的成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不可作任何单一的解释,但不管怎样,要想回答世俗化为什么在西方出现的难题,至少要部分地依靠“它在现代西方的宗教传统中的根源”[5]149。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是:“西方宗教传统在何种程度上自带世俗化的种子”从而成为它以后历史的“掘墓人”[5]132?对此,他先从新教对于现代世界的诞生所发挥的作用说起。
(一)新教的世俗化能力
贝格尔指出:新教的世俗化能力,缘于它对天主教悦神仪式的变革,以及在这类变革基础上为一个全面世俗化世界的到来所提供的历史性契机。
首先,悦神仪式变革的基本方向——删繁就简。天主教徒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体验神圣者的存在,如教会的圣事、神职人员的代祷、超自然的东西以神迹方式反复呈现的圣餐等。新教改革则破坏这些人神沟通的渠道或媒介,其基本方式是对原有仪式删繁就简,使其中所蕴含的神圣和神秘意味大为淡化:圣礼的使用被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完全废除了它的神秘性质;弥撒中的神迹意味基本消失;较小仪式中的神迹即便有所保留,也失去对于宗教生活而言的真实意义;代祷仪式不再举行,等等。
其次,悦神仪式变革所导致的后果——为完全祛除超自然神秘性的、彻底内在和封闭的自然世界之形成,创造了认知上的无限可能。所谓“祛除超自然神秘性”,是指新教在宗教仪式上的变革使现实世界尽可能地摆脱“神圣者的三个最古老和最有力的伴随形式——神秘、神迹和魔力”[5]133。在此情况下,世界虽然仍被认为是上帝所造,但却变得与上帝无关,成为彻底内在和封闭自足的存在系统。同时对人而言,居住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也变得孤独起来。贝格尔对此评论道,新教“切断了天与地之间的脐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人抛回来依靠他自己”[5]134。
最后,悦神仪式变革为世俗化创造的历史性契机——人神关联仅剩一条逼仄通道,一旦切断,世俗化的闸门从此打开,势不可挡。贝格尔所言人神关联的“唯一通道”,是指新教徒对“源自上帝恩典的唯一拯救行动”的信仰。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并非完全褫夺神性,上帝迟早会对这一世界实行行动干预,这是新教把世界内在化、封闭化和自然化的同时唯一认可的神迹,目的是为了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上帝的超越性和可畏尊严,以使人类能够向上帝的拯救行动无条件地开放自身[5]118。然而,对上帝及其拯救行动的信仰一旦出现危机,也就意味着人神关联的唯一通道会逐步沦陷,人类世界会不可避免地接受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全面渗透,最终变得世俗化起来,而这样的情形在西方晚近的历史中已经发生。正是基于新教改革为世俗化创造历史性契机的考虑,贝格尔指出:“无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有多大,还是新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1]134
(二)《旧约》“世界祛魅”时代的开启
在确认新教为现代世界的世俗化直接充当开路先锋的基础上,贝格尔又进一步追根溯源,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点:新教的世俗化能力并非空穴来风,在古代以色列宗教中就可找到它的根源。换言之,“世界祛魅”在很大程度上从旧约时代就已经开始。贝格尔所言旧约时代的“祛魅”,是指古以色列民族和周围的文化世界彻底决裂、从“神—人”连续统一体的文化氛围中摆脱出来的过程,而《旧约》记载的“两次出走”①即早期希伯莱人从米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转移以及后来出离埃及。,则是这类文化决裂最终实现的象征性标志。
何谓“神—人”连续统一体?简单地说,它实际上是指某种宇宙观视野,在此视野中,人类世界被视为是把神圣存在包含于自身的整个宇宙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神之间存在某种边界上的流动性和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认定“人间的事件和渗透宇宙的神圣力量之间,有一种不间断的联系”,故“在此‘下界’的人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在神灵的‘上界’都有其类似存在,‘现在’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与 ‘太初’时出现的宇宙事件相关联”[5]136。
贝格尔认为,《旧约》中全新上帝形象的出现,是对上述原始宇宙观的彻底颠覆和摒弃,人类世界因此摆脱曾经的神话和巫魅色彩,为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对此,他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旧约》叙事的三大主题予以论述。
首先是上帝的超越化(transcendentalization of God)[3]122。上帝的超越化体现在多方面:(1)上帝虽然创造了宇宙,但却孤悬于宇宙之外,并不参与宇宙的实际构成并对宇宙进行渗透;(2)上帝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伴侣和后代,也没有诸神陪伴;(3)上帝的行动具有历史性,尤其介入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历史关联和从远方来的上帝,而不是该民族的地方神或部落保护神;(4)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历史关联以契约为前提,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很好地履行契约中所规定的义务,这种关联可以解除,故而《旧约》的上帝又是能动的上帝,既不受地理的约束,也不受制度的限制[5]139-140。
上帝的彻底超越化,在《创世纪》关于上帝创世的叙事中得到典型体现。上帝创世是孤独的活动,并且上帝出现之前一无所有,他在虚无中创造出一切。所有这些,皆与米索不达米亚神话所描述的从混沌中产生并合作创造世界的诸神形象适成鲜明对比。此外,创世的过程以创造出人宣告结束,而人是和其他被造物以及上帝很不相同的存在。正是由于人的这种特殊性,上帝的超越性得到更有力的彰显。在《旧约》的话语中,上帝和人形成根本的两极分化,二者之间则横亘着一个彻底祛除神话和巫魅色彩的自然世界。
其次,神、人活动的历史化。贝格尔指出,上帝的超越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祛魅,“为作为神与人的活动舞台的历史开辟了一块空间”[5]142。也就是说,丧失神话想象的现实世界,同时成为上帝和人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整部《旧约》,就是围绕体现神的伟大活动的“神圣历史”和作为人的活动结果的“世俗历史”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而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是高度个体化的个人,并且“越来越不被视为神话所设想的集体性之代表”[5]142。这样的个体以历史行动者的身份出现在上帝面前,并且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当然,贝格尔也提醒人们:这并不意味着《旧约》“人”的概念就是现代西方的个体主义,甚至也不可以说达到古希腊哲学的认识高度。但是,从历史上人类自我理解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毕竟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尊严和行动自由等观念提供了一个最早的宗教解释性框架。
最后是伦理的理性化(the rationalization of ethics)[3]125。这一主题意味着把理性赋予生活之上。这种理性尽管属于神学形态,并且坚持整个生命服务于上帝这一宗旨,但最终必然归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现实处理,故而能够以冷静务实的态度处理社会人伦关系,摒弃神话世界观的一切迷信和杂乱的成分。传达这一主题的主要有祭司群体和先知群体。最早的祭司群体从清洁仪式开始(去掉其中的巫术色彩),并且在创立作为日常生活基本准则的律法的过程中,起到理性化作用。在此基础上,后来的先知们则进一步地推进,“把一种有聚合力的,事实上是理性的结构加在日常生活的整个范围之上”[5]144。在巴比伦放逐之后,新一轮的祭司伦理继续发展了礼仪和法律制度,使之更趋完善和合理。
基于以上三点,贝格尔认为韦伯所言“世界祛魅”,在历史上要远远早于一般被认为是它的起点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换言之,早在圣经宗教传统的发轫之初,就存在着上述独立的观念因素,成为后来社会世俗化的历史根源。
(三)从《旧约》《新约》到新教改革的历史嬗变
圣经宗教传统在其发轫之初所含藏的世俗化力量为什么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宗教改革才蓄势爆发呢?贝格尔认为,这与从《旧约》中经《新约》一直到新教改革的历史时代嬗变有关。他首先指出,基督宗教的出现,就世俗化的论题而言,事实上代表着某种程度的倒退,理由是:“道成肉身”和“三位一体”的教义破坏了旧约圣经所坚守的上帝超越性,而大量的天使、圣徒和圣母玛利亚中保身份的存在,致使世界重新“复魅”;天主教繁富复杂、无所不在的圣礼体系,提供了从旧约时代先知所要求的那种伦理绝对主义逃离出来的“逃生通道”,从而阻断了伦理理性化的进程[5]145-146。
但是,从《旧约》到《新约》的历史转变也存在着积极的方面,不能一概抹杀。贝格尔就此指出两点:第一,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普世基督教继承了旧约的历史化主题,保留了只有圣经宗教才有的那种历史神正论,同时也拒斥了那些对此世获救的可能性表示失望的宗教形式(如神秘主义),故而它自身就携带着革命动力的种子,虽然这类动力要等到基督教世界濒临崩溃时才会以种种千禧年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第二,基督教教会以其把宗教活动和象征集中在单一的制度框架之内的特点,代表宗教的制度专门化。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形式,它导致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部分,也即路德宗所说的“神圣王国”和“世俗王国”,而后者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相对脱离神圣者管辖范围的领地。一旦支撑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可信性结构发生动摇及其所营造的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世俗王国”便彻底脱离神圣者的管制,以加速度的方式世俗化[5]147-148。
在普世基督教和世俗化的关系问题上,贝格尔尽管辨明以上两点,但依然认为从总体来看,这种宗教形式“可被视为世俗化这出戏的进展过程中阻碍和退化的一步”[5]148。正因为如此,世俗化才需要新教改革作为开路先锋。这场改革被认为是含藏在天主教中的《旧约》观念性因素的世俗化力量强有力地再现和爆发。当然,贝格尔并不认为这些观念因素可以独立起作用,而是需要通过作用于社会基础过程,导致后者在经验上出现可见的变化,最终才会导致全面世俗化社会的产生。然而,这样的社会一旦形成,无疑会反转过来阻碍宗教作为社会构成的力量继续发挥影响,宗教走向式微势不可免。正因为如此,贝格尔说西方宗教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并言“历史的嘲弄恰在于宗教和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当中”[5]153。
三、社会结构层面的世俗化
笔者认为,贝格尔在写作《神圣的帷幕》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崩溃一直是他思考世俗化现象的一个模板。基于这一模板,他认为这样的世界之所以出现可信性危机从而导致自身的最后崩溃,固然可以从基督教文化的内部寻找认知根源,同时也与支撑这种文化的整个社会基础结构在晚近时代出现的重大变化有关,原因在于:圣经宗教传统所包含的“埋葬自己”的观念因素是一种隐性的世俗化力量,不能孤立起作用,而是要通过作用于社会构成的物质要素,使后者在经验上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把基督教推向全面的信任危机,进而才有人们主观上的普遍世俗化现象产生。换言之,主观的世俗化需要社会结构层面的客观世俗化的有效促动才能全面爆发,尽管这两者在逻辑上可能同步,并无时序先后之分。
贝格尔指出:就现实中的经验观察而言,世俗化的效果首先是在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层面上得以显现。对此,他举经济、政治、家庭等社会结构要素进行分析,并就这些要素的变化对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处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判断。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出现在经济领域。贝格尔认为,经济部门尤其与现代工业生产直接相关的部门乃是世俗化的“最早居所”,并且社会的不同阶层依照与这一部门的远近,都程度不等地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对于经济领域的世俗化,贝格尔写道:“现代工业造就了一个核心部门,对于宗教而言,它似乎是一块不受管束的‘自由领地’。”[3]133与此同时,世俗化也从这一核心部门向其他部门辐射,从而造成宗教存在形式的“两极分化 ”(polarization)现象[5]156-157。所谓“两极”,是指国家和家庭这两种分别代表最具公共性、最具私人性的制度部门的两极。贝格尔所言宗教存在形式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是指宗教从政治等其他公共制度部门分化出来以及宗教退居到私人领域这两种客观维度的世俗化。
其次,就最具公共性的一极——国家而言,贝格尔认为尽管在经济世俗化和政治世俗化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滞后现象(如已经走上现代工业社会道路的英国,对政治秩序的传统宗教论证仍在延续),但不管怎样,宗教至多只是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而已,它对国家的控制力已基本解除,“从宗教制度或政治行为的宗教前提等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国家之出现,似乎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3]134。很明显,贝格尔所指是政教分离。他指出:政教分离最重要的后果是国家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不再作为强制力量代表以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发号施令,而是在彼此竞争的宗教团体中扮演相对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在此情况下,教会要想获取人们的忠诚,不得不独自去招募志愿信徒。如此一来,任何企图恢复国家对宗教的强力支持的努力注定会失败。贝格尔论及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力,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以资本主义和工业经济秩序为标志的现代化所释放出来的理性化过程所致[5]156-157。
最后,就存在形式的另一极而言,家庭领域的宗教不像在政治领域那样至多不过沦为意识形态的修辞,而是依然具有保持自身实在性的巨大潜力。具言之,在家庭以及和家庭生活有关的人际关系领域,人们的日常行为动机和自我解释都和宗教大有关系,甚至高度世俗化的阶层如美国中产阶级,也接受宗教对家庭的合法化解释。但是,贝格尔也指出,宗教与家庭这种象征性结缘基本上被限制在私人空间,并且受制于这个空间的种种特性,如个体化。个体化这意味着私人性质的宗教是个体或单个家庭的“选择”和主观“喜好”的事情,本质上缺乏共同的约束力。换言之,不管这类宗教对个体而言如何具有真实性,却不再可能完成传统宗教的任务,即:“建造一个共同的世界,在其中,所有社会生活的终极意义对于所有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3]137。贝格尔认为,宗教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实现与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的隔离,“对于维系现代经济和和政治制度的高度理性化秩序”有积极作用[3]138。
在贝格尔看来,上述经济领域的世俗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世俗化、宗教退居到家庭生活领域的私人化,所有这些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基础结构上的变化对宗教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造成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尴尬处境,即“共同性和实在性的分裂”[5]159。简言之,宗教有时候成为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意识形态的修辞,在此情况下,它是“共同的”,但缺乏实在性;宗教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个体无疑是“实在的”,但又缺乏共同性。他指出:共同性和实在性的分裂,标志着宗教建立完整实在观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意义体系的传统任务结束,宗教建构实在的力量也只能被限制在亚社会群体中发挥,建造片段化的意义体系;而为这类意义体系提供可信性支撑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家庭还是更大规模的教会或宗教集团,由于其本身结构的脆弱性,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维持宗教的可信性和持久性[3]138。总之,根据他的理解,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已是捉襟见肘,衰弱不可避免。
四、世俗化与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pluralism)是贝格尔早年为世俗化现象写作致力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对于这一主题,他主要从多元主义的形成、多元主义对宗教信仰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多元主义条件下的宗教市场经济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多元主义的形成
贝格尔把多元主义的形成明确归之于世俗化:“世俗化造成了各宗教传统的非垄断化,因而事实上导致了多元主义。”[5]160也就是说,前文所述社会结构层面上的政教分离及其所导致的宗教在政治和公共事务领域撤出、国家不再作为传统宗教强制力的代表而是在各种宗教之间保持中立等,是多元主义产生的原因所在。
对于历史上宗教的社会垄断地位打破和多元主义局面形成的过程,贝格尔作出概要式描述。他说,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宗教为社会共同体提供终极意义的合法化论证,一直扮演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垄断者角色。在前现代社会中,宗教制度涵盖社会制度的一切领域,是调节思想和行动的力量,故而这种制度等于就是社会制度本身;宗教所界定的世界也被认为是世界本身,世界的稳定性并不只是靠世俗力量及其社会控制来维持,更多的是靠宗教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共同常识来维持[5]160。就西方而言,“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所传达的社会实在内涵,体现了典型宗教式垄断的存在。尽管教会和帝国两种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斗争,但这属于内部的斗争,它们代表同一个宗教世界,基督教的垄断特征丝毫未因此减损。然而,随着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的爆发以及解决战争协议中“教随国定”原则的确立,虽然真正的多元主义局面并未出现,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却被打破,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此开始。在随后的历史中,新教派别不断增多,无论在天主教还是新教内部对离经叛道者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宽松和容忍,基督教世界进一步瓦解,多元主义局面逐渐明朗[5]160-161。
贝格尔认为,真正的多元主义格局和多元化过程(pluralization)首先在美国开花结果,导致宗教派别林立的局面出现。美国的宗教类型——“宗派”(denomination),可谓是宗教多元主义存在形式的典范,因为这些宗派“一直对彼此永久性地和平共处和自由竞争这一点达成共识”[3]141。多元主义并不限于宗教之间的相互竞争,作为世俗化的结果,宗教团体也被迫在世界观和价值主张方面与各种非宗教的对手竞争,因此不仅在拥有美国式宗派类型的那些国家里可以谈论多元主义,而且在没有宗教垄断、宗教不得不和各种世俗的竞争对手打交道的地方,也可以谈论多元主义[5]162。
(二)多元主义与宗教“理所当然性”的丧失
贝格尔指出:宗教在当代人意识中的情形,最大的特征是“理所当然性”的丧失,即:个体不再把原有的宗教内容视为客观实在的自明性真理对待,而只是作为“看法”和“情感”保留在意识之中。这意味着宗教在意识中的位置发生了变换,用他的说法是:“从含有至少一切正常人都会赞同的基本真理的意识层面过滤出来,进入各种主观看法的意见层面,而对于这些意见,明智的人常不会赞同,而且人们自己也不完全有把握。”鉴于此,他建议可以把当今时代称为宗教史上的“怀疑主义时代”[5]175。
贝格尔认为,宗教在当代人意识中信誉度下降的事实,不能归咎于意识内部或者意识本身发生了某种神秘突变,而应该根据经验上可以把握的社会历史过程作出解释。归根结底,是多元主义环境把宗教投入信任危机的漩涡当中,原因在于:多元主义除了作为一种全球性过程和世俗化密切相关外,同时作为社会结构现象,它消除宗教垄断,制造出相互竞争的多种可信性结构,从而使得某种特定的宗教或宗教派别维持或重建可行的可信性结构变得尤其困难。这样一来,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内容在认知上被相对化也就势在必然。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是各自在意识中的客观实在性地位被打破。正由于此,贝格尔说在社会心理层面,宗教在双重意义上被“主观化”:(1)丧失了主体间自明的可信性,其“实在性”成为个人的“私事”,人们不再可能“实实在在地谈论宗教”;(2)宗教沦为个人的私事,故也只能扎根于个体意识中,其内容“不再涉及宇宙和历史,而只关乎个人的生存和心理”[5]177。
贝格尔早年对多元主义削弱宗教信仰的理所当然性(即确定性)这一点深信不疑。在《神圣的帷幕》出版十年之后的另一本著作中,他写道:“我们的时代境况,是以同时并存、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多元市场为特征。在这样的境况中,确定性的维持实际上非常困难。就宗教本质上端赖于‘超自然者’的确定性而言,多元主义境况具有世俗化性质,并且事实上使宗教深陷信任危机中。”[3]
(三)多元主义与宗教市场经济
贝格尔指出:多元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以往宗教式垄断把信徒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的做法已不再可能,忠诚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结果,过去由国家和政治权威所保障的宗教传统现在不得不进入市场,并且卖给自愿购买的顾客,故而多元主义环境首先是一种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宗教机构变成了参与市场竞争的力量,宗教传统变成了消费品,而“宗教活动则由市场经济的逻辑所支配”[5]163。很显然,贝格尔在多元主义论题下提出了关于宗教市场经济的论说。
对于贝格尔的宗教多元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本文不拟作详细介绍,仅勾勒出如下要点:
第一,市场竞争促使宗教组织以理性的方式优化自身,普遍采取科层制组织和管理模式,结果在不同宗教传统或神学背景的宗教机构中,造就了大量积极务实、不迷恋与行政无关的思索、精通人际关系的宗教行政和管理人员存在,他们的理性工作作风与一般商业公司的职员和管理层无异[5]164-166。
第二,在多元主义市场环境下,由于竞争过于残酷以及市场的不稳定性带来的财政状况的不可预测性,各宗教组织携手进行合作,出现了卡达尔化的“宗教普世联合”即大型宗教集团[5]168。
第三,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由于宗教不再能强加而只能出售给消费者,故而“消费者喜好”成为左右宗教产品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对于宗教机构所提供产品的宗教内容来说,首先意味着可变性原则的引入——没有一成不变的宗教内容存在,消费者所置身世界的世俗化特征和私人生活领域的需要将决定宗教内容的变化方向;再就是由于消费者或者潜在消费者需求相似所导致的标准化,以及与所谓“信仰之重新发现”相联系的强调信仰特质和殊异性的“边际分化”(marginal differentiation)[3]151。边际分化不一定是去标准化,更有可能仅是“包装”上的分化,在包装的里面,可能是同样的标准化产品,原因在于:宗教产品的殊异性不是受特定的信仰传统所决定,而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5]171-174。
贝格尔关于多元主义条件下宗教市场经济的相关论述,被后来的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等人所继承,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更加系统、宣称可以运用到所有信仰之上的普遍原理的宗教市场理论学说(又称宗教“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个体就本性而言是宗教的,故而对宗教的需求是恒定的,与任何时代因素的变化无关[1]107-108,个体在自己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各自的宗教选择[[1]104;在宗教市场自由开放、多元化竞争激烈并且可供选择的宗教产品丰裕的地方,宗教往往会蓬勃发展;反之,如果由于国家的政策干预导致宗教多元主义竞争的活力丧失、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宗教产品匮乏,宗教往往会衰落和萎靡不振。很显然,该理论把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竞争作为有利于宗教发展而非衰落的事项看待,并据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世俗化理论[1]70,这与贝格尔早年提出宗教市场经济思想的初衷相去甚远。在贝格尔看来,多元主义是世俗化导致的宗教去垄断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世俗化的表现形式;即便有充满竞争的宗教市场经济存在,也无以改变多元主义削弱信仰的确定性从而使信仰相对化、内在世俗化的特质,各宗教组织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世俗主义倾向一再剔除或有意淡化作为其信仰核心的超自然因素,就是其自身内在世俗化的一种体现。
从以上对贝格尔阐释世俗化现象的三个最重要方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贝格尔的阐释工作主要还是立足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比照和关联而展开。欧洲现代文明是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直接延续(或说衣钵继承者),因此在这种延续过程中所发生的明显时代断裂,必须回溯到前此断裂时期的文明内部去追根求源,拷问其成因。现代欧洲的世俗化特质即属于这样的明显时代断裂之一,它的成因自然要回到前现代欧洲的价值文化形态及其漫长历史嬗变中寻找答案。基于这种历史还原式的运思方法,贝格尔展开了世俗化之西方宗教根源的探寻,认为《圣经》宗教传统早在其发轫之初就含藏巨大的世俗化潜能,这类潜能中经基督教文化历史的充分沉淀和涵泳,通过新教改革创造的历史契机而爆发。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指出基督教是自己的“掘墓人”。同样的历史性关联视角也体现在他对欧洲晚近时代社会结构层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异即世俗化的分析上,在笔者看来,这种分析明显以前现代欧洲的社会基础结构为参照模板,而后者恰是为基督教建立起“全社会的(societal)”观念统治提供可信性支撑的。从神圣到世俗的观念文化变迁,必然伴随着为观念文化提供可信性支撑的巨大社会结构的历史移易,这是贝格尔对世俗化命题阐释所依据的又一思辨策略。此外,他对多元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前现代欧洲基督教的垄断式统治为历史参照而提出,并且认为这是基督教衰落的标志,尽管多元主义在美国发展最为成熟,但作为欧洲殖民者及其后代所建立起来的国度,贝格尔认为美国的情况也无以改变多元主义赖以从出的历史脉络及其世俗化的效果和实质。
总之,从大处着眼、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和比照,是贝格尔对世俗化命题阐释所采取的基本思辨策略。这样的思辨策略固然使他的相关论述极具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但也导致研究方法上对经验的事实和证据有所忽略或甄别不足的缺陷,为他在后期职业生涯中放弃世俗化命题的重大学术转向埋下了伏笔。
[1]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杨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MARTIN D.Towards eliminating 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C]//DEDONG W,ZHIFENG Z.Sociology of religion:a David Martin Reader.Waco:Baylor University Press,2015:177-189.
[3]BERGER P.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3.
[4]BERGER P.Facing up to modernity[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9:213.
[5]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Berger's Early Elaboration of Secularization and His Speculative Strategies
CAO Yik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Peter Berger is a famo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etician and sociologist of religion.In his early academic book The Sacred Canopy,he elaborates on the intellectually-recognized common secularization of the Western industrial society,which won him a name of secularization theoretician.Berger's elaboration centers on the definition of“secularization”conception,the Western religious origins of secularization,the manifestations of secularization at the social structure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cularization and pluralism.The basic speculative strategies in his elaboration lie in his taking a wider view,and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 and contrast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Such strategies made his relative discussions thought-penetrating and convincing,but led to some defects in research methods,such as overlooking or inadequate screening of empirical facts or evidence,which foreshadows his important academic turning from secularization thesis later in his career.
Berger;secularization;Western religion;social structure;pluralism;speculative strategies
B920
A
1004-2237(2017)05-0015-08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5.003
2017-09-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J001)
曹义昆(1976-),男,江西都昌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宗教学和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E-mail:ganlin076@163.com
[责任编辑 邱忠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