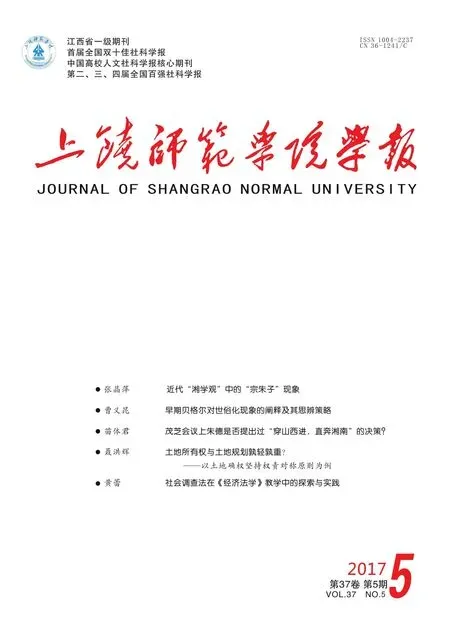刘宗周《人谱》书名及理论内涵探微
余 群
刘宗周《人谱》书名及理论内涵探微
余 群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刘宗周命名《人谱》,其灵感是源于“家谱”概念的,而其目的就是要在人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人的谱系。两相比附,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人谱》书名及其理论内涵:家谱证身世,而《人谱》证心性;家谱寻远祖,而《人谱》寻“意”根;家谱别姓氏,而《人谱》别贤愚。总之,《人谱》书名之含义就是“谱人”“证人”。证明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证明人人具有尧舜之性,此为天命之善性。人由于受外物之熏染,难免会产生一些过错,但只要能够“慎独”与“诚意”,就能够迁善改过,从而入于圣人之域。可见,《人谱》之书名,与众多著作顾名思义颇为不同,它不仅泛指著作内容,还涉及到著作的思想体系。通过细致的探究,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刘宗周的理学思想,还能更好地促进其传播与接受。
刘宗周;《人谱》;家谱;证心性;寻“意”根;别贤愚
古往今来,许多名著的书名含义往往比较直观,而且与书中内容的关联性不是非常密切。如宋代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子张》中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189,而“录”则是朱熹和吕祖谦对理学家门重要言论的摘录之意。又如,王阳明代表作《传习录》,书名“传习”来自《论语·学而》中“传不习乎?”[1]48而“录”则表明是弟子对老师王阳明讲学的记录。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的书名由于与书中思想体系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并不那么通俗易懂。例如,刘宗周的著作就是如此。刘宗周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理论水平非常高深,他的著作有很多,《人谱》就是其代表作之一。此书作于崇祯七年(1634)秋八月,是刘宗周晚年的成熟之作。此书之名,不仅泛指著作内容,而且还涉及到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因此,理解起来就有一定难度,这无形之中也影响了此著作的传播与接受。所以,有必要对《人谱》书名及其内涵进行细致的探讨。当然,要理解其含义,就必须了解刘宗周命名的思路。其实,《人谱》书名的灵感是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家谱”。“家谱”与“人谱”,两者都有一个“谱”,都是要在天地之间为人寻找一个合理的坐标和身份。刘宗周儿子刘汋曰:“《人谱》者,谱人之所以为人也。”[2]106人谱,就是谱人、证人,以证明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和意义。当然,书名不直接用“证”,而用“谱”,还是有深刻涵义的。其实,刘宗周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于崇祯四年(1631)三月在绍兴府创办了“证人社”,用以“证人”,证其所以为人、为心,但他不用“证”,而用“谱”来命名著作,主要原因在于,通过教学实践与理论的双向促进,刘宗周后来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谱人”进而是“人谱”,比“证人”的含义来得更丰富、更圆满。这无论从字义,还是理论结构,都可以得到证明。如果两相比附,《人谱》的书名及其内涵就比较明朗。大致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家谱证身世,《人谱》证心性
在我国,千家百姓的家谱一直都是比较完备的。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于血统、身世都是非常关注的,这就使国人的家谱情结根深蒂固。在生活中,我们热衷追根溯源,对自身的来龙去脉往往了如指掌,并早已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历代文人也往往不知不觉地要对身世进行表白,以此来说明自己高贵的血统和不凡的身世。屈原《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3]此诗一开头就对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描述,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显示了自身与众不同的来历,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志行高远的原由。
事实上,家谱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用来证明自己身世的最好宝典。刘宗周受此启发,创作《人谱》,目的是要在天地万物之中来证明人的价值和意义,而其根本则在于人的心性。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必须证明其所以为人,而证其所以为人,就在于证明其所以为心而已。刘宗周《原心》曰:“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其生而最灵者也。生气宅于虚,故灵,而心其统也,生生之主也。”[4]279人生天地之间,人是天地的精灵,是最为灵巧者。此灵巧由人心来统摄,具有生生之性。
作为一代大儒,刘宗周极力推崇孔子的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而这个慎独的依据则在于人心有一个独体,即天命之性。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曰:“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4]5可见,证人就是要慎独,使之保持中和位育的状态,从而让天命之性自然呈现。而天命之性,就是有善而无恶之心。刘宗周《原性》曰:“夫性因心而名者也。盈天地间一性也,而在人则专以心言。性者,心之性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生而有此理之为性,非性为心之理也。”[4]280性为心之性,心之相同者为理,所以人皆具体相同之善性。刘宗周曰:“总之,一心耳,以其存主而言,谓之意;以其存主之精明言,谓之知;以其精明之地,有善无恶,归之至善,谓之物。识得此,方见心学一原之妙。不然,未见不堕于支离者。”[2]462此心即此性,有善而无恶,是为至善。识得此心,就识得心学本原之妙,否则,学问未有不堕于支离散乱者。所以,学问为为人,就是学为孔子相传的一原之心法。
由于心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刘宗周于1631年即祟祯四年,创立“证人社”,希望以此来聚集士人,传播孔孟儒学,以扭转王学未流空疏禅化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弊端。《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刘宗周著作提要》曰:“宗周讲学,以慎独为宗。”[2]708又曰:“宗周独深鉴狂禅之弊,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务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其临没时,犹语门人曰:‘为学之要,一诚尽之,而主敬其功也。”[2]709证人书院的成立,就是要用慎独与诚意来扫除社会上的“狂禅之弊”。
“证人社”成立之后,刘宗周与当时名士陶奭龄分席而讲,双峰并峙。陶奭龄也是绍兴府人,他与自己的胞兄陶望龄都是王学的传人。王阳明之学经过王畿、周汝登,再到陶氏兄弟,经过三代的传承,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刘蕺山集提要》曰:“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唱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2]710陶奭龄主张识得本体,即是工夫,倡为因果之论。这与刘宗周的理论颇为相左。因为,刘宗周主张本体工夫不能分割,本体要在工夫中得到体认。陶奭龄曰:“行不至处,正是知不至处。致知在格物,则不必复言行矣。”[4]550-551陶奭龄认为,能够致知,则不必再提躬行了。而刘宗周则反对陶氏这种空疏的学问,提出了即慎独即诚意的学术宗旨。慎独侧重于主观之心,而诚意侧重于客观之性。慎独与诚意相提并论,不可偏废,即是心与性打成一片,即心即性。刘宗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曰:“学则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即本体,即工夫。”[5]29可见,刘宗周提倡知行合一,主张即本体即工夫。当然,尽管刘宗周主张慎独与诚意同样重要,但刘宗周鉴于当时不少士大夫重本体而轻工夫的问题,更加注重坐下工夫。正因为如此,刘宗周认为,真正能够证得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即便未尝诵读读书,也是值得推崇的君子,而那些立德、立功、立言之仁人志士,则更不用说了。在刘宗周的著作中,有大量的文章是专门为那些道德高尚的普通无名人士来进行立传讴歌的。例如,胡孺人就是这类言行举止“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贤妻良母。刘宗周《谭母胡孺人七十寿序》曰:“予自辛未三月鸠同志讲学于陶文简公祠,相与证其所以为人者,题其社曰‘证人’。……夫太孺人未尝诵古人书、读古人诗,以求所为人而证之,而所至能不愧其为人如是。”[5]88刘宗周对一个妇女也大加赞赏,可见,《人谱》在于证人,以证得其至善之心性。
二、家谱寻远祖,《人谱》寻“意”根
众所周知,任何家谱首先要认祖归宗,认定自己的某个远祖,让子孙后代逢年过节虔诚地祭拜,以便排辈序齿,歌舞宴席,从而和谐家族,凝聚人心。元代无名氏《合同文字》第四折:“我只为认祖归宗,迟眠早起,登山涉水,甫能勾到庭帏。”[6]登山涉水,起早贪黑也要回归故乡,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不易的情愫。所以,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并使人为之潸然泪下,其深刻的内涵就在于此。
从伦理上来看,既然家谱要从家族源头上确定自己的远祖,那么,《人谱》也应当在人生心性方面寻找最初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就是“意”根,即“独体”或“诚体”。
据此,刘宗周反对许多学者把“意”看得太浅的作法,于是特意提升了“意”的品格。打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意”不是稗种,也不是枝叶,而是嘉谷、根荄。刘宗周曰:“争之者曰:‘意,稗种也。’予曰:‘嘉谷。’又曰:‘意,枝族也。’予曰:‘根荄。’是故知本所以知至也,知至所以知止也。知止之谓致良知,则阳明之本旨也。”[4]278“意”是生根发芽的种子,具有生生之机,是致知之本、良知之本。正因为如此,意才能成为心之主宰。可见,意既是伦理的,也是道德的。刘宗周《学言下》曰:“心之主宰曰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4]447意为心之本,不是以意生心,而是说,意是心的灵明。因为,心是一个虚体,其中有一点精神,这就是“意”,它是心的指南针,总有一个固定的指向,但并不滞于有与无。刘宗周曰:“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着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然定盘针与盘子终是两物。意之于心,只是虚体中一点精神,仍只是一个心,本非滞于有也,安得云无!”[7]1554
既然意为心的指南针,则意不是心之所发,而是心之所存,因此,刘宗周反对朱熹视意为所发的观点,并认为意为吉凶先见之机,也为阳动之微。原因在于,如果意是心之所发,则无法知晓何者为心之所存。如果心为所存,意为所发,就意味着所发先于所存,这就与《大学》知本知善的主旨完全相反了。刘宗周曰:“意者,心之所存,非所发也。朱子以所发训意,非是。《传》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一于善而不二于恶,正见此心之存,主有善而无恶也。”[2]394-395此“意”一于善而不二于恶,表明心有善而无恶。而有善而无恶之中又见出一个“独”体,此意此独也,而此“独”乃仁义礼智之别名。刘宗周《阳明王子》曰:“‘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4]258可见,王阳明学术主旨在于致良知,而刘宗周学术主旨则在于寻意根,证独体。诚如彭启丰《刘蕺山先生文集序》曰:“阳明教人致良知,而先生教人证独体。”[5]725
既然“意”为“独”体,则意与“知”“念”和“志”等都有区别。首先,意与知并不相同。意属于道德理性,而知则属于知识理性。其次,意与志也不相同。意,是心的指南针,是心的所往,而志则是心的所之。所往与所之并不相同。心之所往是中气,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而心之所之则是和气,处于已发之时。刘宗周说:“心所向曰意,正是盘针之必向南也。只向南,非起身至南也。凡言向者,皆指定向而言,离定字便无向字可下,可知意为心之主宰也。心所之曰志,如‘志道’、‘志学’皆言必为圣贤的心,仍以主宰言也。心所之与所往异。若以往而行路时训‘之’字,则抛却脚跟立定一步矣。意者心之中气,志者心之根气,故宅中而有主曰意,静深而有本曰志。”[7]1557另外,意与念也不同。意没有起与灭,而念有起与灭。所以,意还可以纠正念的偏差。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一点:“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又问:‘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7]1555所以说,“意”位于心之隐微之处,是太极,是至善,永远处于不动不静、亦动亦静之中。
理解了“意”之所以为“意”,则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本体工夫都可以做到一齐俱到。姚名达《刘宗周年谱》记载:“推之‘存心’‘致知’,‘闻见’‘德性’之功,莫不归之于一,然约言之,则曰:心之所以为心也。又就心中指出本体工夫合并处;曰诚意。‘意根本微,诚体本天’,此处著不得丝毫人力;惟有谨凛一法,乃得还其本位;所谓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此慎独之说也。”[2]466从心中指出本体工夫合并处,称之为“诚意”。而从心之表里来看,则“存心”“致辞”“闻见”和“德性”之功,都可以归之为“诚意”。“意”根本微,“独”为其本,“诚”为其用,则“诚意”又可称之为“慎独”。所以,“谱人”就是在“意”根上讨个分晓,以便见之于躬行。刘宗周《证学杂解》曰:“古人慎独之学,固向意根上讨分晓,然其工夫必用到切实处,见之躬行。”[4]264
三、家谱别姓氏,《人谱》别贤愚
任何家谱对自己的姓氏都是情有独钟,而且还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对不属于自己的族群都有一种天然的排他性。同样,《人谱》也对自己心目中的“族群”有着执着的认同,这个“族群”就是历代的圣贤。在这种观念下,刘宗周特别有意识地区分人之贤愚,其整个著作中,常常运用“圣愚”“人禽”“君子小人”之类对比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刘宗周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使人迁善改过,从而进入圣贤之境界,这就是《人谱》的创作意图之所在。
正是本着别贤愚、入圣域的理想,刘宗周《人谱》努力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之谱系。从整个理论结构来看,《人谱》分正篇、续篇和杂记等三大部分。正篇包括《人极图》和《人极图说》等两篇。续篇包括《证人要旨》《纪过格》《讼过法》(即《静坐法》)和《改过说》等四篇。而杂记包括《体独篇》《知几篇》《定命篇》《凝道篇》《考旋篇》和《作圣篇》等六篇。从理论体系来看,正篇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推导出自己的“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4]3,这是一个从天道落实到人道的过程,此乃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张本。续篇《证人要旨》则通过闲居体独、动念知微、知礼成性、五伦敦笃、百行谨慎和迁善改过等六个方面来确定成为圣贤的整个过程。而《纪过格》《讼过法》(即《静坐法》)《改过说》则论述了迁善改过的具体做法。杂篇则通过大量历代圣贤的嘉言懿行来证明迁善改过的实际可行。总之,正篇立本体,续篇定工夫,杂篇则通过历史人物来树立入于圣域的榜样,三大部分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实际上,《人谱》的哲学起点在于从天道的“无极而太极”转化为人道的“无善而至善”。其中,天道是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而人道就是刘宗周自己所说的“无善而至善”。所谓天道,就是太极阴阳五行的化生机制、运行规律,而其核心则是“太极”。在刘宗周看来,天道就是太极的生生不息。其生成的过程是:太极与阴阳两仪、四时四象、五行五伦等等是“相蕴而生”[8],一齐俱到,即太极即阴阳,即阴阳即四象。而所谓人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的繁衍生成、全面展开,而其核心则是“人极”。这个“人极”就是“仁”,也就是“至善”“善”。从刘宗周的思想来看,天道落实到人道首先在于人极的确立。而天道的根源在于“太极”,人道之根源在于“人极”。这就是意味着天道之“太极”落实于人道之“人极”。换言之,天道之“无极”落实于人道之“无善”。由于“无极”是“太极”的“转语”,所以,“无善”也就是“至善”的转语。概括地说,无善就是至善,至善就是“善”。总之,天道、人道都是天理,也都是“至善”“善”“仁”。刘宗周《人谱·人极图说》曰:“无善而至善,心之体也。即周子所谓太极,‘太极本无极也’。统三才而言,谓之极。分人极而言,谓之善。其义一也。”[4]3在刘宗周看来,人心统摄易道,即心即易,这就意味着人心即是易道、天道。人心呈现着天地运行的规律和法则,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阴阳五行的交感变化而产生万事万物、一年四季,以及人伦道德,从而构成宇宙人生、大千世界。易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能够凭借人心而显露其自身,它总是活泼泼的、生机盎然。因为,阴阳之气流行不已,它生生不息,无始无终。而天地之间的易道又可以通过人心来统摄。刘宗周《读易圆说·自序》曰:“余尝著《人极圆说》,以明圣学之要,因而得易道焉。盈天地简皆易也,盈天地间之易皆人也。人外无易,故人外无极。人极立,而天之所以为天,此易此极也;地之所以为地,此易此极也。”[4]122人心之外没有易道,人心之外也没有所谓的太极。所以说,人心就是易道,易道就是人心。简而言之,就是“即心即易”。这就是说,人心灵虚,也具有生生之机,能够开显整个世界、孕生万事万物。刘宗周《会录》曰:“盈天地间,本无所谓万物者,万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类之五伦以往,莫不皆然。君父二字可推却身分外乎?然必实有孝父之心,而后成其为我之父;实有忠君之心,而后成其为我之君,此所谓反身而诚。至此才见得万物非万物,我非我,浑然一体,此身在天地间,无少欠缺,何乐如之。”[4]522“万物皆因我而名”,所以,万物非万物,我非我,我与万物浑然一体,没有间隔。
既然人道即是易道,人极即是太极。那么,人心即是至善,心性之本原就是一个“善”,人人具有尧舜之心,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然,现实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小人。其实,这些小人并不是天性如此,而只是由于他们的心性受到了蒙蔽,好像太阳因为云朵而见不到光明一样。而人只要拨开心性之中的云雾,就立即见到了太阳,成为圣贤。所以,圣人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心性是否受到了社会杂质的熏染。这种社会的杂质,就是阴阳二五之浊气。因为,天地之间,元气流行,生生不息,真实无妄。如水必寒,如火必热。人得之以为性,即为至善之性。当然,同此阴阳二五之气,陶铸万物,各不相同。即使在人类之中,也有清浊厚薄之不齐。所以,君子之中不能无小人,大道之外往往有异端。这就好像“桃李之仁同禀一树,而其仁各各化生千树万树,各一其树,枝枝叶叶,岂能尽如其母?亦有夭折而不成,臃肿而不秀者矣,然其为天下桃李则一也。故孟子一言以断之曰性善”[4]480。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刘宗周就把“善”立为人极,定为独体、本原,而体用一原,知行合一,即本体即工夫,形成了一个圆融的完美结构。
可见,《人谱》理论体系非常完备,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刘宗周自己也颇为自得,他特别告诫儿子,要把它视为家学一代代传承下去。因为,《人谱》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异端邪说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对于儒学的正本清源无疑有着莫大的裨益。其实,刘宗周创作《人谱》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当时虚无、功利之说进行辩论,使人明辨是非,知所趋向。刘宗周《〈人谱〉自序》曰:“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之惑人为甚。……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传染至今,遂为度世津梁,则所关于道术晦明之故,有非浅鲜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证人之意,著《人极图说》以示学者。继之以六事功课,而《纪过格》终焉。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总题之曰《人谱》,以为谱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训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4]1-2刘宗周认为,佛、道之说,沦于虚无,否定儒家性命之说,可谓是功利之说的极致,其语性而非性,语命而非命,而非性非命,则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这就是使人远离天道,迷惑世人,为害非浅。而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把修身养性、修齐治平视为立身处世的根本,而且要求每个人对社会对人类都要有积极的责任和担当。因此,儒释道之辨,就是仁义与功利之辨,就是人禽之辨。刘宗周《证人约言》曰:“语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利,利也;名,亦利也。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学者只就动念处早勘人、禽关头,是利是义,总不能瞒昧自己。”[4]489天理只有一个,全在起心动念之际。可见,学者应当“凛闲居而独处”,而不该让习染蒙蔽了心性,瞒昧了自己,从而变成了小人。
所以,要成为一个君子,就应当远离虚无与功利之说,并坚信自己具有善根、善性。刘宗周《学言中》曰:“学不可不讲,尤不可一时不讲。如在父便当与子讲,在兄便当与弟讲,在夫理当与妇讲,在主便当与仆讲,在门以内与家人讲,在门以外与乡里、亲戚、朋友讲。若是燕居独处,便当自心自讲,如何而为食息,如何而为起居,如何而为圣、为狂、为人、为禽。有一时可放空邪?才一时放却,便觉耳目无所施,手足无所措,大之而三纲沦,小之而九法。”[4]428-429为人就应当讲学不辍,不可有一时松懈,这是人禽之辨的关键。因为,学者,觉也。使本心常醒,保持一种天然的善性,而不使之受到世俗的熏染。否则,耳目滞塞,手足无措,从而致使治理天下的三纲五常、大法彝伦变得紊乱、颠倒。因为,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是相同的,并无凡圣之歧、彼此之异。但现实中,毕竟是非人即兽,间不容发。可见,天地之间,只有第一等人可做,而不可指望做个二等、三等之人。刘宗周对学者曰:“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人人可做。于此信得及,方是良知眼孔。因以‘证人’名其社。”[2]101
当然,刘宗周《人谱》中这种君子小人之辨,是儒家传统思想的一种拓展。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73,到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293-294,再到王阳明“人胸中各有个圣人”[9]93,等等理论都涉及到贤愚之辨。在他们来看,小人之出现,不是天然造成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所以,人只要能够克己复礼,就能够呈现出圣贤之本性。王阳明《书魏师孟卷》曰:“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9]280换言之,“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良知之外无学矣”[9]280。正因为人人皆有此良知,皆可为尧舜,所以满街都是圣人。那些害道之人,不是不知其中的原由,而是没有发挥自己的本心而已。其错误要么是失之于情识,要么是失之于玄虚,这都是用心不诚,从而造成对意根求之不实的表现。所以,真正的学者应当以良知为极则,以诚意为起照,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刘宗周《证学杂解》曰:“吾学亦何为也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尧舜之道,尧舜之心为之也。尧舜之心,即吾人之心。同此心,同此觉也,吾亦觉其同者而已矣。凡夫而立地圣域,一时而远契千秋,同故也。”[4]277-278
这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谓千载同心,遥遥相契。此心此理,它不因君子而增多,也不因小人而减少。刘宗周曰:“君子存之,善莫积焉。小人去之,过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积善积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尽人之学也。君子存之,即存此何思何虑之心。周子所谓‘主静立人极’是也。然其要归之善。补过所繇,殆与不思善恶之旨异矣。此圣学也。”[2]3-4刘宗周认为,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就是要做到“无欲故静”,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人极(至善)的典范。这就是说,既然人道至善,则为学者应当主静而立极,随时感应,感而遂通,达到无思而无不思,无善而无不善的境界。当然,天道有阴阳,人事亦如之,则君子小人之进退,就是否与泰轮转变化的象征。刘宗周曰:“天道有阴阳而人事应之,其象为君子小人。君子小人之进退,则否泰之象也。”[2]155智者当然懂得吉凶悔吝、趋利避害的奥秘。因此,能够做到日三省乎己,并且知错必改,这就是君子。这正如王阳明《悔斋说》所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9]909人之在世,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即为圣人矣。
四、小结
综上所述,《人谱》通过证心性、寻“意”根、别贤愚等方式,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人之谱序。生而为人者,皆具有一心。而此心即性,即有善而无恶。此心之中,一点精神即是“意”,即是“独”。而人之所以具有贤愚之不同,不是本心改变了,而是本心是否受到了遮蔽。所以,复归本心,就可以成为圣贤。在日常生活之中,君子应当懂得如何“慎独”与“诚意”,即慎独即诚意,即本体即工夫,从而迁善改过,入于圣域。这就是《人谱》的用意所在。人谱,就是谱人、证人,它不仅为众生指明了处于天地之间的“身世”,而且也为众生指明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正确方向。
总之,在当今人心浮躁的社会,推广《人谱》大有必要。而理解其书名,进而领悟其思想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读者的普遍接受,也有利于著作的广泛传播。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六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29.
[4]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5]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6]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434.
[7]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刘宗周.刘宗周全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234.
[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On the Title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Liu Zongzhou's Human Spectrum
YU Q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xing Zhejiang 312000,China)
Liu Zongzhou entitled his book Human Spectrum,the inspiration of which was derived from “family tree”concept,and the purpose of which was to build a personal pedigree on the basis of people.For two-phase comparison,peopl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title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Human Spectru:Firstly, “family tree”confirms the origin,while Human Spectrum confirms disposition;Secondly, “family tree”searches the genealogy ancestors,while Human Spectrum searches the root of“meaning”;Thirdly, “family tree”differentiates genealogy surnames,while Human Spectrum differentiates the sage and the fool.In a word,the meaning of the title is to“distinguish man”and“prove man”.To prove the reason for being a man is to prove that everyone has the nature of Yao and Shun,which is considered good nature of destiny.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objects,people inevitably make mistakes,but as long as they“cautiously live alone”and“keep sincere”,they can thus come into the domain of the sage.It is obvious that Human Spectrum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many other works,whose title give direct suggestion.This title not only refers to the content of the book,but also relates to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book.Through a careful inquiry,people can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Liu Zongzhou's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but also better promote his works'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Liu Zongzhou;Human Spectrum; “family tree”;confirm the nature;seek the root of“meaning”;differentiate the sage and the fool
B248
A
1004-2237(2017)05-0008-07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5.002
2017-08-31
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社科规划课题(16JDGH053)
余群(1968-),男,江西樟树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E-mail:teacheryq@sina.com
[责任编辑 邱忠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