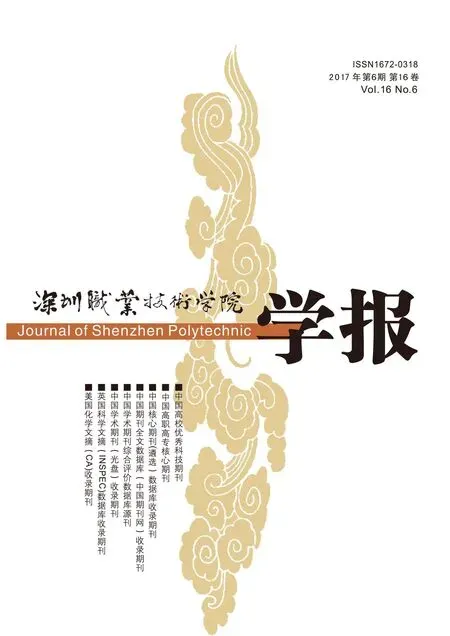失根的飘萍——评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悲剧人生
梁 晴
失根的飘萍——评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悲剧人生
梁晴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语学院,广东深圳 518055)
艾丽丝·门罗在小说《幸福过了头》中描述俄国数学家、小说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一生。19世纪末的欧洲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使得索菲娅短暂的一生经历了远离故土、失去家园、爱情幻灭等情感创伤,更无法拥有与她的学识相等同的社会认可。门罗对索菲娅的认同源起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深知在一个男权社会,追寻自由与理想的女性所面对的阻力和遭遇的挫折。
女性;情感创伤;歧视;挫折
2009年艾丽丝·门罗发表短篇小说集《幸福过了头》。时年78岁的门罗罹患癌症,此小说集曾一度被视为她的天鹅绝唱。小说集中收录的十个短篇弥漫着哥特式的恐怖气息:谋杀、性侵、暴力、创伤记忆……在门罗特有的波澜不惊的平静、含蓄叙事下,涌动的暗流是每一位主人公太多无法承受的幸福与伤痛。小说集的压轴之作——《幸福过了头》,以19世纪俄国女数学家、小说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850-1891)的生平故事为线索,追溯这位不平凡女性的悲剧人生。她远离故土,失去家园,一生飘泊不定。她的不幸看似个体命运的偶然,然而,深究其因,19世纪末的欧洲政治社会体制对于女性,尤其是出类拔萃的女性造成的束缚和歧视才是促成索菲娅凄苦人生的隐形推手。
1 逃离故园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出生于沙皇统治时期的圣彼得堡,父亲是一位脾气暴戾的将军,在巴利比诺的郊区拥有庞大的家族庄园。严格恪守东正教传统的贵族庄园是索菲娅和姐姐阿纽塔成长的家园。对于家园,曾有论者从地理意义、社会向度和精神屏障这三方面给予界定,在谈到家园的地理意义时,他给出如下定义:“家园的一种意义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它大而言之是自然,小而言之是那个美丽、和谐的葡萄园。”[1]18家园带来的安全感和温暖感是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的。巴利比诺庄园是索菲娅度过青春岁月的地理家园,见证了这位热爱数学、天资聪颖的小姑娘成长为婷婷少女。
然而,这座美丽的庄园并非遗世独立的伊甸园,它是沙皇统治下的千万个庄园之一,是俄国社会的微观缩影。19世纪的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也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一个女子在年幼时只能听命于一家之长的父亲;成年后则依附于丈夫。无论她多么聪颖优秀,都只能嫁人,成为全职家庭妇女。她不能违逆丈夫的意愿,更遑论抛头露面去社会上谋职。姐姐阿纽塔初涉文学创作,就招来父亲的勃然大怒,“现在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2]297年轻女人要想出国读书,只能选择先嫁人,由丈夫带出俄罗斯。为了能去德国求学,索菲娅嫁给自己并不爱的激进青年弗拉迪米尔,他们逃也似地离开了满载青春记忆的庄园,开始了带有欺诈性质的白色婚姻,这为索菲娅日后的情感不幸埋下伏笔。逃离故园的索菲娅终生被乡愁情绪所笼罩,她只能不断地通过写作遥寄对祖国和故园的思念。“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一切的热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2]325为了接受先进教育,为了赢得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人生,她逃离农奴制俄国,来到德国,希望在陌生的国度重新开始建立新的生活。
2 无处栖身
家园指示除了地理意义上的某个空间之外,还是一个开放的指向社会的概念,它联结个体与社会。社会成员也是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个体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处,获得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可和尊重时,也能感受到家园的安全与温暖[1]19。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渴求,索菲娅满心希望在德国能够重建家园。
与农奴制俄国相比,19世纪的欧洲其它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索菲娅曾先后在海德堡、慕尼黑和柏林求学,却因为其外籍女性的身份处处碰壁。德国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教授是唯一摒弃偏见、发现索菲娅才华的人。起初,他也不把索菲娅放在眼里,准备用几个难解的数学题就打发走这个登门求学的小个子女人。一个星期后,索菲娅带着新奇的解法再次到访。魏尔被深深折服,他不得不承认:“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飞得更远的学生。”[2]314就是这样一位让著名数学家倾佩的聪颖女性,在知名杂志发表文章时,却不得不以匿名身份投稿,以免被编辑识破她的女性身份。最后,也是魏尔教授悄悄瞒着索菲娅,将她的著作向法国科学院匿名投稿,才使她获得了世界瞩目的勃丁奖。人们给她鲜花和掌声,却“永远不会给她提供与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机会。”[2]290她以为在巴黎没有势利也没有欺骗,但是,“当她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他们的门。他们考虑这件事儿的时间,不会比考虑雇用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更久。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看见她,当然也不愿意请她去家里。”[2]309她热爱巴黎,却在那里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
魏尔教授写信求助以前的学生,请他帮忙在瑞典的一所大学为索菲娅谋得教席。瑞典是欧洲唯一一个给女性提供大学教职的国家。索菲娅因此成为第一位在北欧获得教授职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位在严肃的科学杂志担任编委的女性。即便如此,索菲娅依然得不到社会正确的认同和家的温暖。斯德哥尔摩的太太们邀请她去她们家,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们赞美她,炫耀她,因为她们把她当作一个怪人,“就像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者某些天才儿童,能毫不犹豫、不加思量地脱口而出十四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是礼拜二的天才儿童。”她得到的社会认可仅仅局限于一个有特殊才能的人,而没有被作为一个普通人接纳到日常生活当中。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脑子里全是旧观念的男人们仍然拘泥于这样的观念:女人的大脑里只有紧身胸衣和名片,和女人一说话,灌进喉咙的全是香水尘雾。”[2]310世代轻视女人的男人无法容忍一位女性可以做出比他们更杰出的成就。作为家园的社会外延,19世纪的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从真正意义上向索菲娅敞开大门。
3 爱情幻灭
家园同样也指由亲情、爱情、友情等人类高级情感构筑的精神屏障[1]21。索菲娅非常渴望被男性关爱和保护,她渴望婚姻家庭生活的宁静,但她的婚姻爱情生活从一开始就埋下不幸的伏笔。丈夫弗拉迪米尔只是她出国求学的工具,她从未爱过他,他们维持的只是生活伙伴关系。法学教授马克西姆给了索菲娅初次的爱情体验。他们的相遇注定会擦出爱的火花。他们都是被放逐在欧洲的俄罗斯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归故土。从最开始天涯羁旅的惺惺相惜,到后来互相被对方的才华所倾倒,索菲娅满心以为可以和马克西姆共度余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提供一个女人想要的舒适、稳定的生活,更是因为当索菲娅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她被他的自信深深迷醉,“这种他拥有的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小的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自信是你一生都需要的。”[2]339索菲娅纵然拥有过人的数学天赋,但终究还是和所有平常女子一样,希望与相爱的人,以一纸契约的婚姻方式相守终生。
他们的婚礼没有如期举行。订婚后不久,马克西姆写给索菲娅一封分手信,用冰冷的语气告诉她自己并不爱她,并请求解除婚约。大男子中心主义是促使他前后发生如此巨大心理变化的根源。马克西姆无论体型,还是知识结构都体积庞大。他通晓六国语言,精通俄罗斯、美国和古代帝国的法律与社会体制。他拥有自己的产业,不用工作都能过上富足舒适的生活。他是如此的骄傲与自信,却不得不生活在身材娇小的索菲娅的光环之下。因为他们共同的俄罗斯姓氏,马克西姆投稿的文章总会被误认为出自科瓦列夫斯基小姐。索菲娅凭借荣获勃丁奖而声名鹊起,鲜花、掌声、鸡尾酒会让她应接不暇。寂寂无名的马克西姆慢慢地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他觉得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更感觉自己受到冷遇和忽视,于是他选择了离去。他没有一个与他庞大的体积相匹配的宽广胸怀。
仅半年后,索菲娅孤身一人,凄然离世。一生与幸福失之交臂的索菲娅,却在临终留下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遗言:“幸福过了头”[2]348。马克西姆匆匆赶来参加葬礼,神态和语气依然冷漠,似乎希望撇清之前两人之间所有的情感纠葛,“他提起索菲娅,更像是提起一位他相熟的教授。”[2]348
4 隔世知音
门罗在小说集末尾的致谢中,专门介绍了与索菲娅的因缘交集,完全没有掩饰对她的喜爱。“某天,我在百科全书上查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她兼有小说家和数学家的身份,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有关于她的一切。”[2]350门罗在这个短篇小说中采用了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她希望客观地讲述这位优秀的女数学家坎坷跌宕的一生,却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不时地插入她的主观看法和评价,以表达对索菲娅的悲悯、惋惜之情。例如,门罗在叙述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的白色婚姻时,就使用过这样的语义独立片断:
“没错。年轻人,指年轻女人要是想出国读书,就会被迫经历这样的欺诈,因为未婚的俄罗斯姑娘没有父母的同意,就不能出国。朱莉娅的父母很开明,同意她出国,但是索菲娅的父母不同意。
多么野蛮的法律。
嗯。俄罗斯。不过,有一些年轻姑娘,在年轻小伙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路。”[2]318
“多么野蛮的法律。”“嗯。”“俄罗斯。”这三句话与前后叙述的文字并不相连,它们是独立的语义片断,是门罗作为叙事者插入的评论,却一句比一句强烈地控诉了俄罗斯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对女性的压迫与歧视。
与索菲娅相比,同样天资聪颖的门罗是幸运的,因为她有受教育的权利。出生于1931年的门罗,从小成长在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当时的加拿大,整体社会的高等教育程度并不高,大多数平民家庭的女孩子读完高中就会选择嫁人,成为全职家庭妇女。门罗却凭借11门课程中9门第一的优秀成绩拿到了西安大略大学新闻系的奖学金。她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普通女孩无法继续的大学学业,但是她依然处处感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种种压力。大学只读了两年,就不得不辍学结婚生子,一口气生下三个孩子,成天忙于照顾家务,她只能在餐桌边、在洗衣房的小桌前利用一些边角余料的时间从事自己热爱的写作。她也曾回忆自己与男性作家竞争而惨败的经历。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拒绝了门罗向他们递交的写作项目经费资助申请,原因就是她在申请书上填写了想利用部分经费来雇佣保姆,这样她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3]215。在门罗开始写作的年代,女性的角色首先是妻子、母亲,然后才是她的职业角色。社会还没有开明到可以允许一个女子雇人来帮她完成家务的地步。
门罗从未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也很反感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为了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过分压抑自身的女性特征,但从女性的视角关注和书写女性的生命体验一直是她小说的重点。1981年,门罗来到中国访问,与著名的女性作家丁玲会晤时,她说:“我只写我自己的故事,因为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真相”[4]13。门罗凭借她个人的成长经历,深知一个社会的女性期待对女性的生存影响有多大。门罗把索菲娅的故事作为压轴放在小说集末尾,正是为了回应男权社会不断对卓越女性的讽刺性提问:“你以为你是谁?”
如失根飘萍的索菲娅,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创伤,她的不幸并不是个人命运的偶然,在一个对女性充满歧视与压迫的社会,优秀的女性追寻自己的自由、爱情与职业理想注定会面对阻力、遭遇挫折。
[1] 李建军.坚定地守望最后的家园[J].小说评论,1995(5).
[2] 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 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4] Beverly J. Rasporich. Dance of the Sexes- Art and Gender in the Fiction of Alice Munro[M]. Edmonton: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90.
On the Tragic Life of Sofia Kovalevskaya—A Review of Alice Munro’s
LIANG Qing
()
In, Alice Munro depicted the traumas of Sofia Kovalevskaya, a famous Russian mathematician and novelist. In her brief 41 years’ life, Sofia had experienced more than she could bear. Her tragic life was the result of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old 19thcentury Europe where women were belittled and discriminated. Munro wrote this short story from the experience of her own setbacks in a male-dominated society.
women; trauma; discrimination; setbacks
10.13899/j.cnki.szptxb.2017.06.009
I206
A
1672-0318(2017)06-0050-04
2017-05-19
梁晴(1976-),女,四川乐山,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