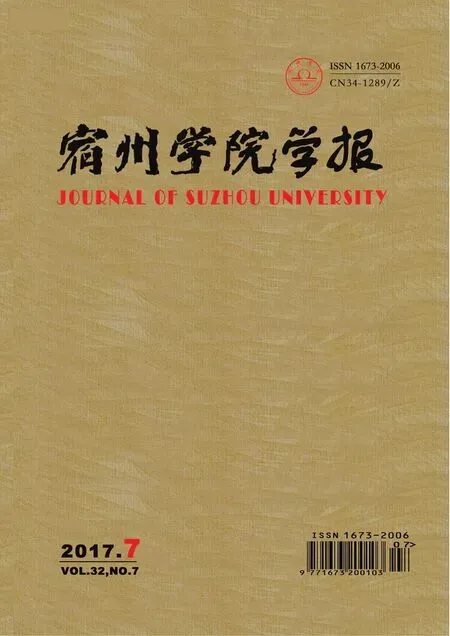知识产权“利润剥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邬晨牧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410083
知识产权“利润剥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
邬晨牧
中南大学法学院,长沙,410083
为了找到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最佳解决方案,运用比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通过对不同路径的法理基础、适用难点的思考,认为:利润剥夺纳入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将不当得利作为返还救济的一种方式,以无因管理作为调整办法都难以适用。因此,将利润剥夺并入法定赔偿,作为确定赔偿额的影响因素存在,将有利于发挥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也能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
知识产权;利润剥夺;请求权;法定赔偿
在传统民法中,侵权往往伴随着损害结果发生,侵权救济的依据就是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在知识产权的案例分析中,关于侵权的结果一般表现为侵权人的必然获利,而权利人有两种对立的潜在可能:(1)因侵权而遭受到实际损失,即“损害型侵权”;(2)间接获益,即“受益型侵权”[1]。对后一种侵权结果的不同理解和定性,会影响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选择,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利润剥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学说,如侵权损害赔偿说、不当得利说、无因管理说、利润剥夺独立说、法定赔偿说[2]。不同的学说对于利润剥夺中“利润”的性质认定不同,从而导致实践中对具体赔偿数额的认定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1 “利润剥夺”中“利润”的定性
首先需要区别开“利润”和“侵权损害”中关于“损害”以及“不当得利”中关于“得利”的意义。
1.1 “利润”与侵权损害中“损害”的区别
侵权语境下,与利润相区别的损害是指财产所遭受的现实意义上的损失。损害赔偿作为矫正正义的手段、填平规则的工具,是弥补受害人的“法律所认可的损害”[3]。具体内容既包括受害人既得利益的减少,即实际(直接)损失,也包括预期可能获得利益的损失,即期待(间接)损失,这种损害的计算标准将重点放在权利人利益方面。利润剥夺则不考虑受害人是否真正遭受所谓的现实或者预期的损害,计算标准将关注点放在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利润上,也就是说,“利润剥夺”是一种全部违法获益的返还[4]。因此,两者的区别:(1)所代表的主体是不同的,是对立面;(2)一个是数额的减少,一个是数额的增加。
1.2 “利润”与不当得利中“得利”的差别
从返还功能和实际效果上看,利润返还与不当得利返还是一样的,但两者仍有本质区别:第一,法理基础不同。得利返还遵循归属理论,法益的归属依据衡平思想确定,一方获益致使他人受损,必须向对方返还该得利;利润返还则是强制理论,侵权人只要获利就要返还,不论对方是否有利益减损[5]。第二,获利与损失的关联性不同。不当得利制度框架下,一方得利即为一方受损,获利与损失关联紧密;“利润剥夺”中,获利与所失根本没有关联性,侵权一方获利,被侵权一方也有获利的可能性。
2 对“利润剥夺”请求权基础的反省
2.1 纳入侵权损害的赔偿制度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实际损害的结果,也就是“无损害无赔偿”,赔偿的范围是以损害的范围为依据和界限。对物质损害范围的认定,先后经历过差额说、规范说[6]。德国法学家莫森在1855年就提出“差额说”。该学说表面上是站在权利人的角度,以权利人的财产遭受侵权的前后差额来确定赔偿的数额,实际范围是既得利益的损失,没有考虑期待利益,赔偿结果往往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规范说”则认为,只要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权利人的利益状态出现了差异,且二者有因果联系,即构成法律上的损害,也是侵权行为所致不利后果。也就是说,认定时不仅包括了“差额说”的范围,还要以权利人长期的经营状态为标准,按照侵权时间内应该获得但是没有获得的利益数额来判定。除此之外,侵权人付出的额外努力所获取的利益也被算入不利后果[7]。
在现实案例中,如果实际损失难以确定,把利润剥夺作为替代方式,将与侵权关联的获利都纳入赔偿数额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权利人的预期获利属于损失利益的性质,将其纳入赔偿范围无可厚非,但是,不具有可期待性和可确定性的获利部分,也就是即使不发生侵权也不会获利的部分也纳入到损失利益中请求赔偿,反而会使权利人不当得利。
2.2 纳入不当得利制度的反思
最先采取以不当得利制度解决“利润剥夺”问题的是1875年德国法院的一个经典案例:由于被告人没有经过原告人(作曲家)的同意,主观上有意地复制了原告作曲并且还进行了实际使用——投放到市场而获得很大的利益。德国法院最终认定:被告需要返还所获利益,让被告人把因为使用作品在市场当中所获得的所有利润“归还”原告人所有[8]。主张将利润剥夺并入不当得利学说,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侵权获利案中损失要件的认定。不当得利首先要求一方获利而使他方受损,二者间须有因果关系。然而,侵权之人的盈利不仅完全是因为侵犯了他人知识产权而所获得的,也有侵权之人自身所贡献的一部分,比如,通过市场营销、自身人脉、个人能力和影响等因素而产生的产品增值效果,这部分由于不是使他人受损而获得的利益,就需要刨除在外。不当得利的功能在于实现“去除由于不当行为所受的利益”,如果凡是因为不当行为所获利益就要返还,反而让受损的人获取另一部分不当的利益,这就有违背衡平的思想[9]。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在于如何确定其不当利益的范围、如何计算,实践中有客观和主观标准的划分:前者是根据市场授权许可的费用来计算;后者则考虑到受损之人的期许利益,即可区分出来的涉及知识产权的贡献的比重。
因此,通过不当得利规范利润剥夺问题,在实践中也很难实现利润分摊的剥离难题,如何计算专利在获利中的实际贡献率、剔除侵权获利中侵权人自身的贡献部分仍有待解决,尤其是在当今产品大多不是单一专利产品,作为集合专利产品,对每一项专利进行分离评估成本过大。而且,利润剥夺的前提是实施侵权行为,侵权和不当得利分别作为债的发生原因,解决路径是不同的,以不当得利的返还来作为侵权之债的救济途径,将会导致民法体系中逻辑结构的矛盾。
2.3 纳入无因管理制度的思考
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为他人来管理事务。立法目的是使无因管理人的权益不因救助他人的行为而受到一定的损害,是阻断侵权违法的一种法定行为。在我国民法中,与合同、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并列,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实践中,最早使用准无因管理理论支持侵权获利返还请求的是德国帝国上级商事法院于1877年9月12日的判决。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该案并非是适用无因管理的规定,而是类推适用了不法的无因管理之规定[10]。这种类推适用也存在问题:首先,不法无因管理在构成要件上强调“明知”,而在实际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很多侵权人并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其次,我国民法制度只承认“无因管理”,“不当管理”并未被纳入体系,与我国的立法现状不相适应;最后,无因管理制度的性质是鼓励互助精神、阻断侵权违法的一种法定规范,解决的是不法行为发生后,将不法性质合法化,是一种事后救济,将其作为利润剥夺的请求权基础,显然与利润剥夺原有的预防功能背道而驰。
2.4 对利润剥夺作为独立请求权制度的反思
主张利润剥夺独立作为一项赔偿制度的学者认为,“利润剥夺请求权”兼具损害赔偿与不当得利两种请求权的特性,当侵权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而获利,权利人就有权要求其返还该“利润”。但利润剥夺在性质上既不同于侵权损害赔偿,又无法与不当得利相契合。而实践中被认为支持此种学说的判例就是被称为我国专利侵权赔偿第一案的正泰集团诉施耐德专利侵权纠纷。
这一判决事后遭到了学者们的大肆讨论和质疑。学界普遍认为此做法有违现行专利权法的赔偿序位规定,而且缺乏合理性,作为国际知名商标的施耐德,其对所获利润的贡献率也很可观,品牌价值对涉案产品的价值提升与销量影响并未测算,该案在提起上诉之后以和解告终,法院也认为,在施耐德公司的利润中也存在品牌和技术因素。
尽管该案最终调解结束,但不妨碍人们思考利润剥夺作为独立请求权基础在实践中适用的问题。将利润剥夺作为独立的赔偿制度,不仅无须继续受“顺位”的限制,而且会僵化法院裁判,不利于案件实现社会效益。这极易引发对“专利蟑螂”的激励,不利于平衡技术发展、权利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三者的关系,尤其对于并未想要使用专利的权利人而言,此种做法方便他们通过诉讼获得意外之财,本来用于科技研发的精力被大量的诉讼时间占据,从而客观上阻碍了技术运用与创新,恰恰有悖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初衷。在网络环境中更是如此,实施直接侵权的用户由于分散、目标小、追究成本大、性价比低而不需要承担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则需要承担间接责任,如按照利润剥夺独立请求权要求以其所获利润赔偿,不仅区分单个侵权利润法律成本和技术成本过高,难以适用,而且与避风港规则相左[11]。
从法院的相关调研报告可以看出,以侵权获利来作为损害赔偿额的判定标准的难点在于:“由于被告不配合,法院又无强制调查的权利。”将利润剥夺作为独立的制度,不仅在理论层面缺乏基础,在实践层面也有操作难度。
3 “法定赔偿”吸收“利润剥夺”之合理性
知识产权内容的复杂性导致侵权损害结果的多样性,损害后果的查证和计算难度大,成本高,由此造成了诉讼事件中损失举证困难的现象,如果严格遵守侵权赔偿中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则会使权利人难以获得“全面赔偿”。而利润剥夺正是基于解决此种情况才出现的。与其相同,同样为了解决举证难应运而生的一种制度就是法定赔偿,也就是定额赔偿,我国《专利法》第65条第2款、《商标法》第63条第3款和《著作权法》第49条第2款都作了相关规定[12]。法定赔偿作为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在解决举证难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因而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法定赔偿的适用比例最高。例如,北京市各级法院2002-2013年著作权侵权赔偿案件分析显示,法定赔偿案件占比达98.2%,其他三种赔偿方式中,仅0.08%的原告提交了证据证明遭受损失,提交被告获利证据的原告有1.16%,有合理许可费证据的原告占0.56%。
第一,从实践操作而言,“法定赔偿”和“利润剥夺”都能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中举证困难的问题,并且都是知识产权全面赔偿原则的体现,这为“法定赔偿”吸收利润赔偿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依据。从制度目的而言,“法定赔偿”和“利润剥夺”都突破了传统的“无损失无赔偿”的民法理论,都强调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行为不易察觉,实施难度小,如果损害赔偿只是单纯的事后补救,不具有预防功能,实质上是激励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就是降低同一侵权人再次侵权的可能性,警示其他侵权人不敢侵权,具体而言,需要将赔偿数额标准提高到超出侵权获利,惩罚侵权人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有利于法官在确定赔偿额时对侵权获利进行考察,通过比较以实现预防效果[13]。超出侵权获利的部分赔偿给被侵权人,也并不会使被侵权人因获得额外的赔偿而被冠以“不当得利”的名号,因为法定赔偿将这一部分的赔偿法定化,剔除在“不当得利”的范围之外。
第二,从实践效果而言,将“利润剥夺”并入“法定赔偿”制度,能有效避免“赔偿过度”与“赔偿不足”的问题。前述几种途径都没有办法把侵权人的主观错误归纳到判定损害赔偿金额的考察因素当中,侵权人具有的对错与否,把侵权的利润全部赔偿于权利人,没有进行划分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在侵权人获得利益时,在实际所损失的侵权利润的构成因素没有穷尽排查的情况下,在此时将获利全部都归还给权利人,这不仅剥夺了侵权人本身的劳动或资本的价值,又让权利人有了获取不当利益的弊处;在侵权而获得利润没有办法包括实际的损失时,只把获得的利润当为赔偿的标准,权利人的损失将没法获得持平,不利于知识产权法“全面赔偿原则”的实现。因此,要做到衡平,就需更多地依赖于实践中法官对实际案情中各因素的把握,把利润剥夺作为“法定赔偿”中法官确定赔偿额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4 结 语
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赔偿案件中,“利润剥夺”侵权损害中有关赔偿范围的确定是以侵权人通过一定的侵权行为的获利来作为标准的,其请求权基础值得探讨。“利润剥夺”并入侵权损害赔偿的路径将侵权获利推定为“实际损害”,实质上是缩小了“利润”内涵,违背传统赔偿观念,且无法将基于侵权人自身的品牌价值、资本运作、营销能力等与侵权行为无关的因素所获得的收益纳入“损失”范围;不当得利说难以解决技术分摊的难题,无因管理说不适于我国民法规定的现状,其维护公序良俗的宗旨也与利润剥夺原本的预防功能难以契合,独立说缺乏法理基础和必要性。因此,将利润剥夺纳入法定赔偿制度,作为确定赔偿额的重要考量因素,不仅解决了难以剔除获利中侵权人自身贡献部分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实现损害赔偿的预防功能。此外,也很好地体现了利益平衡的思想。
[1]杨彪.受益型侵权行为研究:兼论损害赔偿法的晚近发展[J].法商研究,2009(5):77-87
[2]胡晶晶.知识产权“利润剥夺”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研究[J].法律科学,2014,32(6):113-120
[3]Dobbs D B.Law of remedies:damages,equity,restitution[M].1993:281
[4]王泽鉴.不当得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6[5]周友军.德国民法上的违法性理论研究[J].现代法学,2007,29(1):132-140
[6]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2
[7]Sharpe R J,Waddams S M.Damages for Lost Opportunity to Bargain[J].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82,2(2):290-297
[8]朱岩.“利润剥夺”的请求权基础: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0条[J].法商研究,2011(3):137-145
[9]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11
[10]张晓霞.侵权获利返还之请求权基础分析[J].知识产权,2010(2):51-57
[11]刘强.专利阻遏与专利强制许可[M]//安徽大学法律评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151
[12]周晖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司法适用[J].知识产权,2007,17(1):3-10
[13]温世扬,邱永清.惩罚性赔偿与知识产权保护[J].法律适用,2004(12):50-51
(责任编辑:周博)
DF523;D923.4
:A
:1673-2006(2017)07-0022-04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7.006
2017-03-15
邬晨牧(1992-),山西太原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方向。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