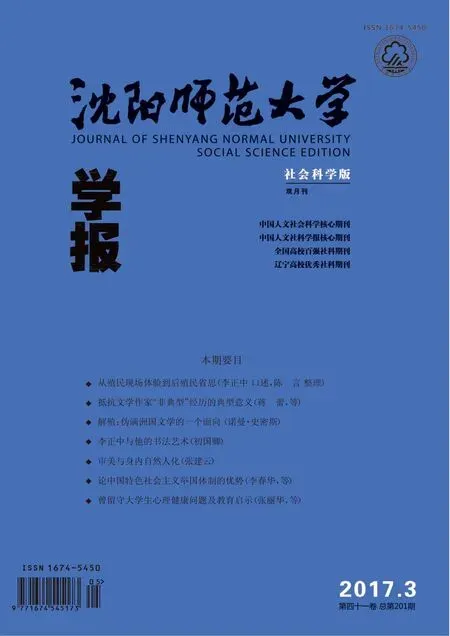抵抗文学作家“非典型”经历的典型意义
——以李正中文学生涯为个案
蒋蕾,荆宏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抵抗文学作家“非典型”经历的典型意义
——以李正中文学生涯为个案
蒋蕾,荆宏
(吉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在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作家中,李正中似乎是“非典型”的——不是最激烈的、不参加政治组织、没有被捕或逃亡。但对于抵抗文学研究来说,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生涯、作品发表途径等恰恰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他经历了伪满时期抵抗文学创作者的共同苦难:退稿、删稿、作品被撕页、诗集被扣押、被警察特务追查和监视。李正中发表抵抗文学作品的方式和途径,恰好也是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四种最主要呈现方式——公开发表、作品“逃亡”、非公开刊物发表、战后呈现。他于战后主编《东北文学》,为抵抗文学重新发表提供重要平台。李正中文学成就在于:不仅真实书写了伪满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更冒险传达抵抗意识,进行抵抗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东北沦陷时期;李正中;朱;《东北文学》;抵抗文学
在经历过伪满时期的东北老作家中,李正中先生是唯一至今仍在“书写”和“说话”的老人。尽管他的“书写”主要为书法而非文学,“说话”也限于和来访者交谈,很少在社会上“发声”,但他的存在表明:那特定时间地域的文学并未远去,仍与今天的我们发生着某种联系。
近年来,李正中先生作为书法家声名鹊起,而作为重要东北老作家的身份却被淡忘、遗失。对于这种“遗忘”,文学研究者是有责任的。在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作家中,他是“非典型”的。他不是言辞最激烈、作风最张扬的(当时作家李季风就特别大胆——被关东军宪兵队记录在案的抵抗文章有32篇,许多青年成为李季风“粉丝”),他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当时参与地下政治活动的作家不少——共产党员作家花喜露、国民党员作家王觉等);他也没有被捕入狱或逃亡经历(当时被捕作家很多,如哈尔滨作家陈、关沫南、王光逖被捕后都先后押解到长春,作家杜白雨、山丁等很多作家逃亡到北京)。然而,这位“非典型”的抵抗文学作家却经历了伪满时期抵抗文学创作者的共同苦难:退稿、删稿、作品被撕页、诗集被扣押、被警察特务追查和监视……如果没有法官身份和机智应对,李正中也面临被捕,也走到了牢狱边缘。李正中发表抵抗文学作品的方式和途径,恰好也是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的四种最主要呈现方式——公开发表、作品“逃亡”、非公开刊物发表、战后呈现。他于战后主编《东北文学》,为抵抗文学重新发表提供重要平台。非典型案例却具有典型意义。李正中作为抵抗文学作家的“非典型”经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明:伪满时期,无论作家多么小心、“低调”,只要作品暗含抵抗意识,就逃脱不了黑暗命运。
一、一位价值被低估的东北老作家
多年以来,李正中的文学地位与文学价值被严重低估。
我最早知道李正中先生是2006年,从发黄的老报纸上。一位笔名“柯炬”“靳革”的诗人,1939年前后开始频繁出现在伪满《大同报》《新满洲》等报刊上,作品连篇累牍。从伪满《大同报》1939年5月一篇文章末、被编辑误发的信息中得知:柯炬,本名李正中,就读于“新京法政大学”。之所以从当时的百余位文学人中关注到李正中,是因为他的诗清新俊朗又饱含抵抗意识。我在博士论文《精神抵抗: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以伪满〈大同报〉为样本的历史考察》(2008年)中将李正中列为两位书写抵抗文学的“愤怒青年”之一。
完全想象不到自己能与“柯炬”面对面。2009年,我到沈阳寻访李正中先生。初次访问,除了手里拿着李春燕老师提供的电话,也采取“外围采访”方式向一些学界前辈请教,了解他们对李正中文坛地位的看法。一位研究者说:李正中在伪满快结束时才进入文坛,其文学地位无法与古丁、山丁等相比。这个观点很长时间束缚着我。随着手中资料不断增多,对李正中文学生涯了解越来越深入,发现情况远非如此。
首先,李正中步入文坛很早,伪满结束时已是成名的成熟作家。李正中7岁开始发表诗歌,1938年登上伪满时期东北文坛重镇《盛京时报》副刊和《大同报》副刊,1941年被《新满洲》杂志称为“新进作家”。1945年战争结束时,李正中已出版5本书,这还不包括3本因时局动荡而排版却未出版的书。至此,他已在东北文坛活跃8年,创作丰厚,与当时诸多作家都有密切交往,是颇有名气的成熟作家。
其次,李正中在1945年光复后一度担当过东北文坛“召集人”角色。他担任《东北文学》主编,在东北作家中拥有号召力,集结了近二十位知名作家继续创作。他编辑出版5期《东北文学》、4本“东北文学丛刊”,主持了战后关于“东北沦陷十四年文学”的第一次总结。他个人创作在1945年达到巅峰:上半年出版1本小说集,“丢失”3本小说集和诗集;下半年出版2本诗集、1本小说集。
从7岁至25岁(1928年至1946年),李正中主要文学生涯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学少年:“九一八”前即发表文学作品。李正中生于1921年,从年龄看确属东北作家“小字辈”。他比作家小松(1912年生)小9岁,比作家山丁(1914年生)小7岁,比女作家梅娘(1917年生)小4岁,比女作家杨絮(1918年生)小3岁……1945年战争结束时,他年仅24岁。但其文学生涯却早在“九一八”前就开始了。1928年,他在上海《小朋友》杂志发表短诗,当时还是吉林省伊通县立第一模范小学的学生。李正中13岁步入东北旧体诗坛。1934年12月,“吉林北大街市立中学第二十五班”学生李正中向《大同报》投稿“杂记《记李进士轶事》”,并在新年征文中获奖。1936年,15岁的李正中出版旧体诗集《余荫馆诗存》(吉林市永吉印书局)。从他以“郑中”笔名发表在《盛京时报》的旧体诗《新秋吟:并序》[1]《呈寄园主人二首》[2]等来看,虽是少年,诗中却大量用典,与年长的文人雅士有往来交集。
第二阶段,新进作家:伪满中期进入东北新文学领域。1939年,他以笔名“柯炬”“靳革”“里刃”等频频出现在伪满时期东北的新文学领域,在《大同报》的《文艺》副刊及《新满洲》《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此时,他就读“新京法政大学”,与同班同学满占鳌成为文友,二人并肩创作。1941年底,他出版第一本新文学作品——小说集《乡怀》①《乡怀》由长春益智书店出版,作者署名柯炬,全书共104页。。到1945年8月战争结束,他共出版4本新文学作品集:小说集《乡怀》(益智书店)、诗集《七月》(自费出版)、小说集《》(国民书店)、散文集《无限之生与无限之旅》(兴亚杂志社),还有3本书因时局原因排版而未印刷:小说集《走向旷野的人们》《绿色的松花江啊》、诗集《待旦集》。
第三阶段,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东北文坛“召集人”。1945年是李正中文学创作爆发期,也是其文学生涯顶峰。1945年1月,他的4本书先后交由出版社,但只有小说集《》问世,另3本书则排版未能印刷。1945年8月光复后,他不再有法官身份,进入国民书店担任编辑,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1945年9月,诗集《春天一株草》出版;1945年10月,他的小说集《炉火》出版并再版诗集《七月》。他同时主编出版5期《东北文学》、4本《东北文学丛刊》。1946年5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离开长春,文学生涯基本结束。李正中文学成就在于:不仅真实书写了伪满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心态,更冒险传达抵抗意识,进行抵抗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二、李正中经历是抵抗文学作家的苦难缩影
退稿、删稿、撕页、扣押、追查……李正中的经历是所有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作家经历的缩影。虽然他以法官身份侥幸逃脱牢狱,但是那些文字带来的险境,那种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及接踵而来、让人喘息不得的威压和恐吓,紧紧缠绕他、压迫他。他经历的是抵抗文学作家无法逃避的黑色遭遇。
相对于退稿、删稿而言,作品被撕页、书籍被扣押、本人被弘报处约谈并受警方调查而进入司法程序——这些才真正让人感到心惊肉跳。这意味着伪满当局正严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可能实施抓捕。许多作家处于危险境地选择逃亡,如作家李民(诗人杜白雨)、山丁等化名逃到北京。李正中没有逃亡,他说:“到了没有路可走的时光,一个人往往会因了绝望而归于冷静”[3]。他利用法官身份,巧妙运作、拖延调查,最终逃脱牢狱。以下是他的两段历险。
(一)诗集《七月》被扣,诗人被警方调查
2010年,与李正中先生聊到伪满新闻统制机关——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李老苦笑着说起一段往事:弘报处官员多次约谈,为着私自印刷诗集《七月》①2010年2月和5月,笔者多次到沈阳访问李正中先生。李正中曾经担任伪满“新京”地方法院法官。笔者围绕“伪满洲国新闻统治研究”向其了解伪满新闻法规的执行情况。李正中先生介绍法规情况之余,提及私印《七月》被伪满弘报处约谈的亲身经历。2015年4月18日,李正中先生接受笔者访谈,讲述此事来龙去脉。。他说起往事时轻描淡写,而我找到1945年再版的诗集《七月》,并从70年前旧杂志上找到事件的前前后后时,才知道李正中当时几乎身处绝境。
关于诗集《七月》被扣押,李正中1945年10月再版《七月》时写下《再版题辞》说:“它的第一版刚刚送到市场上去的时光,非但在仅少的部数之中遭到了扣押的噩运,并且,还因而牵连了作者。”[4]
到底是一本怎样的诗集?给作者带来怎样的“牵连”?1946年2月,李正中在《东北文学》撰文《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细叙自己和这本诗集的遭遇。原来,这部诗稿在出版过程中一次次受挫,未能通过官方出版审查。当这本诗集已在作者手里度过两年多时,李正中找到一条“忍辱偷生的路”,他到一家印刷工厂自费印刷。身为法官的李正中当然知道应该“避免被审查的当局发觉这种脱法行为”,但让诗集与读者见面的想法太迫切了,他铤而走险。然而形势不妙,“这一年,出版物的审查更加严厉起来,同时,思想犯开始了一批一批的大检举,我在这时期来销售这一册不经审查许可的书,无疑的是在给自己制造炸药。”[3]结果,他终于接到弘报处检阅股的电话,又有人到“班上”来调查。来人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写《七月》?第二,你为什么不经许可便擅自出版?第三,看情形你并非营利,那么印行的目的何在?”弘报处官员们研讨后认为,该书除出版手续不合法之外,还有三大罪状:
第一,书中的年代,具系中华年代;
第二,《霜花》一篇,寓意为弱小者的反抗;
第三,书名《七月》,在响应着卢沟桥事变的“七月”[3]。
由此,该案“移牒给伪首都警察厅特务科来发动司法权处理了”[3]。该案进入司法程序后,“约摸有两个月的期间,特务科的手足到处调查我,特务科也曾传唤过代售的书店,他们的搜查的魔网已经是张开了”[3]。此时,被捕只是时间问题。李正中在身处绝境时冷静下来,终于找到机会利用法官身份平息此事。但他仅仅逃脱入狱,痛苦煎熬都已经历。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那本被扣押的《七月》已无处找寻,我将这本1945年再版的诗集放在手中,只有巴掌大小,但印刷精美、图文并茂,书中配有诗人好友王金的版画。版画线条简练,诗歌隽永含蓄,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一种感伤的情愫。这本诗集堪称李正中诗歌代表作,长诗短句意境幽远,对于现实有一种明显的疏离感。那首被弘报处认定为“寓意于弱小者的反抗”的《霜花》,1944年11月发表于《华文大阪每日》,诗的开头让人心头一颤:“我和你是小小的,凝在人家窗板上的霜花。从开始了小小的生命,小小的心里充溢了恐怖。”[5]诗集中涉及的年代,确实是以隐去“民国”后的数字标注的。
(二)小说《诱惑》被撕页
不仅诗集《七月》被扣,李正中还经历了小说《诱惑》被“斩头去尾”的事件。
1944年7月,李正中的小说《诱惑》在《新潮》杂志发表,但遭到撕页处罚——第61-62页被撕,小说变得“无头”。这篇小说为连载,1944年8月编辑听命撤稿,小说又变成“无尾”。直到1945年12月《东北文学》创刊,《诱惑》重新刊载,才基本完整地发表,但原稿中被涂墨之处却再也无法恢复了。
李正中先生1986年撰文《〈东北文学〉发刊前后》②韦长明:《〈东北文学〉发刊前后》,《东北文学研究史料》第三辑(1986年9月),第107页。时写道:“《诱惑》是我1944年写的一个四万字的中篇,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连载的第一部分时,印刷完了的杂志被命令撕掉小说的第一页,这样的‘无头鬼’真比干脆禁止出售还难堪。”[6]这一本《新潮》杂志(1944年第7期),我们找到了,目录页中标有“《诱惑》……第62页”,但翻看整本杂志,没有第61、62页,第60页之后直接跳到第63页。这种撕页连累得前一篇小说——田琅的《漂泊者》(第56-61页)也没有结尾。
《诱惑》究竟写了哪些不被许可的内容呢?李正中回忆说:“书报检查老爷用毛笔在原稿上把以后章节中有关伪宪警贪赃枉法、买办资本家蹂躏妇女,市场萧条,民不聊生……这些作为时代背景和故事发展缘由的片片断断全给涂抹得不可辨认。”①2010年5月3日,笔者在沈阳李正中家中进行口述访谈,李正中讲述了关于《诱惑》被撕页的事件始末。从《东北文学》创刊号上重新刊发的小说开头来看,被撕页的“前半段”主要写了主人公“我”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及“就任”的情形和心态,这些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十分吻合,小说中男主人公情绪灰暗、女主人公之所以沦落完全是社会过错。
三、抵抗文学作品发表的典型途径
李正中在1939年至1945年间创作和发表许多具有抵抗意识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时命运怎样?能否公开发表?我们今天如何能够阅读到它们?总结李正中抵抗文学作品的发表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公开发表;二是作品“逃亡”,到伪满洲国以外地区的刊物上发表;三是在非公开出版物上刊登,逃脱新闻出版检查;四是战后呈现,伪满时期被退、被删、被撕页、被查封的作品在战后得以完整刊登或再版。李正中抵抗文学作品的发表方式,恰恰代表了伪满时期抵抗文学的书写与呈现特征。
(一)曲折书写,公开发表
曲折书写的诗歌,可以形成多种解释,在新闻检查中容易通过。李正中擅长采用隐喻手法,巧妙运用诗歌的象征性与朦胧意味。1941年3月5日他以“靳革”笔名在《大同报》上发表长诗《虚谎的誓语》,以一种欲言又止的口吻表达对现实的怀疑、对历史的沉思、对黑暗的痛恨及愤怒与抗争。他在诗中写到:“一个人生了,一个人被征服了,一个人死亡了”“为什么要有生?为什么要有斗争?为什么要有死亡?”“用人类的语言,你喊,——从现在起,我将不在温室里种花草了”[7]。
1941年12月9日,他在《我们的文学》副刊上发表《古城之献》,诗歌在对古城吉林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反复追问:
多少年火烧过船厂
多少年又矗立起楼房
然后话题一转:
新街市你带来了什么
载古城愈寂寞,寂寞
穿着都换上人造丝
吃食就都是高粱米[8]
所谓“新街市”指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进行的充满殖民气息的都市建设。而“吃食就都是高粱米”一句,直戳中国人痛处。1938年,伪满颁布《米谷管理法》,规定中国人只能食用“乙类粮”即高粱、玉米、谷子,这是伪满时期日伪统治者对东北民众的歧视和迫害。不仅仅食物让人感到难以下咽,还有一种强烈的屈辱感挥之不去。
(二)直抒胸臆,作品“逃亡”
相对于《虚谎的誓言》《古城之献》等诗,李正中发表在《华文大阪每日》上的散文《江山》②韦烽:《江山》,《华文大阪每日》1944年第4期,第32页。《丑笑》直抒胸臆,率直表达。这两篇文章是被伪满洲国检查机关“砍掉”的,“曲线”在海外发表。《华文大阪每日》是在日本办而在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中文杂志。由于报刊检查存在空隙,许多沦陷区作者将其作为作品发表的另外渠道。
散文《江山》大胆表现了作者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对于故国的怀念,他写道:
唉!铁打的江山哪!
从梦里我记忆着你屹立,从梦里我又看到你粉碎,你的豪华岁月呢?
……
有一天暴风雨吹来,你终于粉碎了。
我知道这是个梦,这全然是个梦[9]。
“铁打的江山”意为“国家”,这一说法尽人皆知。李正中毫无避讳地书写自己对于江山“破碎”的痛心及“记忆着你屹立”的梦。
与《江山》同时发表的《丑笑》更加露骨。文中写到一种“丑笑”的“可憎的动物”,他“拉着我坐下”,但我从他身上的某部分“嗅到了血腥”,看着他露出“一排白色的牙”[10]。
这两篇散文原是1941年写给“激流艺文丛书”第二辑《草莽集》的,被检查机关删掉后,作品“逃亡”到日本,在《华文大阪每日》发表。
(三)非公开出版物上发表,逃脱检查
李正中1939年到“新京法政大学”读书时,被推举去办校刊。他借用诗经中的“凯风自南”而将校刊取名为《南风》,实际是表示内心向着南方的祖国。在校刊上,他发表小说《华丽的废墟》,小说表面讲一个学生误入歧途的故事,实际却说伪满洲国都市表面华丽却是乱石岗。半个世纪后的80年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到长春旅行,他感叹伪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好像“废墟”——实际上它们建造时就是华丽的废墟。
李正中说,当时校刊是非公开出版物,不接受出版审查,他作为校刊主编有发稿权。这种非公开出版物实际上带有准地下传播性质。1940年,校方不让他主办校刊了,校刊名称也改为《八》——取自日本战时提出的“八 一宇”。
(四)战后出版,重见天日
伪满期间被扣押、查封的诗集《七月》及被撕页、退稿、删改的作品《诱惑》《长城外的人》等,在1945年光复之后获得再版和重刊,重见天日。这种“战后重现”也是东北抵抗文学在战后浮出水面的重要方式。
1945年10月,诗集《七月》作为“东北文学丛刊”之一获得重新出版。再版的《七月》,前面写有《再版题辞》,结尾处在《后记》后面又添加了《再记》,简要叙述了诗集《七月》被扣押、查封的经历,算是一种控诉。
被撕页和撤稿的小说《诱惑》,刊登在《东北文学》创刊号(1945年12月)上,被撕页的前半段得以恢复,被撤稿的后半段也得以重现。虽然小说被检查官用墨涂黑的段落无法恢复,但重新刊发的小说基本叙述了完整的故事。当有人质疑《诱惑》为何曾经发表过又再度发表时,李正中在《东北文学》一卷四期(1946年4月)的《现实与态度》中说:“诱惑,它的前半部刊出当时便遭受到了被删除的命运。”“像这样被断腰砍头的作品,似乎在光复之后也没有什么不可全盘刊出的理由。”[11]
李正中的另一部小说《长城外的人》(署名魏之吉),发表于《东北文学》一卷第三期(1946年2月)。这篇小说也是1944年被《新潮》退的稿子。这篇小说为书信体,表面上看是两个兄弟相称的好友间的通信,仔细看来却发现它隐藏着另一个秘密:一个抵抗文学书写小群体的故事。通信双方是秦莽和李正中,恰好是我在博士论文中提到的书写抵抗文学的两位“愤怒青年”。秦莽(伪满医科大学的学生)撰写过更多、更为激烈的抵抗文学,1941年底“一二三零”事件中被捕。入狱前他一直在筹备出版“激流艺文丛刊”,包括诗集《野火集》和散文集《草莽集》,这两本书的出版困难重重——既遭受检查机关干涉,又缺少出版资金。后来主编秦莽入狱,书没有出成。小说《长城外的人》恰好记录了“激流艺文丛刊”筹措过程中的通信往来,其中提到的书名和涉及的作品名都是真实的,比如《野火集》《草莽集》及李正中的散文《江山》等。这些“通信”也记录了当时伪满文化界真实情况:一些杂志“废刊”、诗歌无处发表;某杂志申请审查,一期就有3篇文章“遭厄运”,其中有李正中和秦莽的诗。这样具体写实的小说,在伪满时期还没到审查机关就被杂志社退回了。
另外,发表于《东北文学》一卷五期(1946年4月)的散文《跋涉·忍耐·微光》也是李正中撰写、伪满时期被撤的稿件。这篇散文再次写到“废墟”,它说:“某个废墟的地带,宛如太古的洪荒。某个饥馑的岁月,熬干了大地的血液。”“我们这群渴望新的生命的汉子,拉着酸楚的两脚,拽着没有气力的身子,越过了一条条辽阔的江河,越过了多少险峻的山岭。我们依旧继续走向无限的江河,无限的山岭……”[12]文中说:“我们知道:不是希望,就是死亡。”[12]这篇散文本已编入《新潮》1944年5月号“散文特辑”,被检查机关命令撤掉,最终于战后得以公开发表。
四、抵抗文学撰写的内在动力
既然写抵抗文学有生命危险,作品又很难发表,李正中等作家为什么还非写不可呢?由李正中创作经历可知:创作共同体是抵抗文学作家的精神支柱,对伪满现实黑暗的了解及内在爱国情愫是写作的强大动力。
李正中文学创作受到朋友影响。他最主要的文友是满占鳌和秦莽。李正中1939年5月一到“新京法政大学”,就认识了同乡和中学校友满占鳌。从此,他们两人每天晚饭后一起散步、一起投入文学创作。他们合作发表过很多作品,如1939年11月至12月在《大同报》连载17次的长诗《北地梦》是“克大、柯炬”联合署名的(克大为满占鳌笔名)。满占鳌也具有抵抗意识,他于战后加入国民党。秦莽是一位笔锋更为犀利的诗人,他在《大同报》上发表过多篇抵抗文学诗歌,因与《大同报》编辑、抵抗文学作家李季风关系密切、受牵连入狱。正如小说《长城外的人》中所展现的那样,秦莽曾在一段时间里与李正中频繁来往和通信,相互切磋,共同撰写抵抗文学。李正中的散文《江山》《丑笑》等本来都是为秦莽编辑的“激流艺文丛刊”而写的。写作群体对李正中构成很大影响,他们之间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评价标准,有共同的文学追求,鼓励着他朝这个方向前进。
李正中的法官身份也使他更加深切地了解伪满洲国的黑暗,产生更强烈的爱国情感。他曾为几位受冤的农民辩护。当时长春发生一起日本警察被杀案件,几位恰巧经过的农民被当作杀人犯抓起来,屈打成招,即将判处死刑。李正中担任了他们的辩护律师,经过调查发现这完全是冤案。他为这几位农民收集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辩护成功,几位农民无罪释放。但李正中先生说起这个故事时苦笑了一下,因为这几位农民刚刚逃脱监狱和死亡,就被送去做劳工了,估计还是难逃噩运。法官身份使他接触到更多底层,也更了解殖民统治的残暴。
李正中的另一位好友梁肃戎,在爱国思想方面给予他更大激励。梁肃戎是李正中在“新京法政大学”的同学,也是法官同事,他秘密参加国民党地下组织,进行反满抗日活动,身份暴露后被捕并被审判。李正中冒险与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为梁肃戎做辩护律师,想使他免刑。没想到,梁肃戎在法庭上大声斥责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愤然地说:“不要为我辩护了,判我死刑吧。”李老回忆此情此景时,眼角湿润了①2010年5月3日,笔者在沈阳李正中家里进行口述访谈,李正中讲述了1944年为梁肃戎辩护的经过。。对他说,撰写抵抗文学成为不说不快的事情。
书法对于李正中文学道路也有深刻影响。李正中自小习书,1938年11月——当时还是高中生,他的书法作品就在“满日华书道亲善展览会”获得最高奖。此后,他几乎每年都在伪满洲国美术书法展中获奖。他因此与一些年迈的书法大家产生交往,经常出入原《大同报》社长王希哲家中研习书法,与著名书法家孙晓野来往颇多。1938年前后撰写旧体诗与其擅写书法有密切关系。与书法、旧体诗紧密相连的是文人志士忠贞爱国的情怀,李正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骨髓的继承,气节、爱国与旧体诗等一起内化于心。
五、李正中为抵抗文学战后重现搭建平台
1945年是李正中人生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创作爆发——一年中出版3本书、再版1本书,还不算3本在动荡之中已排版而未能印出的书。这一年,他抛开了法官身份,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文学人,施展文学抱负。这一年,他不再仅仅进行个人书写,以当时东北唯一大型纯文学刊物主编身份对东北文坛进行建构。虽然属于他的时间非常短暂,他来不及实施那么多计划,但他组织了战后对东北沦陷十四年文学的第一次清点与反思,尽最大努力组织作家继续创作,并为那些曾经湮没无闻的抵抗文学地下书写提供重现舞台。
(一)组织作家对东北沦陷十四年文学进行清点与反思
《东北文学》于第二期(1946年元旦)开始,设立“结算与展望”专栏,陆续刊登关于东北沦陷十四年文学的研究,一共形成7篇总结性文章:《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姚远);《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林里);《过去十四年的诗坛》(李文湘);《东北童话十四年》(陶君);《译文十四年小记》(孟伯);《沦陷期中的东北戏剧》(孟语);《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林里)。
一期刊物中重磅推出5篇关于“东北十四年来”的文学总结,显然出于精心策划。这是战后对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第一次研究与反思。7篇文章均出自东北作家之手,从小说、散文、诗歌、童话、译文、戏剧、女性文学的角度回顾梳理伪满时期文学创作,对于重要作家、作品进行标记。李正中亲自撰写了其中的2篇:《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东北女性文学十四年史》。
作家姚远撰写的《东北十四年来的小说与小说人》梳理了报纸副刊、杂志、单行本所刊载的重要小说。这篇文章排除门派之见,以公允客观态度列出一份伪满时期重要小说创作的清单,其中既有“艺文志”派作家,也有“文选”“文丛”作家,还有其他无派作家,特别是关于资料零散的“报章文艺”给予详细梳理。李正中撰写的《东北散文十四年的收获》同样开列关于伪满时期优秀散文的清单,推出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并对作家进行评点。诗人李文湘撰写的《过去十四年的诗坛》,更是对于伪满诗坛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开创了对于这一时段诗坛的深入研究。陶君的《东北童话十四年》也开列出多份关于伪满时期童话创作的作品清单,这些在今天都已成为宝贵资料和重要研究线索。孟伯的《译文十四年小记》对伪满时期译文作品进行了全盘梳理。这些作者是李正中认真挑选后确定的,他们都对研究领域有深入了解、有发言权。
“结算”是为了新的开始,在《东北文学》第二期的后记里,李正中说出自己的计划与抱负:“我们打算逐渐确立战后建设东北文学的全盘问题。在这之先,作为一种准备工作,似乎也是非常必要的。由是,我们才特约了各部门的知名之士来执笔了过去东北文坛十四年的结算文字。”[13]对于引领东北文坛朝着新方向努力,李正中有着宏大计划,可惜动荡的时局没有给予他时间与机会。
(二)做了八个月的东北文坛“召集人”
“八一五”光复后,苏联红军进入长春,城市治安混乱,作家们各奔东西,创作停滞。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正中创办《东北文学》,将东北作家们重新组织起来、鼓励大家继续创作。当时集结在《东北文学》旗下的作家除了“编辑委员会七人”的张文华、张辛实、张戈禾、田琳、朱、方季良等,还有田兵、李文湘、韩护、姚远、孟语、杨絮、金羽、蓝苓、乙梅、南吕、君颐等,总共约20位。李正中主持分工,请编委会成员各自联系一批作家,如由张辛实负责联系原《艺文志》同人,张戈禾和田琳联系电影厂作者等。
李正中曾写诗回忆当年艰辛的约稿生活:“为索新篇敢跳墙”[14],这说的是去电影厂找田琳要稿时跳墙爬窗的经历。经过努力,许多作家接受稿约、在纷乱环境下坚持写作,如田琳写出了《失掉太阳的日子》,回忆自己的狱中生活和入狱的前前后后。田兵撰写了诗歌《黄尘》,张文华撰写了《胜利之歌》,歌颂抗战胜利。韩护撰写了文艺评论,对战后书写的“抵抗文学”进行尖锐点评。《东北文学》在短短时间5个月时间里共推出约七十八篇作品,除掉为伪满时期未能发表的文章提供重见天日机会以外,更多的是刊登东北作家在光复后的新创作。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李正中集合作家开展创作,推出5期《东北文学》。这是当时东北唯一大型纯文学杂志,也是光复后东北作家群体的一次大聚集。《东北文学》结束后,东北作家分散各地,再也没能聚拢在一起发表作品。
(三)为抵抗文学地下书写的战后重现提供舞台
《东北文学》创刊号是厚厚104页“巨献”,其中至少有60页为伪满时期抵抗文学作品,占总篇幅的60%。这一期刊登了但娣的《血族》、朱的《小银子和她的家族》和韦长明的《诱惑》,这3篇小说都是伪满时期被杂志社退稿和撕页、删改的。
但娣(田琳)的小说《血族》讲述了主人公“我”自“首都”的病院(象征监狱)逃命出来,到吉林市哥哥家里勉强度日。文中展现的日常生活反映了残酷事实:伪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从肉体到精神。从生存到尊严,他们都受到无情践踏。小说中呈现的是阴天暗地的伪满景象,文中有大量象征和隐喻,充满了死亡意象。关于这部小说的来历,《血族》作者但娣在《东北文学》第二期的篇首文章《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中确切地说:“首先我要解释的是《血族》那篇稿子,确系伪满时代所写作的。因为检阅不通过,所以就没有出版。所以,其中不但发生的故事是伪满时代的故事,就连我这写故事的立场,亦站在伪满的立场上。所有中间有日本人的故事,并且没有敢深刻的露出反抗的意味来,但在暗暗中自信尚有一种潜在的思想,而针对着当时的政治。”[15]这部小说在伪满时期只能保存在作者手中,成为一种地下文学,而《东北文学》给予小说重见天日的机会,使其能够与读者见面。
在《东北文学》作者中,有一位特殊女性——笔名“金羽”。她在《东北文学》上发表诗歌《你揉碎了我的梦》《泥泞的路》、小说《某医师的手记》,其诗歌创作于伪满时期。她是一位以主动隐藏方式进行地下书写的抵抗文学作者。金羽酷爱写作,伪满时期经常与李正中夫妇切磋诗艺,私下撰写大量诗篇,但直到战后才拿出来发表。金羽的诗集《泥泞》在《东北文学丛刊》中出版,诗中含有强烈的抵抗意识。
《东北文学》不仅刊登伪满时期不能发表的抵抗文学,还为作家们提供回忆伪满时期作品被封杀情况的机会。杨絮的《关于〈我的日记〉的被扣押》、满占鳌的《关于〈灵草〉》和李正中的《关于〈七月〉被扣押的经过》,刊登在《东北文学》一卷三期(1946年2月)上。杨絮在文中透露:有一篇《老妈子的日记》在《大同报》上刊载,未等刊完,编辑就被弘报处叫去数落一顿,原因是文章有辱官吏,老妈子的丈夫当兵去应该回来大团圆,不该一去无消息。结果编辑只好删改一番,写成大团圆结局。
在东北沦陷区抵抗文学作家中,李正中似乎是“非典型”的——不是最激烈的、不参加政治组织、没有被捕或逃亡。但对于抵抗文学研究来说,他的人生经历、文学生涯、作品发表途径等恰恰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
2017年是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八年抗战”也已改为“十四年抗战”,而关于那段文学史的研究却仿佛刚刚开始。李正中先生超然睿智,他的生命接近于“百岁”。他经历过太多风雨,并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但我们却必须铭记这些以笔为剑、以生命作代价书写抵抗文学的勇者,特别是需要深入剖析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文学形态的生成与属性。
[1]郑中.新秋吟:并序[N].盛京时报,1938-9-18(4).
[2]郑中.呈寄园主人[N].盛京时报,1938-10-20(4).
[3]韦长明.这都是为了我的《七月》[J].东北文学,1946(3):22-24.
[4]韦长明.再版题辞[M]//七月.长春:国民图书公司,1945:卷首.
[5]韦长明.霜花[J].华文大阪每日,1944(11):29.
[6]韦长明.《东北文学》发刊前后[J].东北文学研究史料,1986(3):109.
[7]靳革.虚谎的誓语[N].大同报,1941-3-5(6).
[8]柯炬.古城之献[N].大同报,1941-12-9(4).
[9]韦烽.江山[J].华文大阪每日,1944(4):32.
[10]韦烽.丑笑[J].华文大阪每日,1944(4):32.
[11]韦长明.现实与态度[J].东北文学,1946(4):6.
[12]徐衣雪.跋涉·忍耐·微光[J].东北文学,1946(5):40.
[13]编辑后记[J].东北文学,1946(2):109.
[14]李正中.田琳新居[M]//正中吟笺.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7.
[15]但娣.关于奴化思想及伪满作家——质之于要望先生[J].东北文学,1946(2):6-7.
Typical Significance of the“Non-typical”Experiences of Resistance Literature Writers——A Case Study of Li Zhengzhong’s Literary Career
Jianglei,Jinghong
(College ofJournalismand Communic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 130012)
Of the resistance writers in China’s northeastern Japanese-occupied areas,Li Zhengzhong is a seemingly“non-typical”one—he was not the most violent,he did not join in anypolitical organization,he was never arrested or became a fugitive.To resistance literature studies,however,his life experiences,literary career and publishing approaches are just loaded with heavytypical meaning.He experienced the miserycommon amongthe resistance writers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period:work rejected,abridged and torn off,poetry collection distrained,himself investigated and monitored bythe police.Li’s publishingapproaches are preciselythe four main demonstrations ofthe resistance literature of the northeastern Japanese-occupied areas,i.e.,public publishing,work“on the run”,non-public journal publishing and post-war demonstration.He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Northeast Literature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which became a significant platform for the re-publishing of resistance literature.Li’s literary achieveme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not just genuinely described the thoughts and mentality of the young intellectuals of the Puppet Manchukuo period,but took great risks conveyingthe consciousness ofresistance bycreatingand publishing.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Li Zhengzhong;Zhu Ti;Northeast Literature;Resistance Literature
I206.6
A
1674-5450(2017)03-0007-08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王凤娥】
2017-03-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ZW124)
蒋蕾,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伪满洲国文学与媒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