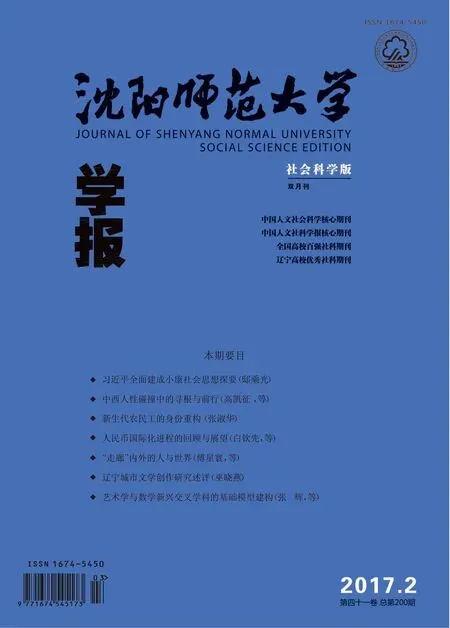中西人性碰撞中的寻根与前行
——李泽厚儒家美学思想评析
高凯征,张永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哲学动态
中西人性碰撞中的寻根与前行
——李泽厚儒家美学思想评析
高凯征,张永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型中,李泽厚以儒家传统为根,将生存、道德、自由三大人性问题进行连通整合,并通过其自创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儒家传统同化康德与马克思等人的理论,试图建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西方启蒙精神为辅的新时期美学。其儒家美学的重要功绩包括:强化了儒家的生存论传统,试图回归到中国文化的生存根基;强调了康德理性至上的道德观念对儒家实践性道德的补充,旨在建立情理交融的道德体系;坚持了中国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主体性地位,提出了美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发展构想。但在中西人性的根本差异面前,其儒家美学建构也面临着在发展前行中的迷茫与困境,如以西方二元论思维割裂中国传统的整体生成性,陷入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误区;将西方理性至上的道德观与中国情理交融的道德观混为一谈,造成自身美学体系的混乱;陷入概念与语言中心论的牢笼而难以自圆其说;对如何坚持中国美学的主体性仍旧语焉不详等。
李泽厚;儒家美学;强制阐释;西论中化;主体性
李泽厚美学思想如同一部百科全书,从中国先秦儒家、道家、法家,直至现代新儒家;从西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直至后现代,李泽厚的美学都有论及。虽然李泽厚并非纯粹的孔子、康德、马克思的专业研究者,但其紧紧抓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问题这一中西美学关注的共同焦点与终极问题。因此,李泽厚关于人性的诸多论述可以视为连接中西美学的中介范畴,成为中西美学融合的关键因素。而在中国新时期美学的现代性转型中,在中国美学西论中化与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李泽厚作为典型代表,其对儒家美学的研究理应成为当代学者的重要学术参照,其儒家美学思想的立场、思路与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文化是中国学术繁衍进化的根基,也是学者无法回避的文化根基,中国学术与学者都身处儒家文化环境之中,因此完全脱离儒家来谈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李泽厚将自己定义为第四期儒学学者,但实际上,在儒家文化的传统语境中,中国美学不可能脱离儒家来谈发展前景。中国学者们出生成长于儒家的文化背景当中,儒学在中国学者们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李泽厚等老一辈学者而言,这种思想的模铸作用尤甚。虽然李泽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儒家学者,但从其对儒家的重视程度与其思想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程度来看,其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因此,无论怎样界定与定义,李泽厚美学思想以儒家文化为根基,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很多研究将李泽厚美学定义为实践美学,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李泽厚美学与儒家注重生存实践传统的不谋而合。正是因立足于儒家文化根基建立起自身的美学思想体系,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寻根的色彩,而在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型中,李泽厚的儒家美学思想对于中国美学的前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这里不妨以李泽厚儒家美学为出发点,探讨中西理论共同关注的人性问题以及中西理论融合的前景与融合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有抓住“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问题,中西理论才真正有可能走到一起,在这一方面,李泽厚有着重要的贡献。
一、重回生存论传统,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李泽厚紧紧抓住了儒家立足于人的现实生存的要旨,认为儒家和儒学并非狭义的概念,而是“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称其为汉族、华人也好——的行为、生活、思想、感情的某种定势、模式。”[1]李泽厚以此反驳牟宗三等人的“儒学三期说”,认为儒学的精髓并不在于“心”和“性”等形而上的抽象理论,而在于儒学始终与人的现实生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李泽厚看来,现代新儒家这种心性论的道德形而上学甚至不能作为正式的分期儒学,只能成为宋明理学在现代的回光返照。因此,儒学要真正发展,还需另外开头,另起炉灶,寻找新的发展途径。这种新的途径在李泽厚看来就是以“生”为根基的儒家传统。
儒家人性观念的形成以人的现实生存为基础,儒家的道德与审美观念都整体生成于人的现实生存当中。高楠指出:“无论延续的道德的历史稳定性,还是因时代而变化的道德规范的差异性,都建立在生存整体性的基础上,这生存整体性即灵肉一体性,亦即感性与理性的一体性。”[2]儒家非常重视现实生存的意义,而且这种生存是现实的、真实的、此岸的生存,人的一切道德与审美活动的最终指向依然是现实生存。而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的道德形而上学恰恰忽略了这一关键因素,李泽厚也因此质疑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一味地阐释康德却忽视了自身的儒家传统。但李泽厚非常认同梁漱溟“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1]66的态度,认为自己立足现实生存的观点与梁最为相似。儒家传统融入日常生活的独特属性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古人每天生活在儒家传统当中,对于所受的影响却丝毫察觉不到,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与审美观念如同“润物细无声”的绵绵细雨,又如海德格尔所言“上手性”,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交织而又了无痕迹。因此,儒家虽不设立宗教,人们却严格按照儒家传统行事,儒家虽不刻意强调道德与审美对人性的约束和导向作用,人们却在现实生存中自觉地形成了稳固的道德意识与审美追求。
在近年来的谈话录中,李泽厚愈发强调中国传统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美学想要寻求发展,还是要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发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上来。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诸多理论,李泽厚认为只有儒家能够包容和同化一切外来理论,正如儒家思想历经千年演化,逐渐渗透进入道家和佛家思想当中,从而使道家和佛家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一样,西方理论只有经受过儒家的洗礼,才能够真正被国人接受,真正在中国发挥作用。这正是因为儒家文化具有对外来思想的强大同化能力,也更符合中国立足于现实生存的文化传统。例如在对待海德格尔哲学的态度上,大多数学者往往将目光集中于其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似性比较,但李泽厚却认为只有儒家才真正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宗旨相吻合,才能够更好地诠释出海德格尔思想的真谛。
因此,以儒家传统为立足点与出发点,是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也是适合中国美学发展的道路。李泽厚正是在立足儒家传统的前提下,才会对康德、马克思的思想理论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并强调中西融合中儒家传统的主体性地位。面对儒家在发展中容易固步自封的弊端,李泽厚反对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一味强调传统而忽略时代性的极端做法,而提倡用西方的启蒙与理性精神来弥补儒家在形而上方面的缺失,提倡儒学要在新时期的转型与发展中重视启蒙,重视理性,从而推动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对此,李泽厚认为,“与‘三期说’提出者仅仅抓住康德哲学不同,要在今天承接发展儒学传统,至少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等方面广泛吸收营养和资源,理解而同化之”[1]25。因此,李泽厚不断在孔子与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对照当中寻求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不断用儒学来消化西学,并注重儒家传统与西方思想的对接,对儒家传统与当代理论进行积极互释,确保了儒家思想的理论生命力在当代的延续发展,树立起新时期的儒学观。
二、注重启蒙理性,完善儒家情理交融的道德体系
中国古人在现实生存中形成了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的生存文化,而道德亦生成于其中。高楠指出:“注重人伦之德,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有其久远的生存根据。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维持氏族时代种群生存的支柱,已构成人们的基本生存形态,即是说,人们必须合于宗法血缘关系的规定才能生存。”[2]158儒家的人性观念以道德为指向,道德在儒家文化中体现为人伦关系对个人的约束,在古代,个人为使宗族和群体获得更健康长久生存,以牺牲个人自由而服从血缘宗法和人伦序位作为道德的体现。孔子正是将这种在现实生存中形成的经验性道德理性化,从而建立起儒家情理交融的道德观念与准则,而这种道德观念与准则因为与生存、与审美密不可分,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所以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因此,古人虽不设立宗教,不拜孔子,但却在生活中时刻服从儒家的道德准则。
康德的道德学说对李泽厚亦有着重要的影响,李泽厚认为康德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根本,而康德理性至上的道德观念则展现出人性中神圣性的一面。为实现儒家对康德学说的同化,李泽厚大胆地对康德的道德学说进行了修正,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将康德的先验理性道德转化为经验和实践的产物,并以此来解释康德的先验“道德律令”的形成过程,认为理性、道德、自由都并非先验范畴,而是形成于人的历史生存实践当中,从而将康德的先验人性纳入历史范畴,与人的生存实践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李泽厚进一步认为,“如果将中国儒学的‘仁’灌注于伦理的理性本体,就可为操作性奠定基础。”[3]可见,李泽厚试图让康德的先验理性与儒家传统经验形成呼应,从而与儒家的生存论思想汇合。
近年来,李泽厚又进一步提出“孔夫子加Kant”的构想,试图让孔子的实践经验性道德与康德的先验理性道德形成互补,从而弥补儒家道德思想在形而上方面的缺陷,用康德的启蒙理性精神助推中国情理交融的道德体系的完善建立。李泽厚认为,中国传统的道德观“以情为主,由情入理”,但在现实中却往往因为注重人情关系而忽视了理的重要性。但在中国的现实生存实践当中,道德又不能完全脱离情而存在,李泽厚也以电影《秋菊打官司》为例,表明了情在中国现实生存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对建立情理交融的道德体系的迫切需求。
三、把握自由的尺度,视美学为第一哲学
李泽厚注意到当下人的主体性不断高扬的时代现实,因此将人性的自由解放视为其美学的宗旨之一。但李泽厚同时继承了儒家的中庸传统,强调自由的尺度,将“度”作为其美学的第一范畴,认为审美能够为自由提供尺度,进而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度”——中庸将成为美的形式,美学将成为第一哲学的宏观预言。
儒家传统的自由观念建立在维护群体生存延续和服从道德约束的基础之上,个人的独立自由则融入到社会群体的人伦关系当中,因此儒家从不谈个人自由,而追求群体生存延续的大自由境界,并将这种境界视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在人伦传统的模铸作用下,儒家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存尺度,并将这一生存尺度延续到审美观念当中。因此,儒家的审美观念在人的生存实践中与道德观念整体生成,以群体的生存延续为最终指向。在儒家审美观念中,人的自由的实现以维护群体的现实生存为前提和目的,以中庸为尺度。因此,儒家的自由观从未脱离生存和道德而单独存在,而是整体融合在现实生存当中,与道德相辅相成,并维持生存的井然有序。
在古人的现实生存中,生存意识、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浑融一体,审美与生存、道德亦处于密不可分的完整状态当中。因此,中国古代的审美需要依靠体验来实现,只有在体验的心理状态中,人才能感知审美与生存、道德共在的完整状态。高楠认为,“体验是人与外部世界相关联的主体生存形态,人通过体验而建构、把握、构入外部世界,并使外部世界内在化,从而使生存成为此在生存或世界生存。”[2]59因此,通过体验,人完整的生存状态得以呈现,审美也始终与生存和道德同行。而西方单纯依靠逻辑和语言无法让人的生存状态得到完整的呈现,并因此衍生出一系列割裂审美与生存和道德本然联系的做法,造成西方美学发展的无限困惑。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艺术是对人的本真生存境遇的呈现,美和真理在这一过程中现身。而本真的生存即是完整有度的生存,亦是道德化、审美化、艺术化的生存,道德的约束和对自由的追求都是本真生存完整状态中的重要构成,维护着人类种族长久延续的生存。因此,人们在呈现本真生存的艺术作品当中体验到的自由是有度的自由,生存、道德、自由在艺术作品中完美地融为一体,通过审美体验引起人们内心的共鸣。而李泽厚也据此提出“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的理想,将“度”视为其哲学的第一范畴,并多次表示,在哲学未来的发展与转向当中,中国哲学即将登场,儒家守持中庸的美学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登场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人性的探究中,李泽厚抓住了中国传统立足现实生存、情理交融、自由有度的人性特征,将生存、道德、自由(真、善、美的外化)统一于人性,这既符合儒家传统,又与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的、理性的、绝对自由的人性观念形成对照互补。可以说,孔子和康德立于生存与道德或真与善的两端,而李泽厚在自觉倾向于儒家传统的同时,试图用美学将二者相连,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二者建立沟通的桥梁,并因此将美学视为第一哲学,预言中国哲学即将登场。不可否认,李泽厚的这些构想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但是李泽厚的儒家美学思想形成于混乱的年代,在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受了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受时代影响,其理论也难免出现了一些谬误与自相矛盾之处。而在当今西论中化与探寻中国美学发展前景的过程中,面对中西人性的根本性差异,李泽厚儒家美学思想也体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一)中西理论融合过程中的强制阐释
李泽厚美学思想虽然以儒家传统为根基,但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受西学的影响颇深,其虽然避免了牟宗三等人脱离儒家传统现实生存根基的错误,但却陷入了西方二元论思维和语言中心论的泥潭当中。
中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正如钱穆所说:分则俱存,合则两伤。中国的农耕文化与家族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伦关系传统,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已经成为个人必须服从的社会关系,但西方则更重视个体的独立,强调个人的自由,因此在人性的追求上中西也大不相同。虽然中西都以解决人性问题为终极目标,但儒家传统中并不存在个人自由的概念,个人的独立自由淹没在社会人伦关系当中,而西方的个人则是追求绝对自由的个人,一切人性都以个人自由为前提,而并不强调人伦关系。总之,中国传统的人性是一元的,西方则是二元对立的,如果运用西方的二元对立传统对中国传统进行强制阐释,则破坏了中国注重现实生存的传统,造成了对其完整性的破坏而无法解释其中的精髓。在早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意境、审美等问题的阐释中,李泽厚将意与境、美与美感分割开来,而忽视了意境、审美本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李泽厚强行将其一分为二,无疑是在西方二元论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产物。
如上文所述,儒家传统的审美是体验性的,通过单纯的理性逻辑和语言是无法认知和描绘的,而李泽厚过于强调“情本体”“实用理性”等概念,将儒家体验性的审美意识强行的纳入概念的范畴当中,而忽略了儒家起源于现实生存的根本,也与其遵从的儒家思想自相矛盾。在这其中,李泽厚又将儒家文化归结于侧重情感“情本体”,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生成性,中国文化中的情与理整体生成于生存活动当中,情理是交融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情中有理,理中有情,并不存在先后与轻重之分,相比之下,“情本体”反而成为先验的产物,从根本上违背了儒家扎根于现实生存的文化根基。而“实用理性”同样如此,李泽厚认为孔子的重要功绩在于将情感的经验理性化,从而在历史中形成了理性的积淀,但儒家的传统生存文化向来都注重情理交融,从未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李泽厚再一次陷入了二元论的误区。
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形成和发展于西学盛行的时代背景当中,受西方理论思潮影响较大,在自身美学体系的建构中也自创了许多概念术语,这与其青年时期所受的西学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后来李泽厚虽将研究焦点转向中国哲学,提出反对西方以语言为核心的哲学传统,而主张回归中国的生存传统,但在解释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仍经常出现以西律中的顽疾。
(二)西论中化过程中的体系混乱
李泽厚的美学体系兼容并包,这得益于儒家传统对外来思想理论极强的吸收同化能力,但面对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其思想体系内部也存在着许多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处。其中包括将康德、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强行纳入“历史积淀说”当中,将儒家源于生存的道德意识与康德先验的道德律令混为一谈,将马克思的经济学物质基础理论强行带入孔子与康德的道德观念形成过程当中。
李泽厚主张以儒家传统为主体,以康德的启蒙理性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为辅助,并对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理论进行同化吸收,因此,孔子、康德、马克思三者在其美学中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其“历史积淀说”表明文化意识的形成有其历史积淀过程,但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论观点的影响下,李泽厚将康德、马克思等人的理论强行纳入“历史积淀说”的范畴,从而违背了西方理性至上的传统。尤其是康德的先验理性道德被李泽厚完全视为历史积淀的产物,直接导致了康德道德律令神圣性的消失。李泽厚既要发扬康德道德观的先验神圣性,强化儒家以“情”为主的道德观,但又要把康德的先验变为经验。康德的先验理性在李泽厚美学思想中变成了历史实践的产物,这就消解了康德的理性道德作为绝对律令的神圣属性,导致二者无法形成完美的互补融合。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理论也被李泽厚不断运用到对儒家传统与康德道德伦理学的阐释当中,成为儒家生存论道德与康德先验理性道德形成的基础,从而否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康德的理性道德稳定性的一面,导致二者道德观的神圣性大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李泽厚所言儒学传统中的孔子与代表西方启蒙理性的康德更是经黑格尔与马克思理论洗礼过的孔子与康德。因此,“孔夫子加Kant”,虽然旨在强调中西文化的互补融合,但实质上已经不再是二者单纯的相加。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违背了孔子和康德学说的原意,因此,李泽厚在西论中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提出自己的哲学。
由于孔子与康德身处于不同的文化根基,因此对理性、道德、审美、自由等人性观念的看法都不尽相同,而李泽厚试图融合的设想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源,也与他的人生和学术生涯有关。透过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可见,孔子、康德、马克思之外,海德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休谟、杜威等人对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近年来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在其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以后,李泽厚又一度偏爱心理学,甚至强调要用脑科学的发展来解释文化在人的意识中的积淀原理。而这些西方理论不断被李泽厚加以同化与套用,造成了其思想体系的内部混乱。
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环境动荡不安,李泽厚历经“文革”等历史政治变迁,深受与传统文化断裂之苦,而在西学涌入后,中国学者们在丧失传统根基的情况下往往饥不择食,对西方思潮理论往往应接不暇,因此,在西论中化过程中体系建构的混乱乃是时代的弊病。而李泽厚在美学思想的研究中坚持儒家传统的主体性地位,这是李泽厚美学的可取之处,但其“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也造成了其思想的混乱和体系的庞杂无序。
(三)中国美学前行中的困惑与迷茫
李泽厚虽极力宣扬中国哲学即将登场,并预言美学将成为第一哲学,但从其美学思想体系中尚不能找到中国美学的前进之路。正如彭富春所说:“李泽厚在此世纪之交的时刻不是怀着一股乡愁来思古恋旧,而是试图构造‘新梦’。”[4]一方面,李泽厚高呼重回中国儒家传统;另一方面,又强烈呼吁西方的理性启蒙精神的介入,中国美学的发展前景依然需要继续探索。而对于如何进行西论中化及坚持中国美学的主体性,李泽厚语焉不详。中国哲学即将登场,如何登场,是李泽厚2010年和2011年两次谈话录的主题,但这两个疑问依旧没有确切的答案。按照儒家传统文化的延续规律,西论中化与中国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自觉的过程,但中国美学未来的走向仍需进行准确地把握与探索,避免少走弯路而迅速前进。
李泽厚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将“美学作为第一哲学与物自体问题”分为上下两章对“度”与“情本体”问题进行分别阐释,旨在通过美学形成康德与儒家传统的联系。在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与对不在场的态度上,儒家对天地的敬畏与康德对物自体的敬畏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于人认知的有限性,孔子对未知领域心存敬畏,往往避而不谈,而一贯崇尚的“天人合一”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人在这种生存中保持了对世界完整性的体验。这种态度在康德哲学中亦有体现,康德的“物自体”同样建立在人认知有限性的基础上,人只依靠知解力无法认知到事物的完整属性,康德虽然相信上帝或物自体的存在,但康德终生不去教堂,因为康德对宗教的性质存疑,认为只有通过审美的判断力才能弥补认识的不足。因此,李泽厚试图通过审美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审美成为儒家传统与康德哲学在人性上的共同突破口。但由于儒家传统与康德在审美问题的根基上存在着质的不同,儒家传统审美来源于人的生存实践,康德美学则以人的先验判断力为基础。因此,二者能否互补融合还有待理论的发展与实践的检验。李泽厚反对国粹主义,但也忽视了中国儒家传统极强的延续性。李泽厚提出儒家传统与康德对接设想的意图虽好,但他对儒家传统与康德进行的生硬对接、转化对接都并不适于中国的现实语境。
正如钱穆所说:西方思想如花,种类繁多,繁花似锦,然则并不实用,中国思想如果,虽不见花团锦簇,然而却硕果累累,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对注重此问题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还要以中国学术为主体,在此基础之上同化西方思想,西论中化、西体中用,开拓属于自己的前进道路。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正处于现代性转型时期,但西方理性至上的传统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西方理论虽然逻辑严谨,但在在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实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正如梁漱溟所说:“西洋人风驰电掣地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1]68如果将这种文化强行带入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经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才能真正被广泛接受。
中西互释本就是复杂的过程,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应以西方的理性和概念来加以阐释,而是应立足于中国文化在现实生存中的整体生成性,才能做出更准确地阐释。中国美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坚持儒家情理交融的文化传统,注重人伦体验思维,同时广泛地吸取国外的新兴理论,确保思想的常新与活力。李泽厚提倡不依傍宗教来建立以人为本的美学,为人性建立道德的规范与自由的尺度,确保人类整体更长久健康的生存,这本与儒家的传统相一致,但其提出的“情本体”“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学说却因偏离了儒家整体性生成的文化根基而无法解决中国在当今面临的现实问题。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当中,西方理论如不经中国化阐释必将带来问题。因此,只有在西论中化与中国美学发展前行的过程中坚持中国传统的主体性地位,才能最终开拓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前进道路。
[1]李泽厚.说儒学四期[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31.
[2]高楠.文学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33-234.
[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58.
[4]彭富春.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J].文艺争鸣,2011(3):82-89.
Seeking Roots and M oving Ahead in the Colli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uman Nature——A Case Study of Gain and Loss of Li Zehou’s Confucian Aesthetics Gao Kaizheng,Zhang Yongjie
(Collegeof LiberalArt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6)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s,Li Zehou took Confucian tradition as the root,combining the threehuman issuesofsurvival,morality and freedom.Heattempted to construct thenew aestheticsbased the Chinese Confucian traditionsand thewestern enlightenmentspiritby assimilating Kant’sand Marx’s theorieswith Confucian traditions through his ow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tology.His main achievements are as follows: strengthening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the existentialism;trying to return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survival foundation; emphasizing the supremacy of Kant’smoralconceptofConfucianmoralpractice;aiming toestablish a reasonableblend ofmoral system;adhering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of Confucian aesthetics as the first philosophy.However,i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umanity there are also confusion and difficulties.For instance,the overall generation of western dualism Chinese fragmented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the West into forced misunderstanding;western rationalism moral values and confused Chinese reasonable blending morality;involving aesthetics into the chaotic system;the future prospects of the China aesthetics are still confused;the concept and language center of confinement are difficult to justify;unclear description of how to adhere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i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aesthetics transformation.
Li Zehou;Confucian aesthetics;compulsory interpretation;chinalization ofwestem theories;subjectivity
B83-0
A
1674-5450(2017)02-0009-06
【责任编辑:李 菁 责任校对:赵 践】
2017-01-12
高凯征,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