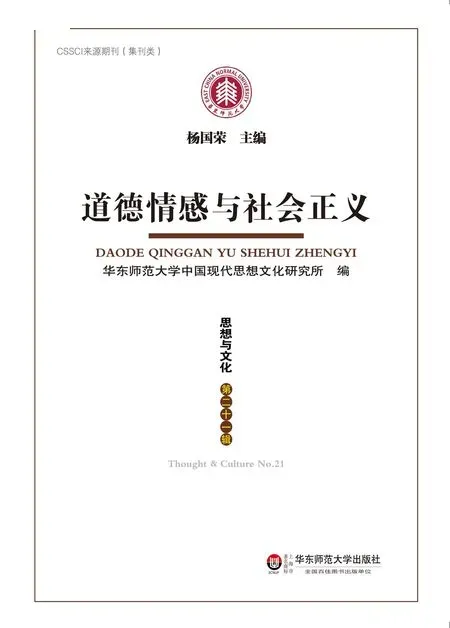全孝、经权与忠勇
——中江藤树对传统武士道的反思*
日本学者中江藤树(1608—1648),少时聪慧,11岁读《大学》,15岁袭祖父武士职,16岁从禅僧学《论语》,后自修《四书大全》,18岁起信奉朱子学。27岁时为奉养寡母而弃官返乡,之后讲学于村故宅藤树下,门人称为藤树先生。藤树极重孝道,32岁始带领门人每日清晨拜诵《孝经》。次年读《王龙溪语录》,阳明学开始对藤树发生影响。33至34岁作《翁问答》,35岁作《孝经启蒙》,37岁读《王阳明全集》,终于信从阳明心学,晚年著《古本大学全解》。藤树一生笃志向学,修身进德,诲人不倦,建构了以“全孝”、“明德”为纲的神学本体论与心学工夫论,创立了日本阳明学派,因而被尊称为“近江圣人”。
《翁问答》与《孝经启蒙》堪称是藤树的代表作。《翁问答》采用天君老翁与弟子体充的问答体,“天君”出自《荀子·天论》,象征人之心;“体充”出自《孟子·公孙丑上》,象征人之气。《翁问答》的内容很丰富,除神学本体论与儒佛道宗教思想之外,其关于五伦与仁、义、孝、忠、勇、经、权等人伦思想也很突出,并对当时日本的武士风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孝经启蒙》借用明末虞淳熙的《全孝图》、《全孝心法》作为诠释《孝经》的开卷语,解释上以《四书》与《礼记》为依据,另广征《诗》、《书》、《易》及《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等典籍,重点阐发了全孝思想。本文以此二部著作为据,以全孝、经权与忠勇诸问题为中心,探讨藤树对日本传统武士道的反思。
一、全孝之道与人伦之经
在日本阳明学的兴起过程中,诸学者除了像宋明理学一样重视《大学》解释之外,对《孝经》解释也格外看重,他们对《孝经》的推尊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张昆将:《晚明〈孝经〉风潮与中江藤树思想的关系》,辑于张昆将:《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学与阳明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第207页。藤树阐发的孝道思想可用“全孝”概括,旨在建构一种以人我与“太虚”之亲缘关系信仰为基础的神学本体论,而其伦理学内涵是将父母、祖先、主君、天地与太虚都视为孝的对象。
一方面,太虚是形而上的本体。藤树云:“太虚寥廓,吾人之本体也,故天地万物无非己”,吾人“为天地神明立心。”*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太虚何以能视为吾人之本体?藤树在《孝经启蒙》中做了推理论证:“身之本父母也,父母之本,推之至始祖;始祖之本,天地也;天地之本,太虚也;举一祖而包父母先祖天地太虚。”*[日]山井涌、山下龙二、加地伸行、尾藤正英:《中江藤树》,东京:岩波书店,1974年,第260页。即从起源上讲,一切事物都是太虚化生或派生的,因而太虚是吾人之祖先,亦是吾人之本体。对照中国儒学,“太虚”应是作为“形而上的实体”之天的别名,不过藤树主要是在生成论而不是本体论的层面上展开论述的。*任文利:《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页。
另一方面,藤树相信太虚并不单是物质的而是其中有精神性的主宰,确切地说就是皇上帝或太乙神。*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第225页。“天神地祇,万物之父母,太虚之皇上帝,即人伦之太祖,于此神理观之,圣贤人如释迦、达摩、儒者、佛者、我、人,在世界中俱有人之形,皆皇上帝、天神地祇的子孙也。”(《翁问答》*[日]中江藤树:《中江藤树文集》,塚本哲三编,东京:有朋堂书店,1930年,第1—190页。第81条)藤树神学的来源与构成很复杂,有来自道教的太乙神信仰,有来自《尚书》的皇上帝信仰,还有来自日本本土的神道信仰,或许还受到耶稣会上帝观的影响。*张昆将:《晚明〈孝经〉风潮与中江藤树思想的关系》,第206页。
藤树的太虚思想虽源自宋儒张载的“太虚”说,但有自己的发展,即将从太虚至万物此种一气连续的“生理”伦理化为“孝”来把握。*[日]荻生茂博:《“太虚”与日本的阳明学》,辑于《“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0年,第548—559页。藤树认为孝亦是本体,其“全体充塞于太虚”,而“其实体备于人”,通过人之感通而行于天下。具体地说,孝是从士庶人之爱母、敬父、养父母开始的,终于天子(如周公)之“严父配天”、祭祖郊祀的德行而达至“莫大之孝”。当孝德落实到人之本心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爱”与“敬”。爱敬可以感通于一切人伦关系,士人“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卿大夫谨遵先王之道“然后能守其宗庙”,诸侯敬慎故而“居上不骄”,天子爱敬其亲故而博爱于百姓,莫非孝也。*[日]山井涌、山下龙二、加地伸行、尾藤正英:《中江藤树》,第260—262页。
可见,藤树的“全孝”本体论与其孝道伦理能够弥合无间。在藤树的伦理学体系中,外言之孝道是五伦之经,内言之孝德是“五性之本实”。*同上书,第259页。“五性”即“五常”,仁义礼智信也;“五伦”为亲子、君臣、夫妻、兄弟与朋友;“五教”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与朋友有信。藤树用大篇幅重点讨论了亲子与君臣伦理(其余略说),尤其是他对“父母千辛万苦之厚恩”的细描,读之令人动容。(《翁问答》第13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藤树用孟子、象山与阳明一系的心学来诠释中国儒家推崇备至的“仁义”道德:自外言之,亲子与君臣伦理分别代表仁与义,自内言之,“爱敬”之情实为仁义之心,爱敬始于孝顺父母的赤子之心,又可以感通推扩至兄长、君上乃至一切人伦。来自孔孟的“仁政”理想,也被藤树视为天子与诸侯之“孝”行:天子孝行的结果是万民爱敬,四海德化,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天下一统,万国心服;诸侯孝行的结果是大夫守职,家臣忠义,国中安定,百姓淳朴,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翁问答》第6、7条)虽然日本德川学者对“仁义”的理解偏向于具体化、政治化,藤树却不仅从“忠孝”的角度,也从心学的立场来解释仁义:爱亲,仁也,忠君,义也,此孝忠之心乃是真实明德,从而为其提出“仁义之勇”的武士理想奠定了基础。(《翁问答》第75条)
二、藤树所处时代的武士道
在9世纪中期,即日本平安时代,武士与武士团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成长为日本社会的重要阶层与政治力量。*吴廷璆:《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武士与武士道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武士道的精神渊源包括神道、佛教、儒学与心学等。武士道,“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只是一些口传的格言,“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5—22页。在日本史上对武士道的称谓有“弓箭之道”、“武道”、“士道”与“武士道”等十多种,明治维新后才统一称为“武士道”。*本文标题所称的“传统武士道”是指藤树所处时代俗世主流的武士道,其受儒学的影响还比较弱。
藤树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川幕府统治(即所谓的江户时代)的前期,统治阶级是由从将军、“骑本”、“御家人”、大名一直到“足轻”的大小武士构成的。随着和平时期到来,中下层武士变成领取俸米(或折成货币)、游手好闲(不需作战)的特权阶层。*吴廷璆:《日本史》,第215—221页。
藤树批评道,武士被置于“四民”之首,其道德品行理应成为农、工、商贾三民所崇敬和学习的对象,然而藤树所见之武士大多是酒囊饭袋,身着轻暖衣服,满足于甘酒美食而已。(《翁问答》第74条)他借用中国儒学对社会等级的划分,认为人可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等,其中士(相当于日本的武士)是为了协助卿大夫或诸侯(相当于日本的大名),为了实现道而从事各种活动与担任各种职务,且必须忠于君、孝于父、明明德、行仁义。*蒋四芳:《中江藤树的士道观——〈翁问答〉》,《安徽文学》2010年第3期,第237—238页。后者才是藤树心中理想的武士。
藤树指出,日本国之传统武士道,对武士均有三方面的要求:才德、忠节与军功;但现实并非如此。德川幕府时代,武士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武士被要求“明明德”,无名利私欲,具有行仁义之勇气,这是只有文武兼备者才可以担任的;中等武士虽做不到“明明德”,但他不受功名利禄迷惑,不顾生命危险,能够坚守名誉和义理;下等武士虽然表面上注重义理,但内心却受利欲迷惑,一心只想出人头地。由此可见,德、才、功应是武士等级之分的标准。藤树主张,作为主君,应当以此三点来区分武士的品质,给与相当的待遇。(《翁问答》第71、35、37条)
三、经权与武士之忠德
在儒家义理系统中,“经”指人类那些根本的或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在藤树那里,“经”以孝为首,或者孝能够统领群伦;而忠与孝同样重要,孝亲与忠君可以被统合起来。他诠释《孝经·事君章》说,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因为君父恩同——“父生之,君食之”。(《翁问答》第5条)对于武士而言,因为君、亲给予的恩德一样宏大,孝德与忠节可以感通,故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翁问答》第61条)
在儒家义理系统中,“权”指人类运用道德原则的具体方法与实践智慧。藤树对权法极其推崇,他认为,君子在工夫成就上是有次第的,权法之善可谓“圣人之大用”、至极无上之神道。(《翁问答》第91、92条)圣人在行迹上不凝滞,独来独往,善于变通,活泼泼的*“活泼泼”一词在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中经常出现,用以指良知之生动灵活的特征。,不拘泥于礼法,而“非礼之礼”才是真实之礼。(《翁问答》第89条)
师曰:“权者,圣人之妙用、神道之惣名。大者如尧舜之禅让、汤武之放伐,小者如周公之吐握、孔子之恂恂便便,一言一动之细微皆权之道。权者,反经之道。”(《翁问答》第89条)以上是从权变、权宜的角度理解“权”。藤树还主张,真儒心法不拘于行迹,行动应考虑时、处、位——天时(时代)、地利(场所)、人位(身份地位),做到相应适当,轻重恰好,圣人制作礼义也应按照时代而有所损益。(《翁问答》第40、95条)以上是从权宜、权衡的角度理解“权”。*权宜、权衡与权变的定义及运用,参见王剑:《论先秦儒家的“权”法思想——兼与亚里士多德比较》,《孔学堂》2015年第2期。
在权的层面,藤树阐述了他对忠德的独特看法。首先,他区分了“大忠”与“小忠”。“所谓忠即无二心地为君而思尽职奉公之德。由此,奉公之事即或有大小差别,尽忠之心却无二致。……大臣的忠节因其事大而云大忠,小臣的忠节因其小谓之小忠。主君厌恶之事,对君对国对家来说只要是好事,也要促其完成;主君喜好之事,于心于身于道于国只要是坏事,也要竭力相劝。……不论是非善恶,一切顺随主君,一心听命主君,不顾身体尽职尽责勤于事务,此谓小忠。”(《翁问答》第13条)可见,在藤树的忠德观中,义的地位高于忠,以义帅忠、忠义合一才成其为“大忠”;而“小忠”反是,忠凌驾于一切其他价值,以忠掩义,可谓“私忠”、愚忠。
其次,当时身为一名武士,信奉“忠臣不侍二君”,绝不可以变更主君,但是这绝对正确吗?藤树引用《孟子》中百里奚的例子来支持他的异议——虞君不义,百里奚离开虞国转而侍奉秦穆公,后担任宰相并取得伟大的政绩,孟子赞扬其为贤人——“一位武士是否侍奉二君,此须依主君的品行而定,若主君是昏君、贪图私利、不明事理,武士便可视情形变更主君。”(《翁问答》第73条)
藤树进而言之,变更主君是否违背士道的问题,需要依据“时处位”来判定,同时考察行权者的动机。不变更主君合乎士道,但是像百里奚这种注重修身、无私心之士,顺应时势而变更主君的做法也是正确的。为了治国与行道,作为武士必须舍弃私心,尽职尽责,不拘泥于形迹,按照“时处位”原则行权,只有这样,合理的主从关系才能维持下去。(《翁问答》第73条)
为了巩固幕府统治,当时的统治者试图不断强化不侍二君的主从道德,像藤树这种自由选择主从关系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无可奈何之下,藤树选择了脱藩归乡,做到终身没有侍奉二君——既然不能自由选择,他就退而求其次,放弃对任何主君的效忠,这是他对自己学问与良知的实践。
四、血气之勇与仁义之勇
武勇与忠义是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核心,传统武士道当然是将勇武与忠义置于最高地位。但一味的赞美勇敢与依仗武力是浅薄的道德,传统武士风气比较粗陋,与藤树的武士理想差距甚远,招致藤树的深刻批评。
藤树感慨世间俗人毫无探讨,总是将悍勇杀人看做武艺惊人并以此为傲,这其实是凄惨可悲之事。武艺应在关键时使用,战场上应毫无保留地为主君献身,作为战斗者应痛快地为主君去死,“死得干脆”之勇是最高的道德品质,这是仁者之勇;若平时借勇猛之拳胡乱杀人则是血气之勇,显得愚蠢,对他人毫无益处。一则,血气之勇会成为精进武艺的妨碍;二则,血气之勇者因激烈的战斗心易寻衅打架,往往给亲人和主君造成很大的麻烦。
藤树区分“血气之勇”与“仁义之勇”的观点源于孟子思想。他说:“丝毫不惧死,无贪生之念,故能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即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称为“仁义之勇”。能够达到文武合一境界的武士,其勇乃“仁义之勇”,“大勇”也;不知文武之道,不辨义与不义,只知凭血气、逞私欲,如虎狼一般凶猛,不过是“血气之勇”,“小勇”也。(《翁问答》第31条)藤树相信,“仁者必有勇”,“仁者(如桓文节制、汤武仁义)军法无敌”,仁者用兵之典范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如夹谷之师堂堂正正,依然五帝三王之风”。(《翁问答》第34条)仁义之师才能拥有真正的军法与勇武之德,刚强暴逆之师不过如盗贼之类不可赞美。(《翁问答》第62条)
针对传统武士道对武勇的狭隘理解,藤树指出:《孝经》所说的孝行,《大学》所说的忠节,《中庸》所说的勇强,才是真正关于武勇的教训。曾子曰:“战阵无勇,非孝也。”(《翁问答》第61条)况且,武士之勇,除了战阵之用,平日何尝无用?如《二十四孝》中的杨香扼虎救父,爱父的一念之仁可以激发巨大的勇气,这也是仁义之勇的例子。(《翁问答》第76条)可见,藤树已经将传统武士道的武勇观提升到仁义之勇的层级。
藤树阐扬“仁义之勇”,并不是照搬孔孟儒家思想,而是基于其对仁爱的深刻理解与认同。他认为,五常是天神地祇之大德,亦是人生而具有之天性、明德。“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戒杀生乃是仁德,人间慈爱是神理,一草一木都应爱护,杀人更是违逆天道生理之罪恶。(《翁问答》第86条)藤树将佛家的五戒*佛教的“五戒”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的五常贯通起来诠释,还有如藤树说“忘佛、儒之名,致本来至诚无息、不二一贯之心学,悟太虚寥廓之神道,无惑也”等,不难发现藤树融摄儒佛的企图,但无论如何,藤树对“仁”的理解与中国儒家强调的爱、不忍或恻隐之心并无二致。(《翁问答》第80条)
五、理想的武士道:文武合一
藤树认为,理想的武士道是文武之道的合一。“文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元来文武只是一德(同一明德),天地造化,一气分阴阳,人性感通,而使一德分出文武之差别;春夏为阳,秋冬为阴,文为仁道之异名,武为义道之异名;仁为文德之根本,文学、礼乐、书数为文德之枝叶,义为武德之根本,军法、射御、兵法为武德之枝叶。”“武道的目的是刑罚惩戒、征伐统一,最终目的是止戈为武。”(《翁问答》第27条)
江户时代之前,日本武士的经验主要是武道,对于当时重武轻文风气的盛行,藤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传统武士道将文学艺术与性格柔弱称为“文”,将兵法武艺与性格刚毅称为“武”的文武两道观是世俗的误见。文是能够治理好国家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而武是指当有邪恶不逞之徒欲妨碍文道时,或以刑罚惩之或兴军讨伐之的武力行为。所以,武道的目的是行文道,故武道之根乃文也;文道依靠武道之威而治,故文道之根乃武也。*蒋四芳:《中江藤树的士道观——〈翁问答〉》,《安徽文学》2010年第3期,第237—238页。
当时社会人心灰暗,认为勇者只要学武,武艺则会高强,学文艺无甚用处。藤树赞美说,中国士人中无学问的文盲百难觅一,立大功的大将军们个个都是武艺超强且具修养之士。(《翁问答》第51条)他批评说,日本的武士中文盲特别多,反而在一些和尚、神道信仰者、公卿和医生等人中却产生了亲近文艺、勤勉学问的风俗习惯。(《翁问答》第49条)作为一名武士,学问是必备的,若无志于学问单学武艺,不可能到达武艺的巅峰之境。说武艺与学问、文艺难以相容,正是因为文盲之士嫉妒他人有才艺而设法掩盖自己文盲之耻辱。
藤树还用文武合一诠释了圣人、贤人与英雄这三种伟大人格:“文武合一之明德十分、才德出众、神明不测之妙用者为圣人,如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也;比圣人次一等是贤人,如伊尹、傅说、太公、召公、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孔明、王阳明是也;德、才逊于贤人一等的,有大将之才的是英雄,如管仲、乐毅、孙子、范蠡、张良是也……义经公、正成公等就是日本国的英雄。”(《翁问答》第66条)
只学武道者不是真正的武士,只学文道者也不是真正的儒者,只有做到文武兼备、文武合一才是真正的武士、真正的儒者,这是藤树对近世武士阶级提出的新的文化与人格理想。作为武士必须勤勉学问,真正的学问即学儒学、明明德,人的内心若明明德、饱含仁义,文武便能统一,便可成就仁义之勇。(《翁问答》第49条)藤树“在理论上完成了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尚武传统的结合,为武士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促进了文治主义的兴起。*王志:《日本武士阶级的文武合一思想》,《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第62—69页。
六、结语
以上依据《孝经启蒙》与《翁问答》的论析表明,藤树严厉地批评了传统与时俗理解的粗陋武士道,而热情地赞美了融合日本传统尚武精神与儒家仁义忠孝道德的一种理想武士道,同时阐发了全孝心法、行权之忠与仁义之勇等深刻的本体论与伦理学思想。藤树提出的文武统一的新武士道观,对后来江户时期如山鹿素行武士道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德川时代政治经济结构的变迁,需要儒家伦理参与塑造新的意识形态,客观上也要求武士阶层身份与功能之转型*[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10页。,因此藤树提出的新武士道观,顺应了和平时代幕府平稳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藤树思想已然超越了狭隘的大和文化本位主义,能够广泛吸取、借鉴优秀的东亚儒家、道家、佛教与西来基督教思想,创建自己的神学本体论,并闪耀着仁(人)道主义的光辉,对一味强调武勇与忠君的日本传统武士道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与批判。日本学者吉田公平也认为,只有以舍弃日本之“古”,别树东亚之“新”来定位藤树思想。*张昆将:《近二十年来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辑于张昆将:《德川日本儒学思想的特质:神道、徂徕学与阳明学》,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第322页。
从藤树文武合一士道观包含的中庸智慧来看,藤树的武士道思想与日本近现代武士道或者“皇道的武士道”*娄贵书:《日本武士道源流考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81页。有显著的区别。如果藤树泉下有知,会对后来《叶隐》一系主张绝对服从君主与迷恋美化死亡的偏执狂妄武士道不能苟同,会对被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化的、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崇尚愚忠和献身的武士道加以反对。今天的日本要摆脱军国主义的梦魇,须对传统武士道的思想毒素及其被政治利用的历史展开进一步反思与批判,这或许可寄望于本国再出现一批像中江藤树这样真正理解和认同儒家价值观的思想家。
——读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