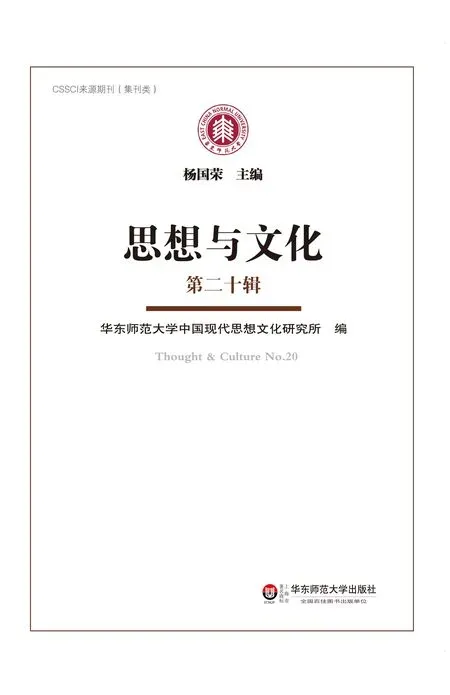陈荣捷《朱子门人》商兑
●
前言
朱熹(以下称“朱子”)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寿七十一。朱子一生仕宦不过七年余*黄榦: 《朱子行状》:“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此就整数而言。《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00页。,其余绝大多数时间,都以著书讲学为乐。四方从学者“抠衣而来,远自川蜀”*黄榦: 《朱子行状》,《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第703页。,门下弟子达“数千百人”*陆游: 《方伯谟墓志铭》:“闻侍讲朱公元晦倡道学于建安,往从之。朱公之徒数千百人……”马亚中、涂小马校注: 《渭南文集校注》第四册,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28—129页。田中谦二博士推测受教于朱子之门者或达三千人之众。参见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序说》,《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东京: 汲古书院,2001年,第8页。,蔚为壮观。明人已留心搜集朱门弟子生平事迹,汇录成编,入清续有述作(详后)。20世纪70、80年代,朱子门人的考证与研究获得突破,以田中谦二博士(1912—2002)《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与陈荣捷先生(1901—1994)《朱子门人》,为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京都大学田中谦二博士发表《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44号,1973年)、《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续》(《东方学报》48号,1975年),充分利用《朱子语类》和《朱子文集》的记载,详考弟子师事朱子之年次、时期,在朱子门人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陈荣捷先生誉之为“澈底之作”。*陈荣捷: 《朱子门人》,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3页。后经增补改订,收入《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汲古书院,2001年),内容较旧稿近增一倍。*金文京: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解题》:“旧作にほぼ倍する本篇の量だけからでも、博士がこの道草にそそがれた竝々ならぬ情熱が知れるであろう。”《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453页。田中博士是俗语文学研究专家,因而也关注《朱子语类》的俗语现象。自1969年6月起田中博士在《东洋史研究》(28卷1号)上开始连载《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系列文章,持续至1973年6月,后辑为一书,由汲古书院出版(1994年)。田中博士的论考前冠有《序说》一篇,交代考证的意图、方法以及资料的使用情况。田中博士考定门人师事朱子年次、时期,为判断《语类》问答、《文集》书信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依据,为考察朱子思想的变化,追踪其演变轨迹提供了坚实和可靠的基础,厥功至伟。
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出版于1982年,是在吸收田中博士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另外,1988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陈荣捷先生《朱子新探索》,收录《丁克抑丁尧》、《杨楫果非门人乎》、《朱子门人补述》等散论朱子门人之作,可参看。杨儒宾在《战后台湾的朱子学研究》一文中评论陈著“考证精详,足补以往典籍记载之疏漏”,堪称“此领域内的集大成之作”。*杨儒宾: 《战后台湾的朱子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19卷第4期,2000年11月,第577、573页。笔者拜读陈著,以为作者的核心关注是朱子门人与朱子学壮大的关联及朱门之特色,卷首所冠《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此文又收入陈荣捷:《朱学论集》,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271—297页。一文之标题,已经明示了此书的主旨。正如陈先生所言:“朱学之能支配中日韩思想数百年者,其中原因必多。而朱子门人,是其主因之一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页。朱子门人之于朱子学意义如此重大,则历代典籍所记载之朱子门人,是否确实为朱门弟子,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陈荣捷《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今一先决问题,则是谁为弟子。”《朱子门人》,第6页。因而此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考订传统文献记载中的朱子门人是否名副其实,辨析非门人而误作弟子,或者讲友而误为门人的情况。
作者逐一检讨明代以来有关记载朱子门人的文献,主要有: 戴铣《朱子实纪》,宋端仪撰、薛应旂重辑《考亭渊源录》,朱衡撰、张伯行改订《道南源委》,朱彝尊《经义考》,万斯同《儒林宗派》,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李氏朝鲜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等书,认为《宋元学案》“取舍颇严,态度足称客观。全祖望按语特重源流,精审公正”,“最称严谨”,而其他各书均不免有“炫耀朱门之盛”的“滥收之病”。*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3—4页。根据作者的考订,“诸书以为弟子而实只是讲友者六十九人,诸书作为弟子而实既非弟子亦非讲友者七十二人,诸书重误者十四人。换言之,诸书以为弟子而今证实其只是讲友或直与朱子学术无关者一百四十二人。”*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页。去“伪”存“真”,此为本书考订朱子门人贡献之一方面。另一方面,作者“从《语类》考究,确证其曾请教故是弟子而为诸书所未载而今乃增入者三十四人”*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页。,补充了传统记载的漏略。
作者又说“实非弟子而各书滥作弟子者达一百四十余人”*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4页。,就是将本书“证实”并非弟子,而在传统记载中列为门人的情形,不加区别一概都指为“滥收”。所谓“滥收”,包含主观故意的意味,是很严重的指控。读者必然关心: 作者如何界定门人,如何确定门人与非门人、门人与讲友之别;作者指摘传统记载“滥收”,证据是否充分,论述是否恰当。这实际上关乎如何认识和看待传统文献记载之问题,所系甚大,不可轻忽。
因此,本稿第一章考察《朱子门人》指摘为“滥收”的弟子,检讨传统记载是否如作者所论出于夸大朱门而滥收。第二章分析作者辨别门人、讲友的方法,检验作者的判定能否成立。第三章附考见于《朱子语类》的弟子“赵唐卿”,说明如何通过扩大材料的运用补充以往考订的不足。希望借由对陈先生的名著《朱子门人》的检讨,思考考订朱子门人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对进一步推进朱子门人的考证与研究有所裨益。
一、 门人、非门人之辨析与所谓“滥收”
作者不满明代以来的记载取舍失当、辨别不精,为夸耀朱门之盛,多有“滥收”,并指出“诸书所以滥收之故,则以其门人之定义不严”。*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页。何谓门人?作者认为:“其有正式表示,如奉贽求教,执弟子礼,或以面书求进,或明言奉侍,或自称弟子者,当然是正式门人。严格而论,凡亲面请教,只发一问者,亦为弟子。”*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页。作者根据此一自定的“门人”标准,在所叙述六百二十九人中,指控传统文献记载“滥收”误作弟子者一百四十余人。“滥收”人数之众,可谓惊人。兹举作者指为“滥收”的刘学古、陈利用以及疑非弟子的杨复为例,检讨本书的辨析是否合理,论证是否恰当。
(一) 刘学古
作者定刘学古非弟子亦非讲友,谓《语类》一条“亦是训壻之词,不得以此便是弟子”,又云:“《语类》以为训门人过矣,而《渊源录》、《实纪》八、《宗派》十,《补遗》六九据《宗派》,皆列为门人,则志在标榜朱门而已。”*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316页。
盖作者以《语类》一条朱子所言为讨论“做人”,遂谓训壻,非训门人,其实不然。如《语类》卷一二一(训门人九)第八九条,陈文蔚录:“先生过信州,一士子请见,问为学之道。曰: 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矣。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第2945页,下划线为引用者所加,下同)又如《语类》卷一三第一四二条,余大雅录:“或以不安科举之业请教。曰: 道二: 仁与不仁而已。二者不能两立。知其所不安,则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尔。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第243页)又如《语类》卷十第五条,魏椿录:“为学之道,圣贤教人,说得甚分晓。大抵学者读书,务要穷究。‘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第162页)就朱子之思想而论,教“做人”亦是讲学,正不必以今日之眼光,而目为训壻之词也。
且作者斥《语类》录刘学古入“训门人”为误,而指《渊源录》、《实纪》等著作“志在标榜朱门”而滥收。此说有违常理,论述难以服人。须知《语类》这一权威文献已经认定刘学古是门人,《渊源录》、《实纪》等著录朱子门人,没有理由置之不收,否则必致当世学者漏收之质疑。若明知刘学古非门人,而多多益善故意揽入,谓之“志在标榜朱门”可也。然刘学古非朱门弟子之认识,始于陈先生,非明清人所及知。既然如此,《渊源录》、《实纪》等录为门人,实在谈不上“滥收”。现在陈先生却说明清人主观上有标榜朱门的意图,所以才滥作门人,岂非强词夺理,厚诬古人。
应该承认,《渊源录》、《实纪》等的编者没有陈先生这样严谨考订的精神,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们不加考订接受已有的认识,但很难指摘他们主观上有意滥收。毕竟《渊源录》、《实纪》这类著作,更多的是剪裁、整理旧有的文献记载,他们追求的也确实是广搜博讨,尽量齐备,唯恐有所遗漏,而非考订传统文献记载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换言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在保存和延续“文献记载之真实”,而进退朱门弟子,辨别真伪,是考订“历史事实”的工作,他们并未积极在此方向上用力。只有到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尤其是颇具史学精神的全祖望,才会更多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传统记载,提出与以往认识不同的见解。陈先生称“全祖望按语特重源流”,颂扬《学案》“最称严谨”,原因也不外乎此。我们也清楚看到,陈先生继承了全祖望的批判精神,对传统文献记载,以更严厉的态度加以审视。但这种抱有先入为主偏见的审视,有时候也未必能实现其“求真”的素志,令人惋惜。
(二) 陈利用
笔者认为,考订朱子门人,首先要检讨已有记载的来源,像《渊源录》、《实纪》等著作录朱子门人,可能参考了哪些资料,其依据是什么,都需要尽可能理顺清楚。在对传统记载的来龙去脉有确切认识之后,才能进一步论证“历史事实”的问题。笔者未曾学史学,自愧没有能力讨论“历史事实”的问题。追踪文献记载上的传统认识的形成过程,比考定事实上是否为门人,对笔者而言是更加紧迫、重要和有趣的事情。
如《朱文公大同集》的编者陈利用,字光卿,《朱子门人》考定既非弟子亦非讲友*陈利用名字以括号括住,按该书体例,示其既非弟子亦非讲友。,其说谓:
《实纪》八谓其为同安县(福建)学司书兼奉祠,尝编《大同集》。《语类》无其名、《文集》亦只于《别集》七“与一维那”诗下注云:“以下朱子八诗,见陈利用编《大同集》。”《实纪》乃以为朱子门人,可谓滥而又滥。*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12页。
按照以上叙述,将陈利用列入朱门始于《实纪》,而《实纪》只因《朱子文集·别集》曾取材于陈利用所编《大同集》,遽揽为朱子门人。若如所言,则“滥而又滥”的评价并不为过。
但《实纪》录陈利用为门人,或非如其所论。《大同集》是陈利用编选的朱子同安主簿任内及与同安有关的诗文之作。*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存目,评价不高。最近尹波、郭齐、白井顺合撰《关于朱文公大同集的若干问题》(日文题名《朱熹『大同集』に関する若干の問题》)一文,考辨版本源流,详尽探讨《大同集》与现行本《朱子文集》的异同,对《大同集》的价值有新的评估。见《东方学报(京都)》第91册,2016年,第45—71页。陈先生于《朱门之特色及其意义》一文中谓“陈利用只收朱子诗入其《大同集》,而《实纪》即列其名”*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4页。,似并不知《大同集》一书之性质,误当作陈利用的个人文集。检元至正刊《大同集》(《中华再造善本》所收)卷首载至正十二年(1352年)孔公俊序云“文公筮仕尝五年,簿领于兹时著诗文若干卷,门人陈光卿辑录成编,名曰《大同集》”,明确以陈光卿为朱子门人。显然陈利用为朱子门人的认识,并非始于明代,至少元人已经视陈利用为朱门弟子。然则《实纪》之录陈利用为门人,有文献上的具体依据,是沿袭继承前人的认识,并非因《朱子文集·别集》曾采录《大同集》而臆断为弟子,主观上也无意于滥收,不可谓之“滥而又滥”。
《实纪》的记载渊源有自,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体现了“文献记载之真实”。它的记载是可以追溯的,并非自我作古、无中生有或者无端揽入。至于陈利用在事实上是否为朱子门人,是有关“历史事实”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展开讨论。陈先生急于论定“历史事实”,以为陈利用既非门人亦非讲友的认识才是“事实真相”,轻率指《实纪》的记载为“滥收”,对旧有记载的来由缺乏追根溯源的耐心和热情,态度粗暴。退一步说,即便陈利用事实上并非朱子门人,作者对《实纪》“滥收”的指控也无法成立,因为将陈利用视为朱子门人是有文献根据的历史认识。
(三) 杨复
笔者揣摩陈先生斥陈利用于朱门之外的根源,正是由于其认定传统记载普遍存在滥收以光大朱子门墙之弊,故严辨门人与否,即使并无确凿证据,亦务必剔除“可疑”之人,宁缺毋滥。如此于不必疑处求疑,精神可贵,而与陈先生自己所批评之“滥收”,本质上实则无有二致。传统记载唯恐于朱子门人有所遗漏,陈先生唯恐非门人而误作门人。最典型的是,陈先生甚至怀疑杨复也非朱门弟子。《朱子门人》“杨复”条考论如下:
《渊源录》十一8谓从文公游,复卒业黄榦之门。《源委》三27如之。《一统志》七四21云:“受业朱子,与黄榦相友善。”《统谱》四一22亦云然。《实纪》八3与《宗派》九11列为弟子。《学案》则只谓其与黄榦相友善。*按《宋元学案》卷六九:“受业朱文公之门,与黄榦相友善。”《宗派》九3与《补遗》六九79冯云濠据《渊源录》又以之为勉斋(黄榦)门人。是则是否朱子门人,实一疑问。*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71页。
此外,又于“陈德本”条谓:“然杨复是否弟子,大有问题。”*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24页。陈先生虽未将杨复摒于朱门之外,但上述论说逻辑,实在大有问题。传统记载如《大明一统志》、《考亭渊源录》、《朱子实纪》、《道南源委》、《万姓统谱》、《儒林宗派》、《宋元学案》及《补遗》,无一例外均以杨复为朱门弟子,没有异议。*杨复屡称朱子为“先师”,其为朱门弟子,夫复何疑。如杨复《仪礼图自序》云:“复曩从先师朱文公读《仪礼》,求其辞而不可得,则拟为图以象之,图成而义显。”又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序》:“先师朱文公集家、乡、邦国、王朝及丧、祭礼,皆以《仪礼》为经,而诸书为传,名曰《仪礼经传通解》。”叶纯芳、桥本秀美点校: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1年,第1页。所可疑问者,只在杨复是否又为黄榦门人而已。*实际杨复始从游朱门,朱子没后,复卒业黄榦之门,《考亭渊源录》“从文公游,后卒业黄幹之门”或当如此理解。陈先生却说“是否朱子门人,实一疑问”,大谬不然也。以陈先生之高明,而论证疏失有如此者,其要因端在勇于“疑古”,疏于“释古”,以致对传统记载之分析和理解出现本不该有的偏差。
明代《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等著作记载杨复、刘学古、陈利用等人为朱子门人,陈先生疑杨复非弟子,考定刘、陈皆非朱子门人。今据宋元人记载,则杨复自述师承朱子,宋人认为刘学古是朱子门人,元人以陈利用为朱门弟子,《实纪》、《渊源录》等不过继承宋元以来的认识,加以著录,并非蓄意滥收。陈先生指摘为“滥收”,并无实据,其论证主观色彩严重,猜测的成分很大,缺乏说服力。
二、 门人、讲友之分别及其论证方法
根据作者的考订,“实非弟子而各书滥作弟子者达一百四十余人”,其中“诸书以为弟子而实只是讲友者六十九人”。换言之,传统记载中将讲友误为门人的人数占据“滥作弟子”的总数的一半左右。门人、讲友之辨别,在《朱子门人》一书中所占的分量,由此可见一斑。本章首先以李如圭为例,检讨作者在分别门人、讲友方面以“《语类》无问答”为根据的有效性。其次,检讨作者以称谓区别门人、讲友的论证方法是否能够成立。
(一) 关于“《语类》无问答”
有关李如圭其人,《朱子门人》考述如下:
抚干李如圭,字宝之。……文公与之校定礼经。……《实纪》八17、《渊源录》十四14、《宗派》十14、《学案》卷六九18,均列于朱子之门。然《语类》无问答,《文集》卷五九18至19答李宝之一书,论祭礼祭义,于校定礼经有所指示。《补遗》六九60至65亦作弟子。惟王梓材案云:“先生之视朱子,盖在师友之间,故朱氏《经义考》数朱子校*《宋元学案补遗》确作“校”,然据《经义考》当作“授”。礼弟子,不数先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114页。
陈先生不信李如圭为朱子弟子的旧说,而从王梓材“师友之间”之论,定为讲友*条目“李如圭”前标记“△”,据本书凡例,标“△”者为讲友。,也即“诸书以为弟子而实只是讲友者六十九人”之一人。作者的关键证据一是“《语类》无问答”,一是王梓材案语之说,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有力证据。
然王梓材案语虽云“师友之间”,而《学案补遗》仍作弟子。《经义考》卷二八一至二八五为“承师”,述经学师承授受源流,其中卷二八三录有“朱子传易弟子”,卷二八四录有“朱子授诗弟子”,卷二八五录有“朱子授礼弟子”。助朱子编《礼书》(即《仪礼经传通解》)之弟子而不为《经义考》“朱子授礼弟子”所收者或不止二三人而已,最明显的是刘砥、刘砺兄弟二人皆在朱门,同助朱子编《礼书》*根据戴君仁先生的考察:“刘氏兄弟当是朱子晚年修礼很得力的人。”参见戴君仁: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与修门人及修书年岁考》,《戴静山先生全集二·梅园论学集》,台北: 戴顾志鹓,1980年,第663页。,而“朱子授礼弟子”数刘砥不数刘砺。*刘砺仅列入“朱子传易弟子”、“朱子授诗弟子”中。以李如圭不在“朱子授礼弟子”之列,揣测是因《经义考》编者不以李如圭为门人,与朱子乃“师友之间”,恐嫌武断。
至于“《语类》无问答”,作者想要说明的是,既然《语类》不载问答之辞,那么李如圭未登门的可能性很大。按照陈先生对门人的定义,未尝登门面见,不足以称弟子。上述“陈利用”条,陈先生即举“《语类》无其名”证利用非门人。陈先生分别门人、讲友,亦屡屡举“《语类》无问答”为证。如“吴仁杰”条,旧以仁杰为弟子,陈先生分析朱子书简,认为二人“似始终未面”,故定为讲友。*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0页。又如“吴翌”条,以“《语类》无问答”,认为“谓为讲友则可,谓为门人则不可。”*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8页。又如“符国瑞”条,云“想始终未曾相见,不宜列为弟子”*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199页。,定为讲友。然宋人对“门人”的认定,是否如陈先生之严格,不无疑问。若不必登门亦为弟子,则陈先生之“门人”标准,于古人有何意义?尚且登门与否,实际上只能推测,很难论证。
关于此《语类》无问答之李如圭,朱子弟子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义例》有如下叙述:
《祭礼》所引古今诸儒之说,如孙宣公奭、司马温公光则以“公”称,程子、朱子则以“子”称,或奏议于君前则以名称。其余皆以名见。间有以姓氏称者,曰“陈氏”,则三山陈祥道,先师尝称其《礼书》该博者也。曰“李氏”,则门人庐陵李如圭,尝问祭礼者也。曰“陈氏”,则门人三山陈孔硕,尝问释奠仪者也。*叶纯芳、桥本秀美点校: 《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第8页。近年宋燕、邓声国撰文考证李如圭生平履历,但未论及是否朱子门人,只谓李如圭“曾经为同时代著名理学大家朱熹所邀共修礼书,并赢得了朱氏的赏识。”参见宋燕、邓声国: 《李如圭生平事迹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第84页。
是杨复明言李如圭为朱子“门人”,则宋人已视李如圭为朱门弟子矣。杨复本人也是朱子门人,他的认识和意见我们自当格外重视。由此可见,即使某人在《语类》中无问答,也不妨碍其成为朱门弟子。《语类》无问答,不仅不能作为判断门人与非门人或门人与讲友的决定性证据,甚至作为旁证也并非十分有效。
此条杨复的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明代《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以下将李如圭列为朱子门人,应当是在掌握一定史料依据上作出的判断和处理,因而可以与较早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笔者深信《实纪》、《渊源录》等著作整理、编排旧有文献记载,系统辑录朱子门人事迹,主观上没有故意将讲友滥作弟子的意图。反而是陈先生始终不能摆脱对传统记载的偏见,主观认为传统记载多将讲友滥作弟子,所以陈先生辨别门人、讲友,势必反其道而行之,凡以为能当作“讲友”的,务求排除朱门之外,以还朱门之“真实”。但将李如圭当作朱子讲友,只是猜测悬揣,没有可靠的依据,自然不会成为“历史事实”或学者共识。
(二) 关于称谓
《朱子门人》在分别门人、讲友时,大量根据称谓作出判断,引人注目。兹举数例如下:
如开篇第一条“丁仲澄”,云:“《文集·别集》五9答丁仲澄一书说为学,函中称‘老兄’‘吾友’‘贤者’‘见教’,则讲友无疑。”*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49页。按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卷八《宋季朱门诸子七》:“丁仲澄,先生有一答书见《大全·别集》,但其书三十五卷以为答刘子澄,而《别集》以为仲澄,恐或《别集》误,故不录书类。”《增补退溪全书》第三册,首尔: 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1—1972年,第475页。根据退溪之说,该书简当为答刘清之(字子澄)。陈先生《朱子门人》据《宋元学案》以刘清之为朱子讲友,而近年石立善发现刘清之贽谒朱子之书,考订并非讲友而是弟子。参见石立善: 《朱子门人丛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15页。
又如“方耒”(字耕道)条,云:“《别集》五1至2三书,履称‘老兄’,《续集》六与方耕道第二书亦称‘老兄’,又自称‘浅陋’。……《正集》四六答方耕道第三书中称‘士友’,皆友辈之言。”“观其关系,友生为多,师弟为少。”*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56页。
又如“方谊”(字宾王)条,云:“朱子每称为‘方君’,‘朋友’,‘老兄’。《语类》一百第四六‘方宾王’条,非师生问答,乃记其来书。《学案》所谓问学于朱子者,乃师友之问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58页。
又如“王时敏”(字德修)条,云:“《文集》六一3致林德久(至)第五书,称‘德修王丈’,不如以讲友待之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63页。
又如“陈旦”(字明仲)条,云:“朱子辨其禅学(第二书),称‘老兄’(第一书),‘尊兄’(第十三书),‘长者’(第一书),恐非弟子而是讲友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10页。
又如“曾极”(字景建)条,云:“《文集》六一33至36答曾景建七书,乃与朋友讲学。书云‘辱书’‘鄙见’(第一书),‘贤者’(第五书),‘深荷录示’(第七书),‘相约俱来,以践前约’(第七书),皆友生之词……《实纪》不应以弟子视之。”*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38页。
又如“程深父”条,云:“闻深父死客中,深为悲叹(别六5与林择之第七书)。读择之《深父埋铭》,则云‘使人恻然兴于朋友之义’(别六9与林择之第十三书),可见感情颇好。其谊在讲友之间,实非门人。”*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45页。
又如“叶永卿”条,云:“然朱子称之为‘永卿主簿老兄’(别六19),亦说先天图。又云‘永卿诸公’(别六21),盖师友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78页。
以上八人,旧皆以为朱门弟子,陈先生于方谊仍作弟子,于曾极则定为非弟子亦非讲友,其余六人皆指为讲友。陈先生相信自己的感觉,凭直观认为“老兄”、“吾友”、“朋友”、“丈”、“诸公”等为友辈专称。按《朱子语类》乃朱子与门下弟子日常论学与交谈之实录,为我们提供了朱子称呼弟子的绝佳材料,而卷一一三至卷一二一凡九卷为“训门人”,尤便参考,不妨以之为主验证陈先生的判断是否成立。
1. “老兄”
朱子称门人“老兄”。如《语类》卷一一三第三一条,训大雅:“临别请教,以为服膺之计。曰: 老兄已自历练,但目下且须省闲事,就简约上做工夫。若举业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尝知义论》……”(第2749页)同卷第三二条,训大雅:“如老兄诗云‘中伦中虑’,只恁汎说何益?”(第2750页)朱子直呼弟子余大雅为“老兄”。此外,《语类》他卷余大雅录诸条,亦可见朱子数称大雅为“老兄”。卷二十第五五条“今看老兄此书只是拶成文字”,“乡令老兄虚心平气看圣人语言,不意今如此支离。”(第456、457页)卷三二第六二条“今且为老兄立个标准”。(第819页)卷九三第八九条“更有一说奉祝: 老兄言语更多些”。(第2363页)卷一四第一二条“大抵老兄好去难处用工”。(第2614页)朱子屡以“老兄”称大雅,是“老兄”不为友辈专称。
2. “吾友”
3. “诸友”
若泛称门人,则或云“诸友”。如《语类》卷一二一第一七条,叶贺孙录:“某平日于诸友看文字,相待甚宽,且只令自看。前日因病,觉得无多时月,于是大惧!若诸友都只恁悠悠,终于无益。”(第2923页)同卷第一九条,陈淳录:“诸友只有个学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度了日子。”(第2924页)同卷第一九条,潘时举录:“先生不出,令入卧内相见,云:‘某病此番甚重。向时见文字,也要议论,而今都怕了。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第2948页)
4. “诸公”
泛称弟子,又或以“诸公”相称。如卷一一三第三三条,训大雅:“诸公若要做,便从今日做去;不然,便截从今日断,不要务为说话,徒无益也。”(第2750页)卷一一四第二五条,训贺孙:“但觉得近日诸公去理会穷理工夫多,又自渐渐不著身己。”(第2760页)卷一一五第二七条,训道夫:“为学之道,在诸公自去著力。”(第2777页)卷一二一第八条,叶贺孙录:“诸公来听说话,某所说亦不出圣贤之言。”(第2919页)
5. “朋友”
朱子履称弟子为“朋友”。如《语类》卷一二一第一六条,叶贺孙录:“谓诸生曰:‘公皆如此悠悠,终不济事。今朋友著力理会文字,一日有一日工夫,然尚恐其理会得零碎,不见得周匝。若如诸公悠悠,是要如何?……’”(第2923页)此处“朋友”与“公”“诸公”,皆呼弟子之词。又如卷一一七第九条,训(周)谟“既受《诗传》,并力抄录,颇疏侍教。先生曰:‘朋友来此,多被册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第2809页)又如卷一二一第一条,王过录“朋友乍见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来此,先看熹所解书也。’”(第2917页)此“朋友”,亦明指弟子。《语类》亦有“浙中朋友”、“浙间朋友”、“江西朋友”、“漳州朋友”等,意谓出身以上诸地之弟子,非今日所谓朋友也。
6. “丈”
说了,德明起禀云:“数日听尊诲,敬当铭佩,请出整衣拜辞。”遂出,再入,拜于床下。三哥扶掖。先生俯身颦眉,动色言曰:“后会未期。朋友间多中道而画者,老兄却能拳拳于切己之学,更勉力扩充,以慰衰老之望!”德明复致词拜谢而出,不胜怅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赴官来相别,某病如此,时事*“时事”指庆元“伪学之禁”。又如此,后此相见,不知又如何。”道中追念斯言,不觉涕下!伯鲁进求一言之诲。先生云:“归去且与廖丈商量。昨日说得已详,大抵只是如此。”(小注: 称‘丈’者,为丈夫。伯鲁言。)(第2690页)
此条是廖德明于庆元五年(1199)拜辞朱子时所录。*参见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28页。文中两“朋友”,前一朋友,泛指门下弟子,后一“朋友”,则专指德明,“老兄”亦指德明。其中“廖丈”一词,亦指德明。文末有小注,解释称“丈”只是丈夫(男子)之意。可见,“丈”亦并非友辈专称。
通过以上对《语类》“老兄”、“吾友”、“朋友”、“诸公”、“丈”等语例的分析,可以确定这些称谓都是朱子称呼门下弟子的常用语。*兹仅就《语类》举例,其实《朱子文集》所载与弟子往复书简,此类称谓亦常见,毋庸详举。至如书简中习见的“浅陋”、“见教”、“辱书”等客套语,不足深论。陈先生根据上述称谓论证某人非门人而是讲友,不免“以今律古”,结论无法成立。门人与讲友身份完全不同,陈先生在没有坚定的证据支撑的情况下,轻易对传统记载提出异议,凭感觉和直观进退朱门弟子,从结果来看,与其说是在提出和解决问题,毋宁说是在制造混乱。
三、 附考赵唐卿
关于“赵唐卿”,《朱子门人》叙述如下:
如陈先生所述,“赵唐卿”在《朱子语类》正文中共出现两次,一次徐录、一次陈淳录。
赵唐卿问:“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机决矣,何也……”(第366页)
《语类》卷一一八第六八条,陈淳录云:
杨子顺、杨至之、赵唐卿辞归请教。先生曰:“学不是读书,然不读书,又不知所以为学之道。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圣贤之书说修身处,便如此;说齐家、治国处,便如此。节节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会,一一排定在这里;来,便应将去。”(第2855页)
对此“赵唐卿”,《朱子门人》谓“字里未考”,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亦云“名讳、里籍未详”。*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50页。其中卷一一八陈淳录中出现的杨履正(字子顺)、杨至(字至之)皆泉州晋江县人。田中博士根据赵唐卿和杨履正、杨至同时辞归,推测赵唐卿与二人当为同乡,也是泉州人。*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50页。然只是推测,未能证实,“赵唐卿”究为何人,仍待考证。
我们知道,《语类》正文出现的弟子,如非记录者自称,一般尊称字,“唐卿”也应为赵姓弟子之字。值得注意的是,卷一六第二四二条徐录“赵唐卿”三字下,在《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中有小注“汝仿”二字。*《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京都: 中文出版社,1982年,第234页。关于此本的特色和价值,参见石立善: 《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について―兼ねて语类体の形成を論ず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六十集,2008年,第163—180页。这条小注提示我们,赵姓弟子有可能名汝仿、字唐卿。检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六七《人物志(泉州府)》正有“赵汝仿,字唐卿,晋江人”的记载:
赵汝仿,字唐卿,晋江人。绍兴初,与父善新、弟汝偰同第进士。郡守表其里曰三秀。善新为封州倅,汝仿通判德庆府,筑堤障晋康江亘三十里。先是,濒江之田数滛于涝,至是,为上膄。知宾州,筑城,覆之以屋。居民旧江汲,汝仿于城中凿七井,民便之。提举广东市舶*黄榦《辞知潮州申省》所云“照对,榦九月十一日准省札二道,三省同奉圣旨……赵汝仿除提举广南市舶”,与《(弘治)八闽通志》小传“提举广东市舶”的仕履一致。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二,第666页。,迁提举常平茶盐。*黄仲昭纂修: 《(弘治)八闽通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845页。
此传虽未明言赵汝仿为朱子门人,其与《语类》之“赵唐卿”为同一人则属无疑。前述田中博士据《语类》卷一一八第六八条推测“赵唐卿”为泉州人,与《人物志》小传记载若合符节,博士的文献解读能力着实令人惊叹。
惟《人物志》汝仿进士及第年刻作“绍兴初”,“兴”当为“熙”之误。卷五《选举志(科第 泉州府)》“绍熙元年(庚戌)余复榜”条录有“赵汝偰、赵善新(汝偰之父)、赵汝仿(汝偰之兄)”*黄仲昭纂修: 《(弘治)八闽通志》,第703页。,即汝仿与父善新、弟汝偰同登进士在绍熙元年(1190)。父子三人同登进士,誉为“三秀”*传称“郡守表其里曰三秀”,此郡守为颜师鲁,绍熙二年知泉州。《(弘治)八闽通志》卷一四《地理志》云:“三秀坊,宋郡守颜师鲁为赵善新、汝仿、汝偰父子同第进士立。”《(弘治)八闽通志》,第182页。,传为佳话。汝仿又有弟汝佟,登嘉定四年(1211)进士第。*黄仲昭纂修: 《(弘治)八闽通志》,第705页。又同书卷六七《人物志》赵汝佟传云:“复与其兄之子后登嘉定进士第。”《(弘治)八闽通志》,第947页。似赵家另有一人在嘉定四年登第,然检《选举志》未得。汝佟有一子名崇,登绍定二年(1229)进士第。*黄仲昭纂修: 《(弘治)八闽通志》,第706页。汝佟又有子崇彪、崇靇与汝仿之子崇同第绍定五年(1232)进士。*黄仲昭纂修: 《(弘治)八闽通志》,第706页。一门三世,科第之荣,甲于东南。
又据《(乾隆)晋江县志》卷一一《人物志五仕迹》:
赵汝仿,字唐卿,(1)太宗八世孙。绍熙初进士,判德庆府,筑堤以障晋康江,亘三十里。知宾州,凿七井,城中以免江汲,民便之。提举广东市舶、常平茶盐。(2)归卒。*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 《(乾隆)晋江县志》,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94页。
此传(1)(2)两处是《(弘治)八闽通志》没有的信息。(1)“太宗八世孙”,谓赵氏为宋宗室之后,是所谓“南外宗子”,身份特殊;(2)“归卒”,知汝仿从岭南任满返乡后辞世。
陈荣捷先生曾说:“史传墓志与各地方志记其曾从学于朱子者,大概可信。难免少数府县,以参加朱门为荣,故偶与朱子过从者,亦言其从学。”*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9页。此或道出了一面之事实,但赵汝仿为朱子门人,而明清志书皆不书从学朱子事迹。或朱门弟子见于志书而诸志未予表出从学朱子事迹者,其人数反在以参加朱门为荣者之上,亦未可知。
关于汝仿的师事期,陈先生据《朱子语录姓氏》载杨至录“癸丑、甲寅所闻”,认为:“杨至录语类癸丑(1193)与甲寅(1194)所闻。三人于此时同门可知矣。”*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93页。此说可商。
第一次: 绍熙元年(1190)5月至绍熙二年(1191)二月。
第二次: 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至庆元元年(1195)十一月。
第三次: 庆元六年(1200)三月前后。*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63—170页。
刘砥的二次师事期如下:
第一次: 绍熙元年(1190)在漳州,下限在绍熙二年(1191)四月末。
第二次: 庆元五年(1199)左右。*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71—176页。
陈淳的二次师事期如下:
第一次: 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至绍熙二年(1191)五月二日。
第二次: 庆元五年(1199)十一月中旬至庆元六年(1200)一月五日。*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43页。
杨至的三次师事期如下:
第一次: 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二年(1191)四月二十九日朱子离开漳州以前。
第二次: 绍熙四年(1193)至绍熙五年(1194)。
第三次: 庆元五年(1199)末。*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152页。
综上,汝仿与上述诸人同席的时期只可能是绍熙元年(1190)至绍熙二年(1191)之间。朱子于绍熙元年四月知漳州,至绍熙二年四月辞职名归建阳,汝仿于此期间从游朱门,并于绍熙二年离开漳州返回家乡泉州。
确认“赵唐卿”的身份里籍,为我们探讨《语类》其他记录也提供了参考依据。如《语类》卷一二,第三四条,徐录云:
语泉州赵公曰:“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此条前论读书穷理,后论居敬。上引《语类》卷一一八第六八条,陈淳录:“先生曰:‘学不是读书,然不读书,又不知所以为学之道。’”云云与此条论“读书”大旨一致。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阙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阙这一事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后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云云,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便是个关聚底道理,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后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尝谓‘敬’字似甚字?恰似个‘畏’字相似。”(第2891页)
关于此“泉州赵公”,陈荣捷先生推测是赵汝腾。《朱子门人》“赵汝腾”条云:“其名不见《文集》、《语类》。然《语类》一二4619第三四条‘语泉州赵公曰:“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朱子门人中只汝腾来自福州(即泉州)。若赵公果是此人,则《语类》以之为门人也。”*陈荣捷: 《朱子门人》,第291页。传统记载未见以赵汝腾为朱子门人者,《宋元学案》及《补遗》皆以为只是私淑朱子,陈先生“《语类》以之为门人”的推测太过大胆。今知朱子门人中泉州赵姓之人有赵汝仿,并且汝仿与本条记录者徐曾同席,则此“泉州赵公”为赵汝仿的可能性很大。
《语类》两次出现“赵唐卿”,而其名讳里籍久为难解之谜。今结合利用《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和明清地方志的记载,成功考证出弟子“赵唐卿”的名讳爵里、师事年期,证实了田中博士对“赵唐卿”里籍的推测,订正了《朱子门人》“赵唐卿”、“赵汝腾”条的误说,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田中博士在《朱门弟子师事年考·序说》中介绍资料使用情况,也特别提到地方志的重要性*田中谦二: 《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三卷,第9、15页。,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个人精力,不可能做到穷尽检索。现在重要的地方志大多已影印出版,比田中博士著论时的条件已经有很大改善,自然要多加利用。像《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这样特殊的文献,有其独特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也要勤加翻检。
结语
《朱子门人》论列六百二十九人,举重若轻,立言简括,不蔓不枝,无繁琐考证之弊病,可读性强。此为本书之长处,亦为其缺陷之所在。立言简括,意味着作者常常在未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已经作出判断,得出结论。
陈先生考订明代以来关于朱子门人的传统记载如《朱子实纪》、《考亭渊源录》等,验以正史、地志与《朱子文集》所载书简及《朱子语类》问答之辞,判断其人与朱子是否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应该说,陈先生关怀很大,志在追求“历史真相”。但陈先生无视传统文献记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传统记载抱有甚深之成见,主观认为传统记载每多滥收以光大朱门,结果既不能平心静气分析传统记载,也未能比较准确解读《文集》书简、《语类》问答的内容,往往以今律古,凭感觉、直观匆忙下结论,任意进退朱门弟子。陈先生轻易驳斥传统记载,意图建立新的认识取而代之,但是这种缺乏文献依据和充分论证的认识不可能成为“历史事实”。笔者关心具体的文献记载和白纸黑字的真实,不能完全同意陈先生对传统记载的批评和判断,认为陈先生的部分辨析考订结果难称确论,论证逻辑、考证方法亦多可商榷,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2016年6月 初稿
2016年12月 修订
(附记: 本文初稿曾在2016第九届朱子之路研习营(福建·泉州)口头发表,修订成篇,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方旭东先生的亲切指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