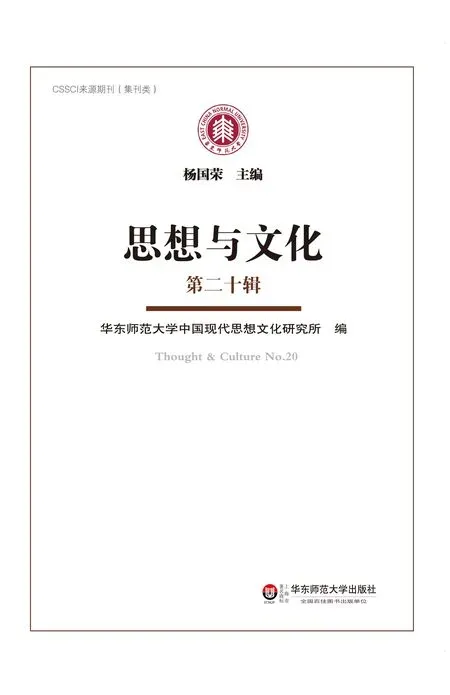贝克特与叶芝*
●
W.B.叶芝与贝克特,这两位爱尔兰文学巨匠,因分别获得1923年和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而享誉世界,两人虽相差41岁,却曾共同活跃于1930年代的世界文坛。致力于弘扬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叶芝,如今已被视为爱尔兰文化的正统代表人物,而定居在法国巴黎发展自己文学事业的贝克特,却更多地被认为吸收发展的是欧洲文化,加之其作品中几乎没有真实爱尔兰民族语境,故此,长期以来,在其故乡爱尔兰,尤其在爱尔兰文学传统的系谱梳理上,为人忽略。*贝克特196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爱尔兰国内学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逐渐将贝克特纳入到爱尔兰经典作家行列,爱尔兰研究的重要学刊《爱尔兰大学评论》(Irish University Review: A Journal of Irish Studies)直到1984春季才出了一期专刊研究贝克特作品。贝克特母校圣三一学院的经典学评论期刊Hermathena: A Trinity College Dublin Review对贝克特的研究更是姗姗来迟,在1986年才出了期冬季专刊,此时贝克特已八十高龄了。甚至在1997年Christopher Murray的专著《二十世纪爱尔兰戏剧: 国家镜像》(Twentieth-Century Irish Drama: Mirror up to Nation)里,贝克特依旧被排斥在以叶芝、格里高利夫人(Lady Gregory)为代表的爱尔兰戏剧传统系谱之外。随着对贝克特作品中爱尔兰性的发掘*如Eoin O’Brien的《贝克特的国度: 萨缪尔·贝克特的爱尔兰》(The Beckett Country: Samuel Beckett’s Ireland)(1986),以大量照片形式,将贝克特作品里暗指到的爱尔兰的人物、地方和风景展现出来。John Harrington著的《爱尔兰人贝克特》(The Irish Beckett,1991年)将贝克特作品完全放在爱尔兰知识分子圈、文化圈和社会环境里来考察。S.E. Wilmer编写的《都柏林的贝克特研究》(Beckett in Dublin,1992年)论文集里,第三部分多篇文章对贝克特本质上是都柏林人的特性做了专题讨论。,这个问题逐渐提上日程,即,在爱尔兰文学传统的系谱上,贝克特是否该有一席之地?要明确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研究另一个问题得到启发,那就是: 与贝克特同处一个时代的、为爱尔兰文学传统立足于现代文学呕心沥血的W.B.叶芝,是否对贝克特产生过影响?两者之间有无对爱尔兰文学的传承关系?
从表面看,以诗歌闻名文坛的叶芝似乎与后来以小说和戏剧享誉世界的贝克特交集甚少。1930年代的贝克特血气方刚,刚刚旅居于法国巴黎,进入的是爱尔兰同乡乔伊斯的文学圈,和乔伊斯一样,他不遗余力地寻求文学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对欧洲先锋艺术强于吸收的贝克特经知己好友托马斯·麦克格里维(Thomas Macgreevy)介绍,得与爱尔兰画家杰克·叶芝结识并很快成为挚友,但贝克特似乎刻意与画家之兄W.B.叶芝保持距离,两人终生只有一面之交。另一方面,贝克特对W.B.叶芝的态度本身就含混矛盾,这一切使得后人在考察W.B.叶芝是否存在对文学后进的贝克特的影响力时,都倍感棘手。然而,克实言之,无论在艺术创作理念还是创作实践上,两位文学大师间的关联都是那么微妙和深刻。而在爱尔兰文学现代化的建立和突破上,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亦有迹可循。本文拟从分析贝克特与叶芝复杂的纠葛入手,探寻两人之间隐秘的文学关联,以期对贝克特作品的爱尔兰性做出认定。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贝克特早年作为爱尔兰文学的浪子对叶芝的叛逆与逃离,第二部分梳理成熟时期的贝克特对于叶芝的认同与回应,第三部分以贝克特晚期作品《但,那些云……》为例说明贝克特对叶芝的承继与发展。
一、 叛逆与逃离
叶芝活跃的年代(1890—1930),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以叶芝为代表掀起的爱尔兰文艺复兴就是使爱尔兰摆脱英国化,拥有自己独立文学传统的一种努力。为此叶芝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回到爱尔兰历史中,去挖掘凯尔特民族传说和神话资源,着力重建爱尔兰独特文化身份。他将这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收编进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TheCelticTwilight),此名后来逐渐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代名词。由于叶芝在诗歌中成功将凯尔特民族传说深植人心,其许多诗句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当时许多青年诗人竞相模仿其早期浪漫风格,将爱尔兰神话传说尽皆入诗,追求对想象的古代世界的浪漫憧憬,以至有吹嘘炫耀凯尔特古代文明之嫌。这让叶芝感到不自在。因为他对自己早年略显浮夸的诗风并不满意,同时也觉得过分追求模仿其诗风有违其创作初衷。他为此写过一首诗《一件外套》(ACoat)讽刺那些盲目追随者:
我为我的歌 缝就
一件长长的外套
上面缀满剪自古老神话的花边刺绣
但蠢人们把它抢去
穿上在人前炫示
俨然出自他们之手*译文引自傅浩: 《叶芝的影响及其后的爱尔兰诗歌》,《外国文学动态》2001年第1期。
爱尔兰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的这股追风潮流让另一位未来文学大师也感到很不自在,那就是初出茅庐的贝克特。贝克特也是以诗歌开始立身于文坛的。1930年他在巴黎的时间出版社发表诗歌《占星术》(Whoroscope)并赢得头奖。这家出版社创始人南茜·古娜德(Nancy Cunnard)设奖1000法郎以“时间”为主题征诗,意在扶持嘉奖在诗歌现代性方面做出贡献的新人。贝克特这首98行的长诗占4个页面,其中17个脚注就占据了其中2个页面。在诗中,贝克特广征博引笛卡尔12卷著述,以时间为线索、以怪诞的讽刺笔法描述笛卡尔的精神生活。尽管有卖弄学问之嫌,但才华显而易见。南茜事后盛赞道:
多出色的诗句,多棒的形象和类比,通篇生动的色彩,技巧高超!这首长诗,部分地方写得神秘、隐晦,但很明显是知识渊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写出的。*Bair, Deirdre, Samuel Beckett: A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8, p.95.
贝克特对叶芝诗歌的民族性主题是颇不以为然的,从根本上就对叶芝所宣扬和代表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凯尔特薄暮”、“贵族立场”等都不信任,并在自己早期作品中对此加以嘲讽。在小说集《刺多踢少》(MorePricksThanKicks)中有个故事叫《谈恋爱,压马路》(WalkingOut),主人公巴拉夸与其未婚妻露西逛马路,而跛腿的露西走路的样子则被贝克特描述成“看起来像贵族叶芝”。*Beckett, Samuel, More Pricks than Kicks, London: John Calder Publisher, 1993, p.114.在贝克特早期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DreamofFairtoMiddlingWomen)中有一只停在一大卷卫生卷纸上的蝴蝶: 一个旋转起飞,像是“驶向拜占庭”。*Beckett, Samuel, Dream of Fair to middling Women, Eoin O’Brien and Edith Fournier eds., Dublin: Black Cat Press, 1992, p.129.在小说《莫菲》(Murphy)中,莫菲的朋友尼瑞(Neary),在都柏林邮政总局里以头撞向神话英雄库丘林雕像*库丘林(Cuchulainn),凯尔特传奇中英雄人物,在与敌作战中身受致命伤,为使自己直面屹立在敌人面前,临牺牲前将自己绑在柱上,敌人最后看到乌鸦停在库丘林肩头才敢靠近。爱尔兰雕塑家奥利维·舍帕德(Oliver Sheppard)将临死的库丘林形象塑成雕像,1934年雕像被官方安放在都柏林邮政总局(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指挥部)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英雄。叶芝曾在自己的诗《雕像群》(The Statues)中将库丘林和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联系在一起,歌颂复活节起义的英雄大无畏牺牲精神。参见Yeats, W.B., Collected Poems, London: Macmillan Collector’s Library, 2016, p.430。的屁股,以此嘲讽加诸英雄库丘林雕像身上的民族主义内涵。在其成名戏剧《等待戈多》里,贝克特对“凯尔特薄暮”做了颇具诗意的反讽。如果说叶芝笔下凯尔特的薄暮,是对母亲爱尔兰这片土地的热爱,充满无限神秘浪漫的美感:“这里露水永远闪烁,暮色永远灰蒙蒙”;“灰色薄暮比爱情更仁慈,清晨露水比希望更亲切。”*Yeats, W.B., Collected Poems, p.98.那么贝克特则在《等待戈多》中借波佐之口表达着对叶芝和对祖国复杂的心绪。当波佐站在自己的领土上,面对着黄昏,说了一番既有诗意又有深意的话:
它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如此地异乎寻常?作为天空?它苍白而又明亮,像是白天这一时刻在任何地方的天空。(停顿)在这地方(停顿)天气好的时候……(他的嗓音变得像是在唱歌似的*此处暗含着贝克特对叶芝强调其诗歌应像歌唱样吟诵的调侃。)在不知疲倦地为我们倾泻了(他略一沉吟,语气平淡地)就说早上10点之后吧,红色与白色的光芒之激流之后,(饱含深情)它开始失去它的光亮,开始变得苍白,再苍白,越来越苍白,直到后来,(突然停下,双手张开)噗!完蛋了!它不再动弹!但是,但是,在这道温柔与宁静的帷幕后面,黑夜疾奔而来,(嗓音变得有些颤抖)并将扑在我们的头上。(打了个响指)啪!就这样——(灵感离他而去)就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沉默。阴沉地)在这婊子养的大地上,它就是这样发生的。(长久的沉默)*Beckett, Samuel, The Complete Dramatic Work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6, p.37.
两人虽以各自拿手的艺术形式对祖国爱尔兰的薄暮做了诗意的描述,但不同于叶芝神秘的浪漫,贝克特的描述中透着戏谑式的现代主义的幽默,充满反讽的张力。细读之下,还能发现他对毕生要处理的现代主题的真诚描述。与叶芝对凯尔特薄暮的浪漫想象相反,贝克特看到的是黑夜将要扑在我们头上的冷峻事实。那种人类存在中并不光明的境况。
贝克特文字中如此或隐或现、密集地提到叶芝和叶芝作品,就不能说他不承认叶芝的成就或对叶芝不感兴趣。贝克特对叶芝的一些诗歌稔熟于心,信手拈来加以引用,说明了对叶芝诗歌成就的仰慕,但有时故意篡改引文形成反讽,又表明了他对叶芝宣扬的重建传统的深刻怀疑和全面否定。这种仰慕和讥讽参半的含混态度使其自己也难以察觉来自叶芝的影响力。
直接导致贝克特叛逆叶芝影响力的是20世纪30年代都柏林文艺圈盛行的民族主义氛围。贝克特对此的不满和对爱尔兰诗坛未来发展方向的焦虑,集中体现在他1934年化名安德鲁·贝利斯(Andrew Belis)发表的一篇评论《近年爱尔兰诗歌》(RecentIrishPoetry)中。文中贝克特直接将当前爱尔兰诗人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追随叶芝的“凯尔特薄暮迷们”,另一类则是追求更现代主题的“其他诗人”(比如他的好友诗人托马斯·麦克格里维)。而当前“凯尔特薄暮迷们”的诗歌,则缺失现代性的主题,徒具主题的灿烂光辉(注: 意指他们沉醉于描述爱尔兰景色、神话传奇等狭隘民族性内容)。文章嘲讽了叶芝及其众多追随者们(如诗人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e])对古代爱尔兰传说和神话的过分迷恋,称他们为“老古董”。他尖锐指出叶芝“逃避对自我的意识”,调侃地建议“曾经编织了最绚丽的绣品”*语出叶芝的诗《一件外套》。贝克特在此称叶芝为“编织了最绚丽绣品”的诗人,本身就有既仰慕又讥讽的双重态度。的叶芝应意识到“裸体派诗歌”优点,“裸体行走才更有意义”。*Beckett, Samuel, “Recent Irish Poetry”, Disjecta: Miscellaneous Writings and a Dramatic Fragment,Ruby Cohn ed.,London: John Calder, 1983,p.70.
对爱尔兰的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新方向,年轻气盛的贝克特表达了与引领当时文学风骚的叶芝迥异的看法。不同于后者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寻求文学灵感,贝克特的视野投向国际,他从法国诗人和先锋派艺术家——比如兰波,超现实主义者们,艾略特和庞德,先锋派画家范·费尔德兄弟(van Velde, Bram and Geer)、亨利·海登(Henri Hayden)等——那里寻求艺术灵感和发展方向。在《近年爱尔兰诗歌》一文里,贝克特提醒“凯尔特薄暮迷们”应察觉到主客体间关系的崩溃,人的自我与世界之间存在的真空或荒原地带。他建议爱尔兰诗人们从艾略特或杰克·叶芝作品里去寻找、发现要关注的主题。在他看来,杰克·叶芝作品的伟大就在于他在绘画中“用光照亮了人类困境的黑暗大门”。*Beckett, Samuel, “Recent Irish Poetry”, p.71.这也使他自己开始执着于描绘人类存在的困境,重复着“除去习惯、无聊、遗憾和痛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主题,并将这主题贯穿在其小说和戏剧作品中,表现出对现代人的存在的透彻的体察。这种一以贯之的现代主题与叶芝诗歌中对凯尔特传统的宣扬的民族性主题恰恰遥遥相对。从这方面看,《近年爱尔兰诗歌》不啻是贝克特对叶芝代表的民族主义诗人发表的现代主义宣言。在构建现代爱尔兰文学方面,贝克特更强调立足于世界的原创性而不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古籍挖掘。
艺术创作理念上的背向而驰,使年轻时的贝克特一直刻意对名声日炙的叶芝保持距离并尽量回避。贝克特传记作家拜尔(Bair)解释说,此举还因为贝克特认为叶芝为人傲慢自大,装腔作势。俩人终生所见过的唯一一面,是1932年9月在都柏林乡村丢恩丽瑞(Dun Laoghaire)海边小镇基莱尼(Killiney)的沙滩,当时贝克特对叶芝在家人面前的假笑很是反感*Bair, Samuel Beckett: A Biography, p.121., 但此次会面中,向来对现代主义诗歌没好感的叶芝*叶芝对当时一些现代主义诗人这样批判: 结构方面“从头到脚全不成样子”(参见Allt, Peter, et al.,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ms of W. B .Yeats, Macmillan, 1971, p.639 ),又缺乏想象力,将“最糟糕的乏味和晦涩结合到了一块”(参见Howes, Marjorie and John Kell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 B .Yea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3)。竟夸赞了贝克特获奖诗歌《占星术》并背诵了其中几行,这让贝克特深感意外和吃惊。*Ellmann, Richard, Samuel Becket: Nayman of Noland, in Four Dubliners,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7, p.98.
也许贝克特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创作实践上对叶芝的追随。但也许旁观者清,贝克特的知己好友托马斯·麦克格里维在初识贝克特不久就观察到了贝克特与叶芝的相似。在麦克格里维看来,贝克特与他向往的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创作模式迥然不同,反倒是和叶芝在艺术探索上非常相似。作为当时都柏林艺术俱乐部活跃的成员,麦克格里维与叶芝父亲画家——乔治·叶芝过从甚密,在他1929年7月写给乔治·叶芝的信中提及“我的朋友贝克特在20岁就越来越像W.B.(叶芝)了”。*参见麦克格里维网上个人档案馆: http: //www.macgreevy.org/style?source=let.mac.1929-07.xml&style=gyeats表面上看,贝克特炮轰了叶芝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文学,最后选择远离都柏林文艺圈,转而加入在巴黎的乔伊斯文学圈,他追随的是乔伊斯而不是叶芝,但随着他文学探索的深入,他发现了自己真正要表达的与乔伊斯是不一样的:“(我们之间)不同在于,乔伊斯对材料的驾驭,是让词发挥到极大功用……而在我所做的工作里,我不是素材的驾驭者。乔伊斯知道得越多,他能做的越多,他是趋近于全知全能的艺术家。我要处理的是无知无能。”*Mercier, Vivian, Beckett/Becket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8.
二、 认同与回应
摆脱了乔伊斯直接影响的贝克特,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叶芝也有了更清晰的判断和认识,更多的认同替代了以前的嘲讽。据贝克特朋友安娜·阿提克(Anne Atik)回忆,晚年的贝克特在饭桌上经常引用叶芝的诗,将叶芝和弥尔顿及莎士比亚相齐并论,认为他们的作品中关注到元音与辅音间的和谐。*Atik, Anne, How It Was: A Memoir of Samuel Becket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1, p.55.他认为叶芝写过一些很伟大的诗歌,晚年的一些诗歌尤其好,接着他就背诵起叶芝的《塔》(TheTower)。*Atik, Anne, How It Was: A Memoir of Samuel Beckett, p.95.阿提克着重指出贝克特背诵叶芝诗歌时的特殊的方式,他采用一种特别的“低吟浅唱”*Atik, Anne, How It Was: A Memoir of Samuel Beckett, p.106.,非常接近叶芝本人对诗歌朗诵的探索。*叶芝一直极在意念诵其诗歌的嗓音和念诵的质感,具体体现在他在BBC广播电台朗诵自己诗作的录音,其念诵方式接近于“无调性的吟唱”。参见Schuchard, Ronald, The Last Minstrels: Yeats and the Revival of the Bardic A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01。这似乎说明贝克特也像叶芝一样深刻认识到声音的音乐感在其诗歌中的重要性。
尽管贝克特在评论爱尔兰诗歌时,对叶芝为代表的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内容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妨碍他从叶芝作品中获益,他不仅欣赏和接受叶芝在诗词上的音乐性,对叶芝在戏剧形式上的探索成果更是兼收并蓄。
叶芝其实对爱尔兰戏剧现代化做出过可贵的探索。当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叶芝时,他的获奖理由是:“用鼓舞人心的诗篇,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参见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http: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23/叶芝的反应则是,更强调自己在爱尔兰戏剧现代化方面的贡献。在颁奖典礼上他演讲的竟是“爱尔兰戏剧运动”,他想告诉世人“假如我没有写任何剧本或任何戏剧评论,假如我的诗歌不具备被搬上舞台的品质,英国委员会很可能不会将我的名字推荐给你们(瑞典皇家学会)”。*参见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http: //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23/yeats-lecture.html叶芝期望通过戏剧活动使更多爱尔兰人热爱、认同本民族文化。出于复兴爱尔兰文学需要,叶芝与格里高利夫人一起创办了阿比剧院,演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戏剧,发现并栽培了像辛格(John M. Singe)和奥凯西(Sean O’Casey)这些剧坛新秀。面对当时泛滥的低俗的都市剧和商业剧,叶芝感觉“(本国)戏剧在其剧本、言词、表演和场景方面都必须进行改革”。*Yeats, W.B., Samhain: 1903 The Reform of The Theatre, in The Irish Dramatic Movement, Mary FitzGerald & Richard J. Finneran eds., New York: Scribner, 2003, p.1.为此他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倾力打造一种理想戏剧,在叶芝看来,理想的戏剧不是当时一统天下的现实主义戏剧,不是流行的肤浅、低级趣味的都市剧和商业剧,而应当是接近戏剧之初始状态时的诗意的戏剧。演员必须再变得像荷马时代吟游诗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保有诗的韵律、声音的音乐感。戏剧的目标就是对崇高、英雄的生活的思考。*出自叶芝1899年3月在都柏林的爱尔兰文学社的一篇演讲,参见Pierce, David, ed., Irish Wri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Reader,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pp.49-52。可以看出叶芝倡导的理想戏剧意在通过戏剧对观众产生精神影响,唤起崇高民族意识。为此叶芝自己也积极投身戏剧创作,将爱尔兰古老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融入到自己近三十部戏剧作品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凯斯琳伯爵夫人》(TheCountessCathleen)、《凯斯琳·尼·胡里安》(CathleenniHoulihan)、《在鹰井边》(AttheHawk’sWell)和《炼狱》(Purgatory)等。
为实现这样的戏剧理想,叶芝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戏剧上的一系列实验。诗人的天分使其在戏剧方面非常强调台词音韵之美,讲究台词的发音方式和节奏,力图创造出富于诗歌气息的戏剧效果。为了让其戏剧在表演中凸显语言的诗意,1902年,他和阿比剧院女演员弗罗伦斯·法尔(Florence Farr)在一起进行人声实验,用改良过的中世纪拨弦乐器索尔特里琴伴奏,寻找念诵诗化台词的新法,这种发声方法要超乎说话和唱歌间区分,力图将诗的念诵变成吟唱。这对演员来说挑战很大,至少需要大量嗓音方面的长期特殊训练。而叶芝的探索并未尽于此,他又将日本能剧中面具、伴唱和舞蹈等元素引入他的《在鹰井边》等四部剧作*四部舞剧指: 《在鹰井边》(1906)、《埃玛的唯一嫉妒》(The Only Jealousy of Emer,1919)、《骸骨之梦》(The Dreaming of the Bones, 1919)和《卡尔弗里》(Calvary,1921)。中,使他之前的戏剧从讲究言说的诗剧转变为舞蹈性戏剧,力图创作融音乐与舞蹈一体的诗性戏剧。
尽管其戏剧文本具有诗性特点,但其戏剧总体上更像是吟唱式表演,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戏剧。许多艺术家、学者认为其戏剧“缺乏戏剧性”(untheatrical)。年轻时的贝克特也不例外。贝克特早在圣三一学院做学生时,就受过叶芝戏剧的耳濡目染。当时阿比剧院常年上演叶芝、辛格(M. Singe)和奥凯西(Sean O’Casey)等人剧作。贝克特在1934年8月7日给密友麦克格里维的信中,提到自己观看过叶芝的《复活》(TheResurrection)和《大钟塔王》(TheKingoftheGreatClockTower),他当时的评价和多数学者一样: 认为两剧枯燥无趣,不够戏剧性,难以忍受。*Knowlson, James,Damned to Fam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181.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戏剧创作体验的积累,贝克特逐渐表现出受叶芝戏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贝克特难忘叶芝在戏剧中创作的一些形象,1960年他刻意找来叶芝作品阅读,并在自己戏剧作品中回应式运用,这回是敬意大于不恭,比如贝克特的《戏剧草稿I》(RoughforTheatreI)中盲人与跛子这种共生的形象(互相依赖又彼此独立的两人),非常接近叶芝戏剧《在波伊拉海滨》(OnBaile’sStrand)中盲人与愚人形象以及《猫与月》(TheCatandTheMoon)里盲人乞丐与跛子乞丐形象。叶芝的戏剧不同于当时主流的现实主义戏剧,反映的是主观世界,展现的更像是心灵之眼所看到的景观。贝克特在导演自己戏剧过程中,逐渐认同叶芝戏剧的这种特点,1971年贝克特在德国柏林席勒剧院导演自己戏剧《快乐的日子》(HappyDays)时,在自己的这段剧场笔记*参见Knowlson, James, ed., Happy Days: Samuel Beckett’s Production Notebook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5, p.51, 61, 71.里,就引用了叶芝《在鹰井边》(AttheHawk’sWell)开头的句子“我对着心灵的眼叫喊”,显示了自己的戏剧在对内心景观的展现方面趋同于叶芝戏剧。
贝克特受叶芝戏剧的影响,尤其见之于他对剧场空间的运用。叶芝戏剧为了呈现给观众以心灵的景观,舞台布景总是清空到极简。《在鹰井边》里,除了舞台后方一堵墙,靠墙立着的一个装饰屏风之外,舞台几乎是空荡荡的。其最后一部戏剧《炼狱》(Purgatory),1938年8月10日在门剧院(Gate Theatre)上演时,尤其在舞台布景上大获全胜。在这部戏里,叶芝已将一切不必要的舞台布景尽皆去除,只剩下光秃秃的场景: 空旷的乡村道路、两个孤零零的男人、一棵枯树和一块可以歇坐的大石头。当时已在巴黎发展自己的贝克特恰巧回都柏林探亲,他第一时间在信件里将上演消息告诉了自己密友麦克格里维*Fehsenfeld, Martha Dow & Lois More Overbeck eds., The Letters of Samuel Beckett Volume I: 1929-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39.,可见其对叶芝戏剧的在意。而且多年后贝克特在自己戏剧中对叶芝这部戏剧有所回应。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的开头景象即是: 乡村道路;一棵枯树;黄昏;两个流浪汉,其中一个正坐在矮丘上脱鞋。
如果说在舞台空间运用上,贝克特在戏剧上牛刀初试时就表现了对叶芝戏剧的回应,那么在突出视觉形象方面,叶芝的戏剧实验手法无疑给贝克特提供了更多启发和发展可能。叶芝的《在鹰井边》除了舞台布景极简,还吸收了能剧元素,叙事也减少到最少的程度,实际上已没有动作,只剩守井人的鹰舞蹈的视觉形象。贝克特对这部戏的凝练风格非常欣赏。在不断去除舞台上任何不必要的布景到只剩视觉形象方面,贝克特彻底吸收叶芝的实验性做法并运用于自己的戏剧中,甚至将之进行得更彻底。纵观贝克特戏剧,如果说早期的《等待戈多》中还能在舞台上看到乡村道路、光秃孤树和四五个舞台人物的话,那么越到中后期作品,人物和人物的动作越来越少,背景越来越单调,直至空荡荡的舞台上黑暗中涌现出的头颅(如《戏》[Play],《那时》[ThatTime])或嘴巴(如《不是我》[NotI]),甚或一束强光下的一堆垃圾和一声呼吸(如《呼吸》[Breath])。以极简风格突出舞台形象方面,贝克特似乎已经超出对叶芝戏剧简单的认同和回应了。
三、 承继与发展
晚年的贝克特甚至将叶芝诗歌中的语词和形象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戏剧作品中,表现出对叶芝艺术手法的更全面的承继和发展。这突出体现在他1976年的戏剧《但,那些云……》(But,TheCloud...)。这部戏剧的名字即出自叶芝1928年的诗《塔》。在此之前贝克特曾考虑用《诗歌仅有的爱》(PoetryOnlyLove)为剧名。但最终还是叶芝诗歌魅力占了上风。叶芝在这首诗里以设问方式将想象力聚焦于“能爱却不能赢得”的女人形象上:
想象力是关注于
赢得的女人
还是失去的女人*Yeats, W.B., Collected Poems, p.272.
贝克特对此心有戚戚焉。贝克特与自己表妹佩吉(Peggy Sinclair)间有缘无分的爱的经历和叶芝与茅德·冈女士(Maud Gonne)无果的爱有几分相似。困扰着这两位文学巨匠的“错失的爱”进而被他们分别转化为诗歌、戏剧创作的灵感。叶芝在《塔》中塑造的“能爱却不能赢得”的女人形象在贝克特作品中一再出现,萦绕不去。*如小说《莫菲》中主人公莫菲的女友西莉亚(Celia),舞台剧《克拉普的最后一盘磁带》(Krapp’s Last Tape)里老年孑然一身的克拉普,对着录音机倾听自己年轻时和女友划船的美好回忆。广播剧《啊,乔》(Eh, Joe)中萦绕在乔脑中的一个声音提醒他,他曾放弃的对一个年轻女人(后自杀)的爱才是真爱;电视戏剧《但,那些云……》里被男人M从记忆中召唤出的年轻女人W等。
晚年的叶芝在这首诗歌里,借用富于质感的形象集中表达的是诸如“记忆力衰败、想象力、灵魂自由”等人类境况中普遍的主题,这也是贝克特欣赏并在创作中予以表现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贝克特更进一步以戏剧形式对叶芝诗中语词和形象做了创造性运用。
贝克特的《但,那些云……》展现了一个叫M的男人的意识世界里三组动作,观众感觉到他在重拾记忆里一段未得到回报的爱情。M在意识中尽力唤起对W(一个女人)的回忆,渴望她出现在自己的意识中。他设想出三种她出现的方式: 第一种,她出现但很快消失;第二种,她出现并逗留,“我苦苦恳求她,趁还在,看看我”;第三种,她出现,然后,过了一会,蠕动嘴唇无声地念着叶芝《塔》的结尾“云,但那些云……挂在天空……”,M则同时轻声地与W一起念叨叶芝《塔》的这一小节:
但,(它们都像)那些云彩,
随着地平线隐去,
或像暗下去的阴影,
小鸟的一声倦啼。*Yeats, W.B., Collected Poems, p.274.
无疑M对第三种她出现的方式很满意。在其中叶芝诗歌语词和形象似乎分开,但又因男人M随W即“错失其爱的女人”口型念出诗词而又合二为一。
在诗歌《塔》中,叶芝用想象力聚焦的“失去的女人”是已逝去的,叶芝试图召唤的是鬼魂,而贝克特通过采纳此诗中部分词语为他的剧名,表现出他对逝去的爱人的鬼魂形象的兴趣。这部电视戏剧是应BBC之邀而创作的,在创作此剧之前,贝克特刚刚完成他的戏剧《鬼魂三重奏》(GhostTrio)的排练。他告诉友人,新创作的这部戏《但,那些云……》与《鬼魂三重奏》在情绪上是一样的。*Knowlson, James,Damned to Fame, p.559.他将BBC 2台即将播出的自己的三部戏剧《鬼魂三重奏》、《不是我》和《但,那些云……》冠以总称“阴影(shades)”,这亦是取自叶芝诗《但,那些云……》中最后一词,而shade的另一层意思即是“鬼魂”。
但叶芝诗里的词与形象在贝克特戏剧里被巧妙转用了,以服务于贝克特式主题: 追求来自无意识的词语和形象。整部戏剧充满仪式感,像是由M进行的一场降神会,剧中M在夜晚蜷在禁闭的小房间里,在意念中召唤已死的心爱女人的灵魂出现:“我开始恳求,她,出现,在我面前”*Beckett, Samuel, The Complete Dramatic Works, p.450.,尽管她的灵魂只以她模糊的脸的形象浮现。观众更像是在出席一场招魂会,在缓缓进行的仪式里,通过灵媒人物M,看到已死者的鬼魂,或一段已逝的记忆被神秘召回到M意识里。叶芝对招魂的迷恋,对神秘精神现实的探寻,对戏剧仪式感的追求,似乎都在晚期贝克特这部戏剧里有了回声和创造性运用。贝克特创造性地运用招魂仪式展现人的潜意识里稍纵即逝的记忆瞬间。比起叶芝,贝克特则更具才能将意识中不相关联的几个片段,以戏剧形式,更简洁、直接地呈现出来。贝克特在戏剧领域似乎达到了叶芝设想的艺术境界: 诗意的戏剧。英国批评家阿尔瓦雷斯这样评价贝克特戏剧:
贝克特戏剧所达到的是真正的诗歌般的剧作。无论是从戏剧概念还是从语言来说,它们造成的印象,像诗一样直接而省略,通过一种删除多余笔墨而抓住本质,同时又富有生气、激动人心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一旦摆脱了小说中那种注重自我的抑郁,他的想象力的遨游似乎更为自由、酣畅了。*A.阿尔瓦雷斯: 《贝克特》,赵月瑟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反观叶芝一生,为使爱尔兰戏剧有别于长期以来在这个国家占支配地位的英国戏剧,他利用爱尔兰传统文化中远古神话和古老传奇素材,大胆引进吸收日本能剧元素,在戏剧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使爱尔兰戏剧立足现代化世界的一种努力。可惜的是,叶芝的戏剧探索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戏剧对演员的专业训练固然有较高要求,但他戏剧的非戏剧性和诗化特点又使人们宁愿将其作为案头戏(closet drama)甚至诗歌的变换形式来读。
叶芝的戏剧在其生前,除了在其亲手参与创立的都柏林的阿比剧院常有上演外,在爱尔兰国内其他地方及国外,鲜有演出,在其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则很少在叶芝戏剧节之外的舞台上演。尽管他坚持探索戏剧艺术四十年之久,一生排斥低俗商业化戏剧,力图将观众和戏剧从商业主义基调中带回到戏剧艺术崇高和尊严的基调中来,但他的实验性戏剧并没有受到当时观众的追捧*奥斯丁·克拉克描述自己第一次接触到叶芝戏剧时提到:“大部分座位是空的,舞台上灯光幽暗,仪式缓缓展开。”参见Clarke, Austin, “My First Visit to the Abbey” , in The Abbey Theatre: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E.H.Mikhail ed., London: Macmillan, 1988, p.128.,直到今天,也未能成功地走向世界。而贝克特就不一样了,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贝克特的理由是“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转引自焦洱、于晓丹: 《贝克特: 荒诞文学大师》,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易言之,正是贝克特,使爱尔兰戏剧变得更国际更纯粹成为可能。
无疑,叶芝作品已经成为爱尔兰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贝克特作品的爱尔兰性却晦暗不明。然而,根据本文的研究,叶芝为爱尔兰打造屹立世界的诗意戏剧的理想,恰恰由一度在艺术上叛逆他的贝克特承继和发扬光大。这一事实不是足够耐人寻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