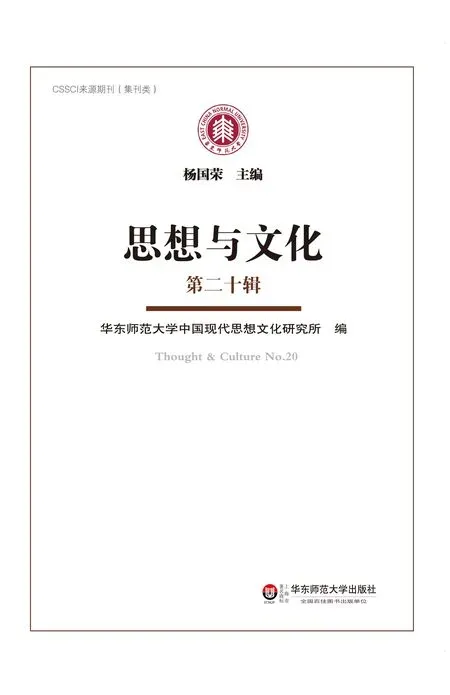推理与做事*
●
推理与做事处在知行关系这一问题域的中心地带。推理当然不同于做事。尽管有反心理主义的强势潮流,但通常认为推理(至少是很多时候)生自内心,而做事尽管也离不开内心,却往往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显露于外。另一方面,推理显然又与做事紧密关联。我们可以对他人做过的事进行推理,以便看它是否合乎情理。而从哲学上来看,二者之间最吸引人的联系莫过于: 推理可以指导我们(至少是认同理性的人)做事。根据通俗的讲法,这种指导就是,如何推理决定了我们如何做事,“正确”做事总是伴随“有效”推理。甚至,在某些专注于推理研究的逻辑学家或哲学家看来,这其中有专门的“实践推理”问题,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能够导致行动(即以行动作为结论)的“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或安斯康姆倡导的用以表示行动中手段与意向之关系的、后来很多人所谓的“工具型推理”(instrumental reasoning)。
本文的讨论将从有关未来偶然命题的哲学困惑切入,先考察逻辑真理对于自然事件的“逻辑要求”,然后推进到实践推理的有效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推理有效性何以与我们做事相关。
一、 从未来偶然命题之难说起
我们都是拿语言来说事的,譬如,“这是一名外国人”,“人非圣贤”。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说“明天将会下雨”。后者在语言形式上比前两句话多出了用以表示将来的时间词。*在英语等语言中,还会体现在时态变化上。但是,当在逻辑上处理这些句子时,我们通常将它们全部都称作命题。也就是说,即便是像“明天将会下雨”这样被认为表示未来偶然事件的句子*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西维茨所举例句分别为“明天将会有海战”和“明年12月21日正午我将会在华沙”。,也属于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的命题。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件事要么发生,要么不发生,因此关于这件事的断定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有人可能想说: 你不能简单地说这句话是真(假)的,而要具体说这句话明天是真(假)的,或者在某一地域范围是真(假)的。但“明天”这个限定词分明已经包含在这句话本身之中了,而至于地域范围,由于这句话本身并没有讲,所以,跟这句话的真假并不相干。还有人可能会说: 你无法提前知道这件事是否发生,因此没办法判定其真假。但是,一个人(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为真(假)的命题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是真(假)命题。能不能知道以及如何知道一个命题的真假,那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跟逻辑无关。这里关键的一点是,从逻辑上来看,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其本来面目,不管怎样,真(假)的就是真(假)的,真(假)的永远都假(真)不了。于是,若某一命题为真(假)命题,它一定就是真(假)的,不可能是假(真)的。而这里所出现的“一定”、“不可能”等用语其实不外乎是说:“真命题必然就是真的,假命题必然就是假的。”
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我们带上“必然”这样的修饰词之后,一个重大的哲学困惑便随之产生了。根据上述思路,“明天将会下雨”这句话便意味着: 如果它是真(假)命题,那么,它必然是真(假)的;即便在明天到来之前,它也是真(假)的,没有什么能阻止其为真(假)。尽管我们用了“如果”一词因而尚未明确那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其实已经很清楚,不论它是真还是假,那句话所表达之事发生或不发生都是早已注定好的、无法改变的、不可避免的,因为那句话本身的真或假是必然的。事实上,我们有时连“如果”一词也不需要用到。譬如,我们可能并不是在“今天”而是在“昨天”来说“明天将会下雨”这样的未来偶然命题。在这种情况下,该命题所表示的其实就是现在已发生了或未能发生的事件,难道能说现在的下雨(或没有下雨)是早已注定好、无法改变、不可避免的吗?很明显,这违背了人们关于天气的常识,即,明天是否会下雨,是未来的一个偶然事件。即便我们是在全方位观察了气象条件或查看了气象专家的预报之后才那样说的,我们(包括气象专家)也都会坦率承认那句话并非“必然”为真或“不可能”为假。我们相信,虽然我们所说的那句话很可能是真的(即概率很大),但它所要表达的事情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违背人们常识的这种理论,在哲学史上被称作宿命论或命定论,在神学上经常用来证明“上帝”(神)具有预知一切的能力。今天,当剥去神学外衣后,这种理论在社会上已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它依然常常成为当代哲学家们的困扰。哲学论证上让人困惑不解的是: 为何它竟是(至少看起来是)从逻辑原理出发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问题要远比初看上去时棘手得多。因为,上述论证完全可以脱离开神学上所谓“上帝”或“先知”的预设而成立,它甚至不必预设有任何“人”或“主体”能够具有预言能力。就纯粹的逻辑形式来看,命定论的核心前提是存在所谓的未来偶然命题,即,我们可以在事件A实际发生之前去说“A将会发生”,而且这种说法有真假可言。为了能避免从逻辑上得出命定论的结果,有些现代逻辑学家发现二值原则(即任何命题只有“真”“假”两个值)或许是一个可以质疑的、仅适用于“经典逻辑”的理论预设。于是,我们看到有逻辑学家通过指派给未来偶然命题第三种真值(甚至有更多的真值,用0和1之间的分数来表示)来建立三值逻辑、多值逻辑或模糊逻辑,试图达到修正“经典逻辑”之目的。但是,对于这种第三值属于“非真非假”(truth-value gap)还是属于“既真又假”(truth-value glut),存在重大争议。由此所付出的更为严重的代价是:“矛盾律”和“排中律”在这些非经典逻辑中失效了。这些困境的存在*更多有关该困境的逻辑哲学讨论,可参看Jennifer Fisher, On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Belmont: Thomson Wadsworth, 2008,pp.91-138.,意味着,我们无法轻易地抛弃命定论的核心前提,即,我们可以在事件A实际发生之前去说“A将会发生”,而且这种说法也可以是真的。在肯定或否定这个“前提”之前,我们至少需要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 逻辑必然性能影响自然事件吗
我们有时在事件A实际发生之前去说“A将会发生”,而且这种说法是真的。对此应该如此理解呢?这正是哲学家赖尔在其《“过去早就如此了”》(“It was to be”)一文所试图回答的问题。*Gilbert Ryle, Dilemmas: The Tarner Lectures 19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pp.15-35.在本节中,笔者无意展开他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也不准备严格遵循他的论述用语或关注视角,而是重点呈现其中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基本观点,即,逻辑真理尽管对自然事件的发生有某种逻辑上的要求,但并不会干预自然进程。我们将看到,这个基本观点不仅对于我们认清未来偶然命题之难起到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实践推理有效性问题进而正确把握推理与做事之关系有启示意义。
基于对自然语言的敏感性,赖尔提醒我们: 当有人在事件A实际发生之前说“A将会发生”时,其所指的只是他对于未来的一种预测而已,而对于此种预测之所谓的“真假”,日常语言更加自然的表达则是“预测(不)正确”或者“猜对(错)”。*Gilbert Ryle, Dilemmas: The Tarner Lectures 1953,pp.18-20.譬如,在赌马时,有人在赛马前预测“这匹马将会赢”,这种预测就是所谓的未来偶然命题,而且这种预测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当我们说“某人猜这匹马会赢,是正确的”时,意思不过是说:“他猜那匹马会赢,而那匹马果然赢了”,即,他此前的预测现在被赛马结果验证为真了。这应该就是我们说某未来偶然命题为真时的最纯朴想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事件决定了命题之真假,即,一个说“某件事发生”的命题为真的,当且仅当,这件事的确发生了。这可谓是逻辑学上二值原则的经验基础。此种二值原则的逻辑要求,反映在作为预测的未来偶然命题之上,便意味着:“这匹马会赢”作为一种预测是对的,当且仅当,这匹马果然赢了。
此种符合逻辑原则的“朴实真理”,何以能让有些人从中得出了命定论(即做什么也挡不住事件的发生)呢?赖尔告诉我们,那是因为他们把事件发生之前的“预测”混同于事件发生之后的“记录”了。简单来说,我们对于某件事所形成的命题,可以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对其所作的“记录”(描述),也可以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对其所作的“预测”(预言)。不论是“记录”型的命题还是“预测”型的命题,都符合二值原则的逻辑要求,即,要么是真的(正确的)要么是假的(不正确的)。唯一的差异是:“记录”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命题,“预测”是在事件发生之前的命题。它们相对于事件而言的先后位置可以表示为:
图式1 预测→事件(发生)→记录。(“→”表示“时间方向”)
这种表示时间先后关系的位置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是位于前面(即相对靠左)的东西因果性地导致了位于后面的(即相对靠右)的东西,即,正如事件的发生使得记录为真一样,预测为对使得事件得以发生。然而,这种联想是很成问题的。不可否认,记录之所以为真,原因总是因为事件的确发生过了,以至于可以说时间上位于前面的“事件”发生使得位于后面的“记录”为真。但是,我们并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预测(对)”与“事件(发生)”之间的关系。虽然预测在时间上总是位于事件发生之前,“预测之对”却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前。恰恰相反,每当我们说“预测为对”时,总是意味着事件已经发生过并据此才判定“预测”为对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完全不是“预测为对”使得事件得以发生,而是它在逻辑上要求事件已经发生。事实上,不只是“预测为对”在逻辑上要求事件发生过了,即便是“记录为真”也在逻辑上要求它: 若不是事件发生过了,“记录”就不会有真假可言,“预测”也不会有对错可言。于是,在“预测为对”、“事件发生”和“记录为真”之间,存在着一种与上述时间位置图表面相似、实质却不同的逻辑关系图:
图式2 预测为对→事件发生←记录为真。(“→”“←”表示“逻辑上要求”)
现在,我们可以说,围绕未来偶然命题所产生的命定论论证的实质是: 由于把“预测”型命题混同于“记录”型命题,从而把“记录为真”与“事件发生”之间的关系混同于“预测为对”与“事件发生”之间的关系,最终从上述在各自意义上分别成立的图式1和图式2中得出了明显不成立的因果关系图:
图式3 预测为对→事件发生。(“→”表示“因果上导致”)
图式3所代表的正是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担忧的那种命定论的论证要义,即,当我们说一种偶然命题为真(假)时,不止是在逻辑上要求而是在因果上必然导致“事件(不)发生”。譬如,昨天有人猜“明天会下雨”,今天果然下雨了,根据图式3,今天之所以下雨,原因正是因为他(像神一样)猜对了,是“他猜对了”在因果上导致今天下雨的。
我们不必继续驳斥命定论作为一种学说的可信性,上述对于赖尔解答思路的概述已经让我们注意到了有关逻辑命题与自然事件的可能关系,即,一个命题(不论是“记录”型的普通命题还是“预测”型的未来偶然命题)根据二值原则或真或假,这虽然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某种自然事件发生或不发生,但此种逻辑必然性对于后者并不具有因果上的强制力,即,逻辑命题丝毫不会真正影响或干预到事件的自然进程。一个人的预测(“明天会下雨”)在逻辑上的真假对错,并不会影响到,更不会预先排定自然事件的进程,因为当我们谈到其真假对错时,相应的自然事件已经完成了*当然,对于来自不同主体的对于同一事件的预测,在相应的事件实际发生之前,我们通常还是可以区分好的预测与不好的预测。但是,“好的预测”并不意味着“预测对”,“坏的预测”也不意味着“预测错”。,不可能再受到什么影响。倒是那些真正的影响因素(如风向转变、气温升降、地震、海啸等变数),在那种预测可以被判定为真或假之前,一直都在发挥着因果上的“干预”作用。
需要同时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说在事件发生之前,未来偶然命题作为一种预测并没有真假对错可言,但作为一种预测,“明天会下雨”仍是有意义的(甚至有好坏之分),并能得到理解。不过,此种预测中所提到的“明天下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作为哲学史上所谓“偶性”(accidents)的事件,只是对于属于某种情况的某一类事件的描述。*Gilbert Ryle, Dilemmas: The Tarner Lectures 1953,pp.24-26.为便于区分,本文这里姑且把前者所谓严格意义上的事件称之为“偶性事件”,把后者经过描述而来的事件称为“事件描述”。当我们说该预测后来被验证为对时,也只是指其中所提到的“事件描述”适用于(可以谓述)今天(基于各种变数)实际发生的“偶性事件”。当我们在前文说“预测为对”在逻辑上必然要求某种所谓的“事件”发生时,此种逻辑必然性所涉及的正是“事件描述”而非真正处于自然进程中的“偶性事件”。这种“偶性事件”与“事件描述”之间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种从二值原则出发所得出的逻辑上的必然性并不会影响到自然事件的实际进程。
三、 以行动为结论的实践推理: 是否在逻辑上有效
我们在第二节中关于推理与事件的分析及其结论,主要是针对“天下雨”之类的自然事件。与纯粹偶然性自然事件不同的是人的做事或曰行动。可以说,行动并不完全是“自然的”、人们身外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人们做出来的。因此,很多人不愿意把人之行动理解为纯自然事件那样的偶然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设想,有人尽管承认逻辑上的真理无法干预自然进程的偶然性,但依然相信,至少对于足够理性的人来说,行动可以不具有类似自然进程那样的偶然性。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不乏有哲学家相信,除了那些以断言某一自然事件真假为结论的“理论推理”之外,还存在着以人之行动作为结论的“实践推理”。前者是“理论上的”,因而与我们做事没有直接关系;后者则不同,前提(意向、信念等)与结论(行动)所说的直接就是我们做事时的道理。而更能吸引人的是,当代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有人已经表明,实践推理也可以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这种关于实践推理之逻辑有效性的观点向人暗示: 只要我们能从逻辑上确保推理的有效性,我们做什么事、有什么行动,将能得到“逻辑上的”严格指引。因此,我们似乎的确不必把前一节中提到的赖尔那种观点照搬到有关我们人的行动问题上。
在当今关于实践推理之有效性的诸多论证中,具有职业逻辑学家背景的冯赖特所做的尝试引人注目。我们在本文也将以冯赖特所提供的两个基本论证(分别针对第一人称的和第三人称的实践推理)为样本来看实践推理如何可能在逻辑上有效。
冯赖特在1962年的《实践推理》一文中认为以下型式可以用来刻画第一人称实践推理。
[型式Ⅰ] 我想要获致E。
除非我做A,我将不会获致E。
因此,我将去做A。
第一前提中的E代表“我”想通过行动达到的目的。第二前提表达的是“我”所相信的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必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结论是“我”主观上的意向宣告或行动承诺,可以视作是“行动”的言语表达。我们该如何表明从逻辑上来说“我”不可能不“据此行动”呢?
可以设想,有时“我”有了意向以及相应的信念但却不是立即采取行动。而在真正采取行动之前,会有各种异常情形出现。首先,“我”虽然想要获致E,但等到弄明白只有做A才会获致E之后,很可能会修改“我”的目的,即,不再想要获致E。但是,在这种情境下,所指的那个“实践推理”根本就没有形成或已经消解,因而也就无所谓“实践推理的有效性”问题了。其次,有可能,“我”的确想要获致E并且明白只有做A才会获致E,然后试着去做A,但是“我”失败了或者说受到了某种阻碍,也就是说,“我”最终无法去做A。这种情境似乎是与“实践推理的有效性”相关的。但是,冯赖特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是看我们如何理解“去做某事”。这种说法可以是指“完成了所需要的业绩成果”,也可以是指“动身去做某事”(“尝试做某事”或“接下去做某事”)。而如果我们照后一种意思来理解,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在上述实践推理型式中,“我”是“据此而行动的”。
在考虑到上述各种可能性之后,冯赖特强调并论证: 实践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因为,假若不能由此得出行动,我们将不得不说主体他要么事实上并非想要他所声称的欲求目标,要么并不认为要获得所想要的那种东西就有必要去采取此种行动。于是,第一人称的实践推理必然导致行动或以行动而结束”。*G.H. von Wright, “Practical Inferenc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72, No.2, 1963, p.166.这等于是在说“只要该型式中的两个前提(意向与信念)同时成立,结论(行动)就必然由之得出”,而后者正是逻辑学上通常所谓的有效性(或必然性)。
在1971年出版《解释与理解》一书的第三章中,冯赖特用下述型式来刻画第三人称实践推理。
[型式Ⅱ] 从现在起,X意欲在时间t引发E。
从现在起,X考虑,除非他最迟在时间t′做A,他不能在时间t引发E。
因此,最迟在他认为时间t′到来的时候,X动身去做A,除非他忘记了那个时间或受阻了。
冯赖特相信,此种精心构建的第三人称推理型式,其结论应该是具有约束力或曰定论性的。为了表明此种约束力属于真正的逻辑效力,他希望通过考察有关实践推理之前提与结论的证实问题来做到。而考察的结果表明:“对于实践论证之结论的证实预设了: 我们能证实对应的一组前提,它们可以在逻辑上推致那个观察发现已发生的行为在结论中所给予它的描述下是意向性的。所以,我们不再可以肯定这些前提而否定结论,即,否定对于所观察行为给予的那种描述的正确性。……对于实践论证之前提的证实同样也预设了: 我们能挑选出某一项得到见证的行为,认为它在通过那些前提本身(‘直接’证实)或其他某组可以推致当下论证之前提的前提(‘外部’证实)所赋予的描述之下是意向性的。”*G.H. von Wrigh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pp.115-116.在冯赖特看来,实践推理中前提证实与结论证实之间的此种相互依存,足以表明型式Ⅱ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约束力是逻辑上的。
于是,型式Ⅱ所表示的第三人称实践推理与型式Ⅰ所表示的第一人称实践推理都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毫无疑问,此种来自职业逻辑学家的论证结论,对于某些相信人事也可以像物理事件那样严格设计的人群来说,充满了诱惑。它似乎可以表明: 一个在特定情境下满足“前提”条件的人,一定会有某个行动;否则就是有违逻辑的、不理性的。
四、 实践推理有效性能决定我们做事吗
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有效性的论证尽管让某些人感到了兴奋,但他本人并没有停留在那样的结论上。事实上,我们看到,他在论证并主张实践推理之有效性的同时又试图加上一系列“理解上”的限制。
譬如,在1971年根据前提证实与结论证实的相互依存性对于型式Ⅱ的逻辑效力作出论证后,他立即指出: 在谈到前提或结论的证实程序时,它们都预设了某一事实行为的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确保这里所设定的“事实行为”一定存在。为此,他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其大意是: 某一主体意欲引发某事(譬如射杀暴君)并考虑到为此目的有必要做另外某事(譬如开枪)。他也认为是时候该行动了。他站在这位凶残的人面前,用装有子弹的手枪瞄准他。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可以说,他真实来讲什么也没做。对照型式Ⅱ,我们可以弄清楚: 第一前提和第二前提仍旧维持为真,他并没有因为“瘫痪”等原因而受阻,也没有忘记时间,然而,就是没有出现“开枪”这一行为,他压根儿就没开始做。*G.H. von Wrigh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pp.116-117.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冯赖特认为,我们确实可以设想这一类“前提真而结论却没发生”的情况。于是,我们听到他开始谨慎地表示:“实践推理的前提并非逻辑必然地推致行为。……只有在行动已经出现而且构建了实践推理去解释它或为其辩护时,我们才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定论。我们可以说,实践推理型式的必然性是事实出现之后所认识到的必然性(a necessity conceivedexpostactu)。”*G.H. von Wrigh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p.117.
同样地,对于第一人称实践推理之有效性这一结论的理解,冯赖特后来在1972年《论所谓的实践推理》一文中也做了严格限制。
冯赖特发现,型式Ⅰ的结论是对一种意向的宣告,而第一前提中也有一种意向,可以说,第一前提中的意向借助于第二前提的中介作用传递到了结论中所宣告的意向,或者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获致目的的“意志”传递到被认为对于获致目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上。就此而言,“我们这个第一人称论证的结论是从前提之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G.H. von Wright, “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 Acta Sociologica, Vol.15, No.1, 1972, p.45.,即,型式Ⅰ属于明显的逻辑有效式。但是,他随后紧接着指出,那种逻辑上必然的联系(“合乎逻辑地得出”)并非寻常的那种逻辑必然性,因为型式Ⅰ的结论作为“意向宣告”很可能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命题(即有真假可言)。于是,我们看到他说:“是否从我们所考察的那种前提出发建构起来的论证将以一种意向宣告而结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并非逻辑上必然的。”*G.H. von Wright, “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 p.45.着重字体为引者所加。他还解释道: 不难发现,从上述前提出发所作的论证经常是以意向改变而结束的,因为“我”可能在意识到有必要做什么之后却很不愿意去做,因而放弃对于原来意向的追求。即便是“我”不改变原来的意向,“我”也不一定会(对他人或自己)宣告结论中所谓的意向。不管怎样,原来在型式Ⅰ中“合乎逻辑得出的”结论,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并不会自动出现。*G.H. von Wright, “On So-Called Practical Inference”, p.45.
必须承认,冯赖特对于实践推理之逻辑效力所作的上述“解读限制”是令人迷惑的,我们甚至能感觉到他在下结论时的犹豫不决: 时而说实践推理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时而又说我们无法保证结论中的行动最后果真能出现。但是,笔者相信,冯赖特的总结在设法消除语言措辞上的矛盾(譬如前面说是“逻辑必然性”后面却说“不是逻辑上必然的”)后应该是成立的。对于其所作总结的解读,关键是弄清他所提出的“事实出现之后所认识到的必然性”这种说法。这是他对于所主张的实践推理之逻辑有效性的“设法限定”。它意味着在型式Ⅱ(也包括型式Ⅰ)之结论中提到的“行动A”应该是“已经出现的事实”,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说该实践推理型式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这里的“事实出现之后”让我们回想起本文第二节谈到未来偶然命题作为一种预测时曾说过: 每当我们说“预测为对”时,总是意味着事件已经发生过并据此才判定“预测”为对。实际上,赖尔针对未来偶然命题所提出的分析思路,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澄清冯赖特结论中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既然实践推理型式结论中所提到的行动A是像“今天下过雨”或“这匹马赢了”那样的已经完成了的行动,那么,以行动A为结论的实践推理,实质上是在解释一个已经出现(成真)的行动事实,因而它的有效性并不会影响更不会代替主体决定他当时的行动。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偶性事件”与“事件描述”之间的区分类推于行动问题上,那么,我们不难意识到,实践推理结论中提到的“行动A”并非等于“某一主体凭借自由意志所做的任何行动”(姑且称为“意志行动”),而是“对于具有某些特征的某一类行动的描述”(姑且称为“行动描述”)。当冯赖特断言某某实践推理型式为有效式或具有逻辑必然性时,其中的“行动A”并不是那个有待发生的、可以严格被命名的、“活着”的“意志行动”,而只是从自然进程中抽离出去的、“已死去”的“行动描述”;另一方面,当他说我们无法保证从所建构论证之前提一定得到作为结论之行动(因而具有偶然性)时,其实,他所谓的“行动”已离开“实践推理”型式而“重新回到”自然进程当中,又变成了“意志行动”。
经过如此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冯赖特关于实践推理有效性的断定和论证是可以成立的,但此种有效性并不会(代替我们)决定我们在实际中一定会如何做事。冯赖特在做总结时的犹豫不决或言语矛盾,应该主要是因为他担忧并希望读者不要在理解实践推理的有效性时将它引向某种否定自由意志的决定论哲学。他的这种担忧值得同情,因为尽管当今不再有神学意义上的命定论,但各种形式的甚至带有科学色彩的决定论依然泛滥。但是,他为消除误解所提供的言语措辞是糟糕的。我们都知道,推理应该是由句子组成的,即便是实践推理中作为结论的行动,也只能是言语表达之后的“行动描述”。因此,他不该把仅仅用于句子关系层面的逻辑有效性(必然性)概念不加区分地用于“意志行动”。如果他想要表达某某主体的“意志行动”不具有什么必然性的话,那也只能说“它在实践上并非不可避免”,而不能说“它不具有逻辑必然性”。
五、 结语
本文从自然事件谈到人的行动,旨在表明: 即便有真正的并且逻辑上有效的实践推理,此种逻辑有效性也无法决定我们实际上做事的样子。然而,这种观点,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阻挡某人说他在做事时尽量少带一些甚或不带有偶然性。因为他在那样说时,只不过是想告诉我们: 他做事是有理由的,或者说有充分的理由的,正如一种对于某类自然事件的“好”预测或曰“科学预言”总要提供理由或者充足理由一样。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指出: 我们在说科学预言有充足理由时,绝不是说此种预测就能提前排定自然事件的进程;同样地,当某人在如实说行动有充足理由时,也绝不会是指他做某某事是由某种有效推理先行“注定了的”。
另外,我们也大可以说逻辑上有效的实践推理能够“指导”我们做事。不过,此种“指导”,顶多只是我们行动时的一种参考。事实上,当安斯康姆说“在实践推理中前提与结论(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前提表明了行动有何好处、有何用处”*G.E.M. Anscombe, Human Life, Act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Mary Geach and Luke Gormally,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05, p.144.时,她所要表达的正是有关实践推理之逻辑有效性的此种参考价值。而既然只是参考,那就不是对我们带有自由意志的行动的“决定”。
最后要指出的是: 人们很多时候不想说“思想替代不了行动”这样贫瘠乏味的老套话,而更愿意去说“思想改变行动”这样动人心扉的格言。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并不是思想本身在改变行动,而是掌握了思想的人自己凭着自由意志在“做出”行动,并能认同本文所讲的“逻辑必然性(不论是理论推理上的还是实践推理上的)无法决定包括人在内的大自然进程”,那么,“思想替代不了行动”这句话至少在哲学上将不再是无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