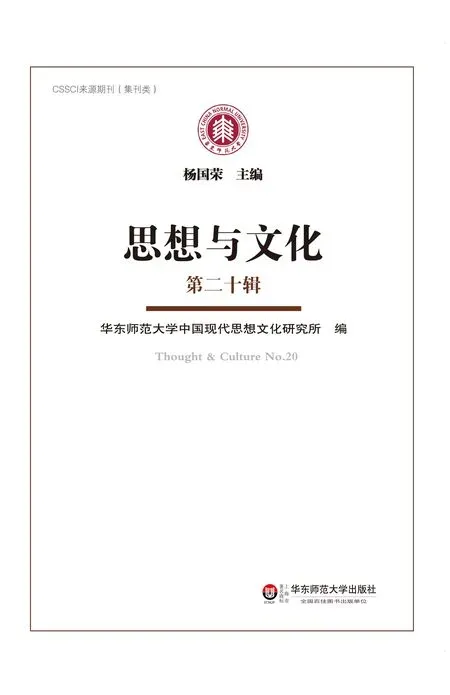叶芝诗歌中的宗教观*
●
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于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评语是“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一整个民族的精神”。*叶芝著,傅浩编译:“编选者序”,《叶芝精选集》,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1页。比他稍晚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称其为“二十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语出艾略特于叶芝逝世次年在艾贝剧院发表的一次演讲,是为艾贝剧院为纪念叶芝而设置的系列讲座中的第一讲,艾略特的演讲辞后来发表于《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1942年第3期。艾略特这句溢美之词的原文是: the greatest poet of our time — certainly the greatest in this language(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当然我指的是英语世界)。参见James Hall & Martin Steinmann (ed.), The Permanence of Yea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0, p.331.,诗人庞德则称其为他们那个时代最值得研究的诗人。*叶芝著,傅浩译: 《歌者立于天地》,《叶芝诗集》(上),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鉴于爱尔兰多年遭受英国殖民的历史,叶芝获奖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自公元12世纪起,爱尔兰就陆续遭到英国侵略和殖民。虽然爱尔兰在1800年正式并入英国,但至1922年爱尔兰成为自由邦时,其已遭受近七百年的殖民统治。叶芝于爱尔兰成为自由邦的次年(192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击败当时声誉正隆的英国大作家哈代(Thomas Hardy)。当时有报道认为是爱尔兰成为自由邦的事实使叶芝登上文学殿堂的巅峰,言下之意是,瑞典皇家学院看中的是叶芝代表的弱小民族独立的背景。事过境迁,从今日角度考察,叶芝本身的艺术成就并不亚于哈代,叶芝获奖应该是实至名归。但就是这么一位被认为创造了一种新的民族文学“爱尔兰英语文学”*语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佩尔·哈尔斯绰姆对叶芝的颁奖词,参见柯彦玢译: 《颁奖词》,《叶芝诗集》(下),第859页。哈尔斯绰姆的原词是Irish-English Literature,后来此种说法演变为“英爱文学”(Anglo-Irish Literature),即指爱尔兰作家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以区别于爱尔兰作家用盖尔语创作的文学。的大诗人,其诗歌中的宗教观念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或视为当然。
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叶芝诗歌研究主要经历了一个从以形式诗学分析为主到以文化诗学分析为主的过程。*本文采用圣经文学和欧美文学研究专家王立新教授的观点,认为“形式诗学”(form poetics)指的是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等为代表,侧重文本(text)分析的批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指的是各种着重对文本产生的历史、文化等语境(context)进行分析的批评。经典研究应该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即一种有机整体观。参见王立新: 《古典时代与东方文学研究中的古典学质量与方法——以古典希伯来文学研究为例》,《东方丛刊》2010年第1期,第28页。最早研究叶芝作品的威尔逊和奥登从象征主义手法和诗歌叙写技巧等方面剖析叶芝诗歌*See Edmund Wilson, Axel’s Castle: A Study in the Imaginative Literature of 1870—1931, New York: Charles Scriber’s Sons, 1931; David Holdem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 Yeat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8, p.118.,之后的新批评大家如布鲁克斯等更是直接以新批评常用的术语“肌质”(texture)等来分析叶芝诗歌。*Cleanth Brooks, The Well Wrought Urn: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etry, New York: Mariner Books, 1956.叶芝诗歌形式批评的集大成之作是《叶芝之永恒》(ThePermanenceofYeats),此书几乎囊括了20世纪40、50年代所有新批评大家的叶芝诗歌分析。*此书收入的大家有早期的威尔逊和布莱克莫,新批评大家布鲁克斯、兰瑟姆(J.C. Ransom)、退特(Allan Tate)、沃伦(Austin Warren)等,以及诗人及批评家艾略特、奥登、利维斯(F.R. Leavis)等。在这一时期,逐渐涌现出两位卓有影响的叶芝研究专家: 埃尔曼和杰法瑞斯。两人不仅专事叶芝作品研究(尤其是诗歌),也结合诗人生平进行传记式研究。*埃尔曼(R. Ellmann)以研究叶芝成名,之后转向乔伊斯和王尔德研究,他通过叶芝太太获得珍贵的未发表资料,写出叶芝研究大作《叶芝: 人与面具》,参见Richard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49; Richard Ellmann, The Identity of Yea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杰法瑞斯(A. Norman Jeffares)更是叶芝诗歌逐一注释的始作俑者,他于1968年出版《叶芝诗歌评论》,即A Commentary 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同年杰法瑞斯出版《评论》的新编本,即A New Commentary o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68。杰氏结合叶芝传记研究的著作有 W.B. Yeats: Man and Poet, 3rd edi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W.B. Yeats: A New Biography,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1。杰氏还是叶芝诗歌作品编纂大家,其所编叶芝诗歌全集或选集均成为叶芝研究的权威版本。与埃尔曼、杰法瑞斯同时期有影响的叶芝诗歌研究著作还有亨尼(T.R. Henn)《孤独的塔堡》和阿特里克《叶芝导读》(J. Unterecker),参见T.R. Henn, The Lonely Tower: Studies in the Poetry of W. B Yeat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0; John Unterecker, 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5.20世纪70年代叶芝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布鲁姆,他在专著《叶芝》(Yeats)中以详尽的分析阐述叶芝所受先贤如雪莱、布莱克等的影响,可谓是其“影响的焦虑”文学批评观点的典范文本。*Harold Bloom, Ye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之后的叶芝诗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其作品生成的背景、诗学思想等,即从形式诗学转向文化诗学。斯托克研究叶芝诗歌与诗人思想*Amy Geraldine Stock, W.B. Yeats: His Poetry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郝伟思探讨叶芝的民族、性别和阶级观念*Marjorie Howes, Yeats’s Nations: Gender, Class, and Irish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贝尔则试图厘清叶芝作品中的形式逻辑思维。*Vereen M. Bell, Yeats and the Logic of Formalism,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6.上世纪80年代一本研究叶芝与法西斯之间关系的专著引起学界注意*这部著作即Elizabeth Cullingford, Yeats, Ireland and Fasc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最近又有两部著作重提叶芝与暴力以及叶芝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分别是Michael Wood, Yeats and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W.J. McCormack, Blood Kindred: The Politics of W.B. Yeats and His Death, London: Random House, 2005。学界一般认为,虽然叶芝晚年支持过爱尔兰的“蓝衫运动”(Blue Shirts),还为之写过三首进行曲,但并不能认为叶芝支持极端民族主义。拉里斯(Edward Larrissy)认为卡琳伍德的说法过于一厢情愿以致出错(so one-sided as to be fallacious),认为麦克科马克则过于依赖叶芝朋友和熟人的说法,从而简单地将叶芝当成纳粹的同情者,参见Edward Larrissy, “Yeats in Light of Recent Criticism”, in Edward Larrissy ed., W.B. Yeats: Irish Writers in Their Time,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10, p.12.,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将叶芝崇尚力量和威权与法西斯强行拉扯在一起是有欠公允的。自上世纪中叶至今,关于叶芝的传记时有佳作出现,皇皇巨著则非福斯特的两卷本《叶芝传》莫属。*除埃尔曼和杰法瑞斯的著作外,有名的叶芝传记还有Douglas Archibald, Yeat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erence Brown, The Life of W.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Hoboken: Wiley Blackwell, 1999. 福斯特(R.F. Foster)的两部巨著分别于1997和2003年出版,即R.F. Foster, Yeats: A Life, Volume I: The Apprentice Mage, 1865-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F. Foster, Yeats: A Life, Volume II: The Arch-Poet, 1915-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最近二十年的叶芝研究除继续延续文化诗学的维度外,也有一股形式诗学的回潮。*例如M. L. Rosenthal, Running to Paradise: Yeats’s Poetic A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len Vendler, Our Secret Discipline: Yeats and Lyric 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比较国外而言,国内的叶芝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弱,且研究多集中在叶芝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国内叶芝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傅浩。他不仅翻译了叶芝全部的抒情诗,并且二十余年来不断修改,还撰写了叶芝研究专著《叶芝评传》(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他另有叶芝研究专论,如《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外国文学》2008年第6期。其他内地叶芝研究著作有: 蒲度戎: 《生命树上凤凰巢—叶芝诗歌象征美学研究》,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静: 《叶芝诗歌: 灵魂之舞》,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王珏: 《叶芝中期抒情诗中的戏剧化叙事策略》,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周芳: 《“清浊本为邻”: 对叶芝诗歌中衰老与灵肉主题的探讨》,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港台地区研究叶芝的专著有: 吴潜诚: 《航向爱尔兰: 叶芝与塞尔特想象》,台北: 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综括国内外研究,对叶芝的作品文本、文本生成的历史和文化进路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唯独较少对叶芝宗教观念的研究。*就笔者搜索所及,集中讨论叶芝诗歌中的宗教观的专著或专论尚阙如。傅浩《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是研究叶芝宗教观念的上佳之作,作者聚焦于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场景、典故、引用等,认为叶芝将基督教与其他信仰等量齐观、一视同仁,当作自己的神话素材。*傅浩: 《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第14页。此文用较大篇幅探讨了叶芝诗歌中的基督教元素,以介绍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场景、典故、引用等情况为主。普迪《叶芝诗歌圣经引用与典故》一书条分缕析罗列了叶芝在诗歌中引用的圣经故事、典故等,但对叶芝作品中的宗教观以及形成原因的探讨阙如。*Dwight Hilliard Purdy, Biblical Echo and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Poetics and the Art of God, London and Toronto: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4.其他关于叶芝宗教观的研究散见于篇章段落,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例如《语境中的叶芝》(W.B.Yeats in Context),此书之第五部分“哲学”之第二十一章“爱尔兰宗教: 新教与天主教”专章分析19世纪末的爱尔兰宗教背景,但只提供背景,不联系叶芝作品分析。参见Nicholas Allen, “The Church in Ireland: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in David Holdeman & Ben Levitas eds., W.B. Yeats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27-236. 艾伦(N. Allen)认为叶芝的宗教特点是富于争辩而不是认同(controversy, not confirmation, was the expression of Yeats’s religious belief),见David Holdeman & Ben Levitas eds., W. B. Yeats in Context, p.228.分析此中缘由,笔者认为,或许是叶芝的诗艺太过突出而遮掩了他的其他身份,也可能是叶芝的宗教观太过寻常(例如与T.S.艾略特相比)而乏人问津。但不容否认的是,叶芝作品中(尤其是诗歌中)对圣经场景、典故、故事的引用比比皆是*据普迪统计,在叶芝的374首抒情诗(据现今权威的费纳然本[Finneran edition])中,有115首与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Bible)有关,共使用265个圣经典故。参见Dwight Hilliard Purdy, Biblical Echo and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Poetics and the Art of God, p.24.,这必然是一种创作心理的反映,而这种创作心理源于叶芝本人的宗教观念。
叶芝祖上是移民爱尔兰的英格兰新教徒,一直隶属爱尔兰国教且为其服务,其外祖家亦是世代殷富的新教商族。受父亲与时代影响,叶芝本人并不是虔诚的新教徒。在近代爱尔兰,新教阶层是统治势力,但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大众是天主教徒,因此诗人不可避免受宗教影响,于作品中表达宗教观点也就势所必然。透过对叶芝不同时期代表性诗作的分析,结合诗人生平与时代背景的探究,笔者认为,叶芝诗歌反映出诗人早期认同爱尔兰国教、揶揄反对天主教,中期一度主张众教平等,后期又回归早期态度。叶芝对于宗教以及政治现实的文化态度,通过他的诗歌得以映现,也就是在这种诗的文化叙事过程之中,叶芝建构起了其基于爱尔兰国教倾向的“新教优势阶层”归属感。
一、 叶芝早期诗歌中的宗教观
叶芝于1865年出生于都柏林,其先祖为移民爱尔兰的英国新教徒,且自其祖父上推一直担任神职。叶芝父亲约翰受时代思潮影响,喜读自由思想家穆勒和进化论学者达尔文、赫胥黎等的著作,对宗教持怀疑主义态度。约翰年轻时先是放弃教职、专攻法律,后来又弃法从艺,矢志以绘画为业。约翰的这些做法无疑影响到对孩子的教育,叶芝后来就承认自己“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的信仰(基督教)”被赫胥黎等人剥夺了。*William Butler Yeats, Autobiographies,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1, p.115.但爱尔兰毕竟是宗教国家,自己的家族又曾以教职为业,约翰还是按照正常的程序给儿子以宗教教育。叶芝本人在国教受洗,所用的圣水可能是其外祖从约旦河取回来的,一直放在橱柜里。童年叶芝也阅读《传道书》(Ecclesiastes)和《启示录》(Apocalypse)等。*David Holdeman & Ben Levitas eds., W.B. Yeats in Context, p.227.叶芝十五岁时还被施以坚信礼。*John Kelly, A W.B. Yeats Chronolo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5.因此叶芝对爱尔兰国教和圣经是相当熟悉的。
《湖岛因尼斯弗里》是叶芝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以细腻抒情的笔法描写了诗人小时候经常去度假的外祖家所在地斯莱戈的风光。诗歌首句“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前去因尼斯弗里”(I will arise and go now, and go to Innisfree)就模仿《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第二十一节“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I will arise and go, will gather all Israel unto my lord the king)以及《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I will arise and go to my father)的句式。第二段首句“我将享有些宁静(亦可译作“平安”)”(And I shall have some peace there)模仿的是《旧约·申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九节“却还是平安”(I shall have peace)的句式。第三段首句除“现在我要起身离去”外,“因为在每夜每日”(for always night and day)套袭《新约·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节“他昼夜常在”(and always, night and day)的句式。*本文所引叶芝诗歌译文(除没有汉译的诗作如《乌辛漫游记》为笔者自译之外)均出自叶芝著,傅浩译: 《叶芝诗集》,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所引原文均出自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以下引用这两部书时仅注出书名,而不注著译者及其他版本信息。所引圣经汉语译文均出自《圣经》,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所引圣经英语原文均出自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University Place: RCK Cyber Services。此处参考傅浩《叶芝作品中的基督教元素》,以及Dwight Hilliard Purdy, Biblical Echo and Allusion in the Poetry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Poetics and the Art of God.虽然后来叶芝认为自己在诗中模仿圣经句法显得技巧不够成熟,但足以看出诗人对圣经的熟悉。
《乌辛漫游记》被认为是叶芝的成名作,也是其早期代表诗作之一,这首诗明显地表露了诗人的国教认同观点。此诗是以对话体写成的叙事诗,对话的一方是爱尔兰古代神话中的英雄乌辛(Oisin),另一方是将罗马天主教带入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诗歌主要以乌辛的叙述串联故事情节,乌辛讲述自己被神话国度里的仙女妮阿芙(Niamh)引诱,进到神仙之国,历经三个地方,分别是“舞乐之岛”、“忧惧之岛”和“遗忘之岛”,乌辛在这三个仙境分别度过一百年。终于,乌辛回想起与芬尼亚勇士们*古代爱尔兰文学最重要的成就是神话和传说,主要由三个神话系统组成,分别是达努神族与深海巨人族的斗争神话系列(Tuatha Dé Danann against Fomorii)、以库胡林事迹为主的厄尔斯特传说系列(Cuchulainn and other Ulster heroes)以及芬恩与费奥纳英雄们的传奇故事系列(Fionn mac Cumhaill and Fianna,即芬尼亚勇士传说,后来19世纪兴起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一支就以芬尼亚为组织旗号)。这些系列自成系统,但有时内容也相互交叉。英勇战斗的时光,决定回乡一探。回到人间的乌辛匆忙间忘记妮阿芙的叮嘱,在无意间双脚落地,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已经三百岁的老翁。在诗歌最后,乌辛不顾圣帕特里克的劝阻,执意去找曾经的勇士战友,无论他们是在地狱遭焚,还是在天堂飨宴。
对于这首诗的分析,不少研究着眼于民族历史和集体记忆,或是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例如丁秉伟: 《记忆恢复与历史重建: 浅析“乌辛漫游记”》,《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第133—134页;杨秋娟: 《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读叶芝的“乌辛漫游记及其他”》,《飞天》2010年第24期,第49—50页。其实这首诗还可以视作叶芝宗教观的一个展示。从全诗的结构来看,这是一场极不均衡的不同文化价值立场之间的对话。在九百行的诗中,圣帕特里克的言说只占二十四行,而且有时候在乌辛充满激情的叙述之后,圣帕特里克只回应简单的一两个词如“继续”(tell on)。俄国文论家巴赫金认为,文本中不同的人物代表不同的“思想”或文化价值,不同的人物不是可以随意摆布的奴隶,而是几乎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人;文本中人物的议论与作者本人的议论一样,有自己的分量和价值;因此一个文本并不是只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和“思想”,而是有着众多各自独立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复调。*巴赫金著,白春仁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在这首诗中,显然乌辛代表的是民族或地方的文化价值(代指爱尔兰),圣帕特里克代表的是基督教文化价值(天主教文化价值,在殖民语境下即代指英国)。显然这是一次失效的价值之间的对话,乌辛不仅没有被规约,还在诗歌最后向圣帕特里克发出挑战。诗人对圣帕特里克为代表的天主教持一种揶揄甚至讽刺的态度。联系到叶芝祖辈的国教背景,诗人对天主教的揶揄态度使得诗人的新教趋同观念更为突出。
在《乌辛漫游记》中,叶芝较多的是对以圣帕特里克为代表的天主教的揶揄,而在其他诗歌中对为数众多的天主教徒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最主要的体现是有关帕内尔和“《西部浪子》事件”的几首诗。帕内尔是19世纪后半叶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袖,其出身是一名新教地主。在他的努力下,爱尔兰朝着自治的方向迈进。1890年,帕内尔与欧谢夫人多年同居的丑闻曝光。即使欧谢夫人与丈夫已经分居多年,众多天主教徒支持者仍然认为不可原谅。*帕内尔与欧谢夫人同居的事实其实已经不是秘密,欧谢本人也早已安之若素,只是为了谋夺妻子可能继承的一笔财产而拒绝离婚。但即使欧谢夫人离婚,她与帕内尔结婚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爱尔兰天主教是禁止婚后再婚的。帕内尔被赶下权力舞台,不久即去世。针对这一事件,叶芝在诗中称那些指责帕内尔的天主教徒为“狂热的一群”(a frenzied crowd),他们的行为是“流行的狂热”(popular rage)和“歇斯底里症”(hysterica passio)。叶芝感叹,假如当时人们宽容帕内尔,按照帕内尔的路线前进,那么就“没有国民间的仇恨把国土撕裂劈分”*参见《帕内尔的葬礼》(Parnell’s Funeral)一诗,《叶芝诗集》(下),第679—682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279-280. 19世纪末,以新教为主的北方几郡有保留合并的愿望,其他各郡以天主教为主,则主张独立。帕内尔去世后,爱尔兰国内的独立派和自治派势力此消彼长,但人心逐渐趋于自治,英国政府也同意作出一定让步。经过各方努力,1914年英国和爱尔兰签订条约,英国议会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但由于一战爆发,爱尔兰自治被推延。1916年都柏林发生复活节起义,英国军队和政府的镇压政策导致人心转向,大部分爱尔兰人主张独立,但北爱尔兰依然主张合并在英国之内。一战结束后,爱尔兰爆发独立战争,1922年又发生内战。同年内战结束,《英爱条约》签订,爱尔兰成为自由邦,但北部新教为主的六郡依然保留在联合王国之内。南北分裂延续至今。(指爱尔兰南北分裂)。显然叶芝极为同情同为国教徒的帕内尔,把他与爱尔兰的前途等同齐观,因此对天主教义和天主教徒自然不满了。
“《西部浪子》事件”更加明显地表明叶芝对天主教徒的批评态度。1907年1月26日,叶芝好友辛格的风俗喜剧《西部浪子》(ThePlayboyoftheWesternWorld)在艾贝剧院上演,引起群众骚动,原因是剧中对西部岛民生活的逼真描绘使保守的天主教徒难以接受,直接的导火索则是辛格在剧中使用了“(女用)汗衫”(shift)一词。观众(以天主教徒为主)认为此词伤风败俗,甚至有人骂辛格为“老混蛋”。*此话出自一位艾贝剧院的女清洁工之口,原文为“Isn’t Mr. Synge a bloody old snot to write such a play?”,引自Frank Tuohy, Yeat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London Ltd, 1976, p.130.其实是剧中逼真的人物和风俗描写刺痛了天主教群体。当时叶芝正在苏格兰演讲,好友格雷戈里夫人给他写电报说观众听到“汗衫”这个词就炸开了锅。以格里菲斯为首的民族主义者更是推波助澜,称该剧“是道德堕落的产物,在全欧洲面前侮辱了爱尔兰妇女”。*傅浩: 《叶芝评传》,第112页。叶芝赶紧从苏格兰转回都柏林,并亲自登台为辛格辩护。叶芝坚持个人言论自由,指责群众不懂艺术,认为艺术与政治应当保持一定距离。在《论那些仇视〈西部浪子〉(1907)的人》一诗中,叶芝将那些群众称为“地狱中的阉人”(eunuchs ran through Hell),却要在每一条拥挤的街道上凝视“骑马经过的伟大的唐·璜”,他们又是咒骂,又在淌汗,却一边盯着唐·璜“肌肉发达的大腿看”(staring upon his sinewy thigh)。*《叶芝诗集》(中),第295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111.显然“阉人”是没有性能力的(impotence),暗指盲目的群众没有艺术鉴赏力,却一边指责辛格伤风败俗(“咒骂”),一边羡慕对方强大的性力(sexuality,“肌肉发达的大腿”)。叶芝更是指责格里菲斯等人将政治与文艺划等号,他们对辛格天赋的嫉妒反映出自身文艺创作的无能和无力。*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B. Yeats, p.120.在这一事件中,叶芝对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戏剧观众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诗中用词激烈。在《致一位富人》中,诗人直接称呼他们为“白丁”和“鄙弟”,语气接近谩骂,可见其批判态度之深。*《叶芝诗集》(中),第246页。白丁即Paudeen,鄙弟即Biddy,是对爱尔兰普通天主教百姓的谑称,但在叶芝这里,显然是蔑称。在《1913年9月》中,叶芝嘲笑新兴的天主教中产阶级,说他们生来只知攒钱,一辈子在“油腻的钱柜里摸索”。*《叶芝诗集》(中),第250页。此外,叶芝还专门写过一首名为《白丁》的诗,称那些与其意见相左的普罗大众有“愚笨的头脑”,是一些只知在店铺里赚钱的“老白丁”。*《叶芝诗集》(中),第255页。一方面,叶芝对天主教揶揄,对天主教徒批评;另一方面,诗人倾向新教,对出身新教的友人不吝溢美之词,主要表现在“库勒庄园”组诗、休·雷恩组诗和帕内尔组诗等诗中。
在某种意义上,“库勒庄园”成为叶芝理想中的贵族文化诞生地,而这种贵族文化必然是新教贵族文化,叶芝对这种文化是高度赞颂和认同的。在《在那七片树林里》,诗人描写庄园的七片树林里野鸽群群,发出隐隐雷声,花园里蜜蜂低吟,这些能使心忘却徒劳和苦痛。*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77.《库勒的野天鹅》里的野天鹅在诗人眼中是“漂亮的生灵”(brilliant creatures),它们浮在平静的水面,神秘而美丽。它们的心“尚未衰老”,无论它们漫游到何处,却“依然带有热情和征服”。*《叶芝诗集》(中),第305—306页。虽然离诗人初次造访已十九个春秋,这五十九只天鹅依然未变(新旧交替)。优雅、神秘、富有激情的野天鹅象征的是艺术的永恒*Sandra Gilbert, The Poetry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New York: Monarch Press, 1965, p.46.,而这片庄园的主人格雷戈里夫人就是优雅的新教贵族文化的代表。在《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中诗人安慰这位朋友(即格雷戈里夫人),称她“出身高贵”(being honour bred),何必与“白丁”类人物(any brazen throat)竞争,夫人为之奋斗的艺术事业是世间万事中“最困难的一件”。*《叶芝诗集》(中),第253—254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109。“库勒庄园”里还有一位高贵的骑手(指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子罗伯特·格雷戈里),他参加赛马不用缰绳,骑马时在危险的地方一跃而过,使得参加围猎的同伴“惊恐得闭起了眼睛”,然而他的心思“比马蹄更敏捷”。*《叶芝诗集》(中),第312—313页。他集军人、学者、骑手于一身,是贵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当然这种贵族文化是新教贵族文化。
休·雷恩爵士是出身新教的另一位贵族,以慷慨捐助艺术著称,但其义举往往为天主教徒为主的百姓所阻。在《致一位富人》中,叶芝称他为精英,“熟知生活乐趣”,给出的是“令狂喜的心叫好称善的东西”(为艺术馆捐赠名画)。*《叶芝诗集》(中),第248—249页。在《聘任》一诗中,诗人赞扬雷恩爵士“那强悍的牙齿和清洁的肢体”。*《叶芝诗集》(中),第295页。如上所述,帕内尔是出身新教地主的民族自治运动领袖,叶芝对其充满敬仰。在《致一个幽魂》中,诗人称赞他“热心为公”,双手捧出的东西是为了“给予子孙更为美好的感情和更为高尚的思想”。作为对帕内尔赞美的对照,诗人痛斥那些固守天主教教义的群众,称呼帕内尔的对手有“一张老臭嘴,唆使群狗去撕咬他”,以致帕内尔的辛苦“换来了成堆的污蔑”,他的慷慨“换来了成堆的羞耻”。*《叶芝诗集》(中),第257页。在《帕内尔派,来聚集在我周围》中,诗人称赞帕内尔“与英格兰的强权战斗,拯救了爱尔兰的穷人”,他是一个有资格骄傲的人,是一个骄傲且可爱的人(骄傲指其为爱尔兰所做的贡献,可爱指其与欧谢夫人的爱情)。*《叶芝诗集》(下),第754—755页。
由上可知,叶芝在早期诗歌中对天主教和天主教徒持讽刺和批判的态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新教(具体而言即爱尔兰国教)。但在中期诗歌中,其宗教观一度发生转变,由有所偏向转向平等对待。
二、 叶芝中期诗歌中的“众教平等”观念
叶芝早期批判天主教、倾向新教的总体态度一直延续到他写作第四部诗集《绿盔及其他》的时段*叶芝在创作生涯后期经常对自己早期的诗作进行修改,因此其诗作版本各异,现根据国际学界通行的做法(即费纳然编纂的叶芝诗集版本),将叶芝诗集逐一排列,分别是《十字路口》(Crossways, 1889)、《玫瑰》(The Rose, 1893)、《苇间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1899)、《在那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 1904)、《绿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 1910)、《责任》(Responsibilities, 1914)、《库勒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 1919)、《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 1921)、《塔堡》(The Tower, 1928)、《旋梯及其他》(The Winding Stair and Other Poems, 1933)、《帕内尔的葬礼及其他》(Parnell’s Funeral and Other Poems, 1935)、《新诗》(New Poems, 1938)、《最后的诗》(The Last Poems, 1938-1939)。,但这种态度在写作《责任》中的诗作时已经有了初步转变,即诗人一度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白丁》一诗中叶芝的这种主张宗教平等的观念已经初露端倪。虽然诗人指责那些不懂艺术欣赏的大众,但在诗歌结尾,诗人写他自己突然间想到,“一切都在上帝眼中”(all are in God’s eye),即使有嘈杂的声音,但总会有一个“水晶般美妙叫声的魂灵”。*《叶芝诗集》(中),第255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p.109-110。《三个乞丐》、《乞丐对着乞丐喊》、《奔向乐园》、《黎明前的时刻》被称为“乞丐组诗”,这组诗明显地体现了诗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三个乞丐》第一段写一只老鸬鹚伫立在水中,只有垃圾飘到它那里,老鸬鹚便瞧不起水里的小鱼。诗歌中间部分借国王和三个乞丐的故事隐喻和讽刺凡人的痴心妄想。在诗歌结尾,老鸬鹚终于明白,不管是国王还是乞丐,他们都是一样的,就像那河水,即使飘满垃圾,说不定某个地方会有鳟鱼出现。*《叶芝诗集》(中),第260—263页。《乞丐对着乞丐喊》中的乞丐一开始想象自己假如运气好,就能有好房子、娶漂亮女孩、当富翁,但他最终发现好房子也会有魔鬼、漂亮女孩不必太漂亮、富人会受财产所累。在诗歌最后,乞丐感慨,只有在“那里”、在“花园”里(伊甸园,或天堂)一切才会变得休闲、人们互相尊敬。*《叶芝诗集》(中),第266—267页。在《奔向乐园》里,诗人在每一段的第三行反复声称:“我”正奔向乐园(paradise,即天堂),因为那里国王不过跟乞丐一样,穷人和富人一样。*《叶芝诗集》(中),第269页。《黎明前的时刻》写无论是无赖、独腿人、梅娃女王的九个儿子,还是乞丐,其骨和肉都会消失,灵魂也会像叹息一样消亡,而“惟有上帝存留”。*《叶芝诗集》(中),第276页。
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外,叶芝在这一时期宗教态度上的改变还表现在对天主教态度的改变,即从批判到包容,甚至是赞美。1916年的复活节,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为基础组建的志愿军在都柏林发动起义,一个星期后起义被镇压,十五位起义领袖被枪决。大部分志愿军成员为天主教徒,包括起义领袖。原来一直支持自治的叶芝(参看他写帕内尔的诗)被起义震动,转而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武力,对起义领袖不吝溢美之词。在《1916年复活节》中,叶芝颂扬起义领袖皮尔斯兴办教育,而且诗思飞扬;麦克多纳天性敏锐,思想大胆而清新。叶芝对待天主教态度上最大的转变体现在对麦克布莱德的描写上。麦氏是一位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叶芝年轻时便开始追求的对象毛德·冈后来嫁的就是他。更令叶芝气愤的是,毛德·冈为了嫁给麦氏,还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叶芝一度非常瞧不起这位军官,而且对方的劣迹让叶芝耿耿于怀。*叶芝1889年初遇毛德·冈,便被其美貌所打动,开始了对毛德·冈长达三十余年的追求。毛德·冈虽然是爱尔兰新教徒,而且属于上层社会,但她一直从事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叶芝的屡次求婚均被拒绝。1903年,毛德·冈转信天主教,嫁给麦克布莱德。麦氏生活作风混乱,婚后一度调戏毛德·冈的亲妹妹和女儿。两年后,两人分居(因天主教教义禁止离婚)。毛德·冈请叶芝帮助处理分居事宜,此事一度让叶芝燃起希望。之后叶芝数次向毛德·冈求婚,均被拒。1917年叶芝向毛德·冈的女儿伊秀尔特求婚,被拒。同年10月,叶芝与乔吉·海德-李斯结婚。多年坎坷的感情和生活终于进入稳定的时期。叶芝称他是个“虚荣粗鄙的醉鬼”(a drunken, vainglorious lout),曾经对诗人“贴心的人儿”(指毛德·冈)做过极端刻薄的事情。但是起义使诗人对这位曾经的“醉鬼”的看法发生了改变,起义的壮烈使诗人认为“他已被彻底地改弦易辙”,诞生了一种“可怕的美”(a terrible beauty)。在诗歌最后,诗人赞美起义领袖,称只要爱尔兰人民继续努力,绿色(爱尔兰的国色)就会永存。*《叶芝诗集》(中),第431—436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p.180-182。在《十六个死者》里,叶芝再次赞美了复活节起义的领袖,把他们同1789年起义的领袖相提并论,认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谈论给予与夺取,谈论什么应该存在,什么不应该存在。*《叶芝诗集》(中),第439—440页。《玫瑰树》一诗的形式是对话,对话双方是起义领袖皮尔斯和康诺利。两人感慨说话容易,行动不易,也许“一句花言巧语”就能使“玫瑰凋落”(叶芝诗中的玫瑰大都象征爱尔兰)。但在诗歌结尾,两人达成一致意见,只有用“自己鲜红的鲜血”才能造就真正的玫瑰树(即指爱尔兰独立)。*《叶芝诗集》(中),第439—440页。叶芝借两人的对话表达了对起义的赞同,对起义领袖的颂扬。从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宗教平等)到赞扬起义中的领袖,叶芝诗歌中的宗教观发生了转变。诗人从早期的认同国教而批评天主教到中期的主张众教平等,甚至赞扬以天主教徒为主体的起义。
三、 晚年诗歌中对新教的再度趋同
1922年,爱尔兰成为自由邦,同年叶芝当选为参议员,次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与之前的剧院管理事务相比,成为“公众人物”后叶芝的社会和政治职责更多。成为自由邦后,爱尔兰国教势力逐渐消隐,更多的天主教议员在议会当选,不少社会事务由占多数的天主教议员主导,因此国教议员和天主教议员之间针对社会现实经常发生争议和矛盾。与之前一度主张众教平等观念不同的是,晚年叶芝又回到对新教(爱尔兰国教)的再度趋同。
叶芝晚年在两件事情上与天主教议员有过激烈的争论。成为自由邦之后,爱尔兰议会曾一度通过关于禁止离婚的法案,而这个法案的通过完全是天主教教义的体现,自然受到叶芝的反对。叶芝不仅在议会演讲中公开表示反对,而且写文章对之进行攻击,这也就意味着叶芝反对和攻击的是爱尔兰的大多数。具体到诗歌中,叶芝对天主教的讽刺更见明显。《疯珍妮与主教》中言辞犀利善于讽刺的一位老姑娘珍妮痛诉造就自己苦难的主教。珍妮年轻时,主教尚且连教区牧师都还不是,手里攥着本旧书(指《圣经》),对着老百姓说他们活得像牲畜(lived like beast)。那主教长相丑陋,脸皮“皱巴巴就好像鹅的蹼脚”,即使穿着神圣的黑衣,也遮不住那好比苍鹭的驼背。这位伪善的主教驱赶了珍妮的恋人“雇工杰克”,也把珍妮逼成了疯姑娘。*《叶芝诗集》(下),第623—624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p.255-256。在《疯珍妮与主教交谈》里,那位主教更是道德败坏。珍妮疯了之后,有一天在路上偶遇主教,主教竟然指着珍妮说她的“胸房干瘪下垂”。明明知道珍妮到处流浪,无家可归,主教却对她说要住豪宅大院,“别呆在丑陋的猪圈”。珍妮的回答进一步突出了主教的丑陋,她说“美好和丑陋是近亲”,虽然自己肉体低贱,却有着高贵的心灵。*《叶芝诗集》(下),第632页。叶芝晚年写作的“瑞夫组诗”中,有一首《瑞夫驳斥帕特里克》,诗人借“瑞夫”之口再次表达了对天主教的批判。“瑞夫”称帕特里克被一个古希腊的抽象“谬论”迷惑而“发了疯癔”(an abstract Greek absurdity has crazed the man),将“三位一体”变成完全是男性观点(a Trinity that is wholly masculine),即指帕特里克(天主教圣徒)过于死守陈规,而不顾现实处境。*《叶芝诗集》(下),第694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284。叶芝此处意在批判以圣帕特里克为象征的天主教教义的因循守旧,叶芝的这种态度可以联系到其对天主教禁止离婚的反对。叶芝此处所言“抽象的古希腊谬论”所指为何不得而知。叶芝反对的是天主教中将“三位一体”完全看成是男性的观点,与他所持的“自然和超自然”中包含“男人、女人、孩子(女儿或儿子)”的观点相对。在《朝圣者》一诗中,诗人叙写一位朝圣者脚踏砾石,走遍德戈湖圣岛(传说圣帕特里克曾在此禁食斋戒)周遭,并在那里遇见一位老人(即圣帕特里克)。这位老人什么也不说,除了嘴里反复念一句不知所云的话。在诗歌结尾,那位朝圣者没有被圣人感化,而是放弃了苦修,回到从前的放荡生活,可见对天主教的讽刺态度。*《叶芝诗集》(下),第767—768页。
除对天主教中的主教和圣徒揶揄、讽刺外,叶芝还将力图使爱尔兰成为政教合一(即天主教的自由邦)国家的天主教大众称为“暴民”。在《教会与国家》一诗中,诗人称教会和国家的权力被它们自己的“暴民扔在脚下踩踏”,诗人担心假如教会和国家的支持者都是那些“在门口咆哮的暴民”,爱尔兰该怎么办?*《叶芝诗集》(下),第690页。在《帕内尔派,来聚集在我周围》里,诗人谴责那些制造悲剧故事(即推波助澜极力揭发帕内尔丑闻导致其下台、去世)的政党和主教神父(the Bishops and the Party),诗人更是指斥那位出卖妻子又背叛的“无耻丈夫”。*《叶芝诗集》(下),第755—756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30。“出卖又背叛”的丈夫,即指欧谢上尉,他对妻子与帕内尔同居的事实早已知悉,只是为了能得到妻子可能会继承的一笔财产而“隐忍不发”,直到妻子继承财产的希望变渺茫,他才将此事公诸于众,引起天主教徒的不满,而终于导致帕内尔的下台。叶芝认为帕内尔的去世导致爱尔兰国家方向的改变,而最终的罪魁祸首是欧谢。
叶芝晚年对新教身份的再度趋同,除了体现在对天主教的批评上,还体现在诗人对“库勒庄园”所代表精神的温情回忆与再次肯定。《库勒庄园,1929》是诗人为这座象征新教贵族文艺精神的场所而写的一曲挽歌。*受19世纪末土地运动的影响,库勒庄园曾一度受到冲击,被天主教佃农要求没收和充公。爱尔兰成为自由邦后,要求库勒庄园充公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子罗伯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殉职,庄园归其孙女安妮·格雷戈里所有。但来自外部的压力迫使格雷戈里夫人签署协议将庄园充公,但格雷戈里夫人可以在庄园居住直至去世。格雷戈里夫人去世不久,库勒庄园充公,且很快被夷为平地。在庄园里,产生了伟大的盖尔文学翻译家海德,伟大的戏剧家辛格,还有艺术赞助人泰勒和雷恩。这里有“谦恭之上的自尊、布局甚佳的风景和良好的友人”,这是一个梦想的空间,在这里才能找到实在与真切(found certainty upon the dreaming air)。*《叶芝诗集》(下),第587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243.在《库勒和巴利里,1931》里,叶芝更是哀叹新教贵族文化的消逝。诗人回忆自己曾经在庄园的一小片榉树林中伫立:
那所有的怒吼都是我的心境的镜子:
听见天鹅起飞的骤然的雷霆巨声,
我转过身去看树枝在何处击破
那泛滥的湖泊的粼粼闪耀的水波。*《叶芝诗集》(下),第590页。此处可对照诗人在《库勒的野天鹅》中的描写。
庄园是诗人诗思勃发的灵感源泉,庄园里曾经到处有“著名的手装订的可爱的书籍”(beloved books that famous hands have found),有古老的石雕头像和绘画。受这片庄园及其主人庇护的艺术家寻找到“时间的诗句的理性之美”,而诗人骄傲地称自己和这些艺术家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the last Romantics),选择的是传统的圣洁和美好,选择最能祝福人类心灵的一切作为艺术主题。*《叶芝诗集》(下),第590—591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p.244-245。显然在诗人心中庄园成为人类最高艺术“伊甸园”的象征,而庄园主人和进驻庄园的艺术家是创造这种艺术的代表,这种“最能祝福人类心灵”的艺术就是新教贵族文化。
四、 叶芝诗歌宗教观折射出的“新教优势阶层”归属感
如上所述,叶芝在诗歌中表现出宗教观念变化的一个过程,而这种变化除了与诗人本身的经历息息相关外,更是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宗教与历史处境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折射出诗人“新教优势阶层”的归属感。
叶芝祖上属于在近代爱尔兰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新教优势阶层”(Ascendency),这一阶层由两类人群组成,一类是占有地产的神职人员(如叶芝家族),一类是广有资产的工商业主(如叶芝外祖波莱克斯芬家族)。*叶芝祖上曾在斯莱戈担任神职,在当地颇有影响;叶芝外祖则是斯莱戈有名的富裕家族。因此当叶芝父亲向叶芝母亲求婚的时候,两人的结合被看作神职人员与工商业主的完美联姻。叶芝母亲在结婚时也以为自己能过上稳定的富有生活,殊不知叶芝父亲志向大变,家族地产也逐渐式微,在叶芝童年时母亲不得不带着孩子在伦敦、都柏林和斯莱戈之间来回奔波。自17世纪末以来,这一层级一直占据权力核心地位。但到了19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改变,这一阶层(尤其是占有地产的神职人群)已逐渐衰落,叶芝家族就是典型的代表。在罗马天主教传入之前,爱尔兰属于异教的凯尔特文化,此种文化的传承者主要是名为“德鲁伊”(Druid)的祭司。*凯尔特文化中最有名的“德鲁伊”非亚瑟王故事中的梅林(Merlin)莫属。亚瑟王故事系列属于威尔士文化传统,而威尔士文化传统与古代爱尔兰文化同源。公元5世纪,罗马天主教传入爱尔兰,自此成为爱尔兰人的主要信仰。自公元12世纪起,爱尔兰屡遭英国侵略,但新教影响微弱。17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王朝复辟与光荣革命。1688年信仰天主教的英王詹姆斯二世流亡爱尔兰,英国议会将信奉新教的玛丽公主与荷兰奥尔良王子威廉(即威廉三世)迎回伦敦,自此确立英国国教的统治。两年后,威廉三世在都柏林附近的博因河击败受爱尔兰支持的詹姆斯二世,大批新教徒涌入爱尔兰,以武力和贸易等方式逐渐成为爱尔兰的统治阶层,是为“新教优势阶层”。自此之后,以地主、神职人员、工商业主为主的新教阶层与以佃农、劳工、仆役为主的天主教阶层矛盾不断,直至20世纪初表达两个阶层之间互相轻蔑的文艺作品仍然层出不穷。*1904年《领导者》杂志还刊发一篇《仲夏夜之梦》的拼凑戏文,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互相轻蔑的情态展露无遗。参见Paul Bew, Ireland: The Politics of Enmity 1789-20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7,pp.7-8.19世纪中叶,爱尔兰大饥荒发生,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英国政府政策的迁延、大饥荒的惨痛后果导致佃农要求土地权利的运动兴起*爱尔兰大饥荒导致一百余万人死亡,近两百万人移民国外,而受灾的主要群体是天主教佃农。参考罗伯特·基著,潘兴明译: 《爱尔兰史》,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2页。,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占有地产的新教神职人员。叶芝的祖父还能够从神职上安然退休,享受庄园地主的生活。*叶芝祖父1853年退休,居住于其姻亲的桑迪蒙特城堡(Sandymount Castle),直至1862年去世。参看Yeats in Context, p.16.到叶芝父亲时祖传的地产收入逐年缩水,直至不敷用度而遭变卖。新教势力的衰落也就意味着天主教势力的崛起。*1869年《爱尔兰宗教法案》(Irish Church Act)通过,天主教教徒获得选择、拥有土地等权利,因此这一法案的通过及其影响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解放运动”(disestablishment of Catholics)。家族经济的日趋破落使得叶芝对“库勒庄园”提供的稳定、富裕环境更具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对祖先的“新教优势阶层”身份更加怀旧。例如在《责任》这部诗集的《序诗》中,诗人充满敬意地缅怀自己的新教祖辈,称他们是“老都柏林商人和乡村老学者”,这些筚路蓝缕的祖辈“把那不曾流经任何贩夫走卒腰肾的血脉,流传给我的商人和学者”。*《叶芝诗集》(中),第235页。
叶芝诞生于19世纪土地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家族的命运在少年叶芝成长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痕迹,生活的奔波使叶芝对稳定的生活充满向往,对先祖的荣耀充满缅怀之思。叶芝出生的年代又正好是基督信仰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刻,叶芝在不彻底接受任何一种信仰的思想准备下积极参与文艺创作。19世纪80年代之后,土地运动逐渐消隐,文艺复兴逐渐兴起,叶芝成为此一运动的领袖。虽然叶芝希望以文艺复兴的方式推动民族复兴,但他认为文艺和政治应该有一定距离。叶芝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引起的反映(例如《西部浪子》、休·雷恩爵士、帕内尔三个典型事件)使他更加确信新教贵族在文化上的优势和领导力。自从第一次踏足库勒庄园,叶芝便将其视作新教贵族文化的象征所在。叶芝一度的生活中心在于对艾贝剧院事务的管理,而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观众在一些事件中的反应让叶芝对天主教持批评态度,而趋于认同新教身份。关于休·雷恩爵士捐画事件,格雷戈里夫人曾写过回忆录,称为收藏捐画而建画馆的募款要比预想的困难,都柏林的市民认为自己已经交过税,乡民则视之为奢侈,少数富人裹足不前,一位本来答应资助的富人变卦,称“除非证明百姓愿意要这些画”。为此叶芝写了一首“言辞激烈”的诗,即《致一位富人》,在诗中他称爱尔兰中产阶级天主教徒为“白丁”和“鄙弟”。针对这首诗,《爱尔兰天主教》报纸很快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反对叶芝的代表人物莫菲在多处反击,并在文章署名时声称出自“一位白丁的意见”。叶芝也毫不客气地写文揶揄说“那就是白丁的意见”(Paudeen’s point of view it was)。*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9, p.251.在《1913年9月》一诗中,叶芝再次对中产阶级天主教徒进行嘲讽,称他们“怯懦,只会算计”。叶芝认为,大多数爱尔兰教徒(天主教)视神圣事物为一轮职责,与生活无关,而爱尔兰政客则认为好公民就是抱持某种观点的人。与这两种人不同,还有一类少数人,颇有教养,沐浴传统文化的遗泽。这类人之前较多,但中产阶级天主教徒兴起之后则日趋减少。叶芝甚至感慨,在帕内尔事件中,“这些天主教徒第一次公开展示,在关键时刻一个人若只有头脑,没有文化是多么卑贱”!*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pp.224-225.可见对天主教徒揶揄之切。
叶芝的这种态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之后,有了改变,诗人开始主张众教平等,并对参与起义的天主教徒领袖赞誉有加。如上所述,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使叶芝不得不重新评价自己以前的看法。在《1916年复活节》一诗中,叶芝赞美以天主教徒为主的起义中诞生了一种“可怕的美”。在为诗集作注时,诗人说之前认为天主教徒是“白丁”的说法显然已经过时,并室称1916年的起义将永存史册。他说:“没有哪件事像1916年复活节起义那样触动我,不管公众如何评价此一事件,我认为其英雄主义必将永存……为此我试着为那些被枪决的人写一首诗。”*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p.88.这种态度在《十六个死者》、《玫瑰树》等诗中得以延续。
然而,成为自由邦以后的爱尔兰,新教势力进一步衰落,天主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数。天主教教义导致的一些政策自然不为叶芝所接受,在此消彼长的时代趋势下诗人自然更加怀念曾经的“新教优势阶层”,此种怀念形诸于诗歌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你满足吗?》一诗中,诗人赞美曾祖在斯莱戈地区“树立起古老的石十字架”,称赞红头发的祖父是“一个骑马的好人”,也对外祖家的赫赫声名充满敬仰,说他们是“半传奇式的人们”。*《叶芝诗集》(下),第788—789页。格雷戈里夫人家的库勒庄园一直是叶芝羡慕的家庭传统,因此在《你满足吗?》一诗中诗人也极力构建自己的家族传统。*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p.48.在自传中,叶芝还曾记载外高祖因在大饥荒期间照顾病人而献身的事迹,在他心目中,自己的家族祖先好比猎手: 务实、按本能行事、崇尚自然。*转引自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p.48。后来叶芝本人经历过土地运动的冲击,曾经在名为《关于一幢被土改运动摇撼的房子》的诗中热情赞誉库勒庄园融“激情和规矩”(passion and precision)于一体,痛伤庄园被土地运动影响,并感叹假如庄园象征的文化(新教贵族文化)变得颓败,“这世界又怎会更幸运”?*《叶芝诗集》(上),第222页;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p.95。而《库勒和巴利里,1931》中,诗人将库勒庄园因土地运动而被充公比喻为一个“高大的骏马没了骑手”,也就意味着爱尔兰这匹骏马没有了象征高雅文化的骑手。这些在在表现出诗人的“新教优势阶层”归属感。
近代爱尔兰天主教和新教的对立,除了双方的此消彼长之外,也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混杂形态(cultural hybridity)。*Anthony Bradley, Imagining Ireland in the Poems and Plays of W.B. Yeats: Nation, Class, and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2.19世纪末在天主教和新教之内各自有不同的教派*在新教内,除爱尔兰国教外,还有循道宗(Methodism)、浸信会(Baptism)、长老会(Presbyterianism)等;而在天主教内,则有圣衣会(Carmelites)、耶稣会(Jesuits)、多明我会(Dominicans)等不同派别。参考W.B. Yeats in Context, p.227.,而更重要的是基督宗教*此处使用学者何光沪和赵林等的说法,即“基督宗教”指的是以圣经和基督为核心的宗教的统称。参见何光沪: 《当代中国的国家目标——一种基督宗教兼非宗教角度的思考》,《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2014年第41期,第71—101页;赵林: 《基督宗教的全球本土化与汉语神学的应对方略》,《道风: 基督教文化评论》2014年第41期,第103页注释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来自生物进化论的挑战。这种相当复杂的文化混杂形态又与近代爱尔兰被殖民的历史相裹挟,从而使近代爱尔兰人民在心态上产生碎片感和断裂感(fragmentation and discontinuity)*Imagining Ireland in the Poems and Plays of W.B. Yeats: Nation, Class, and State, p.3.,如叶芝这般敏感的艺术家必然亟需在混杂和碎片中寻找自我身份,包括宗教身份。从上述三节的分析来看,叶芝显然倾向对国教身份的认同,除家族影响外,国教所代表的贵族文化传统更是诗人念兹在兹的对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进化论的冲击和自由思想的流播,叶芝受父亲影响,青年时期曾对一切持怀疑态度,包括宗教。叶芝曾经在自传中说自己与同时代人在一点上有所不同,那就是诗人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religious)。当时的人受到赫胥黎、廷代尔的影响,对基督宗教持怀疑态度。虽然叶芝也认为自己童年时代专一信仰的权利被剥夺,但很快他就建立起一个诗歌传统的宗教(Church of poetic tradition)。*W.B. Yeats, Autobiographies, pp.115-116.正是因为叶芝有过这样的表达,因此有观点认为叶芝不信仰任何宗教,对各种思想等量齐观。笔者以为,认为叶芝对各种思想等量齐观固然准确,这一点是叶芝受父亲和时代影响的结果,但叶芝在作品中表露出的宗教观念亦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更公允的说法是,叶芝并不彻底相信某一种思想或信仰,他只是在这些信仰和思想的基础上采用符合自己意愿的观点,来构造一个自己的“神话世界”。*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叶芝的历史循环论(cyclical theory of history)。叶芝认为,历史以两千年为一个周期,例如公元前两千年至公元元年为古典时代(以古希腊文明为代表),公元元年之后的两千年为基督教文明时代。每一个周期都有一个起点,古典时代以海伦的诞生为起点(参看《丽达与天鹅》一诗),基督教文明时代以耶稣诞生为起点(参看《再度降临》一诗)。历史周期以这个起点为核心,像一个螺旋(gyre)一样不断往外扩散,直至崩散。一个文明的终结意味着另一个文明的开始,历史便以这种相向对立的螺旋方式循环。参考叶芝著,西蒙译: 《幻象》,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叶芝历史循环论融合了基督教思想、贝克莱和维科哲学、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新柏拉图主义、犹太卡巴拉思想等。参考Edward Malins & John Purkis, A Preface to Yeat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4; Edward Larrissy, W.B. Yeats (Irish Writers in Their Time),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Ltd, 2010.但显然,这个 “神话世界”是一个以新教贵族文化为底色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