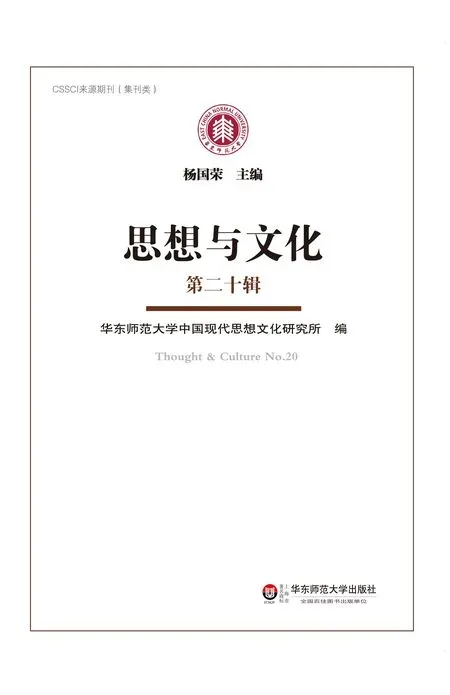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文文相生”:“内互文性”与“外互文性”
——一个比较诗学研究*
●
“文文相生”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小说戏曲评点家金圣叹提出的理论范畴,是对我国传统戏曲、小说之文本组织形式的精辟概括。然而,由于中国古典文论自身感悟式、印象式的特点,金圣叹虽然提出了这一范畴,但对此并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阐释。与中国古典文论相比,西方文论是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因此,笔者试图从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出发,以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为参照,阐释和挖掘“文文相生”的理论内涵。
一、 “互文性”理论: 内互文性与外互文性
目前在中国学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通常也被译为“文本间性”(文学理论界)或“篇际性”(语言学界),并被理解为文本与文本、语篇与语篇之间的关系。而随着解构主义对“文本”(text)的解构所造成的“文本”的泛化及其意义的不断拓宽,“互文性”也进一步被用来指称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文学史,乃至文本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联。“互文性”的理论旨趣,也通常被理解为打破“文本”的封闭性,恢复对文本之外的因素的关注,恢复文本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重新链接,从而解构文本中心主义,肯定“文本与文本之外的事物的广泛联系”*张良丛、张锋玲: 《作品、文本与超文本——简论西方文本理论的流变》,《文艺评论》2010年第3期。。
上述对“互文性”的理解,其实只揭示了“互文性”含义的一个方面,即“外互文性”(extratextuality)。而“互文性”应当包括“内互文性”(intratextuality)和“外互文性”两个方面的含义。众所周知,“互文性”是法国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在向当时的法国理论界引介巴赫金理论时提出的术语。回到“互文性”理论提出的原初语境,可以更好地把握其理论旨趣和丰富内涵。
(一)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是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时提出他的“对话”理论的。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复调小说。而“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76页。它不仅包括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而且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人物的每一手势、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从而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的一切因素,都具有对话的性质”。*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76页。“整个小说他是当作一个‘大型对话’来结构的。在这个‘大型对话’中,听得到结构上反映出来的主人公对话,它们给‘大型对话’增添了鲜明浓重的色调。最后,对话还向内部深入,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这已经就是决定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言风格特色的‘微型对话’了。”*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77页。
可见,巴赫金所说的“对话”,首先指的是“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亦即同一文本内部不同文本单元之间的对话,是文本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对话,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一文本与他文本之间、文本与文本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对话。在巴赫金看来,正是这种“内在对话”*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9页。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众不同的结构。
巴赫金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和指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结构上的“内在对话”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他还深入挖掘了这一特色的深层根源。巴赫金指出,对话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艺术形式的基础,这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所决定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作者对主人公所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作者是和主人公谈话,而不是讲述主人公。作者充分尊重主人公的自由,他正如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创造出来的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无声的奴隶。这自由的人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见。
巴赫金进一步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作品的主人公的这种对话关系,与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性质密切相关。俄国早期资本主义异常尖锐的矛盾,是创造复调小说的最适宜的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发现,人由于物化而贬值的现象已经渗透到他那个时代的各个时期,渗透到人的思维的基础之中,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全部热情,就在于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他对主人公所采取的对话的态度,正体现了他试图使人摆脱物化的努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传统的文学作品中那种稳固坚实的作为完整的实体的主人公,恰恰是人的个性物化的表征。为了不使人物化为客体对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任何时候也不会与自身重合。对他不能采用恒等式: A等于A。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思想告诉我们,个性的真谛,似乎出现在人与其自身这种不相重合的地方,出现在他作为物质存在之外的地方。”*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98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人是自由的,因之能够打破任何强加于他的规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总是力图打破别人为他所建起的框架,这框架使他得到完成,又仿佛令他窒息”。*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97页。换言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专注于表现“心灵的自由,心灵的不可完成性”,表现“不能完结也不可意料的心灵变故”*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00页。,它“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内在的自由、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03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处在痛苦的挣扎之中,承受着特殊的精神折磨。他们不但总是在努力打破别人对他们所下的定论,而且同样努力地打破自己对自己所下的定论。他们以这种努力抗拒着社会对人的物化,证实着人的自由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争取自由的努力,尽管它的结局常常是悲剧性的。因此,它不试图证明一个既定的观念,而只是以一种极度紧张的对话的积极性,让这种悲剧性的努力获得最大限度的呈现。简言之,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统一于紧张的对话之中,统一于人类在高度物化的环境中争取自由的悲剧性努力之中。
综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首先关注的是同一文本内部不同文本单元之间的对话,但又不局限于文本之中,而是由此生发开去,进一步探讨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以及作者与时代社会环境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入乎文本之中,又出乎文本之外的理论,文本外的对话是文本内的对话产生的原因,并通过文本内的对话得以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二) 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
如前所述,克里斯特瓦是在向法国理论界引介巴赫金的理论时,提出“互文性”这一概念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克里斯特瓦的理论缺乏原创性。总体看来,克里斯特瓦的《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的基本思路是: 着眼于当时文学创作中的诗性语言现象,为寻找一种新的符号学研究模式,将视野投向巴赫金。
克里斯特瓦认为,文学符号学的任务是建构与诗性语言(即文学语言)同构的结构模型。在这方面,巴赫金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使用一种新的动态模型代替了从文本中抽离出来的静态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文学结构不是简单地存在,而是产生于与另一种结构的关联中。这是因为,巴赫金不把文学词语(literary word)看成一个有着确定意义的点,而是把它看成各种书写的一种对话。这一对话包括三个方面或三个坐标: 写作主体(writing subject)、接受者(addressee)和外部文本(exterior text)。这三个方面形成了纵横交叉的两轴: 写作主体与接受者的共时性关系构成横轴,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历时性关系则构成纵轴。巴赫金将前者称为“对话”(dialogue),将后者称为“复义”(ambivalence,也译作“二重性”、“不确定性”或“语义双关”)。但克里斯特瓦发现,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二者并没有得到清晰的区分,巴赫金经常将二者都称作“对话”。有人因此指责巴赫金缺乏严谨,而在克里斯特瓦看来,“巴赫金之缺乏严谨更能说明,他是首次将一种深刻的洞见引入到文学理论中来: 任何文本都是一种引文马赛克的建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观念,诗歌语言(poetic language)的阅读至少是双重的(double)”。*朱莉娅·克里斯特瓦: 《词语、对话和小说》,李万祥译,《文化与诗学》2011年第2期,第253页。
这段文字是“互文性”概念的原始出处,也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互文性”的权威定义。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从理论旨趣来说,“互文性”的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取代“主体间性”的概念,其理论出发点是为了质疑作者的权威。作为“如是”小组这样一个激进的理论团体的成员,克里斯特瓦具有强烈的主体批判倾向,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学观中以理性主体为中心的作者观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传统文学观认为,作品是作者创造的,作者之于作品,就如同上帝之于世界。人们相信,对于文学作品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终极解释,而这个终极解释只能从作品的创造者——作者那里找到。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在作品中发现作者的意图和观念,从而正确地解释作品。
事实上,作者的这种中心地位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动摇了。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理论,已经把作者驱赶出了文学批评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如果作者的意图体现在文本中了,那么文学批评只需要研究文本;如果作者的意图没有体现在文本中,那就与文学批评无关。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是发现作者的意图,而是发现文本的结构,这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俄国形式主义者关注语言的“陌生化”;“新批评”致力于揭示文本中的“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结构主义者则认为,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析某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而是为了寻求所有文学作品所共有的某种结构模式。
与上述文本中心主义理论相比,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是对作者主体的进一步消解,从而力图把研究者的目光由“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转移到文本上来。在克里斯特瓦看来,无论是写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要想进入文学活动,只能以词语的形式进入文本。主体要实现对话和交流,首先要在文本中取得言说的位置。换言之,对话必须通过文本实现,无论写作主体还是接受主体,都必须以话语的形式被包容在文本的潜在空间里,并作为文本的一部分与文本的其他部分展开对话。这样,在克里斯特瓦看来,主体的对话和文本的复义这两个维度,原本就是重合的,二者在克里斯特瓦这里汇合而成“互文性”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特瓦认为,巴赫金没有对这两个维度进行清晰的区分,恰恰是一种洞见。总之,克里斯特瓦“互文性”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 坚持文本空间的优先地位,将主体、社会和文化问题放置在文本之内观照。
后来,克里斯特瓦又在《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两篇论文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在《封闭的文本》中,克里斯特瓦说:“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在一个确定的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审美的’特征)。”在《文本的结构化问题》一文中,克里斯特瓦又说:“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 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秦海鹰: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不难看出,在克里斯特瓦这里,“互文性”首先是指“同一个文本内部的文本互动作用”,而这一文本内部的互动作用,则显示了此文本与其他文本,以及写作主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无论是巴赫金,还是克里斯特瓦,都是从文本内部不同文本单元之间的关系入手,但最终达致对一文本与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以此为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普遍主张将“互文性”划分为“内互文性”与“外互文性”。早在1985年,杰伊·莱姆基(Jay Lemke)就提出,“互文性”包括“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两种形式。其中,“内互文性”指的是一个给定的文本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外互文性”则是指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Jay L. Lemke, “Ideologie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 in Systemic Perspectives of Discourse, eds. Benson and W, Greaves. Norwood: Ablex Pub, Corp., 1985. p175.哈特姆(B. Hatim)也认为,除了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外,互文性也可能存在于同一文本内,即“内互文性”。*B. Hatim,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ntrastive Text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218.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也提出,当前,“互文性”通常用来指某一文本对其他文本的暗示或提及;那么,与之相应,在一个文本内部的各种关系就应称为“内互文性”。*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02. Daniel Chandler, Semiotics for Beginners.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Part 13:“intertextuality”.这些学者都认为,片面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极易导致对“互文性”理论的误解。
总之,“内互文性”与“外互文性”是“互文性”理论的一体两面。“外互文性”是“内互文性”的基础,而“内互文性”则是“外互文性”在文本中的呈现。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的文本单元之间之所以会采取特定的组合形式,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文本”影响了文本的组织形式;而某一特定文本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必然通过该文本内部的组织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对“外互文性”的研究不应脱离文本,否则就会沦为空洞的政治口号;而对“内互文性”的研究则不应封闭于文本,否则就会沦为琐碎的技巧罗列。就一个具体的文本而言,对其“互文性”的研究应当从“内互文性”开始,通过对其“内互文性”的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则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外互文性”。
时至今日,“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的划分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并呈现出较强的理论普适性,这正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堪借照焉”的“邻壁之光”。*钱钟书: 《管锥编》,北京: 中华书局,1979年,第166页。借助这一亮光,或可照见“文文相生”这一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与之相通的诗心文心。
二、 “文文相生”的“内互文性”考察
如前所述,“文文相生”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小说戏曲评点家金圣叹提出的理论范畴,是对我国传统戏曲和明清小说之文本组织形式的精辟概括。金圣叹是在对《西厢记》的第三本第三折《赖简》的第十五节的夹批中提出这一范畴的。这一折大体的故事情节是: 张生收到莺莺的书信,当晚跳墙至花园中与莺莺相会,却遭莺莺斥责其行为不检,只得失望而归。显然,这一情节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 莺莺既以简招张生前来,又为何赖简,反而斥责张生?
对于莺莺“赖简”之原因,前贤时哲曾作了多种解释,却均难以自圆其说。如明人李贽认为,莺莺与张生“此时若便成交,则张非才子,莺非佳人,是一对淫乱之人了”*贺新辉、朱捷: 《〈西厢记〉鉴赏辞典》,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但是,在许多戏曲作品(如元杂剧《墙头马上》)中,青年男女邂逅钟情便立即传书递简,私相媾和,仍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佳作,男女主人公也没有被称为“淫乱之人”。今人宋之的认为,“莺莺的耍赖和撒谎,也是一种阶级根性”*李修生、李真渝、侯光复: 《元杂剧论集》,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61页。,那么,具有这种统治阶级劣根性的莺莺何以反倒赢得古今读者的喜爱呢?
相比之下,金圣叹的解释更为合理。莺莺赖简,一是为了使行文更加曲折有趣,“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赖简总评)*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9页。莺莺如一逾而行,行文则缺少了趣味。二是为了与前文对比。“此翻跌前文成趣也,不知是前文特为翻此文,故有前文;不知是此文特为翻前文,故有此文。总之文文相生,莫测其理。”(赖简第十五节夹批)*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96页。换言之,这样写是为了行文的需要,是文与文互相生发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内互文性”。
(一) 整体还是缀段
如前所述,“内互文性”指的是同一文本内部不同文本单元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各个不同的文本单元是如何组织成一个文本的。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中国古代的评点家,如金圣叹、毛宗岗等人均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结构十分精巧。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序三)*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 《水浒传会评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9页。;《西厢记》的整体结构有着严密的完整性,“谓之十六篇可也,谓之一篇可也”(三之四)。*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100页。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九十四回回评)*罗贯中著,毛纶、毛宗岗评点: 《三国演义》,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562页。而西方传统的汉学家则多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结构缺乏艺术的整体感,其致命的弱点在于其“缀段性”(episodic),也就是说,是将一个个单独的事件单元连缀起来,而每个事件单元之间缺乏紧密的因果联系,造成结构松散,条理不清。
之所以会产生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对于叙事的整体感和统一性的理解不同。在西方文学中,“整体性”或“统一性”通常指的是故事情节的因果律(casual relations)。西方以史诗和悲剧为源头的叙事传统,以情节(plot)的人为而周密的组织为其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曾指出,悲剧包括六个成分: 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的组合(即情节——引者注)是成分中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4页。,“情节是悲剧的根本,用形象的话来说,是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 《诗学》,第65页。“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模仿,就必须模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要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 《诗学》,第78页。
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结构大多不够严密。以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为例,其中没完没了的生日、节日宴饮,如果减少一次,对整体的故事情节有什么影响呢?又如《三国演义》所写的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其中大部分事件在情节上是分立的,这与《荷马史诗》集中讲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五十一天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长篇小说如此,篇幅相对比较短小、情节相对比较简单的戏曲也是如此。以《西厢记》为例,它比较集中地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然而,与西方同类题材的戏剧作品(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其情节结构仍是比较松散的。正如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所说:“《西厢记》正写《惊艳》一篇时,他不知道《借厢》一篇应如何。正写《借厢》一篇时,他不知道《酬韵》一篇应如何。总是写前一篇时,他不知道后一篇应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只顾写前一篇。”“《西厢记》写到《借厢》一篇时,他不记道《惊艳》一篇是如何;写到《酬韵》一篇时,他不记道《借厢》一篇是如何。总是写到后一篇时,他不记道前一篇是如何,用煞二十分心思,二十分气力,他只顾写后一篇。”*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11页。这大概就是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结构不够精密的原因。
但是,支配着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之结构的,恰恰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美学观念。运用西方理论进行挪借式的操作,只会导致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结构的误判。与西方小说戏剧强调情节的周密组织不同,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结构安排上追求的是另一种精巧: 在篇幅相对比较短小的戏曲中,体现为由一个叙述单元向其他叙述单元的“那辗”;在长篇小说中,则体现为不同叙述单元之间的“照应”。
(二) 那辗
作为中国古典戏曲的代表作,《西厢记》在结构安排上以“那辗”为基本模式。在为《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前候》所写的总评中,金圣叹对“那辗”作了这样的界定:“‘那’之为言‘搓那’,‘辗’之为言‘辗开’也。搓那得一刻,辗开得一刻;搓那得一步,辗开得一步。于第一刻、第一步,不敢知第二刻、第二步,况于第三刻、第三步也?于第一刻、第一步,真有第一刻、第一步;莫贪第二刻、第二步,坐失此第一刻、第一步也。”*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71页。金圣叹认为,《前候》这一出写红娘探病、张生寄简,情节十分简单,“题之枯淡窘缩,无逾于此”。若直接破题抒写此事,则必然有如“以橛击石,确然一声则遽已耳,更不能多有其余响也”。故作者用“那辗”之法,将这一简单情节“那辗”出“前、中、后”三截,因“其中间全无有文”,作者又将前后两截“那辗”出“前之前、前之中、前之后”、“后之前、后之中、后之后”,因而洋洋洒洒写出“如许六七百言之一大篇”。红娘探病,见到张生之前为“前”,而此“前”又分为“前之前”——以[点绛唇]、[混江龙]详叙前事,回顾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一封书信解围的经过;“前之中”——以[油葫芦]双写两人一样相思,谴责老夫人悔婚之举;“前之后”——以[村里迓鼓]写走到张生门前,又觉不便敲门,点破窗纸窥视张生和衣而睡的凄凉景象。见到张生,张生托红娘送简,红娘若即刻答应,则文竭矣。但作者又“那辗”出“后之前”——以[上马骄]、[胜葫芦]写红娘害怕小姐责怪,不肯送简,张生怀疑红娘借此索贿,惹怒红娘;“后之中”——以[后庭花]写二人误会消除,张生一挥而就,红娘赞叹其才华;“后之后”——以[寄生草]写红娘答应送简后,忽作庄语相规,劝张生不可为儿女情长耽误了鸿鹄之志,显示出红娘与众不同的见识。正所谓“题固蹙,而吾文乃甚舒长也;题固急,而吾文乃甚行迟也;题固直,而吾文乃甚委折也;题固竭,而吾文乃甚悠扬也”。*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72页。
不只《前候》一折,在金圣叹看来,整本《西厢记》的结构都是“那辗”而成。他说:“仆思文字不在题前,必在题后。若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不信,但看《西厢记》之一十六章,每章只用一句两句写题正位,其余便都是前后摇之曳之,可见。”“知文在题之前,便须恣意摇之曳之,不得便到题;知文在题之后,便索性将题拽过了,却重与之摇之曳之。”*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9页。按照西方传统的叙事观念,这些“摇之曳之”的文字,都是情节中可有可无的,是多余的冗赘。在西方人看来,“事件”(event)是一种“实体”,“叙事”就是对这一实体的讲述,与此“事”无关的,皆应排除在“叙事”之外。与此相异,在中国的叙事传统里,“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按照中国传统的自然论宇宙观,天道自然,人事周流,本来无事可叙。因此,“叙事”的重点在于“叙”而不在于“事”,“事”本身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对“事”的叙述,揭示其背后隐含的自然而然的“天道”。著名汉学家浦安迪发现,中国的叙事文学作品很少集中叙述一件事,而是往往“习惯于把重点或是放在事与事的交叠处(the overlapping of events)之上,或是放在‘事隙’(the interstitial space between events)之上,或是放在‘无事之事’(non-events)之上”。*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页。“在大多数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作品里,真正含有动作的‘事’,常常是处在‘无事之事’——静态的描写——的重重包围之中。”*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第47页。这正是金圣叹所谓“题之正位,决定无有文字”的理论内涵。用金圣叹的话说,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是“为文计,不为事计”*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第246页。,因此可以“因文生事”。*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1页。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中,“因文生事”通常被理解为文学的虚构性;其实,中国的叙事传统本不重视纪实与虚构的区分。金圣叹借“因文生事”所强调的是,“文”自身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它不但决定着“事”的安排和组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无中生有地创造、派生出“事”来。“事”不是根据自身的因果逻辑向前发展,而是根据行“文”的需要被组织和创生。金圣叹认为:“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8页。“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如彼滚,实都为球也。”*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8页。这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共同遵守的美学原则。
(三) 照应
中国古典长篇章回小说在主结构的安排上非常注重不同叙述单元之间的相互照应。关于这一点,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的评点中有着十分精彩的论述:“《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卷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余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榷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罗贯中著,毛纶、毛宗岗评点: 《三国演义》,第8页。显然,这种结构的精巧与西方不同,它不以情节对事件的严密组织见长,而是以看似孤立的各个事件单元之间精神内蕴的相互呼应作为结构内在完整性的基础。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腰斩”,遵循着同样的美学原则。圣叹自恃才高,谎称手中握有“古本”,伪造作者原序,并据此对原书进行了大胆的删改(将《水浒传》“腰斩”为七十回,并自撰了“梁山泊英雄惊噩梦”的结局),自然是“英雄欺人”之举。然而,金批水浒一出,即成最为权威之流传版本,其他各本均湮没不彰,这一版本史上的奇迹让人不得不思考圣叹“腰斩”《水浒》的合理性所在。在《水浒传》评点中,金圣叹不止一次地提到“古本”(实际是经金圣叹“腰斩”、删改过的)“《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116页。,“以‘天下太平’四字起,以‘天下太平’四字止”*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39页。,首尾呼应,结构谨严。与之相比,罗贯中所续(其实是原本)纯属“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598页。“石碣”不但出现在小说的起点(“楔子”写洪太尉误走妖魔,掀起石碣放走一百零八道金光,暗示梁山好汉事业的开端)和终点(第七十回写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团圆聚义,一块石碣从天而降,暗示着梁山事业的收场),而且与梁山泊的第一位领袖晁盖密切相关。晁盖的绰号“托塔天王”便“暗射开碣走魔事”,而晁盖造反的开端“七星聚义”则是在三阮所居住的“石碣村”密谋完成。显然,这种结构安排与毛氏父子所说的“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遵循着相同的美学原则。
上文所说中国古典小说重“照应”而中国古典戏曲重“那辗”,只是就其大概而言。事实上,中国古典戏曲中也有“照应”,如《西厢记》中的“两来”——《借厢》写张生慕莺莺之色而来,《酬韵》写莺莺慕张生之才而来;“两近两纵”——《请宴》一近与《赖婚》一纵,《前候》一近与《赖简》一纵;“实写虚写”——《酬简》实写崔张爱情的实现,《惊梦》虚写爱情不过一梦等等。同样,中国古典小说也有“那辗”,如金圣叹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提出的“弄引法”和“獭尾法”。“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 《水浒传会评本》,第21页。《水浒传》如此,《三国演义》也是如此,毛氏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指出:“《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先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又云:“《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霡霂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余势。如董卓之后又有从贼继之;黄巾之后又有余党以衍之;昭烈三顾草庐之后,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罗贯中著,毛纶、毛宗岗评点: 《三国演义》,第6页。可见,“那辗”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非常普遍的文本组织形式。只不过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多以“照应”为整部小说之章法,而以“那辗”为具体段落的组织方式;而中国古典戏曲则多以“那辗”为“最大章法”,而以“照应”为“那辗”的一种手段。
三、 “文文相生”的“外互文性”考察
如前所述,“外互文性”是指一文本与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封闭地存在的,它与其他文本、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文相生”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基本组织形式,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浸染,甚至可以说,它就是由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所孕育的。因此,要探索“文文相生”的深层意味,不能不将之放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加以考察。
在以往的“互文性”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不同文本故事间的相似,而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大量取材于民间文学作品,如灵怪、传奇、公案、妖书、神仙等故事,以及演义、弹词、平话等民间流行的艺术表演,这使得前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时,一般倾向于将其与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强调其脱胎于民间文学并试图超越民间文学的特点。这种研究方法在文学的“材料—形式”二元素之中,更看重材料而忽略形式,而没有意识到,“形式”对于文学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李卫华: 《形式: 作为“肌质”与“神理”》,《福建论坛》2012年第2期,第139页。民间文学只是古典小说戏曲的材料,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完全取决于作者自己的审美趣味。古典小说戏曲自身的审美特质,取决于作者赋予这些材料的形式,而非材料本身。仅仅关注材料的“互文性”研究只看到了民间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影响,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因而不但极大地贬低了古典小说戏曲作者的创造性,而且贬低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艺术价值。
早在明清时期,文人们已经意识到,《三国》、《水浒》等作品与同时流行的演义、弹词、平话等完全不是同一类作品,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体现在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上。文人们对那些“言辞鄙谬”*蒋大器: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颇伤不文”*高儒: 《百川书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113页。、“鄙俚浅薄”*绿天馆主人: 《古今小说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217页。、“读之嚼蜡”*笑花主人: 《今古奇观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263页。的民间文学作品是非常鄙视的,而对那些“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高儒: 《百川书志》,《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第113页。的《三国》、《水浒》等作品则称赞有加。著名汉学家浦安迪通过对《三国》、《水浒》的体例和叙事特征的研究发现,这些作品体现的完全是文人的思想抱负和审美趣味,因而提出了“16世纪文人小说”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在他看来,由这些“文人小说”所开创的“奇书文体”与民间文学的联系,远不如其与正统的经、史,甚至诗、词之间的联系密切。*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第28页。这是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实际的。事实上,明清的小说评点家们也总是将所评点的作品与《左传》、《史记》等正统的史传文相比较。明末清初的金圣叹曾将《水浒》、《西厢》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等正统文学并称为“六才子书”。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又特别强调,“《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此书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 《水浒传会评本》,第15页。在具体评点中,金圣叹也常将《水浒》与正统的经史著作进行比较,如在第八回评点鲁智深野猪林救林冲的描写时,金圣叹就专门“以《公》、《穀》、《大戴》体释之”,并认为“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 《水浒传会评本》,第186页。在评点《西厢记》时,金圣叹又说:“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金圣叹: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第7页。可见,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固然从民间故事、说书、平话、弹词等民间文学中取材,但熔铸成现今的写定本,同长久以来的文人的审美趣味、同正统的诗文传统,恐怕有着更为深厚的关系。
(一) 八股文的程式作法
中国传统小说戏曲中,以“那辗”和“照应”为基本特征的文本组织形式,最为直接的渊源恐怕就是“时文”(八股文)的影响了。八股文,又名四书文(因这种文章的题目出自《四书》),八比文(因文句用比偶),是我国自宋元以来初见端倪、发展至明清则臻于完备的科举考试的文章体裁。以科举取士为源动力,宋元以来的文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八股,并且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到了明清之际,八股文更成为文人学习的基本内容。“明清各级学校教育,学作八股文是中心的内容。学童由启蒙开始即为八股文写作打基础,一般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识字为主。接着学四书,要求学童背诵,在四书开讲之后即‘开笔’进行八股文的写作训练了。蔡元培先生在谈到八股文的训练程序时说,‘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共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写得及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王凯符: 《八股文概论》,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作为一种作文之法,八股文的结构,通常可分为三个部分: 题前部分、正题部分和收束部分。题前部分,包括破题、承题、起讲等,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解释题意,说明题目本身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并由此引出自己的正解。正题部分要求根据题意阐发儒家的有关思想,表达作者的认识,文字要用对偶,形成相对成文的两股文字。通常要有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作成八股,这是全篇文章的重心。八股文最后还要有落下、收煞,收煞总括,照应全文。此外,文中还有入题、出题、过接等名目。并且,它们各部分之间还主要呈现为一种起承转合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即“起承转收”。破题,解释题意,这是文章的“起”;承题、起讲进一步阐发题意,从而引出“入题”的文字,即是八股文的“承”;用排比、对偶写的八个段落(八股),阐述发挥作者的认识,这是八股文的“转”;文章末了的“收结”或“落下”,收束全文,则是八股文的“合”与“收”。
进入现代以来,在西学东渐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学界对八股文大多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种僵化定型的文体模式严重压抑了写作者的创造性,只能产生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这种观点指出了八股文的稳定机制压倒创新机制,从而使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张力失衡,成为作文的“死法”,这确实是八股文的突出弊端。但平心而论,八股文的结构自有其合理之处。这种由一代复一代的士人呕心沥血琢磨出的精致的文体结构网,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汉字表达的传统写作经验,强化了汉字表达的弹性感和精致感,充分发挥了汉字表达的潜力。其之所以遭人诟病,只不过是因为它把这种宝贵的写作经验过度极端定型化了。
将八股文与古典小说戏曲进行比较,则不难发现,二者在文本组织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结构中的“照应”,明显受到八股文两两相对、前后相应的结构模式的影响;而八股文固定的三段式结构,正题前面必须有“起”(破题、承题、起讲),正题之后必须有“合”(落下、小收煞,大收煞),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前铺引文、后叙余韵”的“那辗”模式。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作者大多为科举士子,他们对八股文的常年习练,使得八股文两两相对的结构与起承转合的模式,直接渗透进小说和戏曲的文本组织形式中,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二) 诗词的对偶体式
中国古典诗词都十分讲究对偶的使用,而元曲(以及其后的明清戏曲)作为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最重要的诗歌形式,自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中国古典戏曲不但在唱词上重视对偶,而且在情节、人物等多方面采用了对偶式的结构。以《西厢记》为例,其中的大多数唱词如“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碧云天,黄花地”等,都是明显的对偶句,而前述“此来彼来”、“两近两纵”、“实写虚写”则属于情节上的对偶,莺莺与张生(才子与佳人)、莺莺与红娘(贞静与活泼)、张生与郑恒(才子与小人)等则构成人物形象上的对偶。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在语词上虽不如戏曲使用的对偶多,但每回均以对偶句作回目,类似骈文,而且在情节、人物、场景等多方面均采取对偶式结构。以《水浒传》为例,金圣叹在第四回总评中指出:“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仿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43页。这段话清晰地揭示了“鲁十回”与“武十回”在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等各方面的对偶式结构。又如《红楼梦》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这里不仅是言辞的对偶,而且也是人物形象(黛玉、宝钗)、故事情节(轻快的游戏与善感的饮泣)、文学典故(杨妃、飞燕)的对比。毛宗岗论《三国演义》的结构章法时,就多次强调对偶这种美学原则。他说:“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如昭烈则自幼便大,曹操则自幼便奸;张飞则一味性急,何进则一味性慢。议温明是董卓无君,杀丁原是吕布无父。”*罗贯中著,毛纶、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第7页。不但人物有对偶、情节有对偶,思想观念也有对偶。如《红楼梦》中的真与假、色与空、盈与亏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诗词的对偶体式,是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结构上的“照应”模式的主要渊源。这种体式,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架构的中心原则;而对这种体式的关注和评价,也已成为中国古代诗文评点的重要内容。
从比较诗学的观点来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偶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段,都是“相邻的短语或句子通过语法结构的对称关系实现意思上的对仗或反衬效果”。*艾布拉姆斯: 《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等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页。然而,与西方对偶强调双方的对立或主从关系不同,中文对偶强调的是一个自足整体中互补的两面。在“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divine”(凡人多舛误,惟神能见宥)中,“人”与“神”是对立的两极;而“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说的则是同一个道理的两面。一个是“二元对立”,一个是“二元互补”,显示了中西方对偶的同而不同。
(三) 史蕴诗心的史家笔法
中国悠久的史传文传统,也是作为“稗史”的章回小说和古典戏曲组织文本形式的一个重要参照。章回小说和戏曲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演义,许多人物、情节皆取材于史实,结构技巧也明显取法于史传文。早期的史传文,是更早的记言记事之史的注释,如《左传》是对《春秋》的解释和说明。这一体例决定了史传文必然将重点放在对某一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叙述上。例如,《春秋》“隐公元年”中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要解释《春秋》中的这一句话,就必须先回溯此前发生的事,再说明这件事造成了哪些后果。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弄引法”、“獭尾法”,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那辗”,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仍以《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为例,如果采用金圣叹的话语,《左传》的叙述方式也可以称之为“那辗”之法。它将“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简单情节“那辗”出“前、中、后”三截,又将前后两截“那辗”出“前之前、前之中、前之后”、“后之前、后之中、后之后”,因而洋洋洒洒写出“一大篇”文字。郑伯克段之前为“前”,而此“前”又可分为前之前——庄公寤生,惊姜氏,致使姜氏偏爱小儿子段;前之中——姜氏为段请制,请京,段屡次做出违背礼法之事,祭仲、子封、公子吕多次提醒庄公;前之后——大叔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庄公曰:“可矣!”但具体到郑伯克段这件事,因《春秋》中已经说过了,就说得很简略,正如金批《西厢》所说“其中间全无有文”。但郑伯克段之后,则又有后之前——庄公置姜氏于城颍,语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后之中——颍考叔巧言劝谏,令庄公回心转意,并提出“掘地及泉,隧而相见”的妙策;后之后——庄公依计行事,与姜氏和好,遂为母子如初。这种叙述格局与前述《西厢记》的“前候”一折何其相似!事实上,这种叙述格局普遍存在于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与史传文之间的强互文性。
联系西方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缀段”的讥评,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种互文性。作为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历史著作必然呈现为缺乏因果联系的一个个单独的事件单元。但中国传统的史传文又并非“止于叙事而止”,与那种“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246页。的官修史书不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是“才子之书”、“文人之事”。这类历史著作虽仍以“事”为基础,但重在“文”而不在“事”。“事”只不过是“文”的材料,“文”赋予“事”以形式,也赋予“事”以意义。如前所述,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天道自然,人事周流,万物都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的,因而本来无事可叙。之所以要叙,乃是为了通过对事件的叙述,揭示“事”背后深刻的道理,表达记事者内心的“志”。经过叙述者的“以文运事”,看似散乱无联系的事件就围绕着作者之“志”被串在一起,形成一篇完整的“文”。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照应”模式与此如出一辙。《三国演义》所写的魏蜀吴三个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其中大部分事件在情节上是分立的,但这些事件串在一起,却体现了作者“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观、“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人生观以及呼唤仁德爱民的贤君的政治理想。
(四) 阴阳对立互补的文化观念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考察,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那辗”与“照应”,则源于由《周易》开启的以阴阳对立互补为基本内涵的“二元补衬”(complementary bipolarity)和“多项周旋”(multiple periodicity)的思维原型。*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第95页。“二元补衬”指的是中国文化里“阴阳”、“盈虚”、“涨退”等概念的对立,“多项周旋”指的是各种源自于四时循环顺序的现象,如何能推演成五(阴阳五行)、十二(地支、十二生肖)、六十四(卦)等数目的演化模式。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正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诸子集成》第三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4年,第26页。道是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的“道”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 阴气和阳气,阴阳二气相交产生新的事物,万物都由此生成。万物都背阴而向阳,并在阴阳二气的对立消长、相生相克中,得以和谐发展。这一发展遵循着纵横两条路径: 就纵向而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着信(伸)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周易正义》,第304页。是“日”、“月”,及“寒”、“暑”在序列组合中顺序呈现,塑造了万物生生不息的外在形状,正所谓“生生之为易”。*《周易正义》,第271页。就横向而言,万物皆以“通变之为事”*《周易正义》,第271页。,求变是万物的本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正义》,第300页。变的根源在于事物内在的矛盾,即“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周易正义》,第261页。、“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孔颖达正义云:“刚柔即阴阳也。论其气即谓之阴阳,语其体则谓之刚柔也。”*《周易正义》,第294页。阴阳是万物内部本来就有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约的力量,万物就在这两种力量的不断消长中,不断运动和发展,并在运动与发展中成就了万物内在和谐平衡的生命性态。这种二元对立互补而又不断生发变化的观念,体现于我国传统戏曲和明清小说的文本组织形式上,就是以“那辗”和“照应”为基本特点的“文文相生”。
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文文相生”,就是前文与后文、此文与彼文的互相生发。由生发而产生新文,即“那辗”;而相互生发的前文与后文、此文与彼文,往往构成了冷与热、明与暗、生与死、离与合、悲与喜、盛与衰的对照,即“照应”。如前所述,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各事件单元之间常常缺乏密切的因果联系,它们常常是由一个中心事件“那辗”而来,而将这些事件单元组织到一起的,是它们之间的“照应”关系。以《水浒传》为例,不但楔子“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可以完全删掉而不影响后面梁山故事的讲述,即便是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的故事,如果单从情节进展的角度来说也可有可无,二者皆属“那辗”而出的文字。但从文本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与后文形成了鲜明的“照应”。金圣叹曾盛赞《水浒传》开头一首诗的后两句“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是“好诗”,因为它使得“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 《水浒传》,第1页。太平与动荡,正如阴阳两极,在二者的相生相克中,才产生出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故事。而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王进的故事,也具有明显的对照意义: 高俅来,王进去;王进去,史进来。奸臣当道,则忠臣离去;忠臣离去,则天下大乱。王进既与高俅相对(忠臣与奸臣),又与史进相对(王道与史籍,理想与现实),彰显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总之,以当代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为参照,“文文相生”作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的文本组织形式,可以从“内互文性”和“外互文性”两方面来加以考察。就“内互文性”而言,“文文相生”呈现为“那辗”与“照应”两种基本形式;就“外互文性”而言,“文文相生”与八股文的程式作法、古典诗词的对偶体式、史蕴诗心的史传文传统以及阴阳对立互补的文化观念,都有着深层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