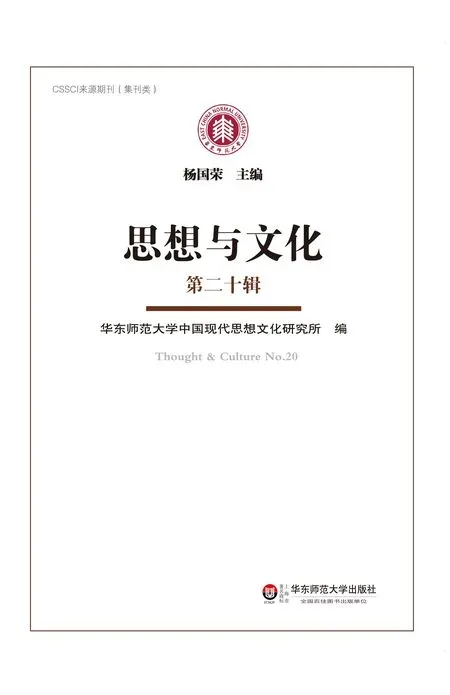儒学与启蒙思想之关系再议*
——以朱子哲学为中心
●
作为儒学的“集大成”形态,朱子哲学是特殊的“历史世界”(余英时)和“思想世界”(田浩)造就的。它形成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政治、思想、学术与话语的纷争。之后,在包括皇权、思想与学术团体的共同历史合力作用下,朱子哲学逐渐被推到儒学“正统”、“权威”的位置上,在帝制后期成为一种具有“宰制性”的话语力量。考虑到政治语境和思想脉络的嬗变,在解读和评价朱子哲学时,有必要对“原始朱子哲学”和“学派化朱子哲学”、“制度化朱子哲学”进行适当的形态学区分,由此激发朱子哲学的潜能,并将其融入当下迫切的时代问题、哲学问题之讨论中去,重构其因应现实的思想活力,使其成为一种建构性思想力量。——这是朱子哲学之意义再造的基本路径。
探讨朱子哲学的当下“相关性”(relevance),一种跨语境的参照是非常有益的。个中原委并不难寻绎: 首先,在由不同时空构成的思想脉络中,朱子哲学的何种潜能能够通过“再脉络化”而呈现出来,这本身即是耐人寻味之处。海外儒学研究之所以会成为近些年文史领域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原因即与此息息相关。*此处所言“跨语境”(或曰“去脉络化”)除了应关注欧美、日、韩、越南的历史文本外,亦应关切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跨语境”问题。唯限于篇幅与题旨,本文不拟展开。其次,依据一种宏阔的理论视野,朱子哲学的当代重构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其哲学意义的发生有赖于来自不同背景(语言、思想、文化)的人士的对话与交流。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国际知名哲学家的参与,成为朱子和儒家哲学自我敞现、自我丰富的直接契机。
在朱子哲学与西方近现代思潮的关系问题上,朱子理学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的关联得到的关注最多,然而亦最为聚讼纷纭。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从理论文本和历史环节两个层面追索朱子理学思想对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成为研究的主流。这一研究路数的潜台词是,只要找到充分的文本相似性证据,并挖掘出启蒙思想家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理学促生因素,就可以证成朱子理学对启蒙运动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理论文本对照时的钩玄提要,以及历史环节的探赜索隐毕竟是有限度的,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这一聚焦“影响研究”的研究模式已逐渐丧失其阐述的效力。这并非意味着这一话题已经得到了穷尽式的阐明。
实际的情形反而是,朱子理学思想与启蒙运动之间并非首先是一种简单的“历史-文本”层面的影响关系,而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深层契合关系。在耶稣会士(Jesuit)等天主教传教士引介、传递到欧洲的芜杂的、甚至不可靠的中国思想文本中,启蒙思想家们敏感地意识到其中与当时时代具有精神关联性的方面,并心领神会地做出了深具穿透力的思想阐发。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思想的“重构”。从“历史-文本”层面挖掘启蒙思想家思想中的理学因素,不仅容易遮蔽二者关系的真相,而且,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引导人们留意的主要是历史中的偶然性细节,容易将启蒙思想家的“重构”视为一种过去时态的昙花一现,而这一“重构”乃至朱子理学思想与我们当下时代的关联性连带着也被忽视了。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首先追溯并反思194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在此议题上的诸多论述*国外学界亦有几篇综述性的论文,如: (1)陈荣捷: 《欧美之朱子学》,日文版、中文版1974年发表;增订英文版“The Study of Chu His in the West”,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6(30)4;此文之中译《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第5辑,1981年;最后,增订补述版收录于《朱学论集》,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2)田浩(Hoyt Tillman): 《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江宜芳译,《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3年第4期;《北美的宋代儒学和朱熹研究之演变——六十年回顾》,《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2期。(3)吾妻重二: 《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最近的情况》,《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6卷第1号,1996年,后收录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杨立华、吴艳红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4)司马黛兰(Deborah Sommer):“Recent Western Studies of Zhu Xi”,吴震编: 《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之后依照一种“接受研究”而非“影响研究”的思路,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为例考察启蒙思想家通过重构儒家思想来因应时代课题的致思努力,继而探讨朱子哲学在当代之意义生成的可能路径。本文的探讨,贯彻了一种“批判性现代重构”的整体思路,这是一种哲学式的研究进路,但它并非要忽视朱熹思想与启蒙思想双方各自的“历史世界”,而是旨在兼顾人类普遍兴趣和各自文化之本真性。
一、 “影响”抑或“接受”——两种诠释路径
伴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欧洲启蒙运动与儒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已经得到比较充分地说明。就学术发展与成熟时间而言,汉语学界中的这一研究领域相对落后于欧美和日本的相关研究。对于汉语学界来说,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利奇温(Adolf Reichwein, 1898-1944)、毕诺(Virgile Pinot)、马弗利克(Lewis A. Maverick)、艾田蒲(René Étiemble, 1909-2002)、劳端纳(Donald F. Lach, 1917-2000)、后藤末雄、五来欣造、小林太市郎等人是先行者。这些学者的论著为复原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与思想场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具体到朱熹理学思想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关系,学界的论述就不那么清晰了。总体来看,大陆学界的相关论述以挖掘和强调朱熹理学思想对启蒙运动的正面影响为主线,比较晚近的研究才逐渐步入以“接受”为线索的学理分析。接下来,笔者分别以“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为焦点,梳理大陆学界的一些代表性论述。需要指出,笔者关注的论著,有的并非专以“朱熹理学与启蒙思想的关系”为限,而会延伸到诸如德国古典哲学(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李约瑟,乃至最近二三十年的西方朱熹研究成果。
(一) 第一类: 以“影响研究”为线索
在汉语学界,真正能与欧美、日本学人成果媲美的早期汉语论著是朱谦之(1899—1972)先生1940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尽管1985年此书增补修订本更名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但是,不变的是“影响研究”的学术进路。此书新版第二章“中国哲学与启明运动”讨论了“宋儒理学传入欧洲的影响”,朱先生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观念部分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在当时,欧洲主流意见认为理学是无神论,即便笛卡儿“中派”之马勒伯朗士(Nicolas de Malebranche, 1638-1715),亦强调“理”与“神”之异。于是,在倾向于无神论的“一般知识界人士”那里,“理学”成为他们启蒙运动的“旗帜”。朱谦之敏锐地意识到,“在18世纪法德学者,无论反对或欢迎中国哲学的人,都是以宋儒的‘理气说’来做对象”。*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在他看来,宋儒理学能够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歪打正着”的产物: 欧洲人“在接受原始孔家的时候,宋儒理学也夹带着接受过去了”。*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01页。在德国,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对“理气”说有过直接的辩护,而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被哈雷大学驱逐的非凡遭际反而使得“他的哲学更为有名,甚至于支配那个时代了”;甚至像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这样的古典哲学家,也因为与沃尔夫的师承关系,而“可能间接地受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理学的影响”。*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52页。朱谦之清楚地分析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中国哲学知识的来源,但是并不以中、西哲学理论的细致比照作为重中之重。要而言之,朱谦之将西方哲学家关于理学的正、反两极评论,都视为理学的“影响”。
尽管朱谦之的某些说法因为过于坐实而夸大了理学对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其论说的博洽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最早确立了“影响研究”的阐述范式,而其起点之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为多数后来人所难望其项背。
时间一跃而至1991年,傅璇琮、周发祥发表《西方的朱熹研究》*孙钦善等主编: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8—449页。,主要依据陈荣捷先生《欧美之朱子学》一文所提供的材料,而做出较朱谦之远为审慎的立论。《西方的朱熹研究》提及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 )为代表的“理学派”,并称许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傅、周两位并非朱子专家,故此文仅有文献学之存目价值。
在此之后,1996年程利田发表《朱熹理学思想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程利田: 《朱熹理学思想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兼论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作用》,《学术论坛》1996年第2期。,同年林金水、谢必震所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第四章“明清之际来闽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之第六节“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林金水主编: 《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6—305页。,2004年张品端发表《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张品端: 《朱子理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2004年张允熠发表《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张允熠: 《论朱熹哲学的世界历史意义》,《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以及2011年徐刚发表《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以莱布尼茨、李约瑟为例》*徐刚: 《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朱熹理学因素——以莱布尼茨、李约瑟为例》,《东南学术》2011年第4期。,都延续或重复了朱谦之的“影响研究”路数,多依据常见的中文资料,辗转授受,都无法达到朱谦之的研究水平。有的论者立论孟浪,如张允熠认定朱子哲学亦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中重要的思想来源与材料,则显属推论无度。
在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关系问题上,2010年陶秀璈发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中国思想元素》*陶秀璈: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中国思想元素》,《“当代欧美汉学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以罗哲海为中心”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国语大学,2010年5月。,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形成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2011年谢文郁发表《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谢文郁: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亦认为形成康德思想的17—18世纪欧洲思想界弥漫着“一股强劲的中国文化热;康德不可能不受到这股热潮的感染”。两位作者都注意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称呼康德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这一有趣历史细节。虽然他们没有强调朱子哲学的影响,但考虑到17—18世纪传教士译介孔孟原始儒学思想时多借重朱熹的经典诠释,要证成朱子哲学对康德的影响似乎也只有一步之遥。
从其学术愿景来看,这种重视“影响”、带有“索隐”性质的致思路径显然是诱人的。然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因素中进行探赜索隐、钩玄提要,毕竟是有限度的。而且,这种索隐派做法很容易流于一种挟洋自重的民族主义心态,而导致新的自我封闭,从而错失进一步挖掘朱熹哲学潜能并与西方展开哲学思想对话的新机遇。
(二) 第二类: 以“接受研究”为线索(并不限于启蒙思想)
跟“影响研究”相比,“接受研究”是一种较为晚出,然而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范式,它实质上并未抛弃“影响研究”所关注的从“始端-因”到“终端-果”的思想授受关系,但它是通过聚焦于接受者这一主体而展开探讨的。在这种范式看来,接受者是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存在,接受者有相对的完满自足性。正因为接受者是丰富复杂的,所以接受者对某一种思想的接受过程也是丰富而复杂的。而对这一丰富而复杂的接受过程的揭示、阐明,本身即是对一个丰富而完满的思想世界和历史世界的揭示。需要说明的是,“接受研究”并非要把对于“影响—接受”性质和成果/后果的价值判断问题悬置起来,或者是要迂回地取消这一问题,而是要赋予这一价值判断以更丰富的历史性内涵,因而在根本上是一种积极的回应策略。总之,“接受研究”因为能够揭示更为丰富、更为多层次的思想(史)面貌,故而以其学理性常常给人更多启示。
在这一路向上,值得提及的论著包括: 2010年陈嘉明发表《朱熹研究在西方》*陈嘉明: 《朱熹研究在西方》,《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集刊》第二辑,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第86—94页。、2011年卢睿蓉发表《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卢睿蓉: 《美国朱子学研究发展之管窥》,《现代哲学》2011年第4期。、2012年彭国翔发表《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彭国翔: 《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同年黎昕、赵妍妍发表《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黎昕、赵妍妍: 《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以及2013年张柯发表《德文语境中的朱熹思想——对朱熹思想之德语接受史的考察与反思》*张柯: 《德文语境中的朱熹思想——对朱熹思想之德语接受史的考察与反思》,《孔子研究(学术版)》2013年第3期。。
陈嘉明在陈荣捷文章的基础上,提到1980年以来Oaksook Chun Kim、艾周思(Joseph Alan Adler)、唐格理(Kirill Ole Thompson)、金永植(Yung Sik Kim)、区建铭(Kin Ming Au)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但止于绍介它们的主要内容,而没有深入分析和判论。
卢睿蓉和彭国翔的论文除了介绍新出文献外,特别留意“比较宗教学”或“精神性研究”领域,认为朱子哲学与西方神学的比较与会通仍然是朱子哲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在现在以及将来仍具有阐释空间。而黎昕、赵妍妍的论文有志于研究海外(包括日本)朱子学研究的“二阶”(second-order)问题,亦即重在发掘其方法论。在作者概括出的五种研究方法中,“义理分析”、“文化思想比较”和“体认式”三种方法都与哲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而于“文化思想比较”一路举了白诗朗(John Berthrong)和秦家懿(1934—2001)的例证,要之,二人所关注的朱子思想之宗教性,亦回应了两百多年前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的核心关切。
张柯的论文亦有其概括出的德国学术“着重于研究哲学问题本身和追问思想自身的意义”之倾向。莱布尼茨把“理”解读为“隐德莱希(Entelechie)”,就是发现了二者同样具有二重性意义: 整体(存在自身)的实现与个体(存在物)的实现。张柯认为莱布尼茨的这种解读极为深刻,“远远超越了我们的期望”。“正是基于这种宏阔而深邃的思辨视野,莱布尼茨不可思议地把握住了让其本己思想与东方思想发生深邃共振的关键契机。”*张柯: 《德文语境中的朱熹思想——对朱熹思想之德语接受史的考察与反思》,第106页。张柯还引述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晚年论述莱布尼茨的一段话*海德格尔:“若我们想得足够深远的话,就可以发见到,莱布尼茨的思想承载着和烙印着近现代形而上学的主要趋向。因此,在我们的沉思中,莱布尼茨这个名字并不代表着一种过去的哲学体系。这个名字命名着一种思想的当前,这种思想的力量还没有消逝,而这种当前,我们还有待于与之相逢。”(Der Satz vom Grund, GA. 10),抑或以此暗示朱熹哲学的思想意义亦有待于我们与之相逢。
除了上述分别从“影响”和“接受”进路考察朱子哲学与启蒙思想关系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论著致力于朱子哲学与启蒙时期哲学家(不限于启蒙运动阵营内部)的比较研究。笔者在此仅举两个较早的例子: 1930年贺麟(1902—1992)《朱熹与黑格尔太极学说之比较观》*贺麟: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学说之比较观》,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1942年庞景仁(1910—1985)《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Jingren Pang: L’idée de Dieu chez Malebranche et l’idée de li chez Tchou Hi, Paris: J. Vrin, 1942. 中译本,冯俊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这两部论著都形成于作者在国外求学时期,尽管它们仍有点稚嫩,基本上是平行地比较异同,理论深度上有所欠缺,但是两位作者却由此具备了较为宏阔的理论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可以说,这些论著的写作为他们自身哲学生命的“点醒”与自觉打下了基础,并为他们学术生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二、 “他乡”有夫子——欧洲启蒙运动中的朱子哲学
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末进入中国,很快他们就敏感到理学的所谓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在研读理学文献时发现,理学聚焦的“理”、“太极”等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并不重要,而原始儒学经常提及的“上帝”、“昊天”在宋代理学那里已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格神含义。在耶稣会士们看来,理学家们歪曲了原始儒学的教义,而这种歪曲又跟佛教的影响息息相关。所以,即便提倡“适应”(accommodation)政策的耶稣会士,也强调区分原始儒学和宋代理学,并做出厚古薄今的价值评判。
然而,不管传教士们如何排斥朱熹,他们在译介先秦原始儒学材料(主要是“四书”)时,却无法绕过朱熹的诠释。耶稣会士的“四书”译介,一般都首选张居正(1525—1582)的《四书直解》作为主要底本*参考Knud Lundbaek,“Chief Grand Secretary Chang Chü-cheng & the Early China Jesuits”以及David E. Mungello,“The Jesuits’ Use of Chang Chü-cheng’s Commentary in Their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Four Books (1687)”, in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50-1800) Bulletin 3 (1981),pp.2-11,12-22.,以往关注此问题的论者多倾向于夸大作为汉学的《四书直解》与作为宋学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间的差异,实则前者基本只是后者的一个通俗版白话译本,二者体现的思想没有多大不同。*传教士选用张居正《四书直解》,或许真的有扬汉抑宋的倾向。关于这一扬汉抑宋倾向,举一个例子: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在译介《孟子》时,就有意弃用朱熹的解释,而选用“最新最好的诠释著作”——焦循(1763—1820)的《孟子正义》。他认为焦著虽然后出,但采用赵歧(约108—201)的古老注释,这一点正与朱熹相反(朱熹将佛教哲学引入了他对孟子的解读中)。见Ernst Faber, The Mind of Mencius; or, Political Economy Founded upon Moral Philosophy: A Systematic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Mencius, trans. Arthur B. Hutchinson, London: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 1882, “Preface”. 但是,这不等于说《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直解》这样的经典诠释著作在思想或精神上存在多么大的差异。实际上,传教士选用《四书直解》,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浅显易懂。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等人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 1687),选译的是《四书直解》中的《论语》、《大学》和《中庸》三部分,译者有意无意对“命”、“性”、“教”等重要概念做了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意义上的“经院神学化”(Scholastic theologizing)处理*可参考梅谦立(Thierry Meynard): 《〈孔夫子〉: 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理性”与“信仰”的统一成为其潜台词。而卫方济(Francis No⊇l, 1651-1729)独立完成的《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imperiilibriclassicisex, 1711;包括“四书”以及《孝经》和《小学》)则因为有意加入更多朱熹的注释而更贴近朱熹。*参考黄正谦: 《论耶稣会士卫方济的拉丁文〈孟子〉翻译》,《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2013年第57期。尤需指出,柏应理、卫方济“四书”拉丁译本所传达出的思想意味的差异,并不能说明翻译所依底本也存在这种差异。总体来看,传教士们身处宋明理学的笼罩性影响之中,可以说,朱熹是他们译介儒学的主要“中介人”。
如众多论者已经注意到的,传教士之间以及阅读传教士所译介儒学资料之后的欧洲哲学家之间辩论儒学是否为“有神论”,往往聚焦于“天”、“上帝”、“理”、“气”、“太极”等概念,显而易见的是,“理”、“气”、“太极”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朱熹宇宙论的核心内容。由于汉语和拉丁语概念内涵的不对应性,以及跨文化理解的脉络偏差,完全对等的翻译和对话是无法实现的,“译名之争”亦源于此。不过,于彼时的辩论参与者而言,具备思想意义的并非是几个术语概念的词义辨析,而是这些概念的思想指涉。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大部分启蒙思想家们所依据的译介材料并不是非常可靠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由此做出了很有意义的思想阐发。笔者以为,在他们之中,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二人尤其值得再次回顾。
学界一般认为,沃尔夫是莱布尼茨哲学思想的继承者,治早期中西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的学者也多认为沃尔夫在重要性上依附于莱布尼茨。*如张西平: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413—470页。但如果充分留意莱布尼茨和沃尔夫在接受儒家经典方面的不同文献来源,则二人之间的细微差别便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彰显。以下试为申说之。
作为17世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几位理性主义者之一,莱布尼茨对中国投注了以往欧洲思想家少有的热情。他编选的传教士文献《中国近事》(NovissimaSinica:Historiamnostritemporisillustratura)出版于1697年,而1716年初于去世前完成的《致德雷蒙先生的信: 论中国的自然神学》(LettreàM.deRèmondsurlathéologienaturelledesChinois)则是一篇阐述其中国哲学认识的长文。要而言之,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主要是在形而上学与宗教方面”*见秦家懿: 《论莱布尼茨与沃尔夫》,《秦家懿自选集》,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他从“自然神学”(Deism)立场出发,发现儒家的“理”、“太极”等概念本身即是合乎理性的,站在“上帝跟理性是合一的”或“上帝是理性的化身”这一理性主义视角上,很容易得出“中国人是信神的”这一结论。在启蒙时代的欧洲,莱布尼茨主张欧洲的启示神学应该辅以中国的自然神学,所以,具有启示信仰的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此点在孟德卫、秦家懿等中外学者那里已得到充分论述*参考孟德卫: 《莱布尼兹和儒学》,张学智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文潮、H.波塞尔编: 《莱布尼茨与中国: 〈中国近事〉发表3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2年;张西平主编: 《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郑州: 大象出版社,2010年。,兹不添赘。
式中:Roj表示经典域物元,Noj表示所划分草原生态安全的第j个评价等级,j=(1,2,…,n);Ci表示第i个评价指标;(aojn,bojn)表示对应评价等级j的量值范围,即经典域。
沃尔夫也是一位中国文化爱好者*Donald F. Lach,“The Sinophilism of Christian Wolff (1679-1754)”,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14, No.4,1953, pp.561-574.,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主要体现在1721年交接哈雷(Halle)大学副校长一职时发表的演讲《关于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OratiodeSinarumPhilosophiaPractica)。与莱布尼茨不同,沃尔夫本人虽非无神论者,但有极强的无神论倾向。他从“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德性与世俗的行为规范)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直言“我们所推崇的孔子之诚”是那些虔敬派神学家“全然不懂”的。*沃尔夫: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李鹃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沃尔夫在儒家哲学中发现了类似斯多葛学派(Stoics)的大、小宇宙至善论,他认为中国人的行为或德性准则完全合乎自然与人心的理念,从未尝试过违背自然的事。与信仰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的人不同,古代中国人“不知道创世者、没有自然宗教,更是很少知道那些关于神圣启示的记载。所以,他们只能够使用脱离一切宗教的、纯粹的自然之力以促进德性之践行”;因此,“所有试图从中国人那时找到超越此种德性者的举动,都是无谓的。所有以超越自然之力者加诸中国人的做法,都只是证明了他对哲学德性、哲学虔敬以及基督教德性间最大差别的无知”。*沃尔夫: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第69、74页。一句话,中国人其实是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论者。
在解读儒家思想时,莱布尼茨强调“自然神论”,沃尔夫则突出“自然理性”,二人得出的结论实则大为不同。之所以如此,除去二人哲学倾向的差异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理解中国哲学时所依据的文献不同。莱布尼茨接触的中国文献较多,既有耶传教士寄回欧洲的大量报告、信函,又有来华耶稣会士在欧洲出版的论著(亲适应路线和反适应路线的著作都有),其中相关一部分都聚焦于儒家信神与否。他还跟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来华传教士有较多过从。可以说,莱布尼茨是一位中国问题的及时跟进者,对于传教士及欧洲哲学家们对“理”、“气”、“太极”等概念的最新辩论,他心知肚明。而在中国文献译本方面,他依赖的是柏应理整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早期耶稣会士适应路线的集大成译作,以一种经院哲学的眼光来挖掘孔子“三书”中的上帝信仰遗绪,强调理性天性(natura rationalis;或“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对人自身德性的开启作用,是其特色。莱布尼茨本来就对耶稣会的适应路线颇多同情,他敏感到儒家“四书”(实为“三书”)的神性倾向,并糅以自己的理性主张,以一种理性化的自然神论来看待理学思想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沃尔夫理解中国哲学的途径较窄,几乎全赖卫方济的《中华帝国六经》译本。跟柏应理等前辈相比,卫方济在儒学重点哲学词语的翻译方面表现得更有学理。比如说,在朱熹和张居正的“四书”诠释中,“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卫方济将“理”译为拉丁文ratio。ratio源自希腊语λóγο(logos),本意是“比例”,但其意义远超过数学本身;在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斯多噶派的古典哲学中,它具有“神性”的涵义,指涉一种至神、至善的存在,至中世纪前期,ratio仍然指称“正义之理”(recta ratio)。就此而言,朱熹之“理”与ratio确乎有相当多的指涉交集。只是愈到后来,ratio的“理性”含义愈加突显,越来越多是指人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在卫方济所处的17—18世纪,ratio一词多被用来指不相信启示真理的理性主义。在此背景下,卫方济以ratio对译“理”,就会把包蕴丰富的“理”囿固为理性、智性,汉字“理”中原来具有的神性、德性涵义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而沃尔夫恰恰就是依据卫方济译本而进入儒学大门。他几次坦承:“我写这篇演讲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因而也就没读过柏应理的‘绪论’。当时我手头上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献就只是卫方济翻译的拉丁文版《中华帝国经典》。”“在我作此篇演讲时……我之前还没有看到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他更反复明确指出,卫方济译本“与巴黎版本差异颇大。但我认为卫方济译本较之更为可信”。*沃尔夫: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第70、93、106页。卫方济译本强烈的伦理学倾向深刻影响了沃尔夫的中国认知,后者所称许的“实践哲学”其实就是儒家的伦理学。沃尔夫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人主张人自身拥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自主理性,他称这种自主理性为“自治的原则”(相对于“为恐惧上司或追求报赏而行善”这种“他治”原则),“尽管有德性的行为是通过身体被完成的,但德性却住存于心灵”,并且中国人“将目光聚向人心之完满”,追求至善,“中国人首先强调的便是,要正确地养习理性,因为人必须获得对善恶的明确知识,从而才无需因畏戒长上、希求长上奖赏而致力于追求德性”。*沃尔夫: 《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第112、74、106页。
莱布尼茨、沃尔夫二人对中西共通哲学视域的开掘,以及他们这种开掘所蕴含的哲学与思想史意义,仍然值得我们玩味。前引张柯之文已经点明,莱布尼茨把“理”解读为Entelechie,于是不期然地、甚至“不可思议地把握住了让其本己思想与东方思想发生深邃共振的关键契机”。而对于沃尔夫来说,他把“理”解读为ratio,亦从“自然理性”的人文主体性角度慧眼独具而心领神会地扪摸、洞察到了儒家道德人类学与启蒙时代思潮“深邃共振”的关键所在。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的一个看法:
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亲华学者而言,往往招人非议的是,他们所从事的对声名渐起的中国文本的讨论是基于糟糕的译本的,在哲学上并不可靠,更多的是以投射而不是科学研究为基础。这当然是事实,不过在其后世纪中在材料上广博得多的汉学知识并没有颠覆这些缺乏根基的判断。不过,在我看来,沃尔夫确实成功地达到了一种辩护式的、心领神会的释义,这种释义优于其后黑格尔和韦伯对儒家思想的流传更广的他治论解读。他的许多表述读起来像是对儒家伦理真正核心理论的直接改写。*罗哲海: 《天命的内在化: 论儒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哲学与宗教”(Philosophie und Religion)中德学术会议论文,柏林自由大学,2017年07月15日,http://philosophie-religion.de/tianming-de-neizaihua.html。
这一现象让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评价: 一个真正的思想家能够借助那些并不充分的历史学报道辨认出本质性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他作为思想者和追问者自始就切近于有待思想和追问的东西了——这是一种无论多么精确的历史学科学都不能达到的切近”。*海德格尔: 《尼采》,孙周兴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7页。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思想家。
三、 “批判性现代重构”: 朱子哲学意义的当下生成
“批判性现代重构”的提法借鉴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的“理性重构”说。法兰克福学派向来以其“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闻名。到1960年代,哈贝马斯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讨论“知识”,将“批判性知识”确认为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外的,以自我反思和解放(emancipation)为导向的认知与兴趣类型。*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与这种批判理论相关的哲学释义学,在方法论上是通过一种“理性重构(rational reconstruction)”来完成对批判性“潜能”的释放的。所谓“理性重构”,是指把存在于特定类型现象背后的那些普遍而不可回避的、然而尚未结构化的前提条件,通过明晰化、系统化的理论表述出来。它与智力的深层结构息息相关,其任务不是描述现实中所是的事物(“实然”),而是按照应该是的样子确立现实事物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应然”)。借助这种“重构”,一种前理论的实际知识(know how),可以整合到确定的理论知识(know that)中。
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站在了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顶峰,所以当下的朱子哲学研究也应该努力以“尖端的论述模式”来处理他的思想,挖掘其哲学文本所包含的广泛潜能,而“重构(Rekonstruktion)”显然就是这样一种从当代哲学、伦理学的高标准出发,以严谨态度来讨论朱子哲学的特殊方法论。汉学家罗哲海如此来界定“重构”的方法论:
“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瞿德瑜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页。另可参考: Heiner Roetz,“Gibt es ein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30. Jg., Heft 2, Mai 2002, p.31.
罗哲海将这种诠释学称为“批判性现代重构(critical modern reconstruction)”,并与安乐哲(Roger T. Ames, 1947- )等美国实用主义汉学家的“复辟/复原论”自觉划清了界限。“这种重构超越了那种仅仅满足于解释和对比的相对主义式做法,它关注的是共同的、跨文化的理解。”罗哲海认定,如此做绝非忽视了“中国独特性”这一互补性因素,而是致力于实现一种兼顾人类普遍兴趣和中国文化之本真性的“辩证解释学(dialectical hermeneutic)”。*Heiner Roetz,“Validity in Chou Thought: On Chad Hansen and the Pragmatic Turn in Sinology”, in Hans Lenk & Gregor Paul ed.,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SUNY Press, 1993, p.104.
依照这种“批判性现代重构”的方法论视野,朱子哲学的当代“重构”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比如说,在宗教对话领域,过去论者多关注朱子哲学/理学与阿奎那神学之间的比较,有的学者已意识到朱子哲学中身心能量、修养工夫、亲情孝道等内容可以丰富托马斯主义的理论*参考戴尔奥里欧(Andrew J. Dell’ Olio): 《朱熹和托马斯·阿奎那论道德自我修养的基础》,傅有德、斯图沃德等编: 《跨文化对话: 中国与西方》,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203页。;在当下,朱子哲学的精神性内核如何与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的过程神学、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的宗教神学、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 1939- )的“波士顿儒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如何与包括伊斯兰教、批判佛教在内的其他世界宗教进行对话,都有可能取得“重构性”的思想成果。
又如,在伦理学和个体修养层面,过去论者多比较朱熹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 1632-1677)、莱布尼茨、康德等西方哲人;在当下,朱子哲学中“诚”、“敬”的内在超验维度如何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世俗时代》*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提出的世俗时代之后重返“有神论”立场构成对话?*参考马恺之(Kai Marchal): 《超出世俗理性: 从泰勒(Charles Taylor)到朱熹以及牟宗三》,陈来、朱杰人编: 《人文与价值: 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朱子诞辰880周年纪念会论文集》,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52—574页。再如,朱子伦理学可以在与近些年兴起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德性认识论(virtue epistemology)的对话中收获哪些自我敞现与丰富的契机?*参考Stephan Angle: Sagehood: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9.
显然,这里列出的远不是对朱子哲学进行批判性现代重构的所有可能。
小结
本文追溯并反思了中国大陆学界考察“朱子哲学与启蒙思想关系问题”的两种致思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倡一种“批判性现代重构”的研究方法论,并借此方法论展望朱子哲学当下意义生成的可能途径。本文倾向于认为朱子哲学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概念与命题系统,而应是一个开放的、蕴含因应当下时代问题和精神困境的潜能的思想库。
笔者以为,儒学和中国哲学的当代诠释早已成为一项“跨文化”的事业。这一跨文化的问题意识与视野,赋予哲学对话以新的可能,而中国哲学的思想潜能借由哲学对话不断得以开显。汉语学界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真正哲学对话不应停留于某个具体问题,而应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哲学关切与方法论渊源。由此出发,我们在与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的思想对话、学术交流中方能真正做到“中的于现状,发言于心声”,而不至于因为深层次隔膜,而在批判地理解西方哲学/汉学思想时要么陷入盲目的“无的放矢”之窠臼,要么重蹈盲从的“汉学主义”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