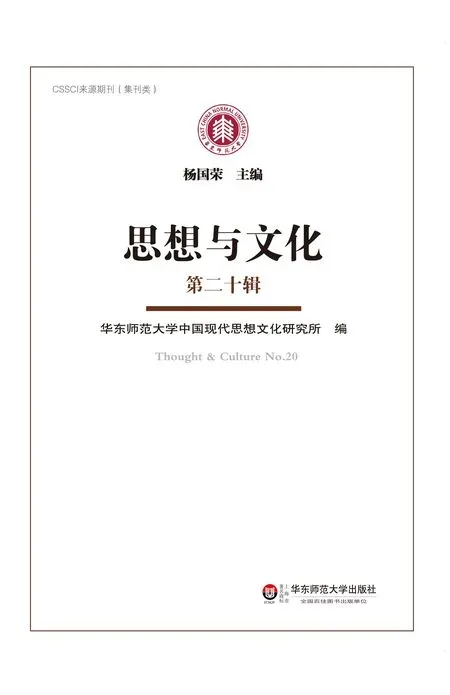重审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与现代启示
●
浪漫主义自20世纪初被引介入国内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和创作风格。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浪漫主义在文学中展现出中国化的独特一面。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和读者接受群对中国的浪漫主义存在着误解和偏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固有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优秀的前沿研究成果还没有被及时翻译进中国,语言障碍是进一步研究的绊脚石。因此,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还未得到恰当的评价。
而在西方学界,早已掀起一股重估浪漫主义的热潮。以赛亚·伯林、雅克·巴尊、施密特、蒂利希等很多学者纠正了不少传统研究和接受视野中对浪漫主义的误解。*详见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页。雅克·巴尊: 《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侯蓓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页。Carl Schmitt, Political Romanticism, trans. Guy Oak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6.保罗·蒂利希: 《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尹大贻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8年。近年来,学界开始了对中国的浪漫主义的重估事业。美国学者王敖、奚密,中国学者陈晓明、刘小枫等,对浪漫主义内涵进行探讨和厘清,对不同阶段浪漫主义给予新的评价,并对浪漫主义前景作出展望;由当下文学现状入手,回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脉络,重新审视被遮蔽或误解的一面。*参见奚密: 《早期新诗的Game-Changer: 重评徐志摩》,《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61页。王敖: 《怎样给奔跑中的诗人们对表——对于诗歌史的问题与主义》,《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48页。陈晓明: 《曲折与激变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历史变异》,《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第4—28页。刘小枫: 《汉语神学的释义学热情》,《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65—82页。
中国浪漫主义诗学发端于五四时期,几乎和启蒙理性同时进入中国,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著有《摩罗诗力说》,这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对浪漫主义诗学谱系的梳理。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美伟强力”。简言之,通过对强生命意志的张扬来构成诗学上的壮美景观,突破了启蒙理性范畴,达到新的美学境界,这不仅是对过往美学传统的颠覆,而且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乃至当代都实属罕见。鲁迅对这一美学范式的尝试体现在他的部分散文诗中,譬如复仇主题中所展现出的生命力的狂欢。在早期新诗中,能够真正体现鲁迅的这一宏大诗学构想的也许只有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尽管这一尝试很快就被启蒙大潮所淹没,但仍在中国文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小枫则认为:“汉语学界还老是记住启蒙与没有启蒙的事,不晓得20世纪的思想问题不再是启蒙以后,而是浪漫主义以后;不是康德以后,而是尼采以后。”*刘小枫: 《汉语神学的释义学热情》,《圣灵降临的叙事》,第74页。刘小枫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浪漫主义彻底改变了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影响了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给中国文学带来多元化的新的可能。站在国际学界的广阔研究视野中,反观当前学界对中国的浪漫主义的误解,我们有必要从浪漫主义的最初形态来重新审视浪漫主义的发展,发现其潜在价值,为中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正名。
郭沫若对浪漫主义自我意志的把握和展现,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开拓性作用,超越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诗人,创作出气象宏伟、图景广阔的诗歌。尽管因时代思潮的影响和自身思想的转向而浅尝辄止,但是这一尝试却时隔多年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子、昌耀、骆一禾等人的诗歌中产生回响,书写出“壮美”的文学图景,引领着精神向上的道路,成为新诗史上不可忽略的向标。
一、 强自我意志与壮美文学图景
郭沫若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浪漫主义“创造”理念的理解和再创造上。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创造”理念极力推崇,他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着重表示:“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on),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前者是纯由感官的接受,经脑神经的作用,反射地表现出来。就譬如照明一样。后者是由无数的感官的材料,储积在脑中,更经过一道滤过作用,酝酿作用,综合地表现出来。就譬如蜜蜂采取无数的花汁酿成蜂蜜一样。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属于后一种。”*郭沫若: 《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页。“创造”理念是浪漫主义的核心理念,源于基督教思想。我们知道,“创造”一词在基督教文化中,用于造物主上帝。上帝以其自由而强大的意志,创造了世界万物。而到了浪漫主义的时代,由于科学理性的发展,上帝被怀疑,宗教信仰受到动摇。再加上工业文明的兴起,人越来越工具化、功利化,对于人的灵性的思考被忽视。从而出现人类新的精神困境: 人如何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以往宗教为人们提供了通向永恒的途径,但是由于科技理性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的神圣性,宗教已经不能成为解决精神困境的唯一途径。因此,浪漫主义提出要建立一种“新宗教”,以实现人类对永恒的渴望,“这意味着浪漫主义哲学用审美直觉代替宗教”。*保罗·蒂利希: 《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第335页。也就是说,浪漫主义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在此过程中,自我代替了上帝,进而自我拥有了绝对意志。帕斯认为,在尼采之前,浪漫主义就宣布了“上帝已死”,自我意志成为新的绝对力量。*Octacio Paz, Children of the Mire: Modern Poetry from Romanticism to the Avant-Grad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pp.25-29.
一旦在诗学层面,自我意志取代了上帝,那么就涉及到浪漫主义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对于无限性的思考:“在尼古拉和路德的神秘主义思想——路德的神秘主义起初是公开的,但后来是隐蔽的——看来,上帝和世界是相互包含的。现代思想超越了晚期古代世界流行的神的领域在天上,人的领域在地上的狭隘二元论。……这意味着,有限不仅仅是有限的,而在某个方面它也是无限的,并以神作为它的中心和根据。……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原则是浪漫主义的首要原则,任何别的东西都依赖于它的。”*保罗·蒂利希: 《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第331页。浪漫主义的一切努力——想象、反讽、情感等——都是为了从人本身去找到通向无限的途径。“对无限的向往(Sehnsmcht)……对蓝色花朵的追寻。对蓝色花朵的追寻,是自我吸收无限的尝试,是自我与无限合一的尝试,也是自我融入无限的尝试。”*刘小枫: 《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8页。因此,浪漫主义对强自我意志的推崇,最终是为了突破一切对自我的束缚,达到无限性的精神状态,自我获得绝对的自由。这样一来,传统基督教视野中有限的不完美的自我,便可以无限趋向完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浪漫主义“创造”理念脱胎于基督教文化,也是对传统基督教思想的颠覆。
尽管中国相对而言缺乏深厚的基督教思想基础,这间接影响了郭沫若对这一理念的吸收和理解,但是他超越了同代作家所多关注浪漫主义的反抗性,以更锐利的眼光,洞察到了浪漫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已经将这一希望之光照亮了中国新诗,创造出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宏伟诗篇。
“创造”这一诗学理念不仅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核心,也缔造了创造社并成为其文学活动的宗旨。1922年创办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封面仅用颜体题名“创造”二字,不过,后来再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的封面上画了已怀孕的夏娃,正在凝望一艘已扬帆起航、准备环游世界的帆船,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创造世界”的寓意自不必多言。郭沫若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波斯诗人莪谟伽亚默》*郭沫若: 《波斯诗人莪谟伽亚默》,《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这一文章此前一直被学界视为郭沫若的译介文字,而并未加以重视。事实上,这一文章道出了《创造》季刊的发刊词《创造者》这一宣言背后的诗学体系——郭沫若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便系统阐释了自己的“创造”诗学理论的来源及建构。而郭沫若对形而上学层面的思考,代表着中国新诗的一种重要美学向度,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鲜有回应。郭沫若从对人生、世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出发,认为宇宙找不到其本源所在,形而上学假设的本质和宗教论提供的上帝都不能够提供满意的答案。在作为《创造周报》的创刊词《创世工程之第七日》中,郭沫若表达了对上帝造人的不满,因为“你最后的制作,也就是你最劣等的制作/无穷永劫地只好与昆虫走兽同科。/人类的自私,自相斫杀,冥顽,偷惰/都是你粗滥偷懒的结果”。*郭沫若: 《创造工程之第七日》,《创造周刊》第1期,1923年5月13日。上帝将人与走兽昆虫一并造出,人若不能认识到自我的价值,便与蝼蚁无异,而这一点正是郭沫若在《波斯诗人莪谟伽亚默》中借屈原、贾谊之口道出的。郭沫若强调:“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当人的心眼“睁开内观外察”时,会知道自身的有限性,想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性。郭沫若所欣赏的是歌德提倡的“泰初有业”:“宇宙自有始以来,只有一种意志流行,只有一种大力活用。”*郭沫若: 《波斯诗人莪谟伽亚默》,《创造》季刊,第1卷第3期。而从这种宇宙观所演绎出来的人生哲学,便是一种强大的自我意志力的施展,“犹如一团星火,既已达到烧点,便索性猛烈燎原,这便是至善的生活”。人一旦拥有强生命意志,便如造物主有了创造的力量。
然而,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成为造物主并不是指如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一般可以创造实际的万物,而是指“意志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切生命过程的普遍驱动力。康德、谢林、费希特的意志论对浪漫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促使了创造论的产生”。*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21页。在传统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的诗歌多是对外界世界的反映或自身心境的投射,却很少有以强自我意志构筑诗学世界的尝试。郭沫若所要表现出的诗歌是如他所钦佩的歌德那样,“对于宇宙万汇,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他的心情在他身之周围随处可以创造出一个乐园: 他在微虫细草中,随时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爱无私者底彷徨’。没有爱情的世界,便是没有光亮的神灯。他的心情便是这神灯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种种图画,再死灭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郭沫若“决定让我的内在自我任意地支配我”。*郭沫若: 《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第314页。
郭沫若在1936年的回忆性散文《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表达出他的创作动机:“在‘五四’之后我却一时性地爆发了起来,真是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这在别人看来虽嫌其暴,但在我深有意义的,我在希望着那样的爆发再来。”*郭沫若: 《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象火山一样爆发了起来”,是郭沫若在形象地表达强自我意志释放在诗歌中的状态。比如《天狗》中“吞月”、“吞日”、“吞宇宙的一切”*郭沫若: 《天狗》,《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0、54—55页。,也就是将万物都纳入自我的范畴,因而自我获得绝对的能量,摧毁一切阻碍自我的东西,只剩下绝对的精神层面的自由和至高无上的自我。再比如,《立在地球边放号》中,郭沫若通过外界事物的广阔壮大来展现内在强意志力的汹涌澎湃,“无数的白云”“怒涌”、“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无限的太平洋”,这些宏伟的景象是为了表现出自我意志的强大,以对“力”的强调的方式展现“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这些宏伟的自然景象和伟“力”实际上是强自我意志的外化和美学想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强意志力,才能够造就宏伟的文学图景。尽管郭沫若的尝试还不免有些幼稚和简单,但已经开拓出了一条新的诗学道路。
二、 浪漫主义自身逻辑的矛盾和郭沫若的思想转向
强自我意志在美学层面能够带领诗学走向自由和无限,创造出壮美的文学图景。浪漫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绝对自我和绝对意志,必然会与“群”的要求发生冲突。这里并不是说浪漫主义一味摒弃现实,而只注重美学层面的建设。实际上,浪漫主义想要介入现实和政治,但是一旦接触到现实和社会层面,就会存在绝对自我以外的原则和束缚,这会瓦解浪漫主义思想的根基。这是浪漫主义自身逻辑的矛盾所在。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感时忧国”意识颇为普遍。*详见夏志清: 《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1—462页。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亟待重建的状态,都使得文学家不得不面对社会和历史现实。这就使得浪漫主义“我”与“群”的张力这一基本母题在现代中国尤为突出。
前面提到,浪漫主义的无限性是有其宗教背景的。而缺乏宗教文化基础支撑的郭沫若的“创造”哲学,在20世纪早期中国激进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并未能够持续很久。“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活着就是要有所为,而有所为就是表达自己的天性。表达人的天性就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虽然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可表达的,但必须尝试着去表达。……这是无止境的向往。……当我们发现自我只有在主动努力中获得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世界无限性这一点。努力是行动,行动是运动,运动是永不终结——它是永恒的运动。这是浪漫主义的根本意象。”*以赛亚·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第107—108页。郭沫若原本试图用“创造”的方式来表达人的天性,来表达人和自然、人和世界的关系。但是,郭沫若发现这套“创造”哲学只能在自我内部实现,一旦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就会面临困境。1924年,在与成仿吾的通信中,郭沫若表示,青年人共通的苦闷在于自我的实现,而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常想自杀”,我们无法找到自我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郭沫若: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8页。,是社会阻碍了自我的实现。由于缺乏哲学思考和宗教背景,自我意志的力量在郭沫若的诗歌中表现得肤浅而空洞,这也是郭沫若诗歌后来遭到批判的原因之一。于是,当郭沫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他便寻求到了解决的方法。*有观点认为郭沫若此前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在19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女神》开头的《序诗》中,郭沫若表示:“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了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称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她公开了。”茅盾指出:“在诗集上公然写出‘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当时还没第二人。”但是,茅盾接着又指出,“郭沫若后来自己承认,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事实上,这里的“无产者”和“共产主义”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是文艺层面的说法,郭沫若借此表现《女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并希望和大家一起共享这一创造成果。详见茅盾: 《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创造社资料》,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2页。强自由意志由冲破内部自我实现的阻碍转向改造阻碍人天性发展的外部因素——社会。郭沫若认为:“在社会主义实现后的那时,文艺上的伟大的天才们得遂其自由完全的发展,那时的社会一切阶级都没有,一切生活的烦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没有了,那时人才能还其本来,文艺才能以纯真的性为其对象,这才有真正的纯文艺出现。”*郭沫若: 《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8页。让人还其本来,让自我得到自由完全的发展,这是郭沫若对社会革命的期待。可以看出这和郭沫若的“创造”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自我意志得到自由、无限的扩张。只是由于受马列主义的影响,郭沫若将自我不能实现的原因从内部意志力之强弱转向外在社会的阻碍。至少在当时,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了解得并不深入。此时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只是混淆了政治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文艺美学上的个人主义,认为革命需要强调集体的力量而否定强调自我的浪漫主义。然而,在短暂的否定以后,郭沫若在1936年4月接受蒲风的采访时表示:“新浪漫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的侧重主观情调一方面的表现,和新写实主义并不对立。”*郭沫若: 《诗作谈》,《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理念的重新肯定和应用,其根本原因是浪漫主义的“创造”理念一直潜藏在其诗学脉络中。即便是表面上转向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自我创造自由之实现。他从一种无根基的“自燃”状态,找到了一种可以解释宇宙运行的体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和郭沫若的“创造”理念是契合的,只是这是一种通过外部活动实现自我的方式,而并非通过内部。
自我意志实现的途径由此从内部转向了外部。当抗战来临的时候,郭沫若极力提倡为战争献身的精神。他在一篇纪念在保卫腾县战役中牺牲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的文章中表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终有一死。而若“把自己的生命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郭沫若: 《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八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62页。,只要民族能够存续,个人的生命便永远“延续”着。“把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的无限的生命里去”,这样的口号在当时并不鲜见,但就郭沫若的整体思想而言,则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郭沫若所一直追寻的另一条外在的、现实的、超越人的有限性的道路。抗战只是提供了超越的契机。
因此,郭沫若最终选择转向马克思主义,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以外,郭沫若自身的思想瓶颈和缺陷也是其作出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转向,不仅是郭沫若一人的选择,而且体现了浪漫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矛盾和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所必然面临的困境。
三、 历史回响与现代启示
郭沫若对浪漫主义“创造”哲学的思考在当时并不能为人们所理解,表现无限性的强自我意志所展现出的“冲破一切阻碍”的文学图景被解读为是向旧社会制度宣战。这与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西方浪漫主义是在理性充分发展、工业化社会趋向成熟和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下形成的,而中国在接受浪漫主义时,既没有理性发展的哲学基础,也没有工业化和市民社会的社会基础,那么难道中国的浪漫主义就是一种“错误的时代”的产物吗?抑或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浪漫主义”?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接受一般在两个维度上: 反旧社会、旧有制度和反现有伦理。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浪漫主义在作者和读者层面找到了根基。因此,尽管郭沫若的《女神》集并没有明确表示是为反对旧社会、冲破一切现有体制而作,但在当时的文坛和读者接受中,只有将其与这一主题联系起来,浪漫主义才获得了“存在的理由”。
不仅读者群对浪漫主义缺乏理解和接受,而且可惜的是,创造社成员虽都聚集在“创造”的名目之下,但大多并不理解郭沫若的“创造”之意。“创造”一词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除旧布新、自由创造之意,而是蕴含着浪漫主义的诗学体系。郁达夫、张资平、王独清等人的作品只能说是对郭沫若“创造”理念的庸俗化表现。比如郁达夫的颓废沦为一种自怨自艾,而张资平的创作只能说是“浪漫”而不是“浪漫主义”,而正是这些创作使得创造社遭到诟病。郭沫若所开创的这一新的美学向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昌耀、海子、骆一禾的作品中才又重新展现。这些诗歌中的宏大宇宙景象、自我的绝对地位和丰富而震撼的想象力,接续半个世纪以前《女神》带来的美学冲击力。
此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一“创造”哲学和强自我意志若应用在诗学层面,的确能够给文学带来新的美学向度,但是如若用于现实层面,则会带来隐患。这一点很多现代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都进行过思考。如保罗·蒂利希曾严肃指出:“这种意志是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的驱动生命力的力量,甚至超越了有机的生命。可以说是驱动力。是生命的自我肯定,不仅在保持生命的意义上,而且是在生命的进一步发展的意义上。而将意志作为终极性、本质性的东西,就意味着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并存。尼采《超越善与恶》就指出,这是一种批判,即没有规范。这种没有规范的后果是很明显的,因为它使歪曲利用尼采的观念成为可能,纳粹主义就是这样非理性地运用强力意志的。”*保罗·蒂利希: 《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第438页。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以激进的姿态赞扬德国浪漫主义精神,试图使其成为民族精神,来为战争服务。他们提出,艺术家和天才的使命就是创造,不仅创造统治者和政治领袖,而且也创造被统治者和奴仆。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家被政治化,政治家被艺术化,以艺术原则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把政治领袖界定为艺术家,浪漫主义者也将他们置于法律之上,并创造了一个独裁主义的理想。这遭到了克汀、汉夫、李心清、欧阳凡海等人的猛烈批判:“战国策派理论是近几年来在中国大后方出现的一种法西斯主义理论。”*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三集第三册):战国策派法西斯主义批判》,辽宁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1982年,第1—5页。当自我意志成为终极目标,那么道德、社会原则就会被架空。正如雪莱所言,在浪漫主义中,只有一种道德,即天才。尼采的生命意志哲学在文学和哲学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但是也被法西斯主义所利用,原因也就在此。所以,我们要警惕浪漫主义逻辑中存在的将自我意志上升为国家、民族意志的现象,这既对民族国家利益本身有潜在威胁,也对文学创作无益。
综上所述,郭沫若所开创的浪漫主义“创造”哲学,是对鲁迅所提出的“美伟强力”诗学新范式的尝试和发扬,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子、骆一禾、昌耀等诗人的作品中产生回响,谱写了新诗史上壮阔宏伟、主体强健的一系脉络。尽管出现于新诗发展早期的郭沫若诗歌还有很多不成熟之处,但其开启的美学新图景仍值得借鉴。当今诗歌在现代主义大潮之下,绝对自我被削弱,这一“创造”哲学无疑是一剂有力的强心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