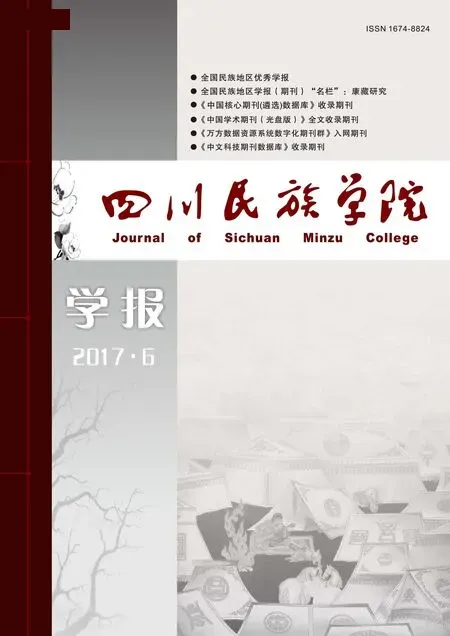象雄文明研究综述
尕藏扎西
目前藏学研究者一般将公元七世纪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之前的藏族历史时期划定为神话时代,尽管后期文献中存在7世纪以前即藏族部落时代的历史记载,但这些记载无非是7世纪创制藏文后人们根据口传记录下来的。除了极少部分留存至今的吐蕃金石、简牍、以及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塔波寺文书外,藏文史书基本上都是10世纪以后出现的,苯教史家宣称为吐蕃时期詹巴郎卡所著的《札巴林扎》(bsgrgs-pa-gling-grags)也实为十世纪由塔希赤塞新创而托名为伏藏的史书,[1]故此,遥远的7世纪之前的历史尤其象雄十八王国时代的历史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相关“象雄王国”的论题莫衷一是、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象雄作为吐蕃王朝崛起之前青藏高原规模最大、疆域最广的王国,其孕育和承传了灿烂的苯教文化,象雄的标志性神山冈底斯曾一度成为喜马拉雅文化圈的中心。可见象雄文明在整个藏族文明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据昌都卡若等遗址出土的文物考证,藏族历史可追溯至七千年到一万年以前的新旧时期时代,[2]但囿于可靠的文献资料,人们对藏族部落联盟时代的漫长历史知之甚少,所以,科学合理地重构前吐蕃时期的藏族十二部落及其中最大部落即象雄王国的历史成为摆在藏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旅居意大利的南喀诺布教授首先认识到了这一学术问题的重要性,他于1982年出版《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和《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两部著作,就远古象雄历史与文明的论题作了破砖引玉式的探讨。当时国内学者才让太和土登平措等先后赴南喀诺布教授任教的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访学,因受南喀诺布教授的影响,回国后陆续写了一批学术质量较高的有关象雄及远古藏族文明的文章。才让太教授于1985年用藏汉两种文字写的《古老的象雄文明》即为代表性的成果,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被视作国内象雄研究起步的标志。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万象更新,新中国的藏学研究刚刚开始,许多领域的文章少而又少,苯教和象雄方面的文章更是无人问津,因而,这篇文章的主题及其观点也在当时都较新鲜,在藏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随后相关象雄研究的出版物相继问世,象雄及苯教文化研究逐渐发展,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涵盖大部分古代丝绸之路通道的象雄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15年1月在西藏拉萨召开“首届象雄文化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继挪威奥斯陆、日本大阪和法国巴黎召开的象雄文化研讨会后,首次在中国国内召开的关于象雄文化的学术会议。此后,2015年6月在四川金川召开“中国金川'象雄-嘉绒'文化学术研讨会”,2015年9月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国际象雄文化学术探讨会”,这些密集召开的学术会议将象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截止目前,象雄研究方面问世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和书籍,回顾和总结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将有助于象雄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本文拟将近三十年来的象雄研究成果归类为象雄的疆域、象雄的文明、象雄王国覆灭、象雄考古、象雄与嘉绒藏区关系等六个方面,并对其进行综述和评介。
一、象雄的疆域
可靠史料之匮乏成为进一步推进象雄研究的瓶颈,在此困境下,对时隔几千年之前的象雄疆域做出科学研判是难乎其难之事。但基于象雄疆域的确切定位对于象雄研究的重要性的考虑,学界前辈未逃避这一重要课题。才让太教授于1985年在《西藏研究》第3期上发表题为《古老的象雄文明》的文章,主要依据格桑丹贝坚赞所著的《世界地理概说》,首次对象雄的疆域作了深入的探讨。他经过分析认为,《世界地理概说》记载“里象雄”及其疆域为“冈底斯山以西三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par-zig)、巴达先(bha-dag-shan)和巴拉(bha-lag)一带”,其地理位置应为波斯至冈底斯山之间的某个区域,因为无史料记载象雄的实力发展到波斯以西,而中象雄应被定位为今天的冈底斯山,外象雄则应被指认为今西藏丁青一带。[4]他进而根据《世界地理概说》的记载,就象雄疆域的大致轮廓做了界定:象雄最西端为大小勃律(吉尔吉特),即今克什米尔,从勃律向东南方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延伸的地域包括今印度和尼泊尔的少部分领土都属于象雄的疆域;北邻葱林、和田和羌塘;东面不清楚,但据佛教文献朵康地区不属于象雄。同时,他也认为,文献的记载非常矛盾,进而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外象雄东达朵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古时候象雄的地理位置大致就是今天的大部分藏区,亦即最初的象雄包括象雄和蕃两个民族。只是到了聂赤赞普时代,雅垅部落兴起,其逐渐脱离了象雄王室脆弱的统治,加之苏毗的崛起,切断了象雄王室与东部象雄(朵康)地区的联系,以后的象雄就只限于今天的阿里和克什米尔了。”[5]此篇文章作为国内首次解读象雄及其文明的文章,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尽管此前意大利杜齐先生的《尼泊尔两次考察报告》广泛讨论了象雄的问题,*杜齐.尼泊尔两次科学考察报告[M]的第十章:象雄及其扩张(71-75页);第十二章:象雄(92-105页)第十三章:西藏西部历史调查均对象雄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探讨。见《研究尼泊尔历史的资料》,罗马,1956年。转引自张琨著、玉文华翻译的《论象雄》,载于《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但当时因外文查阅条件所限,国人无从了解象雄,及至《古老的象雄文明》这篇文章问世,象雄文明开始被人专注。当时才让太先生提出的对于象雄疆域的观点得到宗教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同,但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晏春元先生写的《本波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浅析》(上、下) 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1989年第4期)最具代表性。晏先生在文中另辟蹊径,竭力论证了象雄即为嘉绒地区,他的启发来源于张琨所著的《论象雄》一文的记载:下象雄为吐蕃东北的一处地域,而非杜齐教授《尼泊尔两次考察报告》认为的“吐蕃西南”。[6]晏春元从嘉绒方言研究和史实考证相结合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大食”“獽戎”“象雄”和“嘉绒”为同一地域的观点。他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嘉绒有“打日王朝”之称,“打日”嘉绒语意为“虎豹”,这与藏文记载中的“达斯”相对应。他进一步认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苯教兴起之时嘉绒金川流域雍仲朗(雍仲拉丁)地方建有“打日王朝”,此即象雄,魏磨隆仁即为嘉绒苯教中心雍仲拉丁寺。1990年他在《西藏研究》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从藏文字的渊源探讨象雄为嘉绒藏区》的文章,文中对他此前的“象雄即嘉戎”之说进行了补证。他在此篇文章中引用大量的嘉绒民间口传故事,认为藏文由辛饶和桑波奔赤创造的“堆”字逐渐演变而来,而辛饶出生在马尔加国(今丹巴县巴底乡、金川县马帮乡和安宁乡等地),故象雄即为嘉绒。[7]身为金川县人民政府官员和嘉绒人的晏春元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象雄就是嘉绒,并作了较具说服力的论证,这种不同的声音给当时的象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嘉绒地区的地名、王朝名、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化符号中确有诸多象雄文化的烙印,所以晏先生的一厢情愿也是有情可原的。尽管这样,后来陆续发现西藏阿里一带的“琼”部落东迁嘉绒地方的写本资料后,象雄文化和嘉绒文化为何有诸多相似之处的谜底被揭开了,写本文献显示象雄“琼”部落东迁嘉绒后在当地复制了很多嘉绒的文化符号,晏先生的观点也因这些写本的发现而变得很难坐实。
此后,有关象雄疆域的讨论未曾间断,嘉措顿珠先生在其《漫话苯教文化之源》中引用和比较《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等汉文文献以及《苯教源流》和《佛法铁注》等藏文文献记载,认为,象雄虽有上中下的分法,但象雄本土应该为今阿里专区所辖全景,这种地理概念沿用至10世纪为止。黄布凡在《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上发表的《象雄历史地理考略-简述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引述《世界地理概说》《象蕃古代史》《卫藏道场胜迹志》《五部遗教》以及《贤者喜宴》等藏文文献的记载,并对之进行甄别和考证,认为,古象雄的地理位置大致是今阿里地区和藏北羌塘高原,向西还可能包括拉达克这一范围,大羊同在今阿里地区北部和藏北羌塘高原,小羊同在今阿里地区南部。[8]霍巍于1996年发表在《西藏研究》上的《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一文对下象雄的地望定位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对以往象雄疆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认为象雄的地理疆域在历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阿里冈底斯山应为象雄部落的中心,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下象雄为“东部象雄”(朵康地区),反之,若将下象雄的地理位置定位在西藏的中部地区偏南一带,而不是在西藏的东北部去寻找下象雄的踪迹,既符合很多史书记载的“上象雄与突厥接壤,下象雄与苏毗接壤”的说法,也能够对当时象雄与苏毗、吐蕃三足鼎立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9]从霍巍先生的这番论述可知,象雄疆域定位问题在学界出现分歧的焦点不在于上象雄和中象雄,而在于下象雄疆域的定位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于1987年对那曲地区进行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提到今那曲东部、昌都地区及玉树南部为外象雄中心,作者还提到苯教史籍中甚至把今甘孜西部囊括在“外象雄”的范围。*“那曲地区明确见于史料的最早主人,便是古老的象雄政权-汉文史籍中称之为羊同,外象雄的中心是'松巴朗戈金肖'和'希莱加嘎',包括今那曲地区东部、昌都地区北部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南部,”这次调查报告的作者还提到有的苯教史籍中甚至把黄河源头地区和澜沧江、长江及雅隆江的上游(含今甘孜州西部)统计于“外象雄的范围。”参见,格勒、刘一名、张建世、安才旦编:《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第9-11页。转引自才让太:《古老的象雄文明》,原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收录于才让太主编《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51页。顿珠拉杰和君.温森特.白莱嚓通过对西藏西北部象雄文化遗迹的考察,认为“西藏西北部包括现在的阿里地区以及那曲地区的西部四县即班戈、申扎、尼玛和双湖,还有日喀则的吉隆、仲巴和萨噶县为象雄文化分布区”。在这些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让太教授深入分析和仔细推敲有关象雄的汉藏英三文的史料和传说故事,再次对包括象雄疆域在内的象雄文明进行了界定,其成果发表在《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上,在这篇题为《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的文章中,他援引丹增仁青坚赞德青宁布写得《瞻部洲雪山之王冈底斯山志乐意梵音》等藏文史书,对他20年前写的《古老的象雄文明》中的内容和观点做了补正,加深了认识,其研究结论认为:吐蕃崛起以前的象雄疆域包括南边的拉达克和克什米尔、西部的巴基斯坦东段巴尔提斯坦,北至那曲高原甚至包括今青海省玉树的一部分,东达以丁青为中心的包括今天那曲和昌都一带的辽阔的区域,几乎包括整个藏区。但是,对于有些学者提出的长江以东今甘孜州的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在古代象雄疆域的说法,先生持怀疑态度。[10]后来才让太教授在《苯教史纲要》中对苯教传统史料记载的上、中、下象雄的地理划分及其疆域包括长江以东全部西藏的说法进行了较为贴切的分析:虽然现有的资料不足以证明象雄对遥远的东部藏区即下部象雄有过统治,但至少象雄这个古老的地域概念及其疆域在吐蕃王朝崛起之前曾经覆盖长江以东的整个西藏是可以坐实的。[11]才让太先生把可靠的史料和自己多年来研究象雄历史的经验相结合,在《苯教史纲要》中详细介绍了象雄疆域的变迁及其所覆盖的大致区域,基本终结了三十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
二、象雄文明
首先提出“象雄文明”这一概念的学者是南卡诺布教授,他在其鸿篇巨著《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中使用大量的篇幅对象雄文字的产生、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的身世与传法事迹、象雄的天珠、岩画、工匠术、音乐、禳灾法、占星术、卦、梦、星算、医学等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2]这部著作问世时间较早,但在国内1996年才得以出版,故这部堪称“象雄百科全书”的著作在“象雄”一词概念及其文化含义完全被国内学者熟知和接受之后才得以推介。其实,早在1985年才让太先生发表《古老的象雄文明》一文后,“象雄文明”这一概念逐渐得以普及,相关研究论文陆续出现。《古老的象雄文明》从象雄的宗教、象雄文的产生和演变、象雄文明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象雄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从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观点,比如,文章从象雄文、辛饶米沃进藏的路线、《世界地理概说》的记载三个方面批判了张一纯在其《<经行记>浅注》中提及的苯教发源地“达斯”即“大食”的说法,认为“stag-gzig”不完全是“大食”,应译作“达斯”,以便表达特殊的地理含义。另外,文章依据苯教文献否定了7世纪之前没有藏文的说法,认为象雄文先于藏文产生,而藏文是吞米桑布扎对象雄文和梵文经过一番取舍而创制的,其与象雄文和梵文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最后,文章从医学与星象学、语言、神衹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象雄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继《古老的象雄文明》之后,有关象雄文明的文章出现了不少,代表性的有,顿珠加措在《漫话苯教文化之源-象雄》一文中从象雄文、象雄人的起源和图腾崇拜、象雄为苯教之源三个方面论述了象雄文明,但其内容和观点基本与之前问世的《古老的象雄文明》相似,没有多少新的观点。十年磨一剑,1996年才让太先生发表了题为《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的文章,对作为象雄文明中心的冈底斯山及其周前的文化做了细致入微的论述,文章着重对冈底斯山与苯教文化的关系做了阐述,提出,冈底斯神山崇拜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原始苯教文化时期,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为冈底斯山在原始苯教中常以三界宇宙中心的地位而出现,尤其早期苯教文献中鼓基芒盖这一古老的苯教神衹被认为与冈底斯有很大的联系,但晚期出现的雍仲苯教文献中则很少提到这个字。该文将这一主题进一步引申到与鼓基芒盖有关联的什巴贝钟钦波上,认为藏族的牦牛崇拜来源于相传混沌初开时从天界下凡到冈底斯山的什巴贝钟钦波。苯教祖师辛饶米沃的降生及其在冈底斯的传教活动使冈底斯山与苯教的关系更加密切,并影响吐蕃。文章还对冈底斯山与印度古代文化的关系做了富有洞见的考证,认为冈底斯与印度文化的千丝百缕的联系发端于大自在神崇拜,并以此作为主线传播的,因为大自在神派、胜论派以及正理派均把大自在神奉为各自的导师和主神,而据吠陀文献,大自在神之栖息之地不在印度,而是在北方的冈底斯山。[13]文章最后对冈底斯山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做了解读,提出藏传佛教诸派中与冈底斯山关系最密切的教派首推噶举派,这种关系是从米拉日巴和苯教师“那若苯琼”斗法的故事开始,随后岗波巴索南仁青等历代噶举派高僧修行于冈底斯山,由此可知,佛教对苯教圣地冈底斯文化是一种接受和延续,而不是抵制。作者对冈底斯文化的定位是,以三界宇宙观为载体、以冈底斯山为崇拜对象、以各种原始“苯”文化为具体内容的强烈的地域文化氛围。[13]每一文化载体都与周围的文化有联系,因此,文化载体放置在整个文化圈中去考虑才能透视得更彻底、更清楚,此篇文章把冈底斯文化放置在喜马拉雅文化圈中,考察其时间上亘古千年的嬗变及空间上覆盖中亚的变迁,解决了作为象雄中心地带的冈底斯山文化的源、流及其面的问题。
霍巍先生在《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一文中同意有学者提出的象雄曾是西藏古代早期的文明中心之一的观点,但是关于象雄的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他觉得很费解,可能因为汉文史料中把“象雄”写为“女国”的原因,他一方面觉得象雄这类骑马民族的国家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男性没有大的区别,如此看来像汉文史籍记载的那样女性国王统治“象雄”的说法也不是不合情理,但他也觉得张琨所讲的从象雄国王李迷夏和他的藏族妻子的传说能印证象雄国王为男性的说法有道理。[9]霍巍先生的困惑或许正是象雄研究者们的集体困惑,由于汉藏文记载有出入,关于女国的问题越说越模糊,象雄统治者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也值得继续探讨。霍巍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把苯教和原始苯教严格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是辛饶创立之教法,而后者是一种萨满教,其核心就是对天界、地界、地下界的诸神灵加以崇拜。[9]两者有其不同的来源,雍仲苯教起源于象雄西部的某一地区,有着一套完整的理论与相应的教规,而苯教是起源于象雄本土的、原始的、具有萨满教特点的原始宗教。他还认为,古代象雄的社会特征,是一个以众多的游牧部落或部落联合而成的“骑马民族国家”,其文化是一种处在比较原始发展阶段的文化,与中亚、东北亚游牧民族具有相当大的共性,亦即在早期阶段还只能是一种萨满教文化。总之,他认为必须动态地看待象雄及其文化,象雄文明并不是一开始便具有很高的水平,而是通过利用便利的地理与交通条件,同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方才成为西藏高原早期的文明中心。张云所著的《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对包括象雄文明在内的上古西藏文明的特点做了总结:以原始的民间信仰和地方宗教——苯教为中心的精神文明;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明和不断进步为特征的物质文明;以王权的产生和强化为核心的制度文明;以堡寨碉房建筑为特征的上古城市文明;西藏上古文明的多元性特征,由于同外界的密切关系而呈现出开放性特征。[14]张云先生认为辛饶米沃开创雍仲苯教以前的象雄宗教与其说是苯教,不如说是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间信仰,严格地讲,不能把它们叫做宗教,因为他认为宗教应该是有教义和理论体系的一种信仰。[14]他在这本书中较详细地阐述了祅教、摩尼教和景教等波斯宗教对象雄苯教的影响。
三、象雄王国的覆灭
对于象雄王国的覆灭问题,在学界探讨的不算多,但这个问题对象雄研究至关重要。古格.次仁加布先生于2012年在《中国藏学》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略论十世纪中叶象雄王国的衰亡》一文,对象雄王国衰亡的原因、过程及衰落时间做了详细的探讨,这篇文章依托《太阳氏王统记》等新资料,阐明了象雄王国及其下属五氏族衰落和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征服象雄王国的历史过程。他提出,象雄王国经前11代和后6代左右的承袭后,末代国王于公元10世纪中叶被弑,五氏族纷纷投降,并最终被吐蕃王室后裔取代,而吐蕃王室后裔则靠王室势力在象雄的代表(下象雄的琼布氏家族、上象雄的卓氏家族、觉若氏家族和齐穆氏家族)而占领象雄的。如果背后没有这些家族的支持和辅佐,吐蕃王室后裔吉德尼玛衮就无法在西藏西部高原建立阿里王国,更不可能出现后来的古格王国、拉达克王国和普兰王国等。
同美教授写的《论远古象雄十八王国及其覆灭》一文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象雄王朝的历史传说可以上溯至苯教鼻祖辛饶米沃时代,当时出现了作为辛饶施主的象雄王赤威拉杰,其在象雄十八王中最有名,象雄王朝的历史下限至少可以断代至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他认为,吐蕃王朝的终结史和象雄王朝的终结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吐蕃王朝终结了两位象雄国王的命运,而古格王朝终结了包括王室自己在内的无数象雄百姓和本土文化的命运。同美先生把象雄王国的覆灭和包括象雄百姓在内的象雄文化的覆灭区别开来探讨,细化了象雄覆灭的经过及成因。至于他提出的象雄最后两个国王分别被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作弑的说法,十有八九是佛苯两种教法史记载不一致导致的,对此问题,笔者曾做过核对,佛教文献记载象雄最后国王李弥夏被松赞干布处死,苯教文献则记载李弥夏被赤松德赞降伏关进牢狱,但是前一个说法得到了敦煌文献中松赞之妹萨尔埋盖道歌的印证,所以更具参考价值。故此,笔者生疑,佛苯文献中所称的两位被弑的象雄国王是否是同一个人?这个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
四、象雄考古
象雄相关的考古工作理应始于十四世纪,史书记载当时有欧洲人进藏探险和传教,对象雄地理地貌做了零星记载,十八世纪后半页英国殖民印度并渗透中国西藏,当时他们所派遣的传教士、商人、探险家怀着各种目的以公开或隐秘的身份来到西藏,其进行的地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科学考察零星地记载在他们的游记或综合报告中。[15]1951年后,西藏考古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调查和发掘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童正恩先生于1985年在《文物》第9期上发表题为《西藏考古综述》的文章,将西藏考古分为三个时代,即,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时代,并对其进行了宏观的回顾。其中石器时代的部分中对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出土的打制石器的种类和内容做了介绍。据他介绍,这两地的打制石器分别由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66和1976年发现的,前一处发现打制石器40件,后一处发现打制石器14件。关于断代问题,童先生觉得由于缺乏地层和伴生动物群遗骸的依据,所作判断仍嫌证据不足。
霍巍先生写的《西藏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分析西藏西部地区新发现的“前佛教时期”考古资料,回顾了探索象雄文明的进程中的若干问题。在对新发现的一批考古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敦煌古藏文写卷的记载,对西藏远古历史上的“恰”“穆”、氏族以及古象雄文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霍巍先生在象雄文明的考古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他并没有局限于考古学的研究,而是将考古学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的象雄研究的基础上。[16]
夏格旺堆和普智所写的《西藏考古工作40年》一文在回顾4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西藏全区发现的西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并对相关考古成果做了梳理。
五、象雄与嘉绒关系
宴春元先生所写的《奔波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浅析》(上、下)及《从藏文字的渊源探讨象雄为嘉绒藏区》三篇文章论证了象雄即为嘉绒藏区的观点。宴春元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新颖,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对象雄地望的定位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但后来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宴先生的这种观点是个伪命题,经不起推敲的,最具说服力的首推才让太和顿珠拉杰所著的《苯教史纲要》,其认为,上象雄以琼隆银城为中心 、中象雄以当惹琼宗为中心、下象雄以琼布孜珠山为中心,将象雄疆域界定在长江以西全部西藏。琼氏部落在扎氏的领地上开始繁衍生息,成为古代象雄非常重要的氏族,但后来开始东迁,一直迁到遥远的康区和安多的嘉绒等地,其东迁原因是为了去东方传播苯教,这一点可以从诸多的琼部落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11]这可能是嘉绒文化中随处可找到象雄文化因子的原因所在。石硕先生也认为“象雄十八王”统治时期苯教由象雄地区向藏区各地传播的说法正确,并撰写了《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和《关于唐以前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等文章,认为,“琼鸟”信仰伴随雍仲苯教的形成逐渐由象雄传往藏区各地,尤其是经藏北传播到藏东地区,今碉楼密集的嘉绒地区传说中正是将其苯教、琼鸟和土司来源地指向象雄及西藏琼部。此外,碉楼分布还与苯教呈明显对应关系。[17]这样,他把嘉绒地区的碉楼和象雄的“琼鸟”(汉文史料中称邛笼)巧妙地联系起来,并认为琼鸟的来源为古老的象雄。他还认为,今丁青一带和安多地区有不少关于琼氏的传说和带“琼”的地名,均应为象雄琼氏部落东迁的孑遗,嘉戎地区土司传说中普遍存在的“琼鸟”和“卵生”因素以及土司祖源地指向象雄和琼部,显然与象雄琼氏部落的东迁有关。[17]石硕教授对象雄文明东移的交通问题也有分析,认为,从藏北高原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情况看,极有利于与外界交往,其东北面经青海湖可直抵汉地、突厥与西域东部;从西面经拉达克,可直通天竺;从北面经突厥地区,既可通往西域诸国,也可通往汉地。[18]这种四通八大的交通状况可能是象雄因吸收周边先进文化而成为早期西藏文明中心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可能是象雄文明能够伴随“琼氏”部落的东迁克隆到嘉绒地区的原因所在。不管怎样,如今的嘉绒文化可被视为古老的象雄文化的现代翻版,这点在赞拉.阿旺措成和张学凤所写的题为《略述嘉绒锅庄与象雄琼部文化的历史渊源》的文章中呈现得淋漓尽致,这篇文章提到了《嘉绒藏族文史资料续编》中记载有象雄王时代勒乌尔和达若部族东迁嘉绒的历史,这大概是距今3858年前的事情。距今2000年左右又有象雄琼部王的儿子琼帕察莫等来到嘉绒地区。[19]这些东迁的象雄人在嘉绒理所当然地复制了很多自己家乡的文化,比如,嘉绒地区在表演达尔嘎得(大锅庄)时,必须先表演歌颂琼鸟的《琼莫且木确》舞,不仅如此,嘉绒人还把琼鸟作为民族的图腾,在门楣上方刻琼鸟,在女性头帕上佩戴银制琼鸟装饰品,可见,象雄文化对嘉绒的无处不渗透的广泛的文化影响。
结语
我国象雄文化研究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队伍慢慢壮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对象渐趋细化,但也遇到较大的困境:一来内容涉及前吐蕃文明的可靠史料极度缺乏,加之存世的史料大多出现年代较晚,二来公认的实证力度较高的考古和岩画研究队伍小、成果少。所以,象雄就像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一样无从详细定位。苯教是否是象雄的唯一宗教?象雄时期宗教的理论化程度或文明程度如何?象雄是独立于吐蕃而存在还是作为藏族远古十二部族中最大的部落联盟而存在?这些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因为石泰安提出的远古西藏充斥“无名宗教”(民间宗教)的观点和霍巍所提的“原始苯教实为萨满教”的说法,顿珠拉杰提出的象雄起初为西藏远古十二部落(rgyal-phran-sil-ma-bcu-gnyis)之一的观点,以及丹珠昂奔和张云等提出的原始苯教受过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的观点都给我们不同的分析角度和思维方法。另外,值得玩味的问题是,法国学者石泰安和拉露等人对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关苯教内容的研究显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10世纪后高度理论的苯教与10世纪以前的西藏原始宗教有必然的联系。这些议题可能是国内苯教研究者亟待回答的问题。
[1]雄努洛桑编.苯教史料汇编[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p8
[2]贡乔泽登.略谈藏族祖源问题[J].青海省党校油印本,p3,另见,才让太.古老的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p67
[3]才让太.苯教研究论文选集[A].第一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p2
[4]才让太.古老的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p96-97
[5] 才让太.古老的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85年第3期,p96-97,转引自霍巍.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p45
[6] 晏春元.本波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浅析(上)[J].西藏研究,1989年第3期,p129
[7]晏春元.从藏文字的渊源探讨象雄为嘉绒藏区[J].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p124
[8]黄布凡.象雄历史地理考略-兼述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J].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p16
[9] 霍巍.论古代象雄与象雄文明[J].西藏研究,1997年第3期,p46、p48、p49
[10]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转引自才让太.本家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6月,p52
[11]才让太、顿珠拉杰.苯教史纲要[M].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11月,p9、p24
[12]南卡诺布著.代象雄与吐蕃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5月
[13]才让太.冈底斯神山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J].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p72、p77
[14]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J].西藏通史,资料丛书.内部资料[6],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A].2004年12月,p4、p127
[15]童正恩.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p9
[16]才让太.苯教研究论文选集[M].第一辑序言,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6月,p2
[17]石硕.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与苯教文化[J].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p85、p89
[18]石硕.关于唐以前西藏文明若干问题的探讨[J].原载.西藏艺术研究[J].1992年第4期,转引自才让太.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M],p25
[19] 赞拉.阿旺措成、张学凤.略述嘉绒锅庄与象雄琼布文化的历史渊源[J].西藏艺术研究,2013年第1期,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