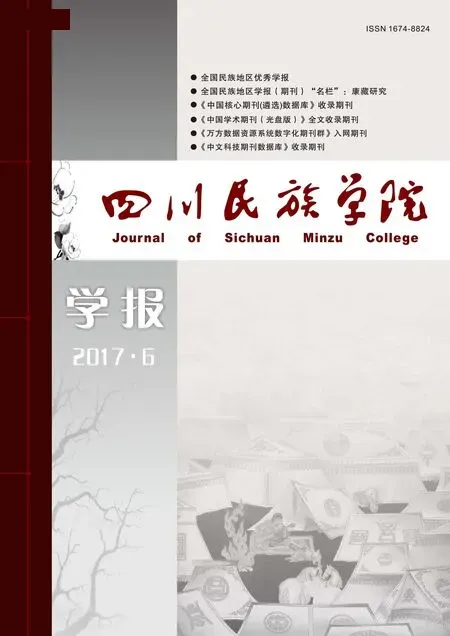论门罗小说《多维的世界》女性空间书写
陈金云 廖述娟 罗楚云
一、前 言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是一位蜚声世界的加拿大女作家。约半个世纪笔耕不辍的文学生涯里,她著作等身,并赢得了加拿大总督奖(三次)、莱南文学奖、欧亨利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布克国际奖和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等诸多奖项。《多维的世界》(Dimension),是她2006年发表于《纽约客》的作品。如门罗的其他诸多小说一般,该故事仍然是讲述平凡女性从婚姻和日常生活逃离寻求新生的一则短篇,体现了作家对现代女性生存和命运的关注。女主人公多丽从十六岁到二十三岁的七年时光中经历了恋爱、婚姻和家庭破碎看似普通的人生历程,但背后伴随的是丈夫劳埃德在极端男性沙文主义意识下对她各种形式的家庭暴力,以及此暴力最终导致他疯狂杀子的人伦惨剧。痛苦迷失中的多丽在一次去探监的路上目睹了一场车祸,用劳埃德曾教她的方法帮助挽救了还未成年的司机的性命。此番救人举动令她获得顿悟,完成了自我独立与成长,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
空间与时间同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二十世纪末的“空间转向”,使空间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越来越多的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视野。结合了文化地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身份认同等诸多批评理论,空间批评发展成为一种跨学科、开放式的批评方法与理论。它打破了传统对文本景观、场景研究的方法,注重挖掘文本中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社会、身份和权力等多元关系,以空间思维审视人类社会,关注人类在其中的生存发展。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日常生活批判落实到空间反思批判层面,认为空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兼备物质、精神和社会多重属性,而“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1],并且“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那剥夺它与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这个人类的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不是直接公开的,也会是拐弯抹角的”[2]。福柯关注空间中的权力运作,认为空间是各种权力关系交锋的场域,权力的操控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来实施完成的。“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3]。韦格纳在总结诸多思想家的论著后称:“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4]。朵琳·玛赛认为性别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空间是性别关系建构的场域。“空间控制无论是通过传统或者符号的力量进行,或者是通过暴力的直接威胁,很清楚都是在其(高度不同的)形式上在性别建构中的基本因素”[5]。由此可见,众多学者都指出了空间中隐藏的性别、身体、权力等多重意蕴,这也是女性主义的几大重要议题。因此,对于《多维的世界》这样一部女性成长小说,空间批评理论为它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该小说呈现跳跃式叙事的特点,随着回忆和现实,女主角多丽在不同时间穿梭于不同物理空间,主要为她婚后定居的“Mildmay”[6],家庭悲剧发生后工作的“the Comfort Inn”[6],以及前往探望劳埃德的旅程当中。她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呈现了她的人生成长轨迹背后日常生活实践与话语中的不平等两性权力关系,书写着她的女性空间。
二、Mildmay——禁锢之地
家,人类栖身和日常生活最重要的物理空间,是社会的隐喻,能够折射出特定文化中的两性关系。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常常是通过空间,通过家这个家庭生活当中男女性别权力对垒的场域对女性身体的禁锢而实现的。在男性中心话语体系下,男性以让女性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各种日常生活琐碎来控制家庭空间,进而使之成为压榨她们身心,束缚她们的灵魂的地方。朵琳·玛赛称:“把女性限制在家庭中,是一种特殊的空间控制”[7]。《多维的世界》里,家庭空间对小说中女主角多丽个体的身心压迫禁锢实则象征着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支配。丈夫劳埃德通过对家庭地理位置安排,继而对妻子多丽进行身体的圈禁支配背后呈现的空间,蕴含的是不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由于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是空间生产的主体,为多丽生产了一个被压缩到极度边缘的生存空间。被压迫女性对男权的抗争,也是从家庭生活空间尤其是身体空间的拓展开始的,尽管这个过程充满被动、妥协和失意。
十六岁的多丽在母亲住院期间,她和近乎是父辈的护理员劳埃德相识相恋。母亲身故,她成为了孤女后迅速怀孕结婚,然后依从丈夫主张,搬离故乡,寓居边镇——迈尔梅德镇,并且没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门罗给他们的定居之地取名迈尔梅德镇,其英文为Mildmay,显然意味深长。与其是将它翻译为“温柔的五月”或者其他,还不如把词翻转阐释为may wild“可能疯狂”——预示着似乎要开始幸福生活的夫妻未来迎来的会是一场人伦惨剧。门罗并未给出小镇细致的物理景观描绘,但多丽在惨剧发生前的晚上投奔住同一区的玛吉时,文本里有这么一番叙述:“开始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马路,然后就转上了高速路。只要有车来,她就得在沟里走”[8],可见不光是他们所在的乡下地理偏僻,甚至在此地他们也是离群索居,处于边缘地带。自此,男权对女性的禁锢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开始,随之延展到了各个领域。
劳埃德自己外出工作,但将多丽限制在家当贤妻良母,使其深陷家庭日常生活的琐碎当中,成为屋子的囚徒,并以各种手段方式压迫她的女性生存空间。从身体自主权,到生育权,到社交,人生种种,男权规训和监督无处不在,多丽逐渐失语直至丈夫对她施加的束缚虐待成为常态。一发现事情脱离他的意志,就会导致他对权威受到挑战的疯狂愤怒与惩罚。劳埃德反对避孕,所以多丽在五六年里生了三个孩子,尽管这时她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可劳埃德后来还是疑心多丽在偷吃避孕药而去搜查她的衣柜抽屉,牢牢控制着妻子的生育权。在养育孩子方面,由于母乳不够,多丽对第三个孩子不得不进行奶瓶喂养,这让劳埃德居然气得状若疯癫,对妻子进行语言侮辱和暴力攻击。“劳埃德发了疯,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吵了起来,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婊子”[8]。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劳埃德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家接受教育,原因是他就是觉得“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咱们的孩子,不是教育部的孩子”[8]。他脱口而出的“我的孩子”,显而易见其内心竟然将孩子们的母亲多丽排除在外了,仿佛她只是个沦为生育工具的“他者”罢了。一句“只要她没有先笑,他也不反对她笑”[8]更是道尽了劳埃德的暴君式压制下,多丽在这婚姻当中的卑微,女性自我意识的丧失。
而多丽的社交状况,更是劳埃德犯下弑子罪行的导火索。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多丽和同为母亲的玛吉有了来往。这个比多丽年长有阅历有见识的女性和她的客货车的出现,为多丽开辟了更广阔的世界。汽车,这一象征着技术、力量与权威的交通工具,在多丽家是掌握在劳埃德手中,由他使用和保养,与多丽无缘。而玛吉这位独立女性却挑战了男性领域,会开车,自己也拥有一辆小型客货车。她开着车子带着多丽和孩子们去学校,去购物,去公园游玩,帮助她暂时逃离压抑的家庭,使其物理、精神和社会空间得以拓展。玛吉问多丽:“你都还好吧?我是说,你的婚姻还好吧?你快乐吗?”[8]她内心受到了震撼。“她发现,有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却无法理解”[8]。这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包括了劳埃德的偏狭狂妄人格、自己的婚姻生活中的自我丧失,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萌芽,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开始被动地寻找“呼吸”的空间。充满男权意识的劳埃德开始日渐不满。“渐渐地,越来越糟。没有命令的禁止,但是越来越多的苛责”[8]。为了巩固权威,他采取的破坏手段除了苛责多丽,还有对玛吉的各种诋毁,暗讽她受教育过多,甚至污蔑她想让他们夫妻分手。终于有一天晚上,家庭琐事让这对夫妻有了争执。劳埃德冤枉多丽买的有小凹痕的面条罐怕是有毒,甚至匪夷所思地质问她是要在孩子们还是他身上试试这毒。忍无可忍的多丽逃到了玛吉家,因为“只是需要点空间,呼吸”[8]。她这一举动在心性已经偏执至扭曲的劳埃德看来,是要逃离他的掌控,在彻底挑战他的尊严和权威,出于惩戒和报复,当晚就丧心病狂地把自己的三个孩子给杀死了。劳埃德被精神病机构关押了起来,多丽受到巨大打击精神崩溃,这个家庭从此被毁。
三、康福特旅馆(the Comfort Inn)——彷徨之所
劳埃德弑子案发生后被鉴定为犯罪型精神病,给关在某安全机构。多丽受刺激过度被送入医院治疗,之后由相关援助机构安排新的住处和工作,到一家名为康福特“the Comfort Inn”的旅馆做客房服务员。Comfort原本意思为“安慰、舒适”之意;inn,旅馆,是人们旅途中的暂时休憩地。字面上the Comfort Inn是能够给人舒服和慰藉之感的所在。但事实上,这份工作,这家宾馆,仍然不是多丽自己的选择,并不能给予多丽真正的慰藉,也不能成为她的最终归属。它只是她人生旅途中一个临时停靠站,她的身心,都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其身体和性别定位,也充满迷惘和冲突。
多丽改头换面,似乎要告别过去,但又充满了矛盾。“她剪短了头发,漂淡了颜色,削尖了波浪,人也瘦了很多”[8],不再是当年的模样,“那时候,她还是长头发,棕色的波浪,自然卷曲,颜色也自然。她的表情正是他喜欢的,害羞温柔的面孔——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8]。她如今不买衣服,除了制服,就是牛仔裤。以前不化妆是因为丈夫不让,现在可以化妆却也没有化。外表也失去了女性的柔美,“谷穗式的刺儿头,配她瘦骨嶙峋的脸,一点儿也不合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8]。外在的变化表明她在经受男权暴力伤害后下意识地反抗男权规训,力图借由解放身体来获得自我,但她塑造男性化的身体外观消解了自己的女性特征,实质上是体现的是她性别身份、两性权利上的迷失下走向了极端 。她的新名字,“弗莱”Fleur,法语里的意思是“花朵”,却又是她对自己女性性别本能固守的明证。
她在康福特旅馆“当服务员,专门清理房间。刷浴缸、铺床、给地毯吸尘、擦拭镜子。她喜欢这份工作。这些事情把她的思想控制在某个范围内,让她精疲力尽,晚上能睡着觉。有人劝她趁着年轻,长得还不错的时候,赶紧去上上培训课,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不想和人说话”[8]。
这阶段的多丽,孑然一身,躲在这家旅馆,毫无人生目标,只希冀如蜗牛一般缩在安全的壳里,暂时借繁重工作等各种方式来麻木自己,以图遗忘发生的家庭悲剧,逃避她承受不了的生命之痛。虽然有如桑兹太太那样的社会工作者帮助她,但她和他们仍然隔着千山万水,内心仍然孤苦无依。每次去见桑兹太太进行心理疏导时,“多丽一直都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她从没有坐过沙发。沙发是花儿的图案,还有几个靠垫。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移到桌子一边,这样她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8]。自我隔绝体验中找不到空间定位的悲剧性感受,找不到自我价值和安全感的生存痛苦让她不可避免地又想起了劳埃德。劳埃德当初对警察说的那句让她蒙受不白之冤的话一直让她耿耿于怀。“我是为了免除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会知道,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他们。悲惨的命运”[8]。多丽觉得这话是对自己的莫大污蔑,倍感屈辱。但她的委屈痛苦却幼稚得如同一个孩子。“你叫我别和你顶嘴,否则就滚出家门,所以我才滚出家门的”[8]。她还是没能看清劳埃德沙文主义的本质,没能真正理解自我的丧失。这个几乎可当她父亲的丈夫,利用父权、夫权,藉由掌握她身体,控制着她的女性意识,改造着她的精神人格。从前在Mildmay是如此,如今多丽的身体空间似乎获得表面自由,经年累月的男权文化体系却已经将她异化,并逐渐内化出女性自我压迫机制,开始彻底的否定自我,“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什么用?”[8]并且,丈夫对多丽的长期压迫规训使她逐渐形成了对规范的认可和自动遵从,让她仍然觉得“要是连他的话都不听,她待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8]。多丽自限在无法真正慰藉自己的the Comfort Inn,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她又试图从劳埃德那寻求精神依赖。多丽收到劳埃德的信,里面声称他在另一个维度见到了孩子们,并且见到他们很好很快乐。这让她觉得安慰,感到自己有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当她自问是谁给了她避风港时,心底的念头是“不是桑兹太太。这是绝对的。不是那些坐在桌前手边放着舒洁纸巾的时光。是劳埃德给了她。劳埃德,这个可怕的家伙,这个被关起来的、疯狂的家伙。”[8],并且这样的想法渐渐在她脑海沉淀。仍然没有摆脱对男性依附,建立自我意识的多丽,一次次的,踏上前往去探望劳埃德的旅程,企图在这个犯罪型精神病患者身上再次找到她的精神家园。
四、探监的公交车——顿悟之旅
无论是作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命运反抗,探监旅程成为了多丽漂泊体验中的精神寄托。她无法放下过往,也无法摆脱对男性话语根深蒂固的迷思,于是屡屡前去看望在看管机构里的劳埃德。她的探监之行,也是她的精神家园寻求之旅,直到最后那次在救人后的顿悟,让她真正摆脱依赖,获得了独立与新生。
多丽得换乘三趟公交,花上约五个钟头的时间奔波一百来英里的路程,才能抵达劳埃德被羁押的机构。作为巨大的社会空间隐喻,三趟公交呈现了三种景观,三种人生体验与心境。
“坐第一趟车的时候,她感觉还好,就坐在车上看看风景。她是在海边长大的,那里至少是有春天的。但在这儿,好像冬天直接跳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现在出门已经热得要穿短袖了。一片片刺眼的水泊躺在田野之间,阳光从枯干的杈枝中倾泻下来”[8]。严酷的气候和惨淡的风光,如同她如今的处境,毫无生机。她忍不住回忆起自己成长的故乡,潜意识地对曾经的美好时光的怀念体现了她心底对幸福的渴望和向往。
等到上了第二趟车,“她开始神经紧张,忍不住琢磨,身边的那些女人,哪一个和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她们都是单身出门的,大半也都精心打扮过,大概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那些年纪大的,看上去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严格的老教区,大家都得穿上长裙、长袜,戴上帽子。而年轻的,仿佛属于灵活的教区,能接受女人穿裤装,配上鲜亮的围巾、耳环,还留一头爆炸式的发型”[8]。与其说多丽在琢磨车上其他女性是否和自己同目的地,不如说她在本能地寻找自己的同质群体。但公交车上众多女性,呈现了其异质多样性。藉由那些女人们的外观可见老一辈女性仍然停留在旧式世界,但年轻一代女性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自我。多丽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两种类型。她仍然是一个边缘人,融入不了新旧女性群体,融入不了社会。虽然她离开了劳埃德,离开了在Mildmay的家,有了新住处和工作,但是,被劳埃德多年圈禁规训至几乎毫无自我的她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变故茫然不知所措,加上和社会脱节已久,自然而然地陷入了痛苦和迷失当中,找不到自己的女性空间定位。
待上了第三趟,“她坐在车窗边,看着路边的指示牌,试图让自己平静。她在心里做游戏,让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要想”[8]。她机械地进行单词拼找,从窗外各种牌子或建筑上看到什么单词,就从里头引出另外的单词,从coffee里引出fee,再引出foe,从shop里找到hop,sop,so,posh等等。她的这番举动其实是在长期被压抑到尽头后的逆来顺受式的自我麻木。她没有选择,也无从选择,只能机械被动地承受一切。
这三趟公交之旅,如同在展示多丽生命中的各个阶段的风景——从年少时在母亲庇护下的美好岁月,到婚后的彷徨失落,再到经历身心摧残后的听天由命。她的女性空间,也从自由到压抑、扭曲。这时候,她还是挣脱不了劳埃德对她深入骨髓的羁绊。但最后那次探监之旅中发生的意外改变了这一切。
高速公路上一年轻男孩驾车出了事故,摔出车外。公交司机让大家不要下车,她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般,跟在后面下去了。她朦朦胧胧“或许是觉得自己特殊,是一个有用的人”[8]。她用劳埃德教过的方法给这孩子进行急救,帮助他恢复了呼吸。在等男孩呼吸稳定的时刻,她心中在呼喊“安静,请安静。......男孩子身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安静,不要让他失去呼吸的迹象。”[8]幸运的是,她心底的呼唤仿佛真的发挥了力量,“微弱但稳定的呼吸。仿佛他听到了,并且乖巧地依从了她”[8]。男孩终于被她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了。这一刻,她向来被压抑的女性话语权利得到了彰显,女性权威得到树立,被男性支配、塑造的女性,反过来又挽救了男性。多丽从救人中获得失去孩子的慰藉,也让她感受到身处的这个真切世界,周围的鲜活生命,自己独立于世的自信与力量。她终于彻底觉醒,当机立断,主动斩断了劳埃德对她的身心束缚。司机问她还去不去伦敦,即劳埃德关押所所在的那个城市,她决然回答“不去了”[8]。至此,多丽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发声,找到了独立的女性空间。劳埃德沉迷在虚妄的世界里寻找慰藉,多丽选择在现实的世界里重建自我,菲勒斯中心主义也就此被颠覆。
结语
如霍米巴巴所言:“空间是隐喻,也是一套实质性的关系”[9],门罗的《多维的世界》,也是个充满隐喻的世界,探讨的是社会性别对立背景下女性的空间,从身体,到性别关系,到精神、社会等等多维的生存空间。女主角多丽在从Maymild到 the Comfort Inn,到探监的公交之行,不同地域环境、空间场景的成长过程,彰显了她的女性空间寻求和建构之旅。个体命运是群体命运的缩影,多丽的生存体验,是古今中外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的写照,体现了她们的生存困境,为她们提供了审视自身的一个参照范本,揭露了女性只有突破男权中心话语,获得身心独立,才能真正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赢得解放。该小说最后叙事的逆转,颇具深意。男性权威貌似高高在上,支配着女性,但最终,却是女性在规训下挽救男性。它消解了以男性社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男女二元对立,超越了这种充满菲勒斯中心色彩的二分法,体现了门罗的女性主义主张,即反对将男女两性绝对割裂开来,提倡一种男女共存人格互补的平等社会意识形态。拒绝被贴上女权主义标签的她在该文本中并未鼓吹建立一种女性话语权威,与男性话语分庭抗礼,而是表达了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构新型两性关系的探讨与协商。这种观点更具理性思辨意识和开放性的包容姿态。
[1]Lefebvre, H.TheProductionofSpace[M].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p170
[2]Lefebvre, H.TheSurvivalofCapitalism[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p89
[3]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p205
[4]Wegner, Philli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IntroducingCriticismatthe21stCentury[M].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2,p181
[5]Massey, Doreen.Space,Place,andGender[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80
[6]Munro, Alice. Dimension[J/OL].(2006-06-05)[2016-07-18].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6/06/05/dimension
[7]Massey, Doreen.ForSpace[M].London: Sage, 2005,p149
[8]艾丽丝·门罗. 多维的世界[M].//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p16、p10、p11、p14、p13、p18、p4、p3-4、p4-5、p1、p7、p20、p32、p33、p5、p34、p36
[9]Bhabha, Homi.TheLocationofCulture[M]. London:Routledge, 1994,p30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