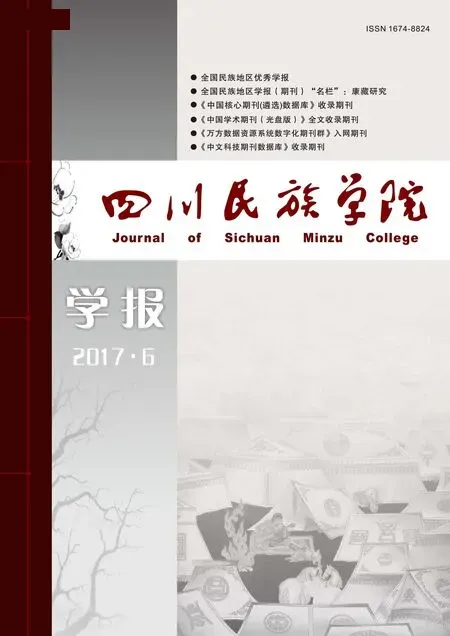近代康区政治变迁与传统地方精英的角色调适
——以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为例
叶小琴 陈 潘
一、变局与新生:近代康区政治变迁与新地方精英的长成
“政治变迁” 是人类学、民族学中出现频次很高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在描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时,该概念的使用得更为频繁,与此同时,“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经济变迁”等概念的使用亦颇为显眼。实际上,“政治变迁”也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步入了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均日益近代化,作为边陲之地的康区,在社会大趋势的影响下,亦产生了深刻变化。仅就政治变迁而言,其政治结构、政治文化等层面无不发生变迁。
首先是政治结构层面,在赵尔丰经营川边,对康区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前夕,近代康区的政治结构变迁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相对和缓的态势。*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康区主要以土司制度间接管理之,后来亦有进行直接管理的尝试,如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在打箭炉设立打箭炉厅,但在清末改土归流之前,康区的土司制度都是较为稳固的。在赵尔丰经营川边之前,四川总督鹿传霖、锡良等已经开始了对康区的革新。鹿传霖在任时,曾对瞻对用兵,主张收回西藏对瞻对的管辖,并实行改土归流,将康区纳入中央直接管辖之下。锡良则在康区积极推行一系列“新政”,从而加快了康区政治变迁的步伐。1905年,康区发生了著名的“凤全事件”,赵尔丰奉命派兵弹压,并由此开始了对康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从而将近代康区的政治变迁引向了更为剧烈的轨道。到了赵尔丰经营川边时期(1905-1911),奉令实行改土归流,每改流一地,便颁布改革之章程,康区的政治结构则发生了质的改变,土司制度的存在也失去了法理上的支撑。至于康区改土归流后的政治秩序重建,赵尔丰、傅嵩炑等人原本是打算筹设西康省,以实现类似于东三省的西藏、西康、四川等“西三省”目标,但由于清王朝的快速崩塌,赵尔丰等人的西康建省的政治理想亦随之幻灭。旧的政治结构被打破,新的政治结构尚未形成,康区的政治秩序进入了一种相对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需要强调的是,康区政治秩序的混乱无序仅仅是相对而论,从政区的角度而言,主要是“省”这一高层政区的混乱无序,在县以下,土司、头人、僧侣的存在仍然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相对有序运转。此后,康区经历了先后由“川边经略使”“川边镇守使”“西康屯垦使”等节制的川边特别行政区时期,到刘文辉接管西康、筹划并最终建成西康省,一直延续至建国之初。
除了旧有的政治结构发生改变以外,近代康区的政治变迁还表现为政治文化的变迁,而且这种变迁是政治变迁研究更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更能体现近代康区社会的变化,也是本文进一步展开的一个分析基础。因为它是基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分析,体现了“政治人”对于政治的一种内心感受的变化过程。政治文化具有民族、地域、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亚文化,因民族方面的差异性可称之为民族政治文化*周平认为,民族政治文化即民族共同体成员普遍存在的对政治的主观取向,这种主观取向有三种基本的成分,一是认知性成分,二是情感性成分,三是评价性成分。具体参见周平:《民族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3页。。笔者认为,近代康区的政治文化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分界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就是巴塘格桑泽仁事件(亦称省防军事件)、诺那事件、甘孜事件的发生,这不仅标志着近代康区精英阶层*笔者以为,对康区而言,传统地方精英主要应当包括土司、头人、上层僧侣等,新地方精英则应当涵盖新式知识分子、商人以及离职官员等。民族主义的崛起,也应当视为近代康区政治变迁质的变化。*其实,除了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区的三次大事件的爆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析对象外,我们还应联想到南京国民政府三、四十年代“新县制”推行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依靠康区精英阶层的鼓吹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同时也营造了西康建“省”的浓厚氛围。在格桑泽仁事件中,格桑泽仁、刘家驹等藏族本土精英打出了明确的政治口号“康人治康”,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实现既不同于川、又有别于藏的康区地方自治。对于今天而言,我们了解这一本土精英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论著得以实现,比较具代表性的如格桑泽仁的《边人刍言》*此外,格氏尚有《康藏最近之情形》《西康改省之计划》《康藏概况报告》《西陲佛教概况》等。、江安西的《西康建省计划》、冯云仙的《目前西康兴革之要点》等。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方面表现出与传统地方精英很大的差异性,他们的政治主体性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中得到进一步强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政治自觉性。*如江安西认为“西康各县,自民国以来,缺乏有力、统一的上级机关之监督之统治,各县执政者均各自为政,各地之政治,全失了政治上分工合作之效用”,“故西康政治之建设,首宜求行政之系统清明,施政有共同的标准”,并建议组织省政府,取消土司等所有特殊阶级之名称,培养地方自治人才,树植自治之能力,渐谋地方自治之施行。冯云仙更是提出了划分政教、废除土司、严修兵备、废除世袭头人制、禁止不通汉文者充头人等西康政治革新措施。参见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纪要(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尽管各自细节之处有所差异,但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西康建省与康人自治的高度政治参与意识。近代康区新地方精英群体的成长,实际上不得不提及赵尔丰等清王朝的革新派人物的贡献,赵尔丰经营川边时期,对发展教育尤其重视,“光绪三十三年,赵尔丰照会吴嘉谟充任关外学务局总办,教育由政府主持,强迫入学,锐意推进。四五年间,成绩卓著,人民虽视读书为差徭,而西康教育,实于此时奠其基础。”[1]巴塘作为巴塘事变的发生地,首当其冲地成为教育改革的试验田,巴塘初定,即划为学区之“中区”,较之康区其他区域更早,这也成为我们今天诠释巴塘在近代康区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一把关键的钥匙。
二、踌躇满志与踟躇不定:末代土司甲宜斋的政治迷思
上文述及,近代康区的政治变迁促使新地方精英的成长,并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与民主国家认同相伴随的自觉的民族主义[2]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新地方精英相比,传统地方精英对于近代康区的政治变迁则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康区的传统地方精英们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呈现出东西二元世界:趋近帝国:向东的摇摆;逃离帝国:进入关外的世界[3]。在他们的观念图式里,始终模糊而清晰地存在着清廷vs拉萨、汉官vs藏官、大皇帝vs甲拉王等二元符号体系。*“大皇帝vs甲拉王”的二元对立,更多的是针对康区民众的观念图式而言的。同时,在康区世界的内部,还存在着寺院vs土司衙署、土司vs喇嘛等二元符号体系。在这个符号体系里,相互对立的两者之间的权威边界是相对模糊的,同时也是一种动态过程。通过了解章谷与朱窝土司争袭、德格土司兄弟争袭、巴塘事变、桑披寺事件、三岩抢案等诸多事件,我们均可从中发现上述二元符号体系的存在,*光绪十八年(1892),在章谷与朱窝土司争袭事件中,章谷土司扎西旺加因为朝廷赏赐的官印、文书、案卷等物被妻子卷回娘家章谷土司府衙内,并企图以朱窝接管章谷,扎西旺加不服,因而向县官张继告状。面对张继让朱窝土司索诺木多布丹将章谷土司的官印和文书交还章谷土司的要求,索诺木多布丹随即翻脸,骂道:“堂堂大汉官,小民全指望大人作主了,没想到大人的屁股坐在了仇人一边”,并扬言“有只活狼,就有一支死羊,要交官印,就拼个鱼死网破,如果汉官不讲理,我就去找藏官论理”;光绪十七年(1891),康区桑披寺与理塘寺发生矛盾,鹿传霖派守备李朝胜前往处理,与其部下施文明等一道被桑披寺堪布普仲扎娃杀死并剥皮填草,悬于寺庙,供人参观。具体参见张永久:《消失的西康》,台北新锐文创,2014年版;(清)张继:《定瞻厅志略》;刘赞廷:《民国定乡县图志》等。一方面,在土司看来,清廷的官印与文书是权力的象征,有了这两样东西,自己的统治才显得更加名正言顺;在遇到难以调和的纠纷时,土司和喇嘛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清廷的官员,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对于这种基于政治而构建的等级秩序是认同的。另一方面,拉萨在他们眼中的神圣性亦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权威与世俗性权威是可以对等甚至超越其上的。他们观念图式中的“汉官vs藏官”分野,显示了在纠纷解决的特殊语境下,两者都可以扮演纠纷解决者的角色,而且他们若是认为一方处理不公,则自己就应当从另一方那里获得权利救济。客观而言,在改土归流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康区传统地方精英们一直试图保持一种游离于汉藏之间的状态,尽管这种中间状态与后来的新地方精英群体的那种高度自觉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有着明显区别。
作为康区四大土司之一的明正土司家族,却是一个例外,其似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倾斜,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其所存续的数百年历史,也就是历代土司追随朝廷东征西讨并获得荣耀的忠贞史与家族辉煌史。我们还可以从《明实录》《明史》等官方典籍中发现明正土司多次前往明廷朝贡的记载,[3]如果说明正土司自备兵马粮草跟随朝廷出征表明了一种誓死效忠、绝不叛乱的姿态的话,那么它与朝廷的频繁互动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土司通过朝贡而融入内地文化体系的心态,如果说前者赢得的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互信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对于内地文化积极靠拢的个体自觉。实际上,“整个明代明正土司都和中央王朝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3],“明正土司效忠朝廷,在康区土司之中为首”[4],值得注意的是,与明正土司一样享有“世代忠贞”美名的还有一个叫做瓦寺土司的家族,这个家族也一样追随朝廷参与了多次征伐活动,并彪炳史册,[5]并且,它们同属“嘉绒十八土司”。终明清两代,朝廷在川、藏域内的绝大多数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有明正土司,包括瓦寺土司的身影,这可以说是一种数百年来形成了政治惯性,也可以说是其家族内部的政治经验,成为土司家族代代相承的一笔宝贵政治遗产。总之,通过朝贡与军功这两大“法宝”,明正土司家族在康区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强盛。
光绪二十八年(1902),甲宜斋承袭明正土司以后,依然延续了祖辈过去的“光荣传统”,在清帝国存续的最后数年里,甲宜斋追随清廷参与了数次平定叛乱的征伐活动,包括德格土司兄弟争袭、泰宁、巴塘变乱等康区大事件,甲宜斋都坚定地站在了清廷的立场,甚至可以说是扮演了马前卒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甲宜斋的积极支持,清廷在川边的改土归流相对而言才进行得如此顺遂。当然,甲宜斋也获得了清廷所赐予的殊荣,“短短数月之内,连续封赏两次,这在土司家族的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土司家族的声望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迅速达到了最高点” 。[3]
然而,就在明正土司家族包括甲宜斋的人生钟摆摆到最高点的时候,猛然间跌入谷底,宣统三年(1911)六月,明正土司被收缴印信号纸,成为德格、巴塘、理塘等“康区四土”中最后一个被改流的土司,这已接近赵尔丰川边改流的尾声。明正土司由于其一贯的恭顺,故被安排在靠近尾声的阶段予以改流,但改土归流是赵尔丰经营川边宏图大业的重要一环,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初六,赵尔丰在川边设治建省的行动及规划终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而且饬令边务大臣仔细调查,凡有土司、土官地方,酌拟改流办法,奏请核议施行,[6]这就注定即便是一向恭顺的明正土司亦难逃被改流的宿命。然而从甲宜斋的过往言行来看,他或许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对于时局的深刻变化,他还尚未具备特别敏锐的觉触能力。在甲宜斋从祖辈那里承继而来的固有观念结构里,只要“世代忠贞”,便可换来家族的荣耀;只要紧随朝廷,便可获得世代的强盛。不得不说,甲宜斋的这种政治逻辑在清末以前是基本适用的,亦符合历代“天下帝国”观念下的边疆政治秩序的内在要求。只是,随着清王朝不断被卷入世界深刻变化狂潮之中,其自身亦面临着近代化的非主动性选择,作为高度依赖从前那种政治互动模式进而巩固自身权威的末代明正土司,甲宜斋的确很难在一时之间适应这种新的变化,他显得不知所措、踟躇不定。
甲宜斋的这种政治心理我们从他人生最后十年的经历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一方面是以叛乱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改土归流的抗拒,一方面则是选择配合以完成国家对康区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构,譬如,甲宜斋在改土归流前后先后有四次叛乱,[3]包括他的死,都与“反对现政府”有关系。*1922年,甲宜斋因为“反对现政府”被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关进监牢,其部属计划越狱,失败溺亡。然而在这一时期,甲宜斋又展现出对于政府的“配合”,1915年,川边镇守使署授予甲宜斋以康定总保正头衔,配合县级官员有限参与原属土司管辖的康定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1916-1917年还曾做过短期的理化县知事,并且在1912年和1917-1918年的两次康藏纠纷中甲宜斋以自身的特殊身份和经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后一次的康藏纠纷中,甲宜斋以“川边镇守使夷情调查员”的政府代表身份与康定县知事韩光钧一道奉命前往昌都与藏方交涉,并出色地完成了议和任务。可以说上述两种行为是重叠交错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复杂而纠结的内心世界。清末民初康区土司的叛乱与复辟可以说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作为“世代忠贞”的“内土司”明正土司,其反叛背后的缘由显然更具有代表意义,刨除个体政治情感的层面,这足以说明明正土司原本对于中央政府的世代效忠正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互动模式之下的,中央政府的改土归流则打破了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必然在一定时期内引起反弹。可以说,正是由于明正土司对于中央政府前后两种近乎极端的政治姿态,才凸显了甲宜斋的作为末代土司所具有的典型意义,这也是本研究选题之初的动机和研究的旨趣所在。
从甲宜斋改土归流前后的数十年的经历来看,他在近代康区社会政治剧变面前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角色调适应该说是不太成功的,尽管他曾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新的政治结构体系,并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官吏,*除了短暂的理化县知事生涯,严格来说,甲宜斋应当属于政府雇员而算不上正式的官员,康定总保正本身就是非官方的协助政府管理基层事务的人员,“川边镇守使夷情调查员”则明显属于临时性质,从名称上看应当是川边镇守使的幕僚或者顾问。以及主动或者被动地将自己置身于新政府的司法性角色中。资料显示,民国以来,甲宜斋曾卷入多次法律诉讼中,既有被动的被告身份,也有主动的原告身份,而诉讼主体则囊括了从前从属于土司的头人、土民,驻扎在康定的商人以及甲宜斋在新政府中的同僚们。[3]在土司制度的话语体系中,作为土司的甲宜斋被自己的头人和土民起诉或者自己起诉头人和土民,这是异常荒诞的。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只可能作为审判者、裁决者而存在而绝不可能成为诉讼的原被告以及纠纷当事人的。由此可见,甲宜斋面临着主动或者被动的角色调适,但实际上却是不成功的,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从前土司权威的眷恋,试图恢复其原有统治。在客观上,他亦被一部分仍忠于自己的部属撺掇挑战新的政治结构体系,同时他还自始至终不被新政府当局完全信任,被认为随时具有反叛的嫌疑。这就几乎决定了这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旧的政治秩序已然不可恢复,一方面作为末代土司的甲宜斋是不可能真正融入新的政治结构体系之中的。
三、末代土司的政治遗产:基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语境
土司制度作为一个时代已经结束,然而,在几百年的延续过程中,土司制度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目前多数人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从整体上把握土司政治文化遗产,实际上,末代土司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群体,特别应当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语境之下。
一般而言,我们在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时候,都离不开地方精英这个概念,地方精英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一直以来便具有重要地位。所谓地方精英,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玛丽·兰金(Mary . Rankin)等人认为是指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7]按照这个定义,笔者认为土司、头人群体,也具备了地方精英的属性,但遗憾的是目前的研究中,基本鲜有将土司群体界定为地方精英的。在多数情况下,学界在研究近代以来的地方社会时,其关注重点在于具有鲜明中原文化特色的“内地”,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地方精英大抵包括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等,[8]由于土司制度主要出现在边疆、民族等语境中,因而鲜有进入精英研究者的关注视野的。*尽管研究者鲜有将土司群体纳入地方精英的关注视野,但并非意味着研究者对土司的不关注,事实上近代以来康区土司曾引起不少外国学者的重视,只不过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之下,土司成为了与中央政府平行的“王国”而自动隔绝了“国家-土司(地方精英)-地方社会”这一思维模式存在的可能性,正如他们把西藏与中国相互对立起来一样。笔者以为,如果完全参照“内地”文化体系,近代以前尤其晚清以前,像康区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更为偏远的乡村,是不不太可能会存在我们平常所指称的地方精英群体的,但这与地方精英连接国家与地方社会这一普遍性社会规律是相悖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县级以下),近代以前几乎不存在士、官、商群体,而土司、头人、上层僧侣等占数量和地位的优势,因此他们担负了连接国家与边疆基层社会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土司的身份是多重的:因为有中央王朝封赏的印信号纸,所以具有朝廷官员的属性;因为在辖区内有较为充分的阶级统治权,所以具有“土皇帝”的属性;因为常常活动于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所以具有地方精英的属性。也就是说,对于土司不能简单而论,需要分空间分时段,尤其是需要分时段,改土归流以来的土司地方精英的属性尤其明显。
相对于近代康区的新地方精英,土司群体可归为传统地方精英。与新地方精英相比,土司群体的权威来源主要是属于传统型,即建立在人们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权威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他同时指出三种权威的划分属于理想状态,实践中找不到三种权威的纯粹形态,而是以混合形态存在。自元代康区正式确立土司制度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在其施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土民眼里,土司就是甲波(王),这种传统型权威因为中央王朝的授权和认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新地方精英的权威来源主要是属于魅力型,这种权威依赖于个人的优秀品质而获得民众的自愿服从,因此魅力型权威不如传统型权威稳固。*在韦伯看来,魅力型权威具有不稳定性,而且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常规的”权威形式,也就是传统或者官僚型支配。“因为查里斯玛权威完全依赖于是否为被统治者所认可……但是当查里斯玛组织处于理性化进程中时,很有可能,这种视之为一种合法的结果认可,会为另一种结果所取代,即为'民主的合法性'基础的结果所取代”。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对于末代土司而言,土司原来具有朝廷官员的身份,对地方具有阶级统治的成分,通过改土归流,其身上的阶级统治者身份逐渐剥离,亦成为为与新地方精英相类似的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者和代表者。但此时康区新地方精英群体尚未长成,新旧精英尚处在分化重组的过渡时期,*随着清末以来新式教育在川边的强力推进,土司、头人群体的子女与川边普通百姓(主要是具备一定财力但无多少政治权力的人家)子女一道,亦开始广泛接受中西学教育,成为川边新地方精英的重要来源之一,譬如末代土司甲宜斋的儿子甲联升,与格桑泽仁曾是同学,后来继续学医。做过康定县县长,曾对木坪土司家族甲安仁的叛乱进行过劝说。参见冯有志:《西康史拾遗》,巴蜀书社,2015年版。因此末代土司在基层社会事务组织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当末代土司陆续离世,其子孙后代与新地方精英在知识结构、政治参与意识、思维、视野等方面可谓几无差异,他们甚至已可划为新地方精英群体,但作为土司后裔,他们却拥有比较优势,也就是其权威的“祖传血统”,[9]具有天然的可承继性,因此他们对于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力和代表性显然更具有“合法性”。尤其是在康区,这种情形似应更为明显。至于土司后裔及其与当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证分析,因为缺少必要的资料,将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在此不予详述。
[1]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纪要(上)[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444
[2]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M].三联书店,2016年版,p89、p182
[4]康定县志编委会.康定县志[M].p418
[5]建德·东周.马尔康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索观瀛传[M].马尔康县政协委员会,1993年
[6]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M].巴蜀书社,2004年版,p147
[7][美年版].玛丽·兰金.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变:1865-1911年之浙江[M].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
[8]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J].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
[9][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M].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