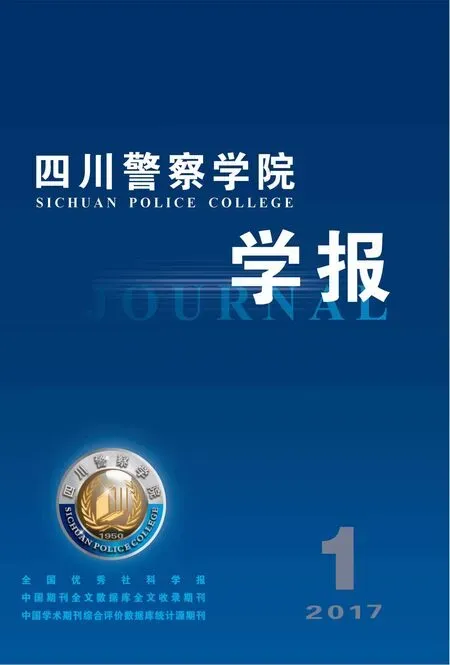滥伐林木罪司法误区及其匡正
——以重庆法院近年来相关判决为视角的考察
胡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 404020)
滥伐林木罪司法误区及其匡正
——以重庆法院近年来相关判决为视角的考察
胡胜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 404020)
滥伐林木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犯罪主体泛化,罚金判处有失妥当,赃物处置有违罪《刑法》规定,与森林法的衔接存在芥蒂等问题。事实上,在入罪上,林木所有权人出售林木是其行使所有权的体现,只要其未帮助砍伐,或主动教唆买受者无证砍伐,就不可能成立滥伐林木罪;在量刑上,罚金的判处不仅要体现罪刑相适应,而且必须考虑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涉案赃物处理上,无论涉案被滥伐的林木最终去向,刑事判决都应严格依《刑法》第64条进行表达;在与森林法的衔接上,必须树立先刑后行的理念。
滥伐林木;罚金;赃物处置;实证研究
森林具有吸烟滞尘、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效,被誉为“地球之肺”。保护森林资源是建设“美丽中国”,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尽管我国法律、政策一再强调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甚至将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入罪,然在实践中破坏森林的行为仍屡禁不止。通过统计发现,在所有破坏森林的行为中,滥伐林木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遗憾的是,在刑法学界,对滥伐林木罪实证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且从其关注层面来看,更多的是对滥伐林木罪司法样态的简单分析,而极少涉及司法疑难问题。以此为出发点,笔者对重庆法院系统近年来滥伐林木的相关司法判决做了实证研究,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据以研究的滥伐林木罪样本及其整体样态
(一)分析对象:基于重庆地区随机抽取的125份一审判决。
本文研究的对象,系重庆法院系统公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一审滥伐林木案件,具体选取过程如下。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栏目中选择“高级检索”,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案由”滥伐林木,再将审判程序限定为“一审”,将地域限定为“重庆”,共得出273份滥伐林木罪判决。然后在此基础上,随机抽取125件作为分析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统计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具体而言,则是以人工方式逐一阅读每一份司法判决,并主要就“犯罪主体”、“行为对象”以及“定罪量刑”等三个大方面情况展开统计分析。
(二)整体样态:对定罪量刑等因素全方位的展开。
通过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滥伐林木罪呈现出犯罪主体年龄段相对集中、文化程度显著偏低、行为动机以牟利为主、刑罚相对轻缓等显著特点。
1.犯罪者年龄段相对集中。在这据以分析的125件一审滥伐林木案中,共涉及142名犯罪人。其中女性犯罪人2名,男性犯罪人140名。在年龄方面,除24名犯罪人由于判决书并未标注出生年月,无法考证外,犯罪者跨越各个年龄段,但又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具体而言,其中出生于1930年代的1人,出生于1940年代的4人,出生于1950年代的15人,出生于1960年代的38人,出生于1970年代的50人,出生于1980年代的8人,出生于1990年代的2人。相比之下,“60后”、“70后”是犯罪主力军,共计88人,占总人数的62%,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比数,都占绝对优势。
2.犯罪主体文化等素质相对偏低。在这125件、142人滥伐林木案中,在文化程度上有13人判决书并未表述,进而无法进行统计。在其他129人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含文盲、肄业)78人;具备初中文化的(含肄业)43人;具备高中文化的6人,具备大专文化的2人。在具体比例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犯罪总人数的93.8%,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只占6.2%。总体而言,犯罪主体文化程度显著偏低。此外,就犯罪主体的职业而言,除一人为工人以为,另外141人要么是农民,要么就是无业者。
3.犯罪人主观恶性较轻,多为偶犯初犯。就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言,除个别犯罪人系明知故犯外,绝大部分犯罪人事实上主观恶性都较轻。在这142名犯罪人中,具有犯罪前科的仅占8人,其中因犯滥伐林木罪被刑事处罚又再次犯罪的4人。另外134名犯罪人并无任何不良记录。且在行为动机上,不少犯罪人系家庭困难迫不得已,或出于自用而滥伐林木,并无任何其他不良动机。
4.行为方式以“买山”伐木出售获利为主。从研究的案例情况来看,行为人滥伐林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利,行为类型以“买山”私伐出售为主。具体而言,这125件滥伐林木案,在行为动机上,主要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出于自用而滥伐林木,这类案件共12件,占案件总数的9.6%;第二类是出于牟利而砍伐自家自留山上的林木,这类案件共13件,占案件总数的10.4%;第三类是出于牟利而购买并砍伐他人自留山上的林木,这类案件共100件,占案件总数的80%。在行为方式上,办理了采伐许可证,但超期或不按规定采伐的7件,占案件总数的4.9%;未办理采伐许可证而私自采伐的135件,占案件总数的95.1%。
5.刑罚处罚相对轻缓。在刑罚方面,整体而言处罚相对轻缓。142名犯罪人中被宣告缓刑的105人,占案件总人数的73.9%;被判处拘役以及有期徒刑等监禁刑的36人,占案件总人数的25.35%;被单处罚金刑的1人。且就被监禁的36名犯罪人而言,在量刑上被判处两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仅8人,只占总人数的5.63%。
二、实践之殇:滥伐林木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入罪对象有失公允。
统计发现,在滥伐林木罪司法实践中,虽然打击的主要是具体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人,但部分法院存在将森林权属出售者与具体实施滥伐林木者“一锅端”的倾向。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出自同一法院的判决,有的仅仅处罚具体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人,有的则将森林权属者与具体实施滥伐林木者作为共犯处理。体现在具体数据上,在笔者研究的这125件滥伐林木案中,有118件只处罚了具体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人,但另外有7件则将林木权属者与滥伐林木者作为共犯处理。如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判决的张某甲、罗某甲滥伐林木案。该案的基本事实是,“2014年2月,被告人张某甲、罗某甲电话商谈,张某甲以200元/立方米的价格购买罗某甲自留山林内的松树。随后张某甲以450元、500元/立方米的价格将木材转卖给李某某,且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授意张某乙雇请工人砍伐。”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被告人张某甲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组织他人砍伐林木,数量较大;被告人罗某甲在明知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其自留山内林木卖与他人砍伐,数量较大;其行为均构成滥伐林木罪”[1]。又如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判决郭某某、庞某某滥伐林木案。该院在判决书中写道“2012年11月中旬的一天,被告人郭某某因家中修房子需要林木,便电话告知被告人庞某某需要砍伐其自留山中的林木,庞某某在电话中表示同意。次日,在二人均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郭某某雇请工人砍伐庞某某家位于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山林里的172株树木。……被告人郭某某、庞某某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滥伐林木,数量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2]。暂且不论此种做法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在规范层面是否妥当,但毋庸置疑的是同案不同判、选择性执法显然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不仅对于犯罪人有失基本公正,且对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亦造成了相当冲击。
(二)罚金判处有失妥当。
在整体上滥伐林木罪的刑罚虽然较为轻缓,但在个案上量刑考量仍存在一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罚金刑的判处上,司法实践对于滥伐林木罚金的数额缺乏统一尺度,甚至存在恣意之嫌。从判决反映的情况来看,被告人滥伐林木的数量一般介于几立方米到几十立方米之间,所获之利也都在万元以下,但在罚金判处上,罚金数额却被判处一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其尺度之大让人难以捉摸。具体而言,其一,在罚金的依据上,并不存在统一标准,罚金的数额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并不成比例。诸如滥伐林木的数量、获利数额等未并必然成为影响量刑的因素。如易某某滥伐林木案,易某某砍伐他人自留山中林木,经鉴定立木蓄积共计为35.4931立方米。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3]。而出自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江某某滥伐林木案,江某某滥伐他人自留山柏树共计150根,经检测立木蓄积28.4793立方米,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4]。应当说无论是从滥伐林木的株数还是立木蓄积方数,易某某的危害都比江某某重,在二者其他量刑情节大体相同的情形下其处罚却比江某某轻。由此,司法实践对于滥伐林木罪罚金条款的滥用可见一斑!其二,并未考虑刑罚个别化,诸如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个人情况等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付某某滥伐林木案,年近七十高龄的被告人付某某因经济困难,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自家位于石柱县山林中的林木43株,后经鉴定立木蓄积为16.409立方米。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付某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5]。而在章某甲滥伐林木案中,被告人章某甲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马尾松20余棵出售。经鉴定,折合活立木蓄积29.922立方米。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滥伐林木罪判处被告人章某甲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千元[6]。虽然在主刑上,章某甲的处罚要比付某某重,体现了罪刑相适用原则。但就附加刑的判处而言,都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则有失公平。尽管付某某滥伐林木也是出于获利,但毕竟其是出于生计困难迫不得已,其主观恶性比纯粹的销售牟利要轻,进而预防必要性较小。人民法院对其判处高额罚金,只会加剧其原本困难的生活,不利于从根本上打击和预防犯罪,缺乏刑罚个别化的特殊考量。
(三)赃物处置有违罪刑法定。
从判决反映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判决都存在“没收违法所得”、“林木予以没收”等表述。从表明来看,赃物处置似乎不存在问题。但仔细分析便会发现,滥伐林木罪司法实践对赃物的处置仍存在问题有待探讨。这集中表现在部分判决对于滥伐的林木已被转化成成品的场合并未对赃物处置做出回应。如杨某甲滥伐林木案,被告人杨某甲在未办理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自家自留山林木83株,立木蓄积18.333立方米,并全部用于修建羊圈。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只是在判决中表述“另查明,被告人杨某甲所采伐的林木已用于修建羊圈”,而并未对赃物进行折价等其他处理[7]。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之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应当说,根据《刑法》的规定及其精神,只要是违法所得的财物,就不论其原物是否存在,是否已转化成其他成品,都应当予以追缴。故司法实践对于滥伐的林木已被转化成成品的场合并未对赃物处置做出回应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无疑问。
(四)与其他法律衔接存在芥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9条之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根据该法律,对于滥伐林木者,无论其是否构成犯罪,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都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在性质上,该法律由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根据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决定》修正。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同属法律,在位阶上并无高低之分。故在行为人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场合,一方面人民法院依《刑法》之规定对犯罪人定罪处罚,另一方面林业主管部门又可依《森林法》之规定对行为人施以处罚。由此,则由于人民法院并无直接判罚被告人补种的权利,致使滥伐林木者在经过繁杂的司法程序后,又得由林木主管部门来“善后”,这不仅有损于办事效率,也极可能导致林木主管部门因缺乏与人民法院的沟通机制而遗漏、甚至推卸责任,致使部分犯罪人游离于补种责任之外。此外,人民法院对于犯罪人的罚金与林木主管部门的罚款界限并不明确,这极可能导致行政机关因处理程序不同而产生不公平后果。若“行政”先于“刑事”。也即行政机关在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前依《森林法》所规定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规定,对行为人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此时,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人民法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同样必须对犯罪人判处罚金。虽然根据规定,行政罚款应当充抵罚金数额,但由于之前行政机关已处以高额罚款,一般而言罚金数额不可能再超越罚款数额,由此致使处罚更严厉的罚金处于宣示意义。不仅如此,若“刑事”先于“行政”,更会使得案件处理不公。从实践情况来看,司法机关的罚金数额一般并未达到行政机关所规定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标准,此时,由于“刑事”先于“行政”显然要比“行政”先于“刑事”的场合对行为人的处理更严厉,进而致使同案不同判现象的产生。而林木主管部门要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的目睹不公正判罚的存在,要么只能依《森林法》之规定,在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范围内“补罚”,但“补罚”的做法是否符合法律原理以及精神本身便存在巨大疑问。因而,在滥伐林木罪司法实践缺乏与其他法律有效衔接的情况下,无论是何种选择,其都非最佳方案。
三、理性回归:滥伐林木罪的规范理解与制度重构
(一)滥伐林木罪构成要件的规范理解。
“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8]。对滥伐林木罪刑事责任的追究必须紧紧围绕犯罪构成。虽然林木权属一方明知对方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将其自留山内林木卖与他人砍伐,在表面上符合教唆犯、帮助犯的规定。但事实上其与一般的教唆犯、帮助犯存在重大差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29条第三款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也即我国法律明确承认村民种植在自留山上的林木,其所有权归种植者所有。既然如此,根据民法规定,所有权人当然就享有占有、使用、收益、销售等处分权。尽管《森林法》第32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但从内容来看,其限制的也只是在采伐时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并非对林木权属者处分权的剥夺。质言之,若林木权属者不采伐,而仅仅只是诸如转让林木所有权,则法律对其并无任何限制。也许也可认为这也是一种采伐程序的限制,但其也仅仅只是针对实施采伐的行为人而言的。根据200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30条规定,个人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还应当提交包括采伐林木的地点、面积、树种、株数、蓄积量、更新时间等内容的文件。从其规定可以看出,在林木所有权人出售林木权属的同时,其并无替买受者办理采伐许可证的义务,若买受者需要砍伐林木,其完全可持林木所有权证书、买卖合同等自行办理。
故司法实践中诸如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黔江区人民法院将林木权属出售者与买受并具体实施滥伐林木的行为人“一锅端”的做法是有违刑法基本原理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滥伐林木罪构成要件的误读。也是对林木采伐许可证办理过程这一基本常识的忽视。在林木所有权人未出售林木所有权的前提下,试问林木买受者何来的采伐许可证?事实上,林木所有权人出售林木是其行使所有权的体现,自其与买受者达成转让协议起,买卖合同就已成立,此时对林木的处分理当由买受者行使,采伐许可证也理当转由采伐者自行办理。故此时只要原林木所有人未帮助砍伐,或主动教唆买受者无证砍伐,就不可能成立滥伐林木罪。
(二)滥伐林木罪刑罚条款的理性适用。
1.罚金刑的限制适用。我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而“犯罪情节是指在刑事案件中能够说明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9]。也即罚金必须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用。但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罚金意味着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故在判决罚金时,既要考虑犯罪人现有支付能力,又要考虑其将来的职业状况和其他情况”[10]。因而,在判处罚金时,除了遵循《刑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条款外,还必须考虑刑罚个别化原则。以此为出发点,就滥伐林木罪而言,罚金必须以滥伐林木的数量、滥伐林木的动机、行为人的一贯表现等反映滥伐林木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为依据。与此同时,又要适当考虑行为人的支付能力等个别情况。我们以为,对于那些因家庭困难不得已而砍伐自家自留山林木出售的初犯,以及出于自用而砍伐少量林木的偶犯,可判处最低罚金数额,也即人民币1000元。至于罚金的上限,参考《森林法》之规定,将其设置为行为人滥伐林木违法所得五倍以下,既可以实现与《森林法》的衔接,又可以体现罪刑相适用原则,并限制过于自由的罚金裁判权。
2.涉案赃物之妥当处理。“任何人都不能因其犯罪行为而获利”,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案财物的一般原则,对此,我国也不例外。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这是我国《刑法》关于涉案财物处理的一般制度。尽管对于该条内部逻辑关系在刑法理论上仍存在一定争议,但通过该条可以明确看出,应予没收的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该退还的则是被害人的合法财产。由此,当前司法实践有的判决不提及赃物处置的做法是否妥当必须依赖此条进行检验。根据我国学者的说法,广义上的“违法所得的财物”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形成控制性支配的财物以及其他财产性利益”[11]。故对于被滥伐的林木,即使是已经转化成成品,只要在其控制之下,就仍然属于违法所得范畴,就理应适用《刑法》第64条之规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杨某甲滥伐林木案中其所采伐的林木已用于修建羊圈,如何追缴成为问题。我们以为,对于在实践中如何追缴那是执行机关的事情,人民法院只需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如实依法表达追缴即可。且事实上对于执行机关而言,此种情况下进行追缴并非束手无策。一是将羊圈拆除,然后将木头予以没收;二是以被滥伐的林木株数以及立木蓄积为单位,由鉴定机构依市场行情进行估价,然后“折价没收”。因而,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人民法院对于涉案赃物都没有不予提及之理由。质言之,无论涉案林木被如何处理,人民法院在判决中都应根据《刑法》第64条之规定进行“追缴”或“没收”之表达。
(三)滥伐林木罪与其他法律的有效衔接。
1.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刑法》与《森林法》相关条文之衔接。根据我国《森林法》之规定,对于滥伐林木的行为,林木主管部门既可以责令补种,又必须对行为人施加罚款。且从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其对于行为性质到底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并无限制。因而在理论层面,《森林法》的相关规定也适用于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诚如上文所言,如此不仅有损于办事效率,也极可能导致遗漏对犯罪的打击,致使部分犯罪人游离于补种责任之外,更有甚至会加剧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混乱。我们以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之下,存在两种解决方案。路径之一便是对《森林法》相关规定进行限制解释。也即认为《森林法》第39条关于“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是对滥伐林木一般违法行为的规制,其对于犯罪行为并不适用。对于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全部交由《刑法》处置。此种解释有法律上的依据,因为《森林法》第39条第四款规定“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体系解释原理完全可认为《森林法》对滥伐林木的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做了不同规定。不过此种解释的问题在于放纵对滥伐林木者补种责任的追究,不利于生态恢复。路径二便是对《森林法》之规定做扩大解释,认为第39条关于“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是对一切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但如此解释,必须树立先“刑”后“行”理念方能得到妥当处理。在滥伐林木构成犯罪时,一方面人民法院依《刑法》对犯罪人定罪量刑,同时将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移送相关林木主管部门,由其依《森林法》之规定,仅责令犯罪人补种滥伐林木株数五倍的树木①。相比路径一,此种解释虽然有损于效率,在司法程序上增加了法院裁判文书移送林木主管部门这一环节,但能最大限度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环境保护立法宗旨。
2.滥伐林木罪“一体式”处罚模式之构建。在规范层面,虽然可对滥伐林木罪与其他法律的有效衔接找到合理路径。但其不仅有损于效率,也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我们以为,相比之下,建立滥伐林木罪一体式处罚模式更具合理性。也即,就滥伐林木的一般违法行为而言,由《森林法》进行规制。但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则全部交由《刑法》处罚。在条文设计上,具体而言,可维持滥伐林木罪的现有条款不变,只需将森林法所规定的责令补种条文纳入《刑法》条款即可。如若坚持对《森林法》第39条的限制解释,甚至无需动用刑事立法,仅由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将责令滥伐林木者补种林木纳入判决书中就可实现这一目的。
四、余论
“化民之道,故在政教而不在刑威”。从司法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滥伐林木罪的犯罪主体主要是初犯、偶犯,滥伐林木再犯只是个例。因而,一味强调查处与打击未必就是保护森林资源的最佳手段。我们以为,滥伐林木罪多发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广大农村地区居民缺乏对滥伐林木的违法性认识,简单的以为是行使林木处分权的体现。由此,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对林木的认识,引导民众合理合法砍伐,方是扭转滥伐林木罪多发态势之根本之道。
[注释]:
①由于已对犯罪人适用了罚金刑,故不再对其罚款。
[参考文献]:
[1]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4)南川法刑初字第00257号刑事判决。
[2]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4)黔法刑初字第00171号刑事判决。
[3]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2011)奉法刑初字第00395号刑事判决。
[4]重庆市忠县人民法院(2010)忠法刑初字第94号刑事判决。
[5]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5)黔法刑初字第00023号刑事判决。
[6]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014)秀法刑初字第00214号刑事判决。
[7]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2015)黔法刑初字第00027号刑事判决。
[8][苏]A.H.特拉伊宁.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M].王作富,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1-2.
[9]杨春洗,杨敦先.中国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7.
[10]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483.
[11]时延安.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的刑事法解释[J].法学,2015,(11):122-130.
Denudation timber crime judicial error and corr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ongqing court ruling in recent years
HU Sheng
Denudation timber crime existing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rime subject generalization,sentenced to a fine is inappropriate,stolen property,disposal against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and coherence are two of the forestry law problem.In fact,in into sin,forest owners to sell is a reflection of its exercise the ownership of forest,as long as it does not help cut down,or active solicitation to buy recipients unlicensed logging,it is impossible to set up denudation of trees;In sentencing,the sentence is not only to reflect the fine punishment,and punishment must be considered individualized principle;On stolen good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ing,whether by denudation of trees,eventually involved criminal sentence expression should be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sixty-four of the criminal law;In with the joining of forestry law,must set up the first initiated the concept of punishment.
Denudation of Trees;A Fine;Stolen Goods Disposal;The Empirical Research
DF6
:A
:1674-5612(2017)01-0035-07
(责任编辑:吴良培)
2017-01-06
胡 胜,(1989- ),男,湖南娄底人,刑法硕士,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研究方向:刑法学、审判实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