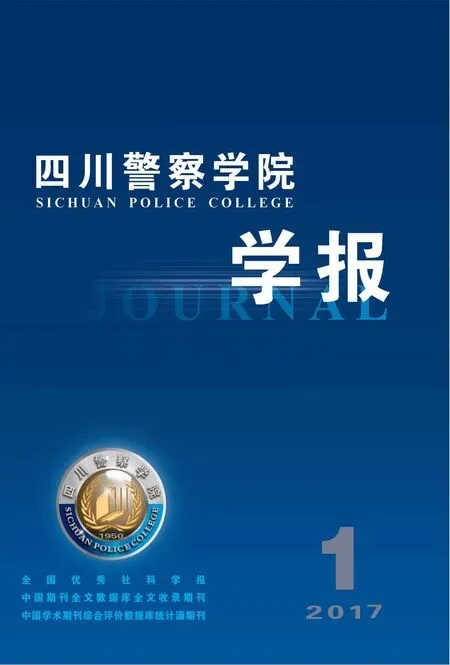辩诉交易:一种政治学路径的思考
彭昕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7)
辩诉交易:一种政治学路径的思考
彭昕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207)
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成因和功用曾有过轰轰烈烈的探讨。视角的狭隘使得讨论结果局限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是为了缓解案件压力、节约司法成本等对西方制度的一种“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识”。如果将制度置于更宏观的视野下思考会发现:在传统的“效率论”之外,诉讼参与者的利益需求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共谋可能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主因。质言之,真正使辩诉交易制度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最大动力是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诉求。
辩诉交易;利益博弈;国家治理;政治分析
近年来,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简化部分案件的审理程序和时间成为了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一大改革热点。对此,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刑事和解制度,并于2014年开展了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试点。随着速裁程序的试点,我国刑事案件的审判也大致依照案情的严重与复杂程度相应进行了“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分流。但由于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适用率偏低,已有改革无法有效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案多人少的矛盾仍然突出。为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第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到试点工作办法的具体规定,很容易将其与盛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中国版本的辩诉交易制度。纵然,我国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可以吸收辩诉交易制度的合理成分,然而在这些话语的背后,是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错误理解及其背后深层原因的忽略。
辩诉交易是当代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建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批评。但这一制度却影响到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并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移植、借鉴,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①。尽管我国学界对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缘由和制度功用进行了轰轰烈烈地探讨,但由于视野的局限和理论工具的单一,使得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把握仍停留在一个较浅显的层面。诸如“辩诉交易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减轻积案压力”[1]、“这项制度不仅可以大大降低检察官的举证压力、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刑事司法效率,而且可以一定程度上免除被告人的重刑处罚”[2]此类表面、浅显的描述分析仍屡见不鲜。在我看来,对于辩诉交易制度的探讨,除了对刑事司法的态势进行观察、描述,还应将其置于宏观视野下进行思考,以便更全面、深刻地把握和运用该制度。本文在简述辩诉交易制度确立历史的基础上,从诉讼参与者的利益博弈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层面逐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能够被接受和适用的深层次原因,并揭示出除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之外,辩诉交易的另外两大重要功用。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谱系
乔治·费希尔在《辩诉交易的胜利》中详细考察了作为一种系统制度的辩诉交易从初现端倪到如今广泛应用的演变过程[3]。按照年代顺序,乔治费希尔将这一历史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这一时段呈现出检察官利用立法授权,在狭小范围内摆脱法官对量刑绝对控制的特征。作为制度发源地的马塞诸塞州,这一时期的辩诉交易主要在违反禁酒法的指控和谋杀案件领域。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主要动机有二:其一,19世纪,由于检察官均为兼职,工作人员匮乏,大量的移民涌入使得案件数量激增,加剧了检察官的工作负担;其二,出于考核目标的顾虑,避免陪审团践踏其指控成果的风险。但由于法官掌握着定罪量刑的权力,这一时期检察官要想摆脱法官的控制,所凭借的是国会特殊的立法授权。由于禁酒法独特的规范结构,对几乎每一种犯罪设定固定的罚金,从而几乎完全剥夺了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但这同时也使得检察官得以通过操纵指控而操纵量刑,获得了一种事实上的、“潜隐化”的裁量权。同理,在死刑案件中,由于当时社会对死刑的排斥,立法赋予检察官有权通过允许被告人对较轻的指控作出答辩而规避强制的死刑判决。因此,检察官很快就利用这些有限的量刑权通过指控交易换取认罪的实践落实到位。
第二阶段为19世纪的最后15年,推动辩诉交易发展的主要力量开始从检察官向法官倾斜。民事案件数量大爆炸推动了法官对于刑事案件的态度转变。数据显示,1880-1900年间,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的蓬勃发展,民事诉讼案件的数量呈倍增趋势,法官们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分配给了民事案件,只能留给刑事案件越来越少的时间,于是他们逐渐同意了通过有罪答辩来解决一些刑事案件。随着法官转换为辩诉交易的推动主体,相比检察官易于操纵的指控阶段,法官对于量刑的操纵就显得驾轻就熟,因而这一阶段辩诉交易更常见的是采取量刑交易的形式,即被告人的答辩换取减轻的量刑。由于法官享有在刑事审判这一战场上最重要的权力——判处刑罚的权力,于是在这一阶段,辩诉交易在法官的支持下打破了禁酒案件和谋杀案件的狭窄范围,扩张到全部刑罚的领地。
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晚期以来,辩诉交易运行的实践逻辑开始悄然变迁,呈现出检察官开始单方面操纵、主导辩诉交易,法官努力摆脱权力失衡状态的特征。联邦量刑指南的出现,将每一种可界定的犯罪都被设定了一个固定、狭窄的量刑幅度,法官必须在规定的幅度内进行量刑。固定的刑罚规定意味着检察官可以通过操纵指控范围来制约法官的量刑选择。这使得原本法官与检察官相互独立共享交易权的模式变革为检察官几乎单方面操纵、主导的模式。于此同时,法官通过审查驳回检察官或辩护律师建议的辩诉交易以及量刑指南中的扩大条款来努力维持交易权的平衡。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政治分析
透过辩诉交易制度确立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每个法庭参与者的权力和利益需求在塑造制度时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辩诉交易制度的肇始起引发作用的无疑是检察官,法官则对制度得以全面系统地确立功不可没。而要避免落入“效率论”这一简单的决定论窠臼,除了对制度本身的分析外,还应跳出制度本身的束缚,投以更加宏大的视野关注,或许方能有新的解释与出路。以下将从诉讼参与主体和国家治理两个层面来逐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之所以能够被接受和适用的深层次原因。
(一)局内人的主导与局外人的无奈追随。
现代社会具有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特点,也越来越依赖专业人士做出以前业余人士作出的判决[4]。纵观世界各国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都经历了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的演进。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特别重视对于长期利润的精细和有系统的计算,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投机行为和短期行为获取暴利。这种理性化的经济形式要求尽可能地对未来的风险作出预测并提出相应对策,以保证投资决策得以顺畅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变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法的理性化、系统化和一般化以及个别案件中法律程序运作的日益增长的可算度性[5]。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如果刑事司法要成为具有可预测性且可靠的威慑犯罪的方式,那么其就不能局限于让社会底层志愿者和被征召的人来操作。这种需求逐渐排挤了外行人作为被授权的参与者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的角色。刑事司法的职业化即是指由律师和在刑事司法领域取代外行人的其他职业人员组成的团体进行一些列活动。有学者形象地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概括为“局内人”与“局外人”[6]。职业化的演进趋势拉大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之间的差异,因而对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与演进也施加了不同的影响。
1.局内人的主导。传统制度主义认为,是行动者构建了那些使他们能够获得想要结果的制度[7]。由此推之,辩诉交易制度的形成也是因为主导刑事程序的参与者根据利益的需要而选择了各种行为方式。在刑事司法机器的运转中,法官和检察官无疑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因其权力性质的差异,部门内部的利益需求也必然产生分殊,因而在形塑制度的过程中必然也会施加不同的影响。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与资源的可替代程度呈反比,这个资源越是不可替代,组织对提供资源方的依赖程度越高。同时,组织还会尽量通过自己掌握资源的方式来降低对其他组织的依赖[8]。在美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各主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独立的[9],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在刑事司法的场域中,审判程序总是位于公诉程序之后,起着最终决定当事人胜负的作用。因此,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的所有案件最终都需要通过法院定罪量刑,其公诉结果无疑完全依赖于法院的判决。对于绩效考评取决于“定罪率”的检察官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通过辩诉交易的案件,仍然可以被统计入定罪率。这无疑是美国的检察官通过自己掌握“资源”来降低对法官依赖程度的一种策略。
最初法官不愿参与辩诉交易的原因在于法官基本为全职人员,未面对同样的工作量压力。加之,薪水保障使其没有和检察官一样尽可能迅速结案的经济动机。此外,基于原则而非全面信息的掌握就草率履行自己的量刑职责,伤害了某些法官对自己权力的骄傲。[3]法官后来态度转变的原因则是由于19世纪后半叶工业的蓬勃发展,民事案件诉讼大爆炸推动了法官对于刑事案件的态度转变。法官们将更多时间分配给了民事案件,留给刑事案件的时间只能越来越少,于是他们逐渐同意了通过有罪答辩来解决一些刑事案件[3]。除上述原因外,法庭业务的组织方式和司法制度内固有的互利实践的低成本也是法官后来同意辩诉交易制度施行的重要原因。
首先,美国法庭的工作方式有别于我国法官的朝九晚五,并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也不需要基于案件数量而获得薪酬。主导法庭程序的人(主要是法官)都想尽快走完当天的日程,这样就可以空出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坦率地说,无论案件压力如何,对于这个制度的许多参与人来说,案件数量总是过多,因为他们大多数更乐意待在法庭之外的某个地方[4]。因此,无论案件负担如何,总会存在快速推动案件处理的动机。
其次,辩诉交易制度节省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时间和精力,也使法官避免了错判的风险,这种互利实践中低成本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职业共同体,局内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手,恰恰相反,他们的立场是合作。他们从事的事业也是共同的事业,即需要在引起逮捕行为的“裁定”上达成共识,而不是一场战争。作为法院的常客,他们是“有着强烈的和谐相处动机的重复玩家”。他们并不是为一方或另一方明确辩护,而是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并暗地里达成妥协[6]。因为不合作的态度不仅打破了必须每天都要继续一起工作的各方持久的友善关系,也于己不利。因此,共同互利实践带来的实际好处亦推动了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与适用。
2.局外人的无奈追随。局外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无奈显著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刑事司法的专业化使得现实的司法活动并不怎么需要外行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各国犯罪率越来越高,并且呈现出科技化、多元化的趋势。案件的破获越来越依靠专业的侦查技术,不再是剧场式的调查。律师对审判的介入催生了证据规则的复杂化与精细化。专业律师对信息和技术性知识的垄断拉大了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鸿沟。局外人对专业人士的依赖也使其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间接落入局内人的操纵。刑事司法的专业化渐渐把外行人排挤出了现实的司法活动。另一方面,对于许多轻微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来说,成本最小化的理性选择也经常是放弃原则而和解,因为大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对被告判处的刑罚往往极轻。但如果想要通过正式诉讼程序作出判决,就得算上请私人律师所需支付的服务费、误工费、交通费等,所必须的成本可能很快就超出了量刑本身[4]。在主张权利的成本经常比丧失的权利本身还要大的情况下,被告人就有强烈的动机去选择“不费事”的辩诉交易。因为抛弃了程序的形式外观,他们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得到了“实体”的正义。毕竟对于大多数轻微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冗长的程序也是一种更大的无形的惩罚。
(二)国家治理现代型的转向。
上述从诉讼参与主体的利益需求角度来分析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缘由可以说是一种“从下往上看”的进路。但如果转换视角,“从上往下看”,即“政治”地理解辩诉交易制度,就会发现制度背后往往存在着统治者“政治统治”的考量。
尽管达马斯卡曾将不同国家的司法区分为“纠纷解决”与“政策实施”两种类型,但它们却具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即承担了整合社会与国家的政治使命,只不过作用的方式有所不同[9]。随着社会发展带来关系的复杂化,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福柯的权力理论和治理术所暗示的,现代性的权力首先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合作性的权力。自中世纪至近代以来,西欧国家的治理方式并不是单一的国王“统治权”的延伸与扩展,或是单纯的“惩罚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出现了以“规训技术”和“治安技术”为代表的新的治理策略。这些新的策略中,国家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从赤裸的暴力或仪式化的剧场效应,转向了一种更为精致、隐蔽、渗透到毛细血管中的微观权力,这不仅使得统治权的运行更加严密,也有效地化解了被统治者的反抗,获得一种更节省也更高效的治理[10]。
从这一视角来看,辩诉交易制度设立的缘由除了案件压力的驱使和满足各方当事人利益的推动外,国家治理策略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用更隐秘的方式使国家权力默默得以施展。辩诉交易制度的施行使国家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应对了爆炸式的诉讼需求,不仅使得治理变得更“经济”,更避免了与反对者的直接对抗,从而有助于减少潜在的矛盾与摩擦。
三、辩诉交易制度之双重功用
(一)对沉默权“副作用”的消解机制。
任何制度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正如制度的建立最初更多是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补救措施或意外事件,最终达到的效果,可能远在设计者的意料之外[11]。在美国,沉默权制度先于辩诉交易制度以判例的形式确立②。正如自然界的生物链,任何新生物的出现都需要另一新物种的制约才能维持生物链的平衡,刑事司法领域亦如此。被告人的沉默必然对破获案件产生了重大阻碍,破案率的下降也将带来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辩诉交易制度就是用于消解新制度产生的对社会治理“不良影响”的“新物种”。
各国犯罪率越来越高,且犯罪呈现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给警察侦破案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除此之外,证据规则的日益精细化使得刑事诉讼需要跨越的“障碍”越来越多。这也加剧了以“定罪率”作为考核标准的检察官的负担。辩诉交易制度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的有罪答辩为条件以换取更轻的刑罚结果,从而激励并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放弃沉默权。有数据显示,美国行使沉默权的人只占被讯问者的4.7%[12]。可见,辩诉交易制度除了起到弥补对抗式审判程序的效率缺陷的作用之外,更是一种通过法律利益悬赏引导被告人招供的重要机制[13]。同时,还能提高警察的破案率和检察机关的定罪率。
(二)化解事实真伪不明的尴尬。
传统对抗式刑事审判以非专业的陪审团为事实的认定者。有学者曾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团发挥了这样一个重大功能,就是避免法官的权威因为对事实问题的认定错误而受到影响。而对当事人而言,人数众多的陪审团实际上只是一个制度化的符号,当事人无法对陪审团的具体成员有多少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陪审团就承担了本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14]。但随着20世纪以来陪审团制度的衰落以及对抗制的式微即司法进一步介入事实认定的情形而改变了审判的对抗式氛围[15]。诉讼中,国家不再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法官拥有越来越大的自由裁量权,当事人也不再有传统对抗式审判中的诉讼主体感,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一旦诉讼结果对自己不利就很容易激发当事人的不满与对抗情绪。
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会通过对制度环境的适应,将组织的行为塑造得符合社会共同意识和认知系统的要求,从而获得合法性的支持,即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并非内生的,而是外部赋予的。辩诉交易制度的精巧之处就在于,面对案件侦破难度的日益剧增以及庭审的苛刻要求,一些事实无法查明的案件,通过被告人的自愿有罪答辩,弥补了证据的缺失,从而使判决获得一种合法性的支持。也即,国家无法在审判中将责任转嫁的情况下将审判中的矛盾转移到审前,以一种“合作式”的外观成功化解了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认定事实的尴尬,也避免了当事人的直接反抗的作用。不得不说,辩诉交易制度既获得了被统治者认可,又使国家的治理更加隐蔽与经济。
四、结语
辩诉交易制度作为当代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建制,其最初萌芽或许更多的是一些针对具体问题的应对措施或意外。但正如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是直面复杂的世界,从表面的“悖论”中去寻找那真实的历史[11]。对制度的探讨,也应该是摒弃狭隘的视角和表面的分析,设身处地地理解制度的发生与功能。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辩诉交易制度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或许都并非偶然,揭开“效率论”和实用主义分析的面纱会发现,真正能使制度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是其背后所隐藏的强大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诉求。
[注释]:
①英国《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第48条就赋予了辩诉交易实践的准合法性:(1)如果一名犯罪人在本庭或其他法庭所进行的诉讼程序中就该项犯罪作了有罪答辩,法庭在决定对其的刑罚时应该考虑:(a)罪犯表明作有罪答辩的意图时所处的诉讼阶段;(b)这种指示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2)考虑到上述第(1)项中所提到的内容,如果法庭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比其他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要轻,那么,法庭应该在公开庭审时说明这一点。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法》第444条至第448条规定:被告人和检察官达成刑罚协议,被告人放弃正式审判的权利,检察官则同意给予被告人最高1/3的减轻刑罚;在适用该程序中,被告人可以获取减轻的刑罚不能超过2年监禁刑。2009年5月28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将刑事协商法典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95条规定了庭前认罪答辩程序。
②通说以1966年的米兰达案件和1970年的布雷迪案件分别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
[1]朱罗成,黄铁文.关于辩诉交易的理性思考[J].广西大学学报,2009,(9):158.
[2]廖 明.辩诉交易: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J].法治论坛,2009,(4):197.
[3]乔治·费希尔.辩诉交易的胜利——美国辩诉交易史[M].郭志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7-49.
[4]马尔科姆·M.菲利.程序即是惩罚——基层刑事法院的案件处理[M].魏晓娜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259;262.
[5]左卫民.背景与进路:法院制度现代化的宏观考察[J].江海学刊,2001,(6):61.
[6]斯蒂芬诺斯·毕贝斯.刑事司法机器[M].姜 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5:2;34;54.
[7]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 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导言11.
[8]王禄生.刑事诉讼的案件过滤机制——基于中美两国实证材料的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4:103;150.
[9]达马斯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法视野中的法律程序[M].郑 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0;111-112;131-135.
[10]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M].钱 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8;87-93.
[11]于 明.司法治国——英国法庭的政治史(1154-1701)[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1;293.
[12]汪建成,王敏远.《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J].法学研究,2001,(1):146.
[13]周洪波.沉默权问题——超越两种理路之新说[J].法律科学,2003,(5):109.
[14]左卫民.在权利话语与权力技术之间——中国司法的新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83.
[15]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刘晓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77;189.
Analysis of Plea Bargaining from the Angle of Politics
Peng xin
There had been an intense discussion about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plea bargaining system in the academic circles,which got a stereotype of the western system,even the misunderstanding that establishment of plea bargaining system is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of the case and save?the?cost?of?justice because of the narrow perspective.In a broader view,besides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theory,the major reas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involve litigation participants’interest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In essence,the real impetus of establishing the plea bargaining system is strong polit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appeal.
Plea Bargaining;Benefit Game;State Governance;Political Analysis
DF7
:A
:1674-5612(2017)01-0134-06
(责任编辑:赖方中)
2016-12-15
彭 昕,(1992- ),女,四川简阳人,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