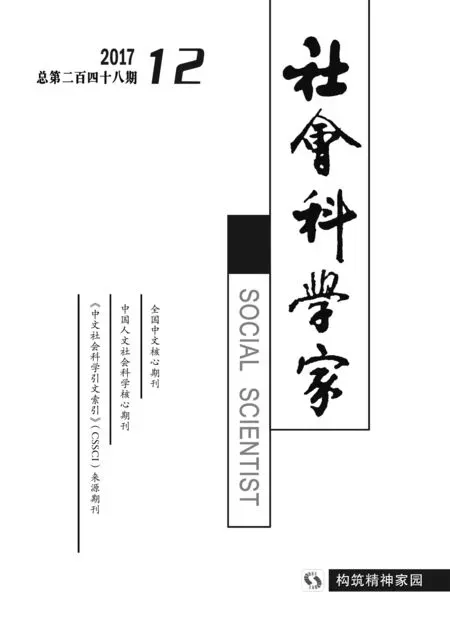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理论变迁与文化脉络
韩秋红
(东北师范大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西方哲学在中国自其产生起就体现为双重线索:从表象上体现为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不断融合、融汇、融通、融铸的过程,在深层上体现为立足中华文化本位的文化移植、文化反省、文化自觉、文化创造的过程。两者合二为一串连起整个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轨迹:文化构成其宏观语境、思想构成其内在要素、时代构成其客观条件、主体构成其能动因素。因此西方哲学在中国不仅是外来文化传入所产生的应急反应,更是在中华文化包容性基础上,适应历史现实和时代需求,学者们“主动应变、自觉反思”的思想历程,构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态势,形成了哲学就是认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创造史这一立足西方哲学本身并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基因的文化脉络,确立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轨迹和整体态势。
一、文化姿态:以主动应变彰显民族本位和主体自觉
在中国,历史推动发展的西方哲学研究首先以对历史现实与时代需求的自我解读表现了主动应变的中国方式。即主动应变是应对变化与其被动植入,不如主动认识、理解,转化其优势为我所用。这是西方哲学一经在中国的中国西方哲学研究者们的意识自觉及努力将其转化为助益中国社会发展的元素,体现了学者们的主体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
陈旭麓曾指出:“‘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1]改变民族意识、改变社会制度是中国人选择“进化论”、“民约论”进行自我解读的根本目的。由此产生的科学主义、民主社会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正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序曲。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中国人启蒙了科学主义思维。他赞许西方学者们对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做法,对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界的启蒙大有进益。“天演论”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未明晰的认识事物的诸方法,以及以此方法透视出的可用于救国图存的启蒙民智、启蒙民德、启蒙自由的思想依据。指出:“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以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享。”[2]给予“天演论”很高的评价,“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2]也认为进化论能够作为谈论治国之道的合理基础,是进化论中的科学实证思维,启蒙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推进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自我解读。
“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哲学更是以主动应变的研究方式适应着历史现实的需求,推进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开显。瞿秋白曾指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有实验主义的出现,实在不是偶然。中国的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性来满足这种需求。”[3]实验主义的哲学无疑指的即是实验主义的西方哲学,中国学者对这种西方哲学的青睐源于其哲学认识所提供的对时代问题的科学指导意义。1919年4月,受胡适、蒋梦麟等人之邀,杜威从日本东京大学来到中国,自5月起在中国12个省市做了为期15个月的百余场学术演讲。杜威在关于社会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思维类型等方面系统介绍了其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反响。正如胡适指出,实用主义中显现的科学方法是最为受用的、中国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哲学方法,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认为实验主义方法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只顾发展目的,缺少正当方法的问题,即“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4]张君劢也曾在就杜里舒访华事件指出:“自杜氏东来,所以告我国人者,每曰欧洲之所以贡献于中国者,厥在严格之论理与实验之方法,以细胞研究立生机主义之理论,可谓实验矣。哲学系统,一以论理贯串其间,可谓严格矣,此则欧人之方法,而国人所当学者也。”[5]实验科学方法是在中国人对历史现实与现实需求的自我理解基础上,所体现的对西方哲学主动应变的进行西方哲学中国式研究的典型事例,中国人试图改良西方哲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是在进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而这种方式无疑对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样需要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主动应变。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估一切价值”的探索,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变革,旧的封建思想需要被剔除,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重新树立发展目标的问题。所谓“重估”,不仅是对西学东渐之路上始终人声鼎沸的“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激辩之思,更是对从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之学到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与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的制度之鉴之思——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便开始了一场以“御侮自强”、“制器练兵”和“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具体来说,是清政府怀着“文化民族主义”的心理,坚持中国自古已有的文武制度,加之西方先进技术(只引进西学中的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练兵养兵之法)以外抗帝侵、内压起义。所以洋务运动的根本失败在于清政府“中体西用”的错误观念及对世纪潮流与西学认识上的肤浅。在反思洋务运动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中国要富强,除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外,还主张中国应该废除科举制度,甚至应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企图通过资产阶级参政来削弱君权。所以正是在可以面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现实面前,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社会整个文化传统和哲学精神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优先性。诚如梁启超所言:“求文明而从形式入,如行死港,处处遇窒碍,而更无它路可以别通”,“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真泻,沛然莫之能御也。”[6]此后,陈独秀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也讲到:“最初促吾人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恪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流离之景。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7]说明社会进步最终要依赖人们精神的启蒙和“全人格的觉醒”。故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指出,旧的封建文化抑或是器物之用、制度之鉴之路都没有使中国真正摆脱愚昧落后之状态,走进先进的“民主”“科学”文明,反倒是裹挟着封建复辟势力一次又一次的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因而真正首先需要“重估”的正是我们的思想文化,要从思想文化的源头上厘清“科学”的价值体系与“民主”的思想内涵,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哲学之思方可“救治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道德上的一切黑暗”。[8]此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9]显然陈独秀意在指明科学是一种主客观的相对性。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谈到,如果要“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必然要“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10]胡适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生活式”。[11]同时指出,“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2]显然,五四运动时期的先驱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民主”对于中国人启发民智,推动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则在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如何进行思维方式转变的问题,如何在合理地、合现实的层面发展中国哲学?许多学者将眼光投射到西方哲学研究之上,以西方哲学的科学方法应变中国哲学及其传统文化的发展需求。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指出,西方哲学的主要贡献便是其分析的方法。他讲在中国:“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负的方法’。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正好是‘负的方法’的反面;因此,也许可以称之为‘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致力于消泯差别,告诉人:它的对象不是什么;而正的方法则致力于突出区别,使人知道它的对象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佛学带来的负的方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人在道家思想里已经有了负的方法,佛家思想只是加强它。而从西方引进了正的方法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中国人有一种新的思维方法,还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态。”[13]可以说,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在西方哲学特殊意义的方法中进行西方哲学中国式的研究是符合当时发展现实情况的。包括冯友兰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积极尝试以西方哲学方法的自我解读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其论著《新理学》就是这种尝试的优秀成果。冯友兰毫不避讳的指出:“在《新理学》中,我使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13]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比如梁漱溟、张东荪、熊十力、贺麟、金岳霖都在以西方哲学为参考,在积极建构中国哲学新形态方面做出了努力。从一定意义上看,对西方哲学方法及其从中吸取的重要理念的主动挖掘,是开启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路径的重要前提。
随着中国学者自我解读方式的不断延伸,即由依据历史现实需求进行的自我解读方式拓展到依据掌握的西方文化诸方法而进行的文化本身的主动应变,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随之在内容上丰富起来,包括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对西方哲学具体派别、问题的研究,对西方哲学经典文本的翻译介绍等方面,西方哲学在中国整体文化发展的维度上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比如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近20年间,出版发行了十多种版本的中国人自主编写的西方哲学史类书籍。包括1930年瞿世英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的发展》(神州国光社);1932年刘伯明编写出版的《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33年洪涛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广益书局);1933年李石岑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三民书局);1934年全甑嘏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张东荪编写出版的《近世西洋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37年黄忏华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纲》(商务印书馆);1941年詹文浒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讲话》(世界书局);1941年李长之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1947年冯友兰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专著]中国哲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侯哲葊编写出版的《西洋哲学思想史论纲》(上海黎明书局)等等。这些出自中国人自我解读方式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表达了中国人早期以总体性的认识眼光主动接纳西方哲学的情况,而这种主动接纳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加以中国式运用与发展,就是将西方哲学进行中国化。将西方哲学进行中国化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自我解读文化的重要路径。正如1941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李长之编写的《西洋哲学史》序言中提到:“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把中国彻底现代化,敌人打击我们不也是因为见我们现代化快要完成了,而眼红,而妒忌么?我们的吃亏,不也就因为我们现代化得不早么?我们的牺牲,说简单了,不是也就在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自由和实践么?什么是现代化?简言之,现代化乃是西洋化。详言之,便是由西洋近代科学、技艺思潮精神所缔造之整个文化水准,从而贯通于今日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生活态度之一切的一切,我们中国都能迎头赶上之谓。然而文化史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14]中国学者意识到西方哲学作为我们社会发展、文化进步重要参考内容,是西方哲学不断来到中国,在中国“西”化之过程的源头和动力,而对这种源头和动力的发展构成了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途径。更进一步,也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成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积极因素。
二、理论转换:以多维阐释植入现实意义与文化基因
西方哲学中国化不但确立了主体的文化自觉,更将这一自觉通过内在理论转换方式加以中国化,即在其内部借用概念、对象和主体的力量,将文化基因植入西方哲学内部,使之发生向着中国社会的理论转换,开启对西方哲学中国文化意义上的理解与中国学术力量上的转化,成为在文化自觉中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工作。
以概念的新诠释确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意义。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概念”厘定是深入到西方哲学中国化内部世界的合理性前提,而在历史历程、解释视域、经历机制、经验借鉴、恰当路径、更迭形态、丰硕成果、基本规律等宏观与微观交织的审视中,我们也逐步接近并取得了对作为“概念化”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完整体认。回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整个演进历程,我们不仅能够在历史梳理中厘清西方哲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动态趋势,更能在逻辑研究的进路中找到西方哲学与中国辩证统一的相互交融。所以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国的蓬勃发展,西方哲学正是在“西学东渐”的起点上一步步走向“西方哲学在中国”、走进“中国的西方哲学”、不断形成“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动态演进的历程中,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中国特色文化之间产生了从西方哲学“化”中国,到中国“化”西方哲学,再到作为辩证统一形态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不解情缘。无论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求“我们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形态乃至先进哲学理念求解,还是在“自强不息”、“民族解放”的征途中再度实现“国富民强”、“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代的不同主题、民族的基本精神都旨在将西方哲学的重要方法与重要理念与中华民族的强盛发展有机的连接在一起。西方哲学在不断地为中国人辨识、采纳、创新、融通中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为不断创新思维方式与方法提供理论前提和问题导源,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地位创造条件。故此,当我们从中华民族由衰转盛、“西学东渐”发生发展的历史历程中一路回溯,在“向前看”与“向后看”的交织中回味、品读“西方哲学东渐”时,我们有理由认为,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自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追求独立解放、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充分释放求新精神,主动将西方文化内化为中国人建构自身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并延续至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创新、文化融通与文明再造的历史性活动。如果进一步对这种立足中国问题意识、借鉴西方哲学资源为我所用的历史活动加以聚焦,我们则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与文化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解释视域,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考察视域恰恰是在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维度上展开的。因而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不断中国化从社会层面而言,是西方哲学思想在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大变动的需求;就文化层面而言,则是指它们取得了崭新的文化形态。在这种社会与文化双轨推进的过程中,西方哲学中国化也形成了自身的经历机制、经验借鉴、恰当路径、更迭形态、丰硕成果与基本规律。透过“变革、融合、制约”[15]的经历机制,我们能够再次体悟西方哲学中国化“辨识、反思、创新、融通”的发展历程;透过西方哲学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借鉴,我们能够再次思索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学者在主体意识觉醒与精神高度自觉中对西方哲学展开的新形态的积极研究、不懈探索以及为此确立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研究范式;透过西方哲学中国化不断探索出的与中国哲学在价值取向、问题向度、采用模式上的对话路径,能够进一步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人旨在以与众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观念、哲学素养创造性的阐发西方哲学、融涵性的吸纳西方哲学、激荡性的转换西方哲学以熔铸性的创造出符合中国人思维和实践需要的中国特色新哲学的历史性活动;透过西方哲学中国化“主动应变、求变求新”的发展规律,我们不仅凝结出“在西方哲学的理论形态中纳入中国传统哲学内容的西方化的中国哲学,以及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形态中加进西方哲学内容的中国化的西方哲学”[16]的思想结晶,更能够再次确证“西方哲学中国化,就是将现代西方哲学移植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实际结合;汇合中国传统哲学之流,相互融会贯通。”[16]所以无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历程、解释视域、经历机制、经验借鉴,还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恰当路径、更迭形态、丰硕成果与基本规律,都是理解作为“概念化”的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视角下所得出的结论:即作为“概念化”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正是中国学者主动将西方形而上学作为原始素材,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作为思想基础,将中国特色的思想发展作为审视维度,将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建构对象,在“接受、辨识、认识、融通”的历程中做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与发展过程。
以对象的不断厘定拓展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空间。西方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对象”被体认与把握,在于这种“对象化”的存在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于它对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所起到的助推与发展。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西方哲学作为文化应对的对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哲学作为对象在对其解读中又出现了新景象,自我解读又一次在以现实需求为背景中体现了自觉反思发展的中国化方式。这就是将哲学等同于认识史,将西方哲学史看作是认识史的代表加以批判性的认知与辨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定位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经历着曲折的发展。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形象有了新的变化,西方哲学的研究更是在自觉反思的进行中逐渐彰显中国化的维度。贺麟先生曾指出的:“哲学史虽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上的斗争、政治上的斗争(两者虽然有密切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区别……而马克思当西方哲学界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17]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哲学的研究应该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的固有观念,以一种真正的“哲学”眼光看待西方哲学,也就是将西方哲学作为人类认识史和人类文明史对待,同样作为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重要的参考系对待。正如汪子嵩在回顾编写《希腊哲学史》感到茫然时联想到的汝信传达胡乔木同志关于编写《西方哲学史》的原则意见:“总体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中国学者的创见。”[18]表达了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变——强调自觉反思的西方哲学研究。在自觉反思的研究西方哲学的状况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建构具有了显著的凸显。表现在:西方哲学在研究问题的甄选上越来越贴近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上也越来越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融合;西方哲学在研究的发展定位上越来越依托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致力说明了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在贴近现实境遇的维度上具有了自我解读、自我阐释的中国意味。相继出现的对尼采超人哲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热潮也都是在进一步关注生活世界的维度上展现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合理意义。西方哲学理论研究上呈现的“对话”或“会通”的形势,也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建构的重要思路。汤一介曾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时指出:“对历史上的哲学,如果要使它具有现代意义,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就必须给以现代的解释……对孔子、老子、庄子思想的解释只能是‘既是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又不是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扩大了孔子、老子、庄子哲学的意义。也正因为它是我们现时代‘根据孔子、老子、庄子哲学引发出来的’,所以它才有现代意义,哲学才有发展……这无疑对我们今日的哲学研究是有意义的。”[19]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如此,西方哲学当然更应如此。所以,西方哲学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具有的重要地位被凸显出来,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中国式研究正因理论发展的真实需求而具有了中国化的必要性。有学者指出,“中、西、马”互动中的哲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可以看作是“一门创造性的学问”。[20]创造性学问的前提是自觉反思,即努力实现反思传统形态的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建构西方哲学中国式的现代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对象化在越来越依托“中国特色”的维度上具有了发展的态势。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当代作为一种必要性的文化形态、理论范式最重要的在于其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意图,而不仅仅是将西方的哲学转移到中国哲学的发展领地之内。“原封不动地把西方哲学搬到中国,这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在中国取得新形态,这是中国化了的西方哲学。前者是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后者意味着西方哲学在中国获得了发展和出新,表现了中国哲学家在建构自身理论时的创造。”[15]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既是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特色,也是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的特色,二者的统一恰恰凸显了西方哲学中国化在建构过程中的主动应变、自觉反思的创新机制。
以主体的不断自觉实现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立场自信。从“主体化”的角度去解读西方哲学中国化,则意味着中国学者在对西方哲学的解读中始终坚持“面向中国事情自身”,让西方哲学“讲汉语”、“培育中国问题意识”的过程中内化为中国人建设自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使西方哲学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
黑格尔在写给J·H·沃斯的书信中说道:“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21]伽达默尔也曾指出,理解的本质正是解读者与文本本身的“视域融合过程”。[22]所以“主体化”视域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中国学者将对西方哲学文本的解读面向中国文化自身,带入中国思想语境,才使西方哲学具有了“中国问题意识”,西方哲学开始讲“中国话”,逐渐内化为“汉语哲学”的有力资源,成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征。赵敦华在《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中指出,“相比之下,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文化意识,远不如中国哲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意识浓厚。我们需要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解读西方哲学,这是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所在。”“这里说的‘中国人的眼光’,有着特殊的含义”,“第一,用地地道道的中国话说外国的道理”,“第二,以中国文化为参照理解西方哲学”。[23]所以“主体化”视域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应当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积极译介、合理解读,使西方哲学具有中国语境下的问题意识,以地地道道的中国话合理阐述自身的思想。邓晓芒更是在《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中明确指出,“如果说,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教哲学说德语’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哲学说汉语’同样将意味着哲学本身在当代的新发展”。[24]所以正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孜孜以求的研究,培育西方哲学“中国问题意识”的精神,教会西方哲学“说汉语”的不懈努力,使得西方哲学能够在“主体化”、“对象化”、“概念化”的有机统一中顺利融入中国语境,成为中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问题凸显:以核心命题确立研究定位与文化脉络
在西方哲学引介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主动意识越发明确,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越发明晰,实现了将西方哲学转基因入中国本土文化,生成“中国的西方哲学”的转变;经过了将西方哲学看作是“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和“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核心命题的三跃迁;体现了从“西方哲学在中国”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哲学史就是哲学”改革开放前的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是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关系,形成的核心命题是哲学史就是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曾提出:“哲学是理性的知识,它的发展史本身应当是合理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25]意指哲学史“不可能是偶然事实堆砌的历史,而是那个唯一真理借助这些事实不断自我显现的历史,也是哲学自我发展的历史。”[26]这里的“哲学史”是展示绝对精神(黑格尔)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规律的历史,因此“哲学史就是哲学”。黄见德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中进一步解释这句话,“哲学史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它不仅展示哲学内容发展的外在的偶然事实,还要昭示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哲学内容本身。因此,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27]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西方哲学,就是强调“哲学”是“哲学史”内在的根据,它既是哲学史的源头活水,又是哲学史一以贯之亘古演变的逻各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学者认为要先对西方哲学史上各个时期、主要代表人物、重要代表观点等“哲学”材料进行前提性的占有,只有掌握足够多的“哲学”,才能为这样的史学工作做好积淀。所以,“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认识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从存在论上说,将西方“哲学”的知识和素材看作是“实体”、“本体”一般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存在样式和变化规律,西方哲学史就是对这个规律的展现;从认识论上说,体现为一种对象性的知性思维和符合论的真理观,抛开对研究主体思维能力的分析而直接对西方哲学史进行断言,追求认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从方法论上说,讲求研究者对西方哲学史只能进行“如其所是”的描画,我们在彼时的西方哲学引介和传播过程中“务在实事求是”,希望“复原”出“是其所是”的“西方哲学”。所以在“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指导下,很多类似“考古”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相继展开,“人物”、“典籍”、“文本”等考据工作取得诸多进展,在知识性引介方面达到了科学和客观,“确切、简洁、清通可读”,[28]易于理解、便于掌握。但是,时至今日再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段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这种将“哲学史”仅仅看作是大量“哲学”材料的罗列和堆砌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将哲学等同为科学,以一种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待哲学,剥离了哲学关怀人的本质属性和辩证法这一哲学活的灵魂,仅仅留下了被简单化、抽象化和绝对化之后的一堆静止的“历史事实”,哲学史成为某种“科学”“知识”的“历史”。因此,虽然彼时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观点已被引介国内,但只能说处在了解、认识、选择中,仍以一种旧的思维方式研究哲学。
“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对“两个凡是”的迷信,强调要恢复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试图从根源上用辩证思维去破解知性思维的毒害。以辩证思维看待西方哲学史,就不再只是“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也不再是“人物的罗列、文本的堆砌和‘厮杀的战场’”,[29]即西方哲学史不仅仅是一些生硬死板的“哲学”知识材料的历史汇总。中国学者逐渐开始接受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表达的观点,“哲学史,因此:简单的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30]以“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体现为人类认识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认识史是主体的觉解过程和思想的植入过程;“认识史”才能辨析清楚各个历史时期“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及其历史变化规律,以探究哲学思想诞生背后的历史前提、时代背景、问题导向、理论蕴含和价值关怀,在历史的开荡中挖掘西方哲学史所表征的人类理性思维发育的历史和在社会的延展中捕捉西方哲学所深蕴的西方社会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并且,既然“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研究原则是对主体思想的肯定,那么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史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开始肯定研究者对哲学史的解读。
这样,西方哲学在中国人眼中就从“哲学史就是哲学”的“知识史”转变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文化史”。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转换就是从以往抛开对人类思维能力发展水平的考察而单纯追求西方哲学知识的客观性,转向对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觉醒。不能否认,认识论的发展才会对西方哲学研究自身进行“反躬自省”。因为在本体论上,只有超越以往将西方哲学看作知识汇总的历史,才会将西方哲学视为一部西方人的思想史;在认识论上,虽然仍是一种对象性思维,但已开始强调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追求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互动的辩证法;在方法论上,从偏重对西方哲学进行概念解析、历史梳理转向注重进行思想挖掘、逻辑阐释和文化比照。这样,“哲学史就是认识史”更加重视哲学家所面临的具体历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历史性价值和思想性价值,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性的历史内在逻辑机理,强调不同历史时期思想观点之间的前簇后拥、更新换代、常驻常新,以及中西方哲学不同所表征的文化差异。这一切皆得益于“思想”的觉解。思想的觉解意味着基于前提性认识以思想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看待历史、建构理论,注重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注入自身的思考并努力达到视域融和。如果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追求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那么“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则强调主观见之客观,强调研究者的思想对历史的认知与改造;如果说以往“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是”,那么“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则侧重追求西方哲学的“如其所不是”,即要展现西方哲学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更要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逻辑及与中国哲学相比照而呈现的不同的文化内涵;如果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注重科学主义的肯定性思维,那么“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则更加靠近哲学的否定性思维,以哲学思想自身具有的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方式,将西方哲学看作是思想之间前后否定的历史过程,将西方哲学研究看作是“思想”否定“存在”的过程,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部否定之否定的具有内在超越性的文化史。实现了以哲学的思辨性对科学的知识性的破解,是致思方法上的进步,体现了西方哲学研究者理性思维能力的提升与发展和主体意识的自觉与加强。
但是,“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思维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每一次“否定”实际上都会造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康德面对的“二律背反”问题似乎出现在新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它揭示对立,却无法解决对立。比如,无论我们如何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对话,其实质还是将西方哲学看作是一种异质文化,并没有最终解决对立,对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并不彻底,亟须更新换代。
“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哲学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思想发展史,不只是对自己学科思想的发展历程及规律的总结,而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承担批判当下和预言未来的责任,负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使命。就是说,我们对哲学史的理解和研究,应该体现哲学所承载的人类历史观——思维的开创性和革命性。德勒兹讲:“哲学在本质上是创造的,甚而是革命的,因为哲学不断地创造新的概念”,[31]“创造必要的新概念一直是哲学的任务……没有概念也完全可以思想,但一旦有了概念,便确实有了哲学。”[31]正因为哲学能引领思维方式革新,才能不断以“概念”、“理论”、“思想”的逻辑方式影响和改造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推动着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
“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将哲学看作是思维活动的创造。哲学史不只是为了“认识”世界所体现的各种认识,不仅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更体现哲学自身独特的理性活动,体现人类追求“精神自由”的过程,体现人类思维所具有的创造性所产生了对世界不同的“阐释”。叶秀山、王树人在多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前言中写到,重写西方哲学史,就是为了“把西方历史上那些载入史册的哲学大师们如何创造性——自由的‘思想’哲学问题真正客观的介绍给大家”。[32]赵敦华在《西方哲学简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们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式,也是启迪批判性思维的实验过程。”[33]对西方哲学史不断进行研究到今天,我们逐渐明晰研究西方哲学,就不再是为了认清西方哲学的本来面目或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和精髓,而是为了融西方哲学于自身的哲学发展,体现本民族理性思维的创造性活动,表达出自己关于哲学的独到理解和全新阐释。在“照着讲”、“接着讲”的基础上,能够“自己讲”,[34]讲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新哲学。“自己讲”与西方哲学在现当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如果说语言学转向“是从近代哲学离开对语言意义的审查而探究思想的客观性的认识论追求,转变为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和理解,意义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切入点”,[35]那么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这次转换就是从以往忽视对哲学语言所承载的意义性的认识,转变为强调语言的分析和阐释对于哲学创造的重要影响。在本体论方面,摒弃以往将西方哲学史看作是知识汇总或认识发展史的固囿,将西方哲学与人的生存境遇相联系,认为哲学以其特有的“概念”、“思想”为载体,阐释着对人类“精神故乡”和“安身立命之本”的终极关怀;在认识论方面,从以往的对象性认识转变为生成性认识,强调主客体互动的思想创造过程;在方法论方面,重视语言分析和意义阐释,哲学作为“创造性的学问”和“自由性的思想”正体现在其语言上。正像德勒兹对“概念”的重视一样,哲学创造一组特有“概念”,并对其进行独到阐释,就是开创一种对世界的理解视角,也就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种全新的向度。因为“概念”代表着特定的哲学语言,既包括语义学维度,也包括语用学维度,即作者在使用语言时的意图何在。不同的哲学家以不同的“概念”表征不同的思想,同一“概念”在历史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阐释下也可能指代不同内容。这就是对哲学思想的不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接着讲”和“自己讲”的可能性和价值性。黑格尔曾在致沃斯的信中说:“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21]我们反复引用黑格尔对语言重视的这段话,旨在说明黑格尔力图用本国语言阐释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努力并努力成功——让哲学说德语和用德语建筑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而登上国王哲学宝座以实现两千多年的“哲学梦”,在于哲学“语言”。海德格尔也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波普指出语言的出现创造了人类生活的“第三个世界”。皆表明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的创造就是思维的创造,思维的创造就是人类理性能力发展,就是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就是思想理论的发展提升,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
在“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语言”与“概念”新的思维方式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强调哲学创作者与哲学解读者的互动,强调哲学研究过程中思想和意义的创生,强调对意义性的阐释和再造的主体自觉,“在知识、思想和意义的三位一体中重塑西方哲学。”[36]以“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为指导,既是对哲学本身的发展,更是对人类认识与改造的生存空间性的扩增——语言具有的多样性、意义具有的开放性、创造具有的无限性,将哲学“向上兼容”的本性和无限开拓的生命力真实的布展于世。所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对西方哲学史的认识需要转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致思方向,要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理解西方哲学,在中西马融通和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意义上重新阐释西方哲学,赋予西方哲学全新的生长点。或者说“让哲学说汉语”,[24]要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解释原则重新阐释西方哲学,让“说汉语的哲学”向世界传达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当下文化及发展趋势,彰显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这是哲学创造的未来之路,也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想目标。
[1]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6.
[2](英)赫胥黎.天演论[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3;94.
[3]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忻剑飞,方松华.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96.
[4]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J].觉悟,1921(07).
[5]张君劢.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2.
[6]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卷)[M].中华书局,1989.62.
[7]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J].新青年,1916(01):6号.
[8]陈独秀.敬告青年[J].青年杂志,1915(01):1号.
[9]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8.
[10]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06):1号.
[11]胡适文集(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3.
[12]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0.
[13]冯友兰文集(第6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214;219.
[14]李长之.西洋哲学史[M].正中书局,1941.1.
[15]陈卫平.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J].学术月刊,2004(07):9.
[16]杨忠文,秦玉峰.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宏观考察[J].求是学刊,1992(05):23.
[17]杨河,邓安庆著.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56.
[18]陈村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写在《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出版之际[M].人民日报,2010-09-10.
[19]汤一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44.
[20]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版)[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前言第2页.
[21](德)黑格尔通信百封[M].苗力田,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2.
[2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93.
[23]赵敦华.用中国人的眼光解读西方哲学[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7):59-60.
[24]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J].社会科学战线,2004(02):49;29.
[2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
[26]江怡.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J].哲学分析,2010(01):73.
[27]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06.
[28]黄见德.西方哲学的传入与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304.
[29]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1):53.
[30](俄)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99.
[31](法)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59;37.
[32]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前言第3页.
[3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前言第2-3页.
[34]张立文.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2):8.
[35]韩秋红,庞立生,王艳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
[361]韩秋红.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J].社会科学战线,2012(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