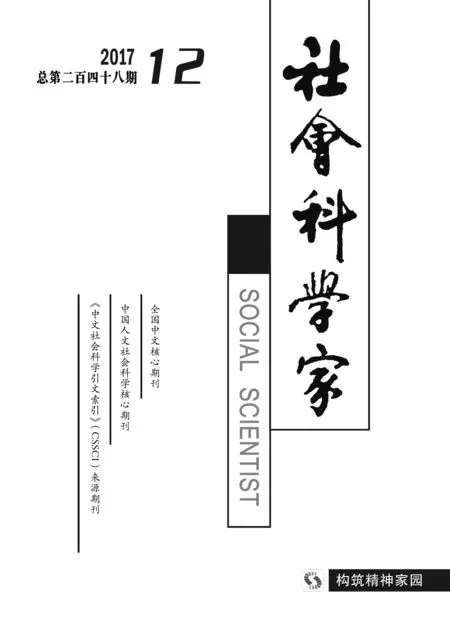从程颐到朱熹、张栻的“休复下仁”解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仁”之一词,自孔子开始,便成为儒学的核心概念。孔子整理六经,修《春秋》删《诗》而序《易》,从而开创了以六经为基本典籍的儒家学派。其中,《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之源,后来亦成为六经之首,其地位无其他经典可比。然而,在这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作为其核心概念的“仁”之间的关系,却颇有些令人寻味之处。
一
《周易》的文本(包括经传),寻以“仁”字,主要出现在《文言》、《系辞》及《说卦》之中,但若按欧阳修《易童子问》的观点来考量,因只有《彖辞》、《象辞》为孔子所作,故这几篇全不能计。从此出发,要看孔子自己之“仁”说,就只能是审视孔子继承先圣而来的《易经》64卦、384爻的卦爻辞和孔子自作的《彖》、《象》。
然而,如此审视的结果,却颇出人预料,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仁”说,在孔子的易学著作中、至少在文字上基本未得到反映,这是否也意味着《论语》中那句颇使人疑惑的“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的“三罕言”之说,实际并不难以理解?朱熹《论语集注》对此条的处理,便是引程子之言而给予了直接认同的立场。其称:“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1]重义轻利视域下不言利很正常,命与仁则被解释为命之理与仁之道,二者在孔子因为属于“不可得而闻”的范畴,说是“罕言”也就可以成立。
张栻《论语解》此条是自注,所解与程子义相近,稍有不同的,是突出了孔子对于命与仁的“未尝指言之”之义,而需要学者“潜心”去体验[2]。张栻突出“指言”与否的问题,与他在为胡宏《知言》作《序》时,因其“论性特详”而与孔子异,以致在同门中引起疑惑时所做辩解的立场是一致的①张栻《胡子知言序》云:“夫子虽未尝指言性,而子贡盖尝识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哉?盖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见《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四,《张栻集》,第975页。,体现了张栻十分擅长的本体论的思维方法。
回到《易传》,全部卦爻辞,包括《彖》、《象》在内,只在复卦六二爻《小象》处出现有唯一的“仁”字,即:
[复卦]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从整个六二爻来看,爻辞以“休复吉”之言肯定了休美之复的吉祥之意。但为何能够如此,则需参考《小象》的解释,从而出现了罕见的“仁”的概念。那么,孔子于复卦此处为何要言“仁”,而且,采用了在其全部“仁”说中独特的“下仁”的表述呢?在此可以略作分析。
复卦《彖辞》在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其“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一句说辞。可是,孔子不但没有揭示此说辞与“仁”究竟有何关系,甚至连此“仁”到底为何意也没有给予说明,问题完全留给了后人。
王弼注《易》是将爻辞与《小象》合二而一的,以为六二爻是“在初之上而附顺之,下仁之谓也。既处中位,亲仁善邻,复之休也”[3]。即六二爻位于初爻之上,但却又依附和顺从于在下的阳爻。以阳为仁,最早可追溯到《说卦传》论天道阴阳与人道仁义的沟通,其后汉儒如董仲舒等亦均以阳说仁。具体落实到复卦,和煦阳气的复生正是仁的爱意的形象展现。所以六二要下到初九之仁,而且是亲仁善邻而关爱他人,从而体现出“复”的美好。
到程颐著《易传》,不赞同王弼以静释天地之心而代之以动,强调“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直接将阳气之复与天地的生意相联系,打造出一整套理学的生生之说。因而,“复”意味着美好的前景大致是公认的。其具体蕴含,程颐以为:“复者,复于礼也,复礼则为仁。初复阳,复于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4]那么,一阳复现于下(初)爻,实际是复归于阳生阴消的天地正常秩序——礼,复礼成就了仁德。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被运用到了阴去阳复、天地生生而溥爱万物的景象上。如此之“复”所以可能,乃是因二爻与初爻相比配而下归于阳,从而产生美好吉祥的结果。这里的关键,一是下仁,一是复仁(复礼为仁)。仁作为普遍之爱,又与公发生了关联,故程颐又说:
为复之休美而吉者,以期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复于仁,二能亲而下之,是以吉也。[4]
对“能下仁”的认定,是“复”之休美吉祥的基本要件。仁在这里,仍然可以从自然的层面去看,它意味和煦的阳气对天地万物的生生来讲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偏私;而从人世的层面看,则是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是公平无私之爱①二程《遗书》记载: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者,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见《二程集》卷九,第105页。。在这里,善之德行虽然可以有伦理上的多种解释,但基本点是普遍无私地满足人们的正当需求——譬如(建立在满足生存需求基础上的)对爱和尊重的需要,这里贯穿着“公”的精神,体现的是仁的本质。初爻与二爻因相比而关联为一体:初爻复于仁(由纯阴转为一阳复升),二爻则亲近而下顺于仁,所以能吉祥美好。
程颐这里所强调的六二爻的秉性——“志从于阳”,“能下仁”与“复之休美”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9]。从其初始的“志从于阳”来看,由于阳即仁而体现公,也可以说是志从于公,而公者背私也,由此,“休复下仁”就可以联系到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去获得解释。
二
作为二程后学的闽学和湖湘学两翼,对于“休复下仁”的关注有所不同。朱熹于《易》有不少著述,朱熹的仁学与《易》亦密切关联,但对于《彖》、《象》中唯一的“仁”字和“休复下仁”这十分特别的表述,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朱熹《本义》于《象辞》尤其是《小象》,绝少解释,通常是原文照转。或许,是因为《象》之真意难有确解,导致了他采取如此谨慎的做法?这与他对卦爻辞及《彖辞》并不吝惜注解的态度是颇有些不同的。既然如此,朱熹对六二《小象》自然也不会特别留意。不过,对于六二爻辞,他却有一简单疏解如下:
柔顺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复之休美,吉之道也。[5]
由于“一阳复生于下,复之主也”的前提[5],六二爻柔顺的性质使其不能自做主,于是下顺于初九之阳,从而才有复之休美的吉祥之道。从程颐走过来,程朱都肯定六二爻由于中正之位而具备主动性,所以其下于仁都是主动为之。事实上,从朱熹以“能下之”言复之休美来说,他应当是吸收了《小象》和程颐的解释的。
此外,朱熹在与弟子的问答中,对六二爻之“下仁”有进一步的说明。他称:
问“六二‘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为仁人之体,六二爻能下之,谓附下于仁者。学莫便于近乎仁,既得仁者而亲之,资其善以自益,则力不劳而学美矣,故曰‘休复吉’。”[6]
初爻的意义,在朱熹提升为仁人之体,六二爻的“下于仁”,相应成为“向下依附于仁人”。由此,学者的近于仁,就不是一般泛言的近于仁德,而是特指学者得遇仁者而亲近之,从而能借助仁者之善增益自身德行,结果就是工夫简易而学行美好。
由此来解释“休复吉”,表明朱熹的重心,在劝导接近仁者而增益德行,并以此为学者最切要的工夫。回想当年,朱熹与象山辩时,象山曾讥其工夫支离而不简易,朱熹这里虽然不涉及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问题,但其教诲弟子,注意在“紧要为己为人”的工夫上着力,亦可看作是他“反身用力,去短集长”经验总结的进一步落实[7]。
与朱熹有所不同,张栻对六二爻《小象》有直接的注解。张栻曰:
《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尝言仁,此独言之,夫子盖有深旨。克己复礼为仁,克其私心,复其天理,所以为仁。二去初未远,上无系应,能休泰而复,所以为下仁也。至四但言“以从道也”,而不谓之仁矣。盖道者,举其大凡,不若仁为切至也。[8]
张栻应当说是有问题意识的,他注意到孔子“此独言仁”的问题,并以为“夫子盖有深旨”。那么,这个“深旨”究竟为何呢?张栻之解是克私为公,从程子体贴而来的天理,是公天下的礼的要求,与私意是正相对立。这与他在其《仁说》中所言之“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9]是相呼应的。意味除去了私欲的障蔽,本具于性的爱之理,在公天下的情怀中能得以彰显。
结合爻辞的运动看,六二爻往上升到倒六四爻,同样也是阴柔得位,为何六四爻《小象》是“以从道也”而不是从仁呢?张栻以为道与仁之间,虽然质性相同,但各自的界域和承担的职责有别,六四爻虽也有志于复阳,但因居于力弱无援之地,难以有真实收效,故只能是一般性地肯定其“从道”。因为道是无所不在的,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故无处不可以从道。但仁则不同,孔子独言或罕言仁,就在于仁有克己复礼、廓然大公的具体内涵,其恳切周至便不是一般之道可比。故六二爻与初九爻相应并紧依于阳,其下仁乃是顺从必然,最终能够获得通泰归仁的收效。
张栻注重从“下仁”的象数机制去解释“为仁”,表明了他对程颐观点的继承。重点在传达人之复归仁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自律,而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相合。当然,就一般原则来看,张栻在《论语解》中已申明,孔子云“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是“言‘为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与也”[10],尚未涉及客观的辅助机制和必然效力的问题。这在朱熹,基本也是如此。《朱子语类》记载:
问“克己复礼为仁”。曰:“克去己私,复此天理,便是仁。只‘克己复礼’,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须更借别人刀也。”[11]
刀是自己刀,自己动手割物异常简便,无须费力,这在朱熹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他注《论语》“克己复礼为仁”时亦称:“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12]“我”在这里居于完全的主宰地位,只要我不以为难——刀在我手,剩下的就只是具体操作的事情了。问题也正因此而引出:既然克己不难,为何人又难以做到呢(圣贤除外)?复礼(理)作为结果,固然离不开人之克欲去私的意志决断和德行涵养的水准,但是,如果只是从人内在的道德秉性及自律责任上着眼,就难以解释世上为什么很少有人能真正实现去私欲而复天理,从而也引出克己复礼缺乏足够的道德动力的问题。
张栻对此问题的分析有不同的侧重。一方面,如前所述,张栻是看重“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的,他曾将孔子强调自觉为仁的相关语录汇聚在一起,集中发明曰:
夫子曾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为仁由己”;于此又明“不让于师”之义。盖道不远人,为之在己,虽所尊敬,亦无所与让。圣人勉学者使之用其力也。[13]
孔子诸语,着眼点都在人用不用力,人若用力则为仁不难。圣人的教诲,都落脚在使人用力上。但是,圣人勉励学者用力,实际也说明人之克己为仁不易,所以需要外部力量的辅助——圣人的告诫劝勉也属于外力的作用,这便是张栻注重的另一方面。他在注《论语》“以友辅仁”时曾称:
为仁固由己,而亦资朋友辅成之。辅云者,左右翼助之意。盖非惟切磋之益,为从容浃洽,相观而善,所辅为多。[14]
很明显,“为仁由己”不是论结果,而是说动机,这与他前面注“克己复礼为仁”时讲“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与也”是一致的,都是在强化自我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强调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力不可能代替你成就仁德。但在此前提下,为仁要有收效,又离不开外部环境条件的支持。在友朋的辅助下,为仁的难度明显降低,最终促成了自我从于仁的践履顺利成行。
联系到他的易学注解,张栻立足于《易》之卦爻运动和象数机制讲“克己复礼为仁”,也就将通常受制于“为仁由己”的一般道德自律意义的复礼或复理,与基于阴自觉复归阳而生气流行意义上的“下仁”趋向相统一。同时,与此相应,张栻这里的“下仁”之“仁”,也就不是朱熹的仁人,而是指仁之德性。至于具体如何“为仁”,历来儒者已有较多的考量,张栻的重点,在阐明人之克己复礼背后的天道必然的趋力。
张栻云:“以时观之,则一元之气方萌于十一月,天地之心可窥见矣。以一身观之,则人心微动之初,亦可以见天地命我者矣。”[8]天地之心”彰显于“复”,意味着“为仁由己”的人心发动,是在“天地命我”的驱动下得以成行。落实到六二爻,由于其与初爻比邻,在上又无其他阳爻的掣肘,故能够自如地复归初阳,取得阴阳通泰而仁德彰显的效果。张栻将休复解释成“休泰而复”,突出了仁意的普遍通泰蕴涵。“为仁”原本面临的“克”、“复”的艰难性,已经被阴从于阳、柔顺于刚的“下仁”或“从仁”的必然性所消解。或许,这也是张栻从《易》之卦爻运动角度讲“克己复礼为仁”的缘由所在。
[1]朱熹.论语集注·子罕[A].四书章句集注[C].北京:中华书局,1983.109.
[2]张栻,杨世文.论语解·子罕[A].张栻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5.179.
[3]王弼:.周易注[A].楼宇烈.王弼集校释[C].北京:中华书局,1980.337.
[4]程颐:《周易程氏传·复》,《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820.
[5]朱熹,苏勇.周易上经·复[A].周易本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5;35.
[6]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卷七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89.
[7]朱熹,朱杰人.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A].朱子全书[C].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3).2541.
[8]张栻.南轩易说钩沉·复[A].张栻集[C].1552;1551.
[9]张栻.南轩文集·仁说[A].张栻集[C].1032.
[10]张栻.论语解·颜渊[A].张栻集[C].214.
[1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一)[M].1051.
[12]朱熹.论语集注·颜渊[A].四书章句集注[C].132.
[13]张栻.论语解·卫灵公[A].张栻集[C].263.
[14]张栻.论语解·颜渊[A].张栻集[C].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