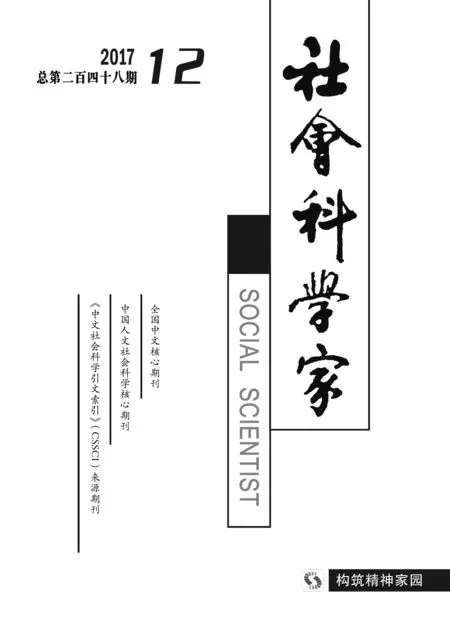生活在此处
——对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克尔凯郭尔式的解读
王 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青年导演邵泽辉编导的话剧《在变老之前远去》首创于2008年,但直到九年后的2017年3月,我才有机会在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观看此剧。距离首演相隔这么久,但曾经困扰剧中人的问题和他的解答方式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社会“后现代”情绪的增长变得愈加尖锐,愈加发人深省。
话剧讲述的是一个诗人M.H①M.H即马骅(1972-2004),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他英年早逝后,友人将他的诗作和信件结集出版,题名为《雪山短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的生存,人物和故事原型来自导演一个朋友的真实故事,戏剧演出过程中,观众甚至能从大屏幕上看到故事原型的影像。作为戏剧艺术的爱好者,我对小剧场话剧情有独钟,感觉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古典戏剧原则似乎更有可能被发挥到极致,而现代戏剧手法的试验性使用的灵活度也更大,《在变老之前远去》中古典与现代戏剧元素的创造性运用再次为我印证了这一点。不过作为一名哲学研究者,我更感兴趣的是话剧所表现的诗性生活方式及其困惑与出路。
话剧开场时,剧中人对着镜子问了一连串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之后,决定辞掉工作,离开北京,独自去不知名的远方寻求一种完全另类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从主人公向自己提出的这些问题中我们不难判断,这是一位写诗的都市白领,他在生活中并没有遇到诸如经济困窘、失恋、工作失利等世俗意义上的所谓挫折,他的烦恼更多源自对诗的生活方式的崇尚与都市的喧哗与骚动之间的不和谐音,因而这烦恼在根本上是形而上的,其深层根源在于诗人丰富的精神性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精神性”(spiritual)是一个来自西方思想传统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宗教性”(religious)。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很强“精神性”的人不一定信奉任何宗教,虽然反过来说,一个具有“宗教性”的人必定是一个“精神性”极强的人。古希腊哲学家就把人分析为“肉体”和“灵魂”的综合体,其中“灵魂”意味着“生命”,代表着永恒不朽和神圣,而“肉体”则从“灵魂”那里获得“生命”;所有的“肉体”都是有变化的、有死的,唯有“灵魂不死”。这个思想为后来的基督教人论贡献了重要的“精神性”的维度。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加入,人进一步被分析为“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综合体,灵与肉的冲突也更进一步成为西方文学艺术中的主题。相比之下,中国儒家传统发达的理性主义使得个体的自我冲突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儒家文化以直接的方式为人的成长指明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大学》),而“修身”之法似又可概括为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反省(《论语》)。在对待人的情感的问题上,儒家强调“中和”的理性态度,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于是乎,从强调情理平衡和实用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出发,人们很难理解剧中诗人在开场时表现的生存烦恼,因为那是一种典型的自寻烦恼,是自我的“无事生非”,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用市井俗语说就是“吃饱了撑的”。只有从西方文化中人作为“灵与肉”、“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综合体的角度出发,诗人的烦恼和困惑才会变得清晰而有意义。
我们的诗人穿过繁华的尽头看到了生活的悖谬,但他并没有一味感叹生活的无意义,而是背着行囊,来到了梅里雪山脚下,踏上了“生活在别处”这条诗人和所有崇尚诗的生活方式、有着丰富精神性的个体的拯救之路。“生活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因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而广为人知。昆德拉在小说的序言中将这句话归诸19世纪末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Arthur Rimbaud),但我翻阅了兰波作品全集,并没有找出直接对应的诗句。[1]根据昆德拉,这句话曾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被大学生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或许这句口号只是兰波的名言,并不一定直接出自兰波的诗作。昆德拉本人最初将小说命名为《抒情时代》,因为他要撰写的是“青春”、“抒情时代”、“抒情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主意,将标题更换为《生活在别处》。这个改动表明在小说家眼中,“生活在别处”就是一种典型的“抒情态度”,它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2]
虽然我目前没有找到“生活在别处”的出处,但毋庸置疑,用“生活在别处”来概括兰波的人生轨迹是再恰当不过了。兰波早熟早慧,是一个典型的不安的灵魂,年仅19岁就在写下名作《地狱一季》(A Seasonin Hell)后告别文坛,从此辗转亚非欧三大洲,做商人、雇佣军、殖民地包工头等,远离他深感厌倦的欧洲“科学”、“进步”和基督教文化,把“前行”(Forward march)当作“惩罚”,去演出生活这场闹剧(“人生是一场我们不得不表演的闹剧”)。[3]我们的诗人没有像兰波那样在猎奇和冒险生涯中折磨自己,追求自我。他也没有走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道路,后者投身于希腊人民抗击土耳其统治的斗争之中。我们的诗人并没有追求极端的、另类的人生经历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求,因此他落脚在雪山脚下的一间乡村小学,悉心教二十几个藏族孩子念书。物质生活的原始性使得诗人毫不费力地实现了海子“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理想,这个模式的开启几乎是本能的。在缓慢、平淡的生活节奏中,在“凌乱的合唱”声中和“鲜艳的四年级学生”纯真的笑脸中①马骅:《小学生》,见《雪山短歌》。,诗人自觉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开始在背山的桃花树下写出了带有民歌风味的、质朴而丰满的诗句②马骅:《雪山上的花开了》,见《雪山短歌》。——
山上的草绿了,山下的桃花粉了;
山上的桃花粉了,山下的野兰花紫了;
山上的野兰花紫了,山下的杜鹃黄了;
山上的杜鹃黄了,山下的玫瑰红了。
偷睡的年轻汉子在青稞田边醒来
雪山上的花已经开了。
拜伦和兰波的“生活在别处”是刺激的冒险,排除个性因素和风起云涌的时代因素,剧中诗人的“生活在别处”的指向无可否认地带有“隐”“遁”的中国文化基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的诗句几乎成为所有中国读书人的理想退路。值得深思的是,诗人并没有引用陶渊明,而是在与友人交谈时道出了“大隐隐于市”。初闻之下觉得不解,明明是舍弃了灯红酒绿的都市跑到乡村,为什么不是“小隐隐于野”呢?细思则恍然大悟,即使梅里雪山脚下的乡村学校仍然是“市”——世间,人间,世俗生活,它跟大都市的“市”只在规模、节奏和复杂性等各类量化指标上有所区别。换言之,“隐于野”只是纯粹的“理想”,凡有人的地方皆为“市”,只不过不同的“市”的衡量标尺有所不同。
在梅里雪山脚下,房子的大小、挣钱的多少暂时尚未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和价值的标尺;生存空间的相对狭小和生存方式的单纯又使诗人比较容易为自己的自我圈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从而更有可能以诗的方式追寻生命的意义。之所以强调金钱“暂时”没有成为衡量标尺,是因为诗人自愿给当地村民传授英语知识,希望他们能够在新兴的旅游经济中胜出,赚到更多的钱。沿着这个思路,人们似乎很自然想到,会不会有一天,梅里雪山脚下的偏僻乡村也将淹没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开始“以钱论英雄”了呢?对这个假想的问题我不予回答,因为不正确的提问会导向不正确的回答,对前述问题的回答有很高的几率会导向对小农经济温情脉脉的依恋,以及在此前提下对商品经济的批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们为利益奔忙原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正是人生存的基础。在《福音书》中有则耐人寻味的寓言“天空的飞鸟和田野的百合”,耶稣告诉世人,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田里的百合不纺不织,神照样养活它们,给它们以美的妆饰,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应“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①《马太福音》7:25-34。。但是,如果不按寓言的方式而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耶稣的话语,此人无疑将会以惨死告终。事实上,耶稣从未否定现世生活的意义。当法利赛人用“是否该纳税给该撒”的险恶问题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②《马太福音》22:21。,以此肯定了人的现世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思想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深受新教浸濡的克尔凯郭尔眼中,弃世绝尘是对上帝赋予每个人在现世的职责的逃避,如果这不是怯懦,至少也是小心的表现。③S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vol.3,Gads Forlaget 1997,pp.230-234;《克尔凯郭尔文集》第3卷《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95-298页。克尔凯郭尔认为,人是有限和无限的综合,精神和肉体的综合,因此“生存持续地奋斗着”④S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vol.7,Gads Forlaget 2002,p.91.,正是生存的“双重性”才使得人的生存变得如此艰难。生存的张力和困难要求个体处理好“该撒的物”和“神的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熙熙攘攘皆为利”的生存洪流之中,在处理好生存的“有限性”的前提下,个体要坚持自我,保持对生存中“无限性”维度的追求,执意探问超出利益之外的生命意义。
从诗人向自己提出的那一连串问题中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诗人没有被利益的洪流卷走,而他的远离尘嚣也不是遁世,而是寻求一种精神的自我康复,就像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他的隐居是为了清理思绪,更好地向世人宣讲他对“大地”的热爱。诗人在梅里雪山的日子是充实的,同时也是“抒情的”;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剧中,友人从北京来访,两人边饮酒边回忆青春烂漫的日子,倾诉生活的烦恼,感叹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时,友人就问诗人提出今后怎么办的问题。这一场戏初看因过于贴近生活的真实而显得平淡无奇。及至二人郑重道别时,扮演诗人和友人的演员竟然角色互换,这时我才顿然领悟到了戏的分量。原来两位演员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看作是同一自我的不同面向,他们正是人的“双重性生存”的象征——诗人更多代表的是生存中对无限性的追求,友人更多代表生存中有限性的羁绊。这一幕与开场时两位演员分别作为“自己”与“镜中的自己”(自我)对面而立、彼此质问那一幕正相呼应。
诗人对自己的未来去向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在酒意之中含糊地回答了“也许回去”的话。不久,命运迫使诗人必须做出选择:他所教的小学生毕业了,将升入镇上更高级的学校念书,这意味着他在梅里雪山脚下的任务-使命即将结束,他不得不离开此地。何去何从?是继续前行,寻找一个翻版的雪山乡村小学,开始新一轮的“重复”;还是回到北京,带着对生命意义的全新思考,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市”中开展全新的生命之旅呢?我们未及听到诗人的回答,一场不幸的车祸便夺去了诗人年轻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悬念。舞台上,演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象征性的弯曲山路。突然,粉笔落地,灯光骤然变暗,这出戏伴随着诗人生命的突然消逝从根本上结束了……如果这是一出纯粹虚构的戏,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结局,它在给观众带来震动之余将引发无数的追问。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生命的陨落,戏剧手法在真实生活中的完美再现不禁令人唏嘘,感叹人生如戏,生活中原本充斥着巧合和偶然,俗语“无巧不成书”表面看似乎是在为书中的各种偶遇和巧合做辩护,事实上人生样态与书的关系应该颠倒过来——是生活中先有巧合和偶然,然后才有了书,戏剧和文学在本原意义上都是对生活的反映-反射。当海德格尔检讨西方哲学对“存在的遗忘”的时候,艺术家们从未远离存在问题半步。
那么,假设没有这场飞来横祸,我们的诗人将何去何从?
当一个人出于丰满的精神性和形而上的原因对生存现状表示不满的时候,这种不满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生活中的各种“重复”,比如“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每日柴米油盐的琐碎。“重复”(Repetition)这个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词汇在1843年即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关注,并被作为哲学-心理学的概念写进《重复》一书。克尔凯郭尔在书的开篇即以比喻的方式分析了三种生存中的行为——“希望”、“回忆”和“重复”。他把“希望”比作一位很容易从手中溜走的可爱女郎,把“回忆”比作生活已被耗尽的智慧老妪,把“重复”比作一位被深爱着的、不会令人厌倦的主妇。“希望”像诱人的果实,但不足以充饥;“回忆”像一笔差旅费,但不够花;只有“重复”才像日常的饮食,它带着祝福供人享用。克尔凯郭尔最终指出,“人生就是重复,重复是人生之美”。“重复”比“希望”和“回忆”都需要勇气,因为每天坚持做同样的事,但每一次都带着最初的新鲜感而为之,倘若没有足够的生之勇气绝无可能做到。①S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vol.4,Gads Forlaget 1997,p.10.过去我倾向于用“再现”来与克尔凯郭尔的概念Gjentagelse/Repetition相对应,取丹麦文词根Gjen-(英文对应为Re)中“再”、“又”的意思,认为“再现”既不失原意,又比“重复”多了“创造”的意蕴。但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显然错失了克尔凯郭尔在强调“人生就是重复”时的附加条件——每一次重复都带着最初的新鲜感。日复一日地完成生活中包括生存下去的琐碎任务,与此同时,拒绝哀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②《旧约·传道书》1:9。,而是认定,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勇气和信念的支撑。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不仅要靠个体去发现,更要依靠个体积极地去建构。任何一种追求意义的人生都缺少不了“远方”(不确定性)和“诗”(艺术)的维度。当一个人的青春热情澎湃之时,一方面青春无敌,没有任何困难能够令其退缩,未来的确定性令人绝望,此时对“远方”的向往更像是冒险;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自我的不确定性——例如,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又会成为个体深层焦虑的根源,这种焦虑因其没有具体对象和指向而更深沉,更难以摆脱,于是“远方”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精神的避难所。生存就是这样充满悖谬性——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令人绝望,而漫漫无边的追求又令人焦虑。换一个生活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像诗人那样从繁华到简朴,既是对生活确定性的突破,也是对人的生存样态的多种可能性的冒险式体验。但无论怎么变化,“重复”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身处何方,一个人每天必须回应生存向其提出的要求。就诗人的个案来说,在梅里雪山脚下,生存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分散了他对精神追求的全神贯注,教书育人的现实目标释放了他对未来的深层焦虑,同时也为他的生活注入了意义和定性。海子在其广为吟诵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作中,把幸福寄托在生活中那些烦琐小事之上——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在戈壁滩,海子写下“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的诗句,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生存现实性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人的精神焦虑。生存的悖谬性和“双重性”无疑使得生存成为一门艺术,片面地偏向任何一边都会导致生活中的“致死之疾病”。只关注生存中的“有限性”维度、但却忽略“无限性”和“精神性”追求的人,极有可能沦为市侩,从而不得不面对《福音书》中尖锐的问题:“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③《马太福音》16:26。“灵魂”一词在汉译《圣经》中写为“性命”,但因该词的希腊文原意为“性命”和“灵魂”,此处根据英译本译为“灵魂”。但若一味偏重“无限性”和“精神性”生存的维度,忽视或者无法有效处理生存中“有限性”因素的束缚,这样的生存很可能会因缺乏现实性的基础而行之不远。
如果没有那场飞来横祸,我相信,我们的诗人会从乡村教师这段经历中成长,他会认识到“重复”之于人生的意义,明白生命历程中的每一天都要通过切实的行动去“建设”①“建设”(opbygge,英译为 up-build)、“建设性的”(opbyggelig;up-building)是克尔凯郭尔的重要哲学和宗教学概念。2,(11):86-90《.旧约·传道书》1:9。),2015,18(1):86-91.;通过“建设”,他在时间中为生命的每一瞬间获得意义;通过这些瞬间,使个体在自由之中得到发展。从这段经历中,我们的诗人应该对生存的“双重性”有更深刻的体会,他也会逐步学习处理生存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悖谬关系。我们的诗人最终会认识到,无论一个人身处大都市还是荒野乡村,只要他有心把太阳看成每天都是新的,他的人生绝不会乏味。
如果没有这场飞来横祸,我们的诗人会回到北京,有一天,他会收获自己的爱情,成家立业。他会不会像克尔凯郭尔的名作《非此即彼》下卷中的伦理生活方式代言人威廉法官那样,“就在起居室里”,但却“努力把每一天当作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一天,把每一天当成是接受考验的那一天”呢②S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vol.3,Gads Forlaget 1997,p.34;《克尔凯郭尔文集》第3卷《非此即彼》(下卷),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无论身处何方,我相信他都会从事更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写诗,写戏,办刊物,像萨特那样有意识地“介入”生存,通过自己的“介入”克服生存的虚无感和荒谬感,以创造的姿态为人生注入意义和价值……
话剧结束之后,导演上台致谢,并为观众解说了这出戏的创作背景,提到当时曾跟诗人商议过,以他的经历写一部戏,而诗人曾答应亲自出演……导演回顾了自己和诗人相仿的青春梦想,讲述了今天为家、为孩子操心的生活,言语中有一丝无奈。我更愿意把这番致谢辞看作整出戏的一部分,而不是谢幕后为观众做的剧情解密。作为剧中诗人的朋友,导演完全可以成为剧中的一个人物,以他自己艺术创作经历——包括这部戏的创作——给那些怀有“抒情态度”的人一个肯定性的回答:只要心怀“生活在别处”的“抒情态度”,生活完全可以就在此处,在市井坊间展开;只要永不放弃对“意义”的探求,人生的“意义”将伴随着个体的行动一点、一点地建构起来。
[1]ARTHUR RIMBAUD,Paul Schmidt,Complete Works[M].Harper Perennial,2008.
[2]米兰·昆德拉,景凯旋,景黎明.生活在别处[M].作家出版社,1991.1.
[3]ARTHUR RIMBAUD.“Bad Blood”in Complete Works[M].Harper Perennial,2008.2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