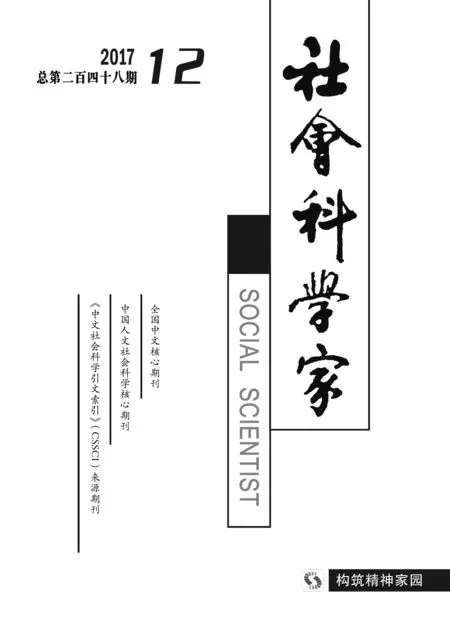海德格尔与谢林的哲学对话
劳赫·胡恩,庞 昕译
(弗莱堡大学 哲学系,德国 弗莱堡 79085)
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诠释,尤其他将《自由论文》①谢林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研究》通常简称为《自由论文》——译者注。解读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s Bsen)这一点,会让人愈发觉得矛盾。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尽管谢林仍然植根于近代的主体中心及其意志命令,但这篇以“自由”为论题的文本已经触及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对存在自身(Seyn)的追问,而这正在于海德格尔用“存在的间隙”(Seynsfuge)所命名的根据(Grund)与实存(Existenz)的区分②Heidegger,Schelling: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GA42),Vittorio Klostermann,1988,S.185.GA 为 Gesamtausgabe,即德文“全集”的缩写形态。。这个区分与谢林对“就其实存而言的本质”与“就其仅仅作为实存之根据而言的本质”③Schelling,S mmtliche Werke VII,J.G.Cotta’scher Verlag,1860,S.357.的基本区分密切相关。凭借该区分,谢林在哲学历史上首次真正迈出了突破“意志形而上学”(Willensmetaphysik)的最后一步。尽管如此,海德格尔仍然认为,这位观念论者并没有完成这个突破。
1955年,海德格尔的学生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出版了《德国观念论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完成》一书。这部指导性的著作为观念论哲学,尤其谢林的观念论哲学开启了一个尤为独特的研究领域,该领域正是由海德格尔照亮。海德格尔在1936年夏季学期的首次谢林演讲④在1926年与雅斯贝斯的通信中,海德格尔就已表明他对谢林《自由论文》的重视(参见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的通信集)。《存在与时间》出版后不久,他便开始细致解读《自由论文》(参见海德格尔全集第86卷中对1927年至1928年冬季学期马堡讨论班的相关记录),并于九年后,即1936年,首次就该文本开设了演讲课——译者注。真正推动了谢林思想的复兴,并使之走出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位观念论者,即黑格尔的阴影。此外,海德格尔也将谢林看作尼采的先行者。尼采因其“创造力意志”(Wille zur Macht)说出了西方哲学的隐秘内核而成为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但根据海德格尔,谢林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Wollen ist Urseyn)①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S.350.这个总结了观念论的表达才是基于“意志”理解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尼采将这种从谢林而来的意志理论发挥到了极致。
一、虚无主义背景中的谢林
海德格尔在谢林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中首先看到的是基础性的“关于恶的形而上学”。在1936年夏季学期对《自由论文》所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解读中,他将整个文本归结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并非偶然。通过“关于恶的形而上学”这个表达,海德格尔阐述了西方形而上学总体的基本特征:始终只是从物的存在者性(如何被表象、被制造)来理解存在者,遗忘了此存在者性的本源(Ursprung),遗忘了对存在自身的追问,也就是说,尽管问题已被提出,但仍然有所错失。“形而上学命名了存在,指的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②Heidegger,Wegmarken(GA9),Vittorio Klostermann,1976,S.370.。在《自由论文》中,这一基本特征已经清晰可见。谢林对“恶”的讨论明确指出了一种基础性的本源的遗忘,而且,正是这种本源的遗忘导致了近代主体性的意志构想难以确立的悲剧。根据海德格尔,“本源的遗忘”贯穿并且隐秘地构造着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相应于此被遗忘的“本源”,也存在这样的“主体”,其作为“使自身成为某种东西的源初且基本的意志活动”③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S.386.建立于“无”(nichts),并预示着虚无主义。
海德格尔有关虚无主义的论断主要集中在他对尼采的阐述中。这些论断也是他解读谢林《自由论文》的中心,虽为背景,但同样具有规定性的作用。《自由论文》出版两年后,雅可比与谢林再次展开了关于信仰与认知、有神论与无神论,或者更准确地讲,与虚无主义的争论,亦即“争执于神圣之物及其启示”④F.H.Jacobi,Schriften zum Streit um die go ttlichen Dinge und ihrer Offenbarung,Felix Meiner,2000,S.33-136.。从哲学历史的维度来看,《自由论文》不只是先于这场争论现世,而且在根本上属于这场争论的直接的“前史”。在关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的虚无主义发端之处的讨论中,雅可比与谢林的这场“争执事件”直至今天仍然扮演着关键角色。在此,正是谢林使得一种单纯基于意志活动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虚无主义前提,即意志活动的自身矛盾得以明确。这个由《自由论文》所揭露的虚无主义的自身矛盾标明了康德之后的观念论讨论“自由”的本源之遗忘。
依据海德格尔对十九与二十世纪虚无主义的论断,西方哲学在整体上的结果与顶点必定是“意志形而上学”。有鉴于此,海德格尔在对谢林文本的细致解读中揭示了这一点:虚无主义的自身矛盾是“关于恶的形而上学”的核心。这与海德格尔所讲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一致。因此,他称赞谢林为尼采首位精神上的血亲,并将“关于恶的形而上学”认定为“创造力意志”的先导形态。
仔细研究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解读便可发现,尽管他强调谢林与尼采在结构上的根本关联,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仍然依循两位哲学家各自思想的变化。相对容易确信的是,无论谢林,还是尼采,他们皆看重单纯基于意志的世界与自我关系问题,并同时划定了这种意志理论基础的批判性边界:谢林关注一种意求实现一切、认知一切的意志,以及该意志悲剧性的、自身矛盾的困境,与此相对,他也设立了一种泰然让之的意志(ein gelassener Wille);尼采从一开始便与那种肯定性的、陈述全体的语义相决裂,比如叔本华的“一种”意志发生(ein Willensgeschehen)这类一元论的表述。伴随着海德格尔将《自由论文》整体解读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谢林意志理论的转变也清晰可见。谢林动用雅可比早已命名的“虚无主义”⑤Johann Gottlieb Fichte,Briefwechsel 1796-1799,in:Gesamtausgab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d.III/3,Stuttgart-Bad Cannstatt,1972,S.245.的自身矛盾来批判费希特,海德格尔将谢林的“关于恶的形而上学”追溯到其批判费希特的对立面。众所周知,雅可比在由他自己开启并推动的关于信仰与认知的争论中,特别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关于无神论的争论中指责了费希特的先验主体性。雅可比认为,先验主体性由于消解了一切非主体,其同时也贬抑、耗尽、消解了自身,变得无所支撑、没有根基。总体来说,去除一切非主体以返回自身主体性的辩证关系,这作为雅可比基本观点的极端化形态乃是谢林“关于恶的形而上学”的核心。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表明的,不应像雅可比反对费希特那样将此用以反对谢林的“关于恶的形而上学”。
一种自身传统成为问题的哲学如何铸就新的概念和思想形态,以结束,或用海德格尔的表达,克服近代主体性哲学基于意志理论的糟糕的自我建构,对此,谢林作为范例可供学习。海德格尔曾将“关于恶的形而上学”简单归为尼采“创造力意志”的前史,然而,对谢林的学习要比海德格尔所确信的做法更为复杂。与此相应,海德格尔从他的角度所推动的观念论思想形态的转变也值得专门研究,该研究有必要试探的是: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他自己的评价相反,其恰恰是受到观念论的推动而获得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动机,尽管他并非观念论的效仿者。这个转变意义深远,不是因为海德格尔的谢林解读对谢林著作的批判性研究有所贡献,而是因为这个转变切中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内在发展的整体,并且非常典范地显示出他对哲学的理解的变化。
根据海德格尔,谢林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最终刻画了“西方的命运”,而且该命运在谢林的“关于恶的形而上学”中才真正首次得到完整的表达。在谢林讨论恶的理论视野中已经可以看到现代自我与世界关系的颠倒与异化。对此,海德格尔用自己的话语表述为从“存在的间隙”到“分裂”①Heidegger,Schelling: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GA42),S.248.的转变。从此,他也获得了根本的触动,继而展开了存在历史之思(seinsgeschichtliches Denken)。
海德格尔与谢林在思想上的内在亲缘关系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当前现实,即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的批判性分析;其二,依据启蒙辩证法的尺度从理性到神话的过渡;其三,否定第一开端,以及第二开端的必然性;其四,作为根本转变的绽出(Ekstase)、转折(Kehre)与新的开端;其五,与现代固化于意志相对的泰然让之(Gelassenheit)。谢林在《自由论文》中阐述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这个基本主题尤其是两位哲学家共同的核心。正因如此,通过意志来解释一切存在者的决断标明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体,这一点也属于两位哲学家的核心问题;相应地,一种针对意志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也属其中,这种存在论将存在理解为被泰然让之者,并在谢林对“存在的不可预思”(Unvordenklichkeit des Seins)②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I,J.G.Cotta’scher Verlag,1861,S.268.的讨论中到达顶峰。谢林所思考的这种存在论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先声,其直接促使海德格尔在与哲学史上的“存在的遗忘”的对抗中去追问存在自身。海德格尔将存在的遗忘理解为存在自身的基本特性,因此,存在自身始终被规定为隐匿、遮蔽以及与存在者的差异,并且被思考为本源与开端。这样的本源与开端不会轻易到场,其必定是在对第二开端的重复不断的争执中才会被争得。
本文旨在揭示,海德格尔与谢林的哲学对话决定性地触发了他晚期哲学的核心思想,尤其转折与泰然让之等问题,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之思,在更早的探讨基础存在论的《存在与时间》中,其已初现端倪。
二、意志形而上学与泰然让之
费希特在其早期哲学中就已谈及意志的优先权这个范畴。从《自由论文》开始,谢林便试图将这种意志的优先权描述为现代人的世界关系自我异化的征兆。基于意愿行为的持续性及其无限制、无条件的绝对性对人的解释导致了世界关系的异化。唯有在“渴求”(Sucht)与“畏惧”(Angst)的现象中,这种不断加深的异化关系才能被遇见。“在恶中是耗尽自身、始终消解自身的矛盾,其力求创造,恰恰凭借毁灭创造的纽带,由于成为一切存在的自傲,其坠入无所存在”③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S.390.。依照谢林的意志理论,从此自身矛盾的历史诊断中可以反观到泰然让之的悖论形态④此处泰然让之的“悖论”并非逻辑的悖论,亦非恶性的、需要被克服的悖论,而是其自身发生的本性——译者注。,即“无所意求的意志”(Wille,der nichts will)⑤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I,S.235.。这样的意志时刻校正着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之合理,并保持开启。
近代以意志为基础的主体性乃是一种自我的遗忘,用海德格尔的话语,即存在的遗忘。此遗忘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性地贯穿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整体,该整体由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关于恶的形而上学”标明,尽管这或许会与他自己的预期相悖。在此,将存在与意志(包括其隐含的侵占、支配、控制等意志命令)等同会导致诸多后果,因为该等同将西方哲学在深层次上建构为一种致力于认知与科学的结构。对于海德格尔这位从《自由论文》中获得思想启示的哲学家而言,存在与意志的等同必定不会陌生。当然,从谢林那里,他也接纳了另一条可能的道路,即克服“意志”这个范畴。谢林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他对意志中心的批判:
首先,谢林批判了早期观念论的主体性理论,尤其针对费希特。此批判从1800年开始,直到1809年的《自由论文》臻于完善。谢林在其早期阶段也偏向于从主体性理论的范畴中引导出人与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关系,但依照他的批判,这恰恰是一种异化与颠倒的结构,该结构表现出对现实社会整体的侵占、支配与控制等基本特征;由康德首次强调,由费希特推向极致的实践的优先权将一切对人而言的陌生的他者归为己有,继而给定特有的印记,并以此最终消解自身。这种植根于对一切存在者的有意侵占,同时又在此过程中消解自身的具有自身矛盾的主体性,谢林将其描述为费希特早期哲学的基本矛盾,并在“恶”这个标题之下思考了自我颠倒与自我超越,思考了本源的遗忘与普罗米修斯赋予自己的权力。基于这样的哲学历史的背景,谢林意识到,该矛盾正是主体性自身的基本特性。海德格尔通过将《自由论文》规定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让人首次经受到这个矛盾结构整体的激烈及其否定的尖锐。
其次,与对理性的一般讨论相区分,谢林转向了神话的叙述,该转向早已从“新神话”这个概念开始,直至1811年到1815年的“世界时代哲学”(Weltalter-Philosophie)完成了方法与内容两个方面的建构。在此,与主体的控制结构密切相关的“理性”被导向其自身抑制在神话中的开端,并且被揭示为认知的意志或认知的控制。经由谢林,在柯罗诺斯(Chronos)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象征着时间与永恒,具有“第一因”之意——译者注。的历史中被记录下来的洞见获得了一种新的当前(现实)批判(Gegenwartskritik)的功用,即不但以一种与现代理性相反的形式(神话的形式)将理性控制现实的命令公布出来,而且也为理性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以揭露其破坏性的发生过程。此破坏性的灾难就在于绝对化意志的自我毁灭与不可能性。因此,谢林说道:“这里有此矛盾:人所意求的东西被其意志活动毁灭”②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IX,J.G.Cotta’scher Verlag,1861,S.235.。
第三,也是首要的,即与意志形而上学相对的泰然让之,这要求一种对哲学的全新的理解。谢林对泰然让之的探讨从1809年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这个标明了观念论的基本原则与最高结果的论题开始,经过“世界时代哲学”,一直到1821年的“埃尔朗根演讲”(Erlanger Vorlesungen)所阐述的将存在理解为被泰然让之者的历史存在论。基于“一个”意志来解释所有存在者的决断刻画了近代哲学的特性。谢林从泰然让之的理论出发批判了这一点,并返回到现代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本源且不可预思(unvordenklich)的开端。海德格尔所谈的泰然让之尽管与谢林有所差异,但也是从高度思辨的历史之思(Geschichtsdenken)中直接继承而来。此历史之思在根本上追问西方“思”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ndnis)的开端。
从图宾根的学生时代,经1800年耶拿时期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直到埃尔朗根时期的哲学,与费希特的争论始终贯穿着谢林思想的内在发展,同时,这也是他探讨泰然让之的起始点。“自由的自身困境”(Selbstverstrickung der Freiheit)③Schelling,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Erlanger Vorlesung WS 1820/21,H.Bouvier u.Co.Verlag,1969,S.42.是谢林指责费希特的“自我”本质结构的关键。“埃尔朗根演讲”将永恒自由(die ewige Freiheit)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权看作是在整体上否定人类获得认知的基本,在此,自由的自身困境是个潜在的主题。此永恒自由的不可被支配、被操作,及其在思想上的不可预思以不同的形式在谢林的著作中延伸,尤其表现在“自我的绽出”(Ekstase des Ich)这个概念中。在埃尔朗根阶段,谢林把“自我的绽出”刻画为早期观念论的基本概念“理智直观”的后继形态;在晚期哲学中,谢林进一步将其规定为“理性的绽出”(Ekstaseder Vernunft)④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I,S.162.。无论是对“出离自身”的思索,抑或是通过“与自身相区分”对“过去”的重新确立,还是“不去认知的认知”(nichtwissendes Wissen),这些皆是谢林对一种否定性的当前(现实)诊断的回应。谢林的思想道路最终在其晚期哲学的“存在的不可预思”(Unvordenklichkeitdes Seins)那里到达顶点。思想总已从此不可预思的存在而来,而且必定从此开启。对此存在,思想只能保持接受,只能泰然让之。
海德格尔在与哲学史上“存在的遗忘”的对抗中追问存在自身,并思考了泰然让之。基于此,对谢林的泰然让之理论的重构将获得清晰的轮廓。鉴于存在自身区分于存在者的遮蔽、隐匿与差异,存在的遗忘有其必然性,也正因如此,现实批判才得以获得其事实性和历史性的根据。当海德格尔早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将真理理解为无蔽(Unverborgenheit)之时,朝向遮蔽(Verbergung)的倾向已经明确地显露出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倾向被把握为历史性的、自行生成(sich ereignen)的隐匿,而且,只有一种不同于认知意志,不似认知侵占存在者的思想行为才能揭示这种隐匿的倾向。海德格尔称此思想为“沉思”(Besinnung),即“对万物的泰然让之”①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1910-1976(GA16),Vittorio Klostermann,2000,S.529.。
三、西方思想的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
如果依照谢林的开端理论来探讨泰然让之,那么在海德格尔那里,对隐匿与泰然让之的相互关系的思考也将获得另外一种视角。在谢林的观念论中,第一开端与第二开端这个基本点已经十分典范地刻画出泰然让之的理论形态:第一开端,即被规定为本源的开端,只能(以形变的方式,以恶的现象)在自身的否定中显现出来,而另一种开端,即第二开端的可能性恰恰表明第一开端是颠倒了的开端。
海德格尔对开端问题的思考直接承接于谢林讨论开端的历史。在《自由论文》以及1811年到1815年对“世界时代哲学”的筹划中,谢林力图描述世界之开端的病史,即一种异化的历史,因为,世界已然从开端异化,世界处于异化的历史时代。这一点直至1821年的埃尔朗根演讲都是指引性的。在此演讲中,谢林也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现代的诊断,即自我异化、自我消解的现代。他并不只是事后注明了这种完全否定性的消解。在世界的开端中,在一种“先于世界”的“过去”中,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消解的可能。
谢林在其自由哲学与世界时代哲学中阐述的诸多“开端”形态最终显示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源初事态(Urszenen)。此源初事态是就其本源性来谈的。一切依于该事态,并从中被给予的人类经验的具体情形仍然由此本源性的、源初的事态维系,而非相反。源初事态并不单一,但有贯穿所有情形的唯一主题。对此,谢林采用不同的事例来说明,比如他为了说明恶的辩证关系而将“成为一切存在的自傲”指责为人类无所限制的自我迷误的狂妄,甚至将其描述为现代的原罪;比如他把“存在”或者生命的整体看作厄运;又比如他曾将奥维德神话中水仙的镜像隐喻②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其代表作《变形记》中讲述了那喀索斯(Narcissus)恋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求之不得而最终死去,并化作水仙的爱情悲剧。西语中的水仙由此得名。——译者注。解读为一次失败的自我关系。这些事例击中要害且意味深远,共同呈现出源初事态的基本主题:人类自由在其自身最初发生之时,在“初现”(in statu nascendi)之时的自我迷误。在埃尔朗根演讲中,谢林总结道:“对于开端之所是,必定有此厄运;没有不自欺自害的开端”③Schelling,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Erlanger Vorlesung WS 1820/21,S.136.。这读起来就像是对他在自由哲学与世界时代哲学中所阐述的诸多开端形态的批注,而且,这些开端形态皆隐含消极的意义。
上述追问无疑是有基本条件的。从第一开端而来的如此存在且不以其他形态存在的经验世界不仅是被追问的对象,其从本源结构而来正是问题本身。如果这个根本的、本源性的追问是被给定的经验世界的基本,或者更准确地讲,此世界与该追问共同发生、同等本源,那么“追问”从一开始就使得现实成为一种自由决断的对象,而且正因如此也使得现实并非特定,当然也充满危险、更为棘手。对此,谢林通过存在之应当把被给定的经验世界“虚化”(Virtualisierung)。此存在之应当从自由的层面来思考便会非常明确,但在宗教学的意义上就过于夸大。谢林及其优秀的后继者,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与保罗·悌利希(Paul Tillich)等,他们皆要求基于对自由的呼求来重新规定现实这个概念,但这仍然难以实现,难能企及。经验世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了开端与从开端而来的存在者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在此,开端自身始终保持隐匿、遮蔽,并以此方式发挥其效用,任何往返重复以侵占或支配开端的企图皆是行不通的。“一个开端只有不停地成为开端,其作为真正永恒的开端才是可能的。同时,开端也不知其自身为开端。以任何一种方式真正去开启、去开端的决断必定不会被意识到,而且必定不能被唤回,因为,开端的开启乃是使得后撤、被撤回的过程。如果谁在决断之时仍还保留重回光明、重做决断的余地,那么必定不能开启一个开端”①Schelling,Die Weltalter.Fragmente.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C.H.Beck,1946,S.184.。
谢林思考的开端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因为不可预思,开端只能在其自身迷误中,继而在形态转变以及“恶”的现象中出场;与此开端同样本源,并且共同被创立的另一开端,即第二开端的可能性使之作为第一开端而表现为一种颠倒了的开端。正如前文所述,海德格尔继承了这种在自身遮蔽中发挥效用的“本源发生”(Ursprungsgeschehen),同时也描绘出从此本源发生而来的隐匿与呈现之间相互对立的辩证关系。在隐匿与呈现的相互对立之中,遮蔽是根本性的,而且遮蔽也并非是一个单纯与认知相对的要素,遮蔽绝不会在认知中显示出来,因为遮蔽构造着、承载着认知。与此相应,谢林在1809年的另外两个概念,源初根据或无根据(Ur-oder Ungrund)命名了一种不再从意志活动来理解的让允(Zulassen)。此让允更是远离了那种有意求的侵占与控制。海德格尔力图守护潜藏在认知中的某种“不可支配性”。这种守护的动力与谢林的晚期哲学密切相关。谢林在其晚期哲学中基于对否定哲学与实定哲学(negative und positive Philosophie)的二分最终展开了隐匿与遮蔽这个中心。鉴于不可预思、不可被支配的存在,谢林指出,任何认知,若是其植根于单纯可被思考之物的可能性形态之中,那么必定有其自身的边界与先行的“现实”相对。
在海德格尔与谢林那里,尽管对存在的追问以不同方式被提出,但皆是对本源的追问。谢林在《自由论文》中谈及的是“根据”、“实存之物”以及“无根据”;海德格尔谈及的是存在自身区分于存在者的存在论差异,此差异维系着其不可通约的组成要素之间的张力,以免各个要素皆被置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之中,或者某个要素独立成为这样的整体。“在此,没有最初者和最终者,因为一切彼此互为前提,没有完全其他之物,也没有完全依于他者存在之物。上帝在自身之中有其实存的内在根据,就此而言,这一根据先行于他的实存;但上帝同时又是根据的先行者,因为,如果上帝没有实际实存着,那么根据,哪怕作为根据,也不可能存在”②Schelling,Smmtliche Werke VII,S.358.。在回到“最终者”或“最初者”,并能够将其认定为建基的基础之前,谢林所述的“创立之发生”(Stiftungsgeschehen)处于上帝及其根据之间不可缓解的张力之中:上帝实存着,其实存的根据始终往复不断地重新先行于他的实存。这种张力的关系直接承接于《自由论文》,尤其在世界时代哲学那里被进一步规定为开端及其历史之间的无尽的争执,历史成为一个不可分解的矛盾分化之地,本源地被意求的东西以及在此意志活动的意求中被颠倒、伪装、误用的东西在这里争执着。正如前文已被引用的语句:“这里有此矛盾:人所意求的东西被其意志活动毁灭”。
在思索世界时代的过程中,对于这种深植于意志活动中的自身矛盾,谢林已经阐明了其辩证关系,并以此将世界的内在时间描述为“过渡”(U..bergang)的时间。在此过渡中,先于世界的“过去”以隐匿与遮蔽的形态在“现实”中显示出其完全的“在场”。百余年后,海德格尔在对时间的分析中将存在的历史整体刻画为从第一开端到另一开端的过渡的历史。但目前,这个过渡也只是临时性或准备性地被思考过而已。在此,值得继续追问的是:海德格尔是否仍然依循谢林所揭示的历史哲学的结构。
海德格尔将“存在历史之思”记为“开端性的”、“过渡性的”、“下沉性的”思想。西方思想的“另一开端”从最初古希腊的开端而来就已获得了“另一”开端的规定性。对此,海德格尔写道:“思想的另一开端之所以被称为另一开端,不是因为此开端只是与迄今为止任意一种哲学的开端形态相区分的另一种,而是因为相应于唯一的第一开端,另一开端必定是唯一的另一开端”③Heidegger,Beitraege zur Philosophie.Vom Ereignis(GA65),Vittorio Klostermann,1989,S.4.。
从德国观念论那里,海德格尔首先接受的是谢林的遗产。他确立了存在自身,并同时确定了存在自身的本源性的力量,正如他坐实了“唯一的第一开端”所预示着的遮蔽与隐匿。这表现出海德格尔在根本上从谢林而来的连续性。从三十年代开始,他以第一开端、第二开端、另一开端等形态规定了思想的张力或宿命(Fügung),尽管此思想只是历史性的,而非像谢林所探讨的那样,是“绝对”自身的形成或显现。在此,可以继续追问:海德格尔是否比谢林自己更加谢林地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入口,以恢复“本源之思”(Ursprungsdenken)。
与其他观念论者相比,谢林的哲学是海德格尔思想得以发生的直接的前史。这一点自从海德格尔的学生,瓦尔特·舒尔茨的《德国观念论在谢林晚期哲学中的完成》出版之后就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令人惊奇的是,直至今天的谢林研究仍然贯穿着对海德格尔解读《自由论文》的阐释,但与此同时,对于观念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继承尚且欠缺一个彻底的、完整的、系统性的研究。海德格尔是第一位从谢林的“意志活动乃源初存在”这个基本论题中看到西方思想在现代的完成形态的哲学家,并因此将谢林看作虚无主义的开路者。尽管海德格尔对谢林仍有诸多批判,但他仍然在西方思想的完成中觉察到一种“关于恶的形而上学”的核心,并将其吸收到他对所处时代的思想诊断中。海德格尔的论题是不断增长的存在的遗忘,这作为不断生长的自我与世界关系异化的历史在技术化的现代愈加恶化、极端化。此存在的遗忘正是海德格尔所谈的无所依靠、最终自我消解的虚无主义的另一面。谢林首次哲学地宣告了这样的虚无主义,直到尼采的“创造力意志”,该虚无主义最终到达顶点。
人们或许会质疑,海德格尔本人不会承认谢林的意志形而上学中具有潜在的现代批判,而且海德格尔对谢林《自由论文》的诸多指责也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展开。但这并不能否定两位哲学家的思想在事实上的内在亲缘关系,其甚至显示出海德格尔误解谢林的创造性,即促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深思哲学历史的整体。这两位哲学家深层的一致性表现在,他们的现代批判皆面临这样的挑战:确立西方形而上学被遗忘了的本源,并且与近代以来的认知的优先权相对,凭借一种更加深入的“本源之思”以获得哲学的基本情态,比如对世界及其对象的开敞状态(Offenheit)与泰然让之,比如绽出之际的倾献(Hingabe)与“转折”,比如古希腊惊讶于存在的激情。这些皆为确立“本源”的情态,在世界时代哲学中,谢林将其归于“回忆”这个传统且有力的标题下。百余年后,海德格尔承接于此(尽管有明显的差异),在形而上学走向完成的阶段,面临“存在的遗弃”(Seinsverlassenheit)而在解读尼采的著作中劝告读者:“有时,通往开端之处的唯一可行的进路会是忆入历史的回忆”①Heidegger,Nietzsche II(GA6.2),Vittorio Klostermann,1976,S.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