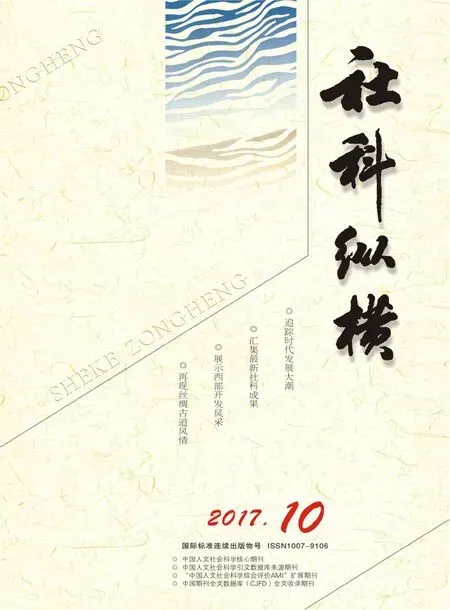秦文化精神述略
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秦文化精神述略
李世忠
(咸阳师范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秦文化从其精神风貌言,体现为一种开放、外向、进取型特色,而非内向、闭锁与守成;从审美情趣言表现出唯“大”是求特色;从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上看,秦文化又展现出它注重实际、崇尚“力量”、“以能为先”的理性务实精神。
秦文化开放唯大是求尚力
自上世纪30年代初,前国立北平研究院陕西考古队苏秉琦先生等经过实地勘察研究,第一次把秦文化从周文化、汉文化中单独区分出来后[1](P12),学界关于秦文化问题所论已多。本文试从文献、考古资料及各种文化因素组合关系入手,对秦人在秦部族、秦国与秦王朝三大时期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及制度、社会关系、伦理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观念形态的成果进行简要分析,以探讨秦文化在精神风貌、审美情趣、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体现的精神特质。
一
秦人崛起的历史是一部壮气淋漓的奋斗史。故秦文化从其精神风貌言,首先体现为一种开放、外向、进取型特色,而非内向、闭锁与守成。
《史记》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2](P173)学者认为这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情形,由此知秦文化的开端至少也可追溯到该时期。翻检相关史料知,秦人立国之前不少人物都以善于打拼、积极进取而闻名。如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的大业之子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2](P137),舜赐其姓嬴氏;殷商末期大费后人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他的儿子蜚廉和孙子恶来,一个善走一个有力,都成为纣王重臣而“助纣为虐”。《尸子》载:武王伐纣时,“亲射恶来之口”[3](P82)。《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4](P155)《荀子·成相》云:“世之灾,嫉贤能,飞廉知政任恶来”[5](P458),《吕氏春秋·当染》亦云:“殷纣染于崇侯、恶来”。[6](P49)又如,蜚廉五代孙造父,西周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在周缪王西巡狩遇徐偃王作乱的危难情势下,造父以“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而立下奇功,终得缪王赐之赵城的奖赏,“造父族由此为赵氏”[2](P175)。另外,周孝王时居犬丘的非子及西周末的秦襄公,也都是秦人崛起中出现的名人。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以其功而“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2](P177);秦襄公在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于郦山下的危急关头,率兵救周,“战甚力,有功,……以兵送周平王”,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2](179)
善于打拼,反映了秦文化开放、外向型特色。打拼所呈现出的冒险进取精神,为秦文化外向型特征抹上了沉雄悲壮色彩,这一点在秦人对外战争及不断迁都举动中也能看得十分清楚。如秦缪公三十六年伐晋曾以“渡河焚船”方式大败晋人。[2](P193)秦人先祖自非子时本居犬丘,后非子被赐以秦邑而居秦,至秦襄公迁都于汧,秦文公居西垂宫四年左右,又于“汧渭之会”营建都邑,秦宁公后迁都平阳,秦德公时迁雍城。雍城作为秦国都城经营三百二十余年后,秦灵公和秦献公又分别把籍姑和栎阳作为临时性都邑,最后直至秦孝公徙都咸阳。历史上,一个王朝的都城迁徙,多因政权内部危机或外族入侵而致,然秦人屡次迁都,原因却都是出于军事上的开疆拓土与政治上经略东方考虑。伴随着秦国都城的步步向东迁徙,秦人东征西讨,不断“收周馀民”,最终完成了对东方、乃至全国的统一。
秦文化开放、外向特色,还体现在不断对外来文化吸收、包容和消化上。《毛诗序》评价《诗经·秦风》《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杜预解释:“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7](P408)这说明秦人确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胸怀。实际上,秦人立国后其实力壮大过程,也正是不断学习、吸收外来文化过程,此亦为考古资料所证明。如据已出土秦公钟、秦公鎛、秦公盤及秦公1号大墓的石磬等铭文知,秦人对西周文字就有过一个学习、接受过程。王国维深入研究秦人的文字使用后指出:“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秦处宗周故地,其文字自当多仍周旧。”[8](P254-255)
除文字外,秦在工业冶炼、建筑、绘画、音乐、丧葬制度,乃至民间风习等诸多方面,都对周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采取一种兼容并蓄态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2](P239)。这是建筑方面对他地文化的借鉴;《礼记·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9](P247),《庄子·杂篇·天下》亦云:“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10](P289),据出土秦国春秋至战国早期墓葬资料可知,秦士、大夫级墓均有棺有椁,有的甚至用两层套棺,显示出其学习周文化、中原文化的痕迹十分明显。另外,秦人屈肢葬仪、洞室墓等,有学者指出其最初应是西戎文化传统。秦人茧形壶、蒜头壶等器物形态,这些过去被视为秦文化的典型物品,论者指出不是秦人原有传统文化,而是受巴蜀文化影响结果。李学勤、尚志儒等就认为秦人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是继承了西周传统。从现已发掘的春秋早期秦墓中青铜器几乎清一色西周风格看,此论极有道理。
秦地音乐,也大量吸收外来音乐文化。李斯《谏逐客书》对此有生动说明:“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11](P275)《史记·秦本纪》载秦民腊日风习来源时说:“(惠文君)十二年,初腊。”张守节《正义》云:“十二月,腊日也。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故云初腊。猎禽兽以岁终祭先祖,因立此日也。”[2](P206-207)这是岁时节日对他地文化的效法,可见秦文化吸纳、包融外来文化是全方位的。
二
秦文化从其审美情趣言,又体现出唯“大”是求的鲜明特色。
秦文化崇尚“大”,以大为美,表现于其文化精神的方方面面。前述秦国历代国君开疆拓土的努力及其统一天下,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宏大”追求在文化心理上的反映。秦文化追求“宏大”,还可从以下方面来看。
首先,秦人建筑、苑囿规模远远超过商周时代的一般情况,体现了唯“大”是求审美观。以雍城为例,该城作为秦国在其整体国力上升阶段所悉心经营的都城之一,宏大价值观之追求体现的极为鲜明。考古发掘表明,雍城占地约11平方公里,其规模甚至比周天子所居之王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座正方形的都城,外有城墙、护城壕,城内有大型宫殿建筑群及平民居住区,整体建筑群设计极有气魄。
又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宫室营建方面的一些举措,亦体现出对“大”的崇尚。《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阿房宫及关中宫殿规模说:“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於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2](P256)《三辅黄图》说秦始皇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桥广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间,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桥之南北堤,激立石柱。咸阳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12](P22-25)秦亡后,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由此知秦人营建宫室规模之大,确乎罕有其匹。论者言及秦始皇陵建筑风格时也指出其“整个场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雄伟壮观。从这些陶俑的身材状貌直到建筑材料(秦砖)的厚大坚实,也无不显示出那难以想像的宏大气魄。这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13](P79)这种上具天象、下形地经、牢笼百代、追求宏伟的气质,正是秦文化唯“大”是求精神气质的典型反映。
秦人的“宏大”审美观,也体现在文化艺术上。以秦乐为例,其不仅音域宽广韵律流畅,且声调高亢昂扬宏伟,极易宣泄情绪抒发胸怀,整体风格上显示出一种自由奔放、粗野宏大的风貌。这种乐曲曾广泛流行于秦地民间,时至今日,从秦腔表演艺术中,还能领略到这种“秦之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的野性魅力。
唯“大”是求的审美观,在精神气质上,也塑造了秦文化不事文饰、古朴厚重的特色。宽大厚重的秦砖,粗野奔放的秦声,质木简古的秦文,笨重朴拙的秦鼎,丘积如山的秦陵,威武沉郁的秦俑,以及荒草丛生、鸟飞兽走、四望无边的秦苑等等,无不展现出这种朴拙浑厚的特色。《荀子·强国》篇载,应侯问孙卿子入秦何见,孙卿子回答“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5](P303)依孙卿子所见,秦国无论官民,皆呈现古朴风貌。甚至到清末,秦人这种古朴风貌犹存。如清人所撰《永寿县志》录《皇华载笔》语云:“乾、永古朴,无杂戏。每逢佳辰令节,酒醋肴核,各从其便,家人父子,各尽其欢。惟元宵社火扮演故事,船灯、竹马、采茶、秧歌,近今始有,古昔无之。”[14]
古朴厚重的文化气质作用于人,便形成了秦人文化人格上重信守义的特色。尽管东方诸侯国一直有人在攻击秦无道,不讲信义,但《国语·晋语》中所载一则秦晋间借粮的故事,却将秦人朴拙而守义的文化人格显露无遗。该书载,晋国岁饥,乞粮于秦,秦穆公以道义之名说服臣下,答应其请求。但后来秦国岁饥需要粮食时,晋惠公却没有卖粮给秦[15](P308),道义之高下判若云泥。《左传·定公四年》载楚国申包胥如秦乞师救楚,秦也是激于道义出兵[16](P1630-1631),秦人所赋明志诗《无衣》直到今天读来,其同仇敌忾、誓与敌人共死的情怀仍呼之欲出。这种为友朋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品格,本质上也是根植于秦文化深处的,与秦人唯“大”是求审美观相关的古朴人格精神的体现。
秦文化宏大审美观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是,与秦人所处北方自然环境有关。秦人所生息繁衍的秦陇大地,山河交错,道路纵横,地形复杂,加之为生存而不断开疆拓土的努力,使得秦人的目光、胸怀很容易超越一山一水的狭小空间而投向外部世界。二是,秦人长期以来与西北戎狄杂处而争衡,剽悍的游牧民族世代逐水草迁徙、时至时去的生活方式,给以农业立国的秦人带来重大威胁。这样的情况下,秦人既要“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又要时时“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17](P2),如此生活格局,自然使他们观照世界的胸怀、审美眼光无法逼仄、狭深。
三
从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看,秦文化又展现出它注重实际、崇尚“力量”、“以能为先”的理性务实精神。
秦人从其先祖中潏开始就“在西戎,保西垂”。后来,在其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又长期面临戎狄裹挟,生存空间狭小,外在生存环境酷烈,安全缺乏保障的困难。故其文化价值观中形成注重实际、崇尚“力量”的哲学并不难理解。直至立都咸阳、走向强盛之后,秦国所面临的仍然是东方各诸侯国“合纵抗秦”尴尬局面。《史记》载:“(昭襄王)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共攻秦,至盐氏而还。”[2](P210)“(秦始皇)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2](P224)这些只是东方各诸侯国联合抗秦的小插曲。凭借强大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始皇,在做皇帝之初,“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同时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2](P239)。这样的举措正说明了他对秦王朝统治长治久安的担心。做皇帝的十几年里,秦始皇不辞鞍马劳顿行千万里路,五次巡视天下,到处刻石纪功以宣示“力量”,竟至在他的陵墓周围,也布下了由强兵悍马组成的庞大地下军阵。其崇尚“力量”的背后,实包蕴着他对反叛自己“力量”的恐惧心理。秦王朝统治维持了仅仅十五年,即在农民起义及六国旧贵族的联合反抗声中土崩瓦解,可见,反对它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所以说,秦文化的“尚武”与崇尚“力量”的哲学,完全与秦人早期的生存处境有关。崇尚“力量”的文化精神竟至演变为秦始皇统一天下过程中的杀人如麻及秦帝国建立后的暴虐统治,此正与秦人由弱趋强过程中长期的军事斗争生活有关,与秦人在军事化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权力高度集中、忽视社会文化建设,不愿对复杂问题投入时间、精力去分析研究而宁愿以武力快速解决的文化心理有关。柳诒徵认为,秦民开化甚迟,“盖虽居周岐、丰之地,而其文教实别为一系统,与周之故俗不相衔接。”“秦既一统,始尚文教。”[18](P354-355)这是很有道理的。《史记·秦本纪》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2](P209)这是发生在秦国国君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秦人不可思议的对“力量”的崇尚。
在崇尚“力量”的文化精神支配下,秦的人才观、国君选择理念均遵循“以能为先”标准。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德能并重,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有显著区别。
以秦国人才使用为例,论者多注意到凡在秦国建立功勋人物,多非秦地所出,由此得出秦文化具有“拿来”他地人力资源的精神。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秦国“拿来”他地人力资源,而是他地人才甘愿“移民”秦国并为之效力。这和秦文化重视人的外在能力,看重使用“能人”,并不遗余力为“能人”提供用武之地大有关系。那些投奔秦国、适秦国所需的人才,往往在一个时期内都发挥了自己的才干。李斯《谏逐客书》就曾指出秦国的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皆以客之功”而成就功业,并对秦国注重人的能力与使用效果而不问出身的人才观作了总结。[11](P275)
这种体现出一定功利色彩的“以能为先”、理性务实的人才选用标准,甚至也影响到了宗法制在秦国的推行。宗法制度源于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内容。在周文化中,嫡长子继承制执行得相当严格。《史记》载西周先世从后稷到文王昌,历十五世,父死子及,无一例外;西周从武王姬发到幽王湟历十二世,其中仅有第八代孝王辟方继承了其侄子懿王的天子之位是唯一例外(第九代天子仍为懿王之子继承)。从东周的情况来看,周平王到末代天子东周君,历二十五世,除第八代匡王班、第十三代悼王猛、第十七代哀王去疾、十八代思王叔、二十代烈王喜等五位外,其他均为父死子及。而秦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则执行得相当松散,从第一代国君秦襄公到秦缪公九位国君中,仅二人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国君之位,其他多为兄终弟及,甚至还发生过祖孙相及的情况。至秦统一天下后,三代继承人,其中有两位(二世胡亥与公子婴)则是错位继承。
由此知宗法制在秦国确实执行得不很严格。这种情况的产生,仍然是秦文化崇尚“力量”、“以能为先”的文化精神的反映。一种文化意识当它从官方到民间代代相传之时,其生命力往往是惊人的。秦地甚至直至近代,亦有民间俗语云:“天高皇帝远,拳头便是知县官。”[19]可见秦人崇尚“力量”的文化观念根植之深厚。
[1]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文物出版社,1984.
[2][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3]李守奎,李轶.尸子译注[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1960.
[5][清]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
[6]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清]王国维.观堂集林(一)[M].中华书局,1959.
[9][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清]王先谦.庄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
[1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中华书局,2005.
[13]李泽厚.美的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永寿县志[M].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15]徐元诰.国语集解[M].中华书局,2002.
[16][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7]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M].中华书局,1992.
[18]柳诒徴.中国文化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9]同官县志[M].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K233
A
1007-9106(2017)10-0115-04
*本文为咸阳发展研究院资助项目成果(编号:16XFY004)。
李世忠,博士,咸阳师范学院关中古代陵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