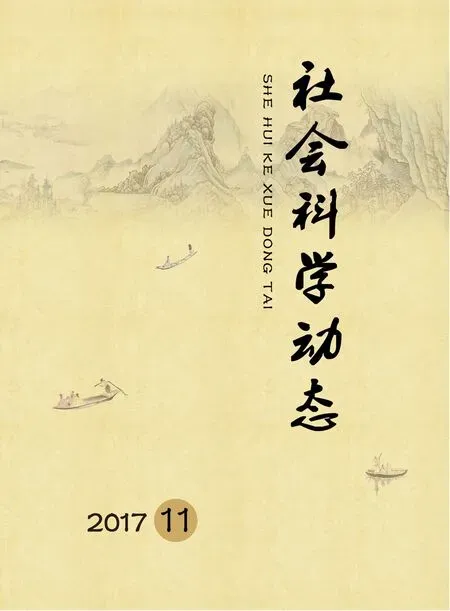论共同体道德债务
罗明星
学术新论
论共同体道德债务
罗明星
共同体道德债务是真实却被忽略了的伦理事实,表征着共同体之间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非平衡关系,其有效性取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承认共识”的达成。共同体道德债务可能因伤害产生,因奉献生成,亦可能是纯粹基于身份的先在规定,分别形成伤害性共同体道德债务、奉献性共同体道德债务和先在性共同体道德债务。物性偿债与灵性偿债是共同体道德债务清偿的基本方式,生命偿债则是共同体道德债务清偿的最高形式。道德债务之于共同体并非绝对的熵性存在,作为实存的伦理资源,道德债务可以实现共同体的精神集成,促成共同体的有机团结,还可以在共同体内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为共同体发展集聚精神动力,而道德债务的加载、清偿、转移或遗忘,则可以成为共同体治理的价值工具。
共同体;道德债务;清偿
共同体道德债务既是影响共同体自身稳定的道德存在,也是关涉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道德因素。正视共同体道德债务并通过道德债务清偿实现共同体和谐,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
一、共同体道德债务的本质
“债”从“人”从“责”,自古以来,债就是人之责。在一般意义上,债务是一个法律概念,即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在主体之间产生的一方享有请示他方为或不为特定行为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法律债务不同,道德债务是主体之间基于道义的非平衡状态而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按照普适性的道德公义,主体之间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应该对等,但是,在实际的道德生活中,当主体获得的道德权利大于其履行的道德义务时,“道德权利”减除“道德义务”的余额,客观上就成为了“道德债务”。与法律债务一样,道德债务亦有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区分,享有权利的一方为道德债权人,履行义务的一方为道德债务人。
共同体道德债务是以共同体作为主体的道德债务,反映着共同体之间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非平衡关系。但是,由于共同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共同体道德债务客观上亦是共同体中每一个体的道德债务。就像卢梭理解的那样,共同体是一个契约性存在,拥有“统一的自我意识,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①。因此,从共同体中获得其社会本质的个体,理所当然地成为共同体道德债务的实际承担者。作为依赖于共同体生存的偶然性存在,个体的唯一选择是,与共同体成员一道以最具效益的方式清偿道德债务,让共同体尽快从道德债务中解放出来,自己亦在共同体的解放之中获得自我解放。
道德债务虽然广泛存在,但只有达到特定阈值的道德债务,即达到了作为共同体的债权人或债务人利益计较值的道德债务,才能引起共同体的集体性关注,成为共同体必须面对和清偿的道德债务。按理说,只要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产生了不平衡,道德债务就必然产生,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不平衡尽管无处不在,可道德债务却并没有如影随形。根本原因在于,绝大多数道德债务并没有触及共同体的“利益计较值”,并不足以引起共同体的道德注意,由于客观的道德债务没有得到共同体的主观确认,道德债务也就成为事实上的无效债务。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共同体本身有层级的区分,而且同一层级共同体由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差异性,其利益计较值的“阈值”也可能尽然不同。这就意味着,同样性质与同等程度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不平衡,在A共同体视域中可能成为有效道德债务,在B共同体视域中则可能成为无效道德债务。
共同体道德债务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承认共识”的达成。事实上,共同体道德债务并不一定同时得到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共同确认,由于道德债务的认知不协调,道德债务有时很难在共同体之间形成共识。其中的情形很复杂。一种情况是,道德债务之债务人否定道德债务的存在,但债权人却坚信这一债务的存在。比如,土耳其人对亚美利亚人因为屠杀引申出的道德债务,亚美利亚人作为债权人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土耳其人作为债务人却拒绝承认。由于对道德债务的承认可能损害共同体的伦理形象,尤其可能引申出重大的经济利益赔偿,作为债务人的共同体可能以牺牲良心的方式拒绝道德债务的存在。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债务人承认道德债务,债权人却对道德债务加以否认。典型的例证是,在中国,子女共同体习惯将自己置于道德债务的债务人角色,因为中国父母从子女出生即予以绝对性付出,子女会将对父母的亏欠理解为不可推卸的道德债务。但作为债权人的父母共同体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将对子女的绝对付出理解为自己的天然职责,并不承认父母与子女之间的道德债务关系。没有承认共识的共同体道德债务只能是单边债务,但单边债务也是债务,道德债务不被承认并不影响道德债务的客观真实,只可能导致道德债务的无法清偿或清偿无效。道德债务的共识达成,需要理性的智慧表达与行动的效果检验,也是一门让共同体走向和谐的道德艺术。
必须说明的是,共同体道德债务与共同体经济债务、政治债务及法律债务往往是一体性存在,通常,经济债务、政治债务及法律债务的清偿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债务的清偿过程。但不管是怎样的债务,唯有蕴含其间的道德债务得到清偿,共同体债务问题的终极解决才成为可能。
二、共同体道德债务的形成
1.由伤害而产生
伤害是共同体道德债务形成的最常见原因。纵观人类历史,国家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家族共同体等在历史的时空转换中兴衰存亡,其中,伤害性共同体冲突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悲剧性记忆。虽然共同体冲突有政治上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在道德世界里,任何一种冲突都是人类的精神苦难,尤其是暴力性的共同体冲突,总是不得不用鲜血亵渎生命的神圣,用生命的毁灭铸就通往拯救生命的希望之路。然而,即便是共同体冲突中的胜利者,在庆祝胜利的狂欢过后,当其冷静下来面对冲突中的失败者时,复位的人性亦会让自己对冲突中的暴力行为进行反思,对失败者的歉疚感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蔓延至整个共同体。可以说,每一次共同体冲突都是一次共同体道德债务的生成。历史上,因为伤害导致的道德债务不胜枚举,如:基督教徒对犹太教徒的迫害,形成了基督共同体对犹太共同体的道德债务;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暴力驱逐,形成了白人共同体对印第安人共同体的道德债务。因伤害形成的共同体道德债务具有显然的恶性特征,它不仅造成共同体之间的心理疏远与情感间离,而且可能为共同体发展设置难以逾越的伦理障碍,尤其在道德债务不能有效清偿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恶变为共同体的历史顽疾,成为共同体之间无休止血腥复仇的道德口实。就像当今世界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袭击总是有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借口,似乎总想依靠恐怖袭击实现某种道德债务清偿,但恐怖主义实施的结果却客观上导致了新的道德债务的形成。
2.因奉献而生成
共同体道德债务亦可能因奉献而生成。奉献是人的类本质的善性表达,是共同体之间爱的传递。奉献过程中利益输出与输入的不平衡,亦可能导致共同体道德债务的产生。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奉献性道德债务也许产生于氏族和部落之中。摩尔根在考察古希腊人氏族继承规则时发现,财产“由同宗亲属按照与死者的亲属次序继承,死者的子女是死者最亲的同宗亲属,由此便获得了独占继承权”②。当子女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获得独占继承权时,客观上是在享有来自父母的权利。按照已经形成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观念,子女必须给予父母相同的权利,才能达致内心世界的道德平衡。然而,父母在子女有能力履行足够的道德义务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子女作为共同体,父母作为共同体,未尽的道德义务客观上成为子女共同体的道德债务。尼采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将先辈的奉献性道德债务理解为一种永恒:“人们相信种族只有通过祖先的牺牲和功绩才得以延续,因此人们应当用牺牲和功绩来回报祖先。人们甚至进而承认这样一种仍然在持续增长的债务,这就是祖先们在其强大精神的继续存在中,从未停止从自己方面向他们的种族提供新的优惠和作出新的预支。”③尼采的意思是,即便先辈已经离世,但其牺牲精神仍然给后辈以恩惠,后辈将永远沉浸在先辈的奉献性道德债务之中。当然,奉献性道德债务并不仅仅存在于血缘共同体之间,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等其他共同体之间也普遍存在。与伤害性道德债务相反,奉献性道德债务是一种善性道德债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彼此将对方视作目的性存在,道德债务的发生与道德债务的偿还,处处体现着人性的高贵与德性的光辉。
3.基于身份规定而形成
人类历史上还存在一种基于身份规定而非真实权利与义务关系而形成的道德债务,我们可以称之为先在性道德债务。宗教性道德债务即属于此种债务。教徒从出生的那一刻起,道德债务就作为神圣性义务与生命相伴,并伴随生命的流逝走向永恒。以基督教为例,按照《圣经》的解释,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善恶树上的果实而对上帝犯有原罪,因此,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原罪。原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债务,是上帝给人赋予灵与肉的同时附加在人身上的精神桎梏。宗教性道德债务具有绝对性,是宗教共同体中所有信徒的神圣义务,除非走出这一共同体,否则没有人可以享受道德债务的豁免权。所以,宗教生活中的人,没有人能够摆脱宗教性道德债务的重负,相反,背负宗教性道德债务恰恰是教徒获得世俗社会主体资格的前提,只有当教徒将道德债务理解为神圣之爱并心甘情愿地偿还债务时,才能在真实世界里获得虚幻的自由。宗教性道德债务本质上是虚假债务,因为我们只能真实确认作为债务人的教徒的主体资格,但不能确证债权人神(如基督教里的上帝)的主体资格的真实性,更不能提供人与神之间道德债务形成的本体论证明。可以说,先在性的宗教道德债务其实是宗教教义在世俗世界的伦理呈现:“吠陀和基督教教义最终都归结为同样奇怪的举措:首先将全部道德准则描述成债务,但是接下来,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却表明道德准则并不能真的被简化成债务。”④
在世俗世界里,先在性的共同体道德债务亦广泛存在。其一,先在性道德债务可能因血缘身份而天然形成。如道教“承负”理论就认为,“如果上辈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就给后代留下道德债务”。⑤古代印度债法规定:“儿子、孙子在父亲、祖父远走他乡、去世或受不治之症折磨时,有义务为之履行债务。”⑥这就是说,先辈的道德债务天然就是晚辈的道德债务,基于血缘身份承继先辈道德债务是个体担当共同体责任的基本形式。其二,先在性道德债务可能因政治身份而天然生成。强势共同体为了实现对弱势共同体的控制,故意制造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平衡,将非真实的道德债务强加给弱势共同体,从而为强势共同体的利益实现提供道德支持。例如,专制政体下的统治集团,总是习惯于将被统治者的平凡生活标榜为自己的“恩赐”,是统治者的特别付出成就了被统治者的幸福生活,因此,被统治者应该对统治者表示感激。在日本,偿还天皇的道德债务就曾经是国民的天然义务:“个人对天皇所欠之债,一个人必须以无限感激的心态来接受这种恩情债。日本人觉得当个人为自己生于这个国家,得以如此生活,得到大大小小的关怀感到高兴的时候,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切都是天皇的恩惠。”⑦其实,日本国民的生活永远由自己创造,是自己的劳动铸就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日本天皇与日本国民之间并不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道德关系。所以,基于政治身份形成的先在性道德债务本质上也是虚假性债务,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的主观联想。
三、共同体道德债务的偿还
有债必还,这是底线性的道德规定,是具有普世通约性的伦理常识。所以,共同体道德债务一旦形成,清偿道德债务就成为共同体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因为从“债务中摆脱出来是人赖以从整体上获得解放的前提”⑧。
1.物性偿债
物性偿债即债务人通过现实物质利益对债权人进行道德债务清偿。尽管道德债务可能因各种不同原因而产生,但通过物质利益偿还道德债务永远是行之有效的偿债方式。由于道德债务本质上是利益关系的伦理呈现,所以,以物性方式对债权人进行利益补偿,成为共同体道德债务偿还的普遍选择。比如,作为对犹太人道德债务的偿还,德国从1952年签署关于赔偿受迫害犹太人的《卢森堡条约》开始,总共支付的赔偿已逾700亿欧元。⑨德国人的物性偿债,给曾经遭受伤害的犹太人以极大的精神抚慰。以物质利益偿还共同体道德债务的优点在于,物质利益是可以计量的,人们可以通过物质利益数量的多少,窥见债务人偿还道德债务的诚意,从而形成关于道德债务偿还事实的清晰认知。同时,由于物质利益可以给债权人带来真实性的生活改良,增加直观性的愉悦体验,客观上淡化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道德积怨,有利于促进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道德和解。但是,道德债务毕竟并不是纯粹的物性债务,因此,物质利益补偿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到底多少物质利益才能对道德债务进行对等补偿,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道德悬问。
2.灵性偿债
正是由于物性偿债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体道德债务的完全清偿,因此,灵性偿债即债务人通过源于心灵的精神性付出对债权人进行道德债务清偿,成为共同体道德债务偿还的重要形式。
集体性道歉与集体性感恩是共同体道德债务灵性偿还的基本方式。
集体性道歉主要适用于伤害性共同体道德债务的灵性偿还。道歉是以语言为载体将道德的自我谴责呈现于受害者的道德行动。集体性道歉的伦理意义在于,作为道德债务人的共同体以在场的方式平等面对债权人,表达了对债权人作为共同体的人格尊重;向债权人坦诚自己的道德过错,将历史伤害的道德责任归咎于自身,还原了曾经可能被扭曲的道德正义;以公开的话语方式昭示共同体的道德歉意,将债权人的共同体利益置于债务人共同体形象的优先位置,显示了债务人的责任担当。正是通过集体性道歉,债权人感知到债务人的内心真诚,进而形成对债务人的情感性包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道德债务在善性的道德谅解之中得以质性递减,共同体道德债务由此得到偿还。作为集体性道歉的经典案例,德国总理的庄严一跪成为灵性偿债的范本。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⑩。下跪谢罪是德国人对犹太人表达歉意的极端举动,但正是这一跪,化解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沉积在心底的愤怒,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共同体道德债务得到了实质性清偿。
集体性感恩主要适用于奉献性共同体道德债务的灵性偿还。感恩即债务人通过心灵的虔诚付出铭记债权人的道德恩惠并表达对债权人的道德敬意。由于奉献性道德债务源于债权人的无私付出,集体性感恩就成为债务人偿还道德债务的必然选择。债务人通过对债权人内心的道德尊重或言行的道德赞美,亦或通过“物化良心”的直观展示,回报债权人曾经给予共同体的道德恩惠。正如亚当·斯密所说:“那个把温和、仁慈和文雅等各种美德同伟大、庄重和大方等各种美德结合起来的人,肯定是我们最为热爱和最为钦佩的自然而又合宜的对象”。⑪在债务人的心目中,债权人就是“最为热爱和最为钦佩的自然而又合宜的对象”。当债务人用虔诚与敬意表达对债权人的尊重时,债权人藉此获得道德回报,曾经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不平衡得以修正,共同体道德债务得以偿还。所以,感恩与其说是人类道德高贵的伦理表征,毋宁说是人类平衡道德债务以寻求内心安宁的伦理法器。无论怎样解读,感恩成为滋润共同体关系的德性力量都是没有疑义的。
3.生命偿债
生命偿债是以生命作为利益载体偿还道德债务,是共同体道德债务清偿的最高形式。生命偿债可以有两种解读,其一是以直接的生命牺牲一次性偿还共同体道德债务,其二是以终生的生命付出持续性偿还共同体道德债务。无论是哪一种形式,以生命偿还道德债务均具有绝对性,体现出道德的极致境界。尼采就清楚地表述了生命的偿债功能,他说:债务人“在自己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下,根据契约把自己尚且‘占有’的其他东西,还能支配的物品抵押给债权人,比如,他的身体,他的妻子,他的自由,或者他的生命”。⑫共同体成员作为债务人主动以奉献生命的方式偿还道德债务乃是道德上的至善之举,但是共同体成员作为债务人被迫以牺牲生命的方式偿还道德债务则是道德上的极恶之行。以生命偿还道德债务的生活实景集中体现在宗教领域。例如,对基督徒而言,出生就意味着用生命清偿共同体道德债务的开始。耶和华对犯有原罪的亚当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直到你归了土”。⑬亚当的命运客观上成为基督共同体中每一个教徒的命运。在上帝面前,教徒事实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存在主体,就像詹姆士·里德所说:“我们放弃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放弃我们从前的生活,努力去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人,努力去做上帝要求我们做的事。”⑭基督教以剥夺自由的方式赋予信徒以信仰自由,让教徒在对上帝的绝对信仰中丧失理性的判断力,让生命的延续过程成为对上帝的偿债过程。
四、共同体道德债务的价值
由于道德债务需要共同体通过利益付出进行清偿,而利益付出可能消解共同体的有机活性,因此,人们习惯于将道德债务理解为共同体的负面资产,共同体中的个体甚至可能“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背负道德债务的囚徒”⑮。然而,道德债务之于共同体却并非绝对的熵性存在,作为实存的伦理资源,道德债务对维系共同体生存与发展亦具有积极的效用价值。
1.共同体凝聚
马克思曾经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⑯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个体生命的栖身之处并让个人获得自由,关键在于共同体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实体。道德债务,恰好是增加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粘合剂。
道德债务之于共同体的凝聚价值在于,可以促进共同体“集体意识”的形成,并通过集体意识实现共同体的精神集成。集体意识是“一般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⑰,共同体道德债务一经形成,偿还道德债务就成为共同体成员当然的道德责任,亦在精神世界汇聚成共同体的集体意识。道德债务通过对共同体成员利益共生关系的实质性同构,达成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共识,基于道德债务的共同记忆让共同体成员在情感上保持着历时性的密切关系,避免了离散性的利益纷扰对共同体精神世界的空间挤压,客观上为“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创建预制了条件。共同体成员清楚地知道,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体,既然自己不能舍弃也不能独立清偿共同体道德债务,就必须与共同体成员实现精神上的有机团结,通过寻求共同体的道德解放获得个人自由。正是在践行这一理念的过程中,共同体的凝聚力得以形成。况且,个体对共同体道德债务承担责任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共同体表达道德忠诚的过程,就像迈克尔·桑德尔所说:“改正我的国家的过往错误,是一种确定我忠诚于它的方式。”⑱当个体通过偿还道德债务对共同体表达忠诚时,忠诚自然也就成为共同体凝聚力的价值源泉。
2.共同体动力
共同体的发展来自于个体力量的张扬。卢梭曾经说:人类“只能把他们分散在个体的力量联合成一种强大到足以抵抗任何阻力的力量,并且利用一个唯一的动机调动它,从而使它能够协调一致地行动”⑲。对共同体而言,道德债务显然具有“唯一的动机”的协调功能,足以作为精神动力促成共同体一致行动。
道德债务带来的集体性内疚,是其作为共同体动力的原始依据。众所周知,内疚本身是一种蕴涵痛苦与自责的情绪体验,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己道德过失实施的精神上的自我惩罚。集体性内疚实质上是共同体对自身负性社会形象的接纳与反思,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体,只要“把自己归于施害群体,承认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过去的所作所为威胁到了群体认同,并且内群体应为之负责,就会体验到群体内疚”⑳。集体性内疚可以催生共同体良心的自我发现,为共同体的偿债行动加注精神动力。同时,集体性内疚强化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纽带关系,促进了共同体意识的发育与生长,激励个体将自己的情感、意志与勇力一并奉献给共同体,从而在共同体内部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为共同体发展集聚最大化的主体动力。必须说明的是,道德债务作为共同体精神动力并不绝然是善性的存在,尼采曾经警告:债务可能“让债权人得到一种愉悦来作为还债和弥补——这种愉悦就是债权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无权的人行使权威,就是‘从作恶中得到享乐’的纵欲放荡,就是在强暴中获得的满足”。㉑所以,让道德债务展示其善性的动力意义,避免恶性的动力展示,是共同体不可规避的道德责任。
3.共同体治理
通过制造道德债务,为共同体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几乎是所有当权者的政治本能。比如,美国总统布什对伊拉克宣战时发表演讲:“我们怀着对伊拉克以及他们伟大人民和宗教信仰的尊敬来到伊拉克。我们在伊拉克没有任何的企图,我们只是想摧毁一个威胁,使伊拉克人民恢复对国家的控制。”布什的演讲将美国出兵伊拉克包装成解放伊拉克人民的高尚之举,本质上是给伊拉克人民加载道德债务,赋予美国以道德债权人资格,从而为美国政府的战争选择加注合法性,同时为战后美国利益的实现准备道德资本。在这里,道德债务成为处理国家共同体关系的价值工具。
通过偿还道德债务,正面树立共同体道德形象,为共同体治理提供道义支撑,亦是实施共同体治理的经常性选择。类似的道德案例随处可见,比如,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19世纪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道歉,2008年美国众议院代表美国人民为非洲裔美国人及其祖先所受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法的折磨而道歉,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代表政府向澳土著族群上百年来蒙受的苦难道歉。这些道歉实质上是通过历史道德债务的灵性偿还,以政府名义树立国家道德形象,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共同体的有效治理。
通过道德债务的“转移”与“遗忘”,将道德债务作为共同体治理的技术性工具,也是司空见惯的为政之道。“转移”是共同体作为债务人将道德债务移位于他主体的伦理行为,道德债务的转移本质上可以实现对痛苦道德记忆的选择性遮蔽,从而获得内心世界的道德救赎。比如,将大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而不是人为因素,本质上是将对饥饿死亡者的道德债务从执政共同体转移至非主体的自然,可以实现执政共同体道德责任的卸载与集体性愧疚感的缓释,并有利于共同体道德形象的保全。“遗忘”则是对共同体道德债务进行有意识的信息封存,人为制造共同体的集体失忆,试图让道德债务在时间的流逝中走向消亡,进而实现共同体精神世界的道德救赎。尽管“转移”与“遗忘”最多只是实现共同体“免罪认知”的技术性手段,只能暂时规避共同体道德债务,并不能实现道德债务的真正清偿,但客观上可以维护共同体的价值稳定,为共同体治理提供精神性保护。
注释:
①⑲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戴光年译,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5页。
②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7页。
③⑫㉑ [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善恶之彼岸》,谢地坤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43、43页。
④ [美]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孙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⑤ 陈霞:《道教公平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平》,《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1期。
⑥ 李启欣:《外国法制史研究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⑦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田伟华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
⑧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王晓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⑨ 李超:《对历史负责的又一证明》,《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
⑩ 《勃兰特那“惊世一跪”》,《新华网》2013年5月14日。
⑪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84页。
⑬ 《旧约·创世纪》第3章《违背主命》。
⑭ [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页。
⑮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上),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3页。
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⑰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⑱ [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页。
⑳ 石伟、闫现洋、刘杰:《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群体内疚》,《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2期。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16JJD710016)
B82
A
(2017)11-0005-06
罗明星,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