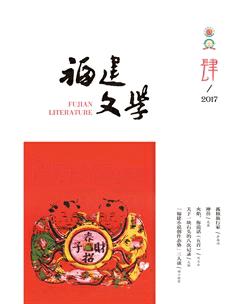杀青
安庆
一
哥接到大学通知书那天,父亲格外兴奋。那天中午,父亲让我们和他喝酒,往常他都是自己独饮,这一次,他在我和哥面前都放了酒盅,甚至忘记了我还是个孩子。他和哥碰杯,夸哥哥争气,对我说你哥就是你的榜样,你要努力,再过几年你也领一张这样的通知书回来。
一瓶酒喝完,父亲带着我们到祖坟上去,说祖坟上冒烟了得去见见祖宗。村外长满了青色的庄稼,只有路是黄色的,冒着白气。玉米很高了,棒子上甩着红缨,我们蹚在地里,扒拉着玉米稞,玉米尖上的花粉落到脖子里,痒痒的。父亲没有喝高,很快带我们找到了祖坟,他踩断坟前的几棵玉米,让我们磕头,絮絮叨叨地说哥考上了大学,是祖上的阴德。磕过头后,父亲的酒劲到底上来了,在爷爷奶奶的坟前长跪不起。我们只得把父亲架回家。
接下来,父亲奔走在为哥哥凑学费的路上。每天出门前,父亲微笑地看着哥哥,脚步轻盈地跨过门槛,仰着头,好像自信会凯旋。那几天,他刮了脸,头剃得光光的。我们特别喜欢出门的父亲,相信他一定会带着惊喜回来。他手里握着草帽,走出大门,仰头看一下天,在太阳晒到了他光亮而干燥的头皮时,拍打几下草帽戴到头上。庄稼叶耷拉着,小鸟的叫声又干又哑,草蒙上厚厚的土尘。走到村外的十字路口,父亲会有短暂的迷茫,他回忆着家里的亲戚,哪一个亲戚的面目在他的记忆里格外清晰,他就会朝着哪一个方向走。
父亲身上有一个小本本,所有的亲戚都被他记挂起来,每天出门前父亲在一些亲戚的名字上标着记号。村里人都知道父亲去干什么,他们看着父亲先是步行,后赶着驴车,一次次走在外出的路上,一副骄傲的神态。只有在出了村后,这个骄傲的债主才露出沮丧,暴露出他借债的本相。
所有能想到、有可能的亲戚父亲都去了一趟,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收获不太理想。我们家的老亲戚在奶奶生病时曾经帮助过我们,欠人家的钱还没有还清,对这样的亲戚父亲要不是绕过去,要不就是碰了钉子。那段时间,父亲不断地赶着毛驴车奔走在十里八村的路上,常常在黄昏的时候疲惫地回来,母亲腰里系着粗布围裙站在门口等待着父亲。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客人,一匹瘦马驾着一辆架子车,车子停稳,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瘦瘦的女人,细瘦的手朝前挥着,像扒在水里,身子轻得听不到她的脚步声,赶车人是一个大个子。母亲出来,女人叫着母亲姑姑,两个人拉着手,很亲热。母亲喊着我和哥哥,让我们叫姐、姐夫。姐姐走后,母亲告诉我们那是我们一个叔伯舅家的女儿,我们的一个老姐姐,叔伯舅舅早已经不在了,那个表哥也就是表姐的哥哥我们见过,每次去舅舅家几乎都能见到,大高个儿,气喘,还喜欢吸烟。就是这个不常见到的表姐,那天给我们送来了两百块钱,说是听我们表哥说的。她拉着哥哥看,说你这孩子真有出息,好争气,考个好学校不容易。那两百块钱是从她的一个衣兜里掏出来的,小手绢卷着,一层层地展开,里边是叠好的钱,大都是一些零票。老姐姐递给母亲,让母亲数数。母亲接下了,没有数,换了一个小手绢包好,说等手头宽裕了还给你们。姐说,你不要搁心上,就算支持孩子了。母亲说,这钱迟早得还的,都不容易。那钱到底是还了还是没还我不知道。午飯后,姐姐和姐夫要走,我们去门口送他们,母亲一直站在门口,直到看不见了马车的影子。
父亲又开始去河滩里掘沙子,算着该攒够多少钱,让哥哥的路上宽裕。他每天赶着驴车,车上带着萝头和筛子。父亲又干起了老本行。父亲掘过沙子,可那时候的沙子多,现在的沙子越来越少了,河都掘空了,一镐下去碰着的都是石头,镐尖在石头上迸火,一颗颗小石子迸出老远。父亲还想像以前那样,一点一点地攒够哥哥上学的钱。天正热的时候,父亲起得很早,赶早上的天凉快。掘出的沙子要先用萝头担出来,再装到车上。河滩上的沙越来越少了,父亲一把镐,一把铁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掘,试探着一处又一处的沙子,像河滩上的勘探工,有时一天也掘不出一车沙子。掘出的沙子先拉到家里,在门口攒着,隔几天父亲用驴车往镇里或县城里送一趟,等在县城门口的黑木桥头,把沙子卖掉。我也跟着父亲和哥哥去掘沙子。整个河滩十分苍凉,一股细流在河道的一侧流淌,一阵风旋起灰黄的沙尘,鹅卵石叮叮当当作响。更多的时候我扶着筛子,任父亲和哥哥将掘出的沙子一锹一锹地掀到筛子上。我们家的黑驴孤独地站在河岸边,闲极无聊了叫几声,远处是京广老铁路线,不时地会看见火车“哐啷哐啷”地穿过。
父亲在后来的一天,看到了那个大牛场,他是去一个亲戚家回来看见牛场的。他很远就闻见了牛粪的味道,牛的叫声穿过院子,半空中飘着细丝样的牛毛。牛场大门口的广告抓住了父亲,他牵着驴,在夕阳里看清了广告上的意思:牛场要收青稞了,就是那些七八分成熟的玉米稞,青贮起来喂牛。他咂着嘴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一遍,意思越来越清楚了。他仰着头,开始合算着我们家的八亩玉米有多少斤重,能卖出多少钱。他扒拉着一根根指头,每一根指头像算盘上的珠子。父亲揉了揉胸口,天无绝人之路啊!他拍了拍驴脖子,说你等着,我再去问问,得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了。父亲朝大门里走,被看大门的拦住,他说,我想问问收青稞的事,就是你们说的什么青,青……门岗说,青贮,每年都收很多,存起来喂牛,青贮的青稞有营养,牛吃了长得快,对牛的口味。父亲说,好,你说得太好了,我们怎么不知道呢?门岗说,你是哪儿的?父亲说,老塘南街!门岗说,广告可能没贴到你们那个地方,你要想卖你得抓紧。父亲说,是是是,我想我想,能不能拿一张广告回去?我得让老婆看看,不然她不相信,卖青稞也不是一件小事。门岗也是个热心肠,说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找找。门岗去了房间,可他出来时对父亲说他没有找到,他这儿没有了,他说你再等等,我去办公室里给你找一张,有小一点的广告你可以拿回去!父亲说,要不,我就把这张撕下来吧?父亲指指他刚看过的广告,风吹动着,广告翘起了一个角儿。门岗说,你等等,我找找再说,往牛场里边去。父亲看到门岗的腿有些拐。门岗很长时间才出来。夕阳落到了最低处,地面上一层细黄,牛粪味不断地刮出来。门岗说,管广告的那个人回家了。父亲说,那让我撕下来吧,老兄,我得带个证据回家,不然老婆会不相信,我没法做通她的工作,也不是她不相信,那么多玉米弄倒了卖不出去谁也不会放心。门岗说,你想好了吗?真要卖青稞?你们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父亲叹了一口气,说,玉米长得好歹且不说了,儿子要上大学,得多筹学费,孩子他让俺家争脸了。
父亲将哥哥考上大学,他一路借钱的事对门岗说了。门岗犹豫着,和他一样将一只手摁在驴身上,同情地看着父亲,说,揭去吧,明天我再要一张贴上。父亲很感激地去揭墙上的广告,从边角一点一点地去撕,黏得结实的地方,父亲用指尖抠,门岗帮忙,两个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揭下,一张广告还是变成了几瓣。父亲说,我到家再打糨子把它黏到一块儿。
二
父亲和母亲去了地里,父亲不说话,紧紧地握住一穗玉米。玉米已经六七分成熟了,可父亲算过几次账,不能等,等不起,秋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收了玉米,还要等晒干了将玉米脱了粒才能卖出去。他和母亲商量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每亩少收入三分之一没问题,可不卖青怎么办呢?开学的时间是不能改变的,通知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父亲又朝里边走走,玉米地像一座小森林,棒子长得越来越粗了,麻雀呼啦啦从玉米上飞过。父亲抓住了一颗玉米棒,合算着是不是掰开,他想看看玉米粒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他看看母亲,母亲手里也摸着一颗玉米棒。父亲知道母亲心疼,可不卖青又怎么办呢?父亲拍了拍眼前的玉米,这棵玉米上长了两穗棒子,下边的棒子比上边的小,父亲下了决心掰开下边的那个棒子。玉米衣有三层。最外边的一层硬,厚,青色;剥开了第一层,第二层露了出来,第二层的玉米衣发黄,淡黄,比第一层薄,玉米衣上沾着黏黏的一层东西,颜色和黏度像淡淡的奶汁;剥了第二层玉米衣,玉米粒已经凸现出来了,像女人拱着内衣的小乳头,父亲犹豫了一下,又继续剥下去,这一层像薄纱,奶黄色,像绑在床上的蚊帐,颜色又明又亮,却更潮湿,更黏更沾手。最后一层玉米衣剥开,看见了嫩嫩的排列整齐的玉米粒儿,灌着奶气,一颗颗晶莹透明,玉米粒中间的小缨儿一根根像细细的发丝,玉米芯儿的尖头嫩嫩的,青涩中露着玉白。父亲心疼了,有些愧疚,觉得伤害了玉米,自己的想法不地道,对一地的好玉米不公平,它们长得这么好,没有亏负自己,自己却要提前将它们宰割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把那剥开的玉米衣再一层层覆好,不知道能不能裹严实,影响不影响它的生长。父亲这样想着就动手了,把掀开的玉米衣往嫩白的玉米穗上裹,裹得很细致,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裹,小心翼翼,尽量恢复原来的样子。母亲在几棵玉米的间隙里看着父亲,她从没见过父亲这样小心的模样,蹑手蹑脚,又慈祥又爱怜。父亲按顺序,把三层玉米衣一层一层、一点又一点地裹严了,覆好了,那穗玉米在父亲粗壮的手里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比剥开时多费了很长的时间。父亲不放心,弯下腰,在地里找到一种长藤的草,用几根草藤在玉米棒上又系上了几道,这才离开了那棵玉米。
穿过玉米地,他们走到地的那头。身前是浑浑汤汤的一条卫河,雨水季,河水多,成群的麻雀飞过河床,比麻雀飞得低的是各种颜色的蜻蜓,还有小燕子,斜着飞。一只白色的水鸟,从河这边飞到对岸,落在草地上。麻雀叫,水鸟不叫,在我的记忆里没有听见过水鸟的叫声,它们只在河床上慢慢地飞,像沉默的河神。河滩上的草长得野,野花从草里钻出来,河滩湿漉漉的,河边的树不说话,仿佛累了。远处一座桥静静的,偶尔走过几个行人。两个人无语,坐在河堤上,看着眼前的玉米。
三
父亲被叫到了村委会。一个老院子,几座老房,房顶上绑着大喇叭,房子和房子间的胡同堆满了沤烂的树叶,树叶上落着几根鸽子的羽毛。一只野猫在房顶上慢慢走,低声地叫。村委后边是一座庙,瓦缝里长着瓦松。
村主任看父亲进来,没有和父亲打招呼,干咳几声,捏着烟在院子里转圈儿,溅起的土和烟雾拧成一股灰绳。走了几圈,村主任把另一根烟续上,开始说话。他若不开口,父亲会让他憋死。村主任知道,这样性格的人很倔,不能和一个倔人耗下去,做工作不说话不行。时势变化,村里的事儿越来越少,公粮取消了,这个主任当得越来越没有意思。
村主任说,朱老二,听说你对恁家的玉米有想法?父亲点点头。村主任歪着脑袋,一股烟喷出来,随着是一声低咳,你说说你到底有啥想法?父亲听出了村主任在兜圈子,官大官小的都这样。父亲不想接他的腔,你算什么毬官,这样绕弯子,绕得像驴毛一样,说出的话带着驴粪味。他想看看村主任能把这个弯子兜多大,都已经在喇叭里广播了,还兜圈子。村主任把一根烟又接上,深吸了几口说,朱老二,你倒把你的想法说说呀。父亲偏偏不说,坐在院子里一把连椅上,连椅吱吱扭扭,上边的虚土被父亲的屁股震得漾起来。村主任又接着往下说,朱老二,你今天哑巴了呀?你连烟都不舍得吸,你也嗓子疼?村主任终于入了正题,朱老二,我现在郑重其事地对你说,你家的青稞不能卖!
父亲一下子弹起来。
村主任趔了一下身。
村主任继续往下说,朱老二,有些话我得给你说明白,不是我不让你卖青稞,是你种了一地好玉米,你狗日的种了一地好玉米!
父亲抬起头。父亲知道我家的玉米好,这样一地的好玉米说真心话不想当青稞卖,如果将来卖玉米,多收入一两千没问题。村主任越说越平静了,主任毕竟是主任,做工作时城府出来了。朱老二,你家的玉米就要光荣了知道吗?有一个大领导要来咱村看玉米你知道吗?村委和镇里已经决定让你家的玉米代表咱村咱镇上哩!代表啊,不容易呀,挑来挑去还是恁家的玉米好!朱老二,你是一把种地的好手哩,毛主席当年视察一块棉花地你知道吧?那块地现在还竖着一块纪念碑,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毛主席視察纪念地。不过人家是棉花你是玉米,玉米怎么样,玉米就不能竖碑了?玉米也能光荣哩。
村主任越说越激动了,村里决定的事不能变,我在喇叭里广播了。说着话下意识地看了看天上的喇叭,喷出粗粗的一股烟。村主任说,朱老二,你把头扭过来,你倒成了爷求你了,都不服我这村主任了是不是?以为我管不了恁多了是不是?可村里谁真能离开这一级政府哩?有很多事情还是村里说了算,村里还管着划宅基、管着给谁家办低保哩,还管着发放上头的救济款,还管着,管着……现在村一级政权还说了算。不然,我算个毬,连个毬毛都不算。
父亲想说你就是毬毛都不算,忍住了。村主任说,我得上对镇里负责,下对老塘负责。父亲不说话,觉得有些可笑,心里说,你负责个毬哩,年年都没给村里办过什么事,最大的本事就是在喇叭里吆喝,嗓子都吸哑了还叼着烟。
村主任又续了一支烟,对父亲说,朱老二,你不能擅自作为,镇里和村里一起定的,说了算定了干,定过的事不能变,懂吧?那天来村里看玉米,确定地块的还有镇长、副镇长,都说你家的玉米好哩。你要记住这件事,这件事就是恁家的玉米不能卖青稞!父亲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话了,村子里那么多玉米地多一块少一块又咋样?杀青稞卖是我心里的意思,我不知道亏?那玉米稞我都回家称了,再重也没有将来卖玉米值钱,这账我都算几遍了,可我不卖咋办?儿子考上了大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当官的就没有问一问?人家老塘北街出一个大学生,村里还演场电影哩。
村主任“扑哧”一声笑了,说,朱老二,你可他娘的开腔了,可你说的话比屁还臭,你儿子考上大学是好事,演场电影顶屁用。你既然知道为啥还要卖青稞?就不能多跑几家去借借,等卖了玉米再还他们?父亲扭过头,剜一眼村主任,你觉得借钱是件容易的事儿吗?我又不是村主任,有脸面,亲戚又都是穷亲戚。
村主任说,朱老二,你就不要这样对我说话了,你家的玉米稞不能卖,是因为你家的玉米长得好,而且你家玉米一割掉,整方地戳个大窟窿,咋看咋都不顺眼。这样吧,村主任又走了几圈,把烟屁股撂地上,我就自做一次主,电影的事儿不仿效北街了,争取给你家补贴两百块钱,我问问会计能不能挤出这个钱。
父亲愣了愣,可又摇摇头。父亲想了想,两百块钱和卖青稞的作用差远了,不能比。父亲一摇头村主任就恼了,朱老二,不要不识抬举,是叫你的玉米光荣,叫你朱老二光荣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叫其他几户过来做工作?他们的工作不用做,是你特殊才喊你,你果真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朱老二,好好想想,不要鸡蛋硬往石头上碰。
父亲不想和村主任说下去,转过身,朝外边走,不看村主任的脸。父亲有些伤心,听见村主任在背后喊,没回头,出大门时,使劲拽了一把大门,半扇铁门“哐当”一声响。
四
那天的磨镰声,从午后开始,一直在院子里响。父亲把所有的镰刀都找了出来,磨刀石支到了枣树下。父亲先用一块砂布擦着镰刀上的铁锈,暗红色的铁锈细粉样飞翔,又落到地上,脚下的地面染红了,镰刀上半部的黑色和月牙处的银色露出来。父亲开始蘸水,“嚓啦嚓啦”,弯着腰,镰刀在磨石上磨,放了半年的镰刀重新焕发了亮光,刀刃锋利。镰刀磨完,整齐地搁在枣树下的一块帆布上,黄昏慢慢地降临,接下来将是巨大的夜幕。母亲在厨房里烙饼,满院都是烙饼的味道。磨过镰刀,父亲坐在枣树下看天,一直都没有说话。天上的一轮月儿升起来,父亲到底说话了,独自地念叨,天阴了就好了。后来,天果然阴了,月儿看不见了,云彩在天上走动,夜色更加黑浓,父亲比较满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坐在一起,父亲又喝了两杯小酒,拿起一块烙饼对我们说,今天都好好吃,好好吃晚上干活才有力气。父亲看看放进筐子里的镰刀,说等夜静了我们出发,先下手为强,不能再等了,再等牛场里不收了青稞我们就傻眼了,青稞杀倒了谁也没有办法对我们。我和哥哥使劲地点头,使劲地吃着烙饼。父亲又让母亲把那张广告拿出来,一边端着手里的小酒一边又看一遍,嘴里念叨着,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快半夜的时候,父亲上了房顶,观察着一个村庄的动静。父亲的身边搁着我们家的小闹钟,小闹钟在夜里“咔咔”响着,我和哥哥坐在院子里看着房上的父亲。父亲从房顶上下来,挎起了装镰刀的筐,哥哥轻轻地打开街门,我们一家朝小胡同里走。村庄真是很静,刮过胡同的只有深夜的小风,透着凉气。这个晚上,我才知道我们的村庄原来那么大,有那么长的街,那么深的胡同。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村庄,走到了我们家的玉米地。杀青的战斗就要开始了,父亲把镰刀分给了我们,我们一字儿排开,玉米地黑黢黢的,一棵棵玉米在夜风中摇动。
父亲对着玉米地深鞠了一躬。父亲站到了地头,摸着一棵玉米,摸着了玉米棵上的棒子,他好像有些犹豫,一声叹息飘过我们的头顶。父亲摸住了另一棵玉米,夜色里的玉米地黑压压的。父亲还在犹豫,他把手里的镰刀递到我的手里,往后退了几步,忽然将腰弯下去,弯成了一个丝瓜,那一鞠躬让我们心里酸酸的。然后我们听见父亲说,对不起了!这个夜晚,木讷的父亲竟然变得那样缠绵。
父亲不再犹豫,在夜色里弯下腰。眼前划过了一道弧光或者贼星样的光。“咔嚓”一声,声音在寂静的田野,在田野的夜色里格外重。夜色里闪耀出几道嗖嗖的寒光。父亲使劲地咳了一声,又弯下腰,“嚓啦”,一棵玉米应声倒下,倒下的玉米沉得像一架小梁,宽大的玉米叶子带着厚重的潮气,玉米稞的落地声,像为土地叩了一个很响的头。父亲扭过身,催着我们。哥哥弯下腰,几棵玉米倒了下去。母亲却在地头癔症着,她发现地里忽然长出很多的萤火虫,萤火虫在潮气里膨胀着,越来越近越来越多,像天上的星星碎到了地里。她尖叫了一声,叫了一声朱老二。父亲抬起头,几十道光亮已一起向我们围过来,光亮被满地稠密的玉米弄得枝枝杈杈,带着寒气。父亲在一瞬间被灯光圈住了,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镰刀,锋利的镰刀刚刚杀倒几棵玉米。他握着镰,不知该不该再弯下腰,迷迷糊糊地看见了村主任的影子,听见了村主任的狂笑,朱老二,你真来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村主任在灯光的簇拥中一步步向父亲走来,向我们一家走来。父亲浑身的血液贲张,他“扑扑嚓嚓”地扒拉着玉米,把脚边的玉米疯狂地踹下去,玉米棒从玉米秆的腰里落下,镰刀在玉米地里飞舞着……整個玉米地响着父亲声嘶力竭的吼叫,狗日的村主任,我日恁祖宗,我要去告你,啥时候了,我管不了我自己的地,啥人来地里看,俺就不能卖青稞了?父亲被围得越来越近了,灯光把他的眼照花了,把他包围了。他挥起镰刀,你们不要俺活了,不让活我死给你们看……父亲举起了镰刀,朝自己的手腕上砍下去。哥哥疯狂地叫起来,爹,爹……母亲“哇”一声哭了,哥哥和母亲搂住了父亲……
我永远记着,那个夜晚,让我们的希望成了失望,让我们的憧憬成了悲伤,父亲的计划泡汤了。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父亲歇斯底里的喊叫,还记得父亲挥舞镰刀,“咔嚓嚓”玉米倒地的声音,记得那些逼近父亲逼近我们的光……父亲吐出了一口浓痰,不,父亲吐出的分明是一口血,一口浓血。父亲是被担架抬回去的,不,是直接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父亲还在吐血,父亲的喊声越来越弱,他失去了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