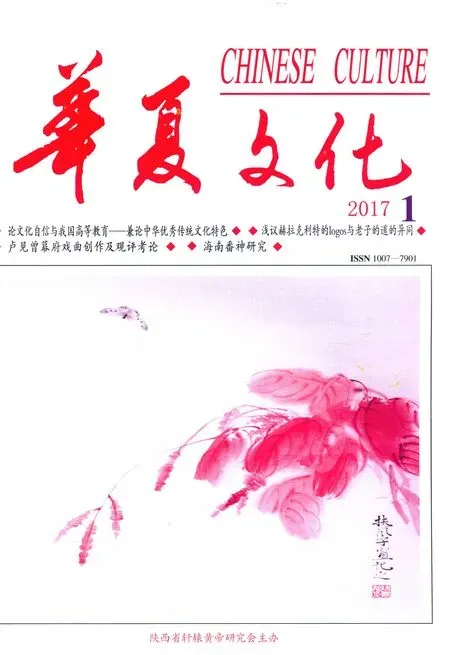古代小说研究视野的思考
□ 张 泓
古代小说研究视野的思考
□ 张 泓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分为八种类型,而将短篇小说分为两类,这在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的古代小说研究者均继承了鲁迅先生的分类法,将讲史、神魔、人情、讽刺四类长篇小说及两类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称为名著,研究工作围绕着这几部作品展开。下面将近五年来名著与非名著的研究论文作一对比,以探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视野问题。
一、研究现状
人们一般将“四大名著”、《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称为小说名著,再加上近年来异军突起的《金瓶梅》,这些作品的研究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第一方队。

?
上表是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输入小说篇名而得出的数据。另有些论文是以小说作者或作品中某人物为标题的,均忽略不计,所以真实的论文数应远远超出此数据。
从上表可知,《红楼梦》的研究论文一直遥遥领先,每年的研究论文都大致相当于其他七部小说研究论文的总和,可见《红楼梦》在古代小说研究者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三部小说的研究论文大致相当,仅次于它们的是《聊斋志异》,《金瓶梅》又稍逊于《聊斋志异》;因为题材的原因,《儒林外史》的研究论文较少,“三言二拍”垫底。
我们再把与上述八部小说题材类似,但影响稍小的作品作一分析。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醒世姻缘传》36 25 18 24 20《隋唐演义》1 3 10 7 5《三侠五义》6 8 5 2 4《封神演义》18 21 17 20 15《老残游记》20 16 19 27 21《阅微草堂笔记》27 20 27 22 15《林兰香》5 4 5 2 8《欢喜冤家》7 12 8 8 5
从此表可看出,在非名著古代小说的研究论文中,《醒世姻缘传》首屈一指,其原因除了胡适、徐志摩等名人的不断推崇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作者,即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蒲松龄创作了该书,可见名人效应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封神演义》、《老残游记》、《阅微草堂笔记》的研究论文数量大致相当,而《阅微草堂笔记》之所以被一部分研究者所重视,也在于名著效应,因为研究者往往将它与《聊斋志异》作对比。而剩余的几部小说每年的研究论文基本都是个位数。
二、原因分析
1995年,陈大康先生就提出名著研究过多,重复研究频繁,而非名著特别是文言小说研究过少;1999年郭英德先生更明确提出“悬置名著”,此后一些刊物和二次转载刊物在选稿时也确实向非名著倾斜,但直到现在,研究过度集中于名著的情况仍然没能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不能否认大部分非名著的价值确实乏善可陈。正如卡夫卡所说:“古籍经久不衰,是因为具有传承性。新的事物都不过是短暂一瞬。今日美丽绽放,明日就荒唐滑稽。那就是经典名著和普通读物的区别。”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能令人百读不厌,自有其原因,而部分古代小说则是令人不忍卒读,连提倡“悬置名著”的郭英德先生都认为:“明清时期除了几大名著以外的小说作品,不管古人多么标榜它们,也不管今人多么宠爱它们, 其中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价值,实在是无法让人恭维的。”(郭英德:《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现在学界出现了一种现象,博士论文选题大多还是在几部名著中徘徊,而硕士论文除了几部名著以外,更多的是往非名著小说中靠。原因很简单,学子们已经发现挖掘新的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希望独辟蹊径,但非名著的价值实在无法支撑一篇博士论文。非名著研究的价值不够,名著的研究则已经满坑满谷,所以现在很多学生连选题都已经成为问题。
其次,名著研究容易出成果。名著除了作品本身吸引人以外,研究论文较多,参考资料齐全,相对更容易出成果,在当前学生面临毕业压力,教师面临考核压力的情况下,没人愿意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小说中耐心寻找除名著以外的其他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小说。鲁迅先生极力推崇《儒林外史》,并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叶紫作〈丰收〉序》)把一部普通小说推崇成名著,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和鲁迅先生独一无二的话语权有关,也与他及其他著名学者的持续、耐心推荐有关,但现在很少人有这种耐心去挖掘一部伟大却没人关注的小说。当然,除了缺乏耐心、急功近利以外,也与学者的话语权有关,现在学界缺少如鲁迅先生般一言九鼎的人物。
再次,世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数千年封建文化使国人心目中习惯于把任何事物都分成三六九等,人分等级,文体分等级,小说也分等级,学者心目中往往有一个不成文的观念:非著名学者研究非著名小说,著名学者研究著名小说;非著名学者研究文本,著名学者研究版本和考证。上世纪初,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影响下,胡适先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认为只有科学才有研究价值,文学文本属于人文学科,自然就不属于科学,所以他偏重作者考证和版本研究。直到现在还有学者坚持这种观点,有学者一方面从事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又轻视文本,形成一个很明显的悖论。小说研究的重点应该在文本,研究作家生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但现在舍本逐末的现象不断发生,如近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成为研究的热点,已先后有学者提出了五十多种说法。但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考证来,考证去,最终的结果“还是兰陵笑笑生而已”。对理解文本没有帮助的考证是没有意义的。
三、对策方法
十几年前,孙逊先生就提出:“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地集中在十几部小说名著的研究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现象。”如此行为带来的一个结果势必就是重复研究,不断地炒冷饭。好一点的,将他人的观点稍微加以改头换面,加上些新的、外来的语言,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述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恶劣的则直接照抄他人的论文,用众所周知的语言讲述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如2015年,在各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即达976篇,而众所周知的是,“若没有新的、可靠的文献资料的发现,《红楼梦》研究的学术空间已比较狭小。”所以绝大部分论文势必都是在炒冷饭。
小说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陈大康先生曾说:“尽可能清楚地辨析与古代小说相关的种种史实,恰如其分地分析各作家作品,进而梳理创作的发展线索,概括其间的特点与规律,并对现今以及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借鉴。”(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除此以外,引导和提高广大读者的欣赏水平更是一个重要目的。作为名著,读者已经喜闻乐见,习以为常,即便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对“四大名著”的内容说个大概,但非名著的情况则远非如此。
笔者曾对非中文系“古代小说欣赏”选修课的学生做过一个统计,以上所列表格中篇目为调查对象,了解学生对其的熟悉程度,发现学生对名著都较为熟悉,无论对作者还是内容都能说个大概,有意思的是,学生对名著的熟悉程度刚好与名著的研究论文成正比。而对非名著,学生对《隋唐演义》、《三侠五义》、《封神演义》三书内容较为熟悉,原因是受电视的影响,对《老残游记》知道书名,但不知道内容,因中学学过部分内容,对其他书目则一无所知。
引导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学者的责任,但现在很多学生对尚且比较著名的小说都一无所知,这和学者长时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大树、不见小草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一方面很多有价值的课题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和刊物的版面都被一些重复劳动占据,难怪陈大康先生要发出警告:“若是长期地被这种感觉纠缠、困扰,那么该学科的生命也就该终结了。”(陈大康:《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中华书局2006年版)
要改变这种现象,首先,广大学者要改变研究思路,要勇于从无人问津的课题中寻找有价值的事物。尽管这样做难度很大,风险也很大,可能长期的劳动成果不被社会承认,甚至被一句“没有研究价值”简单否定,但只要能挖掘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一定会被学界和社会认可,而这种意义就比在名著上炒冷饭要重大得多。例如,陈文新先生致力于《阅微草堂笔记》研究,连续发表数篇有分量的论文,并得出结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陈文新:《〈阅微草堂笔记〉:一个经典文本和一种小说类型》,《上海师大学报》2011年第2期)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现在的《阅微草堂笔记》几乎有成为准名著之势。这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其次,刊物要做出适当的引导。学者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表,只要刊物做出引导,效果会事半功倍。近年来,一些刊物确实做了改革,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曾对该刊1980年至1995年发表的古代小说论文作过一个定量分析,在全部160篇论文中,包括《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在内的‘名著研究’,共有82篇,约占总数的51.3%。一部小说研究史,几乎就成为名著研究的组合史。”(郭英德:《悬置名著——明清小说史思辨录》)但现在这种情况有了很明显的改变,据不完整统计,2015年《文学遗产》所发表论文中和古代小说相关的有十三篇,其中涉及名著的有五篇,分别为《儒林外史》二篇,《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各一篇,所占比例明显下降。可惜的是,除了个别刊物以外,绝大部分刊物还在围着名著转圈。一旦大部分刊物都转变了观念,研究情况就会有迅速地改变。
总之,名著的研究已经满坑满谷,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课题却少有人问津,如各小说之间的关系、小说和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小说和经史子的关系、小说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小说和经济的关系、小说和旅游的关系、小说和出版的关系等;文本研究中,在非名著中挖掘有研究价值的小说更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让读者既看见树木,也看见森林。相信在刊物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古代小说的研究局面会有明显的改观。
(作者:浙江省杭州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讲师,邮编31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