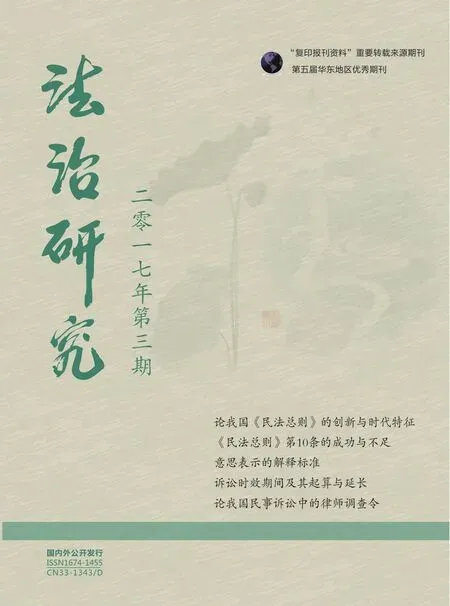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之检讨*
——以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为中心
孙思琪
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之检讨*
——以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为中心
孙思琪**
《海商法》第9条第1款、《物权法》第24条构成了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基本规则。法释[2012]8号第10条有违登记对抗主义的基本价值,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贬损我国船舶登记制度;法释[2016]5号第6条将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在“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外,同样难以贯彻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旨。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的完善应当坚持“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贯彻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价值,重新认识船舶与机动车的属性差别,审慎考量法学理论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舍。
船舶所有权 物权变动 登记 交付 法释[2012]8号 法释[2016]5号
船舶虽属动产,但由于其价值高昂、权属变动频繁,因而在法律上通常被视为特殊动产或准不动产处理。①通常认为,由于船舶、机动车、航空器等特殊动产的经济价值较高,因而世界各国都对其采取类似不动产的处理方式,要求进行登记;同时又由于实践中此类特殊动产的权属状态变化频繁,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能够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参见朱岩、高圣平、陈鑫:《中国物权法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由于船舶的这一特征,船舶物权的变动模式也不同于一般动产。我国关于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9条为基础,一般认为采取“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②郑蕾:《船舶所有权变动效力立法模式之反思》,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年第4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称《物权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法释[2012]8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法释[2016]5号”)相继出台,我国船舶所有权的变动模式也受到一定影响。本文以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基本规则为基础,分析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之缺陷,反思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一、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基本规则
凡是权利都会产生动态现象,物权也不例外。物权所产生的动态现象称为物权变动。③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就物权本身而言,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的运动状态;就物权主体而言,物权变动意味着物权的取得、设定、内容变更与丧失。究其实质,物权变动是人与人之间对于物的支配和归属关系的法律关系的变更。④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9页。关于船舶所有权变动,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则主要集中于《海商法》第9条第1款、《物权法》第24条。
(一)《海商法》第9条第1款
《海商法》第9条第1款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关于该款规定,值得分析之处有二:
第一,就该款之文义而言,并未明确规定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应属不完全法条,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规定加以解释。《海商法》通过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结合《海商法》第9条第1款和《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之规定,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应以交付为生效要件。
第二,有观点认为该款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不符合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逻辑以及强调当事人意志的立法宗旨,⑤参见李志文:《船舶所有权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以下。难以反映登记对抗主义的真义。⑥同注②。此种观点值得商榷。船舶登记行为的法律性质是行政机关依申请的行政行为。⑦王秀芬:《海运行政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要求当事人就船舶所有权变动进行登记,主要是基于船舶管理法的行政管理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下称《船舶登记条例》)第5条第1款亦有相同规定。⑧《船舶登记条例》第5条第1款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要求当事人登记船舶所有权变动并无不妥。至于当事人是否切实依据《海商法》第9条第1款的规定进行登记,并不影响私法上船舶所有权变动效果的发生。当然,对于船舶登记制度不能仅有非此即彼的片面理解。既然要求当事人对船舶所有权变动进行登记,登记自然也就成为了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之一,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至于有观点将该款理解为船舶所有权变动以登记为生效要件,⑨参见李小年、李攀:《〈物权法〉第24条规定对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影响》,载《法学》2009年第11期。该款第二句已明确规定了不进行登记的法律后果,即“不得对抗第三人”,而非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不发生效力。而且,“不得对抗第三人”本身已在逻辑上包含了船舶所有权变动已经生效的前提,能否对抗第三人决定着船舶所有权变动效力的强弱和范围,尚未生效的船舶所有权变动根本不必讨论是否能够对抗第三人。因此,此种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对法条含义的误读,不能据此反而质疑法条本身的合理性。⑩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4条第1款关于民用航空器所有权变动的规定亦有“应当……登记”的表述:“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二)《物权法》第24条
《物权法》第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相较于《海商法》第9条第1款,本条的变化有二:第一,删除了关于应当登记的表述;第二,将第三人的范围限定为善意第三人。但是,善意本是民商事活动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之义,《海商法》第9条第1款未强调善意的要求并不属于立法缺陷。《物权法》第7条也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三人基于虚假船舶登记等不诚信情形而作出的恶意主张本不能产生法律效力,因而船舶所有权变动无论登记与否,均可对抗恶意第三人。考察域外法上的相关规定,也鲜有专门突出善意要求的立法例。⑪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海商法”第9条规定:“船舶所有权之移转,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日本《商法》第687条也规定:“船舶所有权的转移,非经登记并载于船舶国籍证书,不得对抗第三人。”刘成杰译注:《日本最新商法典译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物权法》第24条的此种规定反有蛇足之嫌。
《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于《海商法》第9条第1款和《物权法》第24条均无船舶所有权变动不以交付为生效要件的例外规定,加之《物权法》第23条、第24条同属该法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二节“动产交付”,因而船舶所有权的变动仍应遵循《物权法》第23条确立的原则,即船舶所有权的变动在交付时而非登记时发生效力。⑫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因此,《物权法》对于船舶所有权变动仍采“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有观点认为《物权法》有意识地抛弃了该条关于“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而且物权变动应由《物权法》而非《合同法》规范,加之《物权法》相对于《合同法》为新法,因而不宜继续承认买卖双方当事人关于特定动产所有权自买卖合同成立时转移的约定的效力。⑬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笔者赞同此种观点。《物权法》取消动产交付约定例外的原因在于,交付例外应当限定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法律规定已可满足商业实践的需求。⑭高富平:《物权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43页。
二、法释[2012]8号第10条之检讨
法释[2012]8号第10条是关于特殊动产多重买卖履行顺序的规定,该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优先于登记。法释[2012]8号起草小组认为该条是对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要件之争的回应,即交付生效抑或登记生效。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以下。此种认识值得商榷。既有《海商法》《物权法》相关规定的存在,学界对于船舶所有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争论相对有限,争议更多在于作为生效要件的交付与作为对抗要件的登记之间的关系及其效力优劣,因而交付和登记在船舶所有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即成为评价该条规定合理与否的重点所在。由此,该条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一)违背登记对抗主义之本旨
登记对抗主义作为公示生效原则的例外,其意义在于未通过登记进行公示之前,已经发生的船舶所有权变动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可以当事人未进行登记为由否认船舶所有权变动的效果。⑯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因此,设立登记对抗主义的基本价值即在于贯彻登记的对抗效力。法释[2012]8号第10条赋予交付优于登记的效力,显然有违登记对抗主义的基本价值。
首先,设立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意即在于限制交付所产生的物权变动效果,因为单纯采用交付作为船舶所有权的变动要件不足以充分贯彻公示原则。⑰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肯定法释[2012]8号第10条的观点,通常均以交付已经产生船舶所有权变动效力为基本论据。⑱参见宋晓明、张勇健、王闯:《〈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2年第15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以下;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页以下。但是,登记对抗原本即是作为交付生效的例外而存在。如果仅以交付已经导致船舶所有权变动发生为理由,便赋予交付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优于登记的效力,即是以原则否定例外,不符合法理演绎的基本逻辑。
其次,物权优于债权应是法释[2012]8号第10条所依附的基本原则。所谓物权优于债权,是指物权对于债权具有优先效力,即同一标的物上有债权与物权并存时,物权的效力为优。⑲郑玉波:《民法物权》,黄宗荣修订,三民书局2013年版,第37页。在船舶多重买卖中,买受人之一已受领交付而未登记,但已基于交付取得船舶所有权;买受人之二虽已登记而未受领交付,仅能基于船舶买卖合同享有债权。但是,物权优于债权在民法理论和现行规范中均不无例外,“买卖不破租赁”即是物权优于债权的一项典型例外。⑳虽然人们惯以“买卖不破租赁”称之,实际上因赠与、继承、分立、合并致使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同样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即租赁物所有权变动不能击破租赁。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页。所谓买卖不破租赁,是指承租人可以对继受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受让人主张租赁权。㉑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9页。虽然学界关于租赁权的物权化多有讨论,㉒同注㉑,第336页。但其本质上仍是基于租赁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该条即是赋予了租赁权对抗所有权的效力。而且,由于船舶所有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形成的船舶所有权不具备完全的物权权能及绝对性、排他性等特征,应属不完全物权,㉓不完全物权说由日本学者我妻荣提出。我妻荣认为:“作为公示原则的适用,只要采用对抗要件制度,则不能产生完全排他性的权利变动;因此,让与人也不能成为完全的无权利人。”(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I·新订物权法》,有泉亨补丁,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国内学者论及登记对抗主义时对此亦有援引。(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评最高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10条》,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笔者赞同此说。不可与一般物权等同视之。此时如果仍然坚持此种不完全物权具有优先于已经登记的债权的效力,似乎有欠妥当。虽然有学者就此提出诘问:“交付而发生的物权变动‘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如此一来不是和债权效果没有区别了吗?”㉔王文军:《登记对抗主义的挽歌——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0条》,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年第3期。但是,不完全物权与债权的区别其实不可谓不清晰:不完全物权相较于一般物权仅欠缺登记这一对抗要件,因而一经登记便可获得完全的物权效力,而债权则自始至终不具备此种可能。
再次,由于法释[2012]8号第10条赋予了交付相当优先的效力,致使《海商法》第9条第1款、《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法释[2012]8号第10条的解释之下效力几乎不复存在。由此,本应不具备对抗善意第三人效力的未经登记的船舶所有权变动实际几近可以对抗任何人,导致登记的对抗效力有名无实,而与纯粹的交付生效主义相差无几,有违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旨。
(二)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设立登记对抗要件的目的之一在于保护价值高昂的特殊动产的交易安全,以及相应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法释[2012]8号第10条赋予交付颇为优先的效力,由于忽视了船舶及其运营的特殊性,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动产交付并不限于现实交付,还包括简易交付、指示交付、占有改定等观念交付,即交付本身并不导致实物占有的移转,仅发生观念上的占有的移转。㉕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而且,由于船舶营运的客观需要,实际占有船舶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并非船舶所有人,而可能是船长、船员以及光船租赁承租人等占有辅助人或非所有权人。尤其近年来我国船舶融资租赁行业快速发展,许多船舶的所有权属于以银行业为典型的融资租赁公司,此类船舶所有人通常并不实际占有、营运船舶。因此,实践中船舶所有权变动中“占有”与所有权人的分离致使“交付”难以具有外部识别性。㉖同注②。同时,船舶买卖中船舶的交接通常分为实际交接与法律交接两项程序。由于船价是在法律交接时收付,所有权凭证等法律文件也是在法律交接时交收,因而船舶交接以法律交接为中心,㉗杨良宜、林源民:《船舶买卖法律与实务》,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实践中船舶交付通常以买卖双方签署船舶交接书的形式作为标志。㉘郑蕾:《中国法下船舶所有权变动的交付生效要件与特约例外》,载《上海海事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例如,上海航运交易所、中国船东协会编制的《船舶买卖标准合同》第7.7条即约定:“卖方确认收到全部船款和剩余油款、未使用润滑油款等款项后,双方即签订船舶交接备忘录。船舶交接备忘录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后,该轮正式移交给买方。”《船舶登记条例》第13条也明确要求就购买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交接文件。㉙《船舶登记条例》第13条第2款规定:“就购买取得的船舶申请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应当提供下列文件:(一)购船发票或者船舶的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件;(二)原船籍港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船舶所有权登记注销证明书;(三)未进行抵押的证明文件或者抵押权人同意被抵押船舶转让他人的文件。”相较于船舶的实际交接,法律交接作为交付手段的公示效果更不理想。因此,在船舶所有权变动中赋予交付高于登记的效力,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此外,近年来船舶融资租赁业务在我国快速发展,船舶融资租赁的模式之一便是售后回租,即出租人、承租人双方以融资租赁为目的,由出租人作为买受人向承租人及出让人购买承租人自有的租赁船舶,而后由承租人租回使用。在售后回租模式下,租赁船舶通常始终处于承租人也即出让人的占有之下。例如,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标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上海格式)·回租模式》第2.5条即约定:“鉴于租赁船舶始终在承租人的占有和使用之下,因此在《船舶买卖合同》项下双方不进行租赁船舶的实体交接。双方应根据《船舶买卖合同》及本合同约定签署《船舶交接书》和《租赁船舶接受证书》(格式见附件四),即视为出租人已根据本合同向承租人交付租赁船舶。”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上海海事仲裁院)组织编写:《航运标准合同系列:上海格式(第2分册)》,人民交通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如果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将船舶出售并交付给他人,此时即涉及占有改定是否属于法释[2012]8号第10条所称“受领交付”。㉛《物权法》第27条规定:“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如果不认为占有改定属于受领交付,即意味着认可第二次船舶买卖的买受人为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从而应当支持其关于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此种结果显然不利于保护包括银行业在内的各类融资租赁公司的交易安全,进而阻碍我国船舶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
(三)贬损我国船舶登记制度
法释[2012]8号第10条认可船舶所有权变动中交付的优先效力,等同于认定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效力劣于交付。具体而言,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是否具备公信力;第二,船舶所有权变动中交付与登记二者之间的效力优劣。
所谓公信力,是指即便登记簿的记载存在错误,第三人也有理由相信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即是真实的权利人,登记簿记载的权利内容就是真实的权利内容。㉜程啸、尹飞、常鹏翱:《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00页。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任何登记制度记载的权利情况均非绝对,也都存在错误的可能。即使是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也相应设立了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等制度,㉝例如,《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82条第1款规定:“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意在通过纠正或阻却等方式维护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因此,对于登记制度的公信力不能仅作全有全无的极端判断。否认我国船舶所有权具备公信力的观点认为,登记并未成为船舶所有权变动的决定因素,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登记一定发生船舶所有权变动,不具有权利正确推定的机能,不能构成足够的信赖。㉞司玉琢:《海商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也有学者指出:“不能因为登记是国家机关组织进行的,就认为其具有当然的公信力。”㉟同注㉔。此种逻辑固然合理,即使认为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具备公信力,其来源也并非单纯由于国家公权力的组织与运行。但是,也不能仅因船舶所有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便认为船舶所有权登记当然不具备公信力,否则在纯粹的交付生效主义与登记生效主义之间设立登记对抗主义也将失去意义。登记对抗主义之下登记的重要功能在于否认未经登记的船舶所有权变动在当事人以外的效力。假使认为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不具备任何公信力,此种对抗效力又从何而来?而且,根据法释[2012]8号第10条第4项之规定,人民法院认可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享有船舶所有权的方式,是支持其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请求,因而其依托仍然在于船舶登记制度。如果船舶所有权登记不具备公信力,此种更正请求就显得并无必要,原因在于欠缺公信力的船舶登记制度展示的权利状态本不值得信赖,进而登记内容是否符合权利的真实状态似乎也无关宏旨。因此,既然赋予船舶所有权登记以对抗效力,就应当认可登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信力。虽然此种公信力不及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登记,并且也更有可能存在登记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况。确认我国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公信力,将有助于增强船舶交易的安全性,保护基于和信赖此种登记而为法律行为的第三人的利益。㊱李海:《船舶物权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此外,有观点认为赋予船舶所有权登记公信力要求登记机关必须进行实质审查,㊲同注㉞。此种观点值得商榷。船舶登记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差别更多关系到登记能否作为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不能仅因形式审查便否认船舶登记制度的公信力。而且,尽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登记的效力不同于不动产登记,但国家为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的登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登记将此类动产上的权利情况尽可能清晰地加以展现,从而提高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㊳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评最高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10条》,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如果轻易否认船舶登记的公信力,进而贬损船舶登记制度的价值,恐怕也不符合船舶登记制度设立的本意。
比较交付与登记在船舶所有权变动中的效力优劣,重点在于比较二者作为船舶所有权变动公示手段的效果优劣。公示公信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的公示要求物权的取得和变动必须采取法律许可的方式向社会予以展示,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保护。㊴梅夏英、高圣平:《物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究其本质,特殊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物权变动的影响,其本身也是物权公示原则的内容和要求。㊵例如,梁慧星主持《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238条第1款规定:“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不动产物权,非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依法律行为设立、移转、变更和废止船舶、飞行器和汽车的物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标题即为“物权公示原则”。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了登记对抗主义,尽管船舶所有权的登记状况可能存在与实际权属状况不符的情形,但依托船舶登记制度的存在,船舶所有权登记毕竟有着较好的社会展示效果。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内容可供公众直观查阅,此为交付作为公示手段所不及。交付的公示方法在于通过占有状态展示权属状况。但是,交付本非完全的公示方法,加之有观念交付的存在,更使其无法完全公示物权状态的缺点加深。㊶崔建远:《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载《法学家》2010年第5期。尤其基于船舶功能及运营模式的要求,船舶占有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形普遍存在,导致交付虽是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其社会展示效果却并不理想。作为两种均存在一定瑕疵的公示手段,交付的不足应当更为明显。因此,在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应当认定登记的物权效力强于受领交付,而不能赋予受领交付排斥登记的效力。㊷例如,甲从乙处购买一辆汽车,甲虽然取得了汽车的占有使用但没有办理汽车的过户登记。此时甲虽然也获得了汽车的所有权,但如果善意第三人丙办理了该汽车所有权的过户登记,则甲不能排斥丙的所有权取得。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
因此,《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认定船舶所有权变动中登记的效力劣于交付,否认船舶所有权登记的公信力,贬损我国船舶登记制度。就社会效果而言,此种规定不利于鼓励当事人办理船舶登记,也不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于船舶的管理,㊸参见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最终势必导致交易安全受到威胁。
三、法释[2016]5号第6条之检讨
法释[2016]5号第6条规定:“转让人转移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对价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物权法第二十四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在《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外。
关于法释[2016]5号第6条的理论基础,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将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于善意第三人之外,意在贯彻物权优先效力。善意第三人保护机制仅系协调民事权利冲突方法之一,无法完美化解所有问题。以破坏物权优先效力为代价,对特定债权人施以对抗保护,理据孱弱。”㊹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条解释只能说是客观上符合了物权优先效力的原则。但将转让人的债权人排除于《物权法》第24条所称‘善意第三人’的范围之外,这一做法本身并不是为了贯彻物权的优先效力,而是基于更深入地对《物权法》第24条确立的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这一规则背后的更深层法理与规范目的的理解以及对债之关系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权利平衡保护的基本原理的把握。”㊺龙卫球、刘保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一)条文理解与适用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两种观点的对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条规定存在的不足。就物权相对于债权的优先效力而言,前文已有论述,此种优先效力本非绝对,而是存在较为典型的例外情形。
评价本条的合理与否,关键在于理解《物权法》第24条规定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对此理论上存在“无限制说”与“限制说”两种观点。无限制说认为,第三人泛指物权变动当事人以外的所有人,㊻同注⑬,第48页。即特定的出让人与受让人当事人双方以外的其他人;㊼李海:《船舶物权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限制说则认为,第三人是指就主张登记欠缺有正当利益的第三人,㊽同注⑬,第48页。即与船舶存在系争关系的第三人。㊾同注㉞,第33页。法释[2016]5号第6条显然并未依据第三人是否与船舶存在系争关系作为确定第三人范围的标准,取而代之的则是第三人属于物权人抑或债权人。根据该条规定,船舶多重买卖中已经取得交付但未登记的受让人之一可以对抗转让人的债权人。如果受让人之二已经登记但未取得交付,由于未取得交付而未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因而受让人之二在性质上仅能基于船舶买卖合同作为转让人的债权人。此时便会产生与法释[2012]8号第10条相同的情形,即交付的效力优于登记,从而导致设立登记对抗主义的本旨难以贯彻。此即法释[2016]5号第6条的缺陷所在。
此外,由于法释[2016]5号第6条是针对《物权法》第24条的解释,因而《海商法》第9条第1款规定的第三人的范围并未随之改变,仍有解释的余地存在。因此,《海商法》第9条第1款是否属于法释[2016]5号第6条规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情形,将会直接影响船舶所有权变动中不得对抗第三人的范围,需要通过海事司法实践进一步加以明确。
四、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完善之原则
综合对于《海商法》第9条第1款、《物权法》第24条、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之分析,未来我国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的完善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船舶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对抗主义总体上已是大陆法系主要法域的惯常立法模式。㊿除前引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外,韩国《商法》第743条“有关船舶权利的转移”也规定:“有关船舶权利的转移,经当事人之间合意,即可发生效力。但是,未经登记并未记载于船舶国籍证书上,则不得以此对抗第三人。”如果单纯采用交付生效主义,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至于有观点建议从船舶的准不动产性质出发采取严格的登记生效主义,(51)参见王国华、佟尧:《大陆地区船舶所有权变动模式新论——以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与〈物权法司法解释一〉为切入点》,载《2016海商法国际研讨会暨国际航运法律与政策高端论坛论文集》。恐怕亦不现实。登记生效主义不仅不利于维护交易效率,当前我国船舶登记制度也不具备实行实质审查的现实条件。2017年2月10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11条规定:“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船舶登记机关对于船舶登记申请仍然仅作形式审查。(52)《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办法》第12条规定:“船舶登记机关收到船舶登记申请材料后,应当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书内容与所附材料是否一致,并核实申请材料是否为原件或者与原件一致。”因此,维持“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不仅符合相关国家立法的通行做法,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平衡海事活动的效率与安全。
第二,贯彻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价值。“交付生效+登记对抗”的立法模式之所以合理,原因在于认可船舶所有权变动因交付而发生的同时,赋予了登记较为优越的对抗效力,从而能够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安全。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设立登记对抗主义的初衷。因此,在未来编纂民法典物权编时,应当慎重考虑是否吸收法释[2012]8号第10条和法释[2016]5号第6条的内容,将司法解释上升为民法典之条文;《海商法》修改之时,同样也应当慎重考虑是否参考上述规定进行修改。
第三,重新认识船舶与机动车的属性差别。长期以来,船舶、航空器与机动车作为交通工具在立法上被一同处理。法释[2012]8号第10条、法释[2016]5号第6条也主要是从机动车的角度进行规定。(53)法释[2016]5号、法释[2012]8号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主要负责起草,而负责海事、海商案件审判的则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但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惯常购置并使用的交通工具。截至2016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8亿辆;(54)参见白阳:《今年第三季度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增幅明显》,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http://www.mps.gov.cn/n2255079/ n2256030/n2256031/c5526726/content.html,2016年11月7日最后访问。相比之下,2015年末全国拥有水上运输船舶仅16.59万艘。(55)参见交通运输部:《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http://zizhan.mot.gov.cn/zfxxgk/ bnssj/zhghs/201605/t20160506_2024006.html,2016年11月7日最后访问。而且,随着船舶不断向大型化发展,船舶与机动车之间的价值差距也愈发明显。基于船舶与机动车的此种属性差别,仍然在立法上将二者一并处理是否合理,值得考虑。(56)有观点认为在船舶、航空器均已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之后,如果对机动车采取交付生效主义,将显得轻重失调。(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笔者不赞成此种观点。对于特殊动产进行专门规定的原因在于特殊动产的价值高昂且权属变动频繁,如果船舶与机动车的价值高低及权属变动程度确实存在明显差别,则应当在立法上分别加以处理。未来将船舶权利的相关问题交由《海商法》进行单独的专门规定,或许更为妥当。
第四,审慎考量法学理论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舍。法律的真谛在于实践,法律的生命也体现于法律的实现,(57)参见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而维护包括交易安全在内的财产安全则是法律秩序价值的维护作用之一。(58)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44页。根据前文对于法释[2012]8号第10条、法释[2016]5号第6条的分析,上述规定至少受到物权优于债权、动产物权变动交付生效等法学理论的限制,进而导致对于交易安全的忽视。当法学理论与交易安全存在冲突,如何进行价值取舍,同样值得审慎考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6FFX010)、交通运输部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海商法》修改之研究”(项目编号:2013-322-810-0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思琪,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