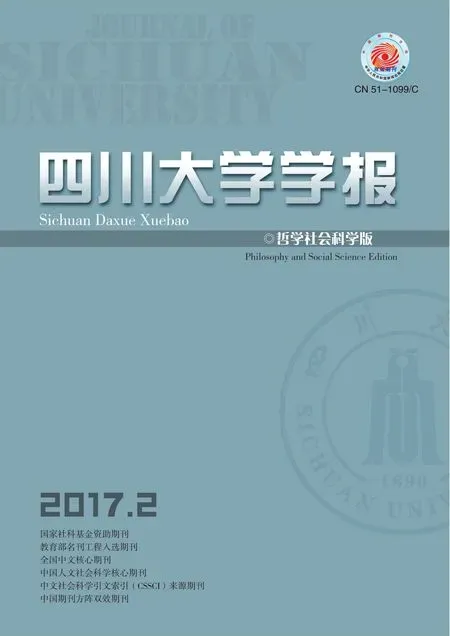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陈雅文
§博士生论坛§
公共理性与动机:一种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
陈雅文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其论证的成败决定着后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说服力。罗尔斯的论证的一个薄弱之处在于,他未从动机的角度对公共理性的实践性和可行性做出充分说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应该借助教化的力量,在个体的主观动机集合中增补他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以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公共理性;政治正义观
约翰·罗尔斯的后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公民被视作自由平等且彼此合作的社会成员,如果公民持有彼此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信念,那么如何可能建立起一个正义而又稳定的社会?”*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xviii.通观这部著作,罗尔斯在很大程度上把论证的任务交付给具有合理性的公民(reasonable citizen),*具有合理性的公民具有这样两个特征。其一,他们愿意在彼此同意的条款下进行合作,愿意提出公平合作的条款,并在其他人遵守条款的情况下也这样做;换言之,他们尊重规则本身的价值,即使条件成熟,也不会简单受利益的摆布,仅为了私利而打破规则。其二,他们承认“判断的负担”(burdens of judgment)会引发不可避免的分歧。他们认识到,除开资讯匮乏、自私自利和视而不见之外,真诚对话的人们也会提出背道而驰的观点,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公共理性在引导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参见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56.也即是说,他所阐述的政治正义观最终欲以取得的稳定性,是由公民的合理性来保障的。可是,笔者认为,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呈现的关于公共理性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其理论的一个空白,在于他没有为个体的现实身份和承诺留下足够的空间,换言之,他的整个论述倾向于忽略人们身上的异质性而选择性地强调人们所共享的品质。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的论证向我们暗示了一点:一种政治正义观要想取得真正的稳定性,公民需要从自己的理由出发来佐证公共理性的要求。不过,罗尔斯的论证不够深入。在触及这个问题时,他要么规定了一种理想化的对人的理解,譬如他所定义的具有合理性的“公民”概念;要么轻易而乐观地绕过去了,譬如他认为即使综合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s)*综合学说是罗尔斯的专门用词,它指那些全面地引导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它们有关我们的人生价值、个人品格、家庭关系、共同体理想,以及许多其他贯穿于我们行为和整个生活的东西。会对人们的公共理性的思考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也是积极的,并不会动摇他们关于公共理性的信念。*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388.事实上,公共理性需要吸纳更加细致的关于动机的思考。当然,罗尔斯并非对这个问题未置一词。正义感(the sense of justice) 就是他论及动机问题的一个重要概念。罗尔斯通过描述道德心理的发展,论证了正义感的形成,但他所进行的是一种普遍化的道德心理学描述,它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从认识论层面讲,罗尔斯只叙述了在理想成长模式下人们如何取得正义感。其二,从规范层面讲,罗尔斯只刻画了人为什么可能具有正义感并按照正义(或公共理性)的要求行动,却未能说明“我”(某个特殊个体)为什么应该按照正义(或公共理性)的要求行动。
事实上,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极大地依赖于该社会中公民的素质以及他们对待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和方式。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愿望影响着公共理性的实现。这些能力包括勇敢诚信的品德、独立的判断、开通的思想以及言说、倾听和回应他人的能力等等,而这些能力的实现则指向了对公民素质的培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人对彼此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关切(care)是滋养一个社会健康稳定且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这种关切感使人们有可能跳出狭小的自我,察觉公共生活中值得被关心和尊重的事物。因此,本文认为公共理性需要借助教化的力量,才能在个体的动机集合中增补罗尔斯所强调的“合理性”要素,从而促成一种在规范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辩护的公共理性,以下试论之。
一、正义感与公共理性的动机
“正义感”是罗尔斯在《正义论》篇末所提出的概念,他想借助正义感论证“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公平的正义”是罗尔斯所阐发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它的形式是“公平的”,因为其原则的提出是处于一种完全公平的初始情景下(原初地位);它的内容主要包含两项正义原则。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9, pp.52-56.能够在道德情感的层面获得支持,因为他意识到“正义观的稳定性取决于动机的平衡:正义观所培养的正义感与它所鼓励的目标必须战胜不正义行为的倾向”。*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398.正义感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被延续下来,并且被作为具有合理性的公民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用正义感解释了一般而言人们为什么会支持他的“公平的正义”;而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则用正义感解释那些具备了这种品质的公民如何恪守多元事实所设下的边界,实现互利而稳定的合作,从而证明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公平的正义”是政治正义观之一)能够取得稳定。
罗尔斯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了正义感如何逐步得到发展,他指出正义感的形成有三个阶段。*在1963年的《正义感》一文中,罗尔斯已经形成了关于正义感的初步想法。只不过,在这篇文章中,罗尔斯是用“愧疚感”来进行描述的:它们分别是权威中的愧疚感(authority guilt)、社团中的愧疚感(association guilt)和原则中的愧疚感(principle guilt)。愧疚感被用来描述以上信任和友爱破裂时所产生的感情。参见Rawl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0.第一阶段是权威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authority)[家庭]:如果父母疼爱子女并表达对他们的关爱,子女也会相应地理解和习得对父母的爱,尽管最初儿童是出于本能和欲求而采取取悦父母(符合父母之要求)的行为。在这个阶段,父母是孩子模仿和崇拜的对象,孩子对父母的令行禁止的理解也只是初级的,他们未能体会规则背后所蕴含的正当与善。第二阶段是社团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association):校园、邻里以及任何存在合作关系的场合,都要求个体理解自己在社团中的角色以及社团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逐渐培养起智识的判断力和道德的洞察力,同时理解了人际间的合作和互惠,并且懂得了换位思考,体会到了合作的美德,诸如正当与善、忠诚与信任、正直与无私,以及相应的恶,诸如贪婪与不公、虚伪与欺骗、偏见与偏袒,还培养起相关的诸如义愤这样更加复杂的感情。在前两个阶段中,人学会了关心他人,也了解了友谊和团体的意义。第三个阶段是原则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principles),它建立在上述两个阶段之上。个体只有在前两个阶段习得了相应的爱与信任、友谊与互信这样的道德态度,他们才能理解自己和自己所在乎的人都是一种牢固而持久的正义制度的受益者,从而相应地产生一种正义感。第三阶段的道德需要更高的推理、抽象能力和想象力,因为它不仅发生在亲友蒙受苦难和不公的情景下,也发生于对遥远的陌生人的关心中,甚至会超出当下某个具体的事件而转向对更普遍情形的思考。*参见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第70、71、73节;对三个阶段的总结,参见该书第 429页。罗尔斯认为,人们会在这样的自然过程中产生遵守正义观念的欲望和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事的动机。
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也认真地考虑了人的道德动机问题,认为应该为一种“合理的道德心理学”留下空间。其中,正义感作为合作的基本品性被继承下来,并贯穿于对公民的基本要求。罗尔斯认为,一个合格的合作参与者需要具备两种道德能力,即善观念和正义感。“正义感是理解、应用和按照公共正义观(它规定了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行为的能力,……同时,正义感也表达了一种根据他人也遵守的条款来行事的意愿”。相应地,他也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欲望:基于目的的欲望(object-dependent desire)、基于原则的欲望(principle-dependent desire)和基于观念的欲望(conception-dependent desire)。*以上引述参见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86, 19, 82-83.第一种欲望是不考虑规范性原则的欲望,它直接与人的本能相关(如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第二种欲望是按照理性原则规范行事的欲望,它与第三种欲望的区别在于,前者希望按照规则行事而尽可能有效地实现目标,而后者包含着一种对政治和自我的构想,诸如对公民、公民关系、良好正义的社会等概念的设想及其实践。相较于休谟,罗尔斯认为自己对动机的阐释增加了所谓“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ing)的部分,*这里的实践理性是指,“人们的慎思受到某些实践理性的原则的引导,诸如,采取有效的方式实现目的的原则,抑或,根据正确的信念矫正对特定的事物属性之认识的原则”。参见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61页。即人的动机不是纯粹由心理学来说明的,还需要借助“基于原则的欲望”和“基于观念的欲望”来加以解释。*罗尔斯认为休谟并未考虑过实践理性的原则,而仅仅考虑的是心理学的原则。有关罗尔斯对他与休谟的区分的说明,可参阅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89.不仅如此,罗尔斯还提出了“涵养的义务”(The duty of civility),尽管这不是法律性的强制义务,却仍然是良序社会中值得提倡和鼓励的公民美德。总的说来,罗尔斯能够认可:公共理性的理念需要对公民的动机做出说明。
诚然,罗尔斯已经尽可能周详地建构起他的整个体系。如果接受他的前提,我们就会心悦诚服地表示,罗尔斯已经完成了他的论证。可现实中的读者也许不会感到满意,这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原因。 首先,罗尔斯所援引的道德心理学事实(主要是在《正义论》中)可能存在争议。对此,罗尔斯已经有所认识,所以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特别强调,书中表述的正义感不是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而是“从‘公平的正义’这个政治观念中推导出的道德心理学,是‘政治的人’和‘公民身份’这样成体系的概念中的一环”。*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86-87. 罗尔斯在关于休谟的讲座中也曾谈到自己与休谟的差别,他认为休谟“心理学化了道德慎思”,而自己的道德心理学有别于休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他希望从规范性的哲学维度而非经验维度(认识论维度)来化解这一批评。就此而言,罗尔斯的论证是巧妙的,尽管他没有给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罗尔斯对论证严谨性的要求。
其次,罗尔斯只处理了在理想情形下道德人格的发展,描述了在充满爱与信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格应有的样子。正义感的发展是环环紧扣的,如果在前面两个环节出现问题,正义感就很难真正在公民的心灵中建立起来。这使罗尔斯对正义感的论证显得头重脚轻。也许有人会反驳说,罗尔斯自始至终都强调自己处理的是良序社会这个理想状况,其说法往往是类似于这样的句子:“良序社会中的正义观是稳定的:如果这个社会中的制度是正义的,参与社会制度的人也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和欲望来履行他们的分内之责。”*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p.398.在此不妨暂且把良序社会这个“乌托邦”搁在一旁,因为规范性的论证要想观照现实,就需要适当地把非理想情景纳入考虑,否则,这个理想社会就只能是愿景了。
第三,“论证是规范性的”符合罗尔斯对自己的定位,可即便如此,他的论证依然会出现问题。罗尔斯只刻画了人为什么可能具有正义感并按照正义(或公共理性)的要求行动,却未能说明“我”(某个特殊个体)为什么应该按照正义(或公共理性)的要求行动:从具体公民的视角来看,他可能完全缺乏履行公民责任的欲望和动机。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并不鲜见。例如,R是一名富商,靠自身敏锐的洞见以及过人的毅力和努力创造了强大的商业帝国。在R看来,差别原则完全是对富人明目张胆的抢劫:为什么我白手起家挣得的产业应该施惠于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呢?即便R极不情愿地按时按额缴税,“合理性的公民”这样的要求也并不奏效。罗尔斯所构想的交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交叠共识寄托了罗尔斯公共理性的终极理想:尽管社会是由持有彼此不同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公民所组成的,这个社会也依然可能保持正义和稳定,这是因为持有深度分歧的观点的人们能够从自己的视角真诚地就基本的正义问题达成共识。依然沦为了临时协议:如果R某天可以操纵政府决策,他就会努力游说政客们降低税率,正如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所做的那样。*史蒂夫·施瓦茨曼是黑石集团的CEO,他在推动有利于富豪的税务政策方面十分具有代表性。抨击R这样的富人为富不仁当然大快人心,但这并不是哲学论证的好方式。我们需要问一问,在R的主观动机里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现在,我们有必要进入有关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讨论,尝试从这个视角剖析正义的动机,寻找推进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的方法。
二、公共理性的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
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讨论涉及一个问题,即一个道德命令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声称,行为者有理由做一件道德上的当做之事。如果行为者不认为自己有按照这个道德命令行事的动机,或者说,行为者丝毫不在乎这个道德命令所提出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声称他有当做的理由吗?这个问题在公共理性的论域里也极富吸引力,尤其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那里。因为罗尔斯把交叠共识作为公共理性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这使公共理性的要求决不能止步于外在的妥协,而需要行为者心悦诚服地同意。由此,回答如下这个问题就是至关紧要的:公共理性所提出的要求如何能够成为“我”行动的理由。
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在其关于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著名论述中指出,“我有一个理由做某事”这一命题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我通过做某事而使我的某个动机得到满足,而如果我不具备这个动机,那么说“我有一个理由做某事”就是假的;第二种解读:不管我是否具备相关的动机,都可以说“我有一个理由做某事”。第一种解读被称为内在理由的陈述,而第二种解读被称为外在理由的陈述。威廉斯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外在理由,所有的理由都
是内在的。也即是说,当一个人宣称“我有一个理由做某事”时,要么在其主观动机集合(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主观动机的集合是指一个人的欲望清单,包括他的“评价的倾向、情感的反应模式、个人的忠诚以及体现行动者承诺的一切计划”(参见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05)。有证据表明,罗尔斯并未对威廉斯所提出的主观动机集合表示反对。在阐释休谟时,罗尔斯认为休谟的观点是纯心理学的,缺乏一种实践理性的观念,换言之,缺乏一种对基于原则的欲望的解释。但他认为在威廉斯那里,这种基于原则的欲望则包含在人们的主观动机集合里。所以,威廉斯的观点相容或者至少不冲突于罗尔斯的观点。参见约翰·罗尔斯:《道德哲学史讲义》,第64页注释1。里能找到如此行动的动机,要么在其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能从他的既有动机里产生一个如此行动的动机。除此之外,宣称“我有一个理由做某事”都是伪命题。威廉斯举例解释了其上述论断:欧文·温格拉夫来自一个军人家庭,家族光辉的参军传统要求欧文从军,但欧文本人并没有任何从军的愿望且憎恶军旅生活。在此情况下,威廉斯认为,欧文没有理由从军,坚持声称“欧文有理由从军”无异于恫吓威胁。*Williams, Moral Luck, p.106.
在公共理性的情景中,我们面临一个相似的问题。按照罗尔斯的设想,公民应该具有合理性,他们愿意提出合作的公平条款,并在其他人都遵守条款的情况下也愿意这样做;这样做并非简单受到利益的驱使,即使条件成熟他们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破规则;在较为尖锐的宗教信念和公民身份之间,他们游刃有余,能够依据合理性的要求有意识地调动或者限制自己的理由。罗尔斯把这些统统算作对公民的要求,将之视为具有合理性的公民所应该履行的义务。然而,公共理性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否从属于每一个参与者的主观动机集合?如果参与者找不到履行公民义务的动机,我们可以称其为“不理性”(irrational),或者用罗尔斯的术语“不具有合理性”(unreasonable)吗?
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数不胜数的道德命令,诸如不可杀人、勿要说谎、善待邻人等等,而大多数人也的确把这些命令作为教条加以遵从。威廉斯指出,人们当然会从道德命令中受到启发,这正是用慎思推理来发现新的内在理由的过程。他说:“经过慎思,一个行动者就可以逐渐看到:他有理由做他原来并不认为他有理由做的事。以这种方式,慎思的过程就可以添加被内在理由所支持的新的行动,……反思可以使行动者看到某个信念是假的,因此使他认识到他其实没有理由做他原来认为他有理由要做的事情。”*Williams, Moral Luck, pp.104-105.慎思推理表述了具有反思意识的行为者的思考过程:他们的直觉、信念和判断是可错和可变的,并且处于动态地来回修正之中。
斯坎伦(T.M. Scanlon)指出,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根本分别,不在于有没有看到行为者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会在主观动机集合里增补新的动机;而在于是否承认行为者只要“经过正确充分的思考”,就应该增补这样的动机。外在理由的核心主张是,即使一个人没有产生做某件事的动机,要求他做这件事也依然是正确的,他可能只是因为粗心、缺乏思考或者方法错误,才没有意识到他应该产生这样的动机而已。斯坎伦就此举例说,如果我认为个人诚信是很重要的事,而你即使被告知了这一点仍对个人诚信的要求无动于衷;个人诚信本身是一种值得推崇的观念,而你经过最充分的反思后依然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只能说你是一个道德思想极其狭隘的人。*以上参见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69, 370.而在这一点上,罗尔斯更倾向于外在理由。尽管他采取了反思平衡的方法来描述人们如何修正和调整自己深思熟虑的判断,又希望通过诉诸心理学的规律来证明正义感的存在,但他在如下这一点上与外在理由支持者们坚定地站在一起,即:公共理性对公民行为所提出的要求是可被辩护的,只要公民具备基本的心智能力,只要公民采取了他所建议的思考方式,他们就会成为具有合理性的公民,并按照这种要求来行动。
如果我们尝试思考得更细致一些,就会发现在外在的道德命令和我们的主观动机集合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例如,U原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在他看来,行为的准则无非就是根据事态的结果来判定,而U的室友K是一个康德主义者。尽管观点极为不同,但并没有妨碍他们在生活上的互助和节节攀升的友谊。K的正直行为和对身边每一个人的关心打动了U,他甚至发现,正是康德主义在教导和启发K做出那些良好的举动。这样,U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信念,即“应该把每一个都当做目的,而非手段”。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个尚不属于U的主观动机集合,又被U认为是正确的道德命令呢?威廉斯认为,“外在理由陈述的全部要点是:不管行动者的动机如何,一种外在理由的陈述都可以是真的。可是,除开激发行动者采取行动的那种东西,并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的行动。因此,我们还需要外在理由陈述之外的某种其他东西——某种心理上的连系——来解释他的行动;这种心理上的连系似乎是信念(beliefs)。如果A相信一个关于自己行为的外在理由陈述,那么那个事实可能有助于说明他的行动”。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存在这样的情形,行为者做某事,是因为他相信存在着一个要他做那件事的理由,但对那个理由究竟是什么,他却没有任何信念”。*Williams, Moral Luck, p.107.这种情形在生活中十分普遍,一些自然的情感,诸如信任、崇敬、爱慕甚至震慑和恐惧,都可能使我们产生一个由外在理由陈述的信念,即使我们并不具有直接相关的那个动机。也即是说,我们是出于一些别的原因相信一个外在理由的陈述并按照它的要求去行动。
那么,相信一个外在的道德陈述,这种“相信(或者说信念)”是否可以为外在理由做出辩护呢?威廉斯认为,当行为者相信外在理由的陈述时,就同时被激发起来行动了,这在本质上可以解释为他产生了一个新的动机。换言之,这种“相信”在付诸于行动的那一刻,就不再是空洞的,而是与动机紧紧结合在一起。只有坚持“行为者正是因为相信一个(外在理由的)陈述,所以获得了相应的动机(或者以某种正确的方式思考才最终相信了外在理由的陈述)”,*Williams, Moral Luck, p.107.才能成其为真正的外在主义者,否则就会沦为内在主义。对于那些活生生的公民而言,如果要把公共理性的要求贯穿于他们的言谈举止,亦即将公共理性的要求从良序社会中的抽象人格降落在每一个具体的行为者身上,我们就应该把具体行为者的主观动机集合考虑在内。如果要实现真正的交叠共识,就需要他们的主观动机集合里包含“公民品格”“合理性”“涵养的美德”这样的因素,或者,需要他们持有这样的信念。
不过,内在理由的支持者需要面临一个显见的荒谬推论的挑战。假设有一个恐怖主义者T,他的主观动机集合包含诸如虔诚、永生、极乐这样的因素,他认为参与人体炸弹的袭击行动是荣耀的,但被告知这一行为是可耻的。那么,依据内在主义的思路,是否T就有理由参与袭击活动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威廉斯只说,如果一个行为要求不属于某人主观动机的子集,就不能说他有理由做某事;但这并不意味说,如果一个行为要求(参与袭击)属于某人的主观动机集合,那么他就有理由做某事。正如威廉斯所给出的例子:我可能错误地以为桌上的汽油是白水而把它喝掉,但这是基于一个错误的信念。所以,威廉斯只澄清了什么不是一个人做某事的理由。然而,什么能够成为要求一个人做某事的理由?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威廉斯指定了一些符合充分理性(full rationality)的条件,试图回应这个问题:(1)行为者没有假的信念;(2)行为者拥有真的信念;以及(3)行为者正确地进行思考。*参见徐向东:《道德哲学与实践理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1页。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如何界定行为者的信念为真,以及什么算作正确的思考?一种直观的回答是符合论式的:如果我说我的包里有100元钱,我一掏腰包,果然有100元钱在包里,这可以算作真的信念和正确的思考。可是,我们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并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予以解答,我们去哪里寻找可供验真的道德事实呢?这不禁令人惶惑。*内格尔提出了一种富有启发的思路,认为道德原则的客观标准可以建立在“自我的形而上学”上,一种“把自我作为同样真实中的他人中的一员”的观念。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不可避免的,又迥异于动机和欲望的观念。本文对这种观点暂且不予讨论。参见Thomas Nagel, 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
有一种方案兴许有助于化解上述困境:存在某些独立的理由,它们不是形而上学的设定,也不是完全独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换言之,这些理由是在我们的教养和习得中形成的。*J. McDowell,“Might There Be External Reasons?” in J. E. J. Altham and Ross Harrison, eds., World, Mind and Ethic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73.戴维·王(David Wong)就此论证说,外在理由是可以镶嵌在人们的动机习性(motivational propensity)之中的。如他所举的例子:罗贝塔是一个成长于优渥环境的少女,她观看了一部关于南非纺织工人的纪录片,并被他们的苦难生活深深震惊了,于是她决定发起一场抵制生产相关货品的公司的运动。事实上,罗贝塔发起抵制运动的动机早已蕴含在她先前拥有的动机习性里,是其对身边人物的同情习性唤起了她对遥远的纺织工人的同情。可以说,外在理由为人们的习性的养成提供了资源,为行为者反思自己的欲求提供了支点,并进一步形塑行为者的动机习性。*David B. Wong, “Moral Reasons-Internal and External,” in Natural Moralities: A 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2.这样看来,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的争论将把我们引向一个新的方案。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存在某些外在理由的话,补充新的论证就显得很必要了,这就是教化。
三、公共理性与教化
让我们回到罗尔斯所思考的公共理性。当人们面对一系列“公民应该如此这般”的要求时,他们如何获得如此行为的动机呢?为什么“我”应该履行“合理性”的要求呢?尤其是,在公共理性的要求可能消解我的主观动机集合中的另一些要素时,为什么那些因素要让位于公共理性的要求呢?要想真正取得关于某种政治正义观的交叠共识而不流于临时协议,我们就需要关心在反思者心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本文认为,只有在反思者的主观动机中注入“合理性”的要求,并使其具有某种优先性,*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优先性完全不同于罗尔斯所提出的那种“正当”对“善”的优先,它不是对理性人的外在规定;与之相对,当反思者未能执行这种优先性时,他会产生一种愧疚感。才能实现真正的交叠共识,而教化是取得这种内在合理性的一种重要途径。
教化早在卢梭那里就被提出来,不过,他是用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说法来表达这个观点的。卢梭看出,国家的团结以及公民对国家全心全意的依附,有赖于公民像崇拜神灵那样崇拜自己的国家。公民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这个国家自己的神、这个国家特有的守护者。它有它自己的教条、自己的教仪、自己法定的崇拜表现”。人们通过公民宗教在政治生活中被维系在一起,从而真正实现遵纪守法甚至为国捐躯。但是,卢梭的公民宗教要求一种强制性的服从。为了最终实现他所设想的公共理性,卢梭认为“要有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条款应该由主权者规定;这些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则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可能是忠实的臣民”,“它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它们可以驱逐这种人,……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性,因为他们不可能真诚地爱法律、爱正义,也不可能在必要时为尽自己的义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上引述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3、181页。
卢梭敏锐地把捉到教化和认同对于保持国家团结的重要性,但他所阐述的公民宗教却必需通过惩处反对派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从而易于塌陷为强制和屈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就此评价说,卢梭的公民宗教“忽略了人与人的维度,因为卢梭所赞许的那种社团纽带间的情感不是直接与个体相关的”,无法真正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个体。*Martha Nussbaum, Political Emotions,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5.所以,卢梭的公意最终会失去它的吸引力。不过,本文在此想要表达的教化与卢梭的公民宗教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教化并不旨在增进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如何促进国家的团结并不是本文首要关心的主题。其二,教化旨在促进公民商谈中的互惠精神和彼此尊重的美德,或者用罗尔斯的话讲,促进公民的合理性和涵养的美德。这种对情感的强调恰恰是出于对个体的关心,保护每一个人不被任意贴上“不具有合理性”的标签。所以,本文格外看重的是卢梭所忽略的个体差异性,而这一教化观念,可以获得罗尔斯的支持。
对于公共理性而言,通过教化增进人们履行公民责任的动机,这一点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罗尔斯认为,我们的公共政治文化就蕴含着这种教化的功能。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写道:“基于原则的欲望和基于观念的欲望,是如何成为人们动机倾向中的因素的呢?一个表面的回答是:它们是人们从公共政治文化的教化中习得的。”罗尔斯的理由很明确,因为公共政治文化是由“宪法体制的政治制度、阐释政治制度的公共传统,以及作为公共知识的历史文本”所构成,所以对当下政治制度的解释和执行,都是一种对公民行为的引导。*以上引述参见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p.85 n.33, 13-14.在此过程中,公民习得了基本的是非观念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基本看法,从而在关于公共事务的判断和行为中产生符合公共理性之要求的动机。不过,罗尔斯并没有进一步对公共理性的动机做出阐述,这为我们留下了阐释的空间。一旦思考得更细致,我们就会关心这种公共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教化如何触动公民的心灵。如果仅仅明白什么是公共理性的要求,并不足以激发我们采取符合相关要求的行为,那么,公共理性的动机从何而来?有没有一种方式既是非强迫性的(区别于卢梭的公民宗教),又是行之有效的?
本文认为,教化在上述意义上能够激发一种公民的情感,从而为个体的主观集合增添有利于推进公共理性的动机。*本文在此不讨论情感与理性判断的认知关系,相关论述可参阅Sharon R. Krause, Civil Passion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2-56.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情感(emotion)不同于情绪(mood)。在此,本文赞成努斯鲍姆对情感的一种认知主义理解,即情感具有认知内涵,它依赖于一种信念(或理由)。*参见Martha Nussbaum, Love's Knowledg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1;亦参见Gerald Gaus, The Order of Public Reason: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Morality in a Diverse and Bounde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88-189.因为信念(或理由)是可以区分对错的,所以基于信念(或理由)的情感也有对错之别(而情绪则很难用是非对错来加以评判)。例如,当人们为ISIS在巴黎的恐怖袭击活动感到愤怒时,他们是基于这一道德判断:滥杀无辜是错误的。情感也可能基于一些错误的判断,例如在纳粹时代,一些人对犹太人表现出强烈愤恨时,他们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犹太人是贪婪虚伪和低等的,他们正在破坏日耳曼民族的团结。尽管情感呈现的样态是十分具体化和个人化的(面红耳赤、心跳加速、血压升高等生理现象),但引起情感的事物却可以是十分抽象和普遍的(也许憎恶犹太民族的人压根儿不认识一个具体的犹太人)。这就反过来有助于我们理解情感的抽象性和可普遍化,也即是说,一种正面的情感无需直接接触具体的事物(人们当然需要接触其他事物,并发生移情),也能够获得一种超越特殊对象的感情。诸如正义感和同情这样的情感,就可以借助于影像、文字甚至是信念和理由的陈述而得以推广。所以,情感可以拓展我们经验的边界,从而取得一种普遍性。
努斯鲍姆就认为文学作品是增进正义感和同情的一种良好范例。它“使读者成为深切关注他人苦难和厄运的人,使读者认同他人,并且在各种认同的方式中为自己展示形形色色的可能性,这种形式本身就在读者中构建了同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文字有特别的力量,它“召唤强有力的感情,使人们惊惶和困惑。它鼓励人们对习以为常的虔诚产生怀疑,并且强迫人们与自己的思想和目标进行往往是痛苦的对抗。一个人可能被告知他所处社会中人们的许多事情,但仍旧和这些信息保持距离。那些促进认同与情感交流的文学作品刺穿了这种自我保护的计划,逼迫我们去观察和感应许多可能难以正视的事情”。*以上参见Martha Nussbaum, Poetic Jus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pp.66, 5. 译文参考丁晓东译《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略有改动。这样一种跳出自我的有限而特殊的圈子去感知他人和世界的过程,被努斯鲍姆称为文学想象。*努斯鲍姆还详尽地讨论了如何推进情感教化,参见Political Emotions 第八章和第九章。亦可参阅 Krause, Civil Passions, pp.135-141,此处讨论了制度和政策如何可能帮助培养和扩展人们的情感。除开文学想象,还存在其他表现方式的想象,诸如影像、绘画、雕塑或者建筑。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人们首先受到情感的激发而做出判断。尽管之后的判断仍然需要用已有的道德观念或者政治理论加以检验,仍然需要在每个反思者的内省判断中加以检验,也仍然需要在每个反思者与其他反思者的对话中进行检验。*Nussbaum, Poetic Justice, p.12.但情感本身是促成和构成我们的公共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
通过情感来触发公民心中有关公共理性的要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公共生活中,人们对苦难的同情、对不公的愤慨、对不义的愧疚,都是支撑公共理性的重要情感。例如,在推进一种敏于平等的分配原则时,几种可能导致彼此矛盾的结论的因素会在富人R的主观动机集合里同时出场:希望财富增加、希望赢得尊重、关爱亲友、对穷人不忍(如果他对相关话题有充分留意的话)以及对贪婪者鄙夷等等。要想促成R对平等分配原则的真正认可,就需要强化诸如同情弱者、鄙夷贪婪以及将心比心的情感要素。抑或,当虔信者C面临公共理性的要求可能冲击其核心信仰时,他的主观动机集合里会同时涌现这样一些因素:宗教经文的教导、不受歧视的愿望,以及一般而言他对支持、希望、机会、尊严、平等、自由等概念的感受。也许,宗教经文的教导在C的清单里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但其他因素也会同时出场,这将逼促C在做出违背其他因素的行为时感到犹豫和不安。只要存在一些彼此抵触的因素,它们相互博弈就是对一种反思者行为的引导和规训,尽管这个过程可能充满挣扎。
事实上,上述主观动机因素的博弈过程为滋养一种个人对公民社会的关切找到了出路,它使人们有可能超越狭小的自我利益,察觉公共生活中值得被关心和尊重的事物。因为既不是规范性的政治要求,也不是以一己私利为基础,所以这种关切感将丰满一种抽象而稀薄的公共理性的理念。正如克劳斯(Sharon Krause)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面对我可能拥有的对立欲望时,(一种共享的关切视域)也维系着我尊重自由言论权利的义务”。*Krause, Civil Passions, p.157.因为公共理性的要求出现在了我们的主观动机集合之中,所以这些要求不再是外在规定,我们选择服从于公共理性的引导(即使这会损伤我们的其他主观动机),它不再是令人抵触和憎恶的强制性要求,相反,这是“构成性”和“基础性” 的。*Harry Frankfurt, The Reasons of Lo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8.
通过激发公民感情来推进公共理性的教化,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种对公民友谊的增进。这立刻把我们带向亚里士多德,然而当亚里士多德把友谊作为一种美德提出来时,*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by Terence H. Irwi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5, 1155a.他所考虑的城邦社会相较于今天的现代社会是如此地小而单一,在今天友谊概念显然已经“被划归私人生活的领地”了,*Alasdair C. 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156.那么,以这种方式理解公共理性,依然是有活力的吗?本文认为,公民友谊尽管不再在城邦的公民关系的意义上指导今天的政治生活,但只要人们依然执着于探究“怎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问题,公民友谊这样的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只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谊或者说对共同体的认同是以把公民联结在一起为前提,而在庞大而多元的现代社会里,这个前提已经被模糊并置换——当我们一再追问推进公共理性的方法时,就不再预设存在着使社会一统的公民友谊,反而是需要增进它。区别在于,当今我们是从个体(或者说私人的)的角度重新审视并力图学会分享这样的友谊。
本文的上述想法能够在当代许多关怀伦理学家那里找到回应。与寻求最佳的道德原则不同,这些理论家关注的正是个人如何才能最好地具备道德行为的能力,*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00.如其认为“虽然正义意味着要有正确的原则,但如何在具体情况下运用正义原则却要求具备这样一些特质和情感,……并且,它们不只是去生硬地诉求原则,然后使人的意志和行为与之一致”。*Lawrence Blum, “Gilligan and Kohlberg: Implications for Moral Theory,” Ethics, 1988, Vol.98, No.3, p.485。转引自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p.406.这种关切感促使人们把他人视作拥有需求、愿望和情感的存在者,一旦进入这种视域,就更能用友谊和爱的要求来对待他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关切感可以取代罗尔斯对公共理性所做出的规范论证,这一点与那些强调“应该依据对特殊情景的观照,而非依据对普遍原则的运用来解释道德”的关怀伦理学家有所不同。*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p.402. Kymlicka在此给出了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的名单,如Ruddick、Noddings、Hekman和 Deveaux。Krause也持有这种观点,她反对把正义原则的规范辩护置于情感关切之前。参见Krause,Civil Passions, p.2.与之相对,本文认为,罗尔斯的论证清晰地指出了对于公共论坛的政治议题而言,政治和正义原则意味着什么,公共理性的理念应该是什么,又对参与者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这些对规范性的政治证成依然是首要的。本文所强调的关切感是一种补充论证,意图从关心的动机出发,去推进公共理性的理念的执行。
如果本文上述观点能够成立,那么,就有望建构这样一个社会:被公民共享的友谊在实践中隐形地支撑着公共秩序的运转,并且使公共秩序生机勃勃。借用威廉斯关于堕胎的例子,得到政府准许的是堕胎,没有得到准许的是杀婴,这种区分在分享某些道德情感的语境中很自然地得到维护,不需要进一步的理由。不需要进一步的理由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区分是不理性的,而只是因为“你不能杀一个孩子”要比其他可以提出来支持这一区分的理由更具有说服力。*威廉斯将这种情形称为“不完全的理性化”。参见 Williams, Moral Luck, p.81.“滥杀无辜是错误的”这个直觉式的判断,要比在“政治正确”还是“真主伟大”的论题上争辩不休更加行之有效,尽管在法理上对二者进行辨析依然是必要的。同理,在更多极富争议的政治话题上,如果公民友谊的确深入人心,也许我们无需走入碎片化的理由的死胡同就有望达成一种交叠共识。
总而言之,仅仅依靠精致的理念辨析,公共理性的理想实践很难找到出路。只有通过教化增补公民的主观动机集合,进而只有公民真正愿意投入到争论和冲突中,去努力理解和把握这些争论与冲突的核心,公共理性的理想才有希望实现。正如威廉斯所说:“如果公共秩序一方面想要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又不使人类经验失去光泽,那么它就必须发现某些方式,以便能够把公共秩序与个人情感联系起来。对于生活着的我们而言,个人情感不仅是一种能与私人理解相共存的状态,而且必须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生活想要具有分量,如果生活是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毕竟在生活中,我们所感受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所理解的多于我们所能解释的。”*Williams, Moral Luck, pp.81-82.
(责任编辑:庞 礴)
Public Reason and Motivation:A Critique of John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Chen Yawen
This essay is devoted to John Rawls's main concept of public reason in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challenges its feasibility in practice. I argue that internal reason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Rawls's public reason, that is, by adding reasonableness into citizens' 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 Furthermore, citizens' reasonableness can be cultivated by civil, especially emotional education.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public reason,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justice
陈雅文,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生
D09
A
1006-0766(2017)02-01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