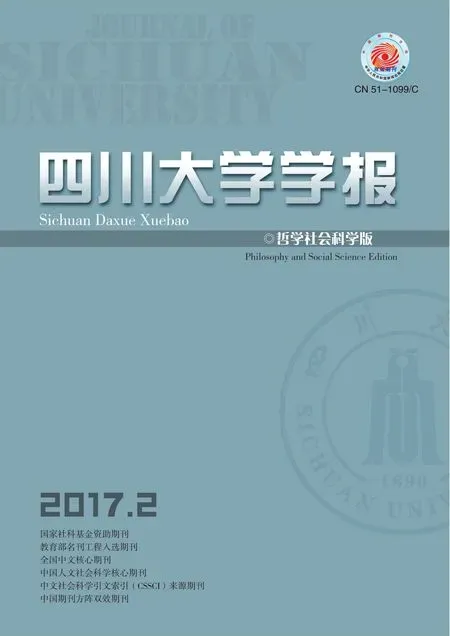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徐法言
§中国史研究§
金川战役与大、小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的兴起
徐法言
山神崇拜是两金川地区苯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墨尔多、甲索为代表的嘉绒神山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崇奉。在乾隆朝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借助山神之力呼风唤雨,念经诅咒,给清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战争结束后,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山川之神”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当中,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顺助灵”的新形象,从而转变为清廷统治与经营嘉绒地区的重要象征。
金川战役;苯教;山神崇拜;山川祭祀
中国自古就有祭祀山川的传统。《国语》韦昭注云:“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故谓之神也。……足以纪纲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徐元浩:《国语集解·鲁语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2页。古人信奉山川有神,故山川祭祀一直是国家礼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川之神被认为拥有“兴云致雨”的能力,因而常常成为人们祈雨或祈晴的对象。*参见朱溢:《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兼论唐代的山川崇拜》,《新史学》(台北)2007年第18卷第4期,第71-124页。18世纪中后期,清廷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过程中,曾多次举行祭祀山川的活动。战后,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又将“新征服”地区的名山大川列入祀典,春秋致祭。此举并非仅仅是数千年来中原王朝山川祭祀传统的简单复制,同时也与“新疆”*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清朝官方将两金川改土归流之地称为“新疆”。地方秩序的重建以及嘉绒地区的苯教(Bun)信仰(山神崇拜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苯教是发源于西藏的古老宗教,曾一度盛行于卫藏地区。公元7世纪以降,印度佛教传入西藏,苯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逐渐式微,最终被驱逐出卫藏中心,退据阿里、安多、康区等藏区的边缘地带。最迟自15世纪起,四川西北部的嘉绒地区已处于苯教势力的控制下,苯教信仰在当地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活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小金川地区又是整个嘉绒地区苯教信仰的中心,明清时期,当地的政治制度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土司不仅是苯教的虔诚信徒,同时也是拥有很高地位的修行者,土司家族兼有世俗与宗教的双重权威。由于苯教具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特点,兼之嘉绒地区群山环抱的地缘环境,嘉绒先民普遍崇奉山神。据清代道光年间《绥靖屯志》所载风俗,每年“正月,各处番夷沿山而行,随行随拜,名曰转经”,*潘时彤主纂、蔡仁政校释:《绥靖屯志》,金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2001年,第221页。即是当地山神崇拜的表现之一。1940年代,马长寿在对两金川地区(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小金两县)的民族、宗教作实地考察后称:“在嘉戎区有所谓‘共伯’,道坞区有所谓‘奥外’者,均信奉本教神祗之一派,……除奉本教之神祗外,兼奉各地之山神,与羌民端公,罗夷毕母所奉旨地方山神性质相同。”*马长寿:《钵教源流》,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张原在阐释嘉绒地区的“山神崇拜”现象时说:“嘉绒人的神山既是世俗的,也是神圣的,最重要的这些神山是历史的、开放的。它们是嘉绒人的宇宙图式、社会意识、文化观念和历史心态的现实集合体,也是演绎各种人物命运和事件的具体场域。”而在嘉绒人苯教化的世界观中,“这些圣山本身就是宇宙之中轴、世界之中心”。*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3、9页。无论嘉绒神山是否如张原所说在嘉绒人的历史中占据如此神圣与重要的位置,但山神崇拜是当地苯教信仰体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嘉绒地区的众多神山中,两金川地区的墨尔多神山最为重要,居于中心地位。当地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称:在很古以前,藏区的各大山神发起召开一次群神大会,以讲经说法、比试武艺来定座次。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讲经答辩,九九八十一天的比武激战,来自东方的墨尔多山神压倒以喜马拉雅、冈底斯为首的众多山神,登上了首席的位置。这一传说充分展现了嘉绒人对山的自然崇拜及墨尔多神山在当地的地位。参见《嘉绒民俗志·山神崇拜》,转自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第291页。
正因为此,当清廷凭借军事力量碾碎大、小金川土司的统治,并按照自身设想重建当地秩序,将此“化外之地”广受崇奉的墨尔多、甲索、索乌等“神山”列入国家祀典,春秋致祭,这一举动背后的意蕴与象征自非中原地区的例行祀典可比,其特殊性及影响亦值得深入探讨。目前学界关于第二次金川战役善后事宜的研究为数不少,但既有研究大都偏重于安设营讯、改土归流、设置成都将军以及其他开发和经营两金川地区的具体措施,即使涉及宗教部分,也仅囿于“废苯兴黄”的各项举措。*有关第二次金川战役善后措施的研究主要有曾唯一:《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6期;潘洪刚:《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之兴起》,《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5期;潘洪刚:《清代乾隆朝两金川改土归屯考》,《民族研究》1988年6期;李涛:《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中国藏学》1993年第1期;徐怀宝:《清代金川改土为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5期;彭陟焱:《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西藏研究》2003年1期;徐建军:《试论清代乾隆年间嘉绒藏族地区改土为屯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年。以笔者目力所及,未见有人提及两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相关的内容,这一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即尝试就两金川地区官主山川祭祀兴起的大致过程、特点与影响做一初步探讨。
一、清军的困境:“邪术”与极端天气
据李大海《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一文统计,在平准平回战役中,乾隆帝曾七次遣官举行山川祭祀仪式,主要目的是“祈获上天之佑,以得平定新疆战事之胜”。*李大海:《清代新疆地区官主山川祭祀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1期。第二次金川战役期间,乾隆皇帝也多次谕令前线将领,“凡遇所过大山,务当竭诚祷祀,冀山神之默为相佑,利我军行”。*《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但祭祀山川的原因不仅仅是出于对胜利的祈求,同时还涉及当地的气候与宗教。
在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1747—1749)与第二次金川战役初始之时,清廷对两金川地区的宗教情况了解有限,*王罗杰认为,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乾隆君臣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两金川地区存在着喇嘛教信仰。参见Roger Greatrex,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rst Jinchuan War,” in Alex McKay, ed., The History Of Tibet,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Press, 2003,p.615.乾隆帝与前线将领可能并不清楚(也不关心)金川地区盛行的苯教信仰与山神崇拜。*实际上,清廷正是在战争中丰富了对金川地区的各种认识,对当地宗教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此点当另文详论。直到当地出现的异常气候极大地阻碍了清军的军事行动,君臣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乾隆三十七年(1772)春,温福、阿桂、丰升额等西路军将领过巴郎拉抵达资哩,途中每日有疾风暴雨,倏来倏去。五月“已交夏令,而北山之营盘连日雷电交作,继以大雪积至盈尺”。*《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丙辰条。南路军于四月进攻小金川果州一带山沟时同样遭遇连日雨雪,乾隆皇帝因素知“红教”喇嘛中有善于呼风唤雨者,*须特别注意的是,清代史料中出现的“红教”一词,大都非如今日所指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俗称,而是一个与“黄教”相对,意涵较为模糊的词汇。其指涉的大致范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以外的所有教派,且带有明显的异端意味。详见徐法言:《清代文献中的红教释义》,待刊。而满人信奉的萨满教中亦有“扎荅”求雨的巫术,*参见萧兵:《灵石崇拜和祈雨巫术——兼谈萨满教的札达仪》,《民族艺术》1997年3期。故断言“此必贼番扎荅所致,其法在番地山中用之颇效”,因而“派善用扎荅之三济扎卜、萨哈尔索丕二人,令翼长富瑚章京扎勒桑带领驰驿分往温福、桂林军营备用。该处番人及红教喇嘛内多有习其术者,著温福、桂林留心访觅精通扎荅之人,随营听用,使贼番技无所施”。与此同时,他又提醒各处领军将领,“此等邪术不过欲使人怖畏。人若见而生怯,则其术愈逞,惟能处以镇定,视之淡然,其技穷而法亦不灵,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对于乾隆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应对之法,主帅温福覆奏称:“至时当盛夏,而连日大雪抑或雷电冰雹,倏忽交加,虽系贼番扎荅所致,但官兵经历既多,绝无恐怖退阻之心,诚如圣谕,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而南路军主将桂林虽然对自四月初旬以来雨雪交加昼夜不停的情形“愤懑之中尤深焦急”,但他对异常天气即系“贼番扎荅所致”并不轻信,奏言曾“察看云气所布,极为广远”,“若系贼番诡施扎答,似不能绵密如此”。*《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丙辰条;卷二十七,乾隆三十七年四月甲午条;卷三十一,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庚辰条;卷二十九,乾隆三十七年五月癸丑条。
即便清军主帅能够对扎荅、巫术见怪不怪,熟视无睹,然而极端天气对普通将弁在行军打仗过程中造成的实际困难与心理影响却难以避免。同年七月下旬,“官兵因风雪雨雹,气候寒冷,将已得之甲尔木山梁,退回不守”,乾隆帝闻讯后大为不解:“现今七月下旬,即使雨雹交作,何至顿感寒暄?”故而斥责“绿营恇怯,架词撤退”,领兵将领明亮、乌尔图纳逊等“军令废弛”,未能鼓励戎行。*《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戊寅条。已得之地退回不守,这或许可以归咎为将弁的无能,但是之前官方曾宣称恶劣的天气乃“扎荅”所致,亦非明智之举,这相当于公开承认了两金川地区的喇嘛拥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结果可能反而令清军军心动摇,士气低落。乾隆帝对此有所警醒,乾隆三十八年五月,清军围攻大金川昔岭山梁,有小金川降人阿忠透露,昔岭有噶拉依、勒乌围两处喇嘛共一千多人帮同打仗,又有许多喇嘛在噶拉依寺里每日念经诅咒官兵。乾隆帝担心此类消息会导致军营恐慌,因而谕令前线将领,若官兵已有所闻,则应当明白告示,“所谓邪不胜正,惟当各持定见,不以么靡外道为意,其术自无所施”;“若无所闻,嗣后遇有此等供词但密存之,勿令营中传说致惑众听”。*《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六十一,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丁酉条。此道谕旨尚未送达前线,清军已在木果木遭遇惨败(六月初),木果木大营失陷,主帅温福战死,大板昭、底木达、登春等大金川各处,由北至南,清军全线崩溃。时在军中的将领明亮曾将当日所见兵溃情形详告礼亲王昭梿,称:“师遂大溃,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索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吾方结营美诺,见溃兵如蚁,往来山岭间。吾遣人止之,……兵方安眠,适有持铜匜沃水者,误落于地,有声铿然,溃兵即惊曰‘追者至矣!’因群起东走,势不可遏,其丧胆也若此。”*昭梿:《啸亭杂录·木果木之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7页。昭梿的记载与绥靖屯务李心衡在金川当地听到的传闻基本一致,*参见李心衡:《金川琐记·三官桥》,蔡仁政等校注,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编印,1998年,第319页。可见当时清军的军心、士气低落到何种程度。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喇嘛的“诅咒”是导致清军惨败的原因之一,但清军士兵在战斗中一触即溃、失魂丧胆的糟糕表现,恐怕多少与两金川喇嘛的“邪术”引发的恐慌有关。
木果木战役后,如何应对两金川喇嘛的“邪术”成为乾隆皇帝必须面对的难题。正如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的分析,无论乾隆帝自己是否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军队是否惧怕“邪术”的侵害。*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Press, 2006, p.57.继任清军统帅阿桂就目睹了清军士卒于夏日雨雪中攻碉的艰难情形:“此番自春入夏,雨雪连绵者七天,特晴雨原为我与贼公共之事,而此间攻守异势,贼人于碉卡之内,安坐据守,不忧雨雪,我兵攀林踰石,涉险冲泥,劳逸迥异,且雨中登涉所有火药火绳火箭一经沾湿,即难应用,所以于攻取之势,筹办颇多费手。”*《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七,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条。而恶劣气候不仅阻碍了前线的军事行动,亦对后方的后勤运输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一直负责粮草调度的钦差大臣刘秉恬曾奏言,两金川之地“连日风雪交作,人夫背运维艰,过山之米比前减少,每日仅有一二百石。最多不过三四百石”,刘氏每思“有数日晴和必得乘时加数赶运”,无奈“人夫因背米过山,冒寒疾病者甚多,而逃亡者亦不少”,“运粮人夫每有冒寒成病并失足跌伤者,即如梭洛柏古番民较之内地民人最为耐寒且善于登山”,亦时有跌伤、跌毙者。*《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〇八,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寅条。进攻受挫兼军粮时有不济,故清军将士常常被迫困坐雨雪之中,冻馁交加。*早在第一次金川战役期间,在四川地区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李安德就曾在成都亲眼目睹许多为严寒冻掉手指脚趾的清军士兵由金川前线返回,可见当地的严酷气候必然对清军士兵造成严重的生理与心理创伤。参见“Andreas Ly on the First Jinchuan War in Western Sichuan (1747-1749),” Translated by Robert Entenmann,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997, No.19, p.10.
一直随军“进剿”的吏部主事王昶以纪事诗的形式记录了他在前线军营经历夏日飞雪时的诡异情景:“一声两声雷迅烈,千片万片雪飘瞥。紫点如虹数道来,乌云黑雾时明灭。空际惟闻风啸号,眼前忽失峰凹凸。岂惟庐帐俱簸扬,直恐营墙旋毁裂。”而对于眼前的可怖景象,王昶显然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能归之于“怪事荒唐夙未经,妖神鬼伯争奇谲”,军营更是陷入慌乱之中,“万马群嘶尾鬃卷,千夫瘁噤旗枪折。仓皇相叩此何时”,士兵们缺衣少粮,“炎天顿觉殊寒热,减灶几无餐可传,燎衣犹仗柴堪爇”,处境艰难。翌日,大雪仍未停息,“暑已当三伏,寒终凝六花。希声仍飒飒,空色尚斜斜”,军心显然已受影响,“敢怨龙公虐,长教虎士嗟”,满营将士惟有“拥炉如饯岁,满幕是霜华”。*王昶:《六月初二日雷雪》《六月初三日雪》,《金川纪事诗》,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上),第424页。王昶的诗或许存在艺术的夸张与想象,但其中所表现的极端天气对清军造成的困惑与影响应是他真实的感受。
面对两金川地区严酷怪异的气候,乾隆皇帝与清军上层始终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大金川降人供称,大金川喇嘛“每日念经咒阿将军、布拉克底、巴旺、革布什咱的人”,乾隆皇帝随即传谕阿桂曰:“番俗虽以念经咒人为事,究系邪术,但须持定此心,勿稍疑惧,则邪法断不能侵损,其术自无所施。所谓邪不胜正及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之说也。阿桂素颇明理,切不可稍为浮言所惑。至其咒布拉克底、巴旺之语,尤不可令其土司及土兵等闻知。”*冯明珠、庄吉发主编:《金川档》,第二册,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初四日上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7年,第1537页。可见当时清廷应对“邪术”仍然不过是隐匿不告与“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二法。次年六月,乾隆帝得闻“番地”尚然下雪,再次重申称:“虽番地气候异常,亦不应乖舛若此,似系贼人扎达所为,但扎达本非正道,只须众人不以为事,法即不灵,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灭,亦邪不胜正之定理也。”乾隆本意或许是想令营中将领兵弁,“皆明于正理而不感于怪异,其技自无所施”,*《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七,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条。然而他一再强调“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这一掩耳盗铃的应对举措本身就反映出他自身对于“邪术”抱持游移不定、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其结果可能反而令前线将士更生疑虑,军心浮动。乾隆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应该不会不知此举背后不合常理乃至荒诞之处,他之所以再三强调荒诞之事,除了说明别无他法外,*乾隆帝曾数次派遣善用扎荅者往前线军营祈晴,可能还向章嘉活佛寻求帮助,据说后者曾多次施法破除两金川喇嘛的“邪术”,不过效果甚微。参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269页。也确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其所思所虑并不限于军事一维,“异常天气”所带来的危险也绝不囿于军事层面,天有异象可能造成的“舆论”困境,令其陷入左右两难的局面中。下文将详论之。
二、“山神”的抉择:“代天司化”抑或“甘为邪术驱遣”
乾隆年间的两次金川战役以持续时间长、耗费巨大而闻名于世,同时也以其投入大、成效小而广受世人诟病。清末学者王先谦曾将平定两金川与平准平回战役相提并论,并高度评价云:“高宗皇帝仰绍诒谋,以育以正,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扰,保世恢基,其极于外。”*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二《东华录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5页。此语难免夸饰之嫌,无论以当时或今日的眼光审视,平准平回与平定两金川功之大小,意义之轻重,有如云壤之别。实际上,在最初商议出兵大、小金川之时,朝臣们就大都持反对意见。乾隆帝自称“力排浮议,天断独行”,*《御制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条。阿桂也说:“金川贼人以内地土司悖恩反噬,此其罪大恶极,不可不灭。惟臣知之最真,故必期殄灭之心亦惟臣守之独力。”*《平定两金川方略》,卷八十六,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壬申条。可见赞同用兵者极少。据《清史稿》载,“方金川用兵”,汉人大学士刘统勋“屡议撤兵”,直到“木果木军覆”,刘统勋才改变看法,认为“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清史稿》卷三〇一《刘统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467页。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也说“刘统勋前言金川不必劳帅”,木果木兵败,“至是则亦以兵不可罢”。参见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5页。乾隆帝在战役期间屡降谕旨,反复申明其“用兵不得已之苦衷”,“并非好为穷兵黩武也”。*《清高宗实录》,卷九一三,乾隆三十七年七月丁巳条。直到战役结束五年后,他仍在《平定两金川方略》的序言中感叹:“呜呼,定方略岂易言而成方略更难睹也!今幸睹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废寝之劳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后世穷兵黩武之讥。”*《御制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七,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壬寅条。这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舆论对金川用兵一事存有不少非议。
时人对第二次金川战役究竟有何议论,史料中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清人赵翼在《平定两金川述略》中说:“两金川地,较之准夷回部,曾不及十之一,攻五年而后得之,勋伐似未足侈述,……或者谓蕞尔小丑,不妨度外置之,殊不屑耗国帑兵力于此不毛地。抑知彼既隶我戎索,自难坐视其跳梁。而番夷之性,但畏威,不怀德,……乘国家全盛之力,兵少增兵,饷少增饷,卒草剃禽狝,不遗孽,自此西南陲可千百年无事,此正一劳永逸之长计,而岂小见懦识所能仰窥万一哉?”*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四《平定两金川述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33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47页。赵翼意在批评反对用兵者见识短小,却可依此推断反对者仍是以“王者不治夷狄,不臣要荒”的儒家传统观念为依据,认为不应将国帑兵力虚掷于“化外之地”。对滇省历史颇有研究的清代学者倪蜕曾论及治边之法,称对边外土司,“仍须羁縻系属,不宜轻有更改,亦非谓其尾大不掉而虞之也。特以地居荒远,瘴疠特甚,设流官不谙风土,立防兵难免瘴病,运粮米又恐劳民。即其渠帅而用之,此固诸葛武侯经营简易之宏模也”。*倪蜕:《土官说》,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六《兵政十七·蛮防上》,《魏源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685页。倪论虽针对“滇夷”而发,但其中包含的治边理念及对土司制度的认识并不囿于滇省一隅,正符合“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71页。之古义,应是当时士人共有的认知。
乾隆皇帝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对于上述儒家观念应是谙习于心。他在金川用兵一事上乾纲独断,一意孤行,必然要承受由此造成的反对和非议之声。而消除质疑最好的办法是在战争中迅速取胜,乾隆皇帝在两次金川战役中时常流露出的急躁情绪,或许就与此相关。无奈第二次金川战役旷日持久,劳师糜饷,清军不仅难以速胜,更屡受挫败,甚至在木果木遭遇耻辱性的大溃败,这已足以令他陷入“舆论”的困境中。木果木兵败后,乾隆帝连续下发长篇谕旨,申明其不得已用兵之苦心,称:“军机大臣日在朕左右承旨,皆所深知,且屡经宣谕再三,谅亦人所共晓。若谓朕饰词愚众,吾谁欺?欺天呼?”说明他始终面临“舆论”的压力,需要不断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乾隆三十八年丁卯条。而两金川地区年复一年的异常天气更是雪上加霜,不断地触动其内心隐忧。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阿桂、丰升额、色布腾巴尔珠尔带兵进攻大金川谷噶,自初五日起,“雨雪大作,日夜连绵”,本就陡峭的岩壁更加湿滑,道路泥泞不堪,清军无法前进,大金川民众乘机在雨雾中添建新碉。阿桂等“焦切愈深,而官兵亦靡不愤急”。*《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乾隆帝接报后,亦深感愤懑,在发给阿桂的上谕中,他透露出内心的忧虑:
从前曾谕阿桂等凡遇所过大山,务当竭诚祷祀,冀山神之默为相佑,利我军行。且以金川用兵情事而论,朕实本无欲办之心,乃逆酋索诺木等敢于负恩反噬,罪恶贯盈,又有不得不办之势,并非朕黩武穷兵,是曲在贼而直在我,应邀上天照鉴,自必嘉佑官军而潜禠逆酋之魄。至所在山神代天司化,亦当助顺锄逆,上体穹苍(之)心,若非雨雪因贼扎达所为,岂有正神以听贼人趋使为此背理妄行之事?况将军等既已虔祷而不应,即属邪氛,从来邪不胜正,或于雨雪来处用大炮迎击,如韩愈之驱鳄鱼亦属正理,着阿桂斟酌行之。*《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九十六,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丁亥条。
此则上谕表明,乾隆帝对异常天气的担忧绝不仅仅停留在军事层面。在他看来,两金川地区出现反常天气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两金川喇嘛“扎达所为”,“即属邪氛”;另一种则来自于天意,是当地山神“代天司化”所为。自汉代董仲舒将天人感应说及灾异说相结合引入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一理论就对之后历代的政治生活及民间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人相信天人相通,相互感应,人的所作所为与上天意志紧密联系,会直接导致祥瑞或灾异的发生。假如德行有亏,上天就会通过灾异降下警告或者惩罚。这一点对帝王尤为重要,天有异象往往被视为天子失德的征兆。如果两金川的“山神”是“代天司化”,那么恶劣反常的天气就可以解释为上天对乾隆皇帝“穷兵黩武”“轻启兵衅”的警示,从而对两金川用兵的正当性、甚至清帝统治的合法性构成质疑。乾隆皇帝临御数十载,不会不知其中的利害轻重。他在上谕中辩解称对金川用兵有不得不办之势,并非其黩武穷兵,“是曲在贼而直在我,应邀上天照鉴”,然而这番说辞颇为无力,战场形势已证明上天并未护佑清军,“岂有正神以听贼人趋使为此背理妄行之事”一语恰恰反应出他内心的疑虑。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阐释了清廷在面对民间超自然力量时的两难处境:“国家与妖术对抗时目标模糊不清的情形,反映了它在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上的立场暧昧不明。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种种联系。它有着自己的天地崇拜,并在为自然神灵归类的同时,也为那些已被融入自身宗教体系的民间神灵归类。国家一直通过宫廷星相家从事着解读天象活动。因此,国家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实。另一方面,国家若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那就只能意味着它承认了它们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从而会大大提高它们的地位。”*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20页。清廷在金川遇到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若承认异常的天气为“扎荅”所致,则意味着承认了苯教巫士“同神灵世界存在着有效联系”,这可能导致清军士兵在战斗中心怀畏惧;若断然否定,那么“夏日飞雪”的反常天气是否意味着上天的警示?这就令乾隆帝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如前文所述,每当清军面对金川喇嘛“邪术”侵害时,乾隆帝总是表现得模棱两可,游移不定,症结或许就在于此。
无论是“邪术”抑或“天意”,根本的解决之道最终要寄望于战争的胜败。清军自木果木惨败后,新任主帅阿桂殚精竭虑,整顿军务,屡屡奏请增兵添饷,清军军势很快复振。乾隆三十八年十月,阿桂兵分三路进攻小金川,仅用十日即克复全境。之后步步为营,节节向大金川腹地勒乌围官寨逼近。战场形势的逆转让乾隆皇帝有了更多的底气,因而在谕旨末尾,他明确表示两金川地区的雨雪“即属邪氛,从来邪不胜正,或于雨雪来处用大炮迎击”,令阿桂斟酌行之。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明亮一路进攻木克什山腿两碉,正当紧要之时,“猛雨大作,斜坡陡路,其滑如油,索伦吉林兵丁略一举步,即全身溜跌不能自主”,明亮只能将士兵撤回。乾隆帝得报后降谕曰:
明亮等奏进攻木克什山腿两碉正当围裹紧要之时,雨风大作,甚为可恨,看此情形贼中必有善用扎荅者,但此等究属邪法,不能胜正,将军等总以镇静处之,并晓谕将佐弁兵不必视以为事,其术自然无所施,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若风雨之故由山神所为,亦属非理,朕奉天承运,为天下共主,兹以金川逆酋负恩反噬,罪大恶极,为覆载所不容,不得已命将申讨,师直而理正,且所至之地谕令将军等致祭祈赛,山神有知,自应效灵助顺,早佑蒇功以膺国家秩祀,若转袒护逆酋,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即属违理悖常,必干天谴。昔韩愈以一州刺史尚能正辞发弩驱除鳄鱼,矧将军奉天子命征剿不庭,岂山神所得而相抗乎?将军等适遇非时雨雪,即当视其来处用火炮迎击,纵有邪魔亦当退却,此亦代天宣化之正道也。*《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一〇五,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申条。
乾隆帝认为他奉承天命,为天下共主,征讨金川“师直而理正”,“且所至之地谕令将军等致祭祈赛,山神有知,自应效灵助顺”,因而金川地区的异常天气不应是山神所为。但对于两金川喇嘛与当地山川神灵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他亦不再回避,而是态度强硬地宣称,若山神袒护金川,“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不仅不能体现上天的意志,且“属违理悖常,必干天谴”,清军将领即可“代天宣化”,视雨雪来处用火炮迎击。
第二次金川战役末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头人、喇嘛为清军俘获,更多金川喇嘛施放“邪术”的细节为清廷知晓。*据喇嘛达固拉僧格供称,“会咒语的只有都甲、堪布两个喇嘛,听见说掠去的人就交与都甲喇嘛,问领兵的大人名字,记下念咒。所咒教人心里迷惑,打仗不得胜”,“至于下雪下雹子他们向来会咒的。又听得说他们会咒起雷来打人”,“又供索诺木教人起誓取下头发、指甲每人各封一小包,上面写了名字交给都甲喇嘛,盛在匣内。有那个逃走的就咒那一个”。参见冯明珠、庄吉发主编:《金川档》,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达固拉僧格供词,第五册,第3431页;堪布喇嘛色纳木甲木灿供词,第六册,第4413页;都甲喇嘛雍中泽旺供词,第六册,第4427页。而清廷既没有否认那些与之处于对抗地位的神灵存在的事实(视雨雪来处用火炮迎击),也不否认苯教喇嘛具有的神秘力量。因而在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置当地的苯教信仰与山川神灵便成为了清廷重建地方秩序的重要一环。
三、效灵助顺:沟通新、旧世界的桥梁
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乾隆皇帝认为苯教喇嘛传授咒语,呼风唤雨,诅咒官兵,斥其为“奔布尔邪教”,决意禁绝。他在向嘉绒各土司发布的诏书中说道:“至尔崇尚佛法,信奉喇嘛,原属番人旧俗,但果能秉承黄教,诵习经典,皈依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修持行善,为众生祈福,自无不可。若奔布喇嘛传习咒语,暗地诅人,本属邪术,为上天所不容。”*《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四,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庚辰条。之后,在清廷“兴黄灭苯”的政策下,大、小金川的苯教喇嘛被全部驱逐,代以格鲁派僧众。嘉绒地区最大的苯教寺院雍仲拉顶寺被改为格鲁派寺院,更名为“广法寺”,乾隆帝还亲书“正教恒宣”四字匾额悬挂于大殿之中。张原认为,清廷此举“将苯教从嘉绒地方政治中剥离,并用格鲁派取代之,这是在嘉绒王与巫合流的地方王权传统之基础上,对嘉绒地方政治制度进行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20页。
此外,两金川地区最为有名的神山也被纳入国家祀典之中。乾隆四十二年,乾隆皇帝降谕曰:
昨岁平定两金川大功告蒇,且地已归入版图,安屯耕种。所有该处名山大川效灵助顺,自因列入祀典。曾降旨令明亮等查奏。今据奏复,金川之索乌、甲索二山及小金川之墨尔多山,均为番众所敬。大军进剿时亦硕著灵应等语。又金川大河当官兵攻剿勒乌围时立栅沿河坚持数日。时值阴雨连绵河水旋长旋消,于沿滩栅寨并无妨碍,及功得勒乌围,官兵移栅后,河水即陡然涨发,前立栅之处均浸水甚大。河神效顺实□成功,均应春秋秩祀,以彰武功之义,著载入祀典,用垂久远。所有撰文及一切礼仪交各衙门照例办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成都将军明亮、四川总督文绶咨明于金川致祭山川事,档卷号0301-054,缩微号020-1261;《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礼部一五四·群祀》,乾隆四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13年,第7页。
首先确定了纳入国家春秋秩祀的对象是大金川的索乌、甲索二山,小金川的墨尔多山以及大金川河四处。
初次祭祀的时间定于乾隆四十三年夏,翰林院撰拟祭文后,由乾隆帝遣官致祭,同时还规定了祭品、仪注、祭文、祭祀费用等。仪式过程较为复杂。首先祭品有牛、羊、豕、鹿脯、榛菱、白饼、黑饼等二十余种,祭祀当天陈设完毕后,由赞引官引承祭官至盥洗所盥洗,执事者各就其位,由典仪引神,承祭官在香炉前上香,并与陪祭官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后由捧帛者祭帛行初献礼,三叩头,再由执爵者献爵于案上正中。接着读祝者至祝案前,一跪三叩头,承祭官与陪祭官俱跪,宣读祝文,读毕,再依次行亚献礼与终献礼。礼毕后,由典仪送神,承祭官、陪祭官等行三跪九叩头礼,捧祝帛者诣祝帛至燎炉,最后承祭官至燎所,焚“祝帛过半”,整个祭祀仪式才告结束。*潘时彤主纂、蔡仁政校释:《绥靖屯志》卷五《仪注》,第95页。仪式中的典仪、赞引、读祝官等皆由川省地方官员充任,地方正印礼生充执事官,州县佐二官以下俱应陪祭。繁复的祭祀典礼须在墨尔多山、索乌山、甲索山及大金川河分别举行,此后每年的春秋二季(二、八月)地方官都照此循办,成为定规,直到民国初年废止。
尽管山川祭祀一直是国家礼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内地并不鲜见,然而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显然又有着不同的意义。透过复杂的祭祀仪式,清廷将两金川苯教化的“神山”纳入到国家祭祀体系当中,虽然乾隆帝难以找到一个事例证明两金川山神曾助佑清军,但随着苯教喇嘛被放逐,这些地方神灵失去了与昔日世界的联系,有关它们在战争过程中“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之事也被刻意遗忘,重新塑以“效灵助顺”的新形象。
清廷在两金川地区建立起新的制度与秩序,然而制度与现实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卫周安就注意到,乾隆皇帝试图在金川地区消灭苯教的努力未竟全功,或许这并非其本意。在持续了六年(五年)耗费巨大的战争后才取得对金川地区的控制权,皇帝不太可能拱手交予达赖喇嘛。他更倾向于将苯教作为在这一地区制衡黄教的力量。*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p.62.无论卫周安的推论是否合理,苯教并未就此禁绝确是实情。有不少学者提到,“兴黄灭苯”后,在嘉绒地区的寺庙里曾出现佛、苯神像同时供奉,一庙住两教僧人,各念各经文的特殊景象,甚至在已被改宗为黄教的雍仲拉顶寺旁边修建了一座小型的苯教寺院,以满足当地百姓的苯教信仰,这种两教共存一地的情况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两寺被毁为止。*参见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齐德瞬、王力:《论金川之役与金川地区的社会变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24页。这一奇特的景象说明嘉绒地区的佛苯对立远非人们想象般严重。*实际上,在第二次金川战役爆发前,金川的土司、百姓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政治、宗教上早有长期、频繁的交流,双方关系密切。当地民众对格鲁派、达赖喇嘛抱有敬意,而且由于佛苯融合,两种宗教在表现形式上有诸多相近之处,普通人恐怕根本难以准确地区分二者。详见徐法言:《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3期。此外,清廷的统治策略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其说乾隆皇帝有计划、有预谋地保留苯教作为制衡黄教的力量,毋宁说其根本无意在新征服地区实行严密的统治,仅维持一种较为松散的秩序,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地方的稳定与安宁才是清廷追求的目标。以笔者目力所见,除了善后处置时清廷对两金川地区的苯教巫士采取了严厉的惩治手段,之后百余年的统治中,几乎找不到一件当地流官与驻军以行政手段或军事力量干涉当地宗教事务、禁绝苯教的案例。乾隆年间曾任绥靖屯第四任屯务的李心衡在《金川琐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在两金川所见风土人情,书中许多记载都反映出苯教信仰在当地民众生活中仍有着巨大影响,然而李心衡既无力分辨孰佛孰苯,更无意干涉土著生活,其置身事外的做法在流官群体中相当普遍。或许正是这样宽松的氛围,使得佛、苯在当地社会能够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最终走上了一条共生共存之路。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山神崇拜与山川祭祀上。清廷将当地的名山大川纳入国家祀典,春秋致祭,藉此表达一种将征服之地纳入到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业已建立的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政治意义。然而清廷从未禁止“番众”以自身传统方式礼拜神山(转山、煨桑、风马旗、玛尼堆等)。每岁春秋,当地方官员代表清廷在墨尔多山脚下举行隆重而复杂的祭祀仪式时,嘉绒各地的土著也正“不惮千里”前来朝拜其心目中的圣山。*李心衡:《金川琐记·玉筍峰》,第153页。络绎不绝的朝山者与祭祀官员在途中相遇,意味着两种传统在此神圣场域中发生了叠合。*实际上远不止两种传统的碰撞与融合,还应考虑到满洲原有的萨满信仰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的“山神崇拜”可能造成的影响,此处难以展开,当另文探讨。双方未必清楚对方行为仪式中所蕴含的全部意义,祈求的目标可能也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彼此在错位的想象中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清朝官方是一种政治表达,类似于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宣示”;而对于嘉绒土著则是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转山即亿万遍的颂读佛经,是信徒往生佛国净土过程中的修行。一座神山,各自表述。或许正是这一模糊契合点的存在,给双方留下了缓冲地带,从而不仅有效地稳定了战后地方秩序,促进了清廷改土归流措施的顺利实施,更使得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有了达成共识,相互认同的空间和可能。而嘉绒“神山”在此成为沟通双方的桥梁,对于中原王朝的“效灵助顺”使得地方神明获得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同时皇权也藉此与嘉绒地方社会建立起更加紧密、有效的联系,其在当地的正统性与神圣性也得以不断强化(与军事力量相辅相成)。
时至今日,金川与小金县的各处大山之间,风马旗、玛尼堆与山神庙、山王庙共存的景象随处可见,两种传统在这片土地上早已相互融合,难分彼此。在两金川地区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西方有一个山神,他有四个又美丽又能干的姑娘。这四个姐妹不管做啥子都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人们称她们“四姑娘”。她们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直到有一天,跟她们相邻的一位叫麦尔都的山神找上门来,要跟四姑娘的爸爸比武艺和道法,并且约定谁输了,就得交出所有领地,还必须规规矩矩给对方当奴隶。四姑娘的爸爸被迫与之交手,最后由于年老体弱,战败而死。麦尔都占领了他的所有领地,还要把四姑娘抢去作他的妻妾。
四姑娘都是有骨气的姑娘,不肯做杀父仇人的妻妾。当天晚上便悄悄逃走,她们要到京城向皇帝告状,请皇帝派兵帮助她们收复领土,重建家园。一天,她们来到小金川的日隆关,天已经快黑了,四个姑娘不愿在街上歇店,怕人多走漏了风声,只好继续赶路。她们顺着长坪沟往北走去。进沟走了许久,天完全黑下来了。又碰上了暴风雪,她们迷路了,最后全部冻死在长坪沟的尽头。好心的人们将她们埋了。后来,这四姊妹的坟堆化成了四座山峰,这就是四姑娘山。*节选自《四姑娘山的传说》,《小金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张清海主编:《金川历史文化览略》(中),第418页。
这个故事最早或出自汉人移民之口,“四姑娘”很可能是嘉绒语“斯古拉”(sku bla)的汉语音译,但其中所反映的皇权在此地区具有的力量与威望不应全然是虚构与想象。故事中,皇帝不仅能够介入山神间的纷争,也有能力帮助“四姑娘”收复领土,重建家园。从中或可窥见,在金川王与巫的神圣性为皇权所摄取、地方的失序与空虚为皇权所弥补的过程中,嘉绒地方权力结构及嘉绒人观念与认同的转变。
另一个能够表现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关系变化的事例是嘉绒地方的屯练、土兵屡受清廷调遣,为清帝效力。乾隆四十六年回民之乱、乾隆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之乱及廓尔喀之役、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金川战役结束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嘉绒屯练、土兵在清王朝广袤的疆域上八方征战,战功彪炳,逐步从之前嘉绒土司手中的地方“私人武装”转变为清王朝控制下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参见彭陟炎:《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4年,第94-95页;陈小强:《金川之乱后清军中的藏族将领》,《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随同嘉绒士兵一起扬威四方的还有嘉绒人的神山。今日嘉绒地区仍流传着许多战争中墨尔多山神显灵的故事,今取其中两则略述如下:
传说一:清代,廓尔喀入侵西藏,达赖要皇帝派嘉绒兵援助。嘉绒兵与廓尔喀经数百战斗,难决胜负。在弹尽粮绝之时,所有嘉绒官兵都面向家乡,向墨尔多山神祈祷,求山神显灵救助。云雾中墨尔多骑着骡子,头戴毡帽,背枪舞剑来到占城,从怀中取出禳袋,撒下千军万马,助嘉绒兵得胜而归。
传说二:嘉绒瓦寺土司奉道光皇帝命去浙江一带抵抗英国人入侵,在与英军角逐过程中嘉绒士兵损失惨烈。这时墨尔多山神显灵来到东海上空,施大风助嘉绒官兵收复了定海、舟山等地。*转引自张原:《“大自在天的传奇”——墨尔多神山与嘉绒人的政治文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7辑,第13页。
这些传说所讲诉的都是墨尔多山神与嘉绒人为清廷四处征战,抗击外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嘉绒地方与中原王朝现实关系的展现。藉由与皇权的结合,墨尔多山神得以与嘉绒人一起四处征战,渐渐从一个地方性的保护神转变为一个显赫四方的大山神,继而在整个藏区获得了极高的声望。这也说明在新秩序下,两金川地区的“神山”仍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透过清朝官方的山川祭祀与嘉绒人的山神信仰,各处山神担负起沟通新、旧世界桥梁的角色,曾经“甘为邪术驱遣,妄行雨雪”肆意与清廷对抗的苯教神山,由此逐渐转变为嘉绒人拥护皇权、认同中原王朝的重要象征。
(此文写作过程中,曾提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部讨论会讨论,得到了王东杰、韦兵、粟品孝、周琳、郭书愚、王鹏辉等诸位师友的帮助与指点,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史云鹏)
The Jinchuan Campaig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Official Cul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in Jinchuan Areas
Xu Fayan
Mountain god worship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Bonpo faith in Jinchuan areas, and the Jiarong holy mountains, represented by “Moerduo” and “Jiasuo”, were widely worshipped by local people. During the second Jinchuan campaign in the Qianlong period, with the power of mountain god, the sorcerers of Bonpo controlled the weather and cursed the Qing army by chanting, and caused great inconvenience to military actions. As for whether the mountain did that on behalf of Heaven, or was controlled by black magic, Emperor Qianlong was caught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After the war, the Qing government integrated the worship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Bonpo into the state ritual system. As the sorcerers of Bonpo were exiled,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lost contact with the old world,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mountains were driven by black magic and snowed and rained unscrupulously was deliberately forgotten and replaced by a new image of “xiaoshunzhuling”, which turned int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Qing's reign and operation of Jiarong area.
the Jinchuan campaign, Bonismo, mountain god worship, cult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徐法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成都 610064)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中心第一批科研项目“康乾时期清廷对川藏边地的经营与治理”(sk2011xtcx-01qn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GT201204)、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zx2015-sb23)
K249
A
1006-0766(2017)02-00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