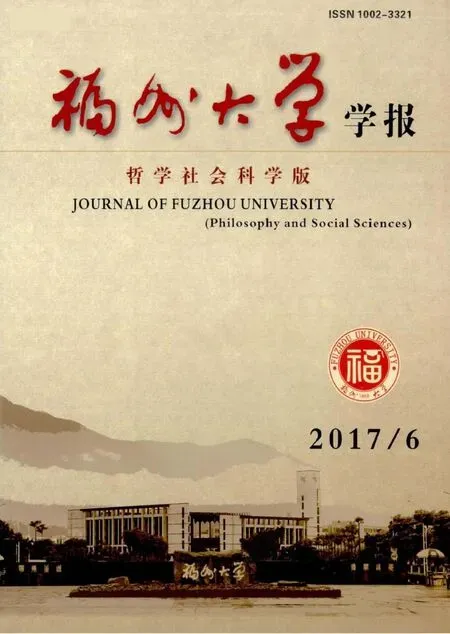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的欲望书写及其消解
庄超颖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张爱玲小说的欲望书写及其消解
庄超颖
(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张爱玲小说把对欲望的消解隐藏在欲望故事的书写之中。其小说不仅深入人性的阴暗面,记叙了种种欲望怎样操控着人们的意念和行为,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深刻揭示出种种欲望怎样导致了人生的苍凉和虚无。这就使其小说文本超越了故事层面,上升到哲思的高度,使其小说达到世俗和超越的统一,冷酷和悲悯的融合,也反映出创作主体对现实人生的彻悟。
欲望书写; 消解; 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创作的聚焦点主要是家庭,题材主要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世俗的家庭,自私的人们,为了金钱、利益、权力等等欲望而争斗、挣扎、沉沦,这就是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最常见的浮世悲欢。然而这只是故事层面。张爱玲小说的深刻和犀利是令人瞩目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这一个个欲望故事里,张爱玲所要揭示的深刻内涵是什么呢?“与其说《金锁记》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写照,不如说它是权力社会的一个哲学寓言……她通过这个寓言,无情地揭示,这个人间世界是一张被权力与金钱所摆布的丑恶的网,而人不过是一些网中挣扎的鱼和野兽,即被文明所包装又被欲望所驱使的两脚动物。”[1]这一论述真可谓力透纸背。但又何止是《金锁记》,张爱玲小说里塑造了许多“被欲望所驱使的两脚动物”,他们上演了一出出食人与自食的寓言,其原驱力就是:欲望。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的各种欲望不断升级,人也一步步蜕变为欲望的奴隶,被欲望奴役和绑架。人本该具有的精神的高贵、心灵的自由,在欲望的重压下日渐委顿,日渐消亡。人类特有的灵智变成只是用来满足种种欲望的资本,人被自己的欲望押进了心灵的牢狱。
细读张爱玲小说我们能够发现,张爱玲书写了一个个欲望故事,但是同时她又消解了这些欲望的意义,讥讽了这些欲望的徒然,最终还欲望以苍凉虚无的本色。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她为世人的欲望唱了一出出的“枉然记”,也使一个个欲望故事尽显“惘然”的底色,这是构成张爱玲小说世俗和超越的统一,冷酷和悲悯的融合的一个重要成因。
一、金钱欲望的书写和消解
金钱在人生中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必须以金钱为手段,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钱万万不能。“由于钱的应用范围太广,以至于很多人迷失了方向,误以为钱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2]尤其是当个体所拥有的钱少到难以维持某一社会历史时期的最低生活水平时,钱的作用就会被无限扩大,以至遮蔽了钱的实际意义,而成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甚或唯一目标。当然也有的人拥有的钱已经不少,也仍然把赚更多的钱当作人生的最大追求。金钱甚至会使人堕落、使人疯狂,使人铤而走险。莎士比亚早就尖锐揭露金钱的魔力:“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3]张爱玲也以其小说生动地表现一个个被金钱欲望驱使的故事,一个个被金钱扭曲的心灵。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也是最容易读解的。而另一个方面,读者却往往轻易地忽略了。那就是,张爱玲在叙写金钱欲望故事的同时,也似乎不经意地消解了金钱的欲望。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原本是一个伶俐健美、招人喜欢的麻油西施,“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4]可是为了钱,她却选择了做富贵大族姜家的二奶奶,尽管姜二爷是个患骨痨的残废人。为了守住以自己一生的痛苦换来的钱,她不惜把主动送上门来以情骗钱的姜三爷又打又骂轰了出去,割舍了唯一一次能够满足情欲的机会,并因此导致人性的完全扭曲。三十年来曹七巧忍受着性的压抑,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提防着周围的人,守着自己的钱。在临死的时候,“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5]这一推,推出了曹七巧一生的苍凉,推出了金银珠宝的虚无。曹七巧耗尽毕生心血换取的“贵重品”,此时对于骨瘦如柴、油枯灯尽的她,意义何在呢?张爱玲仅以这一推便彻底否定了曹七巧一生对金钱的苦心经营。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七巧流泪了,“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6]这是悔恨之泪、大悟之泪?可是已经于事无补,徒唤奈何。破落户葛家的小姐为了金钱,不惜以青春美貌嫁给香港数一数二的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成了梁季腾生前最得意的人儿,遗嘱上特别派了一大注现款给她,另还有房产。“梁太太是个精明人,一个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7]因此梁太太需要许多人的爱,有许许多多的情夫,而且不计年纪不计地位, 就像梁太太的婢女睇睇所说的:“乔家一门子老的小的,你都一手包办了,他家七少奶奶新添的小少爷,只怕你早下了定了。连汽车夫你都放不过。”[8]由于内心填不满的情欲饥荒,梁太太一辈子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诱惑男人、捕获男人、抓稳男人上面。还不惜在年轻姑娘身上下血本,以之为诱饵勾引年轻男子上门来,而后,“梁太太便横截里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9]甚至于与自己的婢女、侄女抢男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演出一幕幕的闹剧丑剧。为了金钱,梁太太一辈子过着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生活在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在小说里,张爱玲这样描绘梁府——“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一座大坟山”, “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10]梁府就是鬼域就是坟墓,是一座魔鬼出没的埋葬正常人生的坟堆,完全消解了金钱的欲望。
张爱玲以一个个捞金的故事记叙了曹七巧、梁太太们沉沦的历程,让她们痛苦无告、不堪回首的生活真相在房产地契、灯红酒绿中显现;让她们孤独苦涩、苍白恐怖的精神世界在鸦片烟、下午茶里蠢动。也让读者窥见煜煜发光的黄金背后狰狞的脸谱,听见叮当悦耳的珠宝背后无奈的呓语。于是,张爱玲撕扯下钱财梦幻的金色布幕,颠覆了金钱和幸福的等式关系,奉献给世人不可多得的金钱欲望的寓言。
二、自私欲望的书写和消解
“人的本性是自私,自私就是为自己。”[11]“人的自私性集中表现为逐利。利,就是一种好处。”[12]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必然有许许多多的需求,必然想得到许许多多的利益。人自然而然地首先会满足自我的需要,会先行考虑自己的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把人自私的本性提到与天地并存的亘古与恒久。张爱玲深谙人的自私本性,也写出了一个个表面看来不动声色,实际上惊心动魄的自私欲望的寓言。
《琉璃瓦》中的姚先生有七个美丽的女儿,在女儿的婚姻问题上,父亲只从自己的钱财和地位的利益去考虑,不曾想过女儿们的利益和感受。他精心盘算女儿们的婚姻,却屡屡失算,并因此病倒了,而且“活不长了”。女儿们也毫不考虑父亲的心思,而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喜好。大女儿琤琤为了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父亲的利益而嫁入夫家,甚至断然阻止公公对父亲的提携,结果却很快地遭遇丈夫的情变,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倒在父亲病床上哭诉。张爱玲讲述了一个世俗的故事,其实又将对世俗的自私和机心的消解隐藏于其中。《花凋》中的郑川嫦患了肺病,父亲愤愤于“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13]母亲则担心暴露私房钱,都不肯拿钱替川嫦治病,而把责任推给川嫦刚认识的男友,男友则结交了新女友,川嫦只好任凭肉体一天天瘦下去。受不了痛苦,川嫦想死,“她所要的死是诗意的,动人的死。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14]这使她想起了两句诗:“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15]多么辛酸苦涩的话语,道尽了人类自私唯我、趋利避害的共性。也道尽了川嫦临死之前看透人性、心寒彻骨、自伤自怜的悲戚。川嫦死了,“她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并且托人撰制了碑文:“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16]多么荒谬的自私,多么可笑的虚假,又是作者多么含蓄的反讽!为了顾及自己的利益,郑先生夫妇不把钱花在为女儿治病上,却把钱花在为女儿修坟上!显然,小说开头对坟和碑文的描述,已先行昭示出郑先生夫妇自私的虚无。《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各自怀着自私的盘算,上演顶文雅的恋爱游戏。白流苏要管住自己直至得到婚姻,得到一份经济的保障;范柳原则要让白流苏主动投入怀抱,而他不需负一点责任。白流苏处在无奈和尴尬中,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香港开战了,“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17]他们才定下心来,过起了“有一点真心”的生活。表面看来张爱玲书写了一个自私的故事,“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8]但她实际上书就了一个精彩的寓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也被种种自私的欲望所束缚,不肯付出真心。只有到了 “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19]的时候,私欲才轰然解体。 “因为作为世界主体的人是自私的,他们被无穷尽的欲望所控制,这种欲望导致了人性的崩塌和爱的失落。只有到了‘地老天荒’、世界走到末日的时候,欲望才会与世界同归于尽,人才可能重新发现爱和复活天性中的真诚。”[20]张爱玲以其特有的犀利和深刻,宣告了自私的破灭,消解了自私的意义。
三、权力欲望的书写和消解
“权力是被依赖的人对于依赖者所具有的一种有效的影响力或驱动力,这是因为依赖者需要被依赖者手中的某种资源或者依赖者所需要的东西。”[21]被依赖者因为掌握着依赖者所需要的某种资源或东西,也就实际拥有对对方的控制力,可以居高临下地将自己的意愿施加予对方,在对方的身上得到实现,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到驱使他人实现自己的意愿的快感。而依赖者由于自我的需求,由于对被依赖者的恐惧,而受制于被依赖者,听命于被依赖者,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感到自卑、委屈、压抑、不满、愤怒等等。如果依赖者对对方缺乏认同、尊敬、钦佩、景仰,而只是出于需要和恐惧,就会更加加深种种负面的情绪。被依赖者的权力和统治,也就在依赖者负面情绪的冲击下被颠覆和瓦解了。
《金锁记》中曹七巧下半辈子带着儿女租房子居住,脱离了姜家大族的约束,手中掌握着钱财大权,实际成了一家之主,她的权力欲望,也就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处置他人的欲望也高涨起来并且付诸行动。她坚持给十三岁的女儿长安裹脚,“痛得长安鬼哭神号的。”女儿上学因丢些小东西,七巧便要找校长问罪,长安只好主动退学了。长安到了三十岁才与人订了婚,曹七巧却整日对着一条街辱骂女儿,间或又对着女儿流泪数落,软硬兼施,长安只好主动退了婚。儿媳娶进门后,七巧便百般羞辱,闹得媳妇只差寻死,受不了七巧的折磨,儿媳很快就死了,扶了正的丫头不到一年也吞生鸦片自杀了。儿子不敢再娶了。曹七巧在她的权力范围内大施淫威,但是最终她只落得个“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的结局。[22]这个“恨毒”,是曹七巧种种权力恶行的必然伴生品,其强悍统治也在这一“恨毒”中受到了无情的嘲讽和消解。《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娶了白玫瑰孟烟鹂为妻,在孟烟鹂的眼里,“他就是天。振保也居之不疑。”[23]孟烟鹂嘴上最常说的话是:“等我问问振保看。”[24]佟振保对妻子却是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他在佣人面前呵责妻子,使妻子毫无当家少奶奶的威信;他随时发泄对妻子的不满和蔑视,而且在外面宿娼;妻子没有倾诉的对象,只好对八岁的女儿诉冤,佟振保就把女儿送到学校里去住读,“于是家里更加静悄悄起来。”佟振保以绝对权威的姿态辖制着妻子,并且实行精神上的虐待。在佟振保看来,苍白愚钝的妻子是自己顺从的奴隶,对自己有绝对的依赖,他尽可以恣意地控制她、支配她,达到权力的最大化。佟振保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妻子竟然背叛了他,与一个小裁缝发生奸情,白玫瑰不再圣洁,完全颠覆了佟振保的权力之道,颠覆了佟振保对二人关系的既定想象。《茉莉香片》中聂传庆生活和学业上的花销全都得依靠父亲,是父亲的依赖者,只好任凭父亲和继母辱骂,还要照例给他们请安,表现自己的恭顺,但是他却从心底里仇视父亲,“他发现他有好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是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行步的姿态与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嫉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25]聂传庆还有很浓厚的夺权情结,“总有一天罢,钱是他的,他可以任意地在支票簿上签字。他从十二三岁起就那么盼望着,并且他曾经提早练习过了,将他的名字歪歪斜斜,急如风雨地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左一个,右一个,‘聂传庆,聂传庆,聂传庆’,英俊地,雄纠纠地,‘聂传庆,聂传庆’。可是他爸爸重重地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劈手将支票夺了过来搓成团,向他脸上抛去。为什么?因为那触动了他爸爸暗藏着的恐惧。”[26]在聂传庆的意识深处,只要到了夺取父亲权力的那一天,自己就会一改如今怯懦猥琐的行状,一变而成为英俊的、雄赳赳的聂传庆。聂传庆憧憬着夺取权力当家做主的日子,虽然他也知道那日子的遥远和代价,“总有一天……那时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奇异的胜利!”[27]权力与夺权,压迫与仇恨,恐惧与反恐惧,纠结在聂家父子之间,宣告权力统治的失败和虚无。
四、报复欲望的书写和消解
《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痛恨前妻,并因此迁怒于前妻留下来的儿子,虐待儿子聂传庆,整天不是斥骂就是挖苦。聂传庆,“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28]这就是聂介臣实施报复的结果之一。聂传庆的确是跑不了,离不开父亲的,可是他对父亲只有痛恨、敌视,恨不能立刻取而代之,这是聂介臣实施报复的结果之二。这两个结果的实质,就是对聂介臣的最严厉的回击,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他爸爸并不是有意把他训练成这样的一个人。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害怕。”[29]《十八春》里顾曼璐假装生病并设下圈套让祝鸿才强暴了自己的妹妹顾曼桢,表面看来似乎不可思议,或者只以为曼璐是为了讨好祝鸿才才这样做的。其实这只是罪恶阴谋的原因之一,更深层的原因是曼璐内心不可抑制的报复欲望。曼桢读过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爱情(当时曼璐知道妹妹已经和沈世钧订婚了),而自己只能在年长色衰的时候嫁给流氓投机商人祝鸿才,可祝鸿才发了横财后就整日在外面寻花问柳,对她弃之不顾了。而且曼璐认为曼桢快乐幸福的存在都是自己当舞女当妓女换来的,心理本就很不平衡,难以接受姊妹间如此巨大的差距。当曼桢遭强暴之后,曼璐到房间里去“劝慰”曼桢,被曼桢甩了一个耳光,曼璐“便冷笑了一声道:‘哼,倒想不到,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去撒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她越说声音越高,说到这里,不知不觉的,竟是眼泪流了一脸。”[30]顾曼璐内心的失落和不平倾泻而出。更让曼璐忿恨不已的是,当年自己的未婚夫张慕瑾如今竟然对妹妹情有独钟,这件事给予她的刺激极大,更激起她强烈的无法扑灭的报复之火。“慕瑾和曼桢一度很是接近,这一段情事是曼璐最觉得痛心,永远念念不忘的。”[31]因此更加激发了曼璐对妹妹不可遏制的报复欲望!虽然曼璐的阴谋得逞了,对亲妹妹实施了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给曼桢的人生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可是曼璐并没能因此拴住祝鸿才的身和心,他依然在外面胡作非为,而且变本加厉。曼桢在分娩后逃离了。曼璐的旧疾则日益沉重。当曼璐意识到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她拖着病体找到曼桢,“她颤声道:‘你不知道,我这两年的日子都不是人过的。’”[32]她哭哭啼啼地求妹妹为了孩子回到祝家去,遭到妹妹坚决的拒绝。过了半个月,曼璐就病死了。小说没有具体叙述曼璐死前的心理,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其忧郁苦痛、悲怨愤懑、悔恨惨伤的内心世界,其灵魂是无处安放的。顾曼璐实施了可怕的报复,但是她得到了什么呢?恐怕只得到了心灵的不安,只让她的人生苍凉再添深浓的一笔。其实,曼璐原本是一个心地纯洁、上进可爱的姑娘,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不得已当了舞女。当舞女之后,仍然关心着弟弟妹妹,一心培养他们读书,希望他们有出息。是报复的欲望像蛇蝎一样侵蚀着她的心灵,使她不顾一切,变成歇斯底里的恶毒妇人。张爱玲通过顾曼璐人生最后一段日子里生不如死的生活、无法弥补的情感罪恶,病入膏肓还硬撑着去求妹妹回来照顾孩子时的艰难和痛苦,宣示了其报复欲望的罪过和荒谬,更直接消解了报复欲望的意义存在。
显然,张爱玲小说把对欲望的消解隐藏在欲望故事的书写之中。
其小说不仅深入人性的阴暗面,记叙了种种欲望怎样操控着人们的意念和行为,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揭示出种种欲望怎样导致了人生的苍凉和虚无。这就使其小说文本超越了故事叙述的层面,上升到哲思的高度,表达了创作主体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和彻悟、劝诫和悲悯。“张爱玲则能……保持一份静观的冷峻与内敛的锋芒,以深邃的洞察与超越性的体悟,揭去种种人格面具,穿透玫瑰色人生幻影,讽刺与悲悯都融化于一片苍凉之中。”[33]而其深在的目的,“是在以否定的形式为理想人性的构建清理废墟。”[34]
注释:
[1][20] 刘再复:《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38,35页。
[2][11][12] 康信明:《撩开人性的面纱》,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248,3,4页。
[3] 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下,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4][5][6][7][8][9][10][17][18][19][22][23][24] 《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24,124,124,31,16,18,11,82,82,65,124,153,153页。
[13][14][15][16][25][26][27][28][29] 《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48,150,150,134,58,51,51,55,51页。
[21] 戚安邦:《管理学》,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209页。
[30][31][32] 《张爱玲文集》第三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1,174,255页。
[33][34] 秦 弓:《荆棘上的生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叙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0,504页。
2017-06-15
庄超颖, 女, 福建泉州人,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I206.6
A
1002-3321(2017)06-0034-04
陈未鹏]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