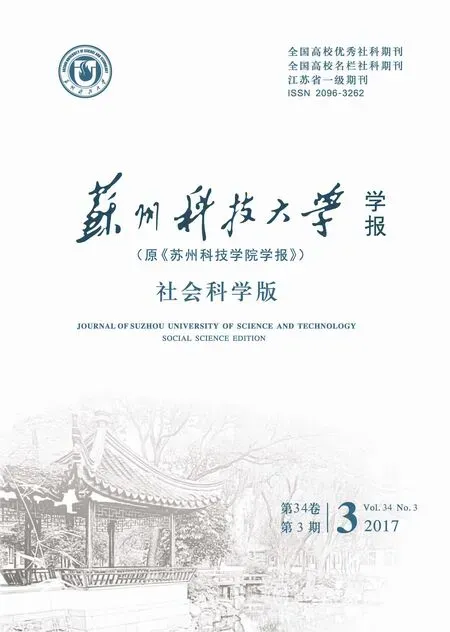吴语太湖片区的金总管信仰考
黄新华
(苏州市道教协会,江苏 苏州 215006)
吴语太湖片区的金总管信仰考
黄新华
(苏州市道教协会,江苏 苏州 215006)
在隶属于吴语太湖片区的浙江湖州、嘉兴,上海和江苏苏州等地的史志中,多有记载供奉金总管的祠庙。考金总管的名讳来历可知,其并非一人,而是南宋时自开封迁入苏州的金氏家族几代人,其中又以供奉金元七总管为主。其总管称谓之由来,并非是因担任总管一职,而是金氏巫师为抬高身份而冒称总管之后。金总管信仰的流布,是元朝以来在太湖流域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民间巫师依附、宣扬的结果。
金总管;太湖流域;总管;巫师
在中国的民间信仰构成中,总管信仰如同城隍、土地一样,不仅分布地域十分辽阔,且不同地域的总管神也都有所不同。栾保群《中国神怪大辞典》“总管”条就称:明王鏊《姑苏志》卷二七记有“总管庙”,即“金元七总管”。又清袁枚《子不语》卷二二“降庙”条,言粤西有降庙之说,每村中有总管庙,所塑之像,美丑少壮不同。《续子不语》卷六“飞钟哑钟妖钟”条,言塞北张家口亦有总管庙,其中有妖钟,三更外无故自鸣。[1]从江南苏州到粤西以及塞北张家口,都分布着总管庙,且往往各有不同。如同文中所言的粤西地区每村中有总管庙一样,在江南地区,总管庙也是星罗棋布。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中称,在苏州府乃至江南三角洲的众多方志中,有着许多关于“总管”名号的神的记载,“其中大多数都以‘金’为姓,也被称为‘金总管’”[2]15。这些供奉金总管的庙,或称“总管庙”“总管祠”“总管堂”,或称“随粮王庙”“金家堂”等,广泛分布于太湖流域的浙江的湖州和嘉兴、上海以及江苏的苏州等地。
对于金总管信仰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关注不多,所论也多是根据个别地方志的记载,对金总管信仰部分神职的单一叙述:如吕威在研究财神信仰时,对金元七总管如何由水神变为财神进行了探讨,认为“其转变的中介据猜测与元代的水运交通的发达有关”[3]。此外还有学者对金总管在饥荒中冒死赈济灾民,而由漕运官成为民众供奉的神进行了关注。[4]目前对于金总管信仰研究最为详尽的当属滨岛敦俊。他在对明清江南地区总管信仰的研究中发现,江南三角洲地区的总管信仰以金总管信仰为主,其在梳理了大量地方史志资料后,基本厘清了金总管的姓名、信仰的产生时间。[2]15-22笔者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长三角地区乡镇一级的地方史志资料,将金总管信仰的区域缩小为以吴语苏沪嘉小片和苕溪小片为中心的太湖片,并对以金元七总管为主的金氏家族自开封迁入苏州后几代人的名讳、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其总管称谓之由来,并非是因担任总管一职,而是金氏巫师为抬高身份而冒称总管之后代。金总管信仰的流布,是元朝以来在吴语太湖片区域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民间巫师依附、宣扬的结果。
金总管庙的分布
对于金总管的信仰区域,滨岛敦俊所说的苏州及江南三角洲地域,事实上可以进一步缩小为以吴语苏沪嘉小片和苕溪小片为中心的太湖片区域。吴语太湖片是根据吴语的发音特点等划分的一个区域,是吴语区范围最大的一片,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市及其辖区、浙江省杭嘉湖一带,其地理位置大部分与地理概念上的太湖流域重合。*太湖流域指的是太湖水系的集水区,从行政区划上包括上海市一个直辖市,杭州市一个副省级城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六个地级市。参见高逸凡、范金民:《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太湖流域:“江南”还是“浙西”》,《安徽史学》2014 年第4 期,第60页。其中苏沪嘉小片包括江苏省的苏州全市和南通、无锡部分地区,上海市及其所辖各县,浙江省的嘉兴市。苕溪小片位于浙江省西北部,包括湖州市、长兴县(西部边境除外)、安吉县(西部边境除外)、德清县、余杭县,共五个县市。[5]在这一区域的地方志中,多有记载供奉“金总管”的庙宇。
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首先引用徐逢吉《清波小志》的记载,称“流福沟东旧有金元七总管庙”,并称“今绍兴、杭州多有总管庙,皆昔守郡者之生祠也,吾邑亦有总管庙几处,则属之于金昌及其子元七”[6]。流福沟为杭州古城门清波门外引湖水入城的沟流,对于此处的总管庙,《楹联丛话全编》“巧对录”卷六称:
杭州清波门外有庙曰“金元七总管”,有客云:“可对‘唐宋八大家。’”众赏其工。[7]
俞樾为浙江湖州德清人,其所说的供奉金昌和金元七的总管庙多见于湖州的地方史志中。同治《湖州府志》记载:“总管祠在府治北,织染局旁,明建。”[8]邢澍修,钱大昕、钱大昭等编纂的《长兴县志》中也有“总管庙在县城东埜桥,旧为育婴堂址,嘉庆三年,邑人改建今庙。一在五里桥,乾隆四年建,……一在便民仓”[9]的记载。同治《南浔镇志》则记载了三处总管庙:“随粮王庙一在东栅口,明通判张佑创建,俗称东总管堂,乾隆十一年重建,道光中重修;一在南栅口,亦张佑建,俗称南总管堂,乾隆中修;……一在东栅御河桥上,明建,乾隆时火,毁,今神像移置船场浜留婴堂内。”[10]112同治《双林镇志》也分别记载了六总管庙、七总管庙和总管堂三处与金总管相关的庙堂:“六总管庙在成化桥南,即观音堂基,明嘉靖中建。…… 七总管庙在东林,创自元季,康熙丁巳重建。……总管堂在塘支湾。”[11]在湖州地区,从府到县再到村镇,都建有总管庙。对此,钟伟今编《湖州风俗志》中在论及清末民初湖州地区在议决做戏、出会、修庙、修桥铺路等事项时,往往以庄为单位,“一般以一个总管庙为中心划分一个庄”。这个总管庙所供奉的即是金七总管。[2]290可见,金总管在湖州地区不仅信仰极其普遍,且在民众生活中具有公权力的象征。这种风俗同样存在于浙江嘉兴地区,在嘉兴的西塘古镇,每年农历的四月初三至今仍能见到围绕随粮王庙开展的庙会活动。
在上海的乡镇志中,也多有关于供奉金总管的庙堂的记载。民国《章练小志》卷三“祠庙·土谷神祠”条记载:“土谷神祠在二十八都九图口字圩,俗名金家堂,祀刘猛将锐曁金总管灵佑侯细,洪济侯昌,利济侯元七。”[12]清陈元模《淞南志》卷四“寺庙”条则记载:“金家神堂,在周家塍南,内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及金宅历代神像。”[13]道光《金泽小志》卷二“祠庙”中有“总管庙在放生桥北,前明建,道光二十年重修”[14]的记载。嘉庆《安亭志》卷十四中也有“惠济侯庙,在真邑祠旁,神俗呼金总管”[15]的记载。
在金总管家族居住的苏州地区,供奉金总管的庙堂更是遍及府县乡镇。王鏊《姑苏志》“总管庙”条就记载了四处总管庙称:“(总管庙)在苏台乡贞丰里……一在阊门外白莲桥桥西……一盘门外仙塘桥下,一在常熟县致道观,一在嘉定县安亭镇。”[16]这四处总管庙,除一处在现在的上海嘉定县外,其余三处分布在现在的昆山市、姑苏区和常熟市。苏州县市一级的地方志中,几乎也都有关于总管庙的记载。如乾隆《太湖备考》记载:“利济侯庙在东山金湾,俗称金七相公,庙初建无考,庭中古柏二株,大可合抱,殆元时物也。”[17]王祖畲《太仓州志》在引用《姑苏志》关于总管堂的名讳来历记载之前称:“总管堂在州治东,元薛道纯建,俗呼薛家总管堂。清乾隆四十年里民张懋中募修,今毁。别有庙在大南门外。”[18]《乾隆元和县志》称:“总管庙在葑门外匠门塘西。”[19]《光绪常昭合志稿》称:“总管庙旧在县治西,宋元祐七年道士时天佑建,明弘治中改为阴阳学,遂徙于报本道院之右。……宾汤门外亦有庙。又东乡长亳塘上总管庙,名长亳庙。”[20]杨逢春《嘉靖昆山县志》记载:“总管堂在景德寺东。谨按:总管金姓名昌,其子名元七,殁皆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俱封总管。今子孙尚在,自当祀之,非小民所宜滥祭也。”[21]光绪《周庄镇志》也有“总管庙在镇北天花荡滨金家荡村,同治四年重修,祀总管金昌,曁其祖和,父细,子元七,从子应龙,孙某某”[22]的记载。莫旦《吴江志》记载:“总管堂祀利济侯金元七,在本城城隍庙中。”[23]对此,光绪《震泽县志》也有“总管堂祀利济侯金元七,在本城城隍庙中”的记载,并说“震泽各乡村亦多有此庙”[24]。确如《震泽县志》所言,各乡村亦多有金总管庙,至今在苏州阳澄湖镇新泾村储家浜、董浜镇西长亳塘畔、娄葑相门塘、娄葑新苏村16组花钵窑自然村、张浦镇下北港等地仍有总管庙的遗迹。
作为群体神称号的金总管
金总管信仰虽然普遍存在于江南地区,但对于神的名讳,普通信众往往莫衷一是。如苏州工业园区吴淞江畔的崧泽道院(高垫庙),庙中供奉的主要神灵当地信众称为“随粮王”,也称“金总管”,至于“金总管”的姓名,当地有“金元七”“金元六”“利济侯”“金八”“金十四总管”“金二十相公”等多种说法。这些称谓,事实上都有所据。
对于金总管的详细名讳、来历,首见于王鏊的《姑苏志》。其卷二七称:
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名和,随驾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子曰细,第八,为太尉者,理宗朝尝显灵异,遂封灵祐侯。灵祐之子名昌,第十四,初封总管。总管之子曰元七总管,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初皆封为总管,再进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16]
王鏊的《姑苏志》写于明正德年间,是现存方志史料中较早出现金总管记载的文献。此后的方志史料,如莫旦的《吴江志》、王祖畲的《太仓州志》、金玉相的《太湖备考》等都沿用《姑苏志》的说法。
对于金总管名讳、来历的记载,还见于章腾龙的《贞丰拟乘》和姚福均的《铸鼎余闻》等史志笔记中。《贞丰拟乘》“人物·金二十相公”条记载:
金二十相公,名和。其初本汴人,随高宗南渡,居贞丰里,殁而为神。其子名细,为太尉,理宗朝尝著灵异,封灵佑侯。灵佑之子名昌,封总管。总管之子名元七,复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亦封总管。与昌之从子名应龙者,同封。再晋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应龙为宁济侯。[25]
《铸鼎余闻》“利济侯金元七总管”条则称:
神汴人,姓金,初有二十相公者,名和,随驾南渡,侨于吴,殁而为神。其第八子曰细,为太尉,理宗朝尝显灵异,封灵祐侯。细之第十四子名昌,封总管。昌之子曰元七,亦封总管,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晋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又有顺济侯金元六总管及金万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总管,金显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诸神。[26]
这两处关于“金总管”的记载,大致与《姑苏志》的说法相同,所记载的金总管并非一位神灵,而是自金和(二十相公)—金细(八子、太尉、灵佑侯)—金昌(十四子、总管、洪济侯)—金元六(总管、顺济侯)、金元七(总管、利济侯)—金应龙(从子、宁济侯)的金氏家族几代神灵。所不同的是,《铸鼎余闻》中多了“顺济侯金元六总管及金万一太尉,金七四相公,金小一总管,金显三官人,金九一太尉诸神”;《贞丰拟乘》中则还提到了“昌之从子名应龙”。
对于金应龙是否为自金和而下的“金总管”之一,滨岛敦俊根据《至正昆山郡志》“金应龙”条记载的都“与漕运、总管无关”,认为他不是“金总管”之一。《至正昆山郡志》记载:
其先居府城草桥,今居郡之氵甲川乡。高祖锜以英伟刚烈,殁而为神,世显灵异,庙食甚盛。至应龙灵迹尤著,书降附托,死生祸福,昭答如响。自浙江被于淮甸,家奉户祀,庙貌像设,无处无之。近代神灵,鲜有其比。[27]
草桥在苏州古城区,氵甲川乡则在上海淞南镇。《至正昆山郡志》这条关于“金应龙”的记载初看与自金和而下的“金总管”谱系无关,但记载中出现的“草桥”,却将金应龙与“金总管”联系在了一起。
在苏州工业园区车坊地区流行的道教科仪中,有一本《祭筵薄》,为民间婚礼喜事举行斋醮中向八方神灵献茶的科仪,科仪所请神灵中有一段与“金总管”相关的文字:
草桥祖神金二十老相公尊神,金西四太尉,灵应托天侯金八老太尊神,岳府朝龙神水仙金梵一太尉,海神洪济侯金十四总管,上坛乡金元一总管,彭华乡金元二总管,顺济侯金元六总管,利济侯金元七总管,大都侯金小一总管尊神,金安一官人,金鼎二官人,易豪三总管,金镇四官人,金岳五官人,金随龙虎舍人,水仙娘子金莲九夫人。[28]
此段科仪中所延请的神灵,同样是自金二十老相公而下,只是在金和(二十相公)—金细(八子、太尉、灵佑侯)—金昌(十四子、总管、洪济侯)—金元六(总管、顺济侯)、金元七(总管、利济侯)—金应龙(从子、宁济侯)的传承外,如《铸鼎余闻》所记载的增加了金小一总管等诸神一样,增加了上坛乡金元一总管、彭华乡金元二总管、大都侯金小一总管尊神、金安一官人、金鼎二官人、易豪三总管、金镇四官人、金岳五官人、金随龙虎舍人、水仙娘子金莲九夫人等诸神。而在对金二十老相公的称呼中,加上了“草桥祖神”的前缀。这一称谓,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族氏系籍贯的归属称谓,即金和南渡吴地后侨居地为草桥,此后再迁徙至氵甲川乡。此外,《姑苏志》等记载的“金细”、《至正昆山郡志》中的“金锜”、《祭筵薄》中的“金西”,在苏州方言中读音相近,而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口口相传,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名字等书写有所不同在所难免。可见,“金应龙”即为金昌的从子。对此,光绪《苏州府志》也记载:“(金昌)从子应龙,皆复为神。元至正间,阴翊海运,皆封为总管,进封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应龙为宁济侯。”[29]
也正因为金总管家族曾多次变更居住地,史志资料在记载金总管籍贯时并不统一。按照王鏊的记载,金总管为河南开封人,南宋时乔迁吴地,并称“金总管庙在苏台乡真丰里”,真丰里即贞丰里,也就是现在的古镇周庄。《光绪常昭合志稿》则称:“神姓金,讳元七,父讳昌,宋淀山湖人。”[20]淀山湖是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邻接苏州昆山的湖泊,毗邻周庄。《至正昆山郡志》除府城草桥外,所说的氵甲川乡在淞南镇,以在吴淞江南部而名。这些区域都同属太湖流域。可见,金和南宋时随朝廷南迁,居住于苏州草桥附近,后迁居于淀山湖一带。这些神灵,同为金氏族人,且多被尊为总管。可见“金总管”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金和而下的金氏家系群体神。在这一家族群体神中,又以利济侯金元七的信仰最为普遍。
关于利济侯金元七总管的名讳,史志记载各有不同,如《姑苏志》等直接以“元七”作为神的姓名;《茶香室三钞》则认为“金者神之姓,元者神之名,七者,神之行次,总管者,其官职也”[6];而《武林坊巷志》引《严州府志》则称“姓金氏,名鉱生”[30]。这些不同的名字也体现了民间信仰的特点,即在口口相传之中,神灵的来历、名称等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总管称谓之由来
“金总管”全都是由人成神的,但对于金总管们显圣封神的时间缘由,如金总管的名讳一样,史志记载也都模糊不清。
对于金总管显圣被封神的事迹,较详实的记载见于弘治八年(1495)博士李佑所撰的《睦州建昌祠碑记》中,徐逢吉在《清波小志》中称:
独有睦州建昌祠碑记,载元季兵构,曹国公李文忠平之,似有人马旌旄拥从前后,命巫祝之,曰:“金元七总管也。神姑苏人。生而灵异,早歾为神。人有求,靡不应验。”兵定,李公立祠祀之。上闻,敕封利济侯。此文系弘治八年博士李佑所撰。[31]56
对此光绪《严州府志》也有记载,“七总管者,……有灵异,幼即为神。元以功封利济侯,三吴庙祀甚盛。明李文忠平睦寇,忽见兵仗旌旄护前,后命巫祝之,曰:金元七总管也。上其事,封海潮王”,并说“国朝敕封随粮王”[30]。对于金总管因何原因被敕封为随粮王,《严州府志》并未说明,此说也不见于其它史志资料,唯《周庄镇志》有记载,“嘉庆十五年,苏台乡总管庙入祀典,惟列在长洲县,意编祭银亦归长洲也”[22]。按照这一说法,金总管信仰或早自明洪武年间,或晚自嘉庆十五年起,才正式由民间淫祀转为国家正典祭祀。而《姑苏志》记载:金和随驾南渡侨居吴地,死后即成为神;金细太尉在宋理宗朝时显示灵异,被封为灵祐侯;金昌被封为总管;金元七亦封总管,元至正年间,因为能阴翊海运,封金昌为洪济侯,元七为利济侯;等等。这些所谓的“总管”等封号,并非朝廷的正式敕封。对此,徐逢吉作了较详细的考证:
予考《道藏》,山川湖海百神祀典,未尝有总管神之号。即水神之说,亦世俗相传,不足以征信。……昔黄梨洲论元官制,谓杭州、扬州,皆为上路,有总管而无知府。今绍兴、扬州皆有总管庙,皆昔郡守之生祠也。据此说,大都神为元时人。生为总管,有善政及于民,死又能捍卫地方,宜乎人之尊礼之。[31]55-56
总管之称号,本是古代官名,为地方高级军政长官、军事长官或管理专门事务的行政长官的职称,作为神灵的总管称号,并不见于《道藏》之中。元朝时,“诸路皆设总管府。达鲁花赤之下为总管,总管之下为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即达鲁花赤之下置知府或府尹”[32]。徐逢吉引用黄宗羲对元朝官制的研究,认为总管庙为元朝时郡守的生祠,因为郡守有善政,按照中国人“有功于民则祀之”的观念,被地方百姓所供奉。因此,王应奎认为总管庙本是守郡者的生祠被后人所附会才形成的。
对于金元七等总管是否为元朝时朝廷的总管官员,庞鸿文在《光绪常昭合志稿》中提出了质疑:
金元七姓名,不见正史,且府县志书或云一人,或云二人,无一定征信之辞。复查礼部,则例所载各神庙祀典,并无总管字样。[20]
按照元官制,总管为地方重要官员,理当被记载入正史,而金元七的名字不见于正史,说明他不是元朝的总管官。
事实上,金总管家族的“太尉”“总管”等称谓,并不是金氏家族中有人担任了朝廷的总管官,而是江南巫师为提高自己的身份,冒称“总管”“太保”。
元明以来,江南一带的巫师神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往往自称为总管等的子孙。同在太湖流域的江阴,正德年间编纂的县志就记载:“盖时俗以有官者之子孙为舍人,而管高者之家称为府。故陈巫自谓为太尉、总管子孙,其家为府,而己为舍人也。”[2]278巫师自称为太尉、总管的后代,称自己为舍人,平日出门也是按照官家的排场,“骑马张伞,大帽红袍,条环系带,驰里社中”。因此与之毗邻的金陵地方志“政务”中有专门“禁治江淮以南庙祝师巫窃称太保、总管,煽惑人众”[33]的记载。《元典章》中也有“禁庙祝称总管、太保”令,称:
至治元年二年口日,江西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王谋言》。江淮迤南风俗,酷事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称为生神,惶惑民众,未经禁治。移准《刑部关》议得。王谋所言,南方庙祝、师巫之徒,称呼太保、总管之名,扇惑人众。合准所言禁止。如有违反之人,事发到官,量事轻重断罪相应。准此。《本部议得》。南方庙祝、师巫之徒,妄称太保、总管之名,扇惑人众,合准刑部所拟,移咨江浙、江西、湖广等省,依上禁止相应。具呈照详。[34]
庙祝、师巫等民间巫师,妄称“太保”“总管”之名,扇惑人众,甚至惊动了朝廷,由刑部专门颁发“禁庙祝称总管、太保”令,足见当时江南地区这一风气的流行。而巫师假称金总管的事例,也多出现在文人的记载中。《西湖佳话》中就描写了一段嘉兴地区的巫师假称神仙下凡的情景:
原来嘉兴最信的是师巫,听得县里要祈祷,便来了八个,这干人口里专会放屁,敲锣击鼓,跳起神来,骗猪头三牲吃;哩嚏罗嚏,请起几位伤司五路,唱了几个祝赞山歌,假说:“我是金元七总管下降。”一个道:“我是张六五相公临坛。”又一个道:“吾乃宋老相公是也。”不过是饮食若流,做个饱食饱餐的饿鬼一通,有甚效验?[35]
在巫师假扮的神仙之中,第一个被自称的就是金元七总管下降。明朝苏州文学家冯梦龙也记载了一则巫师自称金元七总管的例子,他在《谈概》中记载道:
长洲刘丞不信鬼物。子病,妻乘夫出,延巫降神,问休咎。巫方伸两指谩语,适丞归见之,怒使隶执巫,将加杖,诘问:“汝何人?”巫犹伸两指跪曰:“小人是金元七总管。丞笑而谴之。[36]
给人降神、用巫术看病的巫师面对棍杖加身的困境时,边跪边犹自称为金元七总管。这些自称金元七总管的巫师,或如冯梦龙所记载的,可能为金总管的后代;或如饶宗颐先生所指出的,金总管的“后代在明代的真实面貌,却为民间的巫师”[37];而有的如嘉兴的巫师,则与金总管并无关系。正如滨岛敦俊所总结的:“总管祭祀仪式一般都源于个别巫师家族的神,以后就被用来当做周围一带村庄的保护神。”[38]可见,金总管信仰中,总管之名称并非来自于官职或朝廷敕封,而是民间巫师自抬身价之称呼。
金总管信仰广泛流布的原因
金总管从民间巫师的家族神到遍及太湖流域,各乡村多有供奉的祠庙,其背后除了民间巫师的攀附、宣扬之外,与太湖流域的地理环境以及元朝以来社会发展的现实有着密切联系。
金总管信仰是在太湖流域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地域神,他的产生、发展都与“水”紧密相关。
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湖泊众多,面积在0.5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189个。区域内水面率达17%,湖泊面积占流域平原面积的10.7%,河道和湖泊各占一半。整个区域内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为典型“江南水网”。水既为太湖流域的居民带来了丰饶的物产,也给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威胁。正是对水的危害的不确定性和无能为力,人们需要借助神的力量。而金总管的出现,最初也都以护佑海运、拯救落水之人的形象出现。《姑苏志》等记载金总管家族的神灵,元至正间能阴翊海运而皆封为总管。《铸鼎余闻》中所记载的两则金总管显灵的事迹,也与水有关。《铸鼎余闻》卷三记载:
国初陶道敬与奚氏仇,将疏阙下,为奚所缚,投白茅塘。陶号呼神,见神立水中,缚自解,跃岸得免。又叙《氏族篇》云:朱骥字汉房,官广西布政司左参议,尝泛海,遇一舰,投剌者曰金爷来访。及晤语,见其红布抹额,心异之。且属朱曰:我船先行,先生之船可缓遂行。朱报访,舰已远扬,第见标帜为“金元七总管”。顷之,风怒浪号,他舟多败,而骥独全。[26]
姚福均所记载的两则金总管显灵事迹,一则为救溺水之人,一则是为狂风怒浪中的船只提供保护,这两样恰恰是生活于水乡泽国的居民生产生活中最大的威胁。此外,考金总管信仰的发展,其时间大致与天妃信仰的兴起相同。这一时期,随着国家发展对漕运等需求的加大,护佑漕运安全的需要进一步增强。此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借助水运外出经商的人不断增多,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外出押送货物、经商是一件危险的事,船夫和商人的生命财产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得不到保障。因此,外出运送货物和经商的人都有自己供奉的保护神。《元诗选》中就一首描写苏州商人外出经商的诗——《复舟叹》,诗中写道:
吴中富儿扬州客,一身射利多介帛。
去年贩茶盆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
远行香火倚神明,从来风水少遭惊。
近日船行御河里,顺流日日南风喜。[39]
商人远行需要依靠神明的保佑,因为有神明的保佑,才能一帆风顺,少受惊吓。正是借助人们的这一心理需要,能够拯救溺水之人、为船只提供护航的金总管也随着传扬开来。而对商人们来说,平安才能获得财富,因此,能够护佑航运的金总管进一步被奉为财神。光绪《归安县志》就记载说:“又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市井中目为财神,建庙尸祝,每月初、二十六日,用牲醴与五圣同享,名日拜利市。”[40]
此外,金总管能为靠水生活的人提供保护,也能利用水为居民消除灾祸。徐逢吉《清波小志》记载:
雍正四年,有李森者,自伤寥落,祷于神曰:“神之为灵昭昭也,何至裸体而露处,与我同一坎瀼耶?神能授我一臂,我当有以报神。”乃不旬日,而李果得所遇。……(李森)以其事闻之邑侯杨公梦琰,杨公曰:“神于民有利乎?”曰:“神生时往来江湖间,殁后为水神,力可以制祝融。”公曰:“杭民之所患者火也,神能制火,祀之宜也。”[31]55-56
在李森看来,作为航运中的保护神,金总管能够控制水流保护航运,自然也能控制水,消除火灾。不管如何,金总管的神职,始终是与水有着密切的联系。金总管能够拯救溺水之人,保护航运,甚至控制水消除灾难,带来财富的神职在太湖流域以水为主的地理环境下,为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而这种需要经过民间巫师对金总管的依附、宣扬,更扩大了其影响。
民间巫师在自称“金元七总管”等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依附金总管,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使自己的灵迹有所依托;另一方面,也在依附的过程中,不断扩展金总管的神职,扩大他的影响力。按照《姑苏志》等的记载,金总管是因为阴翊海运而俱被封为总管的,但在后世的记载中,金总管的神职却在不断地扩张。《枣林杂俎》“幽冥条”就称:
金元七,前元长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专拯垫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辄著灵异。今其地曰金家庄。一曰有二子痘夭,因愿没身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泾河死。显□国初,金元七总管,万历初封,专管痘司。[41]
由此,金元七就从专拯垫溺之患变成了为救危痘而死、专管痘司的神灵。在弘治年间李佑所撰写的《睦州建昌祠碑记》中,金总管更成了能够襄助军队获胜的神灵。如清初张鸣钧《募修南总管堂引》所称:
(总管庙)皆元时以护漕丕著灵应,沿明至本朝庙名无改,而浔之捍灾降福、阜财裕民,尤捷若桴鼓,故香火报赛极盛。[10]112
金总管从护佑漕运、“丕著灵应”开始,经过民间巫师的依附、宣扬,已不仅能够护佑海运,而且还能消灾降福,为走水路经商的人带来财富,还司职痘司,甚至辅助战事。因此,乾隆年间华万九《重建随粮王庙碑》就称:“敕封随粮王庙,上既护国,下复庇民。”[10]325
这些神职的扩张,都离不开民间巫师的身影。正如《至正昆山郡志》所描写的:
书降附托,死生祸福,昭答如响。自浙江被于淮甸,家奉户祀,庙貌像设,无处无之。近代神灵,鲜有其比。[27]
“书降附托,死生祸福,昭答如响”本是民间巫师的惯用技能,而恰恰是在民间巫师通过这些技能的推动下,金总管信仰遍及太湖流域的城市乡村,甚至成为村镇的中心。
[1]栾保群.中国神怪大辞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9.
[2]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M].朱海滨,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3]吕威.财神信仰[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66-70.
[4]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44.
[5]傅国通,蔡勇飞,鲍士杰,等.吴语的分区(稿)[J].方言,1986(1):1.
[6]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十九[M]∥续修四库全书:11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2.
[7]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G].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396-397.
[8]宗源翰.湖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759.
[9]邢澍.长兴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652.
[10]汪曰桢.南浔镇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1]蔡蓉升.双林镇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2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17-519.
[12]高如圭.章练小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815.
[13]陈元模.淞南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776.
[14]周凤池.金泽小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35.
[15]陈树德,孙岱.安亭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374.
[16]王鏊.姑苏志[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357.
[17]金玉相.太湖备考[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429.
[18]王祖畲.太仓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56.
[19]许治.乾隆元和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83.
[20]庞鸿文.光绪常昭合志稿[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14.
[21]杨逢春.嘉靖昆山县志:江苏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6-97.
[22]陶煦.周庄镇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24.
[23]莫旦.吴江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276.
[24]陈和志.震泽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276.
[25]章腾龙.贞丰拟乘[M]∥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416.
[26]姚福均.铸鼎余闻[Z]∥藏外道书:第18册.四川:巴蜀书社,1992:622.
[27]杨讠惠.至正昆山郡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2633.
[28]祭筵薄[Z].1905(光绪三十一年)抄本.吾水荣藏.
[29]李铭皖.苏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086.
[30]丁丙.武林坊巷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529.
[31]王国平.清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M]∥西湖文献集成:第8册.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32]王应奎.柳南随笔[M]∥续修四库全书:1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35.
[33]张铉.至正金陵新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1721.
[34]陈高华.元典章: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57-2258.
[35]杨长山.京本通俗小说 贪欣误 西湖佳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48.
[36]冯梦龙.谈概 [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406.
[37]饶宗颐.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G].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130.
[38]滨岛敦俊.中国村庙杂考[J].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83(5):8-13.
[39]傅若金.清江集[M]∥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454.
[40]陆心源.归安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14.
[41]谈迁.枣林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06:511.
(责任编辑:周继红)
2016-11-17
黄新华,男,苏州市道教协会副秘书长,《江苏道教》执行主编,主要从事道教文化研究。
B933
A
2096-3262(2017)03-005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