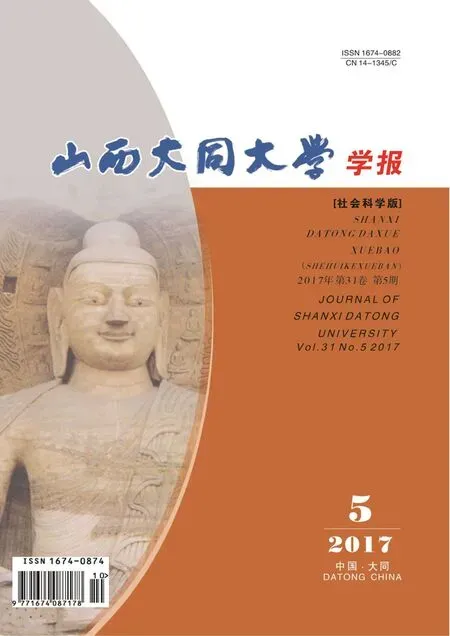向现代人的病态人格掘进
——卡夫卡《判决》的创作指向
张梦瑶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向现代人的病态人格掘进
——卡夫卡《判决》的创作指向
张梦瑶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判决》是卡夫卡的创作进入成熟期的奠基之作。但论者一般是从卡夫卡惯常的艺术创作手法(如象征、隐喻)和其创作过程惯常的主体心理活动特征来谈论这个问题,而忽略了《判决》作为卡夫卡最为自我肯定的作品,它的创作指向也奠定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是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
卡夫卡;《判决》;人格分裂;多重自我;象征
一、独特的自传作家
《判决》的写作,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被评论界公认为是他文学创作进入成熟、成型期的标志。卡夫卡的挚友、作家马克斯·勃罗德评论说:“随着《判决》的诞生,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身相适的形式,一个强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进入了他的天地。”[1](P50)但论者一般是从卡夫卡惯常使用的艺术创作手法(象征、隐喻)和其创作过程惯常的主体心理活动特征(深层隐秘心理的彻底开敞、由情结驱动的自由联想活动、意识流动的自由连贯等)来谈论这个问题,卡夫卡自己在回顾《判决》的创作过程时,也刻意强调了他创作过程的这种心理状态是其成功写作的关键:“《判决》这篇小说,是我在9月22日到23日的夜间10点钟到早晨6点钟一夜之间坐着一口气写成的……这小说在我面前如何发展,就像我是在水面上前进。这夜期间有几次叹息自己背上的重负。对那些最奇怪的想象而言,对一切而言,怎么可能把那一切说出来,那里停留着一大团火,它们再次在火中消亡和升起……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进行写作,只有以这样的连贯性,这样完全敞开的肉体和灵魂,才能进行写作。”[2](P250)《判决》所展现的艺术手法和创作过程的心理活动特征固然形成了卡夫卡成熟期的创作模式,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判决》作为卡夫卡最为自我肯定的作品,它的创作指向也奠定卡夫卡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
在《判决》之前,卡夫卡虽然出版了一个名为《观察》的小册子——一组篇幅短小的随笔和叙事小品,但他对这些作品并不满意,是在马克斯·勃罗德竭力催促鼓动下勉强同意公开发表的。这组随笔性小品的内容,多数是指向主体的外部世界,零散地描述了作者对存在的观察、体验和思考,也有对主体自身在特定情境中的情绪、生命意愿的直接表达。这些作品就表达思想感情上说,都是不完整的;就所展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上说,也还没有触及到人物的深层心理和人格存在状态。卡夫卡向勃罗德评价这些作品时,说它们是“一些拙劣的东西”,属于“不自然的创作和思索”。[3]直到创作《乡村婚礼筹备》,卡夫卡才触及到了人物的主体人格问题——他试图以长篇故事的形式揭示主人公人格的自我分裂状态——但这个作品在只完成了部分章节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从卡夫卡1910年开始写下的日记看,在写出《判决》前的几年间,他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何借助完整有序的故事和内涵丰厚的人物形象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生存体验,展现生命真实的存在状态?这一问题必然指向在创作中,要对人物的人格特征做出深层的展示和完整的把握。1911年11月9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席勒在什么地方说过:主要的事情是(或者类似于)将‘情感转变成性格’。”[4](P123)12月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我相信,有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形成,这东西与那种席勒式的将冲动转变成为性格的东西十分相近。我必须要越过我内心深处的一切阻碍写下这个。”[4](P146)1912年9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首对突破写作困境充满勇气和信心的小诗,同时又颇为自得地写下了这句话:“独特的自传作家的预感。”[4](P235)
“独特的自传作家”在卡夫卡的写作语境中有两重含义:一是以作家自我的生存体验、生命状态为作品表达的核心或焦点;二是以展现主体的人格存在状态、人的深层心理世界为作品的创作指向。依此而言,卡夫卡“独特的自传作家的预感”与“我相信,有什么东西在我这里形成,这东西与那种席勒式的将冲动转变成为性格的东西十分相近”这两种说法的语义指向是同一的。很快,1912年9月22至23日,他仅用一夜的时间就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判决》。
二、分裂的主体人格:三个格奥尔格
有关《判决》的内涵,评论界一般都着眼于作品中的父子关系而视之为是卡夫卡“审父情结”的倾泻。但依这样的视角,就很难理解小说开头部分,主人公关于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的内心独白,竟占了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及其后关于父子关系的描述中,“朋友”的角色一直贯穿其中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判决》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在整体上是象征和隐喻式的,笔者认为,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韩瑞祥、仝保民选编)中“编者前言”里关于《判决》的一段概说是极为准确得当的:
短篇成名作《判决》(1912)是卡夫卡对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理解中的判决,是对自身命运的可能抗拒。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判决》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非是现实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
《判决》中的格奥尔格·本德曼,最突出的存在特征是其经验性人格(主体人格)分裂为多个自我,他们处于相互游离、冲突的关系中,致使格奥尔格作为一个存在的主体,无法以确定性的方式把握住现实中的自我存在,进而造成作为主体性存在的格奥尔格在犹疑、困惑、徘徊中,不能自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现实人生,终至丧失了独立自主地生存的能力和可能性。对格奥尔格的这种分裂人格和存在相态,卡夫卡从小说的开篇,便作为一个隐秘的审视者和剖析者,以冷静、超然的笔调,径直把格奥尔格推到读者面前,让他以自己的言行渐次显露出自身的存在本相。
格奥尔格出场时,已是一个因接管父亲的商业店铺后生意兴隆、颇具成功感的城市中产阶级青年,他一个月前已和一位富家小姐订婚,现在是给远在彼得堡的、自少年就结谊的独身朋友写信,告知他自己就要举行婚礼、行将过上幸福美满的婚姻家庭生活。这个写信给朋友的格奥尔格,正处在令人羡慕的世俗社会成功者的生活状态中:年轻健康,自信干练,务实稳重,精力充沛;白天打理商务,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而以后无疑还会更兴旺;晚上则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或者(近期)去和未婚妻相会。而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朋友,在格奥尔格眼中的生活状态正与自己相反:他因对自己在家乡的发展十分不满,几年前逃往俄国,现在正在彼得堡经营着一家店铺,虽然苦撑硬拼,生意却越来越惨淡;他孤身独居(已安下心过一辈子的单身生活),身体似乎已经患病,而且病情还在发展;他与当地的本国侨民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国家庭也没什么社交往来——即便是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家乡,且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
从这位朋友的生活追求、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看,他开店铺所经营的“生意”,绝不是那种世俗社会中为了赚钱赢利的商业性活动,而恰恰是一种带有超世俗功利型的、属于“自我实现”性的人生事业。“经营店铺”和“做生意”在小说中无疑是隐喻。美国学者凯特·费洛里斯在一篇题目为《判决》的长文中,对这位朋友及其“生意”的隐喻性和指向做了细致、全面的分析,并指出“朋友”是格奥尔格内心深处存在着的另一个自我,代表了他所真正要追求的人生,属于格奥尔格内在的“理想自我”。[5](P136-158)其实,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品中父子二人关于这位“朋友”看似有些诡异的对话,以及父子二人和这位“朋友”看似有些诡异的关系、情感与态度,都能使读者领悟到那个远在俄国彼得堡的“朋友”是格奥尔格内心的另一个自我,是他潜意识中真正的人生追求和理想所在,而这个写信的、和父亲对话的格奥尔格,则是他现实的自我。格奥尔格给“朋友”写信,对“朋友”的长长的独白,都是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是现实中的格奥尔格对其理想自我所做的审视、评价。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现实中的“格奥尔格”,即他处在世俗生活方式中,认同世俗价值观的“现实的自我”,对那个理想自我——朋友的态度和评价是矛盾性的:一方面,他始终关心着这个自少年时代就“结谊”的朋友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和“生意”的经营,一直和其保持着通信联系,甚至对朋友那种不惜任何代价而固守着自己人生选择的性格,有着潜在的钦佩。另一方面,他又以世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质疑、否定这个朋友的生活状态——认为“他显然已误入歧途”,因此思忖着是否该规劝朋友放弃在异国他乡离群索居的生活和惨淡萧条的生意,“迷途知返”,回到家乡,回归格奥尔格现在的生活圈子中;他对这个朋友的态度,不仅言语中流露着成功者的高高在上和志得意满,而且在论及自己的生活选择可能伤害朋友的感情这个问题时,他竟对未婚妻这样说:“我就是这样,他爱怎么看随他的便”,并在心理是这样想的:“我总不能为了这份友谊,为了可能更合他的心意,削足适履。”[6](P1-10)
这样,作品以隐喻的方式展示出了主人公格奥尔格作为一个存在的主体,他人格的分裂状态: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不但是游离的,且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也是对立和冲突的——这两个“格奥尔格”无法统合成一个整体性的人格结构。
但主人公格奥尔格的人格分裂状态还不止于此。在作品中,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当格奥尔格走进父亲的房间与父亲会面后,在父子二人的对话和冲突中,我们又看到,这个现实中的“格奥尔格”,其性格又逐渐显露出了与先前大为迥异的一面。
在走进父亲的房间直面父亲前,格奥尔格无论是在商业经营、人际交往中,还是在处理个人家庭生活及婚姻问题时,都显示出他在日常生活中察人虑事的仔细周详和深思精明,以及处事有主见并能独立自主地果断行动,是一个自信干练、稳健成熟的中产阶级青年精英。特别是在与老迈体衰的父亲的关系中,他近几年完全抛开父亲独自处理商务和个人生活,用冷漠、疏远、无视其存在的方式对待先前那个统治家庭一切人事的专制家长(甚至决定在结婚后单独组建家庭,彻底脱离父亲),以此显示着自己独立自主的生存意志和能力。
但是,当他假借通告给朋友写信这一事(真实的用心是向父亲宣布自己已订婚并即将举行婚礼),不情愿走进已好几个月没有踏脚的父亲的居室时,面对孤独落寞的老父的持续挑战和进攻,格奥尔格竟节节败退,最终被击垮。小说在这一情节的推进中,占了整个作品约2/3的篇幅,从言语神态到心理意识活动,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格奥尔格性格的翻转。
在父亲这一方,对儿子的所为早已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所以他对格奥尔格的言行,起初是假意顺应,目的是迷惑对方,诱敌深入,使其露出破绽,然后抓住要害,攻其不备,一举击垮对方。而在儿子这一方,显然对父亲的心智和能力一向是失察的,尤其是此时,他对父亲的内心世界竟毫无知晓:父亲先是不动声色地接过了格奥尔格关于给朋友写信的话头,然后出其不意地指出对方是在说假话,真实的用心是为其背着老父订婚及决定举行婚礼一事扫尾,接着质问他:“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父亲的指斥都击中了格奥尔格品格上的缺陷——为人不实、骗人骗己,尤其是在对远方朋友的关系上,他这几年在通信中一直以假言虚语敷衍,并自认为是出自友情、为朋友着想。面对儿子在与朋友关系一事上的回避、躲闪,父亲揪住不放,其用意就是逼迫格奥尔格直视自己这些年对朋友的疏远、轻视、欺骗和背叛。接着父亲利用儿子慌乱中抱自己上床、盖被子、令自己卧床休息的举动,指斥其不仅多年来一直在骗朋友,而且骨子里也一直想打败老父,且以为真的已经把老父彻底打垮了。父亲还嘲笑、谴责格奥尔格决定结婚是出于低级的生理欲望,抵御不住女方粗俗、下贱的肉体诱惑,并指出这样做不仅玷污了已逝的母亲,也背叛了朋友。儿子人格上的污点还不至于此,父亲接下来就挑明了格奥尔格为人的愚妄无知和自以为是:
我的儿子春风得意招摇过市,做成了我打好基础的一笔笔生意,高兴得直打滚,在父亲面前俨然一位三缄其口的正人君子,然后就溜了!
我始终还是比你强壮得多。我如果孤身一人,可能不得不让步,然而,你母亲把她的力量给了我,我与你的朋友已建立了友好联系,你的顾客名单现在就在我兜里!
你跑来问我,是否应当把你订婚的事写信告诉这位朋友。他全都知道,你这傻小子,他全都知道!我给他写信了,……所以,……他全都了如指掌,比你还清楚一千倍呢。你的信他读都不读就用左手揉成一团,右手却拿着我的信在读!
父亲最后对儿子人格的判决是毁灭性的——揭露了格奥尔格内隐的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道德品性:“现在你明白了,世上不光只有你,直到现在,你只知道你自己!你原本是个无辜的孩子,其实却更是个魔鬼!”
可以说,在父与子的交锋中,父亲的每一处指控都击中了格奥尔格人格的重大缺陷。正因为如此,格奥尔格面对父亲一个又一个的指控,每一次都惊慌失措,意识混乱,全无招架之功。父亲第一次向他质疑朋友的存在时(“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位朋友吗?”),真实的用意就是要揭破他在情感上对朋友的疏远,在人格上对朋友的轻视和否定,在交往上对朋友的虚假敷衍。格奥尔格当然明白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所以他急忙用一连串表达对父亲关爱之心的话语,躲避这个问题,并且急不可耐地行动起来,以图转移焦点。在父亲故意用——“你在彼得堡没有朋友。你一直就爱开玩笑,连我也想捉弄。你怎么会偏偏在那儿有个朋友呢!我压根儿就不信。”——这样的话语逼迫下,格奥尔格只能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方式来回答,并边说话边为父亲脱衣,企图赶快了结这个话题。但父亲不容儿子在这一问题上的逃避,他说:“我当然认识你的朋友。他倒可能是很合我心意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多年来你一直在骗他。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你以为我没有为他哭过?”这几句话挑明了那个朋友身上待人待己的真诚不虚、追求自己人生事业的勇敢无畏和执着坚韧等品格,正是儿子身上所不具备的。对这样一个朋友的轻视和欺骗,正是儿子品格上不可宽恕的污点。小说中写到格奥尔格听了父亲的话后,随即产生了这样的心理活动:
父亲突然如此了解彼得堡的朋友,这位朋友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猛然间闯进了他心里。他看见这位朋友迷失在辽阔的俄国,看见他站在被洗劫一空的店铺门边。他正置身于货架的废墟、七零八碎的货物、倒塌的煤气灯架中。他干吗非得跑那么远呢!
父亲竟被朋友在彼得堡经营“生意”的处境感动过,为他哭过,而格奥尔格真的不能理解朋友的所作所为——“他干吗非得跑那么远呢!”——其实格奥尔格是不能理解朋友那种人格,不能认同朋友那种人生方式。
父亲嘲笑、谴责格奥尔格决定结婚是出于低级趣味,难道没有击中格奥尔格的虚弱之处吗?正是格奥尔格在给朋友的信中,颇为得意地强调,自己的未婚妻是一位富家小姐,并声言这一婚姻的缔结使自己很幸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连格奥尔格的未婚妻也直觉到了他在婚姻上的选择与那个朋友的人格是冲突的——“你有这样的朋友,格奥尔格,那你原本就不该订婚。”
父亲谴责格奥尔格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冷漠无情的人,难道没有道理吗?父子二人共同生活,但他平日里对老迈体衰、孤独失偶的父亲的衣食住行,不仅没有丝毫的顾念之心,反而总是刻意疏远、冷淡对方,甚至已打算好结婚后抛开老父单独居住——这些有悖人伦常情之处,也致使格奥尔格在时隔几个月才踏进父亲房间的那一刻,有潜意识的觉知:
格奥尔格吃了一惊,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父亲房间里竟如此昏暗。大片的阴影是狭窄庭院对面的一堵高墙投下的。父亲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那儿摆着格奥尔格亡母的纪念物,他正在看报,将报纸举到一侧,以弥补某种视力缺陷。吃剩的早餐还摆在桌上,看上去没吃多少。
在为父亲脱衣时,他的人伦之情、道德良知被唤醒了:
他看见父亲的衣服不很干净,不禁责备自己疏忽了对父亲的照顾。提醒父亲换衣服当然也应当是他的义务。他还没有同未婚妻明说过,将来如何安排父亲,但他们已经达成了默契,认为父亲理所当然应当继续住在这老房子里。而此刻,他匆匆下定决心,要把父亲接进他的新家去。他的心情之急迫,就像是到那时再照顾父亲,可能为时已晚。
不能断言格奥尔格不在意亲伦之情,故事的结尾处,格奥尔格在自溺落水前喊出的是这句话:“亲爱的双亲,我一直都是爱你们的。”但格奥尔格在日常的行为上并没有显示出对父亲的关爱,反倒是因痛恨父亲一向粗暴、专断的家长统治而心怀敌意——暗中的伺机反抗、报复和日常接触中的刻意冷漠、对峙,就成了格奥尔格处理父子关系所采取的方式。这只能说,作为城市中产阶级在富裕生活环境中长大的青年,格奥尔格在心智和情感上是不成熟的,他以自我为中心对待外部世界,使他面对自己和他人的存在,都不能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把握。
在父子冲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本来年轻有为、自信干练、志得意满的格奥尔格,竟在老迈体衰、孤独落寞的父亲的一番指斥、嘲讽下,慌乱失措,虚弱不堪,一击而垮,就像一座立基不实的高楼,一旦遭受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撼动,也会轰然倒塌。这样,作品又为我们展示了主人公格奥尔格人格的另一种存在面相:一个内在虚空、幼稚无知和软弱无力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和社会生活对他人的存在都缺少爱、关切、付出的人——这也是一个现实存在中的格奥尔格,是格奥尔格内在的自我,或者说是现实存在中他心灵深处精神性的、真实的自我。这样,现实中的格奥尔格又给我们呈现了他外在的自我形象和内在自我不能统一的分裂状态:那个在世俗生活中年轻干练、老成务实、自信果断,在商业经营和人际交往上得心应手的格奥尔格,那个有由父子血缘关系维系的安稳的家庭,有往来密切的朋友,有幸福的爱情的格奥尔格,原来只是他浮现在世人面前的外在的、面具化的自我——两个自我在格奥尔格那里,虽然以一个外显、一个内隐的形式并存一身,但却是内外游离、对立分裂的。
如此,卡夫卡的《判决》,在一个由朋友——格奥尔格——父亲三者之间从空间上由远及近,从时间上由过去到现在所构成的完整有序的事件中,用象征隐喻的手法,为读者揭示了主人公格奥尔格作为存在的主体,构成他人格中的三重自我相互游离和矛盾的状态——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分裂与冲突,现实自我中外在自我和内在自我的分裂与冲突。
三、朋友·儿子·父亲——谁受判决,谁在判决
1913年2月11日,卡夫卡核校《判决》的时候,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这部作品的评论,其中关于作品中人物的出现及其关系,是这样说的:“这位朋友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的地方……故事的发展表明,从这共同点,从这位朋友身上,父亲突现出来,并作为对立面在格奥尔格面前出现了……这个共同之处全堆积在父亲的周围。格奥尔格只觉得它是陌生的东西,独立变化的东西,从没有足够地受他维护的东西。”[4](P240)
如何领会卡夫卡这些话语呢?如果“朋友”是格奥尔格内心深处潜在的理想自我,是他被压抑着的所真正欲求的人生,如果我们再连及到故事中父亲是认同、肯定“朋友”的人格的,那么,“这位朋友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的地方。”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其次,故事中父亲还声言“我是他在这儿的代理人”,那么,“从这共同点,从这位朋友身上,父亲突现出来,并作为对立面在格奥尔格面前出现了。”这句话无疑是在说明,“父亲”的形象,是作为维护“朋友”的人格,作为否定格奥尔格现实存在的一种权威或力量的象征出现的。这样,我们又能领会卡夫卡所说的“格奥尔格只觉得它是陌生的东西,独立变化的东西,从没有足够地受他维护的东西。”这句话的含义了——格奥尔格对那个潜藏的、被压抑的理想自我,从来也没有清晰地确认、把握过,它始终是一个游离于格奥尔格现实存在之外一个模糊的影像。卡夫卡自己对作品中朋友——儿子——父亲三者之间存在关系的评论,也正是对《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中“编者前言”里关于《判决》的这一论断——“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最有力的佐证。
谁受到了判决?当然是在世俗社会中活着的中产阶级青年格奥尔格。谁判决了这个格奥尔格,无疑是那个既游离于他现实的自我存在之外,又潜伏在他生命机体深处的,否定他现实人生状态的那个理想自我。只是这个理想的自我,为了显现一个作为洞察他、审视他、评价他的外在权威的形象,为了显示一种不可抗拒的审判他、惩罚他的强大力量,在故事中化身为“父亲”。如果依照卡夫卡在日记中所说——“父亲”是从“朋友”中走了出来并作为对立面站在格奥尔格面前的,那么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格奥尔格最终对自己作了判决。也许令读者有疑惑的是,为什么“父亲”的形象中还携带着狡黠、阴鸷、专横、粗俗的暴君性格成分?可以这样来理解:正是审判者具有的这些形象特征,才逐步从情势上把格奥尔格推向被审判的处境,强化了被审判者的罪责感和对负罪的恐惧感,从而形成被判决者在深重的罪责感和恐惧感中自甘毁灭的效应。
多年以后,卡夫卡在向捷克女作家密伦娜谈到《判决》时,曾这样说过:
在那个故事中,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一段(假如可以这么说的活)音乐都同“恐惧”联系在一起。当时是在一个漫长的夜里,伤口第一次破裂。[7](P390)
在给密伦娜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到了自己一贯的写作追求:
我总是力图传达一些不可传达的东西,解释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叙述一些藏在我骨子里的东西和仅仅在这些骨子里所经历过的一切。是的,也许其实这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那如此频繁地谈到的,但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和对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当然,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而且也是对某种东西的渴望,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7](P420)
这两段话,有助于我们领会《判决》中“父亲”形象所起的作用。
四、卡夫卡和格奥尔格们
《判决》无论是在艺术表达的方式上,还是在作品内涵的指向上,都定型了卡夫卡以后的创作。就作品的内涵而言,《判决》中所展示的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人生的迷惘、心灵的空虚、对人生本真存在的渴望、精神求索的困顿、对外部世界的陌生与恐惧感、生命存在的异化状态、自我存在的罪愆感及自我救赎的软弱无力等——是卡夫卡以后创作中不断深化、扩充、延展的核心与焦点。而这个表达的核心与焦点,如果转换成作家对时代人生的情感体验,就是卡夫卡对密伦娜所说的“已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和对最小事物的恐惧”及“这种恐惧也许不仅仅是恐惧,而且也是对某种东西的渴望,这东西比一切引起恐惧的因素还要可怕”。如果转换到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上,便成了卡夫卡对现代人主体人格分裂状态的深层展示。继《判决》中的格奥尔格之后,《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流刑营》中被判刑的士兵,《乡村医生》中的乡村医生和罹病少年,《诉讼》中的约瑟夫·K,《城堡》中的K,作为格奥尔格的弟兄们,一一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在论及自己所创作的作品与自身的关系时,卡夫卡在核校《判决》时是这样说的:“这个故事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秽混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4](P240)这一断语不仅道明了主人公的病态人格,也道明了作家自身的存在与主人公的亲缘关系。
格奥尔格和他的弟兄们是谁?是西方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人。卡夫卡是谁?在作为生命存在的体验者这一语境中,他是西方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人;在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困境的揭示者这一语境中,他是卓越的文学艺术家。在卡夫卡把自己的生存体验转化为文学作品时,卡夫卡和格奥尔格们亲如弟兄,这也是卡夫卡用“独特的自传作家”指称自己写作模式的话语蕴涵。
[1](奥)马克斯·勃罗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奥)弗兰兹·卡夫卡著,阎嘉译.卡夫卡日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书信(第7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日记(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叶廷芳编.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韩瑞祥、仝保民选编.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0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 裴兴荣〕
Driving towards Modern People's Morbid Personality——Creative Direction of Franz Kafka'sDas Urteil
ZHANG Meng-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
Das Urteilis Franz Kafka's a foundation work that marks his maturity.Critics generally talk about this problem from his artistic creative technique (such as symbolization,metaphor)and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reation,while ignoring thatDas Urteil,Franz Kafka's most self-approving work,its creative direct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irection of his novel creation.Many critics compareDas Urteilwith his famous long letterTo Father,regarding it as his confession.In fact,characters in the novel show the inner division of the protagonist.
Franz Kafka;Das Urteil;split personality;multiple self;symbolization(metaphor)
I521.074
A
1674-0882(2017)05-0068-06
2017-04-25
张梦瑶(1986-),女,河北唐山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