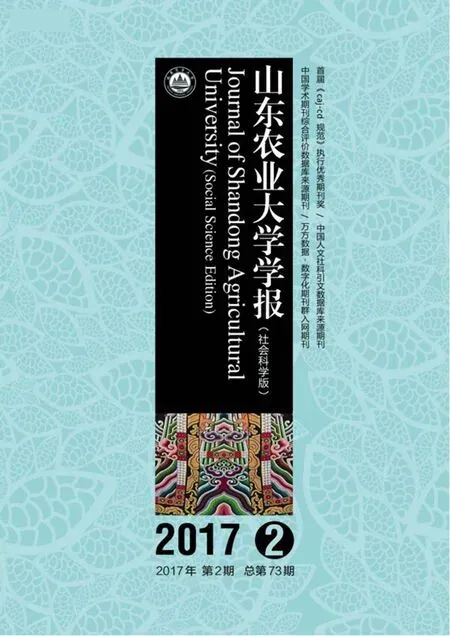传统废墟与现代主流
——评哈代《还乡》中人性的困境
□杨佩佩
传统废墟与现代主流
——评哈代《还乡》中人性的困境
□杨佩佩
托马斯·哈代是现实主义转向现代主义时期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写作特色既继承了现实主义反映客观现实的特点也引领了现代主义人性矛盾复杂主题的思潮。哈代小说的创作背景与乡土传统之间有着难割难舍的关联,然而,他笔下的乡土传统总是要受到现代主流发展趋势的挑战和威胁,由此挑战和威胁带来的矛盾与困境以社会环境、自然法则为载体客观真实地植入到人性内,让主流与边缘的冲突得以再现,从而也展现了人性在面临矛盾和冲突时对复杂环境自我调节和自我适应的进退两难境地。
乡土传统;现代文明;人性
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创作以乡土特色闻名,写作主题更是以“性格与环境”而著称。哈代因其自身的生活和成长经历,对乡土传统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义,在他的小说中,对人物苔丝的塑造以及对埃格墩荒原的描述,除了表明他的乡土情外之外也抒发了他个人对正在消失的传统文明的思念和缅怀,也表达了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忧患意识。哈代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作家,他的思想具有进步和前瞻性,通过他所创作作品的主题来看,他所表达的不止是一种单向感伤的怀旧情怀,也深入地探究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性。《还乡》一直是哈代乡土特色和“性格与环境”长篇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城乡之间的差异渐渐趋于模糊化,面对这种新生的文化和文明,更是加固了哈代成为研究热点的席位。国内学者对《还乡》主题的研究主要是从自然法则、社会文化历史、人物性格和悲剧论等几个方面展开,本文旨在基于前人研究的主题更多地深入探讨作品与当代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意在对新型城乡文化集体意识形态下的个人自我意识建构得到启发。在小说《还乡》中,埃格墩荒原、克林和尤台莎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在他们相互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冲突和困境逐一显现,由于个人认知的短缺和社会道德调节功能的丧失,导致最后和谐解决冲突和困境的途径竟演变成了死亡。尤台莎的死亡成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解的牺牲品,她的死亡是一种与世格格不入精神的离开。由于当时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
的主导地位以及当时乡土文化的边缘化危机,不论是尤台莎的死亡还是克林职业的失意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乡土传统生存空间的缩小和消失以及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势不可挡。在两种冲突的文明面前,由于生活环境和价值观的不同,人性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和忧患意识也各不相同,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灵体验造就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命运,然而,哈代通过尤台莎的死亡命运也向社会大众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只有回归自然、乡土和原生态文明才是人类精神文明最好的归宿和庇护所。
一、社会文化规则下的生存
哈代的作品跨越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两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利益最大化成了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和意义。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追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使物质生产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并且尊定了物质生产的中心地位。随着大量的物质产品涌入社会生活,人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在新的社火环境面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这些新变化都源于工业的空前发展,因此更加充分地彰显了物质生产在工业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原则的支配下,本来体现人的本性或实现人的本质的社会生活丢失了人性,变成了一切根据追逐物质利益、攫取经济效益的原则去展开各种行为的非人的生活”[1]。面对如此强势的发展趋势和价值观念转变的冲击,当时的乡村宗法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伤害,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对乡村这片净土无孔不入。哈代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给乡村和乡民带来的伤害,也感受到了乡土弱势群体的无力反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带有一丝悲剧和宿命的无可奈何的意识。
在小说《还乡》中,究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而言,不同的人物和角色在面对不同于自己的社会文化时,都有各自不同且根深蒂固的反应,也正是因为这些根深蒂固和无法改变让整篇小说敷上了一层浓浓的悲剧和宿命色彩。个体在面对新事物和社会生活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不适应和特殊性受他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在伴随他们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给他们的行为意识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具有决定人类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团体发而出来用以理解、利用它们的环境,并在环境中生存的行为模式。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传承,文化作为习得的行为存续下来,代代相传,塑造着社会成员的行为”[2]。在小说《还乡》中,尤台莎和克林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在面临埃格墩荒原时,他们不同的行为反应表明了各自所坚守的信仰和传统化为一种不可挟制的外界力量控制住了他们的言行和意识。尤台莎作为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代言人,她深受以个人为中心的享乐主义支配,她憎恨埃格敦荒原,一心想要挣脱并且认为“埃格敦是她的冥国,自从来到那里,尽管心底深处永远和它格格不入,荒原黑暗的情调她已吸收不少”[3]。显而易见,荒原的原始文化形象与尤台莎所持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大相径庭,面对与原来不同的乡村生活环境,她内心感到强烈的不适应,随之产生的固执和偏见也证实了资本主义现代主流发展的必然性。然而,荒原这片具有乡土气息的自然原始风光在资本主义现代主流文化面前则成为了一片废墟,在尤台莎的眼中它只是一片荒凉杂乱的黑暗之地,她对荒原的心灵体验以及定位以物的有用性为衡量标准,从而导致荒原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荒原的包围下,尤台莎作为资产阶级价文化值观的代表者,在物质实用性主导的意识观念驱使下,她内在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系统已被打破,脱离了物质的牢笼,她的精神世界犹如一个孤独的灵魂在埃格敦荒原上漫无目的的漂泊无处安放。由此可见,单一的物质利益至上的观念,使人类生活条件改善和提高的同时,也把人类的精神世界推向了“荒原”地带。尤台莎在埃格敦“荒原”的面前,她所感受到的是孤独、黑暗和束缚,并且一心想要逃离和挣脱。然而,埃格敦荒原作为乡土传统文明的最后一片净土,它不止是乡民生活的归宿,更是现代“文化”人的精神归宿。
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乡土传统应该是落后的待开发的,现代主流则是进步的,它作为一种进步的发展力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有责任推动乡村落后的发展。然而,在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交流和碰撞时,不应该有占有和屈服的姿态。两种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时,对两者来言,都应该是一个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所衍生的第三种混合文化,正是推动城乡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主干力量。“在帝国边缘和各种文化的交叉地带,穿越边界的人们创造出混合文化,推动者历史转变”[2]。尤台莎与荒原二元对立的状态,否定了现代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展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侵略本质。
二、自然法则下的生存
自然作为万物的一种,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转变而转变,是一种自在的存在,然而,由于人类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自然也会随之被改变。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对其的改造发生在生存必要之际,并且对它的利用需要以和谐为衡量准绳。人与自然不仅是改造或被改造的关系,它们也是对方存在的意义。对于人而言,自然是生存之本也是回归生命之本原,就自然个体来说,它的存在本身是无意义和杂乱的,因为有了人类的出现和历史文明的发展,赋予了它一种新的存在意义和秩序,所以人类是它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载体,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和依赖。“人依存于自然生命,又通过其实践活动创造着自觉生命,更凭借其自觉生命来返观与体认那自然生命的本原,以实现自身向着自由生命境界的升华”[4]。自然除了作为人存在之外的外部事物,它还具有自身内在的生存系统和法则,表现为一种双向和谐的发展状态。自然法则不是被拿来利用和改造的工具,它是事物运作的一种本质规律,是万物统一和回归的本原。随着自然之外的事物发展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增强,自然与外界事物的和谐被打破,所面临的是自然法则内在规律的失衡以及外部事物的单一和规则化。人是推动外部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随着发展势力的逐渐壮大,外部事物发展成为一种超越人自身可以控制的力量。“表面上,人好像自我做主,实际上是不自觉地被“他人”控制,盲目地浑浑噩噩地生活。另一方面,表现在人“自己和物的关系上”,由于人(此在)遗忘了“物本身”(自在之物、原大地、原自然),好像存在的物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作为主体对象的物(比如耕地、树木、矿山等),而这些对象(物),人可以任意利用和处置”[5]。最终,导致了自然法则与外界事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人则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载体,一种矛盾、无可奈何的生存境地由此衍生而来。
在小说《还乡》中,克林是来自乡村自然法则的典型代表,他来到巴黎谋生,事业风生水起,但是由于个人的乡土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规则的格格不入,他决定返乡,重新开创事业。克林作为自然法则的代言人,首先,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浮华、虚荣和伪善时,他无法与其融合和谐相处,因为他个人内在持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中找不到契合点,价值观念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克林选择了放弃现代社会生活环境,回归乡村。克林决定回到乡村埃格敦荒原,“他回家时没有沿荒原上的小径走,如果说有谁真正熟悉荒原,那就要属克林了。他身上浸润着荒原的景象,荒原的物质,荒原的气味。克林可以说是荒原的产物。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荒原;他记忆中的最初意象便是同荒原的外貌融合一起;他对生活的看法,深受荒原的影响”[3]。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具有乡土传统气息的埃格敦荒原,它从上个世纪悄悄走来,闯进这个不属于它的时代,成为了一个过时的物体,现代人不愿意靠近它,更不会研究它存在的意义,也只有像克林这样生活在当地的乡民会成为传承两个不同世纪文明的纽带。在克林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止是乡土传统的色彩,同时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现代文明的影子,他的还乡之旅,可以看作是一次自我精神本原的回归。经历了现代文明的社会规则与乡土传统法则之间的斗争,克林选择了回归自然,他的选择除了因个人与外界矛盾冲突的结果之外,也隐含着事物内在发展的规律,从简单-发展-异化-完整的演变过程。克林经历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摩擦后,返回家乡,眼前所面对的埃格敦荒原,作为一种自然法则,它具有比先前更深层次的统一与和谐的意义[6]。如果克林当时没有离开,无论是他个人还是带有原始特点的乡土传统和埃格敦荒原都会被动地等待着现代文明的侵蚀,逐渐失掉它原有的意义或者被现代力量毁灭。自然法则存在的意义在于它自身所持有的本真和人类赋予它的精神本原,在自然法则下的生存,并不意味着野蛮和未开化,它意味着人类自身在物质横行世界中的解脱并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人性“物化”和“异化”的和解以及随着社会发展累计的矛盾和差异性的消失。
自然法则与社会规则并不是二元对立的状态,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可以依靠人类这个载体抹掉。人类的意识具有客观能动性,当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时,被改造的客观对象便失去了它的本真面目,然而它的新面貌在没有完全适应周围环境前,自然法则的存在就犹如尤台莎眼中的埃格敦荒原,是一片荒芜、落后的大地,像一座监狱一样,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部的事物亦闯不进来或不愿进来。在自然法则与社会现实人的存在发生正面冲突时,“随着主体中心主义的极端膨胀,人处置对象的能力(科学技术)越来越强,人对原大地、原自然破坏和掠夺也越来越重。于是,原大地、原自然的存在,因被遗忘而“隐匿”起来,人失去了可以诗意栖居的自然家园”[5]。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存在更多地卷入理性地社会现实,离自然法则越来越远,当自然空间被挤压到一定的边缘地带,它就变成了一座荒原,成为了人类精神荒原的象征[7]。
三、个体自我意识的存在
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因其生存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观念,当这种认知观念发展成为一种习俗,并且被后人传承时,它就演变成为了一种具体的“原型”或称“原始意象”。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和所有人都是相通的。它们是人类早期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原型是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范型,是一种先天固有的直觉形式,它决定着人类知觉、领悟、情感、想象等心理过程的一致性”[5]。在个体自我意识与“原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渐渐浮现,这种集体无意识具有时代的特色,并且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经验,影响着同一时代个体的自觉意识观念,这时集体无意识便成了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它对于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个体自我意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个体而言,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思考和认知的能力,但是他的认知和思考不可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生活环境,不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个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他个人的自我意识,都脱离不了社会集体无意识这个主流,他们认知的迥异来源于各自成长环境以及教育背景的不同。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迥异的认知结果,推动者集体无意识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主流中,边缘不应该是落后和摒弃的对象,相反,它是推动主流发展和进步的主要力量来源之一。在面对主流的发展趋势,个体自我意识不应该是随波逐流和盲目的状态,它应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和自我调节意识。
尤台莎作为小说《还乡》中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她个人的自我意识深受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影响,有着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当她脱离个人价值观所属的社会文化环境,来到埃格敦荒原时,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她“身居荒原但不探究其意蕴,就好像是嫁给一个外国人但不学他的语言。荒原美丽的精微之处,尤台莎没能察觉到;她所抓到的,只是其飘渺云雾”[3]。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尤台莎的个人意识依旧未能从“传统”中走出,她未能放下个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带着固有的偏见和执念去看待和理解埃格敦荒原,在她的眼中,它不过是一片废墟。荒原存在的现实价值意义被尤台莎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所遮蔽,从物的有用性角度来讲,荒原成了一文不值的废墟,尤台莎完全没有认识到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8]。荒原从上个世纪走来固然带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价值作用,虽然在这个现代文明盛行的世纪,它的闯入显得有些突兀,但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它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对待,也会成为推动主流发展的巨大力量,社会发展的进步性始于废墟也毁于废墟。克林在现代都市巴黎的生活也并不如意,他憎恨物质利益主导生活中的一切虚假、伪善和虚荣浮华,由于他个人简单地乡土传统观念,无法与复杂的现代社会规则融合,最终,他选择了还乡。由此可见,克林个人的意识也深受传统观念的控制和影响,无发客观正确地对待现代社会生活,资本主义自有它无需揭示的弊端,诚然,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发展力量,它也具有自身的优势。克林应保持原有传统观念的同时,也要抓住现代社会发展的优势,顺势发展,使精神和物质得到和谐和统一,既推动“荒原”的现代性也修复物质的传统性[9]。
在同一时代,由于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的不同,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认知会有巨大的差异,当这种差异遇到陌生环境时,便得以具体的实现。个体面对差异和冲突的态度深受他所处时代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影响和控制,集体无意识总是更倾向于社会发展的主流,而处于边缘地带的意识空间则陷入无足轻重的状态,降低了它的影响力和推动现代主流发展的力量。徘徊于两种意识形态边缘的个体意识,若不具备正确客观的认知能力,终究会陷的太深或走的太浅,从而导致精神和物质的分离,沦为社会悲剧的牺牲品。
四、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曾作为一种进步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这种进步的主流力量可能会被新的发展力量所代替,最终,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然而这种边缘化,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消失和无足轻重,相反,它作为滋生新生力量的地基,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个体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力量的载体,社会文明发展的传承者,由于社会生活环境的不同,自身持有的价值观念也不统一,然而,这种具有个别性和特殊性的价值观念,也源于一个统一的一般概念。这个一般的统一概念,被称为社会主流意识,也称为“集体无意识”,它源于个体有意识,却高于个别,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势力。这种个别的所谓边缘性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状态,也不是征服和毁灭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发展。在两种意识形态的交叉地带,个体有意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是进或退都需要深入的认知和客观的态度。
[1]坎迪斯·古切尔、琳达·沃尔顿著,陈恒、李若宝、谭顺莲、汤艳梅、奚昊杰译.全球文明史[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7.
[2]郑杭生、刘少杰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3]托马斯·哈代著,王守仁译.还乡[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60-159.
[4]陈柏海著.回归生命本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7.
[5]马新国著.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09.
[6]王杰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55-258.
[7]胡克红.从《还乡》看哈代的自然观[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06):29-31.
[8]于淼,金栩竹.情陷荒原 别样凄凉——哈代的《还乡》和艾略特的《荒原》[J].文艺评论,2011,(01):90-92.
[9]杨澜.回归与走失:《还乡》中主人公命运分析[J].中州大学学报,2008,(01):45-47.
2016-12-17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杨佩佩(1990- ),女,山东梁山人,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I106
A
1008-8091(2017)02-01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