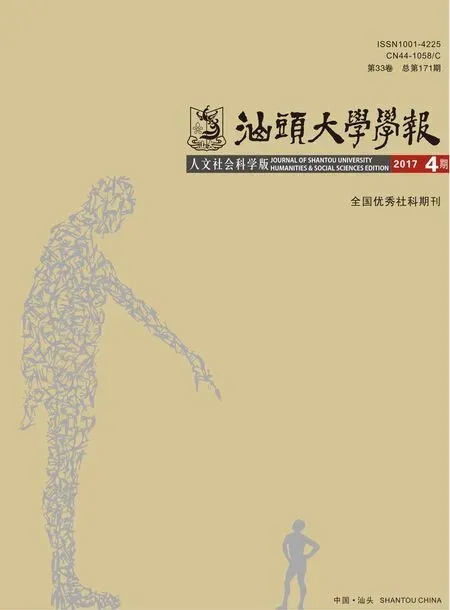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与现代性
——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学的现代性反思
俞航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与现代性
——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学的现代性反思
俞航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不同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所产生的艺术领域的“神的衰落”,俄罗斯的圣像画恪守着拜占庭传统,在东正教文化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无论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审美欣赏层面,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学都不同于从文艺复兴开始转变的西欧宗教绘画。从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开始,俄罗斯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但俄罗斯没有西欧那样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因此现代化进程较为独特。俄国作家在创作中通过对西欧“他者”的观察,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像学刻画了圣人形象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俄罗斯人在现代性体验中的迷茫、信仰和痛苦,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了人在神性消失的现代世界中如何寻找意义。
俄罗斯圣像;现代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像学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皈依东正教,俄罗斯从当时的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丰富的东正教文化。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即沿袭了拜占庭传统,并在十四五世纪迎来古代俄罗斯宗教绘画的黄金时代。当西欧绘画中的圣人形象随着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纷纷发生变化时,俄罗斯的圣像画却依然恪守着东正教的文化和艺术传统。西欧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欧社会的现代性之路并一直走到最后“上帝之死”的祛魅,圣像向宗教绘画转变以及圣人形象的自然主义刻画是现代性进程的症候之一。而在俄罗斯大地上,东正教始终扮演着救赎的重要角色,沿袭拜占庭传统的圣像则是百姓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在俄罗斯,尽管也有公开地对新教的同情,但对圣像的大规模需求却从来没有干涸过。不仅在每个房子都可以发现圣像,甚至在每个社会性的场所(商店、小酒馆、火车站、病房、甚至在妓院和监狱的囚室)也可以找到圣像。”[1]20在俄罗斯,无论在艺术创作层面还是审美欣赏层面,圣像都不同于文艺复兴开始转变的西欧宗教绘画。
尽管没有经历西欧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但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为俄罗斯奠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基石。虽然沙皇极权统治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俄罗斯一度延缓改革进程,但在19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同样迎来了现代转型。同时,俄罗斯社会的发展始终处在与西欧的对比中,而俄国作家在创作中通过对西欧“他者”的观察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不同于现代性巅峰时期西欧思想家对其的歌颂,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了现代性的冲击以及后果。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圣人形象的转变对现代性进行了思考。他的圣像学展示了圣人形象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陀氏刻画了俄罗斯人在现代性体验中的种种悲欢、信仰、迷茫、痛苦,同时陀氏思考了人在神性消失的现代世界中如何寻找意义。
一、圣人之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圣像描写引起诸多批评家的注意,甚至许多批评家将东正教圣像作为其作品的重要类比物:他的作品被称为“叙述的圣像”,他的景物描写被称为“想象的圣像”,他的人物被称为“鲜活的圣像”。①Harriet Murav指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叙述的圣像”包含了三个部分:败退,或曰降入地狱;审判;复活。See Murav, Harriet.Holy Foolishness:Dostoevsky’s Novels&the Poetics of Cultural Critique.Stanford,CA:Stanford UP,1992.(130-35). Marina Kanevskaya同样认为“圣像学通常被纳入《死屋手记》的结构之中”。See Kanevskaya,Marina.“The Icon in the Structure of Dostoevsky’s Note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Transl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Russian-American Scholars in the U.S.A.30(1999-2000):401-12.陀氏喜欢在作品中描绘圣像,一方面是俄国浓厚的东正教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圣像描写在他的作品中已经进入了象征层面。例如在《罪与罚》中,“从象征层面理解,圣像出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道德发展三个重要时刻的前景中:谋杀前,谋杀本身,忏悔。这样的模式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亦即,圣像从最初的偶然事物及描述性的功能转化为更具活力的功能,并且越来越接近主要事件的象征核心。”[2]15这些圣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圣像面对面的时候,人物展现了他们最深的自我,圣像对他们的影响将源于他们面对圣像时的姿态。”[3]5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大量描绘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寺院、教堂、当铺、酒馆以及监狱。在这些描写中,无论是作为细节还是作为刻画主人公的象征性母题,圣像都成为作品中一再出现的要素。事实上,陀氏作品中的圣像画描写不仅仅停留在对圣像的宗教母题的描绘,而是更多聚焦到了圣像面庞的隐喻意义上。作品中,陀氏多次以面孔(oбpaз)来指代圣像画(икона)中圣人的图像②在俄语中,образ主要是指面容以及形象,同时也可以表示圣像,而икона则是圣像的专有名词,来自希腊语,于1096年左右出现在古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中。。无论面容,还是圣像,在陀氏作品中主要指的是对人具体而生动的刻画,这种刻画往往使普通人的面孔有了圣像般的魔力,同时这面孔又折射出人物内心火山熔岩般涌动喷发的精神斗争。当梅什金公爵第一次看到娜斯塔霞的画像时,就被她面孔上的神情所震撼了:“这张脸令人惊讶,我相信她的命运非同一般,脸上表情是快活的,可是又极为痛苦,对吗?这双眼睛说明了这点,还有这两根细骨,脸颊上端眼睛下面的两个小点,这是张倔强的脸,十分倔强,我不知道,她是否善良?啊,如果善良就好了,一切便都有救了。”[4]47同时,在同叶潘钦家的小姐们攀谈的时候,梅什金公爵还建议二女儿阿杰莱达画死刑犯临死前一分钟的面庞。在梅什金看来,那定格的肖像画可以反映出死刑犯临刑前的精神旅途。
尽管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欧慢半拍,但是19世纪中叶无所不在的现代性同样将俄罗斯男男女女卷入令人昏眩旋转的激流之中,陀氏也不得不面对现代生活带给他的“震惊”③本雅明指出,机械(现代文明的象征)以它轰然的节奏打破了个体生活的整体。在机械面前,人要么通过接受训练变得合乎规范,要么毫无防备地陷入震惊。本雅明把“震惊”看作波德莱尔作诗的法则。,其中一点就是作家发现他从小所熟悉的圣像变了。虽然陀氏作品中的圣像描写以及其与人物面庞的关联深植于东正教的文化土壤中,但他描绘了圣像中圣人形象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承载了他的焦虑和痛苦,承载了他就人在神性消失的世界中如何活下去的形而上的探讨。1862年,陀氏第一次出国旅行,关于作家对欧洲的最初印象,他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做了描绘。他在德国、法国和巴黎均有逗留,观察了欧洲文明。在《巴尔》这篇文章中,他传达了对这座“昼夜忙碌和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城市”的印象,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这里,汽车尖叫着轰鸣着;铁轨在鳞次栉比的街区间延伸;“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被煤烟熏染的空气,富丽堂皇的街心花园和公园,可怕的城市角落,如魏特察贝里(Вайтчапель),还有半裸着的,粗野和饥饿的居民。”[5]406在《印象》里,我们可以感到陀氏对西欧现代文明的思考,在现代文明坚固的水晶宫笼罩下,他看到的不是现代化带来的繁荣、不是便利、不是科学,而是惰性,是抑制生命活力的唯理主义。而这可怕的力量带给陀氏的恐惧在他看到小汉斯·霍尔拜因的画作时达到了极致。1867年,陀氏再次出国旅行。在8月份的时候,陀氏在从巴登到日内瓦的路途中,停留在了巴塞尔,就在那里他看到了小汉斯·霍尔拜因1521年的画作《墓穴中死去的耶稣的尸体》。根据安娜·格力戈里耶夫娜的回忆,当她离开丈夫15-20分钟之后回到他身边时,他全神贯注盯着那幅画,仿佛被钉在了那里,“在他紧张不安的脸上有一种被吓到了的神情,这种神情我不止一次在他癫痫发作的前几分钟内看到过。”后来,陀氏对他妻子宣称:“在这幅画前一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信仰。”在那段时间他所完成的《白痴》中,梅什金公爵重复了这句评论。除此之外,陀氏对这幅画更进一步的思考还通过这部小说中少年伊波利特的叙述显示出来。在《白痴》中,陀氏试图描绘纯洁无暇的美拯救世界,对死刑判决①1849年,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被执行死刑前的一瞬间,他的死刑判决被推翻了。和惯性力②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把惯性视为第一运动法则中一切自然物质都具有的天然特性。牛顿的这个定律,给人类心灵带来了一场革命。神性被从自然中排除出去,自然所受的唯一支配力量就是惯性力,自然成为冷冰冰的机器。尽管17世纪的科学家哲学家们并没有放弃有神论,但他们意识到了科学法则与宗教法则之间的矛盾。那时上帝依然存在,但却被笛卡尔、霍布斯等机械论哲学家与其造物分割开,从而否定了上帝出场的必要性。自然概念在机械哲学的改造下成为“物质力学”和普遍惯性的代表,代表着人无法改变、只能服从的审判力量。的反抗串联了整部小说。在小说一开始,梅什金公爵对死刑的一番言论显示了他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关切。西方司法制度中人造斩首机是自然力学的产物,从形而上意义而言,人类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的法则,并最终走向死亡。从隐喻意义上而言,每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在基督教教义中,复活与拯救的弥赛亚意识给了人类希望。基督代表了希望——终有一日,人类会脱离死刑判决。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基督一般的梅什金是如何竭力使娜斯塔霞·费利帕夫娜走向新生的。但是故事最终,他没有使娜斯塔霞获得新生,更没有能够让她摆脱死刑判决。娜斯塔霞把罗戈任看作死刑判决的化身,她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无法在梅什金的帮助下走向精神上的复活,于是一次又一次从梅什金身边逃走。当梅什金前去与罗戈任会面时,罗戈任试图让梅什金明白,娜斯塔霞认为她的死刑判决是无法被推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随后他引导梅什金公爵注意到墙上的一幅画,这就是临摹霍尔拜因的《墓穴中死去的耶稣的尸体》,此时梅什金体会到了娜斯塔霞绝望的心情。正如后来伊波利特再次叙述的那样,这幅画描述了耶稣死亡时身体上所遭受的巨大的痛苦,神性之光在死者脸上消失殆尽,它画得如此惟妙惟肖,以至观者感觉到:要战胜自然法则,要让耶稣复活是绝无可能的。而娜斯塔霞的毁灭同样是最终结局,她要获得新生也是绝无可能的。霍尔拜因画作上的耶稣提醒我们,人类仅仅是凡俗肉体,无一例外地被判处了死刑。
在梅什金的生日宴会上,患了绝症的少年伊波利特再次提到了霍尔拜因的画作《墓穴中死去的耶稣的尸体》。他同样也是在罗戈任家看到那幅画的,这幅画作为表现自然无边力量的表现形式一直萦绕在伊波利特的心头。他说道:“这幅画中,除了自然什么也没有,而这恰恰表明,无论是谁,他的尸体总是要遭受这样的折磨。在这幅画中,关于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4]522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美视为一种启示性的力量而言,伊波利特对这幅画的注释是意味深长的。罗伯特·路易斯·杰克逊认为:“汉斯·霍尔拜因的油画显然是糟糕透顶的艺术品,因为它强烈干扰了人类在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宁静。它是绝望美学(aesthetics ofdespair)的化身。在信仰领域里,以畸变的形式与它一齐出现的伴随物就是无神论。”③杰克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篇题为《1861-1862年艺术学院展览会》(The Exhibition at the AcademyofArts,1861-1862)的文章中,进一步找到了他信奉下列观念的证据:“艺术……改变显示,在道德的层面上使其变得更美。”杰克逊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了展览会上的一幅画,即克洛德克(M.P.Klodt)的《最后一个春季》(The Last Spring),说它对死亡作了过度详细的描述:“不,这不是人们要求艺术家去做的,不要照相一般的逼真,不要机械一般的精准,所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更宽阔、更深刻的东西。”因此,“机械”的艺术家缺乏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过度追求现实主义的艺术家比作镜子,说他们只会“被动地、机械地反映”。[6]67丽莎·克纳普指出:“使这幅画成为‘糟糕透顶的艺术品’的,使这幅画体现了‘绝望美学’的,本质上是它的自然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自然主义是再现唯物主义景观的表现手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艺术提供了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自然的法则被艺术家随心所欲地中止了。但是在霍尔拜因的艺术创作中,自然的法则却发挥着与物理世界中的自然法则完全一样的作用,因而也以极其险恶的形式肯定了大自然至高无上的地位。霍尔拜因的油画阻止人们相信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教义,那便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圣经·罗马书》8:21)’”。[7]134-135
伊波利特对这幅画的观点可以被解读为从启蒙主义开始在现代性中达到顶点的“上帝之死”的寓言。道成肉身(word-become-flesh)的基督在放弃了神性,变成了凡人,遭受了严酷的“皮肉之苦”。这种痛苦在霍尔拜因的画中已经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而是被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生理意义上的。当将这种痛苦转化为真实的圣人形象之后,那些亲眼目睹这具尸体的观众怎能够相信“这个肉体凡胎也能复活”?伊波利特甚至想象如果耶稣自己看到了这幅画,还会为了救赎世人的苦难走向十字架,像那样死去吗?启蒙主义中,机器般的自然作为新神比过去任何动物性的神更加毫无怜悯:不但消灭了人类肉体的生命,也消灭了耶稣脸上的神性痕迹,神圣之谜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被埋葬。“在现代主体的注视下,在霍尔拜因的画作中,道成肉身死亡了。在文艺复兴艺术中,随着直线透视的逐渐发展,“超验感官”(the suprasensual)再也不能以自身的无限灌注现实了。在现代主体看来,所有存在都成为尘世的。正如潘诺夫斯基所言,‘透视画法,将真实转化为事物的外观,仿佛将神性降低为一个人类意识的区区题材。’”[8]221在霍尔拜因的画中,死去的耶稣的身躯被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真实观细致地刻画出来,并被拘禁在一个直线透视将所有神性都排挤出去的空间中(长条形的、狭窄的、木制的坟墓)。即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依然保留着对耶稣圣像的信仰,文艺复兴的圣像却逐渐脱离宗教,成为了自然的模仿,美学上的“镜子说”风靡一时;自然代替神性成为了绘画的最高范本,无论是解剖学还是透视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帮助画家们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自然、反映人。
然而陀氏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上看到了几个世纪之后现代人的焦虑。自然已经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自然,而是在启蒙理性的改造下成为判定人类必死命运的机器。对于非常年轻渴望生命却身患绝症的伊波利特来说,霍尔拜因画中的耶稣形象成了沦落的、颓唐的、受制于自然法则的形而上符号的化身。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丝毫重生的希望。事实上,陀氏并不是臆断。霍尔拜因的创作时期虽然处于人的信念复活的文艺复兴时期,但是画家深深地认识到,即使人类拥有权力、财富和知识,在这个世界中占重要地位,但是依然无法逃脱死亡的阴影。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使节》中,那个通过变体画法展示的怪异骷髅①当时欧洲正笼罩在黑死病的阴影下,最后霍尔拜因也是死于黑死病。非常突兀却又如此和谐地占据着画作的前景。与之相关联的是画作背景中左上角绿色帷幔微微拉开露出的耶稣受难像。画中两位使节中间那本路德赞美诗鲁特琴象征了人的兴起和神的衰落②当时宗教改革正在欧洲酝酿着,这幅画作的背景正是亨利八世与安·波林秘密成婚,并试图与妻子凯瑟琳离婚,脱离天主教。而画中两位使节正是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派出来进行斡旋的。,他们处于画面的主导位置。但是耶稣死亡所象征的宗教的逝去难道不正指示着人身上神性的逐渐消失与自然法则的逐渐占据上风吗?而这正是几个世纪之后陀氏在现代世界中所焦虑的。陀氏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的一个直接源头就是几次游历西欧的所见所闻,包括霍尔拜因的画作。西欧文艺复兴开始的绘画一方面因高扬人的个体意识和创作自由而攀上了艺术的高峰,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对神性的神秘体验而成为了带给观者审美享受的世俗艺术,但东正教的圣像画却却一直保留了超越现实、与彼岸世界进行精神交流媒介的重要功能。
二、俄罗斯东正教圣像对文艺复兴的拒绝
11世纪基督教分裂为希腊正教(东正教)与罗马公教(天主教)。在公元988年“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罗斯皈依东正教,并从拜占庭接受了浓厚的文化传统。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沿袭了拜占庭传统,在十四五世纪迎来了艺术的黄金时代。当文艺复兴时的西欧绘画中的圣像纷纷发生变化时,俄罗斯的圣像却始终恪守着东正教的文化和艺术传统。在东正教的文化氛围中,圣像画承载了传播教义和宗教体验的意义,“道成肉身的神通过圣像的面容传递恩典之光,信徒通过祈祷进入神秘的宗教体验,而圣像画的存在超过了物质层面的形式,被信奉为直接指向它所描绘的上帝、耶稣基督、圣母、天使和圣徒,圣像描绘的画面有一种神圣精神的象征,是理想化人格的符号代表。”[9]141正如《天成救主》(《非人工的救主像》,Спас нерукотворный)的传说①相传在东方城市埃得萨,国王奥加里得了麻风病久治未愈,派人去请能行奇迹的基督。基督没有去但也没有拒绝国王的请求。他让人拿来一块空白画布,然后将自己的脸印在画布上,于是他的面容便自动非手造地印在画布上。国王一接近画布,病就被治好了。所显示的那样,圣像中圣人的面容绝不是尘世匠人的工艺,而是基督的神性自身的展现。而东正教的圣像表现与圣像学也与西欧文艺复兴的大相径庭,当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画吸收了古代希腊的艺术表现了富于生活气息的美感时,俄罗斯的圣像画却依然延续着从拜占庭流传下来的一整套视觉公式、色彩表现、圣人形象等规范和传统。
首先从圣像与观者的关系来看,在东正教中,圣像是以一定的艺术方法来表达神学思想的复杂机体,它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审美价值,而是宗教价值。因此,当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圣像画的观者厌倦了中世纪的圣像画,转而将目光投向富有生活气息、带给他们更多美感经验的画作时,在俄罗斯观看圣像仍然不是一种审美活动,而是一种祈祷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对美的体验转变为对神的认知。“阅读圣像的第一个水平是字面的认识,即了解题材,所画的是谁或什么,是与哪一段圣经文本或圣徒生平相对应的;第二个水平是象征上的认识,即揭示这幅画所包含的神学思想,即理解表现手法,包括色彩、光线、姿势、空间、时间、细节等;第三个水平是教导上的理解,即体会圣像的道德教导方面,理解这一圣像具有哪种神圣性的典范意义。这时圣像与祈祷者(观赏者)的反向联系,不是观赏者认知圣像,而是圣像作用于观赏者,圣像成为主动者,观赏者成为被动者;第四个水平是神秘解释,从可见的东西开启出不可见的东西,进入与圣像原型的直接交流,从而开启圣像的深刻内涵。圣像是朝向彼岸的窗口,神圣力量和拯救之光透过这个窗口达到祈祷者。”[10]27潘诺夫斯基在区分肖像学(iconography)和圣像学(iconology)时指出为了更进一步解释作品,便不能仅仅局限于描述性的肖像学,因此他主张恢复一个旧词汇:圣像学。他认为:“肖像学(iconography)这个词的后缀‘graphy’是从希腊文的动词graphein(写作)发展而来的,它暗示了一种对过程的纯粹描述性方法——有时甚至是叙述性的方法。圣像学的后缀(iconology)的后缀‘logy’——从logos(希腊语:理性、理念)衍化而来,意为‘思想’或‘理智’——包括了某种解释性的内涵。”[11]39虽然肖像学与圣像学的词根都是icon,但是更为古老的圣像学(iconology)更加强调对内在含义的阐释,需要观赏者的综合性直觉,使观者在观看画作时融入到画作的象征意义中去。东正教的圣像观赏正是既强调肖像学的观赏方式,又强调圣像学的观赏方式,而且更多地保留了圣像学的古老含义。
第二,与东正教圣像画的目的与观赏方式相联系的是圣像画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征。古代俄罗斯的圣像画家并不像欧洲画家自文艺复兴时起执着于追求笔下人物形象的真实感与立体感。文艺复兴时期,“镜子说”的盛行反映了一种新的真实概念的兴起,那就是画家所画的图像必须和他们眼睛所看到的自然本身相一致。镜子的表面是光滑的、是澄清的,因而不会歪曲自然界的客观事物。这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对柏拉图的模仿论的改造。柏拉图的模仿论是模仿最高的原型,摹本都跟原型相似,但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完美。因此,可以说每个摹本都是原型的(这个词来自动词意为相似、相像),可译为“相似物”,也可译为“影像”或“映像”(icon一词的由来)。但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模仿并不是模仿最高原型,而是模仿现实的世界,模仿自然、模仿人类。自然科学随着新的真实观念的兴起而兴盛,透视学与解剖学的发展使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能够在画布上再现人类眼睛所看到的真实物体和人体。但是在俄罗斯,圣像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具备宗教仪式意义的艺术创作。真正创作圣像的不是画家,而是圣人自己,因此东正教的圣像画创作始终保留着柏拉图的原型理论。圣像制作者的模型来自于古老的圣像,而不是自然本身。而这些古老的圣像在拜占庭传统中又是那个最初的、不是出自人类之手的圣像的副本。如此一丝不苟对历史原型的保存形成了不同于文艺复兴真实观的圣像学。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像中,凡俗之人的模型在艺术家面前伪装成神圣之物。例如小汉斯·霍尔拜因并没有简单再现经典的耶稣圣像,而是再现了一具人类的尸体。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圣母像也大多是极具人体美的丰腴的妇女形象。但是在东正教的圣像画中,圣徒形象与现实人物是很不相同的:往往是有些变形、不成比例、身体瘦长、形容枯槁。这是在宗教理念中被改造过的人的肉体理念,东正教圣像中没有鲁本斯画中那样的肉体性的胜利。在圣像中,人的头部与身体的比例一般是1∶9,在季奥尼斯的画中甚至达到了1∶11,这是为了表现圣徒的神圣性,表现他们不同于凡俗之人的肉体形象。潘诺夫斯基指出,拜占庭艺术中,圣像画家用一个固定的张开两脚的圆规在画面上组装人物,几乎脱离了人体的有机构造。头部的各种尺寸通过一个常数(“鼻的长度”)的乘积表现出来,有三个同心圆(它们都以鼻端为圆心)来确定整个外形构造。最小的圆——其半径为一个鼻长,是以眉头和两颊为轮廓的,第二个圆——半径为二个鼻长,勾画出了头部的外围尺寸(包括头发)并确定了面部的下部界限,最大的圆——其半径为三个鼻长,则穿过喉头,而且,一般来说也形成一个光环,这个方法自然而然导致了对头盖骨的高度和宽度的过度夸张,这种风格的人物,往往造成一种从上往下观察的印象。[11]94这种特殊的创作手法正是为了表现圣徒形象的神圣性,同时使观者在观看圣像时满怀宗教虔诚感,与圣灵进行交流。
绘画的立体感得益于光线,凸出的部分较为明亮,凹下去的部分则暗淡些。而东正教圣像画没有外部的光源,只有圣徒面容上明亮的光线有些许动感,整个画面基本没有立体感。光是从人物的面容和身体内部发出来的,象征着神圣性。在古代画法的圣像中,找不到光源在哪里,因此也看不到人物的影子,同样不能利用阴影来表现立体感。沃尔夫林指出:“要想产生纵深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由明暗分布和透视所产生。对透视短缩的重视(纵深的力量),使纵深呈现为运动。而在阴影的前景空间上,眼睛立即会投向后面的东西。”[12]92但是俄罗斯圣像画家并不追求三维空间的传递,都是在平面上展开形象,既缺乏纵深感,也无水平线,甚至没有光影。在画法上,圣像通过色彩由深变浅来表现人物的发光。圣像之光集中于面容,而面容之光集中于眼睛。眼睛总被作为面容的突出部分予以表现。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曾告诫众人:“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圣经·马太福音》6:22-23)因此在早期俄罗斯圣像画中,人物的眼睛往往被充分夸张。后来,眼睛不再被过分夸大了,但却依然具有特别的表现力。
在透视的表现手法上,东正教圣像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不同。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帕维尔·弗洛连斯基(П.А.Флоренский)通过考察14-15世纪的俄罗斯圣像,发现了不同于文艺复兴西欧绘画的透视法则。文艺复兴的绘画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绘画中,采用的都是符合正常视觉效果的正透视,也就是画面全部对象按照与视点的距离从近到远而画得从大到小。但是东正教圣像画多采取的是反透视,对象按照与视点的距离从近到远是按从小到大来画的,这就使所有实物平行线的画面线条的焦点不是在画面的深处,而是在画像的前面,在观看者的地点,指向站在圣像面前的观赏者。“这象征着神的世界从高处流入人的低处的世俗世界。圣像中物体的前后关系不具有透视的、绘画的意义,而具有象征的意义。这样,圣像画中的世界仿佛是反过来的,不是我们看它,而是它看我们,包围着我们。我们进入圣像画的空间越深,看到的范围越宽。圣像的世界是无限的,就像对神的世界的认识是无限的一样。”[10]45圣像画违背透视规则并不是因为画家们不懂透视和人体比例,而是因为他们的绘画理念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画家不同。圣像中的大小原则不是依据人的肉眼视觉,而是取决于圣像所要表达的信念。另一方面,在时间的理解上,东正教圣像画也与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现实主义艺术不同。现代人习惯于认为绘画是一种瞬间的艺术,画家捕捉的那瞬间是静止的。但东正教圣像画会在一幅画作中描绘两个甚至三个不同时代的情景,如同一段电影片段,过去、现在、未来聚集在同一幅画面上。例如圣像画《主变圣容节》描绘了三个不同时间段的图景:耶稣和他的门徒登上塔博尔山祈祷,他改变了面容,信徒们拜倒在山下。而两侧则是基督带领使徒上山和下山的场景。东正教圣像画的空间和时间观都表现出不同于文艺复兴圣像画的特征,因为它严格地延续和遵守了拜占庭传统与中世纪传统。
三、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的发展与现代性
文艺复兴中西欧宗教圣像画的转变过程其实是圣像转变为宗教绘画的过程。传统的圣像之所以在时间之流中变化不大,是因为圣像画家们认为他们画的是一种理念,是圣灵,而不是现实中的人。圣像是从永恒的观点来创作的,即使圣像保留了所画人物的肖像特征,但圣像的面孔(лицо)是朝向上帝的面容(лик)①лицо指人的面孔,而лик是前者的旧称或雅称,更多指圣像的面孔。,是在永恒世界中向信徒显现的启示。而宗教绘画却不再表现这种永恒的观点。虽然借用了圣经中的母题,并保留了某种训诫的含义,但从本体论意义而言,文艺复兴之后的宗教绘画只是将圣经内容作为一种题材,对之进行赏析只需要潘诺夫斯基所言的肖像学层面即可,也就是说只需了解某种文化符号系统中约定俗成的题材、形象、寓言就可以。宗教绘画中的人物与日常生活中的人物非常接近。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让圣母从云端走下来,接受教皇和圣徒的迎接,而伦勃朗笔下的圣母则具有了尼德兰的农妇的外形。这种转变在俄罗斯虽然缓慢,但依然在发生。17世纪在俄罗斯逐渐开始了圣像转变为宗教绘画的过程,最终在18-19世纪之交完成。在此期间,许多圣像已经远离了拜占庭和古俄罗斯的宗教精神,具备了古典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风格特征。例如17世纪圣像画家西蒙·乌沙可夫在作品中着重表现基督形象“人性”的一面,对人物脸部的比例和明暗透视都予以特别的重视。而到了19世纪,随着教堂艺术的衰落,俄罗斯的世俗绘画中出现了一些致力于基督教题材绘画的画家。其中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伊万诺夫(1806-1858)是最杰出的一位。他曾经到意大利去学习,在那里接触到了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基督向人民显现》。在这幅作品中,基督的形象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他的影响力是通过河岸边看到基督出现的普通人的反应来表现的。这样的一幅宗教绘画已经与传统的东正教圣像画相去甚远了,而是更多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来表现宗教在普通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在19世纪下半期的画家尼古拉·格(1831-1894)的画笔下,基督的形象与霍尔拜因笔下的基督已经非常相似,列夫·托尔斯泰曾批评他笔下的基督被过于丑化,这一反应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霍尔拜因画作的态度。
传统的延续和宗教力量的强大使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像西欧圣像画那样世俗化。但是俄罗斯社会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现代性的激流同样将俄罗斯卷入其中。西方知识分子往往把西欧的现代起点定格在十七八世纪,而俄罗斯的现代性转折则是从彼得大帝18世纪的改革开始的。彼得大帝继位之后决心改变俄罗斯以村社为主体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向西方学习,同时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之前是一片荒凉沼泽的彼得堡。彼得大帝将之设想为一个海军基地和商贸中心的结合,这座城市成为了“开向欧洲的窗口”。彼得大帝选择这里作为新的首都是为了让整个俄罗斯向西方学习,削弱以莫斯科为代表的数个世纪的传统与宗教统治。18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彼得堡成为了尘世官方文化的象征和家园。彼得一世和他的后继者引进了西方的工程师、法学家、政治学家……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只是“文明的罩蓬”,是表面的文明。在西欧,现代性的开始是从宗教改革运动,甚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重视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宗教走进了与世俗漫长而纠缠不清的张力关系之中,并最终淹没在现代性的滚滚洪流中。然而俄罗斯在18世纪之前从来没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铺垫,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一蹴而就的,是自上而下的,也是极不稳定的。1789年以后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让彼得的后继者们胆战心惊、畏葸不前,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的政治角色显然是欧洲革命的反对面,而在20世纪初的欧洲革命中,沙俄继续以欧洲宪兵的姿态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有了自身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俄罗斯人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是在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中产生的。“在这里现代性的各种涵义很可能是更为复杂的、难以琢磨的和似是而非的。”[13]224正如上面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欧之行,同样事情也发生在托尔斯泰身上。这些俄罗斯作家热爱祖国辽阔美丽深沉的大自然,大多厌恶西方文明现代化大都市。大都市在他们眼里是压制人性的可怕怪物,象征着铁板一块的西方唯理主义,在陀氏这里,则突出表现为“惰性”。陀氏认识到俄罗斯的现状必须改变,但他反思了从西方借“外衣”的方法:“总不会只是穿上欧洲的服装了,了解欧洲的风俗习惯,吸收欧洲的科学或者发明吧……是的,很可能彼得大帝最初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在只图实利、只求近期见效的意义上,开始实行改革的。”[14]227伯曼把俄罗斯的现代性称为“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并指出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迫建立在关于现代性的幻想与梦境上:“在相对落后的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还没有步入正轨,它所孕育的现代主义便呈现出一种幻想的特征,因为它被迫不是在社会现实而是在幻想、幻象和梦境里养育自己。”[13]30419世纪的俄罗斯艺术家竭尽全力要把握住“现代”这一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将经济和社会变迁所喷发的纷乱杂糅的各种能量转化为富有意义的艺术形式。
西欧的现代性是与宗教的祛魅相伴随的。在这个过程中,宗教融入了世俗社会,但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力量。“宗教发展中的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摒弃。”[15]79-80在价值领域,宗教失去了“元叙事”的地位,原本被宗教统摄的文化力量分崩离析。启蒙以对理性的追求和崇拜展开了它对人类未来的美好规划。启蒙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强化了一个工具理性占主导世界的诞生。工具理性精神伴随着启蒙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为人类创造出此前无法想象的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但是,工具理性在对客观世界的支配达到了完全胜利的同时,也将主观世界当作自己的支配对象。只要依据一种可以计算的技术化的理性方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一切都能做得最好,人在这样的工具理性的支配下成为“铁笼”中的异化物。然而,人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中都应当有价值地活着,应当始终有一个为人类的行动提供意义的庇护神,当宗教衰落了,价值理性便担当了重任。韦伯认为在价值理性中,艺术承担了世俗的救赎功能,“韦伯将艺术纳入价值理性的框架中予以说明,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种关于艺术的理解:艺术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宗教同样不可证明的对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这种信仰,首先对宗教构成了一种直接的挑战。对宗教而言,救赎来自事物与行动的意义而不是它们的形式;对于艺术而言则恰恰相反,它自有独立的表达方式,只有感性形式本身就具有救赎价值。”[16]292在人类文明史的初期,宗教与艺术是分不开的,宗教需要艺术来表现,同时又是艺术的重要表现对象。随着世俗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艺术最终脱离宗教成为了独立的价值领域。艺术从宗教中脱离,开始显现出个体性与世俗性,通过宗教传统成为艺术风格的源泉的那些元素,对于艺术而言不再重要。因为艺术作为一种逐渐自觉的、独立的、被理解的内在价值的宇宙已经建立起来,并承担起一种将人从日常生活中解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
然而,俄罗斯的一些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却对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使艺术脱离宗教的绘画表现出了异议,反而转向了俄罗斯传统的圣像。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洞察到了彰显人的力量的文艺复兴绘画与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之间有着某种吊诡的同谋关系。同时,这也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性内部某些矛盾相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冲突,象征着“创造”的现代化和作为“常规程序”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我们在第一部分中讨论的那样,文艺复兴振兴的对人的尊重与启蒙主义对理性的专爱是分不开的。一旦“人是世界主宰”这一观点占据上风,人类必然会与自然万物脱离开,并将自然客体化,同时主张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不再参与到人间的事务之中。当以理性为基础的完美大厦建成,就是人的“自由”的结束,惯性原则将占上风。俄罗斯独特的“欠发达”的现代性让俄罗斯作家通过对比西方那工具理性原则占上风的世界而发现了人类在宗教信仰中所保留的对精神世界的自由的信任与尊重。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叙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有东正教圣像情节的现实主义作品被置于模仿的较低等级。例如在奥尔巴赫的《论模仿》中,他认为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在根本上更接近于古老的基督教而不是现代西方现实主义。然而,随着俄罗斯作家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新的文学批评通过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东正教圣像学融入小说技巧来预示现代主义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结构上的破坏,正如康斯坦丁·巴什特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是现实主义者,这个美学影响——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东正教圣像学——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代主义产生之前就带向现代主义。”[17]54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霍尔拜因画作时产生的焦虑以及他在作品中描绘的古老的俄罗斯圣像并不仅仅是他的怀旧或者复古情怀,而且还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人生存的追问。外部必然性(石墙的坚硬)决定着人的外部状态,人的现实生活必须服从自然规律,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如果人仅仅屈服于外部自然规律,就会丧失内在的精神意志。而古老的圣像面孔上的神圣之光正是人的内在精神意志的写照,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圣像面庞的强调同时强调了他笔下人物强大的自由意志。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梅什金还是伊波利特,在看到霍尔拜因的画作时都在反复思考,这其中贯穿了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试图通过这种自我意识在工具理性的牢笼中使人复活,使人的精神信仰复活。
[1]О.Ю.Тарасов.Икона и Благочестие Очерки Иконого Дела в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и[M].АО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школа,1995.
[2]Jefferson J.A.Gatrall.“The Icon in the Picture:Reframing the Question of Dostoevsky's Modernist Iconography”.The Slavicand EastEuropean Journal[J].2004,48(1):1-25.
[3]Ollivier,Sophie.“Icons in Dostoevsky’s Works”,Dostoevsky and Christian Tradition[M].Gegorge Pattison and Diane Oenning Thompson(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张捷,郭奇格译[M]//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9卷.陈焱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5]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冬天记的夏天印象[M].满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Robert L.Jackson.Dostoevsky’s Quest for Form:A Study of His Philosophy of Art[M].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7]丽莎·克纳普.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M].季广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8]JeffGatral.“Between Iconoclasm and Silence:Representing the Divine in Holbein and Dostoevskii”.Comparative Literature[J].2001,53(3):214-232.
[9]郑伟.圣像之殇与人的复活——背道而驰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与文艺复兴天主教绘画[J].俄罗斯文艺,2014(2).
[10]徐凤林.东正教圣像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M].傅志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2]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艺术风格学——美学史的基本概念[M].潘耀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4]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M].刘季星,李鸿简,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1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87.
[16]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7]Barsht,Konstantin A.“Defining the face:observation on Dostoevskii’s creative process.”[C]//Russian Literature, Modernism and the Visual Arts.Ed.Catriona Kelly and Stephen Lowell.Cambridge:CambridgeUP,2000:23-57.
(责任编辑:李金龙)
I106.6
A
1001-4225(2017)04-0050-09
2015-03-14
俞 航(1987-),女,浙江绍兴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