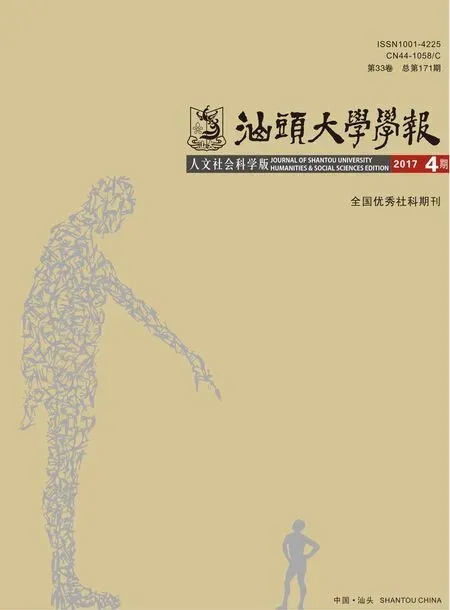中国早期造物演进机制探赜
丁杰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早期造物演进机制探赜
丁杰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早期造物演进具有多维特征,其脉络繁琐杂乱,并无定式。若仅以传统的线性思维将器物按造型、功能、纹样等具体形式进行分类罗列难免以偏概全,陷入只陈述客观事实却难以厘清其传承关系的局面。从环境、意识、技术、文化、经济等多元维度去考量中国早期造物演进中衔接更迭、承袭变化的内在机制,方能避免此类疏忽,真正做到以全面客观的视角去审度其发展规律。
中国早期;造物;演进;机制
一、物竞天择
适应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法则,也是我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根本前提。在非洲发现的距今1400万年前古猿砸击取食的自然石块[1]108,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利用自然工具的例子。它直观地反映了古猿对环境的适应程度,虽然这种适应仅为本能的、被动的,从中很难看出多少创造性,但从其目的、手段与结果来看,这一简单的举砸动作已然具备了人类造物发展所需的必要因素。
随着对环境的认识逐步提升,其适应也愈发主动,人类不仅学会了依据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存行为,还掌握了更具能动性的创造方式。从旧石器时期的木器、骨器到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陶器,这些造物品类均是人类对环境适应的证明。以石器为例,从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的一系列石质工具中发现,几乎所有的石器都拥有相似的形状,它们都是经圆或椭圆的天然石块打制而成,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同时期的石质工具也几乎都拥有相似的外观。这绝非巧合,而是人类适应能力的体现,是与环境长久互动的必然结果。试想当猿人在把持石块的时候,总会因为其不规则的形状而感到不适,它们或尖或棱极易伤手,在制作工具的过程中也不易发力。经过反复地试验摸索,猿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用于制作工具的原材料,即砾石。这种圆润光滑的石头不易伤手,大量分布在河滩两岸,它们易于获取与替换,硬度与韧性也利于制作工具。北京猿人对石器原料的认识过程即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此间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考验着他们的适应力,而适应力的提升又进一步激发了其创造力,外部环境的改变促使内部环境作出相应调整,北京猿人的石器制作工艺便在这内外因素的相互博弈与牵制中逐渐发展成型。
石器工艺的演进提升了造物品质,以前只能依靠双手或牙齿勉强制作一些粗糙工具,现在却可借助先进技术来制作高级工具,这些工具无论在功能性亦或耐用性上都较前者有极大提升,由北京猿人制作的石器中便可见其端倪。首先,从遗址的早、中、晚三个文化层出土的石器来看,早期的石器类型较模糊,存在一器多用的现象,而到了中晚期,器物的功能愈加明确,类型也趋于细分,一器多用的情况基本消失;其次,砍砸器在晚期衰落,尖状器、雕刻器、石锥却得到发展,器型由大变小,工艺也更为精细,说明制作水平明显进步;最后,修整技术显著提高,晚期还出现了指垫与软锤两种修整手段。[2]51,182北京猿人造物工艺的进步为新技术与新品种的出现提供了必要准备。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程度与由此所激发出的创造性呈正比,从当初的天然石块开始,人们逐渐将其分化成砍砸器、削刮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类别,进而又演化为石球、石刀、石斧、石锛、石钺等无数的分支系统,由砾石母体蜕变而来的石器家族正不断地刷新人类造物品类的更新频率。
石器作为中国早期造物活动的重要产物,无论是北京猿人粗糙的砍砸器与削刮器,还是山顶洞人运用钻孔、磨光、刮挖等新工艺制作的细石器,都明确彰显了适应在造物演进中的驱动作用。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扩大,在石器取代木器,青铜器取代原始陶器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适应行为在造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可见物竞天择的道理不仅适用于生物进化理论,在人类造物发展的进程中亦扮演了关键角色。
二、意识演化
思维意识是人类行为的指南针,离开它,造物活动就无从实现。从对目标物体的设想,到实现设想的技术手段,再到目标成型后的使用方式,我们总以头脑中的预先构思为模板,然后再去逐步完成。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创造事物,但意识不会凭空产生,它的生成与发展呈现出波浪型的发展模式,是许倬云先生所讲的“一波接一波的推背行”[3]11,即“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的运动过程。[4]5-7中国早期造物意识亦是遵循这种运动轨迹逐渐发展成型,但它从何而来,有着怎样的承袭关系,在中国早期造物发展中又如何体现,起到何种作用?回答这些问题,仅从夏商周三代的留存器物中去分析已难厘清思路,因此需要我们将目光退回至中国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造物活动中去寻觅线索。
农耕社会以来,生产力的提升促使人类的心智日趋健全,随之出现的原始崇拜、审美意识、阶级分化等现象激发了人们对天地、对神灵、对祖先的想象。该意识体系的形成直接侵染了当时的造物活动,因此反映天圆地方、四方神只、社会伦理的造物意识便成了中国早期造物世界的普遍现象。[5]53意识的演化使得一部分实用器开始向礼乐器转变,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其形制外方而内圆,外壁坚实方正象征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内部圆润中空,象征广阔的苍穹,人们通过它与天地进行沟通,这是中国早期社会对天地形象的抽象概括。方圆结合的造物意识从原始时期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如殷商铜器厚重沉稳,多有方圆结合的设计实例,铜鼎鼎身方正,四足浑圆,双耳外方内圆。另在车体形制的设计中亦可察觉古人方圆结合的造物意识,“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6]122如果将这些器物与良渚文化的玉琮进行抽象比较的话,便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早期形成的天地观念对器物造型演进的影响。
意识演化对造物的影响是全面的,不仅体现在器型的发展中,对纹饰的演进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将新石器时期各个文化区域的造物纹饰进行串联,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主线,即“简单抽象-单体具象-复杂抽象-群体具象-抽象与具象结合”的演进轨迹。以原始彩陶为例,初始阶段的彩陶纹样仅由简单的几何线条组成,这可能是对塑胚过程中遗留在陶胚表面的印纹的模仿,所以呈现出了围绕器型旋转的连续几何图形。随着思维意识的不断进化,这些抽象的几何线条逐渐构成了一些简单的如蛇、鸟、鱼、蛙等自然界中的具体物象,此后人们又根据物象的图形特征对其进行分解,分解后的几何单元再以统一化的手法作变形处理,以致这些解构单元在重组时都具有一定的共同基础,[7]182使得重组后的纹样趋于和谐统一,这种以单组或几组连续重复排列的纹样形式历经发展终成为中国纹样设计中最为普遍的结构形式。
除了连续装饰纹样,一些单独纹样也在造物意识的演进中悄然发生改变。三代青铜器表面常见的饕餮纹饰从正面看呈左右对称状,纹饰内容仅包含饕餮面部形态,兽面双眼呈卵形,嘴部下突,在器型边缘以及与饕餮纹之间的留白处辅以云雷纹衬底。这些特征均与新石器晚期良渚玉器中的兽面纹极为相似,只不过后者的形式更加简单,装饰层次也更为单调。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却十分明显,李学勤先生认为三代饕餮纹继承良渚兽面纹的现象并非偶然,[8]42-48这种承袭关系验证了具有特殊含义的幻想型纹饰在原始社会末期便已成型。这些神怪形象是中国早期造物意识的外在展现,体现了中国早期社会中人、神、权之间的结构关系,是造物意识与当时社会生活互相作用的产物。
北京时间2018年11月3日,在第八赛季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当中,中国IG战队以3比0的比分战胜了欧洲natic战队,成功为LPL拿下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总决赛冠军。
从自然中的具体物象逐步演绎出具有表征功能的神怪形象,从天圆地方的自然地理观衍生出中央优于四方的社会人伦观,意识的演化逐步将中国早期造物从纯实用性中分离出来,成为实现中央帝王领属四方藩臣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神圣性与合理性的途径与依据。[9]88
三、技术革新
技术指标是人类生产力的直观体现,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一些列工艺变革是中国早期造物发展的重要推力。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冶炼技术的成熟使得造物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功能性与装饰性俱佳的青铜器迅速取代了原始陶器,成为三代造物活动的主要载体。而青铜器的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中国早期技术工艺不断积累蜕变的结果。先人在开采石器原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矿石的存在,在烧制陶器时逐渐掌握了塑范与冶炼技术,后人又掌握了铜、锡、铅的调配技术,经此一系列的技术发展才能让铸造青铜器成为可能。
青铜的铸造工艺大致分为三个环节。初为冶炼,包括选矿、初练、提炼三个步骤;再者塑范,包括制模、塑范、合范三个步骤;最后浇铸,包括浇注、凝固、修饬三个步骤。其间还会根据器型的变化而细分出不同的工艺技术。早期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较为简单,以泥制模便可,东周以后器型纹饰繁缛多变,多以腊制模;塑范工艺也分为单范与多范,器型较小者塑单范,器型较大者用多范,如器型过于复杂还可以采用分铸法,而分铸法又分为浑铸与焊接两种技术。从当初的剑、斧、铲、矛等简单工具,到后期的鼎、爵、卣、壶、尊、鉴、盘等复杂日用器,青铜铸造技术的革新使得青铜家族的面貌不断发展变化。
一种技术的突破带动了其它相关技术的协同发展,连锁反应式的技术井喷助推着中国早期造物进入了更为全面的发展阶段。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间接催生了冶铁技术,铁相较于铜更硬也更具韧性,将铁运用到造物领域极大地缩短了物资的生产周期,从而提高了中国早期社会生产的运转效率。由于金属工具的出现,建筑木作技术迅猛发展,如斗拱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早期建筑屋檐深度不足的情况。通过置于柱上斗拱的外延使得屋檐下探成为可能,这种技术既可以增加建筑高度,提高室内光线通过率,还能扩大屋檐面积,增加门前廊道宽度,避免雨雪顺檐而下溅至屋内。同时,城建规划、舟车制作、纺织工艺、兵器锻造、礼器加工等制造业技术均相应革新,不断涌现出的新工艺将中国早期造物技术逐渐推向了一条标准化与规范化的道路,其成熟标志便是《考工记》的出现。
作为一部记录中国早期造物技术规范的成书,《考工记》详细总结了先秦时期中国手工业领域的诸多技术法则,其中对造物总则的阐述十分精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6]117该法则概括了手工业制造的基本技术原理,即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的统一。在手工业时代所有材料都取之于自然的情况下,同一种材料长在什么地方、哪一季节采取,都直接关系着造物的质量。[10]8天时、地气、材美、工巧为造物的四个前提条件,稍有缺失即非良品,所以才会出现橘逾淮水为枳、鸜鹆不逾济水、貉不逾汶水的现象。应此原则,该书相继对舟车、兵器、礼器、日用器、皮革、丝绣印染、金属工艺、城邑营建等技术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制造业领域。
以制弓为例,先秦六艺“射”居其一,弓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考工记》将制弓单独列为一项技术来说明。据书中记载,当时的制弓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化程度。制弓首要选材,材美方能工巧,而要做到材美则需顺应天时与地气,这符合应天时、顺地气、取材美、施工巧的逻辑顺序。制弓由造干、做角、拉筋、胶粘、缠丝、髹漆六道工艺组成,六道工艺又分别对应六种材料,造干是为了让箭射得远,做角是为了让箭射得疾,拉筋是为了增强箭的穿透力,胶粘用以粘合干与角,缠丝辅以坚牢,髹漆抵御霜露,故合此六材以为良弓。先看制干,干由木制,通过对木材的审势来辨别材料的成色,适合制干的木材共分七种,最优为柘,最次为竹,优者视之色显赤黑,叩之声发清扬,且质地坚密、张弛有度,“柘材为弓,弹而快放。”①《太平御览》卷九五八引《风俗通》。当材料确定以后还需因材施艺,如欲射远,则需用埶,即反顺木材的曲势来制作;若想射深,则需用直,即让干材厚且直。而且在剖切干材时不可斜行,否则伤及脉理,箭发枉曲。《考工记》对弓角的制作技术也有明确的标准与规范,“角长二寸有五尺,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6]132角长二寸五尺约合50厘米,三色是指牛角的根部应灰白,中段应发青,末端应丰满,不失理即为三色衔接协调,这样的牛角与一头牛的价值是相等的,称为“牛戴牛”。其后的拉筋、胶粘、缠丝、髹漆各道工艺都有相应的规范标准,筋细者小而简长,筋粗者圆匀润泽;胶色朱红且干燥,深瑕且光泽;丝色欲沈②丝欲沈,即丝色如在水中一样,光泽鲜明。郑玄注《考工记》云:“如在水中时色。”贾公彦疏:“丝欲沈则据干燥时色还如在水冻之色。”;漆色明澈。《考工记》不仅对弓的选材与制作技术进行规范化说明,还将制弓的时节分配、易忽略的瑕疵、成品检测,以及使用与维护等细节逐一描述。从选材到制作,再到检验与维护,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模式浸润了中国早期手工业生产中的每个环节,让造物行为变得有据可依、有理可循,这在生产力低下、民众愚钝的时代局囿中尤显弥珍。
四、文化交融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发展出了众多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化区域。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文化区域整合为六大地理单元,分别是以山东为中心的东部地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鄱阳湖与珠江三角洲为轴线的南部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11]35中国早期造物活动在此六大区域中生根发芽,各自形成了与其区域文化相对应的造物文化,它们之间相互浸染、兼容并蓄,构成了中国早期造物文化的多元统一格局。
六大区域的造物文化均有着极具代表性的设计符号,如东部地区龙山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黑陶、蛋壳陶、袋足鬶;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是玉雕龙、女神庙、鳞龙纹;中部地区的仰韶文化是形式丰富的彩陶纹样;西南地区的大溪文化是筒形陶瓶、陶纺轮,而南部地区的石陕文化是印纹陶、白陶;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则是玉琮、玉璧、祭坛。[5]50尽管不同地域的造物文化各有其鲜明的设计风格,但每种文化之间也包含了众多共同的造物类型。以彩陶为例,虽然彩陶是中部仰韶文化的设计符号,但其它区域也都生产彩陶,只是中部地区的彩陶形式更为丰富,纹样愈加生动,表现尤其突出,且影响了其它区域的彩陶制作。如河南陕县庙底沟的彩陶纹样以红底黑花为主,图案多是围绕器型旋转的变形几何纹,从重庆巫山大溪出土的彩陶筒形瓶上可以看到同类的旋转几何纹,而在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的陶器上也能找到类似的纹样痕迹,这也间接佐证了当时各地域之间的持久交流。
六大区域的交流与碰撞加速了中国早期造物文化的融合速度,那些最为明显的融合痕迹往往先在不同文化区域的交界处出现。据苏秉琦先生研究,中部庙底沟文化与北部红山文化的“撞击”最强烈,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11]99而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也出现了类似的造物融合现象,在江苏与山东的交界地首先出现了交融渗透情况,鲁南与苏北的墓葬中就同时出土了蛋壳黑陶器与兽面纹饰,而且制作水平较良渚与龙山文化的核心区更为精细。文化的交融推动了造物技术、风格、功能等关键环节的演进,中国早期造物多元统一的整体格局便建立在这种融合的基础之上。
历经大小氏族间的吞分合散,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风貌为之一变,中央统领藩邦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国家机器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区的深入交流,亦激发了造物文化的全面融合,各种文化间的造物差别日益模糊,那些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设计语言相互糅合,继而形成了一种多元和谐的造物风格。我们在商周铜器中便可窥探不同文化的交汇痕迹,以鼎为例,作为礼器,鼎由三足器演化而来,而三足陶鬶则是龙山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从鬶的器型来看三足分立便于生火,器身中空用于烹煮,颈部倾斜敞口方便倾倒,是明显的日用器;而鼎亦始于三足,鼎身浑圆中空,双耳立于鼎身之上,同具烹煮功能。可无法笃定后者就是龙山文化的衍生品,因其身上还存留了其它文化区域的遗传密码。若将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与青铜鼎上的兽面纹进行比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清晰。再将目光放至整个青铜家族,会发现每种器型及纹饰都能在不同原始文化区域内找到其母体,除了良渚文化的兽面纹,仰韶文化的蛇纹、鱼纹、蛙纹、龟纹、鸟纹、太阳纹以及一系列变形几何纹难道不是商周铜器上那些绚烂纹饰的起源吗?
五、产业分工
造物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从本质来看属物资生产范畴,当其发展至一定程度,便会显现出经济属性。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生产,生活物资出现剩余诱发了物品等价交换的经济现象,在生产、交换、获取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生产物资与换取物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种经济利益激发了中国早期造物发展的提速。马克思说过,“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区别的共同体或其它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12]106原始社会的商品交换亦从不同区域的交界处开始,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内总能找到来自其它区域的生产物资或产自其它地区的原材料,其中既有通过战争手段获取的战利品,也包含利用经济渠道由商品交换得来的物品。不同的物资与材料通过经济手段以商品的身份在六大文化区域内穿梭不已,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供求关系的消长,大量的手工业人员、技术、物资正悄然地向着专业化、分工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夏商以降,造物品类不断完善,制作水准显著提升,其中不乏工艺先进、结构复杂之作。完成它们需先将整器进行分解,分解后按不同功能逐一制作,最后再拼装聚合,整套工艺已非独力可成。手工业领域开始出现分工合作,这虽是一种初级的产业分工,但带来了更加快捷的生产效率,更为精细的制造工艺。造物的细化与精准使得各个领域更为专业,所成之物愈加精良。以制车为例,车是古时贵族出行的必要工具,制车在木作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制车工艺异常复杂,整车分别由轮、盖、舆、辀四大部件组成,每个部件又根据不同规格与用途细分为若干零件,因此若想制作一架整车仅靠一两个工种是无法完成的。先秦制车业是产业分工合作的典型,“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6]118当时从事制车行业的匠人数量极多,按工种分为轮人、舆人、辀人,其中轮人专攻轮与盖,舆人专攻厢,而辀人则专攻辕、轴、衡。每种工艺都形成了一套独立且完备的设计施工方法,仅车轮制作就由制毂、制辐、制牙三套工艺组成,它们均按选材、制作、检验、使用等环节来制定详尽的技术说明。如对毂材的选用就分阴阳之别,阳指毂材的向阳面,因其终年日晒故稹理而质坚,阴为毂材的背阳面,因其缺少日晒故疏理而质柔,所以在砍伐毂材后要用火去烤其阴面,使得阴阳两面质理相等,用这样的材料做出的毂即便旧了也不会变形。除了毂,辐与牙也有独立的制作流程,三者各行其道,又相互配合,终而合成了优良的车轮。
精细的分工与专门的作业让先秦匠人的制作水准日益精湛,不仅制轮工艺高超绝伦,舆人、辀人的工艺水平也在产业分工的背景下突飞猛进。辀人制辕,曲直相宜,粗细有度,由于辕作为“任木”①凡承受车辆荷载的木材即为“任木”。“凡任木,任正者”,郑玄注:“目车持任之材。”起承重之用,是连接车厢与马匹的重要部件,因此工匠对它的处理尤其严格。辕身势曲,不同的车辆对应不同的牵引工具,所以对辕身曲直的掌握十分谨慎,稍有疏忽便使行车不畅。如辕身过直,在平缓的路面行车尚可,凡遇起伏,车体必易倾覆;若辕身过曲则伤其质,行车过程中易发生折断。因此辕身曲度深浅适中才会让行车既稳又疾,无论乘车之人还是驾车之人亦或马匹都感到舒适。
除了木作行业,金工行业亦因产业分工而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早期的简单工具到后期的复杂礼乐器,金属工艺从源头开始分流,形成了若干独立的制作门类。通过分工,匠人各取所长,每种金属加工技术都由专门的群体所掌握,如上齐①齐,如剂,指合金。上齐即铜锡合金中含锡较少者,下齐指含锡较多者。郑玄注:“多锡为下齐,大刃、削杀矢、鉴燧也;少锡为上齐,锺、鼎、斧、斤、戈、戟也。”之筑氏,下齐之冶氏,乐器之凫氏,量器之氏,镈
六、结 语
张道一先生在评价中国美术史学研究时说:“一提到美术传统,无论是当行议论,还是见诸于著述,都习惯将它穿成一条线。从原始彩陶到商周青铜器,以后是晚周帛画,秦砖汉石,再以后卷轴兴起,分宗列派,如此而已,历史的具体事实是存在的,但在传承的关系上是否客观,便值得怀疑。”[13]57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设计史的研究。中国早期造物的演进更迭具有多维特征、繁杂琐碎,按传统的线性思维去分析既不能窥其全貌,更无法梳理其中的传承脉络。在其演进过程中,既有外力制约的拘囿效应,也有内部调整的适应结果。内外因素的碰撞与糅合使得中国早期造物不断自我革新、进化完善,从而焕发新的机制来适应新环境。若仅以器物的工艺、造型、纹样等具体形式的演变,对其进行分类罗列,难免以偏概全。研究设计史需要我们以更为联动的视角去深入其内部,寻觅造物品类更迭断层、衔接变化的内在原因,厘清其演进机制,才有可能从多元维度去解读中国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
[1]刘晓纯.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108.
[2]张之恒,吴建民.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51,182.
[3]许倬云.西周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1.
[4]许倬云.历史分光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5-7.
[5]李立新.中国设计艺术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3,50.
[6]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82.
[8]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东南文化,1991(5):42-48.
[9]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88.
[10]张道一.考工记注释[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8.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5,99.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6.
[13]张道一.张道一文集:上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57.
(责任编辑:李金龙)
G03
A
1001-4225(2017)04-0066-06
2016-06-19
丁 杰(1983-),男,安徽蚌埠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