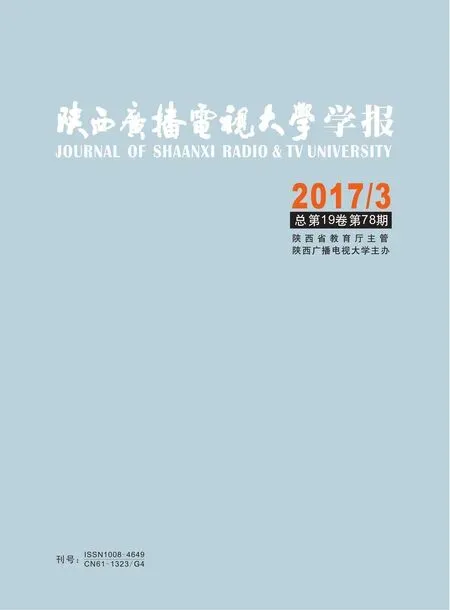庄子“无何有之乡”析义
,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现代服务与管理系,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文化】
庄子“无何有之乡”析义
代道军1,郝米娜2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现代服务与管理系,陕西 西安 710119)
《逍遥游》为《南华经》诸篇之首,是开宗明义之篇章,“无何有之乡”一词出于该章的末段,是《逍遥游》整篇文章的落脚点,也是整个庄子哲学的落脚点。笔者认为,从理解“无何有之乡”入手,更能切中庄子哲学的宗旨和关键。本文以《南华经》内篇为主要文本材料,试图用“无何有之乡”的思想意义来对《南华经》的内篇尤其是《逍遥游》作意义的分疏。
庄子;无何有之乡;逍遥;无己
庄子无疑是古代最有魅力思想家,他与他的后学们留下了一部才华横溢的《南华经》,透过《南华经》的文本,我们看到,在庄子眼中,尽管人在宇宙中渺小而孤弱,人在充满苦难的社会中生活得沉重而无奈,但人的生命中却有另外“一极”,这“一极”的世界中,没有萧杀的机心,没有纷争,没有冰冷虚伪的仁义道德,人的精神世界尚没有被欲望和分别心充满。而是像是一个大花园,满眼都是青绿的树木,芬芳的花草,蝴蝶栩栩然飞舞其间,溪流流过丘陵之间、大壑之中,而人则自由自在地在其间漫游,在旷野间钓鱼闲处,除了欣赏这个世界的大美之外,人可以对一切都保持淡然,包括名利、生死在内,任何事情都不足以惊扰内心的和平。而且,庄子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想象中的世界,而是本然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并非与现实世界绝然不同,或者与现实世界隔绝,而是只要我们改变自己的心灵世界,就像我们取下了一直戴着的有色眼镜,世界本身即是闲适自得、“逍遥”快乐的世界。
一、“无何有之乡”
笔者认为,庄子哲学所开显出来的这一极的世界,用《逍遥游》中的“无何有之乡”一词,是最为精准的描述。“无何有之乡”在整个庄子的哲学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描述了“逍遥”的实际内容,而整个《南华经》的文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启示“无何有之乡”。
何谓无何有之乡?《逍遥游》末段写到: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逍遥游》为《南华经》诸篇之首,是开宗明义之篇章,“无何有之乡”一词出于该章的末段,是《逍遥游》整篇文章的落脚点,也是整个庄子哲学的落脚点。主体是大树“樗”,樗即是臭椿树,是一种无用的散木,就庄子的隐喻而言,散木即是散人,无用之木即是无用之人。无用之人的无用生命,应该存在于(“树于”)“无何有之乡”,这样生命便得以安顿,而“逍遥”、“无为”则是存在于“无何有之乡”的状态。从这段话的语脉上来分析,“无何有之乡”是“体”,“逍遥”是“用”。根据庄子研究者们研究角度的不同,或以适性自足为逍遥(魏晋时郭象),或以至人之心“物物而不物于物”为“逍遥”(魏晋时支道林),或以“大”、“化”为逍遥(宋朝罗勉道、清代林云铭),“逍遥一词的意义多有分歧,但对“无何有之乡”指“恬淡寂漠,虚无无为”的境地,却能保持基本的一致性。按照笔者的看法,按照“本体”唯一、表象多样的思路,这一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无何有之乡”与“逍遥”
以“无何有之乡”为核心,《逍遥游》整篇也能得到前后一贯的理解。《逍遥游》一篇可分文四段文字来看,第一段鲲鹏之喻,喻至人之心大而化之以入“无何有之乡”;第二段文字理论庄子世界中的理想人格,“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写出“无何有之乡”的具体情状;第三段文字姑射山上的神人之喻,摹写游于“无何有之乡”的神人情状。第四段文字回到现实的人生,庄子与惠子作“有用”、“无用”之辩,庄子以无用而游于“无何有之乡”来安顿生命。
大鱼化而为大鸟,即是从“有的世界”走向“无的世界”(“无何有之乡”)的转化,“北溟”为极沉重阴寒之地,大鱼滞于水,正如人受碍于物而滞于压抑困苦的人间;大鱼从北溟中挣脱的关键在于“化”,化而为鸟,“化”掉的正是水的阻力,正如“至人”化掉对外物与自我的执著。“逍遥”一词的“逍”字,与“化”字有内在的关联,明朝庄子注家魏光绪说:“逍者,消也”,“逍”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清除”;“化”的主要意义也在于“清除”,“化”和“消”的作用,也即是从“有的世界”走向“无的世界”。“有的世界”是阴沉、萧杀的,处处隐藏着奸诈和杀机,就像大鱼只要停留在北冥,就为冰冷的水所包围一样;“清除”了世间的机巧、名利、纷争,游心于一个广阔、自由的“无何有之乡”,“心”才轻盈起来,正如鹏鸟一怒而飞,而能“绝云气,负青天”。南方是光明、温暖之地,心摆脱了重负,才生活在光明之中。
此下“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徵一国者”一段,落脚点在“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自我和功名正是要消解而走入“无何有之乡”的最大的障碍,庄子认为即使是御风而行的列子,在庄子看来也是“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看来庄子是要把所有世间依待的东西全部都抛弃干净,因为人类的有所待是真正的悲哀。自由就像是从倒悬之苦之中解放出来一样,而不得解脱,是“物有结之”,“物”把我们的心灵捆了起来。这些物是什么?自我给世界所规定的各种界限和分别,因而让我们想抓住的那些东西都是“物”:贫富、贵贱、美丑、荣辱、生死、梦觉。我们自己给本是一“混沌”的世界做出了这么多的区分,而后总是不遗余力地都想牢牢抓住我们自己区分出来的那些好的东西,为此殚精极虑地相互拼杀,从此我们便生活在北冥这样一个阴沉的世界中,焦虑、荒唐而无奈。所以自我和功名要把它们都用“无”来化掉,也可以说,“无己”、“无功”、“无名”,正是无何有之乡的真实状态。因而,庄子认为,所以要做的不是获得,而是抛弃,“忘”或者“无”,“ 无己”、“无功”、“无名”。连我们想牢牢抓住的那个中心点“我”都要“无”掉。我们可以认为,庄子的逍遥,就是一个无的心灵境界。
此下“尧让天下于许由”至“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一段,其主要意义是描摹了姑射山上的神人。虽然是描摹“神人”,而且这个神人“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但庄子并非讲“神话”,这个“神人”当然也是现实的人,而且只有“神人”才是真实的人,也即是“真人”。在《大宗师》中,庄子对真人的描述很多与姑射山上的神人相同:“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四海也许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过,游于四海之外之外的人,应该同时也是游于世间之物、事以外的人,世间的贫富、贵贱、美丑、荣辱、生死、梦觉,对他是不起作用的,神人也就是“ 无己”、“无功”、“无名”而游于“无何有之乡”的人。
第四段惠子与庄子的辩论,围绕“有用”、“无用”展开。用于世者,在于去贫求富、去贱求贵、去丑求美、去辱求荣,世界必然是一个历历分明的世界,而“无用”的人则是退回到“无何有之乡”的人,存在于一个无彼无此、无是无非、无美无丑、无好无恶、无成无毁的一个“无”的世界,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是真正的、最高的真实“道”的故乡,,最高的真实也是真正的自由,真实、自由也就是真正的安宁,“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息深深”。在庄子看来,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幸福。
三、从“无何有之乡”到“混沌之死”
《南华经》内篇其它六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来开显“无何有之乡”,也即是“虚”和“无”的世界。《齐物论》论“无己”、《养生主》讲虚以养心、《人间世》论虚(“无”)己以应世、《德充符》论虚静以得“和”、《大宗师》论忘己外物以求真、《应帝王》论虚静以治世。
《齐物论》以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开始,以庄周梦蝶结束,其中心观念是“无己”,即是南郭子綦的“吾丧我”。只有从“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是有人我、贫富、贵贱、美丑、荣辱、生死、梦觉。人以自己为中心,把世界进行了各种分割,然后把自己放进这样一个被封限的世界里去焦虑、格杀、纷争,世界因此变成了一个阴沉、不可忍受的世界。进入“无何有之乡”最关键的,就是要把这个把分割世界的自我中心化掉。南郭子綦就是这样一个把“自我”化掉的人。而所谓天籁即是说, 没有“我”所带的“自我中心”的墨镜,世界就是天籁,天籁就是世界按照自己的方式、如其本然的那样去发声。这样的世界,不但众生平等,万物皆是平等,物我、彼此、是非、善恶、梦觉也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决然的界限,此之“我”与彼之“蝴蝶”也是可以相互转化,没有绝对的区分。
《养生主》名为养生,其实为养心。养心的关键则在于“缘督以为经”,所谓“督”,按照王夫之的解释,即是“督脉”,“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缘督即是要循虚而行。庖丁解牛之所以能“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就是因为能以“无厚如有间”,所谓有间,即是骨间的空虚之处,以庄子的隐喻而论,“无厚如有间”就是以无我之心入于“无何有之乡”。
《人间世》以颜回欲至齐、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说明世道的艰险严酷,而应付艰难世事的关键,就是要“心斋”。所谓心斋,就是“虚”。“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所说的“气”,一定不是物质存在意义上的“气”,而是指摆脱自我意识和思虑之心,摒除心灵中的一切杂念,而进入一种虚静、空灵的心理状态,是一种精神经过净化之后的绝对宁静。“心斋”的核心意义,包括其后提出的“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归结到一点仍旧是“无己”。
《德充符》论虚静以得“和”,《德充符》中塑造了一批怪人和残疾人,比如兀者王駘、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奇丑者哀駘它等等,他们不但不招人讨厌,而且刚好相反,人们都乐于归顺于这些人,其原因在于,不管外在形体如何,他们的心灵世界一定是虚静而平和的,这些人不以“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世间的事和物为意。
《大宗师》中的“大宗师”即是道,修道者“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外天下、外物、外生后才能“朝彻见独”,“见独”即是“见道”。所谓“外天下、外物、外生”,庄子的注家王雱以“无”释“外”,他在《南华真经新传》注释该段说:“故有体有用则得道之全真而无我也,无我则无生……”,“外生”即无生,“外物”即无物,“外天下”即无天下,“外”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无化”的过程,
《应帝王》以虚静无为为治天下之要,其末段寓言混沌之死中的混沌,混沌即“无方无体”者(王雱《南华真经新传》),与“无何有之乡”意义相通。
四、“无何有之乡”与老子之“无”
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是对老子“道论”及无为论的继承和发挥。
老子对道的表达没有定义(把定为某物)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对“道”之体验近似的描述,“湛兮似或存”、“渊兮似万物之宗”;更为接近的表达方式,也许是一种否定的表达方式:“道常无名”,“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在提示对“道”的体验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而从老子的描述中,我们发现,“道”的体验类似于对“无”的体验。
老子哲学中的“得道者”,正是以体“无”为特征。“得道者”体“无”,无为、无知、无欲、无名……等等;真人最内在的特征就是体“无”,表现在外就是“朴”,对真人的描述,都是在描述真人之“朴”,圣人是“披褐怀玉”者,婴儿是人之“朴”,因而真人是“复归于婴儿”的。“朴”在“道”就是“道”之“无名”。一般人和“真人”的区别就在于,一般人打破了“无” 、“朴”,落入了区分和界限之中:美与恶,善与不善,有与无,前与后,难与易,成与败,白与黑,荣与辱,生与死,益与损……等等。其实问题不在于天下有万物芸芸之繁,不在于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有天然的分际,如果不是人依照自己的需要和看法去执定这些界限,界限也就不成其为界限,“混成”还是“混成”。
根据南京大学颜世安先生的解释,道家之“得道”,“是在涤除文化眼光后,在枯寂和静穆中进入新的体察世界状态”。也就是说,道家“得道”的关键在于人和人创造的这个文明保持距离,这是归真之途需要主动去全部弃绝的:(1)弃绝行为:无为。(2)弃绝欲望:“少私寡欲”;甚至“无身”;(3)弃绝智慧:“弃智”;“为道日损”。(4) 弃绝思虑:“涤除玄览”。(5)弃绝伦理:“绝仁弃义”;(6)弃绝技术和利益:“绝巧弃利”;(7) 弃绝语言:“知者不言”。弃绝就是要把这些人类社会中被公认的价值“无化”,“无化”的内容包括了功、名、知、欲等。庄子则把这些归结为“ 无己”、“无功”、“无名”,而最为根本的就是“ 无己”,而“无功”、“无名”则是以“无己”为最终指向的。我们可以看到,“无己”应当是是老子“无身”思想的深化,而“无何有之乡”的说法,则是对老子之“无”的一个形象化或者具体化的描述。
《庄子》注家和诠释者在分析《逍遥游》一文时,多把精力放在了对“逍遥义”的辨析上,以深究庄子哲学的要旨,固然有文本和学理的依据。不过我们看到,“逍遥”二字和“无何有之乡”一词同出于这最后一段
[1]庞朴.说無[A]. 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C].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
[2]聂中庆. 从楚简老子中亡、無和道的使用推断楚简老子的文本构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
[3]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2 .
[4](魏)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释德清 .老子道德经憨山注解读[M].逸尘(注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
[6]王博. 庄子哲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方勇.庄子纂要[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宇龙]
TheAnalysisofChuang-tzu'sRealmofVagueness
Dai DaoJun,Hao Mina
( Sha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Xi'an 710119)
Xiaoyaoyou is the first article of "chuang tzu" and the realm of vagueness comes from the end of this article.It is the foothold of this whole article, and it is also the essences of zhuang tzu philosophy. The author states that realm of vagueness is the keywords to understanding Chuang-tzu's philosophy.So we Analysis Zhuangzi 's philosophy on the trail of the realm of vagueness,based on the main text materials of Chuang-tzu.
Chuang-tzu;Free and unfettered;Realm of vagueness;Selflessness;
2017-04-03
1.代道军(1978— ),湖北省随州市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服务与管理教学部讲师,哲学硕士。2.郝米娜(1978— ),女,陕西省宝鸡市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现代服务与管理教学部副主任,副教授,文学硕士.
B223.5
A
1008-4649(2017)03-003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