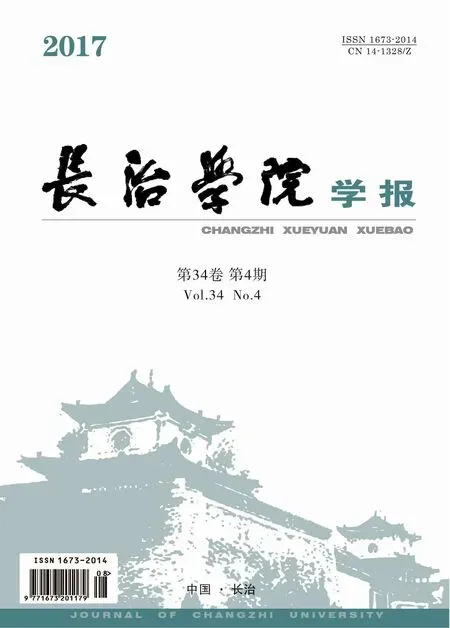士人出妻管窥
赵 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士人出妻管窥
赵 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士人,在此主要指两汉的读书人,即研读经书的人,在两汉中算作一个精英群体,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同样有出妻现象,出妻类型多样,有因传统的“七出”戒条出妻的士人,有因自身前途出妻的士人,也有因自己的观念出妻的士人等等。出妻类型不同,将自己妻子遣归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士人出妻事件不是一句不负责任就可以概括的,仔细分析,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即两汉的士风转变,统治阶层的影响,妇女当时容易再嫁都有密切关系。
士人;出妻;遣归
《礼记·郊特牲》说:“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古代社会婚姻的理想追求,实际上,纵观两汉社会,夫妻间无法白头到老的情况也存在,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出妻现象时有发生。皇家休妻事件不乏列举,他们没有出妻,是因天子以天下为家,弃妻无处可去。平民百姓出妻理由简单,将其视作寻常,因一个细节性的问题,不留情面将妻子遣归。上到皇帝下到平民,都存在出妻现象,可见整体社会上出妻问题之严重。
根据之前学者对两汉士人的研究,如郭帅的《两汉之际士人的政治抉择》,林佳颖的《冯衍考论》,对汉代夫妻关系的研究,如薛瑞泽的《论汉代的夫妻关系》,贾秋燕的《从举案齐眉看汉代的夫妻关系》,妇女婚姻破碎后的研究,如刘伟杰的《由汉代妇女离异与再婚的状况看汉代人的贞洁观》,等等,这些都给笔者写此文有一定的启发。
一、两汉士人出妻的类型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他们在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要么出仕,在政治层面有一定的作为,要么归隐,争取在学术层面有所成就。这样一个算是当时社会的精英群体,同样因各种原因而出妻,有因妻子触碰“七出”戒律遭弃,有因自己的前途、观念而出妻等。为何较平民,多几分知书达理,较贵族,少几分骄傲蛮横的士人,同样会出妻呢?以下将士人出妻类型粗分几类进行讨论。
(一)触犯“七出”戒条出妻
因不顺父母出妻。不顺父母,尤其是母亲,因此出妻的现象有许多。如东汉鲍永,习欧阳尚书,做官一心为民,对待非生身母亲也很孝敬。休妻是因“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1]1017,因为在母亲面前呵斥狗这一小的过错,便将妻子遣归。在唐代,白居易曾对“得甲妻子姑前叱狗,甲怒而出之,诉称非七出”的虚拟案件,判为“若失口而不容,人谁无过?虽敬君长之母,宜还王吉之妻”[2]1394-1395。与鲍永不同,乐天认为在婆母前叱狗,是类似于人们都会犯的小过错,改正即可,不应为此将妻子遣归。
因无子出妻。无子,没有为夫家生育孩子,以此原因被遣归娘家的妇女也有实例。桓荣,习欧阳尚书,任皇帝的老师;何汤是桓荣的学生,作太子的老师,师生二人同样在经学方面有所造诣。“荣年四十无子,汤乃去荣妻为更娶,生三子”[3]1250,何汤为桓荣去妻再娶,使桓荣有子,因此桓荣对这个学生格外看重。这样无子出妻的途径,应与他们夫妻感情淡薄相关吧。
因嫉妒出妻。此时社会上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了自己利益,妻妾间争宠吃醋频繁,使许多妇女因妒见弃。汉元后的父亲王禁,好美色,多娶妻妾,妻妾间争宠成为必然,“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后以妒去”[4]4014,王禁只从传统观点上认为女子不应有妒,忽略了家中的实际情况,使元后的母亲因此见弃。冯衍,二十岁时博通诗书,有气节,不仕王莽朝,东汉建立后,欲出仕却未能得志。“冯衍娶北地住氏女为妻,悍忌,不得蓄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5]1002,他的妻子不仅不让娶妾,就连身边的媵妾都不得蓄养,晚年出妻,与孩子们长大有关,也有一生壮志未酬的原因吧。
因盗窃出妻。王吉的妻子因邻家枣树上的一些枝桠,长到了自家的院子里,顺手摘了几个枣给王吉吃,王吉得知后便要休妻。王吉,“少学明经”,针对婚姻问题提出自己鲜明的看法,“阳尊阴卑”理论,即使贵为皇家公主,也应顺从丈夫。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因妻子摘了几个枣子便要休妻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自己的言行要符合儒家的条条框框,妻子的言行同样也应按儒家思想进行规范。私自摘邻家的枣,明显不符合儒家的思想言行,休妻便会成为一种必然。好在邻居大度,要砍掉枣树,才免去了王吉妻被休的厄运。
因多言出妻。七出中有一条为“多言”,表面上看为话多的意思,实际上指说错了话,或说的话具有危害性,妇女因此遭弃。李充家境贫穷,妻子想分家,让自己的小家过得好起来,李充得知后,假装同意,在大会宾客时,“充于座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斥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6]2684。妻子因在李充面前多言了分家的想法,这个想法在李充看来,是在挑拨自己与父母、兄弟间的亲情关系,这种罪过必须休妻。由此可知,妻子在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
由上可知,士人阶层因“七出”戒律更易出妻,虽然直到唐代,才把七出列入法律规定之中,但当时“七出”在两汉已是约定俗成的出妻戒条。如衡山王的女儿无采,出嫁后被遣归,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七《王女弃归》中说到“以王女之贵,为人妻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能以非礼制制臣下也”。可见七出之条是有一定效力的。两汉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兴儒用儒政策的逐渐推行,儒家思想向现实的各个层面逐渐渗透,这就使一些习儒学的人,行为逐渐遵从儒家的规范。其中用阴阳五行理论推衍出的三纲五常说,“夫为妻纲”,也就是“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7]1。士人们接纳的同时会以此来处理自身的夫妻关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规范,也会将妻子的思想行为规范到儒家的条条框框里。“七出”更是士人们不允许妻子触碰的底线,一旦有所触犯,便会不留情面地将其遣归。
(二)因自身前途而出妻
东汉平陵人窦玄,相貌出众,天子因而将公主许配给他,旧妻在与窦玄的诀别信中写到“妾日以远,彼日以亲,何所告诉,仰呼苍天”[8]533,短短几句看出旧妻的无奈与悲伤之情。有人说这桩婚姻是帝王强加给窦生的,有强迫的色彩,但也有因不妻公主,以死抵抗的事例。窦玄最终抛弃旧妻,与公主结为连理,成为皇亲国戚,深知从此多了一道极为强大的后盾,对于做官和利禄都有了很好的保障,以此看来,最终抛弃旧妻,实是为自己的前途而考虑。
黄允,典型的因自己前途抛弃旧妻的负心汉。黄允知道司徒袁隗赏识他的才能,得知想为自己的侄女寻得一位像他一样的郎君后,即刻休弃自己的妻子。黄允妻夏侯氏亦非等闲之辈,得知此事后,告诉婆母想最后见一面婆家的亲属,当亲属到来时,她把黄允出妻等隐匿秽恶事公布于众,是非曲直自有公论,夏侯氏在理直气壮地讲述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昂扬登车而去,黄允则名声于此废矣,高门女未娶到,前途也不再光明。
士人因自己的前途而弃妻,对于这一阶层尤其是抱有儒家出仕观念的士人来说很可能,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光是“修身,齐家”,更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主要途径是“学而优则仕”,他们以昏灯书卷为伴,埋头苦读十数载,希望在察举、科举中一举闻名天下知,有朝一日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若有捷径,从此可平步青云,多数是不会念旧情了。
(三)因自己的观念出妻
魏霸,“以简朴宽恕为政”[9]1002,对下级官员更多的是抚慰而不是惩罚,妻子死后,长兄为他再娶,他认为自己不用再次娶妻,所以对新娶的夫人说道“夫人视老夫復何中空,而远失计义,不敢相屈”[10]481。新妻因此感到惭愧,不得不请求离去。魏霸间接出妻,只因认为自己步入老年,子孙俱备,无需再度娶妻,这与自己的观念不符,便寻找出妻的理由。
因自己的观念出妻的士人,往往秉持一定的原则,即便世人认为不合适,他们依然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士人大多有一定的官位,为官上也会做出一番政绩,是为民的好官;亦或有自己特殊的才能,大多数人无法匹敌。若妻子做与自己观念相违的事,很有可能因此出妻。
司马光《家范》卷七《夫》曰:“今士大夫有出妻者,众则非之,以为无行,故士大夫难之。按礼有七出,顾所以出之,用何事耳!若妻实犯礼而出之,乃义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余贤士以义出妻者众矣,奚亏于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出,则家道何日而宁乎?”从司马光的这段话说明士人出妻并非是一念之间的行为,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而为之,两汉士人的出妻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缘故吧。
二、两汉士人出妻的原因
以上对两汉士人出妻类型的分类中看出,士人大致会因“七出”之条,自身的前途,自己的观念等而出妻,因这些原因出妻,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
(一)士风的转变
士风,即士人风貌,在此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士人群体长期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观念的外在表现,具体而言,是士人心态,士人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态度均可归入士风之列。
进入两汉,随着政治上的一统,士人效忠的力量明确而单一。西汉初期,受战国遗风的影响,多出侠义之士,如太史公所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11]3181,且侠义之士多为诸侯的宾客。随着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后,用政策来鼓励习儒学,士人更多地转向于研究儒家经学。至东汉,温文儒雅的开国皇帝刘秀,打击飞扬跋扈的风气,推许恭谨守道的士人,实行退功臣进文吏政策,这些都有效的使战国策士般的士风向恭谨柔顺的士风转变。随着士风转变的士人,更加重视自身的名节和德行,自然会对自己妻子的行为有所规范,妻子一旦触碰戒条,或认为碰到了自己的底线,很可能因此被遣归。
(二)统治阶层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记载“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12]1640,即说明统治阶层的一些习惯会对百姓有所影响。上行下效的作用,使士人也会对统治者的习惯有所模仿。两汉时代,最高统治者皇帝,废黜正妻皇后的事件时有出现,如汉武帝废黜陈皇后和卫皇后,光武帝废黜郭皇后,和帝废黜阴后,灵帝废黜宋后等,废小君的原因不尽相同,都未受太大的阻碍,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于出妻之事,并不把它看作一个严重的问题,从而出妻事件对于士人,也视作平常之事。
(三)妇女容易再嫁
女子一旦嫁人,应从一而终。然两汉时期,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妇女改嫁再嫁的例子很多,如汉景帝的王皇后,先嫁金王孙为妇,又进宫服侍景帝,终成为景帝的嫡妻;再如华仲妻曾为汝南邓元义的前妻,因邓元义母亲的刁蛮无理,被善意地遣归,后嫁华仲。华仲做了将作大匠后,其妻乘朝车出行。将作大匠,二千石的官员,身在高位娶曾嫁过人的妇女为妻,从让她乘朝车出行这一点看出,并未因自己的妻子曾嫁过人认为有何羞愧。可见两汉时妇女改嫁再嫁不是什么严肃的问题,且在婚礼仪式上和第一次结婚的女子一样,如《孔雀东南飞》中对兰芝再嫁场面的盛况描写,且再嫁为县令的儿子,身份地位都比为府吏的前夫焦仲卿高,可见妇女容易再嫁,这就使得出妻的阻力较少,士人因一些原因出妻不会受到什么阻碍。
综上所述,对士人出妻类型的粗分几类,可看出受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影响,士风从侠义之风向恭谨柔顺之风的转变,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时值妇女改嫁再嫁不受阻碍,都或多或少的形成了两汉士人为数不少的出妻事件。
[1][3][5][6][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白居易.白居易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刘珍等撰.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责任编辑 王建华)
K234
A
1673-2014(2017)04-0028-03
2017—04—12
赵妍(1993— ),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