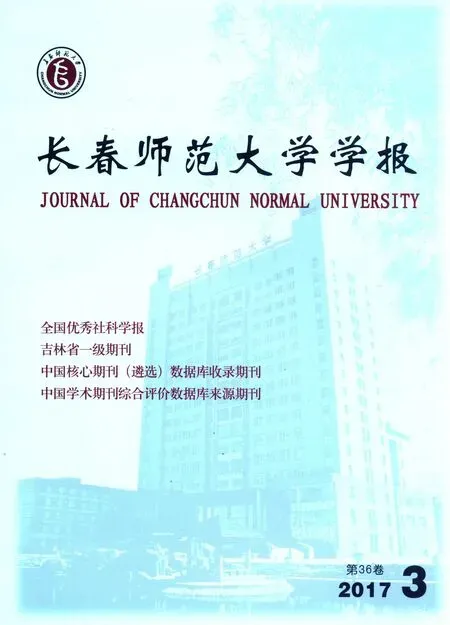浅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郭嘉豪
浅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郭嘉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犯罪行为统一规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该罪作为一种新兴罪名,其犯罪构成要件中的诸多要素在学界尚存争议。厘清该罪中“信息”的具体范围、行为模式的类型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的影响因素,对该罪的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行为模式;情节严重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与现实生活全方位、多层次深度融合,催生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互联网+”。当人们享受互联带来的便捷、高效的红利时,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涵盖范围之广、涉及数量之多、造成危害之大是传统犯罪所不具备的新形态。因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继而引起的其他犯罪,如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绑架罪的发生,也使刑事立法对该类犯罪行为的规制势在必行。2015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新表述却并未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信息类型和范围等问题作出明确阐释,由此引发了学界争议。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进行准确界定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司法适用正确的前提和基础。相对于传统犯罪来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信息网络时代产生的一个新兴罪名,其保护的具体法益是公民个人的信息安全。从《刑法修正案(七)》的两个罪名到《刑法修正案(九)》将二者合二为一,公民个人信息作为核心概念,信息的类型和范围是界定入罪、出罪的基础。究竟什么范围应该归为公民个人信息?什么范围不在此列?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对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表述较为模糊,并未清晰地划定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所以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争议较为突出。有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要从广义角度加以理解,即公民个人信息涵盖所有与信息主体有关联的信息;还有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应当限制在狭义范围,将公民个人信息等同于个人隐私;另有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信息主体的“定位器”,是解锁信息主体的钥匙,理解其内涵要从信息的独特性出发。笔者认为,对公民个人信息内涵的界定应当从刑法的立法目的出发,立足于刑法所力图保护的法益,尽可能全面地对其作出定义。
第一,公民个人信息显著具有标签性。2013年发布的《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中规定,公民个人信息应为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资料。此界定表明,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个体的标签,主要功能是区分不同信息主体。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一一对应的特性,其不仅关系到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人格尊严,也衍生出在人际交往、社会管理、商业运营等多方面的实际价值。司法实践中,公民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相对较为公开的具有身份识别性的个人信息,一般不被视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对象。基于这一认识,大众放松了对上述种类信息的保护,导致大量的商业广告、
推销信息甚至诈骗信息流通于手机短信之间,对公民的信息自由和信息安全造成极大损害。所以要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对公民个人信息加以保护,就必须明晰其标签性特征,在不同种类的公民个人信息之间找出能明确区分信息主体的部分,以此为基础适用法律。
第二,公民个人信息表现为潜在经济性。实践中,不法分子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贩卖,以谋求经济利益。交易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已经从单纯的数据信息转化为可流通的商品资料,所以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公民个人信息往往兼具可流通的商品属性。公民个人信息所表现的价值不再局限于信息本身,而是以象征信息主体价值的形式存在。实践中,商家或者其他主体有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以便发送宣传广告、推送产品等业务需求,这为不法分子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市场。当公民个人信息成为一种营销产品的时候,公民个人信息所包含的潜在经济性特征就必须作为界定其范围的标准。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公民个人信息本身不是其所追求的财产利益,信息背后所代表的信息主体的财产利益才是犯罪的最终目的。犯罪分子买卖流通的公民个人信息,如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等,虽然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相对公开,但仍会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例如风靡于微信朋友圈的投票活动,不法分子利用微信用户的虚荣心理引诱用户参与点击投票链接,链接中有木马病毒,该病毒可以盗取用户手机中的个人交友信息数据,并带有自动向联系人群发的功能,大范围传播木马病毒以获取更多的公民个人信息。交友信息虽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但不法分子往往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骗取他人钱财,甚至直接盗取财物。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已经不仅仅是识别信息主体的数据,其背后隐藏的经济性特征更应该是刑法保护的对象。所以一些外在特征仅仅表现为单纯数据意义的信息,在某种情况下也能列入刑法保护范围。
第三,公民个人信息应当区别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相对于刑法保护的个人信息来说,范围更窄、公开程度更低、受保护程度更高。《刑法》中已有保护个人隐私的条文,如果将公民个人信息和公民个人隐私混为一谈,可能导致法条竞合。另外,值得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不仅包含个人隐私。例如,2015年5月至7月,中国联通公司员工肖某非法获取并出售公司客户的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并获利8~10万元的案件,北京丰台法院判决其罪名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个人信息涵盖较个人隐私更广的范围,个人隐私之外的诸多个人信息遭到侵犯,同样会对公民的人格尊严、财产安全造成损害。如果将公民个人信息草率地理解为个人隐私,会导致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过窄,某些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行为将得不到刑法处罚,不利于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如何确立公民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界限,要综合考虑本罪的立法原意和具体法律适用的实践。个人隐私跟信息主体的人身相关性直接体现在不愿为人所知的私密特征,我国《刑法》中对侵犯个人隐私的犯罪已有专门规定,例如侵犯通信自由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等。基于这个立法现实,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隐私不应成为该罪的保护对象。司法实践中,出售、提供公民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的行为,符合情节严重的情形,也应属于本罪规制范围。
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模式
《刑法修正案(九)》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模式采用例举的方法,仅包括非法出售和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这两种行为。实践中,除上述两种方法之外,还存在诸多同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对这些行为应该如何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一般采用列明的方式,对犯罪行为的方式采用列举进而排斥其他行为的入罪,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一些在社会危险性上与出售和提供相差不大的行为得不到刑法的规制。为了应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现的日益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从立法源头上减少法律滞后性对司法实践的不利影响,应将一些新情况、新方法列入刑法规制范围,更有包容性地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的模式特征,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中的行为模式可以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引入“其他方法”以作兜底。
1.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非法使用是指行为人在无法律依据或者未经信息主体同意的前提下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这里的“使用”仅指自己使用,不包括给予他人使用。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虽然未被刑法禁止,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因此而消灭。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绝大多数情节轻微、不够成犯罪,例如生活中充斥的垃圾短信,很多是因为商家通过注册会员等方式获取客户的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而后滥用这种信息进行各种无用推送,扰乱公民的生活安宁。恶虽小,积少成多,同样侵害了信息主体的信息安全和信息自由。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所使用的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相对特殊性的情况下,造成的现实社会危害可能会大大超越刑法规定的非法出售、提供行为。例如,曾广泛引起社会关注的河南周口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起因就是行为人非法使用他人个人信息。非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在刑法中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所以相关责任人免于刑事处罚,而受害人仅以民事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对于遭受巨大损失的受害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非法使用的行为只有达到情节严重时,才可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但完全将其排除在外,不利于遏制犯罪,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2.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将公民个人信息向特定的、范围较小的人群公布,例如将公民姓名、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予以公布;也可以向不特定的、较大范围的人群公布,例如通过电视、网络、报纸将公民个人信息予以公布。这种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使信息暴露在不特定人的视野内,可能引起犯罪分子注意,继而将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置于危险之下。很多拐卖、诈骗等犯罪行为,均是因为在网络社交圈发布过多的个人信息,导致犯罪分子掌握信息主体的生活轨迹,继而为犯罪的实施提供了空间。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有可能导致其他更严重的犯罪结果的发生,这种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可忽略的。笔者认为,对于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可以通过设置兜底罪名,将情节严重的情形置于其下,较为全面地涵盖犯罪情形,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三、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公民个人信息在实践中受到侵害的方式存在诸多表现,多数犯罪往往会涉及数量巨大的公民信息。根据某网络安全中心的统计数据,仅2011-2014年,经过公开并被证实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数量就达到了11.27亿条。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信息数量大、涉及范围广、侵犯手段多的背景下,对情节严重的认定仅以数量为标准,会产生很多疏漏,导致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未受到刑法规制。情节严重作为对行为社会危险性大小的综合评价,应当从立法目的、刑法保护的法益对象以及犯罪行为所引发的行为结果的具体危害程度等方面进行评判。
第一,涉案信息的量化数据可以作为标准之一,用以界定是否符合情节严重。数量作为可量化的数据,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操作中,司法工作人员往往通过案件涉及的信息数量判断是否构成本罪,涉案信息的量化数据作为直观的案件情况可以反应出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设置可量化的犯罪标准,可以帮助司法工作人员在查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中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也可以明确区分罪与非罪,兼顾法律适用的正义和效率。所以,将涉案信息的数据进行量化并将其作为判断情节严重的标准是没有疑问的。
第二,涉案金额可以作为标准之一,用以界定是否符合情节严重。一般而言,追求获利是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直接目的、通过对犯罪分子获得利益的多寡进行分析,可以推出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及主观恶性大小。涉案金额作为标准。可以弥补单独以数量为标准所造成的法律间隙。针对涉案信息量不大但是非法牟利数额较大的案件,涉案金额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减少刑法规制的空缺,更全面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案件金额又可以细分为非法获利数额和非法销售数额,只要犯罪分子达到任一标准,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第三,案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可以作为标准之一,用以界定是否符合情节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设立,旨在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自由,也力图避免因公民个人信息泄露而造成其他更严重后果。所以判断犯罪行为的情节严重,应当以信息主体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程度为依据,具体分析犯罪行为对信息主体造成的经济损失及身心影响。例如,2016年引起社会关注的“裸贷门”事件,损害的不仅是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和自由,还扩展到了犯罪行为对信息主体的正常生活和心理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负面社会效应。所以,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应视为情节严重的判断因素。此外,一些以贩卖个人信息牟利的不法行为,其贩卖的个人信息导致信息主体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被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获取,继而引发更严重的刑事犯罪的发生。基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导致发生其他更严重法律后果的,通过判断其因果关系,判断是否应纳入情节严重的范围。
四、结语
我国刑事立法对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规定在不断完善,从《刑法修正案(七)》的初次规定,到《刑法修正案(九)》的进一步发展,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在不断加深。诚然,法律相对社会实践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但法律作为相对稳定的规范,是在不断地和实践碰撞、吸收、融合的过程中填充完善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现代化的进步,为实现保护公民个人有序生活、不受侵扰的价值诉求,进一步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刑事立法任重道远。
[1]余意然.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2013(20).
[2]薛皓月.论隐私权的刑法保护[D].苏州:苏州大学,2011.
[3]丁学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体系重构[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0).
[4]王丽.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D].湘潭:湘潭大学,2011.
[5]胡江.互联网时代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困境与出路[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5).
[6]孙力.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事立法解读[J].江苏商论,2009(11).
Analysis of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GUO Jia-hao
(Th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The Ni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provided all the related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Crime of Infring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While as a crime emerging newly, many of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s are still on debate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refore,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range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rime, the type of criminal’s behavior pattern and the factors which can affect criminal circumstan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t for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is crime.
the crime of infring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behavior pattern; serious circumstances
2016-09-19
郭嘉豪(1992-),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刑法学研究。
D924
A
2095-7602(2017)03-0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