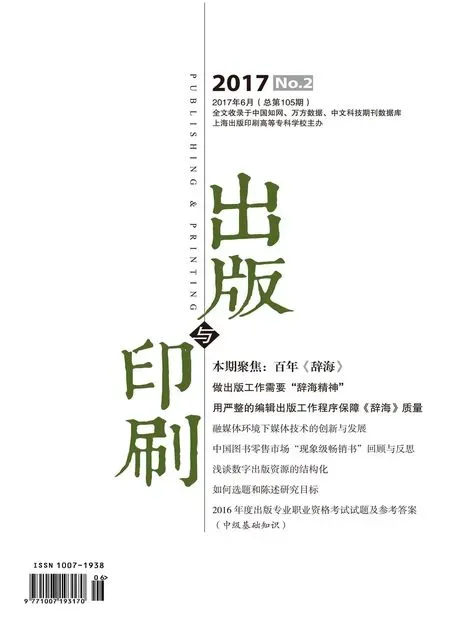书稿差错小议
夏剑钦
书稿差错小议
夏剑钦
有人说:“无错不成书。” 这话似乎是对我们出版工作者的一个安慰——要消灭图书差错颇不容易,因而一本书出点错误也算不了什么问题。说来也是,图书可能出错的情况也太多了:如作者笔误或作者粗制滥造,而我们的编辑人员又未能发现或未进行认真修改;如原稿字迹潦草,排版人员误排;再如排校失误或编辑、校对人员改错了;等等。看来,要消灭出版物上的差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从出版这一方面来说,窃以为提高编辑和校对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其责任心,恐怕是个中关键。这是笔者近来终审、终校部分书稿时遇到一些差错而深有感触的一点。
分析我所遇到的几部书稿中的差错,大致有下面几种类型:
一是常识性的错误。例如有本书稿中提到现代古文字学家、史学家唐兰先生,原稿和清样中都郑重其事地在其生卒年前注上一个“女”字,而且行文中有“她认为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句子,句中“她”字,也说明作者认定唐兰先生是女性。这当然是个常识性的错误。可能是作者孤陋寡闻,凭姓名中的“兰”字而望文生义,信笔雌雄。
又如古代人取名字,一般是“名”与“字”之间有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关系。懂得这一古代文化知识,名与字之间出了毛病就可诊断出来。例如有部书稿中写到“高树勋,字建候”,“建候”就可断定应是“建侯”,因为建树功勋与封侯的关系密切,而“建候”就无解了。又如在另一部书稿中,“孙宣,字仲可”,“宣”字便是“宜”字之误,因为“宜”与“可”意义相近,而不太可能是“宣”,后来在书中别处也证实了确实是“孙宜”。
二是规格、体例方面的差错。一本书的规格体例不一致,这是编辑工作的忌讳之一。有部书稿的作者和编辑对此却未引起重视。例如书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表述,有加引号的(应该加引号),有不加引号的,有省作“文化革命”(是不对的)而加引号或不加引号的,也有省作“文革”的,真可谓五花八门。又如“九一八”事变,也有加引号、不加引号和加间隔号、不加间隔号,以及写成“9·18”等多种表述方式。这些都是对书稿要求不严谨而出现的表述差错。
三是涉及编校者的文学素养和文字功底方面的差错。有部书稿的原稿有一些引文和用典用字方面的错误,稍有疏忽或本来文学素养、文字功底都不够,便很难消除。例如书中引用的杜甫《过洞庭湖》一诗,其末尾两句是:“湖光与天远,真欲泛仙槎。”对唐诗较为熟悉或对古汉语虚词用字比较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诗中的“真”字不妥贴,可能是因形近的“直”字而误。因为“真”字在古代主要用作形容词,与“伪”相对;用作副词“的确”“实在”,那是近现代汉语的事。从这里的诗意看,显然讲的不是“欲泛仙槎”的真伪问题,而是带有强调的语气——竟想泛仙槎,真想泛仙槎,简直想泛仙槎。至于“直”,那是唐宋诗人喜用的一个语气副词,如白居易《伤宅》诗“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及陆游《东山》诗“有酒如涪绿可爱,一醉直欲空千罍”即是。当然,有了这个怀疑,一查杜诗便明白了。
此书稿又有一处有“此在其额,殛坠其恫”的句子,很令人费解。问题就在于“此在其额”实际上应该是“泚在其颡”,典出《孟子·滕文公上》。“其颡有泚,睨而不视”,“泚”是出汗、冒汗的样子,“泚在其颡”可理解为“他额头上直冒汗”。对这么一个令人费解的用典现象,原稿却既未正字,又未加注说明,编校者是否读通了,亦不得而知。
至于在排字方面,形近而错的现象就更为普遍,如有部书稿的清样,“刺史”错成“剌史”就不下20处,再如“萧公”错成“肖公”、“吴瑞”错成“吴端”、“仲宣”错成“仲宜”、“戍守”错成“戌守”、《庄子·庚桑楚》错成《庄子·庾桑楚》、“不以一毫徇入”错成“不以一毫徇人”(原稿亦“人入”不明),等等。此类错处,就举不胜举了。
此外,有的书稿中“昜”和“易”不分,一般是误将“易”写成“昜”,殊不知它们的读音绝然不同,连同它们作形声字的声旁时,那形声字的读音也完全不同。“昜”作声旁的字一般读平声“-ang”韵,如“扬(揚)、杨(楊)、汤(湯)、场(場)、肠(腸)”,而“易”作声旁的字一般是古入声字,今读“-i”韵,如“锡、剔、惕、赐”即是。
上面列举的几种差错情况,大多是原稿和校样都共同存在的,这固然一方面说明作者的不严谨或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编辑人员和校对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于提高,其责任心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至于如何选择作者,避免粗制滥造,如何提高编校人员的业务素质,如何加强他们的工作责任心,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出版社改革的一个方面,值得引起重视。
(作者单位: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