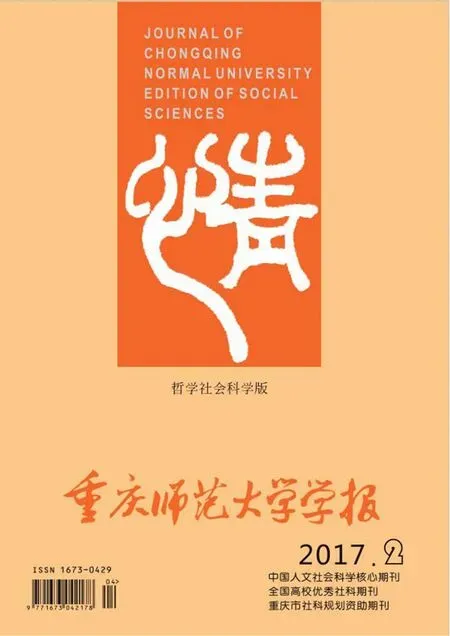温特森《激情》的跨文类实践与性别越界
骆 文 琳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温特森《激情》的跨文类实践与性别越界
骆 文 琳
(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1331)
当代英国著名作家温特森在《激情》中以拿破仑政权的兴衰为历史背景,把象征主义、寓言讽喻和丰富的视觉意象结合在一起,编织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而富于幻想的故事。小说通过线性历史叙述与幻想故事两种叙事模式的交替、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后现代式重写、酷儿身体的乌托邦塑造,戏谑了历史叙事,书写了多元流动的女性欲望,揭示了温特森跨越男/女、异性恋/同性恋的疆界藩篱的酷儿意识。
温特森;《激情》;跨文类;性别越界;酷儿意识
詹妮特·温特森是当代英国著名后现代派作家,同时还是一位极富哲学遐思的作家,她对爱、时间、历史、宇宙和人类生活的深刻探讨奠定了她小说主题沉稳不变的基调。1987年出版的《激情》获得约翰·卢埃林·里斯文学奖。温特森选取了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物拿破仑的御厨和威尼斯船夫之女为故事主角, 将他们的命运置身于拿破仑战争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采用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为故事增添亮色,现实与魔幻的交织使作品看似轻快实则凝重,在看似简单的文本结构中隐藏了一个复杂的螺旋形的叙事体系。
国外温特森研究十分兴盛,国内研究近年也逐渐趋热。国内学者对温特森的第一部获奖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关注较多,对《激情》研究较少,无人从文类实践与酷儿意识的角度解读过该作品。本文将解读温特森如何利用两种文类叙事,对男女主人公性别气质进行艺术化处理,书写多元流动的欲望,表达出作者激进的酷儿身份政治意识。
一、历史叙事与男性身体的阉割
《激情》以1769年到1824年横跨半个世纪的法国拿破仑政权的兴衰为故事背景,将个人命运置于帝国兴衰的轨道中。亨利以第一人称讲述和回忆了他狂热地追随波拿巴的军队生涯。温特森通过亨利的历史叙事,不仅表达了个人对自我身份追寻的过程,而且通过亨利的视角呈现出那些被忽略了的女性声音。
亨利的历史叙述中包括了他为一份战争刊物撰写的回忆录和战后在萨·塞沃罗岛(San Servolo)的疯人院里写下的日记。其叙事呈现出两种不同声音:一种是对法兰西帝国美好前程充满了乐观情绪的声音;另一种则是经历战争后忏悔的声音。日记本是亨利消除战争创伤的有效手段,“自从在海上遭遇风暴后,我就有了些日记的习惯。这样我就不会忘记,这样在晚年的时候,当我倾着身子,坐在炉火边,回顾我的一生,我就有了明确的记录,以反抗记忆对我的欺骗。”[1]41亨利对童年的回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与拿破仑和上帝保持一致的父权维护者形象,而日记则是他的自我反省,对曾经理所当然接受的既定模式和观念的反思。
亨利的讲述从拿破仑军营中的鸡开始,作者用讽喻的笔调,为读者呈现了一幅视觉意象丰富的画面:
只有拿破仑对鸡肉有着如此的激情,他让厨师们马不停蹄地工作。那是怎样的厨房啊!到处都是被拔光了毛的鸡。有些被冻得直挺挺地挂在钩子上,有些被串在烤肉叉上缓慢地转动着;但绝大部分的都堆在那儿烂掉了。原因可想而知:皇帝陛下太忙了。那些鸡以各种姿势赤身裸体……我最初只是拧拧鸡脖子,但不久我就成为端着盘子到他帐篷去的一员。他喜欢我是因为我矮小。…… 它们被欲望所控制。每个笼子里有两三只鸡,嘴和爪子被砍掉了,透过板条看到的是它们那呆滞的毫无区别的眼睛。我不是胆小鬼,我在农场也看见过无数的这样的残肢,但我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毫无准备。没有一点叫声。它们可能早就死了,应该是死了,只有眼睛还活着[1]3-4。
拿破仑军营中士兵如同那些被囚禁待宰的鸡,同样处于被操纵、被囚禁和无语的境地。士兵们出于对拿破仑的崇拜参加了战争,但他们的激情却被当权者利用而成了牺牲品。亨利叙述了自己亲眼目睹两千士兵的生命瞬间消失的情景:
1804年7月20号,夜晚已经过去,黎明尚未到来。1804年7月20日。今天又两千人淹死了。两千士兵在今天被淹死。在这场飓风里,即使是像帕特里克这么强壮的人,也得把自己绑在装满了苹果的木桶上。我们发现,我们的船只只不过是像孩子的玩具一样脆弱。波拿巴站在码头边,告诉他的军官们没有一场风暴能够打败我们。……第二天早上,又有两千名新士兵进驻布洛涅。”[1]34-37
仅仅因为拿破仑急于试航他的新船,在同一天里两千士兵死于风暴。正是数次亲眼目睹了战友的生命瞬间消失的情景,亨利才逐渐意识到当权者的冷漠,爱国主义精神不过是对士兵命运的反讽式嘲笑,战争带给士兵的不是光荣的牺牲而是像一只快被淹死的老鼠,士兵不过是当权者手上的数字而已。血腥的事实造成亨利思想混乱,使他在幻觉中认为自己“被这些死人覆盖住了。”残酷的战争、无意义的牺牲和对自已命运的无助使亨利逐渐意识到拿破仑的权威形象不过是自己一种浪漫的建构,他感叹到:“我创造拿破仑就像他自己创造出的一样。”[1]158亨利在反思过程中逐渐从对权威的认同走上了对它的拒绝。他在回忆录中写下自己对激情的认识:“如果爱就是激情的话,恨将是一种迷恋。恨不仅是自己曾经爱过的,也会是你自己;你怎么会爱上它。”[1]84
历史记载中通常把拿破仑战争描写成十八世纪最后十年到十九世纪初的一场法国领土扩张的军事胜利。而亨利讲述的却是拿破仑对世界不可节制的权力欲望使无数热血爱国青年遭受了身体和精神双重摧残。对此作者写道:“现在人们谈论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自己很清醒。似乎他犯的最致命的错误也只是因其厄运和自大造成的。这真是一团糟。像蹂躏、强奸、屠杀、挨饿这样的字被掩盖了,人们的痛苦被疏远。”[1]5作者从亨利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让读者听到了那些曾经被埋没在边缘的声音。
作为一个始终关注女性命运的作家,戏仿和重构历史的目的还是在于引入当今社会关注的议题,对于温特森来说,其关注的中心一直离不开拒斥传统道德的女性命运。帕墨(Paulia Palmer)认为:“亨利这个人物塑造具有激进性。是亨利引入了女同性恋议题。”[2]69在温特森笔下,亨利的男性身体被艺术化地阉割,其角色定位被性别化地颠覆和置换。在“皇帝”这一章里,从布洛涅军营到整个法国,都被所谓的“行动”、“力量”、“控制”这些男性气概所表征,男人从小就认为成为一名士兵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在战争中强调的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男性气概。在权威之下,个人的身体沦落为被权威放逐的身体,亨利成了一个“女性化”的、性别/性属的不对应的男人。亨利身材矮小削瘦、柔弱、敏感、迷恋拿破仑的男性魅力、畏惧战争。“一个被牧师和虔诚的母亲带大的年轻人。一个不会用步枪射杀兔子的年轻人。”[1]28八年战争中,他没有机会拿起枪冲锋陷阵,却被安排在拿破仑的厨房负责拧断鸡脖子。在军营里,他每周都脱掉袜子修剪指甲。温特森通过男主人公性别气质的颠倒,对性别身份进行了后现代式的塑造,亨利的女性气质使他更接近女性、了解女性、包容女性,为亨利对女性历史叙述提供了可能途径。
二、性别化的叙事声音与隐形女性历史
占据历史主页的往往是在公共领域的男性活动和那些不同寻常的英雄豪杰,女性是第一个被排斥在外的。“温特森认为:女性的历史不是容易被寻找出的直线。跟着我们去寻觅那些隐藏的踪迹。”[3]61酷读文本,亨利线性的历史叙述呈现出反线性的画面,一段段被隐藏在主流历史背后的“她”的历史开始显现出来。
亨利的故事中穿插了母亲反抗传统婚姻压迫的故事。母亲出生在一个并不富有但受人尊敬的保皇派家庭,从小就安静地学习音乐,阅读合适的书籍,十二岁时母亲决定做个修女,但长辈们不喜欢非传统行为。十五岁的一天,在一个牲口集会上,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一个穿着十分得体、肩旁上还坐着一个小孩的结实男人。母亲逃走了,随身带着《圣经》,流落到一个陌生的村庄。由于父亲贿赂了整个地区的修道院,母亲既不能回家也不能进修道院,为了生存,母亲不得不和收留她的克洛德(亨利的父亲)结婚。
亨利同情那些遭受性虐待的军妓,揭开了被隐藏在主流历史背后的军妓的历史。军妓中有离家出走的、有误入歧途的、有大家闺秀、有受不了主人性侵的仆人、还有生意失败走投无路的老妇。她们在军营中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还被要求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为士兵提供性服务。亨利看到了女人间的相互关照,“我们经常看到镇子里那些体格健硕的妓女出于同情,带着毯子和长面包条到营里探望她们。”[1]56当大厨在妓院虐待军妓时,亨利目睹了她们的情谊,“我的女人冲过去把一个酒罐结结实实扎在他的头上。她搂了搂她的同伴,飞快地在她的前额上亲了一下。”[1]21
亨利的故事还包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丈夫忽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女性。村子里有个男人喜欢当发明家,他把大量时间耗费到不切实际的工作中。他的妻子在照看田地、整理家务、照料着六个孩子,除了一句“晚饭好了”之外,她从不说别的。直到她一天中午突然死了,这个男人才意识到“她为他的生活带来了可能。从这点上来说,她就是他的上帝”。[1]40
可以看到,亨利的叙述中心始终离不开对那些被男权制压迫、处于失声状态的女性群体的关注,“我们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过她们。我们不时地想念她们的身体,然后谈论家乡,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她们看成是:最固定的、最爱的、最了解的人。”[1]39作者运用性别化的叙述声音将小说从描写军营和战场的男性中心逐渐过渡到以女性为中心,同时引入了强迫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等性别政治主题。亨利的历史叙事和女性化的叙述声音为维兰妮这一酷儿身份人物的传奇故事作了充分的铺垫。”[2]103
三、魔幻故事与酷儿身体的展演
“西方女性主义认为文艺作品的类别渗透了性别的文化权力,利用作品的类别跨界颠覆来达到对传统性别权力的质疑。因此,酷儿书写常常利用超现实场景,如神话、魔幻写实等,结合后现代叙事技巧等方式演绎酷儿对情欲、性别的阐释。”[4]81与亨利的历史叙事相异,维兰妮的叙事空间里充满各种神话和幻想元素,温特森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挑战男权和异性恋、颠覆传统男女角色定位和性别身体的女性形象。
作者将故事背景置于有着梦幻和神话色彩的水上城市——威尼斯:“这是一座被水包围的城市,水路取代了大街小巷,淤泥堵塞好的后街只有老鼠才能通过。传说中这里的居民能在水上行走。他们都长着脚蹼。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脚蹼只在船夫之间代代相传。”[1]70当亨利来到威尼斯,完全不能理解城市的布局和奇特。它像一座从海平面升起的虚构城市,并且看上去东一块、西一块,没有章法地向外扩建。像一块发酵的面团随自己的意愿膨胀。但维兰妮却能够随意穿越威尼斯的外部空间和内部空间。城市的外部空间指“取代了大街小巷的水路”,它展示历史事件发生的轨迹,而内部空间指的是赌场、鲜有人知晓的城中城。城市的内部空间隐藏着那些被边缘化人们的自我欲望的追求。
酷儿理论认为:个人的性取向是一个“由各种可能存在的性取向组成的变动的、零散的、动态的集合体。”[5]375维兰妮有着多重身体:她时而是基督的化身,时而又是妓女、赌徒、女同性恋、异性恋或母亲。维兰妮讲述了充满了奇异的身世和多重情欲,例如船夫匪夷所思的风俗;亲生父亲的神秘失踪;母亲生产的过程;兀自跳动的心脏,以及和一名叫“黑桃皇后”威尼斯女人的激情故事。与传奇故事的女性身体形象相异,维兰妮有着令人惊奇的怪异身体。她身材高大,长着只有渔夫才有的蹼足,且能在水中行走。当她出生时,她的母亲想让接生婆拿刀把那个不讨人喜欢的部分切掉,产婆试图在两只脚趾间切开口子,但没有成功,得到的只是折弯了的刀尖, “没有一把刀子能割开那些蹼翼。”[1]73作者用带蹼的脚隐喻她的男性性征。童话故事中女性往往是被动的、柔弱的和自我牺牲的,而维兰妮却具有主动、大胆和随心所欲等一系列男性气质。她在赌场上班,常常把自己打扮成男孩。易装不仅为了得到乐趣,更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我打扮得像个男孩,因为那是客人们喜欢的样子。猜测隐藏在紧身马裤和夸张的面部妆容后的性别也是游戏的一部分。我用朱砂抹了嘴唇,又在脸上擦了层白粉。我穿着赌场的黄色马裤,一件海盗式样的衬衣掩藏了我的胸部。小胡子是我自己觉得好玩加上的。或许可以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1]77。
维兰妮的酷儿身体吸引了赌场上的赌徒。为了钱,维兰妮常常将性别置于表演中,“我有时在前面遮一块股囊来蒙骗他。”[1]79并且决定嫁给一个讨厌赌徒,“他向我保证让我过上奢华的生活。拥有各种女人的心爱之物,可以在自己家里继续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他喜欢那样的我……我每个月都在不同的地方喝咖啡。”[1]89-97两年后维兰妮想结束这段婚姻,她用身体作为赌注,最终被卖到法国军营的妓院,沦为军官们的玩物。
维兰妮的怪异身体还吸引了赌场中另一位常客,一个手里拿着黑桃皇后扑克牌的已婚女人。维兰妮和她相识了五个月,享受着九天九夜的激情。然而在第九天,黑桃皇后却要腾出时间为她常年在外热衷于宝藏收集的丈夫回家做准备。维兰妮的付出终究只能换来隐而不宣的地下生活,她们约会的场所只能局限在她的房子或咖啡屋。“温特森小说的女主人公似乎都是在竭力逃脱一种命中注定或禁锢的激情,她们寻找的是一种崭新的激情。”[2]148维兰妮与黑桃皇后的同性关系暗示了这种禁锢的激情。当亨利潜入黑桃皇后那高达六层的屋子寻找维兰妮的那颗心时,他看到一副完成了四分之三的刺绣,上面绣的是维兰妮。黑桃皇后像一个巫师,维兰妮只是她手上的一件艺术品。当再次看到对面屋子里那头发已开始泛白的黑桃皇后时,维兰妮意识到这是一种禁锢的感情:“如果我向这份激情屈服,我的真实生活,最为坚实、最为人所知的生活就会消失,而我就会再次靠阴影为食。”[1]202
在和亨利异性恋故事中,亨利爱上了维兰妮,将她置于女性是欲望客体的传统位置,但维兰妮却颠覆了这个位置。维兰妮的强壮和多重欲望与亨利的单薄清瘦和对性的无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子很单薄,压在我身上感觉如同一张床单。他一点都不知道男人该做的事,直到我给他示范,他才知道他的身体是该做什么的。他带给我欢愉,但当我凝视他的脸,我知道这对他来说不止是欢愉。 我已经学会了享受欢愉,不问来由。”[1]148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异性恋中,维兰妮取代了男性的位置,占据了主动,成为欲望的主体。她的实用主义观和理智在男性空间中为她争取了更多的权利和空间,她宣称:“我对爱情的态度是实用的,我从男人和女人那里得到快乐,但我从来都不需要一个人来守着我的心。”[1]59凭借这份理性,在异性恋中,她始终掌握着爱与不爱、嫁与不嫁的主动权。在两人的交替叙事中,维兰妮逐渐掌握了主动和话语权,成为了整个文本叙述的中心和焦点,最终维兰妮的故事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她说服亨利一起逃到威尼斯,她让亨利帮她偷回了放在黑桃皇后家里的那颗还在兀自跳动的心,为了维兰妮,亨利杀死了她的前夫而被关押。在故事的发展中,亨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兰妮获取自由。不管是异性恋或是同性恋,对于维兰妮,自由比两者带来的激情更重要。她的结局呈现出开放的形态:“我独自生活。我喜欢这样,虽然我不是每晚都孤身一人,而且我越来越多地往赌场跑。”[1]209在男性经典童话世界里,性、欲望和享乐从来都不是女人的特权,女性总是不断地被“阉割”,成为凝视的客体,失去身体的控制权。但温特森通过多元身体的塑造,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新童话。“身体处在改变这个模式中,总有着变成其他形式的可能。因此,身体能以无数方式来对付规范、超越规范、重塑规范,并向我们展现出,那些我们认为约束着我们的现实实际上都有着变化的可能性。”[6]222维兰妮通过对自己身体的自由支配,摆脱了作为男人的他者角色,重新书写了关于爱、性、婚姻和母亲角色,最终创造了主宰自己身体快乐的女性神话。
酷读《激情》,我们看到亨利和维兰妮的人物塑造都超越了男/女、异性恋/同性恋的对立。温特森不仅是一位擅长描写女同性恋题材,表达女性欲望的作家,更能看到作者通过跨文类实践,对性别身体气质身体进行了颠覆式的书写和塑造,挑战性别身体的界限,并且在文本中重建女性主体意识,将一个看似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文本巧妙地嬗变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新童话,创造出一个激进的女性叙述空间,表达了温特森消解性别身体二元对立的酷儿意识。
[1] 詹尼特·温特森. 激情[M].李玉瑶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2] Helena Grice and Tim Woods,ed.I’mtellingyoustories:JeanetteWintersonandthePoliticsofReading[M].Amsterdam-GA. 1998.
[3] Merja Makinen,TheNovelsofJeanetteWinterson[M].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5.
[4] 朱云霞.试论台湾酷儿小说的身体叙事及跨文类实践[J]. 台湾研究集刊,2012 ,(10).
[5] 朱迪斯· 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6] Lois Tyson. 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赵国新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朱丕智]
Cross-genre Practice and Gender-crossing in Winterson’sThePassion
Luo Wenl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Jeanette Winterson’s novelThePassion, set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Napoleon Bonapante as its historic background, is an exotic fantasy with allogoric and symbolic images.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two apparently opposed genres, the historical and the fantastic, to tell the story that both exposes history as discursive construct and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fantastic discourse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s fluid and multiple desire. Her postmodern rewriting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and the utopia representation of sexual body as queer demonstrate Winterson’s queer desire of crossing the limits of masculine/feminine, heterosexual/homosexual binary opposition.
ThePassion; cross-genre; gender crossing; queer expression
2016-10-19
骆文琳(1968-),女,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及文化研究。
I5
A
1673—0429(2017)02—0035—05